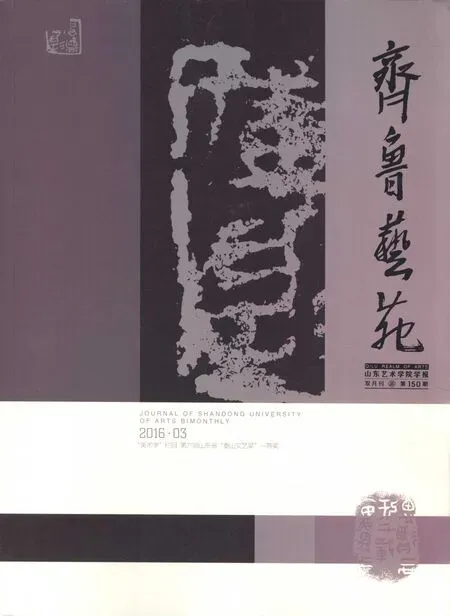艺术、艺术家与社会变迁:基于反法西斯视角的思考
2016-04-08王洪斌
王洪斌
(湖南科技大学艺术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艺术、艺术家与社会变迁:基于反法西斯视角的思考
王洪斌
(湖南科技大学艺术学院,湖南湘潭411201)
社会的变迁影响到艺术家的创作及艺术的发展,反过来,艺术家的创作和艺术的发展又与社会的发展休戚相关,这种艺术、艺术家与社会变迁相互影响的模式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一再出现。法西斯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人为地急剧地改革了社会变迁,在恶劣的社会环境下,世界各地涌现出无数反法西斯艺术家,他们通过各种艺术媒介,谴责、抗争法西斯;战后反战艺术家又不断对法西斯进行反思,守望和平。反法西斯艺术家参与社会变迁的努力,为世界文明进程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这也是对艺术何为所做的一种解答。
艺术;艺术家;社会变迁;反法西斯
一、社会变迁与艺术、艺术家
从艺术的发展史可知,一切艺术的发生和发展都离不开人类社会,经济、科技的发展、政治的变迁、宗教的变革等都对艺术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同样,艺术是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事物,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艺术家通过参与社会、塑造特定的艺术形象来反映和反作用于社会,进而影响社会文明的发展进程,可见,艺术和社会变迁是相互影响和辩证发展的模式。在艺术理论上,艺术是一种远离经济基础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它不直接与经济基础发生联系,主要通过政治、法律、道德等“中间环节”发挥作用。从社会历史的发展来看,政治对于艺术有着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相互的。艺术与政治、社会变迁的关系在20世30-40年代法西斯与反法西斯的较量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长期以来,中外学者、知识分子从军事、经济、法律等领域对反法西斯力量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大量成果,促进了人类对法西斯的认识和反思,对反法西斯力量进行了高度赞扬,但在艺术领域,对反法西斯艺术的研究还较少。
20世纪30-40年代,法西斯及军国主义兴起,极力建立、推行一整套与法西斯及军国主义政权相适应的文化艺术体制,强化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在艺术领域推行艺术为反动政治、强权政治服务,艺术成为法西斯利用的工具,艺术严重政治化、国家化,比如德国纳粹政府在1934年宣称“艺术是为国家主义大众运动服务的”[1](P97),这里的国家主义大众实际上就是法西斯主义。在战争期间,法西斯政府利用绘画、电影、戏剧、音乐等一切艺术手段动员民众参加法西斯战争,扼杀进步力量,美化其反人类的行为,在艺术领域实行专制与独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成立专门的部门,对艺术进行管控与监督,如德国成立了帝国视觉委员会,通过委员会制度来控制艺术家,政治上不可靠、种族不纯的艺术家不能进入委员会,而且不能从事艺术创作。二是对反对法西斯、不符合法西斯利益的艺术家进行迫害和镇压,这在德国纳粹统治时期尤为突出,纳粹政府屠杀了大量犹太艺术家,即使不是犹太人艺术家,只要不顺从纳粹的,也都受到排挤和打击,禁止创作和参加展览,例如德国现代主义设计发源地包豪斯逼迫关闭,大部分包豪斯的师生们转走他国。在日本实行军部审查制度,不符合法西斯统治的艺术作品一律不得发行,违者受到军部的严厉制裁。三是实行怀柔收买政策,通过国家财政等手段给予艺术恩泽,笼络部分艺术家,例如德国就创立了艺术家资助基金,用来资助纳粹艺术的代言人的展览和创作,并且大量购买艺术品。又如日本军国主义通过电影大肆塑造、宣传武士道精神,二战期间,日本的熊谷久虎拍摄制作的《上海陆战队》、田坂具隆拍摄制作的《五个侦察兵》、《土地与士兵》把法西斯塑造成吃苦耐劳、精忠报国、不畏牺牲、充满人情味,进而鼓励民众心甘情愿地参与法西斯侵略战争,为法西斯政府卖命。在法西斯极权统治以及高压艺术政策的管制下,艺术家的创作受到政治的深刻影响,他们不能再为了艺术而艺术,其创作自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束缚。面对社会政治深刻、极端的变化,艺术家何为?不同的艺术家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一部分艺术家为了在乱世能够生存下来或者为了自己的艺术事业,选择向法西斯政权低头,艺术创作不得不符合法西斯政权意识形态的需要,艺术成为法西斯政权的工具、附庸和奴婢,艺术家失去了本应有的尊严,他们违背自己的良知,不顾社会正义和道德,生产了一些反动、落后的艺术作品;另一部分艺术家因为法西斯的迫害被迫选择了流亡海外,在国外继续从事反法西斯事业,还有部分艺术家没有选择流亡或者是来不及流亡国外,他们虽然不公开反对法西斯,但也不与法西斯当局合作,他们对法西斯保持沉默和消极抵抗——开始了内心的流亡。
法西斯的极权政策和残酷统治给各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法西斯发动的世界大战,制造了空前惨无人道的杀戮,引发了社会大动荡,部分艺术家见证、经历了因法西斯人祸而起的死亡、饥饿、恐惧,这种经验成为他们创作的重要来源,法西斯的长期暴行也成为各个受害国不能抹去的民族记忆,在二战期间及战后,艺术家们拿起艺术武器,对法西斯的谴责、揭露和反思,对和平的呼唤和守望成为他们艺术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
二、二战期间艺术家与法西斯的抗争
德国著名女版画家凯绥·柯勒惠支是一位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寄以深厚同情的艺术家,她用不同的艺术形式来表现德国社会的贫困、战争的创伤和劳动人民的悲惨,以及被压迫者的反抗,20-30年代完成的《战争》、《死亡》组画是其代表作,画家以女性特有的敏感和母亲的情怀从不同的角度深刻地揭露了战争的残酷以及战争带给人们的无比苦难,表达了反对侵略战争,进而根除战争根源,实现世界大同的理想。由于其激进的艺术观念和进步的创作,引起了纳粹的不满,1933年,纳粹借她参加犹太画家马克思·李伯尔曼的葬礼,指责她是“白色犹太人”,对其进行恐吓、迫害,柯勒惠支被迫辞去普鲁士艺术科学院院士职务,其作品也被禁止在德国展览和出版。法国著名学者、批评现实主义思想家罗曼·罗兰对珂勒惠支推崇备至,称她的作品是现代德国最伟大的诗歌,它照出了穷人与平民的困苦和悲痛。除了视觉艺术家外,音乐家也参与进来,1941年1月,德国著名作曲家梅西安创作了《时间终结的四重唱》,并在冰天雪地的战俘营里进行了演奏;同年当德国法西斯围困列宁格勒时,著名反战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在空袭声中创作了《第七交响曲》,该曲目在前苏联地区受到热烈欢迎,极大地鼓舞了绝境中的军民,仅列宁格勒,从1942年8月首次演出到1944年突围,该曲就演奏了高达300多场。
当然,在极权统治白色恐怖下进行进步的艺术创作,代价是惨烈的,他们不仅没有收入,还经常受到法西斯的恐吓、迫害,一些进步艺术家甚至直接受到法西斯的残酷镇压和屠杀,他们为公平、正义、良知和艺术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例如德国雕塑家库尔特·舒马赫就是其中的一人。他1942年被纳粹处死,在遗言中他说道“艺术家只有置身于社会运动与社会冲突之中,其创作出来的作品才具有普世价值,才会有生命力,才会不朽”[2](P105)。
法西斯点燃的战火遍及世界大部分国家,法西斯战争所带来的社会变迁也影响到了这些国家的艺术家及其创作。著名现代主义艺术家毕加索无论是他的言论还是他的作品都宣称艺术家要在社会变迁中承担推动社会进步的角色,在西班牙内战和纳粹侵略法国期间,他坚定地站在进步势力一边,积极通过艺术参加反法西斯斗争,支持西班牙和法国的抵抗运动,他创作的版画《佛朗哥的梦幻与宣言》表达了对独裁政权的痛恨与谴责。当记者问他对于艺术与政治关系的看法时,他这样回答:“艺术家不断关注世界上发生的激动人心的大事件,并形象地创作出来,绘画是用来进攻、抵御敌人的武器。”[3](P30)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37年4月28日,德国纳粹对西班牙小城格尔尼卡进行疯狂的轰炸,毕加索闻讯创作了立体主义作品《格尔尼卡》,谴责和抗议法西斯对无辜贫民的屠杀与洗劫,表现了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这幅以立体主义、抽象表现主义手法和单纯的黑白灰三色组成的画面,给人以深沉的艺术震撼力[4](P315),画面中因轰炸惊恐跳楼的妇女,抱着死去婴儿的女人,握着断剑躺在地上的士兵,嘶叫的马匹显示了战争的残酷和给人类带来的伤害,而公牛则象征法西斯的凶残和罪恶。1937年,在纽约举办西班牙共和绘画展时,毕加索写道:“现在发生在西班牙的战争,是一场反人民、反自由的反动战争,作为画家,我的一生都在不断与反动和艺术消亡做斗争……格尔尼卡和近期的作品都清晰地表明了我对这场让西班牙陷入痛苦与死亡海洋的战争的深恶痛绝”[5](P31)。
在中国,日本军国主义早在1931年就开始侵略中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随后染指华北广大地区,1937年,更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试图将中国变成日本的殖民地,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时刻,艺术家们也纷纷行动起来,积极投身抗日,创作了大量形象生动、富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宣传抗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挽救民族危亡。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开始到30年代,鲁迅将珂勒惠支等外国进步版画艺术家的作品介绍到中国,掀起新木刻运动,在中国主张为大众而艺术的美术思潮,发挥艺术作为革命斗争武器的功能,吸引了大批青年艺术家参与。抗日战争爆发后,这些曾经参与新木刻运动的艺术家拿起刻刀,投入到火红的抗日救亡运动之中,一大批青年艺术家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从事抗日宣传。如胡一川创作的《血战卢沟桥》、《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艾炎创作的《火烧阳明堡机场》、《平型关大捷》等都是十分优秀的抗日木刻作品。1942年,毛泽东召开文艺座谈会之后,要求艺术家深入抗日前线、抗日民众生活,涌现出了古元、彦涵、李桦、力群、朱宣咸、夏风、郭钧、石鲁、罗工柳等众多木刻艺术家,他们创作了更多有思想性、艺术性的抗日作品,由于木刻所需材料能就地取材,相对于油画、国画等画种,材料更易得,可以说在抗日根据地,木刻成为当时最有效的抗日宣传工具和艺术媒介。当然,除了木刻画以外,当时也创作了大量其他媒介的抗日艺术作品,如唐一禾在1940年以抗日为题材创作了《七七号角》,采用象征主义和写实主义的表现手法,表现一群青年学生,奔赴抗战前线,为了抗战,他们抛弃了学业,告别了家乡亲人,迈着大步行进的姿态,表明了抗战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心。再如我国当代革命现实主义画家王式廓创作了大量巨幅抗日宣传画,像《总动员》、《保卫家乡》、《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敌》、《再上前线》、《台儿庄大捷》等等。
同样,在音乐领域,这一时期大量优秀的抗战音乐被创作、流传,据不完全统计,从1931年到1945年,在中国创作了上万首抗战歌曲,其中一些歌曲成为了经典之作,到现在仍然被广为传唱。东北沦陷后,作曲家张寒晖耳闻目睹了东北军民的流亡,创作了《松花江上》,诉说对东北故土和亲人的思念,引起了广大东北军民的共鸣,打回东北老家成为广大东北军民的口号,激发了东北军民的抗日热情。著名音乐家、作曲家冼星海根据光未然所作词创作了《黄河大合唱》,该歌曲歌颂了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精神,痛诉日本军国主义残暴和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成为鼓舞中国人民抗日的号角,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可战胜的力量。
三、二战后对法西斯的反思与对和平的呼唤
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围剿下,法西斯政权终于倒台,战争也宣告结束。但战争给世界人民带来的苦难和悲惨,给人类带来的恐惧和罪恶,给世界各民族心灵的创伤和记忆在很短时间内难以抹去,一些经历过二战的艺术家,继续拿起艺术这个武器,对法西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表达了人类要远离战争、珍惜、热爱和平的愿望。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法西斯战争不仅给东南亚各国带来了无穷的伤害,而且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长久的痛苦,大战中300多万日本人被征入伍,为效忠天皇、为法西斯丧命,在反法西斯的最后关头,美国向日本本土投放了当时最新研制的武器——原子弹,给广岛和长崎带来了灾难性的打击,核爆给幸存者留下了长久的阴影。日本画家丸木位里(1901—1995)和丸木俊夫妇创作了系列的反战作品,其中《原子弹爆炸图》就是对该事件进行的反思,1950年,丸木夫妇的另一件作品《幽灵》表现了由日本法西斯战争所引发的核打击给日本人民带来的悲惨和苦难的深重,警示世人要珍惜和平。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但战后日本右翼份子试图否定其侵略行为,为其侵略进行辩护、美化,引起了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众多爱好和平人士的反对、愤怒。其中,特别是围绕南京大屠杀、细菌战、慰安妇等问题,日本右翼分子一直矢口否认、辩解,不断挑衅受害国的心理底线,遭到中国、韩国、朝鲜等各国人民的抗议和声讨,有良知的日本学者和政界人士早就对此表示认罪、悔罪。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反对战争,抵制不公正,伸张正义,揭露日本法西斯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丸木夫妇创作了《南京大屠杀图》,虽然遭受本国保守势力的重重阻扰,但作品最后得以展出,受到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特别是中国人民的欢迎,也表明深受法西斯之害的日本人民也是痛恨战争、热爱和平的。
毕伽索为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毕生的努力,不仅在战时创作大量反战作品,二战后,毕加索又积极参加倡导和平运动,我们今天看到的和平鸽这一表征世界和平的形象就和毕加索有关。*1940年,希特勒攻占法国,一个毕加索的老邻居的孙子被法西斯杀死,并且把他养的鸽子刺死,老邻居请求毕加索给他画一只鸽子,以纪念惨遭法西斯杀害的可怜孙子,毕加索内心悲愤,一边安慰老人,一边提笔就画出一只飞翔的鸽子,成为日后《和平鸽》的雏形。1949年,法国共产党在巴黎召开世界和平大会,毕加索以石版画《和平鸽》作为共产党的宣传画。那个头上有一飞鸽的美丽少女形象,被大量翻印发行到世界各地。1950年,毕加索又为世界和平大会创作了一只衔着橄榄枝的鸽子又名《和平鸽》,作为世界和平大会的宣传画,当时,智利著名的诗人聂鲁达,把这只希望之鸽叫做《和平鸽》,从此,鸽子才正式被世人公认为和平的象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欧洲艺术界兴起了新现实主义运动,新现实主义是反法西斯运动的产物,参加这个运动的艺术家大都是反法西斯战争中有经验的革命政党成员,他们描绘战争灾难和人民的悲惨以及反法西斯战士的艰难困苦与斗志,后来又为社会进步和自由呐喊,在法国以画家弗兰西斯·格鲁贝尔和贝那尔·毕费为代表。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更是震撼了世人,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刚刚结束不久,由K.阿米台依、F.费里尼等编剧,罗伯托·罗西里尼导演的电影《罗马,不设防的城市》真实地反映了在法西斯统治时期,意大利人民的生活,以及意大利民众空前团结与法西斯进行斗争。导演把演出场地搬到战争瘢痕累累的大街上,在实景中拍摄,产生了强烈的真实感,影片中的演员大部分是非职业演员,都亲身经历了这场战争,对战争有着深刻的体验,从而更加真实地还原了历史,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战后的中国,出现了大量的反日本军国主义的爱国作品,如韩景生1947年根据他在哈尔滨机场废墟实地写生创作的,描绘抗战后期被侵华日军炸毁的哈尔滨机场废墟的画面再现了衰败、荒凉、残墙破壁的机场,揭露和控诉了侵华日军罪行。此外,许江、孙景刚、杨奇瑞、崔小冬,邬大勇等创作的《1937.12.南京》,杨克山、崔开玺创作的《七七事变-卢沟桥 》都是类似的作品。除了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侵略行径外,大部分作品高度赞扬了中华儿女奋勇抗击日寇、保家卫国的精神,如姚尔畅的《淞沪抗战》。对法西斯的反思、批判、谴责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和平,警惕法西斯势力和法西斯思想抬头,2002中国著名作曲家赵季平受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之邀,创作了纪念音乐《和平颂》,既是对日本军国主义暴行的控诉,更是对和平的呼唤。
四、结语
艺术家首先是社会的存在,是社会的人,艺术家不可能脱离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环境,他们的日常生活、艺术体验和艺术创作必然受到现实中的社会制度、文化环境等诸多制约。在法西斯极权统治下,艺术家的创作活动受到前所未有的人为压制和束缚,大力推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文化艺术政策,扶持为法西斯服务的艺术家,压迫甚至屠杀反法西斯艺术家。急剧的社会变迁和政治的异化,导致了艺术家及其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些艺术家被法西斯所控制、利用,艺术成为宣传法西斯、蛊惑民众的工具;另外一些艺术家开始了内心的流亡,他们不认可法西斯的所作所为,但也不公开反对法西斯,不参与法西斯活动;但更多的艺术家吹响了反抗法西斯的号角,通过绘画、音乐、电影等各种艺术媒介反对法西斯,揭露法西斯的暴行,号召大众团结起来,打倒法西斯独裁统治。为法西斯唱赞歌的艺术家虽然在战时享受到良好的物质生活和待遇,但他们受到道德的谴责和良心的拷问,被正义的大众所鄙视;内心流亡的艺术家受法西斯强权的压制,长期被排斥在主流艺术领域,没有展览、没有收入,生活艰苦,甚至不得不放弃自己挚爱的艺术事业追求,他们其实也是可敬的,至少是值得理解和同情的。反法西斯艺术家是最令人钦佩的,他们富有战斗力和勇气,他们不顾自己的安危,在严酷的环境下创作了大量优秀的反法西斯艺术作品。
艺术家通过自己的创作,影响了社会的发展变化。堕落的作品麻痹了人民的思想精神,这种艺术为邪恶辩解,为极权服务,而优秀的艺术作品鞭挞丑恶,鼓舞人心。在法西斯统治期间,大量的反法西斯艺术作品对强权者、反动势力的暴行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唤醒了正义力量,教育、团结、鼓舞了大众,成为了打击法西斯、消灭法西斯的有力武器。二战后,反法西斯艺术作品的内涵进一步深化,外延进一步拓展,不再仅仅局限于对法西斯的猛烈批判,对法西斯国家的普通人民也给予了同情,他们也是法西斯的受害者。艺术作品让人们清醒的认识到,只有遏制法西斯思想重新抬头,历史才不会重演,悲剧才不会再次发生。在和平年代,艺术家通过反法西斯艺术作品来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埋下民族复仇的种子,而是为了不再重蹈覆辙,更是为了世界更持久的和平与繁荣。艺术何为?艺术家何为?反法西斯视角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注解。
[1]Glenn Cuomo. National Socialist Cultural Policy,Basingstocke,Hampshire,Micmillan Press,1995.
[2]Brandon Taylor and W. Van der Will. The Nazification of Art: Art, Design, Music, Architecture and Film in the Third Reich,Winchester,Hampshire:Winchester Press,1990.
[3][5]柯提斯·卡特.艺术与社会变迁:国际美学年刊[M].许中云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4]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外国美术史教研室编.外国美术简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杜娟)
10.3969/j.issn.1002-2236.2016.03.024
2015-12-20
王洪斌,男,博士,湖南科技大学艺术学院讲师。
J0-02
A
1002-2236(2016)03-012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