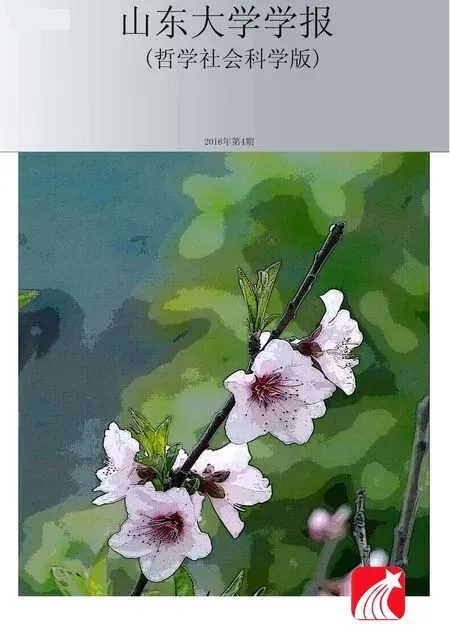孔子“无为而治”政治思想及其国家治理价值
2016-04-05高连福
高连福
孔子“无为而治”政治思想及其国家治理价值
高连福
就现有文献来看,孔子首次明确提出了“无为而治”的思想。与老子的“绝仁弃义”而“复归于朴”的“自然”之“无为”不同,孔子“无为而治”的中心意趣在于为政者以其德化人,因而是“德化”的“无为”。人所皆具的德性之“仁”是孔子“无为而治”思想的人性基础和内在根据。正己化人和举贤任能是达于“无为而治”的现实路径。德是为政之基、惟有德者方可执政是孔子“无为而治”启示给后人的重要政治思想遗产。
孔子; 无为而治; 以德化人
提起“无为而治”,人们总是自然而然地把它归属于老子,视之为老子思想之所以自成一家之言的标志性观念,或以老子为创始人的道家所独具的政治理念。其实,这是一种误读。就现有文献来看,首次明确提出“无为而治”思想的恰恰是儒家的创始人孔子,至少可以说,孔子是最早以文字形式完整表述出“无为而治”这一思想的人。并且,这一完整表述就首见于辑孔子之言最为集中,因而是研究孔子思想最重要的典籍《论语》之中。《论语·卫灵公》篇载:“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朱熹:《四书集注》,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第236页。。因此,“无为而治”作为孔子思想中不可轻忽的一维,理应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本文拟从孔子“无为而治”的中心意趣、内在根据(可能性)、实现路径(现实性)等方面探讨其所独具的思想意蕴,并求教于先辈同仁。
一、“无为而治”的中心意趣
理会“无为而治”,关键在于从思想上松开“无为就是不为或无所作为”的束缚,一如“白马非马”不可径直理解为“白马不是马”一样。从上述所引,可以看出,孔子在称赞舜“无为而治”时,紧承其后便以“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对其作了明确的注解。“夫何为哉”一语表明“无为”并非不为,而是有所为。这所为不是别的,只是“恭己正南面”,且以“而已矣”三字决之,明“恭己正南面”之外,别无所为也。因此,循着“恭己正南面”这一注解去解读孔子所称述的“无为而治”似更贴近其本意,并由此得其意趣、明其旨归。这一注解明示的是,孔子把其所标举的“无为而治”归本于为政者的“恭己正南面”;或者径直说,“恭己正南面”就是“无为而治”,“无为而治”就需“恭己正南面”,二者相辅相成、相互印证。因为在孔子看来,为政者“恭己正南面”而身正,便可自然而然地达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朱熹:《四书集注》,第210页。之“无为而治”之境。因此,把握了“恭己正南面”之义涵,亦即可心领神会于“无为而治”之中心意趣。所谓“南面”,指称的是面南而坐,可指称天子、诸侯的听治理政之位,亦即为政。孔子曾称位列“德行”科的仲弓“可使南面”。“正南面”,就是端正地面南而坐,正直地为政,即孔子所称的“君君、臣臣”。“君君、臣臣”的意涵是君尽君之道而止于仁,臣尽臣之道而止于敬。进而言之,为政的正直与否以及正直到何种程度,根本上端赖于一个人的德性修为,即为政者的“恭己”。何谓“恭己”?程树德《论语集释》曰:“恭己者,修德于己也”*程树德:《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063页。。可见,“恭己正南面”就是在位者恭敬地修德于己,以己身之德作为为政的根本,正直地去为政,所谓“政者,正也”*朱熹:《四书集注》,第199页。。如是为政,为政者便可以己身之德通于天下之人,正己而正人、正人而正天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班固:《汉书》,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503页。,达于孔子所言的“子帅以政,孰敢不正”*朱熹:《四书集注》,第199页。,以及孟子所谓的“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朱熹:《四书集注》,第409页。,“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朱熹:《四书集注》,第49页。,实现人皆具德、“天下归仁”、“君子笃恭而天下平”*朱熹:《四书集注》,第56页。的“无为而治”。“恭己正南面”表达的是孔子把为政者的“仁”德修养视为“无为而治”的根本前提,或者说,“无为而治”只是为政者“恭己”这一德性修养的直接推扩,即《大学》所云的“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朱熹:《四书集注》,第6页。。故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朱熹:《四书集注》,第399页。。这样,为政就不再以向外的治人、治事为能务,而是重点落在了为政者自身的“心正”上,归本于为政者的修己治己上,亦即要求为政者“以修身为本”,修养仁德、涵厚仁德,把仁德的修养作为为政的首要和根基。由此可断定,孔子所心仪的“无为而治”凸显和彰明的终究在于为政者自身的修德正己。单凭这一点,孔子所称述的“无为而治”就与老子的“绝圣弃智”、“绝仁弃义”,因而弃绝人的任何德性修为的努力而听任“自然”的“无为而治”区别开来。也就是说,老子的“无为而治”是超然于人所当有的德性修养和人的任何作为的,而孔子的“无为而治”却须臾离不开为政者的正心修身,或者说,孔子的“无为而治”根本上端赖于为政者自身的德性修养。
“无为而治”既然是“恭己正南面”,其所重在于为政者自身的修德正己,这一命意倘用孔子的另一命题来概述即是“为政以德”。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朱熹:《四书集注》,第75页。。所谓“为政以德”,并不就是俗常意味上的道德说教。因为俗常的道德说教只是对人民的道德要求,却与为政者自身的道德教养无关,或者说,只是专责望他人修养道德而唯独不要求自己修德的一种“求诸人”而不“求诸己”、因而治人而不治己的为政方式。与之相反,为政以德,依朱熹之见,只如为政有德相似,只是以德为本,“德之为言得也,得于心而不失也”*朱熹:《四书集注》,第75页。,“凡人作好事,若只做得一件两件,亦只是勉强,非是有得。所谓‘得’者,谓其行之熟,而心安于此也。如此去为政,自是人服”*黎靖德:《朱子语类》,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36页。,“‘为政以德’,非是不用刑罚号令,但以德先之耳”*黎靖德:《朱子语类》,第534页。。据此,为政以德指称的显然是为政者把要求于人民的道德,首先要求于自己,使自己先有是“德”,即“君子求诸己”,“躬自厚”而以身先之,“如纲常伦理,先自家体备于身,然后敷教以化导天下;纲纪法度,先自家持守于上,然后立法以整齐天下,这才是以德而为政”*陈生玺主编:《张居正讲评〈论语〉》,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第13页。。这表明,修德便是为政,即人之有德,发之于政,便是为政;而以德先之,则政皆是德,因此,德与政非两事,只是一事而已。这可以从孔子的一段话得到确切的理解:“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朱熹:《四书集注》,第83页。在孔子看来,把以“孝”、“弟”等为务的教化施用于政治,也就是“为政”了。因此,孔子“为政以德”思想的重心不在于以德“治民”而在于以德“治官”,即要求为政者“未为政前先有是德”,因而以修身为首要,正心诚意、修德于己。如此为政,为政者无须在政治事务上多所经营,只须“恭己”——恭敬地修德于己,便可以己德表率天下、化导天下,带动人皆由“为仁”而修德立身,达于“天下归仁”。这是一种先觉觉后觉、后觉效先觉而“明明德”的为政方式,此即孔子所称述的“无为而治”。这表明,在孔子这里,“无为而治”的首要前提在于为政者有其德,“无为而治”的实质则是“为政以德”,或者说,“为政以德”的极致境地或理想境地便是“无为而治”。可见,孔子所称述的“无为而治”乃是一种以德治官的“德治”,或者说,以德治官的“德治”是孔子“无为而治”成其为“无为而治”的透底之论。
“无为而治”的命意既然归重于为政者的“恭己正南面”,其实质在于“德治”,因此历来注家多本“德”或以“德治”来理会孔子的“无为而治”。何晏《论语集解》集包咸注:“德者无为,犹北辰之不移而众星共之”*引自程树德:《论语集释》,第64页。。李允升《四书证疑》云:“既曰为政,非无为也。政皆本于德,有为如无为也”;“为政以德,则本仁以育万物,本义以正万民,本中和以制礼乐,亦实有宰制,非漠然无为也”*引自刘宝楠:《论语正义》,高流水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39页。。朱熹《论语集注》承其旨而倡其义,曰:“为政以德,则无为而天下归之”,并引“程子曰:‘为政以德,然后无为’。范氏曰:‘为政以德,则不动而化,不言而信,无为而成’”*朱熹:《四书集注》,第75页。。“无为而治者,圣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为也。……恭己者,圣人敬德之容。既无所为,则人之所见如此而已”*朱熹:《四书集注》,第236页。,并对“为政以德”及其与“无为而治”的关系作了系统的阐发。在朱熹看来,“‘为政以德’,不是欲以德去为政,亦不是块然全无所作为,但德修于己而人自感化。然感化不在政事上,却在德上。盖政者,所以正人之不正,岂无所作为。但人所以归往,乃以其德耳。故不待作为,而天下归之,如众星之拱北极也。”“为政以德者,不是把德去为政,是自家有这德,人自归仰,如众星拱北辰”*黎靖德:《朱子语类》,1986年,第533、534页。。而为政以德,如何无为?朱熹认为“所谓无为……但是我有是德而彼自服,不待去用力教他来服耳”*黎靖德:《朱子语类》,第536页。。“圣人所谓无为者,未尝不为,依旧是‘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是‘己正而物正’,‘笃恭而天下平’也。”“圣人不是全无一事。如舜做许多事,岂是无事。但民心归向处,只在德上,却不在事上。许多事都从德上出。若无德而徒去事上理会,劳其心志,只是不服。”“圣人合做处,也只得做,如何不做得。只是不生事扰民,但为德而民自归之。非是说行此德,便要民归我。……但圣人行德于上,而民自归之,非有心欲民之服也。”“子善问‘为政以德,然后无为’。曰:‘此不是全然不为。但以德则自然感化,不见其有为之迹耳’”*黎靖德:《朱子语类》,第537页。。
这些注解所明示的意趣,主要在于:(1)“政皆本于德”,凸显了为政的根本终究在于“德”,在于为政者德性的自律性提升,亦即政治以为政者自身的德性为基点,从而督勉为政者须自觉修身以涵养“仁”德。故《大学》云:“是故君子先慎乎德。……德者本也”*朱熹:《四书集注》,第17页。。(2)“德者无为”,强调了“为政以德”对于“无为而治”的必要成全,或者说“为政以德”是“无为而治”的不二法门,从而以一个应然的标准衡量并督导为政者的实际所行。换言之,“无为而治”既为现实中的“为政”提供了一种应然的价值导向或极致状态的范本,也贞定了“为政”的价值衡准,以衡量现实中的“为政”是否或何等程度上趋近“无为而治”。(3)阐明了“为政以德”不是“以德去为政”,而是“德修于己而人自感化”、“自家有这德,人自归仰”,从而使政治归于教化,成为引领民心归向、化育民心归于仁德的政治,成为为政者正己以化人的政治。如是,“无为而治”的中心意趣就在于以德化人,引领人人皆以正心修身、立德成人为务,借用《大学》之言,即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朱熹:《四书集注》,第7页。。这样,就把政治的价值系于人本身,以人为政治的价值旨归,即为政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化人、育人、教化人心,引领人人皆具其德,达于天下归仁,而非纯为政治而政治。换言之,孔子的“无为而治”确立了政治是为人而存在、人不是为政治而存在的政治理念,从而拒斥了那种诸侯争霸而把人民作为政治工具、实现富国强兵目的的政治治理方式。借用荀子之言,就是“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方勇、李波译注:《荀子》,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53页。。这无疑是人类政治思想的一大转折点,对于扭转当时的政治方向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基于此,徐复观评价说:“孔子在政治上的无为思想,极其究,乃是要以教育代替政治,以教育解消政治的思想。这是德治最主要的内容”*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192页。。萧公权更是一语中的地指出,孔子“认定政治之主要工作乃在化人。非以治人、更非治事。故政治与教育同功,君长与师傅共职。……政治社会之本身实不异一培养人格之伟大组织。《尚书·泰誓》谓‘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君师以德化人”*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一)》,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第62页。。可见,孔子“无为而治”的中心意趣在于“以德化人”,亦即通过“以德化人”的方式治国理民,“使政治不应当再是压迫人民的工具,而只能成为帮助一般人民得到教养的福利机构”*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第58页。,让人人皆化育为有德之人,从而达于“天下归仁”(天下之人心归于“仁”德)、“天下有道”(天下之人心中有“仁”道)。
由此观之,与老子的“无为而治”以“致虚极,守静笃”、“复归于朴”为宗趣,因而是“自然”的“无为”迥异其趣的是,孔子的“无为而治”则以为政者修德正己为根本、以德化人为旨归,因而是“德化”的“无为”。概言之,“以德化人”而天下之人归心、心归于“仁”德乃孔子“无为而治”的中心意趣所在。
二、“无为而治”的内在根据
现在须进一步追问,“无为而治”的根据何在?或者说,孔子有何根据认定“恭己正南面”就可达到“无为而治”呢?这是关涉“无为而治”何以可能的根基性问题,孔子必然会对此作出回答。
由上述可知,“无为而治”可归宗于以德化人。既然是以德化人,那么无论是能化之人还是所化之人,都必然自身生命中有是“德”,为政者方才可以修一己之德而自正正人、自化化人,庶民百姓方才会如草随风而为德所化,化归于“仁”,达于“天下归仁”。由是,“无为而治”的根据问题也就转换成了确证人自身生命中是否具有此“德”的问题。所谓确证,并非知识性的逻辑求证,而是反躬式的生命体认。而一旦确证人自身生命中具有此“德”,也就意味着“无为而治”具有内在的根据。那么,人自身生命中是否具有此“德”呢?
自孔子视之,人显然具有此“德”,且这“德”并不是由外在于人的要求所强加于人的“德”,而是人人皆具的、发自内在的无限向上之“德”。孔子是以内心之“仁”来明示这人之为人的内在之“德”的。依据《论语》所载:“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朱熹:《四书集注》,第245、86、98页。,并关联着《礼记·中庸》所引孔子之言“仁者人也”*朱熹:《四书集注》,第40页。,以及传承孔子之学的孟子之言“仁也者,人也”、“仁,人心也”*朱熹:《四书集注》,第526、477页。和董仲舒《春秋繁露·仁义法》所谓“仁之为言人也”*董仲舒:《春秋繁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06页。,可证知孔子是径直以“仁”来规定人,且把“仁”视为人之为人的根本,认为人只有存心于“仁”才可成其为人,正如朱熹所言“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朱熹:《四书集注》,第526页。。由是,“仁”则生,生就要“仁”,否则生命就会麻木不仁。正是因为生命中有着那“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之“仁”,人才不失其为人而成其为人。故而,人须臾不可离开“仁”,离开了“仁”,人就无以配享那人之为人的尊号。更何况,“仁”是因着人的践行而成为“仁”,人则因着“仁”的润泽才成为人;这“仁”与人的相即不离而相互成全,明示着“为仁”而涵养“仁”德是每个人终其一生的志业。为此,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引自朱熹:《四书集注》,第150页。鉴于人之为人在于“仁”,“仁”标识着人之为人,“仁”的有无裁判着人是否成其为人,因此,孔子如此垂教世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朱熹:《四书集注》,第238页。。
“杀身以成仁”这所成之“仁”,在孔子看来,并不是外在于人的形上实体,而是内在于每个人自身生命的德性之“仁”。《论语·述而》篇载:“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朱熹:《四书集注》,第143页。。“仁远乎哉”这一设问表明,“仁”并不远离每个人自身,而就在每个人的生命之中,故而隐含着对人的生命中本己地存在着的、内在之“仁”的认可。正是基于对人生命中内在之“仁”的认可,“仁”的求取才不至于有赖于外铄,“我欲仁”才能够“仁至”。假若“仁”并不内在于人,便不可能出现“我欲仁”而“仁至”的随要随有、随求随到、随欲随至的情形。孔子对“仁”内在于人的认可,也可从他所谓“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朱熹:《四书集注》,第191页。的指点和诲示中获得印证。“由己”意味着不由人,因此也意味着由内不由外。因此,这“仁”德的求取只须自致,毋庸外求。由是,孔子称赞伯夷、叔齐是“求仁而得仁”的“贤人”。为此,杜维明指出:“仁毋宁说是一个内在性的原则。这个‘内在性’意味着‘仁’不是一个从外面得到的品质,也不是生物的、社会的或政治力量的产物……‘仁’作为一个内在的道德并不是由于‘礼’的机制从外面造成的。相反,‘仁’是更高层次的概念,它赋予‘礼’以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仁’基本上是与人的自我更生、自我精进和自我完成的过程联系着的”*杜维明:《人性与自我修养》,台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2年,第11-12页。。徐复观则如是断言:“孔子既认定仁乃内在于每一个人的生命之内,则孔子虽未说明仁即是人性,……他实际是认为人性是善的;在孔子,善的究极便是仁,则亦必实际上认定仁是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最根本的规定,亦即认为仁是作为生命根源的人性”*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第87页。。
孔子在以“仁”把握人之为人的同时,也以“仁”喻示他心目中的“道”。《论语·里仁》篇载:“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卫灵公》篇载:“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朱熹:《四书集注》,第101、235页。。这“一以贯之”之“道”是什么呢?依据曾子以“忠恕”解释“夫子之道”和朱熹《论语集注》注解“忠恕”为“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或曰:‘中心为忠,如心为恕’”*朱熹:《四书集注》,第102页。,且无论“尽己之谓忠”的“中心”之“心”,还是“推己之谓恕”的“如心”之“心”,又皆可归宗于孟子所言“仁,人心也”*朱熹:《四书集注》,第477页。,可以推知这“一以贯之”的“道”即是“仁”,离“仁”别无他道。其实,这里即使不去援引曾子所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也可以从孔子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朱熹:《四书集注》,第134页。及《孟子·离娄上》所引“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朱熹:《四书集注》,第398页。,证知“仁”乃是孔子称述其学说宗趣的“一以贯之”之“道”。由此,孔子所谓的“一以贯之”之“道”即是“仁”道,或者说,孔子之“道”是以“仁”为内涵的“道”,“仁”是孔子之“道”成其为“道”的内在规定。《中庸》云“仁者人也”*朱熹:《四书集注》,第40页。,因而“仁”道便是人道,是人之为人所应走的正道、“直道”。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朱熹:《四书集注》,第526页。。因此,孔子之“道”并非先在于人或离人而自在的道,更不是什么logos或所谓客观规律,而是植根于人的内在之“仁”、有待于人在“学以致其道”的践履中予以恢弘而弘大的道。基于此,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朱熹:《四书集注》,第243页。。这“仁”道因着每个人“弘”或“致”的工夫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层级,人便因着这“仁”道在生命中的呈现表现为不同的人格境界。但必须指出的是,“仁”道虽有层级,却无止境。这可以从孔子自谓“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朱熹:《四书集注》,第144页。中获得印证。可见,孔子所志之“道”是一种“依于仁”因而依于人而不外在于人、并有赖于弘道者“弘”或“致”的“道”。孔子之“道”的这一特性,把其所志之“道”从根本上与老子的“法自然”而“复归于朴”的“道”区别开来。也就是说,老子立意中的“道”乃“自然”之道;这“自然”之道高踞于有生命、有性情的个人而超然自足,个人只是以一个样品的身份去见证这“自然”之道;“道”的这种不关涉人的性情和品格的特性,表明不再有个人,而只有作为自然之“道”见证者的样品。因此,老子所立意的“自然”之道只是人所应取法的“道”,却在“道”之为“道”的意义上并不冀望于人的可能“弘道”、因而是与德性人文无关的“道”。孔子之“道”是“仁”道,它植根于人的内在德性之“仁”,因而是有赖于人在切己的修养“仁”德的工夫中去弘大的“道”。
基于对人所皆具的内在德性之“仁”的亲证和信念,孔子坚信为政者通过扩充内在之“仁”正心修身、修德于己,便可以“为政以德”,而为政者“为政以德”自然会起一种上行下效的表率作用,即“道之以德”,带动并引领人们“皆以修身为本”,由是以德化人,人人皆徙义迁善、扩充自身的内在德性之“仁”,同归于德,这样就可以行仁践道,参赞化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朱熹:《四书集注》,第131页。,成己成人成物,建立人间良善的社会秩序,达于天下归仁、天下有道,实现“无为而治”。可见,孔子的“无为而治”是根源于人所皆具的内在德性之“仁”而参赞化育的无为。因此,孔子“无为而治”的根据就在于这人人皆具的内在德性之“仁”,人所皆具的德性之“仁”是孔子“无为而治”的深厚坚实的人性基础和内在根据。
三、“无为而治”的实现路径
政治不仅关涉民之生计,更关涉民之道德、民之风尚,涉及人心归向和风化淳厚,正如萧公权所言:“国家之目的不仅在人民有充裕之衣食,而在其有美善之品性与行为”*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一)》,第61页。。两者相比,孔子所重显然在于后者。无疑,人最不堪忍受的是没有尊严的生活。物质生活的贫乏,不过使人饥渴困苦,害及其身而已;道德尊严的丧失,则是人之根本的丧失,纵有此身,亦无以自立。基于此,孔子如此再三诲示:“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朱熹:《四书集注》,第245、195、238页。。众所周知,行政的规律是上行下效,正如《孔子家语》所言:“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是故人君先立仁于己。”“君上者,民之仪也;有司执政者,民之表也”*廖名春、邹新明校点:《孔子家语》,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5-6、60-61页。。故《左传》云:“上之所为,民之归也”*左丘明:《左传》,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第216页。。基于此,孔子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朱熹:《四书集注》,第207页。;孟子云:“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朱熹:《四书集注》,第409页。。因此,人间的良善与否、社会的清正与否取决于为政者自身的德行修为,取决于为政者的自正其行、以身作则。这也就决定了为政者须“为政以德”、“无为而治”。《论语》载:“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朱熹:《四书集注》,第205页。。“先有司”指的是为政者率先垂范,“举贤才”指的是任官得人。《荀子·成相》篇云:“尚贤推德天下治”*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407页。。可见,实现“无为而治”,一须正己化人,二须举贤任能。自孔子视之,二者兼举并行而无遗,则天下有道可期、人间良善可待。
第一,正己化人。天下有道、天下归仁从根本处讲,实为政治的有道。政治的有道首先是为政者自身的有道,即为政者有其德,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朱熹:《四书集注》,第40页。。这便是为政者须自正其身,化“人爵”(公、卿、大夫)意义上的“君子”为“天爵”(仁、义、忠、信)意义上的“君子”。由此,孔子在谈及政治问题时,无不认为政治问题的发生,根源皆出在为政者自身的不正——德行不端、举止不正,因而,他从未把当时所出现的政治、社会问题,归咎到人民身上,而总是直言规谏人君及卿大夫要以身先之,率之以正。这便有了孔子从为政者必得“正其身”的理路而得出的正人先正己的政治主张。孔子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朱熹:《四书集注》,第210、208页。。因此,当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时,孔子便以“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朱熹:《四书集注》,第199页。对答。以“正”论“政”,这“正”,孔子显然是指为政者自身的心正、身正。这是要为政者正之以“仁”,只有为政者“为仁”而涵养“仁”德,自正其身,才可以正人、正天下,从而达于“天下归仁”、“天下有道”。以孔子之见,历史上从未有过己不正而能正人者,也从未有过为政者自身不正而能天下有道者。故而,天下无道,责任全在为政者“上失其道”,而不在百姓无其道。所以,当季康子因患盗而向孔子寻谋止盗的方法时,孔子非但没有为他就如何以高压态势防盗、如何制定严格的法律惩戒盗贼从而使人不敢盗、不能盗等方面出谋划策,而是把问题的发生引向季康子自身,警示他须从自身找原因、寻症结,切己反求,使“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刘安:《淮南子》,高诱注,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333页。,以自正其身,正己而正人,由此,他只是答之以“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朱熹:《四书集注》,第199页。。而当季康子以“如杀无道,以就有道”问政于孔子时,孔子径直以“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朱熹:《四书集注》,第199-200页。作答而“明其化”,因为“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朱熹:《四书集注》,第363页。,故“君能为善,则吏必能为善矣;吏能为善,则民必能为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吏之罪也;吏之不善也,君之过也”*贾谊:《新书校注》,阎振益、钟夏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41页。。“子欲善,而民善”的作答,无疑是在督勉天下所有的为政者只须从自身做起,向善而迁,修德正己,便自可“道之以德”而为民众昭示一种供仿效的范本,引领民众趋善“以就有道”。
显然,孔子是不赞成用杀戮的手段治国理政的。在他看来,“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只会使百姓因惧怕刑罚而不敢为恶,或者只是心存侥幸地设法避免刑罚而变得不再有羞耻感,反之,“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百姓自会感化于为政者的德行而知耻向善。由此,他这样说:“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朱熹:《四书集注》,第209、210、147页。。这“善人”、“王者”、“君子”无疑是就为政者所具有的德行修养而言。这便是孟子所言的“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朱熹:《四书集注》,第395页。。为政者有其德,就必然会以自己的德行感化于人,化人以自觉向善而归于德。孔子之所以认为为政者的德行修养可以导人以自化,乃出于他对人的信赖、对人性向善的信赖、对人心向化的信赖。正是基于这种信赖,在《孔子家语》中,他如此策勉为政者:“上敬老则下益孝,上尊齿则下益悌,上乐施则下益宽,上亲贤则下择友,上好德则下不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廉让则下耻节,此之谓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定,则本正也。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是故人君先立仁于己”*廖名春、邹新明校点:《孔子家语》,第5-6页。。如是,为政者恭敬己身、修德于己,便可“为政以德”;而“为政以德”则自然上行下效,化人于善;而化人于善,则天下归仁,人成其人;而人成其人,人皆具德,则“无为之治”必成。诚如萧公权所言:“故自孔子视之,修身以正人,实为事至简,收效至速,成功至伟之治术。苟能用之,则‘不令而行’,‘无为而治’。政平刑措,指日可期。天下归仁之理想,于此可以实现”*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一)》,第62页。。
第二,举贤任能。既然“无为而治”是以德化人,而“德化”的首要前提在于有德者有其位,并且“为政以德”就是用有德之人去为政,或为政而用有德之人。这就须举贤任能。故而,前人又多以“任官得人”注解“无为而治”,可谓得其要也。如:何晏《论语集解》注为“言任官得其人,故无为而治”*引自程树德:《论语集释》,第1063页。。《三国志·吴书·楼玄传》引孔子“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恭己正南面而已”之后而申之以“言所任得其人,故优游而自逸也”*陈寿:《三国志》,陈乃乾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455页。。朱熹《论语集注》注为:“无为而治者,圣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为也。独称舜者,绍尧之后,而又得人以任众职,故尤不见其有为之迹也”*朱熹:《四书集注》,第236页。。《孔子家语·辩政》载孔子言曰:“昔尧舜听天下,务求贤以自辅。夫贤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廖名春、邹新明校点:《孔子家语》第171页。。
自孔子视之,舜之所以能够“无为而治”,除“恭己正南面”外,关键还在于他能够举贤任能。据《论语·泰伯》记载:“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朱熹《论语集注》注曰:“五人,禹、稷、契、皋陶、伯益”*朱熹:《四书集注》,第154页。。《论语·颜渊》记载子夏之言,曰:“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朱熹:《四书集注》,第201-202页。。所谓“不仁者远矣”,非不仁者皆远离皋陶而去,乃是不仁者感化于皋陶的仁德之行,而有耻且格,化而为仁,故而不见不仁者矣。它诉说的是“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朱熹:《四书集注》,第201页。的选用品格正直之人而为政的用人智慧:用人是一种引导,用人以“直”即是用人以“德”,亦即对无论所用者还是那些因“枉”而被弃之不用的人,以及意欲出仕而为政的人和天下所有人,都“道之以德”。它体现出的依然是“以德化人”这一“无为而治”的根本旨趣。除《论语》外,其他典籍也申言了舜的举贤任能以成“无为而治”。《大戴礼记·主言》篇载孔子言曰:“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方向东:《大戴礼记汇校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0页。。《汉书》载董仲舒在《贤良对策》中曰:“舜……即天子之位,以禹为相,因尧之辅佐,继其统业,是以垂拱无为而天下治”*班固:《汉书》,第2509页。。刘向《新序·杂事四》篇亦载:“王者劳于求人,佚于得贤。舜举众贤在位,垂衣裳恭己无为而天下治”*刘向:《新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52页。。王充在《论衡·自然》篇则径直以“任贤使能”称述“无为而治”,云:“舜、禹承安继治,任贤使能,恭己无为,而天下治”*王允:《论衡校注》,张宗祥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68页。。这表明,举贤任能乃达成“无为而治”的另一必然不可或缺的实现路径。
必须指出的是,孔子虽然注重举贤任能,但绝不意味着举贤任能是“无为而治”所以成其为“无为而治”的根本规定。这不仅因为,举贤任能就其旨归而言,终在于所举之人能够以德化人,而且因为,举贤任能就其所依据的标准而言,仍在于据德而举贤任能,而非惟才是用。更何况,孔子本人在对答鲁哀公的“何为则民服”的垂问时,就对如何举用人的问题提出过“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朱熹:《四书集注》,第82页。的主张。“直”或“枉”显然是出于对所举之人的“德”或德行的判断,而民的“服”与“不服”也终究在于对所举之人的“德”的服与不服。因此,所谓民服乃在于服其“德”,而服民则当以“德”服之。惟有以“德”服人,人才能心悦而诚服,实现以德化人。据此,举人就在于举用有德之人,使有德者有其位,一如孟子所言“惟仁者宜在高位”*朱熹:《四书集注》,第395页。。可见,相较于举贤任能而言,正心修身、修德于己才是为政者得以“无为而治”的最终依据所在。正是在此种意义上,孔子才再三致意人们:“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朱熹:《四书集注》,第229、159页。。是以,《荀子·王霸》篇云:“论德使能而官施之者,圣王之道也,儒之所谨守也”*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173页。。因此,无论是正己化人,还是举贤任能,贯穿其中的命意乃是为政者自身的德行修为,或者说,为政者自身的仁德修为是二者一以贯之的中枢所在。
四、“无为而治”之于国家治理的价值
孔子“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以为政者的“仁”德修养作为治国理政的根本和保障,表达的是一种“为政以德”、“惟仁者宜在高位”*朱熹:《四书集注》,第395页。的政治追求,诉说的是一种政治的理想状态或极致境地。它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虽难以完全企及,但作为一种政治理想,则具有可践履、可实践的普遍性:第一,它总能激励现实政治中那些觉悟到这一点并愿意“以德化人”的为政者向着这一状态努力而为、尽力而趋,不同程度地实现着“无为而治”,从而把现实的政治引向相对美好的境地;第二,它提供了一个应然的政治标准,以衡量处在不同政治地位的为政者的实际所行,从而劝诫或督责为政者自身修养仁德,提升德行,更好地以“其身正,不令而行”、“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朱熹:《四书集注》,第208、199页。的德行教化引导人;第三,它总能吸引有志于为政之人首先以修身为本,尽心力于自身仁德的修养,因而具有正能量的导向作用,如在自两汉以来的乡举里选的政治实践中,一贯相沿以人品行谊为准,把“孝廉”、“孝弟”、“贤良”、“方正”、“敦厚”、“逊让”、“忠恪”、“信义”等作为用人之目。因此,孔子“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决不是托之空言的乌托邦,而是有志于此的为政者“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朱熹:《四书集注》,第150页。之躬行不懈、孜孜以求的政治理想。
孔子“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以为政者的“仁”德修养作为治国理政的根本,垂示着后人:治国必先治吏,治吏重在加强官德建设;惟为政者德高望重,在道德上率先垂范,执政才有分量,治国理政才能风清气正,从而收到“不令而行”、“不劳而治”的功效;而缺德、无德之人不惟不能执好政,更可怕的还在其“上梁不正下梁歪”、“播其恶于众”的影响,结果“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朱熹:《四书集注》,第280页。,天下无道,人间失序,人心离散。正如《左传》曰:“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左丘明:《左传》,第15页。。当前中国社会所呈现出的集体性的贪腐之弊以及某些不良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根子就出在一些为政者“官德不修”,原因就在“官之失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日中国道德风气败坏的一个重要根源,就是为官者失德。正如2014年11月17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刊发的《德法相依,相辅而行》一文中所言:“领导干部如果在德上出了问题,必然导致纲纪松弛、法令不行,必然违纪违法、走向腐败。……从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看,一些干部没了人形,根本问题都是出在‘德’字上,缺德了!”,并提出领导干部要“为政以德,正心修身”*《德法相依,相辅而行》,http://www.ccdi.gov.cn/xsjw/series3/201411/t20141115_46325.html#Art1,访问日期:2015年11月17日。。可见,孔子以仁德修养作为为政根基的“无为而治”之思想,对于今天净化官场风气、提升官员道德境界、严格官员管理的官德建设,以及构建天下归心、人间有道的良善社会,具有不可轻忽的现实借鉴意义。
可以说,为政以修德为本,德修则聚心凝力而政兴、德失则人心离散而政亡,惟有德者方可执政、无德者不可能执好政,是孔子“无为而治”思想启示给我们的重要政治思想遗产。如何在现实中激活并用好这份思想遗产,把它融入到当下的国家治理实践中去,使之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益滋养,是我们当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体现着当代为政者政治智慧的高度。
[责任编辑:李春明]
Confucius’ “Governing without Intervention”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Nation Governing
GAO Lian-fu
(Political and Law School,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P.R.China)
According to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Confucius is the first to put forward “Govern without Intervention” explicitly. It is different with Laozi’s “Nonintervention” by “Giving up Kindheartedness and Justice” and “Returning to the Nature”. The main idea of Confucius’ “Govern without Intervention” is that the leader may “Influence People by Virtue”. Therefore, his “Nonintervention” is with “Moralization”. The “Benevolence” is the humanity base and the inner ground of Confucius’ “Govern without Intervention”. “Influencing People by Virtue” and “Elect Talents by Their Merit” are the realistic ways to realize “Govern without Intervention”. It is a legacy of thought by inspiring later generations to administrate with morals.
Confucius; Govern Without Intervention; Influence People by Virtue
2016-01-17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人的自我改变’的实践思想与当代中国心灵文化建设研究”(2012M520328)。
高连福,淮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研究员(淮北235000),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博士后研究员(北京100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