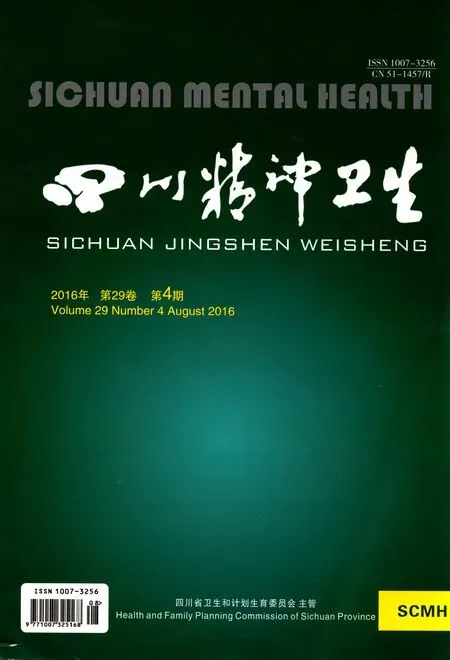协作医疗模式在抑郁症患者社区管理中的应用
2016-04-05沈彦男陆荣荣
沈彦男,庞 娟,张 琳,陆荣荣,李 斌
(1.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华西第四医院,四川 成都 610041;2.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四川 成都 610041)
综述
协作医疗模式在抑郁症患者社区管理中的应用
沈彦男1,庞娟1,张琳1,陆荣荣1,李斌2
(1.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华西第四医院,四川成都610041;2.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四川成都610041)
抑郁症;协作医疗模式;社区精神卫生服务
据WHO报告[1],抑郁症在全球疾病负担中排位第三,是发达国家疾病负担首要成因,而在中低收入国家中抑郁症造成的疾病负担位列第八;在老年人群中,抑郁症与糖尿病、冠心病等躯体疾病共病率高。与单纯患有躯体疾病的患者相比,共病抑郁症的患者躯体症状更加严重,生命质量更低,依从性及预后更差,而其卫生花费更大[2]。
由于精神卫生服务发展水平低、精神卫生核心知识普及不足以及对抑郁症诊治的专业培训不够等多方面因素,我国抑郁症的诊断、治疗及管理均处于较低水平,这与抑郁症的巨大疾病负担形成鲜明对比。加强基层卫生服务中的抑郁症管理,是WHO提出的应对精神卫生问题的中心策略,也是在发展中国家开展精神卫生服务的基石[3],同时,我国最新颁布的《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5—2020年)》[4]强调了基层卫生机构对抑郁症等精神疾病防治的重要作用。
协作医疗模式(Collaborative Care Model,CCM)由慢性病管理模式发展而来,是一种针对有复杂健康需求人群的一种卫生服务模式,在欧美发达国家已有相当多的实践及研究,大量随机对照试验和成本效益分析肯定了这一模式在抑郁症患者基层管理中的作用。我国目前鲜有对协作医疗模式的报道,本文介绍协作医疗模式,关注其有效性,并分析其在我国开展的可行性。
1 简 介
CCM是Wagner及其同事于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是由个案管理者连接社区医生、患者和精神科医生,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中提供多方面的服务,旨在改进抑郁症筛查、诊断程序,促进卫生服务人员在提供积极的抑郁症管理时使用循证的管理方案,促进患者积极参与治疗目标设定,同时提高患者自我管理的临床和社区支持[5]。
多学科协同服务和交流、计划性管理和定期随访等是CCM的主要特征[6]。CCM中的个案管理者承担患者的健康教育、随访管理、调整治疗计划等工作来支持社区医生;而社区医生主要负责高危人群的筛查、诊断工作,为患者开具抗抑郁药处方,在必要时将患者转诊给精神科医生;精神科医生负责向社区医生提供专业的临床指导建议和决策支持。这样密切的协作需要个案管理者的协调,也需要如电子病历这样的电子信息系统的技术支持。除了信息系统,CCM的要素应有[6-8]:自我管理的支持;以预防为导向的卫生服务提供体系重构;决策支持,如使用治疗指南或专家意见。另外,也有人将卫生服务组织支持及整合社区资源归为CCM的要素。在CCM有效性的影响因素上,可能由于CCM中单个要素的偏态分布,目前的研究尚不足以证明以上某一要素对于这一模式的有效性是必不可少或者多余的[9]。尽管如此,研究表明,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卫生服务机构和人群中,甚至对不同类型的精神障碍,CCM都表现出了稳健的有效性,对症状越严重的患者CCM带来的收益越大[10-12]。
2 CCM的有效性研究
2.1CCM对抑郁症患者临床疗效的影响
在各项研究中,抑郁症的临床疗效体现在抑郁症状的改善情况、对治疗的反应、缓解与痊愈这三个方面,同时考虑随访时间长短的影响。
与常规治疗相比,CCM管理下患者的抑郁症状有更明显的改善。Thota等[10]研究发现,经CCM干预的患者,对治疗的反应提高(OR=1.78,95%CI:1.42~2.23),抑郁症状改善更明显(标准化均数差SMD=0.34,95%CI:0.25~0.43)。Coventry等[13]也得出了支持性证据。
抑郁症具有病程长、易复发的特点,而CCM强调有计划的随访,因此不仅能在短期内缓解抑郁症状,还能巩固疗效、降低复发风险。Thota等[10]发现,与常规治疗相比,经CCM干预的患者,抑郁症状的缓解更为持久。Sighinolfi等[14]在研究的短期(<3个月)、中期(4~11个月)和中长期(>12个月)都观察到了这一效应。虽然各研究随访时间不一致,但在缓解>12个月的标准下,两人的证据均表明CCM优于常规治疗。
在临床疗效方面,CCM较常规治疗更具优势,但这些研究多发生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关于CCM在其他中低收入国家的效果研究甚少,尤其是缺乏系统评价的证据支持。
2.2CCM对抑郁症患者社会功能的影响
运用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类(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 ICF)理论框架,社会功能可以从身体结构与功能、活动度和参与度三方面评价。
抑郁症的治疗除了临床疗效外,更关注患者社会功能的恢复。据目前研究,与常规治疗相比,CCM具备更好地改善患者社会功能的趋势。Hudson等[15]发现在6个月短期随访中,CCM能够改善患者社会功能(SMD=0.23,95%CI:0.12~0.34,I2=67.6%,P<0.01),但改善程度较小。在7个月以上的长期随访中,发现CCM对于社会功能的改善降到更低(SMD=0.19,95%CI: 0.09~0.29,I2=45.9%,P=0.047)。Miller等[9]的研究同样也得出了CCM能够显著改善社会功能的结论,但对于共病、不同特征(种族、性别等)的人群效果还颇具争议。现有研究表明CCM对社会功能改善的程度仍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而且这方面的研究甚少,因此未来的相关研究在关注改善症状的同时还要对社会功能的恢复加以观察。
2.3CCM对抑郁症患者治疗依从性和满意度的影响
治疗依从性包括对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等结构化治疗方案的依从性;而治疗满意度主要包括卫生保健提供者的质量、服务可获得性、与提供者的交流以及治疗成功率。
与常规治疗相比,CCM能明显提高患者的依从性及满意度。研究发现[16],即使在CCM要求患者更多参与的情况下,其失访率也并未高于常规治疗(随访3~4个月:OR=1.03,95%CI: 0.60~1.75;随访6~8个月:OR=0.97,95%CI: 0.68~1.38;随访12个月:OR=0.89,95%CI: 0.72~1.09)。Huang等[17]研究发现在药物依从性方面,与常规治疗相比,CCM中患者对抗抑郁药的依从性更好(RR=1.79,95%CI: 1.19~2.69)。Thota等[10]研究也报道CCM可以明显提高患者依从性(OR=2.22)和治疗满意度(SMD=0.39)。
2.4CCM对老年抑郁症患者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加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抑郁症是老年人群中最常见的精神障碍之一[18]。一方面老年抑郁症患者相当比例(50%~70%)存在自杀风险[19],另一方面抑郁症合并其他躯体疾病时明显降低老年人生活质量和治疗依从性等,预后更差。与健康老年人相比,老年抑郁症患者躯体疾病共病率更高,经历更多的负性生活事件,而我国社区中的老年抑郁症患者大部分未被识别、诊断和治疗。CCM在社区普通人群中的作用已被肯定,其对社区老年抑郁症的影响也备受关注。
CCM不仅更有效地缓解老年抑郁症患者的抑郁症状,显著减轻其自杀观念,而且能提高其治疗依从性。Huang等[16]发现,CCM显著地减轻了老年抑郁症患者的自杀观念(OR=0.52,95%CI: 0.35~0.77),且这一效应延续了较长时间,而常规治疗未产生此效应(OR=0.85,95%CI: 0.50~1.43)。此外,随访中发现接受协作医疗的老年抑郁症患者对抗抑郁药和心理治疗的依从性更高。
在老年人群中,抑郁症常与糖尿病、冠心病等共病,患者的生命质量更低,对治疗的依从性和预后更差,抑郁症会增加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而医疗花费更大。CCM有助于改善与抑郁症共病的其他躯体疾病,抑郁症患者的其他躯体疾病相关事件的发生率降低,对治疗其他躯体疾病的药物依从性提高。Tully等[20]发现,CCM下的抑郁症合并冠心病患者,短期内的主要不良心脏事件发生率下降(RR=0.54,95%CI: 0.31~0.95,P=0.03)。Huang等[16]发现,经CCM干预的抑郁症合并糖尿病患者,对口服降糖药的依从性提高(RR=2.18,95%CI: 1.61~2.96)。因此,CCM通过改善抑郁症状,为其他躯体疾病的管理和治疗创造良好条件。
在我国,对CCM应用于社区老年人群的系统评价或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较少,且对此模式的具体操作方法尚不统一,如心境-促进协作医疗(Improving Mood Promote Access to Collaborative Treatemnt,IMPACT)模式、慢性病病案管理模式等,从实质内容上看,亦具备CCM一些要素:精神科医生、社区医生和病案管理员的协作;包括药物和心理治疗的结构化治疗方案;有计划的随访等。这些研究也发现干预组在抑郁症状缓解、降低复发住院率、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和降低费用成本等方面优于常规治疗模式,提示CCM对我国老年人群可能是有效的,尚需进一步研究。
3 CCM实施的可行性
CCM是一个复杂、系统的干预模式,其实施受到多方面的影响。从不同国家的实践经验来看,影响CCM可行性的因素主要分为系统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如果在我国社区中实施CCM,需要解决以下问题。
3.1系统内部因素
3.1.1增加精神科执业医生
精神科医生在CCM中主要承担的是监督者和培训者的角色[21],对于转变卫生服务模式、改善社区中抑郁症患者的诊疗观念等起主导作用。虽然目前我国精神科专业人员数量相当匮乏,可能限制CCM的实施,但随着“互联网+医疗”的发展,近期可以依靠远程指导、沟通解决这一问题。从长远角度考虑,一方面通过实行分级诊疗制度,缓解上级医院的诊疗压力,使得上级医院的精神科专业医生有精力支援社区诊治;另一方面通过政策鼓励等机制,加大精神科医生的培养力度,为社区增加新的精神科专业人才。
3.1.2社区医生培训
我国社区医生大多是全科医生,主要擅长躯体疾病的诊疗,对于抑郁症的识别和管理能力不足,尤其对于老年抑郁患者[23]。一方面,社区医生对抑郁症识别和诊断能力不足,对精神科药物的不良反应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处理能力,同时社区医院药物可选择性低。另一方面,社区医生对于抑郁症诊疗进展的培训机会很少,治疗的规范性观念较为落后,偏重药物治疗,忽视心理干预,缺乏主动的随访和教育。这是影响CCM可行性的一大阻碍因素。因此,需要对社区医生进行有效的培训和业务督导。
目前欧美国家的CCM中主要由社区医生为患者开具抗抑郁药处方,而我国社区医生不具有精神科药物的处方权,因此在我国开展CCM时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可在政府职能部门的协调下,本地专科医院精神科医生在当地社区进行轮转驻点,主要针对慢性稳定期精神障碍患者进行定期随访和开药,可以避免医疗资源的过度使用;随着社区卫生和全科医学的发展,可根据现实需求经过正规精神专科培训合格后授予社区医生一定限度的精神类药物处方权。
3.1.3个案管理者
个案管理者被认为是CCM的核心,是有别于其他卫生服务模式的关键特征[14],他们承担健康教育、随访管理、调整治疗计划等工作,连接社区医生、患者和精神科专家,使得CCM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我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中已有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健康管理,也有对其他特殊人群的健康管理。然而,不同于健康管理旨在实现健康的最大效果,个案管理是一个社会工作学概念,强调案主需要的复杂性。个案管理者将案主所需的各种服务连接起来,改善案主对支持和服务的使用。CCM的个案管理者的服务对象超过了目前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健康管理的服务对象,服务需要也更为复杂。因此,在个案管理者方面,可以认为我国社区卫生在一定程度上具备开展CCM的基础,个案管理者可以由目前健康管理人员(如公共卫生医师)担任;但应加强抑郁症、个案管理等相关知识培训并加以考核。
3.1.4提升患者依从性
患者的参与是CCM得以运行的意义所在。国内外大多调查显示老年人更愿意在社区求医[24]。但由于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部分患者对抑郁症等精神疾病持有讳疾忌医的态度以及对精神疾病认识不足,老年人中表现更为明显,这种现状导致部分抑郁患者拒绝在社区就医,或者只向社区医生诉说躯体症状。这导致社区医生的诊疗难度增大,增加了误诊和漏诊的风险,从而降低了CCM服务的患者数量和服务质量。
其次,患者的配合度也是影响CCM可行性的重要因素之一。虽然个案管理者会主动定期随访,但为了顺利实施CCM并取得理想效果,患者的自我管理至关重要。因此,CCM强调对患者自我管理的支持,进行充分的健康教育和决策支持,促进患者正确认识抑郁症以及自我管理作用和其可利用的资源等,增强其恢复健康的信心,从而改变其就医行为,提高治疗依从性。
3.1.5规范管理流程和完善信息系统
规范的管理流程和完善的信息系统是CCM的技术和信息保证。我国在2003年已编写了《中国精神障碍防治指南(试行)》,其中包括了精神分裂症、抑郁障碍和双相障碍,并于2015年加以完善和修改,新增了老年期痴呆和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出版了《中国抑郁障碍防治指南(第二版)》。因此,精神医学专业人士可联合在此基础上,制定适合社区医生的抑郁症防治指南,并且由社区医生参与评价。
另外,信息共享是组织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在远程医疗中尤为重要。目前,我国只有传染病和慢性病的登记系统,内容较少,不利于对抑郁症患者进行全方位的个案管理。因此,需要组建专业团队来开发和测试适合抑郁症管理的公共电子信息系统,包括患者基本信息、抗抑郁药使用、副反应情况、抑郁症相关评分及变化等。需要注意的是,系统应具有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否则将增加组织内人员的工作量,降低工作效率,甚至降低社区医生和个案管理者对抑郁症防治指南的依从性[25]。
3.2系统外部因素
3.2.1社区对CCM的需求程度
社区对于改善抑郁症诊疗模式的需求程度是CCM产生的前提。需求可来自于社区医生、患者及家属等。这些需求可能为CCM的运行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并促进对社区资源的整合。最初,CCM的产生就是为了帮助社区医生解决所面临的挑战,比如对抑郁症患者的抗抑郁药和心理疗法使用不足或不恰当,患者治疗依从性低等[26],可以说,CCM本身即是社区医生需求的体现。对患者而言,有文献表明,目前对抑郁症的治疗主要以药物为主,但临床治愈率仅为40%~60%,且复发率较高[27]。因此,抑郁症患者和家属都有改善抑郁症诊疗效果的需求。这些需求都有利于CCM在我国的开展。
3.2.2政策因素
抑郁症是慢病的一种,需要纳入社区慢病管理范畴。我国发布的《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年)》[28],强调建立以社区为基础的慢性病管理办法。2012年,我国提出《中国慢性病防治工作规划(2012—2015年)》[29],指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负责相关慢性病防控措施的执行与落实,强化慢性病防控职能,提高服务能力”。进一步明确了社区在慢性病防治中的基础作用。而CCM即是在社区卫生服务的背景下运行,将抑郁症的社区管理作为公共卫生问题,旨在提高抑郁症管理效果并顺应国家政策的新举措。
3.2.3经济因素
在我国,政府的卫生财政投入有限,卫生预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5%,对精神卫生的投入占整个卫生预算的2.35%[30],这与精神疾病占疾病总负担的1/5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限的经济投入必然限制CCM实施。
国外已有相当多的试验和系统评价证明在取得相同效果时,CCM比基本卫生保健所需成本更低。一项美国的研究发现[31],CCM在改善抑郁症患者状态,减轻抑郁症状和成本效果方面均优于普通保健。Green等[32]在英国初级保健体系中进行了随机对照试验,得出CCM每增加一个质量调整生命年所需成本为14248英镑,而政策制定者愿意为此所支付的费用是20000英镑,说明CCM的成本是低于政府预算的。Pyne等[33]研究比较了现场CCM和以远程医疗为基础的两种CCM的成本效果比,结论是以远程医疗为基础具有更好的成本效果性。因此,在我国开展以远程医疗为基础的CCM不仅可以弥补精神科专家数量的欠缺,而且所需成本更低。
同时,目前我国部分地区居民的医疗保险已将抑郁症作为特殊门诊病种,纳入到报销范围,第三方机构的支持同样有利于此模式在我国的开展。
CCM在我国的开展是顺应抑郁症防治政策、满足社区医生以及患者与家属的需求的,同时人员和资金的不足也影响到其可行性。进一步在我国进行CCM有效性和成本效果的研究,提高全社会对抑郁症的关注和认知水平,将有利于人员和资金的补充。
[1]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2004 update[EB/OL].(2014-03-11)[2016-06-01].http://www.who.int/healthinfo/global_burden_disease/2004_report_update/en/.
[2]Moussavi S, Chatterji S, Verdes E, et al. Depression, chronic diseases, and decrements in health: results from the World Health Surveys[J]. The Lancet, 2007, 370(9590): 851-858.
[3]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he World Health Report 2001: Mental health: new understanding, new hope[M]. (2013-07-29)[2016-06-01]. http://www.who.int/whr/2001/en/.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5—2020年)[J]. 中国实用乡村医生杂志, 2015,22(14):1-5.
[5]Katon W, Von Korff M, Lin E, et al. Rethinking practitioner roles in chronic illness: the specialist, primary care physician, and the practice nurse[J]. Gen Hosp Psychiatry, 2001, 23(3): 138-144.
[6]Wagner EH, Grothaus LC, Sandhu N, et al. Chronic care clinics for diabetes in primary care: a system-wide randomized trial[J]. Diabetes Care, 2001, 24(4): 695-700.
[7]Von Korff M, Gruman J, Schaefer J, et al. Collaborative management of chronic illness[J]. Ann Intern Med, 1997, 12(127): 1097-1102.
[8]Bodenheimer T, Wagner EH, Grumbach K. Improving primary care for patients with chronic illness: the chronic care model, Part 2[J]. JAMA, 2002, 288(15): 1909-1914.
[9]Miller CJ, Grogan-Kaylor A, Perron BE, et al. Collaborative chronic care models for mental health conditions: cumulative meta-analysis and metaregression to guide future research and implementation[J]. Med Care, 2013, 51(10): 922-930.
[10] Thota AB, Sipe TA, Byard GJ, et al. Collaborative care to improve the management of depressive disorders: a community guide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Am J Prev Med, 2012, 42(5): 525-538.
[11] Woltmann E, Grogan-Kaylor A, Perron B, et al. Comparative effectiveness of collaborative chronic care models for mental health conditions across primary, specialty, and behavioral health care settings: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Am J Psychiatry, 2012, 169(8): 790-804.
[12] Farooq S. Collaborative care for depression: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a model for implement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Int Health, 2013, 5(1): 24-28.
[13] Coventry PA, Hudson JL, Kontopantelis E, et al. Characteristics of effective collaborative care for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regression of 74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s[J]. PLoS One, 2014, 9(9):e108114.
[14] Sighinolfi C, Nespeca C, Menchetti M, et al. Collaborative care for depression in European countrie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J Psychosom Res, 2014, 77(4): 247-263.
[15] Hudson JL, Bower P, Archer J, et al. Does collaborative care improve social functioning in adults with depressi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WHO ICF framework and meta-analysis of outcomes[J]. J Affect Disord, 2015, 189:379-391.
[16] Huang CQ, Dong BR, Lu ZC, et al. Collaborative care interventions for depression in the elderly: a systematic review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J]. J Investig Med, 2009, 57(2): 446-455.
[17] Huang Y, Wei X, Wu T, et al. Collaborative care for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nd diabetes mellitu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BMC Psychiatry, 2012, 13(1):260-260.
[18] 张玲, 徐勇, 聂宏伟. 2000~2010年中国老年人抑郁患病率的meta分析[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11, 31(17):3349-3352.
[19] 伍小兰, 李晶, 王莉莉. 中国老年人口抑郁症状分析[J]. 人口学刊, 2010(5):43-47.
[20] Tully PJ, Baumeister H. Collaborative care for comorbid depression and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s[J]. BMJ Open, 2015, 5(12): e009128.
[21] Sharpe M, Walker J, Holm Hansen C, et al. Integrated collaborative care for comorbid major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cancer (SMaRT Oncology-2): a multicentre randomised controlled effectiveness trial[J]. The Lancet, 2014, 384(9948): 1099-1108.
[22] 孙学礼. 中国综合医院的精神卫生服务[J]. 中国循证医学杂志, 2007, 7(8):555-556.
[23] 吴海苏, 徐一峰. 社区老年抑郁症研究进展[J]. 临床精神医学杂志, 2006, 16(5):308-309.
[24] 马颖, 胡志, 朱敖荣,等. 农村社区老年人精神卫生服务需求与利用情况调查分析[J]. 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 2013, 33(5):488-491.
[25] Price-Haywood EG, Dunn-Lombard D, Harden-Barrios J, et al. Collaborative Depression Care in a Safety Net Medical Home: facilitators and barriers to quality improvement[J]. Popul Health Manag, 2015, 19(1): 46-55.
[26] Davidson JR, Meltzer-Brody SE. The underrecognition and undertreatment of depression: what is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the problem?[J]. J Clin Psychiatry, 1999, 60(suppl 7):4-9.
[27] Elkin I, Shea MT, Watkins JT, et al.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collaborative research program: general effectiveness of treatments[J]. Arch Gen Psychiatry, 1989, 46(11): 971-982.
[28] 国务院办公厅. 《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年)》的具体任务[J]. 中国乡村医药, 2015, 22(8): 37.
[29] 郭岩松. 《中国慢性病防治工作规划(2012—2015年)》印发[J]. 中国医药导刊, 2012, 14(7).
[30] 接雅俐, 汤先忻. 谈我国精神卫生工作中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J]. 江苏卫生事业管理, 2006, 17(1):64-66.
[31] Jeeva F, Dickens C, Coventry P, et al. Is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cost-effective in people with diabete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economic evidence[J]. Int J Technol Assess Health Care, 2013, 29(4): 384-391.
[32] Green C, Richards DA, Hill JJ, et al. Cost-effectiveness of collaborative care for depression in UK primary care: economic evaluation of a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CADET)[J]. PloS One, 2014, 9(8): e104225.
[33] Pyne JM, Fortney JC, Mouden S, et al. Cost-effectiveness of on-site versus off-site collaborative care for depression in rural FQHCs[J]. Psychiatr Serv, 2015, 66(5): 491-499.
(本文编辑:陈霞)
R749.4
A
10.11886/j.issn.1007-3256.2016.04.021
2016-0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