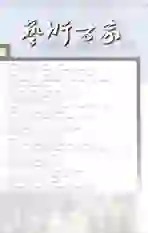当代社会转型与文艺理论发展
2016-04-05杨和平熊元义
杨和平++熊元义
摘要: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在把握西方当代文艺理论上从基本肯定到基本否定的转向不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科学发展,而是对西方当代文艺理论从盲目崇拜到盲目排斥的理论摇摆。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发展不能只是重视古今和中外文艺理论之间的相互影响,还要及时又集中地反映中国当代社会转型阶段的中国人民对文艺的根本要求。这是文艺理论家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在推进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发展中发展。无论是文艺理论更多地指向具体的文艺批评发展论,还是文学文本解读学,都是当代历史碎片化的产物,不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发展的科学途径。
关键词: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文艺理论;社会转型;科学发展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随着中国当代社会从以模仿挪移为主的赶超阶段转向以自主创新为主的创造阶段,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出现了对西方现当代文艺理论从基本肯定到基本否定的转向。过去,有些文艺理论家基本肯定了西方现当代文艺理论,认为西方现当代文艺理论是人类文艺理论发展的最高阶段。有的文学批评家宣称,现代文学理论和现代物理学、现代化学一样,是西方创立的学科,更准确地说,它是现代知识大转型的一部分,无论西方还是东方,都在进行着现代知识转型,只是现在这个过程表现为自西方向东方运行而已。西方当代文学理论已经取得相当高的成就,中国当代文学理论除了认真学习以外,没有必要急着说“自己的话”。有的文艺理论家进一步地认为,西方当代文艺理论“总体上对人类思想文化的发展和进步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整个20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生产力远远超过前两个世纪自由资本主义创造的生产力的总和。在此意义上,资本主义社会仍取得了重要的经济进步。与此相适应,西方资本主义的精神文化也取得了新的进展。……从总体上说,当代西方文化的基本趋向是在19世纪的基础上曲折前进的,它体现了历史的进步,而不是倒退。对当代西方文论,总体上亦应作如是观。虽然它贯穿着离经叛道的反传统倾向,但是,总的看来,它对传统西方文论仍有所继承,并在继承基础上有一系列重大的推进和超越。”而“20世纪西方文论也在理论上从各个方向向资本主义的现代异化发起攻击。可以说,揭露、批判现代资本主义(从制度到思想文化),已成为当代西方文论的主旋律。”西方当代文艺理论是西方思想文化中的“异端”。这种对西方当代文艺理论的高度肯定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家在以模仿挪移为主的赶超阶段盲目崇拜西方当代文艺理论的结果。现在,有些文艺批评家基本上否定了西方当代文艺理论,认为西方当代文艺理论是架空的理论和场外理论的简单挪移。有的文艺理论家尖锐地批判了西方当代文艺理论的美学化、哲学化的倾向,认为西方当代前卫文艺理论虽然号称文学理论,但却否认文学本身的存在,还被当成文学解读的权威经典,从而造成文学解读空前的大混乱,低效和无效遂成为顽症。这种西方当代文学理论不是建立在创作和解读的基础上,而是偏执于把文学理论当作一种知识谱系。因此,这种文学理论是架空的理论,“往往是脱离文学创作经验、无能解读文本的”。这种以超验为特点的文学理论虽然可以批量生产出所谓的“文学理论家”,但这些文学理论家对文学审美规律却是一窍不通的,在不少权威那里,还有不可救药的性质。“在创作和阅读两个方面脱离了实践经验,就不能不在创作论和解读的迫切需求面前闭目塞听,只能是从形而上的概念到概念的空中盘旋,文学理论因而成为某种所谓的‘神圣的封闭体系。在不得不解读文学文本时,便以文学理论代替文学解读学。”有的文艺批评家则进一步认为,西方当代文艺理论颠倒了实践与理论的关系。西方当代文艺理论的生长不是基于文学实践,而是基于理论自身的膨胀,基于场外理论的简单挪移。而文艺批评则不是依据文本得出结论,而是从抽象的原则出发,用理论肢解文本,让结论服从理论。这位文艺批评家认为“强制阐释”这四个字足以概括西方当代文艺理论的根本缺陷,并将西方当代文艺理论的这种“强制阐释”概括为四个特征:“第一,场外征用。广泛征用文学领域之外的其他学科理论将之强制移植到文论场内,抹煞文学理论及批评的本体特征,导引文论偏离文学。第二,主观预设。论者主观意向在前,预定明确立场,无视文本原生含义,强制裁定文本的意义和价值。第三,非逻辑证明。在具体批评过程中,一些论证和推理违背了基本的逻辑规则,有的甚至是明显的逻辑谬误,所得结论失去依据。第四,混乱的认识路径。理论构建和批评不是从实践出发,从文本的具体分析出发,而是从既定理论出发,从主观结论出发,颠倒了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这种对西方当代文艺理论的猛烈批判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家在中国当代社会转型阶段盲目排斥西方当代文艺理论的产物,而不是对西方当代文艺理论的科学把握。
在中国当代社会转型阶段,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如何适应这个变革的进步的时代?如何科学发展?
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家在推动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发展时不能只是重视古今和中外文艺理论之间的相互影响,还要及时而又集中地反映中国当代社会转型阶段人民对文艺的根本要求。这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家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
随着中国当代社会转型,广大人民对文艺的根本要求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少作家艺术家敏锐地意识到了这种巨变,进行了与时俱进的艺术调整。文艺理论家在重视古今和中外文艺理论之间的相互影响的同时要及时而又集中地反映中国当代社会转型阶段人民对文艺的根本要求。但是,中国当代社会改革开放后,文艺理论界一直偏重古今和中外文艺理论之间的相互影响,却相对忽视这个历史阶段的人民对文艺的根本要求。无论是提出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现代转换”,还是提出西方当代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文艺理论界都是停留在古今和中外文艺理论之间的相互影响上,基本上忽视了这个历史阶段的人民对文艺的根本要求,因而收效微乎其微。
其实,文艺理论不仅深刻反映不同时代的民族和阶级或集团对文艺的根本要求,而且集中反映不同时代的民族和阶级或集团的审美需要和审美理想。马克思恩格斯在把握人类的社会分工时深刻地指出:分工以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的形式在统治阶级中间表现出来,“在这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玄想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主要的谋生之道,而另一些人对于这些思想和幻想则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并且准备接受这些思想和幻想,因为在实际中他们是这个阶级的积极成员,很少有时间来编造关于自身的幻想和思想。”这就是说,思想家包括文艺理论家是从事精神劳动的,不仅从属于他们所属的阶级,而且积极编造本阶级的幻想和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把统治阶级的思想与统治阶级本身分割开来,认为这会使统治阶级的思想独立化。马克思、恩格斯深入地批判了这种统治阶级的思想独立化的严重后果,认为这是社会虚假意识形态产生的思想根源。因此,从事精神劳动的文艺理论家不仅要深刻反映不同时代的民族和阶级或集团对文艺的根本要求,而且要集中反映不同时代的民族和阶级或集团的审美需要和审美理想。英国当代文艺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在深刻把握西方现代文学理论同西方社会的政治制度的特殊关系的基础上尖锐地指出:西方现代文学理论“在有意或无意地帮助维持这个制度并加强它”。在深刻把握西方当代文学理论的意识形态属性的基础上,特里·伊格尔顿进一步指出:“即使是在避开各种现代意识形态的行动中,文学理论也表现出它与这些意识形态往往是无意识的牵连,并且恰恰是在它运用文学文本时认为是很自然的那种‘美学的或‘非政治的语言中暴露出它的优越感、性别歧视或个人主义。”因此,特里·伊格尔顿认为,“真正应该反对的是文学理论中所包含的政治性质”。特里·伊格尔顿还深入地把握了美学的政治史,认为:“美学不是简单的艺术或艺术产品,而是工艺品特有的意识形态在18世纪盛行的方式。”这就是说,“美学不等同于任何艺术话语,它指的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历史话语,这个历史话语开始于18世纪,并设法以一种贴合早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方法来重建艺术作品。”因此,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无论是批判西方当代文艺理论,还是发展当代文艺理论,都不能阉割文艺理论的意识形态属性,而是在把握文艺理论的意识形态属性的基础上及时而又集中地反映中国当代社会转型阶段的人民对文艺的根本要求。
随着中国当代社会转型,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将从三个方面发展。
第一,中国当代社会转型不仅是从以模仿挪移为主的赶超阶段转向以自主创新为主的创造阶段,而且是促进社会的共同发展。随着中国当代社会转型,不少作家艺术家进行了艺术调整,自觉地把主观批判和历史批判有机结合起来,把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有机统一起来。他们不是汲汲挖掘中国当代社会转型阶段的人民的保守自私、封闭狭隘的痼疾,而是在批判这些保守自私、封闭狭隘的痼疾的同时有力地表现了中国当代社会转型阶段的人民创造历史和推动历史发展的伟大力量。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不仅在把握和肯定作家艺术家的艺术调整中发展,而且在推动广大作家艺术家与时俱进的艺术调整中发展。
第二,中国当代社会反腐败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清除阻碍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障碍。人类历史发展既有较残酷的形式,也有较人道的形式。历史的发展只有采取较人道的形式,才真正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整个世界当代历史发展中,中国当代社会转型是竭力摈弃采取较残酷的形式的历史发展,尽可能采取较人道的形式的历史发展。而腐败势力却极力阻碍这种中国当代社会转型,无疑是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绊脚石。文艺理论家岂能置身反腐败斗争以外?岂能对那些肆意采取较残酷的形式的腐败势力听之任之?因此,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只有猛烈批判采取较残酷的形式的历史发展,积极推动中国当代社会转型,才能科学发展。
第三,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在促进中国当代民族文艺发展观的完善中发展。在中国当代社会转型阶段,中国当代民族文艺既不能在发展中作茧自缚,也不能在纷乱中迷失自我,而是在世界文艺发展的格局中把握中国当代民族文艺的前进方向。中国当代作家艺术家的艺术创造不仅是民族的,而且是世界的。中国当代作家艺术家应与中国当代社会转型阶段相适应,创造出对人类文艺发展做出独特贡献的民族文艺作品。否则,中国当代文艺将很难成为世界当代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民族的当代文艺没有推动世界文艺的有序发展,就不可能在世界文艺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产生重要影响。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不仅积极促进中国当代民族文艺在大胆吸收一切外来文艺的有益养分的基础上克服民族文艺的狭隘局限,而且积极推动中国当代民族文艺融人世界进步文艺中并为人类文艺的发展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因此,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重视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民族特色是可取的,但推动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民族化则是不可取的。
然而,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却存在阉割文艺理论的意识形态属性的倾向。这严重地制约了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科学发展。有的文艺批评家认为,现代文艺理论和现代物理学、现代化学一样,是西方创立的学科,更准确地说,它是现代知识大转型的一部分,无论西方还是东方,都在进行着现代知识转型,只是现在这个过程表现为自西方向东方运行而已。现代文艺理论是世界现代知识大转型的一部分,并不具有意识形态属性。有的文艺批评家甚至觉得,存在一种所谓科学的、客观的文艺理论,可以从根本上阐释一切文艺现象,正如门捷列夫化学元素周期表那样的理论,既与现实相吻合,又能预见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只是现在还没有找到这样的文艺理论而已,正如冯友兰所认为的,“存在必有存在之理”,“未有飞机之前,已有飞机之理”。飞机之理是早已客观存在的,但也只有到近代人类才认识到这个理,并开始依据这个理来设计制造飞机。因此不能说飞机之理是近代才诞生的,而只能说关于飞机之理的认识是直到近代才诞生的。文艺之理与文艺理论之间也应当是这种关系。这没有区别属于意识形态的文艺理论与不属于意识形态的飞机之理,而是混淆了这两种不同对象,完全阉割了文艺理论的意识形态属性。这种阉割文艺理论的意识形态属性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文艺理论的灰色化。
21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出现了贬低文艺理论的倾向。有的文学批评家提出了文学理论贫乏论,认为文学理论的生命来自文学创作和阅读实践,文学理论谱系不过是把这种运动升华为理性话语的阶梯,此阶梯永无终点。文学理论谱系如果脱离了文学创作和阅读实践,就必定是残缺和封闭的。“文学理论对事实(实践过程)的普遍概括,其内涵不能穷尽实践的全部属性。与实践过程相比,文学理论是贫乏、不完全的,因而理论并不能自我证明,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准则。”这不仅认为文学理论只是对文学创作和阅读实践的概括,而且认为文学理论是贫乏、不完全的。有的文艺批评家则提出了文艺理论局限论,认为文艺理论与文艺现象是冲突的。这就是文艺理论从自足的理论体系而言,它是言之凿凿、自成一体的,但一旦与现象、现实相比照,就显得那么苍白、困窘。从理论自身来说,理论越有概括力,便越抽象、越苍白,这是因为理论所取的是共性,在择取共性的同时个性则被舍弃,所以共性有遮蔽个性的危险。这是文艺理论作为一种理论的形态所天然具有的局限。
在贬低文艺理论上,文艺理论局限论和文学理论贫乏论是如出一辙的。有的文学批评家还提出了“本体阐释”论,认为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始终没有解决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一些西方当代文学理论脱离文学实践,相当程度上源自对其他学科理论的直接“征用”,而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脱离文学实践则表现为对西方当代文学理论的生硬“套用”。从这个意义上讲,东西方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实践都处于一种倒置状态。因此,当代文学理论发展必须重新校正长期以来被颠倒的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抛弃一切对场外理论的过分倚重,从对先验理论的追逐回到对文学实践的认识,让文学理论归依文学实践。
而“文学理论要成为科学,要对无限产出的文本作科学严谨的批评,必须引入现代统计方法,在大规模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再做定性分析,建立具有科学统计依据的自洽体系。”也就是“以文本为中心,对单个文本的阐释做出分析,对大批量文本的阐释做出统计,由个别推向一般,上升飞跃为理论”。这种“本体阐释”论虽然没有直接贬低文艺理论,但却与文学理论贫乏论和文艺理论局限论一样,狭隘地把握了文艺理论与文艺创作的关系,认为文艺理论只是文艺创作的概括和归纳。这既不符合文艺理论产生的规律,也间接地贬低了文艺理论。如果文艺理论只是文艺创作的概括和归纳,就只能跟在文艺创作后面跑,甚至被层出不穷的现象所淹没。有的文艺理论家就在这样狭隘地把握文艺理论与文艺创作的关系时陷入了自相矛盾。这位文艺理论家一方面认为艺术批评的规范是从艺术的历史发展和艺术的现实生成的实际存在中概括、总结出来的,另一方面又认为艺术批评是在一定审美理想支配下对艺术现象、艺术作品所做的阐释与评价,而这种审美理想则是审美领域对于有缺陷的现实的超越,即对丑的或不够美的事物的超越,对更美的事物的憧憬和追求,并不来自对文艺的历史发展和文艺的现实生成的实际存在的概括、总结。这就是说,艺术批评的规范并不是从文艺的历史发展和文艺的现实生成的实际存在中概括、总结出来的。
19世纪德国美学家康德在论艺术天才时指出:“天才(一)是一种天赋的才能,对于它产生出的东西不提供任何特定的法规,它不是一种能够按照任何法规来学习的才能;因而独创性必须是它的第一特性:(二)也可能有独创性的,但却无意义的东西,所以天才的诸作品必须同时是典范,这就是说必须是能成为范例的。它自身不是由摹仿产生,而它对于别人却须能成为评判或法则的准绳。”虽然艺术独创是艺术的第一特性,但这种艺术独创却既有可能是有意义的,也有可能是无意义的。如果文艺理论只是概括和归纳天才的诸作品,就无法在辨别有意义的文艺创新和无意义的文艺创新的基础上批判那些无意义的文艺创新。法国当代文艺理论家茨维坦·托多洛夫在倡导对话批评时认为,文艺“批评是对话,是关系平等的作家与批评家两种声音的相汇”。在这种文艺批评对话中,文艺理论家与作家艺术家的关系是平等的。
如果文艺理论家完全跟在文艺创作后面跑,就不可能与作家艺术家平等对话,而是“颂赞”满天飞。这极大地降低了文艺理论家的地位。这种对文艺理论家的轻视甚至忽视在文艺批评中表现为排斥文艺理论的倾向。有的文学批评家明确地宣称:文学“批评活动不能拿着理论的条条框框教条化地去套具体的文本时,不能用既定的理论去要求作家照样创作。理论只具有思维方式的意义,即是说,在面对具体的文学创作、具体的作品文本时,所有的理论成见都要抛开,所有现成的理论结论都不具有权威性和绝对性,而是要回到文本的具体阐释,从中发现文本的意义,或者提炼出文本的理论素质。”这种对文艺理论家的轻视甚至忽视恐怕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中青年文艺理论人才严重凋零的重要原因。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必须清除这些文艺理论发展的误区,否则,难以推进当代文艺理论的科学发展。
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不仅及时而又集中地反映中国当代社会转型阶段的人民对文艺的根本要求,而且在推进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的有序发展中发展。
首先,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在深入解决文艺批评的理论分歧中发展。
在文艺批评史上,不少文艺批评的分歧究其实质是理论分歧。20世纪80年代早期,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在把握“朦胧诗”时分化了。1981年,文艺批评家孙绍振在肯定“朦胧诗”这种创作倾向时认为,这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与其说是新人的崛起,不如说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这种新的美学原则主要是这批崛起的青年诗人不仅是对理想主义的失望情绪的自然流露,而且是“不屑于做时代精神的号筒,也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这批崛起的青年诗人不是直接去赞美生活,而是追求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而文艺批评家程代熙则尖锐地批判了这种新的美学原则,认为这种新的美学原则根本不是什么“新的美学原则”,而是步了西方现代主义文艺的足迹的自我表现论。程代熙尖锐地指出,不仅“抒人民之情”和诗人的“自我表现”是两种相互排斥的艺术观,而且人民之情和诗人的“自我之情”是存在鸿沟的。“我们丝毫不反对艺术表现人性。我们关心的是艺术家的人性、诗人的人性和人民大众的人性是否相通,或者是否基本相通。如果诗人的人性和人民大众的人性南辕北辙,或者诗人根本不关心人民的痛痒,则不管诗人个人的感情如何的丰满,他个人的悲欢如何的非比寻常,甚至把他个人的心灵世界全部敞开,也终因和人民大众缺少‘灵犀一点,而不能相通。”程代熙对孙绍振所提出的“新的美学原则”的质疑凸显了文艺批评界的理论分歧。
21世纪初期,文艺理论家王元骧力求解决多年没有解决的程代熙与孙绍振的理论分歧,提出了文艺的审美超越论。王元骧认为,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审美理想愿望不仅仅只是作家的主观愿望,同样也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的一种概括和提升。这种将作家的主观愿望完全等同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的审美超越论不仅妨碍广大作家深入人民创作历史活动并和这种人民创作历史活动相结合,而且在当代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在中国当代社会,作家的主观愿望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是不可能完全吻合的。既然作家的主观愿望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不是完全等同的,那么,作家的主观愿望是如何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的概括和提升的?难道是自然吻合的?王元骧认为:“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审美理想愿望自然是属于主观的、意识的、精神的东西,但它之所以能成为引导人们前进的普照光,就在于它不仅仅只是作家的主观愿望,同样也是对于现实生活的一种反映,因为事实上如同海德格尔所说的‘形而上学是此在内心的基本形象,‘只消我们生存,我们就是已经处在形而上学中的。理想不是空想,它反映的正是现实生活中所缺失而为人们所热切期盼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作品所表达的审美理想从根本上说都是以美的形式对于现实生活中人们意志和愿望的一种概括和提升,所以鲍桑葵认为‘理想化是艺术的特征,‘它与其是背离现实的想象的产物,不如说其本身就是终极真实性的生活与神圣的显示,是现实生活中存在于人们心灵中的一个真实的世界,是人所固有的本真生存状态的体现,它不仅是生活的反映,而且是更真切、更深刻的反映,它形式上是主观的,而实际上是客观的。”这实际上是认为广大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只要挖掘自我世界就可以了。
这种将作家的主观愿望完全等同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的审美超越论不过是一种精致的自我表现论。首先,这种人所固有的本真生存状态是人生来就有的,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这是很不同的。如果这种人所固有的本真生存状态是人生来就有的,那么,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只要开掘自我世界就可以了。如果这种人所固有的本真生存状态不是人生来就有的,而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那么,作家所愿望看到的样子(“应如此”)与广大人民群众所愿望看到的样子(“应如此”)不可能完全相同,有时甚至根本对立。其次,在现实世界中,既然作家的主观愿望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之间是存在很大差异甚至对立的,那么,这种历史鸿沟是如何填平或化解的?如果作家在审美超越中可以填平或化解这种历史鸿沟,那么,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只要挖掘自我世界就行了。其实,人民之情和诗人的“自我之情”虽然存在差异甚至矛盾,但却不是绝对排斥的。作家虽然是从自我出发来写作的,即从自己感受最强烈的地方人手和写自己最有把握的那一部分生活,但是,作家感受最强烈的地方却是和整个社会生活分不开的,是整个社会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作家如果局限在自己感受最强烈的地方,而不是从这个地方出发并超越这个地方,就很难反映出他所处时代的一些本质的方面。因而,广大作家应在作家的主观批判与人民的历史批判的有机结合、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的有机统一中化解人民之情和作家艺术家的“自我之情”的差异甚至冲突,而不是蜷缩在自我世界里深挖人所固有的本真生存状态。正是在不断解决文艺批评的理论分歧中,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发展了。
其次,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在清理文艺批评的含混概念中发展。
在中国当代文艺批评中,不少似是而非的含混概念都是理论不彻底的产物。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只有彻底清理这些似是而非的含混概念,才能推进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的有序发展。不可否认,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在20世纪50年代崛起时的确存在简单粗暴和说理不够充分的地方,但是这些文艺批评却深刻反映了中国当代社会刚刚站起来的人民对文艺的根本要求。这样说是丝毫不过分的。但是,中国当代社会改革开放后,文艺理论界在高度重视文艺的审美特性时却阉割了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不少文艺批评家在回避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时提出了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几零后”作家艺术家、“美女作家艺术家”这些以生理年龄和外貌特征为标准的外在标签和“灵魂写作”、“生命写作”这些似是而非的空洞概念满天飞,至今仍然流行。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如果不清理这些似是而非的含混概念,就无法推进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的有序发展。
有些报刊集中推出所谓的“50后”作家艺术家,“60后”作家艺术家,“70后”作家艺术家,“80后”作家艺术家,甚至“90后”作家艺术家,都是以生理年龄为标准,而不是以文艺思想和审美理想为标准。同一时代、同一年龄阶段的作家艺术家在个人成长经历上可能有类似之处,但在文艺思想和审美理想上却可能差异很大,甚至截然不同。在中国当代历史转折关头,不少作家艺术家在文艺思想和审美理想上发生了分化。这种简单的“几零后”划分法不过是在不同年龄阶段的人身上贴上固化标签而已。这深刻地反映了有些文艺批评家陷入了外部时间发展论的怪圈,
文艺批评家不仅需要深刻反映不同时代的民族和阶级或集团对文艺的根本要求,而且要集中反映不同时代的民族和阶级或集团的审美需要和审美理想。因此,文艺批评家应在把握整个历史运动的基础上将真正有利于民族文化乃至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的优秀文艺作品推举出来。
有的文学批评家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首先是生命写作、灵魂写作的缺失。这种文学批评貌似深刻,实则没有把握中国当代文学缺失的要害。作家的才能虽然有高低大小,但只要他是真正的文学创作,就是生命的投入和耗损,就是灵魂的淬炼和提升,不能不说是生命写作、灵魂写作。这种对中国当代文学缺失的判断没有深入区分生命写作、灵魂写作的好与坏、高尚与卑下,而是提倡生命写作、灵魂写作这些似是而非的含混概念,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克服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
在世界文学史上,凡是伟大的文学作品都绝不会局限于反映某一社会阶层,而是在深刻把握整个历史运动的基础上尽可能反映广阔的社会阶层。然而,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有些文学批评家却不是深刻把握整个历史运动,而是热衷于抢占山头,甚至画地为牢,提出了“底层文学”这个狭隘的概念。2001年,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有感于中国当代文坛所有最有活力、最有才华和最有前途的青年作家几无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这种现象,尖锐地提出了中国当代作家直面现实、感受基层这个深入生活的方向。这个深入生活的方向既不是要求广大作家只写中国当代社会底层生活,也不是要求广大作家肢解中国当代社会。而“底层文学”这个概念却狭隘地划定文学创作范围,既肢解了中国当代社会,也限制了广大作家的视野。
首先,社会底层生活是整个社会生活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社会底层民众的苦难就不完全是社会底层民众自己造成的。作家如果仅从社会底层民众身上寻找原因,就不可能深刻把握这种社会底层民众的苦难的历史根源。
其次,广大作家可以集中反映社会底层生活,但却不能完全局限于这种社会底层生活,而是应从这种社会底层生活出发而又超越这种社会底层生活。广大作家只有既有入,又有出,才能真正创作出深刻的文学作品,才能达到高远的艺术境界。可以说,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的一些似是而非的含混概念是一些文艺批评家刻意回避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的结果。这种理论不彻底的文艺批评既不可能把握中国当代文艺的未来,也不可能推动中国当代文艺的科学发展。
因此,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对这些似是而非的含混概念的批判和驳斥至关重要,既可以促进当代文艺的科学发展,也可以在推动当代文艺批评的有序发展中发展。
再次,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在梳理和总结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发展时既不能过于看重文艺批评家的社会身份,也不能过于重视文艺批评的社会影响,而是主要看文艺批评在这一有秩序的进程中的位置。
也就是说,中国当代文艺理论梳理和总结文艺批评既要看到文艺批评满足现实需要的程度,也要看到文艺批评在文艺批评发展史中的环节作用,并将这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文艺批评家积极推动了中国当代文艺的发展。但是,有些文艺批评却将中国当代文艺引入歧途。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有的文学批评家提倡分享艰难的文学,认为:“中国的发展乃是当代历史最为重要的目标,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之中,为了社群的利益和进步的让步和妥协乃至牺牲都似乎变成了一种不得不如此的严峻选择,分享艰难的过程是比起振臂一呼或慷慨激昂更为痛苦也更为坚韧的。”这种文学批评不过是迎合中国当代历史发展的邪路而已。21世纪以来,不少有身份有影响的文艺批评家在文艺批评中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中国当代文艺造神运动,打造了一座又一座的中国当代文艺“高峰”。有的文艺批评家把喜剧演员赵本山与世界喜剧艺术大师卓别林相提并论,认为赵本山和美国的卓别林是东西方两株葳蕤的文化大树,赵本山是从草根文化成长起来的葳蕤的文化大树。有的文艺批评家则宣称赵本山争到了农民文化的地位和尊严,悄悄地进行了一点点农民文化革命。有的文学批评家认为作家阎连科的长篇小说《受活》丝毫不逊色于长篇小说《百年孤独》,而女作家严歌苓的长篇小说《小姨多鹤》的文学成就则远远高于长篇小说《百年孤独》。有的文学批评家已不满足于把作家莫言和卡夫卡相提并论,而是认为莫言超越了卡夫卡,而作家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秦腔》则在美学上超过了中国古代长篇小说顶峰《红楼梦》。不少文艺批评家在这种打造中国当代文艺高峰的造神运动中不仅与那些有地位有影响的作家艺术家形成了相互取暖的利害关系,而且攫取了额外利益并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他们的狭隘目的。这些文艺批评虽然是恶劣的,但却在日趋恶化的当代文艺生态环境中占尽了风流。这严重地干扰甚至破坏了当代文艺批评的有序发展。因此,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应激浊扬清,清理这些影响恶劣的文艺批评,改善日趋恶化的当代文艺生态环境,在推进当代文艺批评的有序发展中发展。
然而,有的文学批评家却宣告了元理论的终结,认为只有那些只是对文学批评的概括和归纳的具体文学理论。这位文学批评家指出,在欧美的文学批评活动中,“文学原理”常常只是对文学批评的概括和归纳。而“国外文学理论的这些发展,有供我们借鉴之处”。这虽然没有完全否定那些国外的文学理论,但却认为“文学原理”只是对文学批评的概括和归纳。这种“文学理论”不仅无法甄别文学批评的优劣高下,而且将在根本对立的文学批评中无所适从。这些文学批评家强调,不是文学批评为文学立法,而是文学作品为文学立法。文学批评家在面对具体的文学创作、具体的作品文本时要抛开所有的理论成见,既不能拿着理论的条条框框教条化地去硬套具体的文本,也不能用既定的理论去要求作家照样创作。这不仅难以甄别文学作品的价值高下优劣,而且从根本上阉割了文学批评的规范功能。有的文艺理论家甚至认为文学理论是无力解读文学文本的,提出超越普遍的文学理论的文学文本解读学,关注个体而非类型,与西方当代文艺理论一较高下。这是站不住脚的。意大利现代艺术批评史家里奥奈罗·文杜里在把握艺术史、艺术批评与美学之间的关系时强调艺术史、艺术批评和美学这三种学科的统一,反对它们的分离,认为艺术史、艺术批评与美学这三种学科的分离就将使得它们变得空洞无物。里奥奈罗·文杜里在把握美学与艺术批评的关系时深刻地指出:“假使批评家惟一依靠的是他的感受,最好还是免开尊口。因为,如果抛弃了一切理论,他就无法确定自己的审美感受是否比一个普通路人的更有价值。”这样,“任何个人的爱好都可以有其历史地位,无所谓判断上的真实或虚假,审美趣味上的优良或低劣了。那么艺术史也不再成其为历史,不过是一堆材料广博的纯粹史料。”英国当代文艺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指出:“倘若没有某种理论,且不说这种理论是何等抽象和含蓄,我们首先就不会知道什么是‘文学作品,或者我们如何去阅读它。”这就是说,如果没有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家就无法甄别出真正的文学作品,遑论在众多的文学作品中判断出这些文学作品的价值高下优劣。
因此,无论是文艺理论应该更多地指向具体的文艺批评发展论,还是文学文本解读学,都是当代历史碎片化的产物,绝不可能成为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发展的科学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