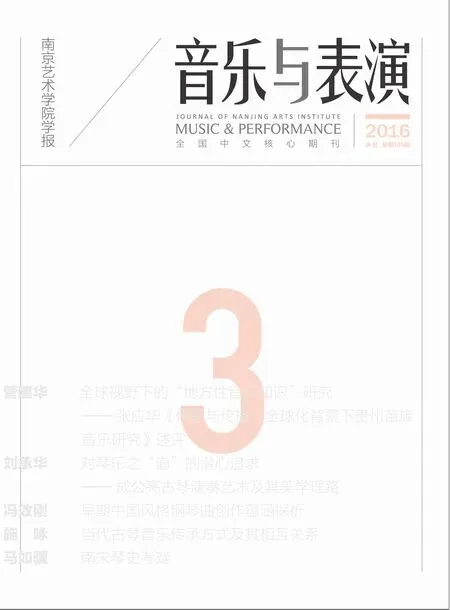感性的回忆—— 城市音乐文化叙事漫谈
2016-04-04西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陕西西安710061
崔 莹 (西安音乐学院 音乐学系,陕西 西安 710061 )
感性的回忆—— 城市音乐文化叙事漫谈
崔 莹 (西安音乐学院 音乐学系,陕西 西安 710061 )
本雅明探讨的“游荡者”在城市生活中的“惊颤体验”,揭示了现代人的作为一种感知的心里机制,而这样的心里机制是建立在“游荡者”对一连串的文化符号的“感性的回忆”之上的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感性的回忆”是当下城市文化研究的一种后现代方式;认为这种方式是建立在“能指与所指的分离”和“伪语境”的社会特征的基础之上的。并且认为伪语境是现代城市生活的一种典型的现象,多元文化符码在各种伪语境中以一种感性的姿态存在,而“惊颤的体验”和“感性的回忆”就发生在大众与多元文化符码的瞬间相遇之中。
感性的回忆;惊颤体验;游荡者;城市文化叙事
一、解读本雅明
波德莱尔的诗歌也许是城市叙事的源头,以一种感性地、碎片化地诗意的方式展示了具有现代性的城市的意象。然而真正将城市文化作为一种研究则还是在瓦尔特·本雅明。本雅明继承了唯美主义的感性呈现和碎片化,即一种关于城市的文化叙事——直接切入研究对象,从生活的感知中获取对社会的更深层次的体验,字里行间总是流露出一种生命的存在。正如阿多诺在《本雅明书简》的序言中所说:“本雅明的个性从一开始就是他作品的介质,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个性中的执著于生命之直接性的精神。”“无论是对自我还是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上,本雅明都怀着他的直接性精神义无反顾地直接切入到所发生的事物中。”[1]的确,在这种叙事风格的基础上,他的思想总是潜藏在一系列感性的记忆之中,在对事物的体验过程中,真理总是使人惊觉地、零星地闪耀在那一个个感性与思考交织的星丛之间。在《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的巴黎》中,本雅明透过波德莱尔的诗看到的不仅仅是巴黎都市中的繁华与奢靡,他更加从对巴黎的体验中感受到了一个真实的存在:在一系列碎片般的感知意象中,受人凌辱的乞丐,孤独无援的老人,丑陋老迈的娼妓,苟延残喘的病人、赌徒、小偷与僵尸与巴黎那五光十色的魅影交织交融,这些意象显现出一个另类的巴黎,“恶之花”正是对这种意象的最好描述。本雅明对波德莱尔的研究“试图描述和说明19世纪人的经验和感知方式发生的变化。因此波德莱尔关注的只是切点和材料,而不是分析的对象”[1]。本雅明总是从对一种事物感性描述,进而将它纳入到深层的社会学分析,洞察这些现象背后的意义。正如他描写巴黎的拱廊街一样,并不是对这一建筑的研究,而是通过对拱廊街的研究使得在商品拜物教下的城市文化尽显无疑。然而他的所有论著都不是体系化的呈现,而是一种类似“废墟”般的,碎片化的呈现。本雅明总是在一系列对于城市的感性意象中,把握事物的意义。
黄凤祝在他的《城市与社会》当中提到本雅明的这种叙事方法,认为“感性的记忆作为研究城市的历史媒介,作为写作手段,是法国作家普鲁斯特提出的理念和方法。本雅明把马克思的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和普鲁斯特的深层记忆挖掘理论融合,作为自己研究和批评历史的方法”[2]。本雅明在普鲁斯特的“感性的记忆”和波德莱尔的诗歌中得到启发,形成了他“启明”式的叙事,透过波德莱尔的诗歌、巴黎的“拱廊街”、“单行道”以及“机械复制的时代”本雅明揭示了现代城市人的心理机制。正如波德莱尔所说:城市是现代性的产物,而“现代性就是过度、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3]现代人的确对于任何新事物都会有一种非常快速的反应和接受的心理机制,“惊颤体验”是瞬间的体悟。而这种心理机制是由快速发展中的城市塑造的。对于城市文化研究来说,抓住这样的心理机制是十分必要的。本雅明在描述19世纪的巴黎中的拱廊街、单行道和在艺术中给人们造成的“惊颤”,以及机械复制的年代并不是已经逝去的记忆,而是正在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活生生的感性的记忆。现代性的城市正在我们的周围发生。
通过“游荡者”①“ 游荡者”是指:“漫步于人群并不是出于日常的实际需要,而仅仅是为了追求漫步于人群所带来的这种刺激:不断遭际新的东西,同时又不断对之作出快速反应。这是现代社会在人身上所造就的一种特有心理机制。休闲逛街者漫步于人群就是为了寻求这种刺激”。“‘游荡者’与人群中走动的其他人不同,他们虽然置身人群,但又与挤在一起的人流保持了一段距离,他们不想在人流中完全失落自己,他们要去观察和体验自己是怎样被人流簇拥(惊颤),同时又是怎样快速觅得自己空间的(对惊颤的消化),在这种不断克服惊颤的体验中,他们也体验到了自己于其中做出快速反应的生存能力,体验到了自己作为一个个体如何在势不可挡的大众中获得了一席之地。”引自:(德)瓦尔特 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M].王才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在城市生活中的“惊颤体验”②“惊颤体验”是指:“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则将个体置入到了一个别无选择地必须快速去应对不断出现之新现象的境地。随着新事物的不断被快速消化,人的心理机制层面也就渐渐生成了一种快速反应能力,这种能力源出于都市中的人群这一现代社会特有的现象。”引自:(德)瓦尔特 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M].王才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本雅明揭示了现代人的作为一种感知的心理机制,而这样的心理机制是建立在“游荡者”对一连串的文化符号的“感性的回忆”之上的。
二、“感性的回忆”作为城市音乐文化叙事的媒介
(一)“感性的回忆”作为城市音乐文化叙事如何可能?
有人会问:这样从感知意象切入的方法是否是科学认识知识的方法,这种叙事得出的知识是否正确。其实,这样的问题已有较成熟的探讨:在哲学领域,有现象学的转向;在人类学领域,有第三次民族志写作“从反思以‘科学’自我期许的人类学家的知识生产过程”的争论;亦有后现代哲学家罗蒂指出的“对一种知识论的渴望,实际上是对束缚的渴望——渴望获得某种可以依赖的‘根基’、某种不许逾越的框架、某种自我强加的目标以及某种不容否认的表征”[4]的著名论断。正如桑顿所强调的:民族志的基本问题是如何运用“撰写”让“日常”与“历史”和“环境”发生关系。某种程度上说,在反本质主义的基础上,当代民族志写作没有任何宏大叙事的追求,唯一遵循的原则就是保有“真诚的底线”。而这首先就要超越传统认识论,无论我们是否承认,这样的看法正作为一种与现代主义不同的世界观悄然形成,它并不是一个历史时期,它甚至与现代性并存过,它就是一种看待世界的另类的眼光。在这样的眼光中,人们生活在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共存的关系网中,强调这种关系是内在的、本质的,构成性的。在生活与历史中并没有必然的规律存在,真正存在的是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之中,人的生活是受到各种因素影响的,而这种因素的发生是不确定的,只有在动态的过程中,我们能够把握那些许的真谛。因此,后现代要求多元化、多视角、跨学科,它更关注的是活生生的过程。通过描述他者的存在,阐释自身,任何个体都是生活在一个活生生的关系场中,总是在与他人、他物发生关系中显现自身的。与普鲁斯特小说的叙事一样“我与非我的界限是可以逾越的。要写此物时,必先写彼物对此物的反映,世界的事物总是彼此联系在一起。没有绝对的自我,也没有绝对的无我。”[5]于是在这种“活性”的研究中,主客二分的界限在不知不觉中被超越、被抹平,只有一个活生生的世界。于是,在这样的一个复杂的、不确定的场域中,作为一个生活在城市中的我对城市的感性体验是最为真实的。
(二)“感性的回忆”运行的机制是什么?
“惊颤体验”作为研究现代人心理机制典型特征,这种心理机制在当代城市文化叙事中具有两个特性:“能指与所指的分离”和“伪语境”。
1、“能指与所指的分离”导致城市文化“符号化”
在这样一个多元和新事物层出不穷的都市中,人们学会了快速的反应和接受,但是这种接受和反应并不是对于意义的反应,而是对于符号形式的一种反应。在一个多元文化的场域中,每个人对于所接触到的陌生文化的内涵都不是明晰的,对于新鲜事物或陌生文化,只是对于能指的感知,当我们的文化背景缺乏对一种文化的内涵的了解时,我们只能关注该文化所显现的形式,只能够把它作为文化符号来进行形式上的体验。如色彩、线条、结构等成为体验的中心,也就是显现为客观事实的文化能指。而当我们能够把能指与所指相互联系起来后,产生的审美又与之前的纯形式的审美不同了。而且当进入一种文化意义域之后,即找到了关注对象所在文化场中的位置,以及它与场中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后,观察者——“我”也成为场中的一元,对象对于我来说,不再是刚才与我无关的被动关系。进入文化场中后,“我”也成为影响对象存在的一个因素。然而,在飞速发展的现代城市中,在对扑面而来又迅速消化的“惊颤”中,人们没有进入所指的时间,当一个能指漂浮而至时,人们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反应,下一个就要来临了。于是在城市中,多元文化对于大众来说就是多元的文化符码,这些符码对于我来说只有现时的意义,而它的文化所指及内涵与我无关,与我有关的是有当下迎接各种符码的“惊颤体验”。是一种被动地迎接而后迅速地忘却。
在现代都市中,艺术不再是那受人顶礼膜拜的对象,艺术也不再是古典、浪漫等一系列理念的化身,在当代,艺术就是艺术本身,艺术要表现的是“一种欲望,活生生的人的具体的欲望”。在文化工业的时代,大众文化是主角,对于大众来说,大众艺术的特点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秀”,也就是展示的艺术作品。艺术沦为失去光晕的东西,是大众与城市共同塑造的结果。人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欣赏到这些艺术作品。这正是法兰克福学派所说的,在资本操纵的社会中,人们承受着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人们最需要的不是一个深奥的让他要费时费力去搞懂的东西,而是一个摆放在眼前的,不用动脑筋就可以娱乐和消费的东西。而大众文化正是抓住了这样一个契机。詹姆逊把后工业社会的大众文化概括为五种差异的消失,它们是:(1)内部和外部的差异;(2)本质和形象的差异;(3)弗洛依德无意识和显意识的差异;(4)存在主义真实性和非真实性的差异;(5)能指和所指的差异。因此,对都市当中的现代人来说,对于周边发生的一切事情,早已形成了一种肤浅的接受,甚至是一种肤浅的消费。音乐与其他艺术一样都是作为一种表象的消费而存在。当艺术作为一种文化符码展现在“我”的面前的时候,“我”本能的体验着的是那纯粹的躯壳。正如本雅明在《普鲁斯特的形象》中所说:“我们脸上的褶皱登记着激情、罪恶和真知灼见的一次次造访,然而我们这些主人却不在家”。[6]
2、“伪语境”的产生
由于能指与所指的分离,造成的后果就是文化符号脱离文化意义,城市化使得文化脱离了原有文化生态,成为文化符号的存在。我们可以借用波兹曼提出的概念:“伪语境”来概括城市文化。所谓“伪语境”是当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提出的概念,“源于电报和摄影术的一个更重要的产物也许是伪语境。伪语境的作用是为了让脱离生活、毫无关联的信息获得一种表面的涌出。但伪语境所能提供的不是行动,或解决问题的方法,或变化。这种信息剩下的唯一用处和我们的生活也没有真正的联系。当然,这种唯一的涌出就是它的娱乐功能。伪语境是丧失活力之后的文化的最后的避难所。”[7]这个“伪语境”在波兹曼的文章中,指的是为了让那些由报纸和电报以及摄影技术共同产生出来的“与我无关”、在社会中没有赖以生存的基础的各种无用的信息,提供一个存在的语境,让它能够充分地在大众文化中发挥娱乐大众的作用,从而赚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在波兹曼看来,美国当时社会中存在的“纵横字谜”,广播电视竞赛和现代电视游戏比赛之类的东西都是一种“伪语境”,在这样的语境下,那些大量“与我无关”的信息,变得开始“与我有关”了。的确,在这样的“伪语境”中,报纸、电视、网络、广播中充斥了大量的无用信息,而这些信息最大的作用就是——娱乐大众。大众在电视中看到的所谓各国的文化和各民族的生活习俗,以及各地正在发生的事情,对于大众来说,仅仅是一种娱乐消费,这些大量的信息与我的关系,仅仅存活在打开电视和关闭电视的那段时间中而已。网络上也是如此,即一种娱乐消遣的消费。将“伪语境”放在城市文化研究中来思考(其外延可能要比波兹曼的观点更为宽泛),我们发现在城市生活中到处都充满了“丧失活力”的文化符号,大量的文化符号通过各种媒介充斥在城市生活中,媒介对于我们来说,并不仅仅是媒介,媒介的重要性则是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又一个的语境。而更为关键的则是在现代城市中,大量地充斥着这样的“与我无关”的符号信息。因此,对于在社会中没有赖以生存的基础的各种所谓多元文化,并不是向学者们想象的是一个真正的多元文化全球化的世界。所谓全球化进程,实际上,是各种媒体的联合制造,在产业化和商业化的进程中,多元文化的全球化为各种媒体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了一个文化符号的“伪语境”。因此所谓的多元文化的全球化,可以说是多元文化符码的全球化。在各种媒介的传导之下,大众娱乐的是多元文化的符码而不是符码背后的文化意义。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城市逐渐进入了“娱乐的时代”,对于城市音乐研究的范畴来说,不管是来自民间的还是传统的音乐,也不管从哪个角度去探讨这些音乐的城市化过程,只要它们走向城市就必然逃不开大众文化的影响。而大众文化则是现代性的产物。由于现代性的内在要求是唯美主义和消费主义,唯美主义导致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而消费主义导致艺术的产业化、商业化及其市场化。因此,趣味与市场在城市文化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
随着文化工业的逐渐成熟起来,各种文化艺术被吸入到商业化运作中,音乐也是如此。在中国的城市生活中,大众开始走向日常生活审美化,它主要体现在市民音乐会和免费的博物馆参观和各种美术展览等等。
随着城市中音乐会文化的产生,大众对听音乐会抱有不同的目的。在这些音乐会中,不可否认,有少数人的确是音乐的爱好者,但是大部分去观看音乐会的大众潜意识却并非如此。在这样的音乐会中,人们依照所谓的“西方惯例”,走进音乐厅中,开始准备经历一场并不熟悉的文化符号的狂轰滥炸。某种仪式感比音乐本身更加重要。在这样的音乐会上,即便是少数的音乐爱好者们,也并不能真正进入文化的所指,纯粹感性的愉悦也许更为重要。当然也不能排除那些真正了解音乐文化的人,但是这样的人在大众之中只是“小众”而已。
在传统音乐、民间音乐的城市化进程中,也体现了这样的分离,传统音乐对于现代城市人来说,更是一种文化符码,现代化的城市中,传统文化所赖以生存的基础已经不存在了,留下来的是文化的躯壳。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更多的是停留在表面的能指。而民间音乐也是如此,离开了真语境的民间音乐在城市中,找不到它赖以生存的土壤,在大众文化中,民间音乐被“艺术化、舞台化和专业化”,“乡村之‘乐’要以音乐会的形式上演,则改造的内容包括曲目的选择(套曲的解体),乐队的排列(仪式场域的解体),唱法的科学性(嗓音的重构)……如此等等。”[8]。
对于城市音乐研究正如在萧梅老师的文章中引用的两段话,引发了我对城市音乐文化的再思考,其一是她引用赖斯的一段话:
在现代性中,民族音乐学家把它们自己看成是世界主义者,在全球的空间自由地移动和操作,这个空间在很大程度上(至少在概念和方法上)对于我们所研究的地方文化来说,对于这些传统的当事人来说是难以进入的。在现代性中,我们能够到他们那儿旅行,但他们却不需要来到我们这儿;他们的经验是地方化的,而我们的是全球化的。[8]
另一段话是她讲述哈萨克小伙“米兰别克”的故事时,引用电台主持人魏小石的话:
城市的体验让米兰别克开始深入接触 “民族”风格。也许很多人会有疑问:同样是新疆来的音乐家,为何在走出家乡时才开始拓展视野去聆听 “民族音乐”呢?由此,我们值得思考的是,“民族音乐”这个概念到底植根于何处?是什么人群在用何种方式去体验 “民族音乐”?[8]
我不敢妄自揣摩作者的意图和观点,但我从这两段话中读出了某种时隐时现,似是而非的东西,一种城市化带来的现代性问题。然而,我并不是要批判现代性的问题,现代性问题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能阻止城市化的进程,但我们必须清楚,城市化的进程是怎样实现的。
基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关系,萧梅老师在文章中阐释了另外一种思路:“在这个表面上看来有着相反路向的背后,共享着同一个思维框架,那就是传统与现代的两分或对立。”[8]传统与现代除了对立是否可以找到一个相同的路径,这个路径存在于米兰别克的音乐中,存在于民谣风格的流行音乐中,存在于具有传统音乐素材的管弦乐曲中,存在于各种“伪语境”的场域中。通过“摆渡”我们可以穿向“乡村”,可以穿向“城市”,而这种“摆渡”不是别的,正是那由一个个文化符号引发的“感性的回忆”——对乡村的回忆、对传统的回忆、对地方化情感的回忆,这也许就是城市文化叙事的所在。正如谭维维的《给世界一点颜色》是很好的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乡土与摇滚的结合的音乐作品,音乐在华阴老腔和摇滚风格之间“摆渡”,当代的摇滚承载着古老的文化符号,这无疑是一个成功的作品。然而我要说的是,华阴老腔还是华阴老腔,华阴老腔并没有因为谭维维的摇滚植根于城市人的文化中,它之所以被人接受,是因为它和摇滚乐的碰撞,是一场“惊颤的体验”,一场地方化的“感性回忆”。同时,也是一场文化符号的异延、增补然后留下踪印。
作为一个研究城市文化的人,一个“游荡者”,他游离于多元文化的符码之中,以一种最基本的反应面对它。“迎接”、“惊颤”,然后“回忆”。当然,在这样多元文化符码川流不息的城市中,要想保存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的根基是难的,保存下来的以及人们能够体验到的也仅仅是文化的躯壳而已。特别是在城市中,除了自己熟悉的语境外,面对其他文化的存在,就是当下的“惊颤”以及随之而来的“感性的记忆”。于是“伪语境”不再是文化批判的对象了,他是城市文化一种独特的保有与“传统”和“乡村”相通的一个路径,在不同的文化伪语境中,勾起的是一个个“感性的回忆”。
而与民间或传统音乐在城市的境遇不同,还存在另一个“伪语境”,即为了给“与我无关”的各种多元文化的符码提供一个“与我有关”的语境,只有使多元文化符码作为一种娱乐,形成一个趣味的语境,它就是主题吧文化。
不论是酒吧、茶馆文化还是各种主题吧的文化,正是来自不同文化,不同时代的符号文化,在这些场所中,人们消费的环境,是一种由主题性文化符码造就的氛围,而这种氛围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语境。当人们穿梭于各个主题性的酒吧时,经历的是多种文化的洗礼,在对各种符码的惊颤体验中,体味着魅惑的城市和落寞的回忆。
伪语境是城市生活的一种典型的现象,它的出现首先是因为在城市中充斥着大量的能指与所指的分离的文化现象,这些分离的文化符码与现代人的生活没有关系,也没有赖以生存的基础。因此在这样的语境下,多元文化符码在大众的视野中仅仅是以一种感性的姿态存在着的,“惊颤的体验”发生在大众与符码相遇的语境中。
综上所述,伪语境是由能指与所指的分离造成的,而能指与所指的分离又是由现代人的心理机制所造成的,本雅明认为,光韵在人们的“惊颤的体验”中消逝了。而光韵又重现在“感性的回忆”中,在对过去记忆的理性反思中,能够重新获得某种现代人缺失的对光韵的追求。对于城市中的个体来说,多元文化共存不是一个宏大叙事,我以我的方式生活,一种我所选择的方式生活,每个人都是一元,在真正的生活中,人们遵循的是属于自己的一元的轨迹。这轨迹交错纵横,共同组成了一个如此包容的城市。不管是感性地观察这个城市,还是描写城市人的感性存在,“感性的回忆”正在发生:人们在行色匆忙中,贩卖音乐的小摊上传来的声响令人“惊艳”,街头艺人那不够精准的琴声令人“感动”,时不时钻进耳朵的手机音乐让你不经意间了解了陌生人的趣味。买茉莉花的奶奶唱起的《茉莉花》,声音尖锐而颤抖,但对于此时此刻正在街头游荡的闲逛者来说这些确是一场温暖而短暂的“感性的回忆”。于是,这疲惫的生活因此有所不同,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城市。
[1]王才勇.本雅明“巴黎拱廊街研究”的批判性题旨[J].哲学研究,2007(10).
[2]黄凤祝.城市与社会[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
[3](法)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M].郭宏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485.
[4](美)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M].高丙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5](法)马赛尔·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M].罗大纲,代序,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6](美)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M].张旭东,王斑,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227.
[7](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01.
[8]萧梅.摆渡与边际——城市音乐体验二题[J].音乐艺术,2013(1).
[9](德)瓦尔特·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M].王才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王晓俊)
J601;J607
A
1008-9667(2016)03-0019-05
2016-01-14
崔 莹(1979— ),女,陕西宝鸡人,博士,西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师,研究方向:音乐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