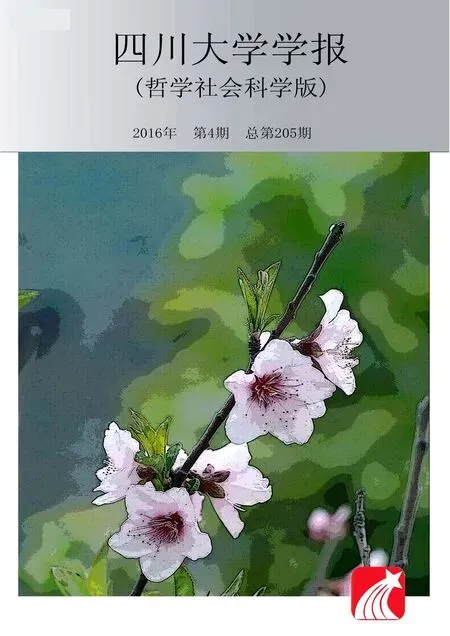刑法中的“可能明知”
2016-04-04钟朝阳
钟朝阳
§法学研究§
刑法中的“可能明知”
钟朝阳
摘要:“可能明知”作为明知的一种特殊形态,意味着降低证明标准,因此它具有特定的内涵、对象和适用范围,其理论基础包括刑法的严格责任、传统故意理论的“认识说”和“明知”的层次性内涵。“可能明知”已经在侵害未成年幼女的犯罪中被“两高”的司法解释所确认。应当结合实体法中证明责任分配的刑事政策、证据距离、公平、效率等因素,扩大“可能明知”的适用范围。
关键词:明知;可能明知;刑事政策;证明标准;证明责任
“明知”是诉讼证明的难点。我国司法解释向来把明知解释为“知道或应当知道”,表明控方对明知的证明标准很高,行为人一旦辩称“不知”,控方往往陷入证明困境,最终不得不依赖口供。为了缓解明知的证明困境并贯彻特定的刑事政策,近年来“两高”通过司法解释在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罕见地以“可能明知”入罪。由此引出这样的问题:“可能明知”入罪的理论依据何在?证明标准的降低是否侵犯了无罪推定原则?等等,这些问题学界尚未关注。为进一步规范“可能明知”在司法实务中的适用,本文拟对有关问题展开分析。
一、“可能明知”的刑法界定
刑法典里并无“可能明知”的表述,司法解释里也比较罕见。但笔者认为,“可能明知”是刑法法理与刑事政策的逻辑结果,它不但存在于明确以明知为构成要件的个罪中,还存在于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但理解上却必须以明知为要件的个罪中。如拐卖儿童罪,刑法典并无明确规定但理解上却必须以明知受害人为不满14周岁的儿童为要件。因此,“可能明知”在刑法典里是客观存在的。但“可能明知”不能任意扩大,它有特定的内涵、对象和范围。刑法的“可能明知”有三个特定性:
第一,内涵特定。“可能明知”区别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在知的程度上低于后者,是明知的一种特殊形态。从语义上解释,“可能明知”是指“可能知道”“大概知道”“基本知道”等,是一种低盖然性的知,即行为人不知的可能性要大于知的可能性。但即便如此,法律仍然基于某种特殊的刑事政策把可能明知入罪,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该特殊法益受到不法侵害。这与刑法的严格责任相类似,但“可能明知”入罪不等于严格责任,即使行为人不知的可能性要大于知的可能性,但“可能明知”仍然排除不知,如果行为人确实不知,则不构成犯罪,故“可能明知”不能等同于严格责任。
第二,范围特定。刑法总、分则里明知的内涵不尽相同。“可能明知”仅是指刑法分则里对特定对象的明知,而不包括总则的明知。因为总则明知是对行为违法性和危害后果的明知,属于另一个理论话题,总则明知也叫“第二明知”,不在本文讨论之列。本文所述的“可能明知”仅限于对特定对象的明知,有学者称之为“第一次明知”。①台湾学者郑健才认为:“刑法总则上所称之明知,与刑法分则上所称之明知不同。前者,系作为基本主观要件之一种基础;后者则系一种特定主观要件。刑法分则之明知为第一次明知,刑法总则之明知为第二次明知。有第一次之明知,未必即有第二次之明知。”参见张明楷:《如何理解和认定窝赃、销赃罪中的“明知”》,《法学评论》1997年第2期。
第三,对象特定。“可能明知”也并非指分则里所有特定对象的明知,而仅限于那些体现特殊利益、需要刑法以特殊政策予以保护的少数法益,如在针对公共安全、环境卫生、食品药品、风俗道德、未成年人等领域内的犯罪。这类犯罪客体深受民众关切,危害后果严重又往往难以被证明,故应当通过“可能明知”来降低证明标准和入罪门槛,贯彻刑事政策,从而加大刑法的保护力度。
因此,“可能明知”只是“知道或应当知道”的一种特殊形态,它并非要全面降低明知的证明标准,只是在特殊犯罪、特殊客体中为了贯彻特殊的刑事政策而对主观要件的证明标准的降低,其内涵、范围和对象均有严格的限定性。
二、“可能明知”入罪的曲折历程
“可能明知”入罪经历了一段曲折历程。在2001年之前,刑法和司法解释都没有“可能明知”之说,但自2001年6月起,“可能明知”陆续在有关幼女保护的司法解释里出现,但过程并不顺利。
(一)2013年之前“两高”对嫖宿幼女罪中是否以“可能明知”入罪存在分歧
2001年6月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最高检)颁布《关于构成嫖宿幼女罪主观上是否需要具备明知要件的解释》【高检发释字[2001]3号】明确规定“行为人知道被害人是或者可能是不满十四周岁幼女而嫖宿的,适用刑法第360条第2款规定,以嫖宿幼女罪追究刑事责任。”自此,“可能明知”首次由最高检以司法解释的方式提出。
但最高检的意见并未得到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法)的积极响应,相反,最高法于2003年1月17日在回复辽宁高院《关于行为人不明知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而与其自愿发生性关系,是否构成强奸罪问题的请示》【法释[2003]4号】时,明确答复“行为人明知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而与其发生性关系,不论幼女是否自愿,均应依照刑法第236条第2款的规定,以强奸罪定罪处罚;行为人确实不知对方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未造成严重后果,情节显著轻微的,不认为是犯罪。”虽然最高法把“确实不知”排除在外,貌似尊重法理,但最高法坚持只有“知”和“不知”之分,没有“可能明知”之说,表明了最高法不赞成以“可能明知”入罪的态度。可见,“两高”在“可能明知”入罪问题上是存在分歧的。
(二)从2003年至2013年的十年间,社会各界不断呼吁法律给予未成年幼女以特殊保护,促使“可能明知”入罪逐步成为司法界共识
一是嫖宿幼女罪本身令学界和民众越来越难以接受。不少人认为刑法第359条第2款的嫖宿幼女罪本身应当废除,因为该罪的处罚轻于强奸罪,不利于保护未成年幼女,“重罪轻判”,特别是2009年发生在贵州习水的5名公职人员“嫖宿幼女案”,最后法院以嫖宿幼女罪而不是以强奸罪对5名公职人员定罪量刑,此案更是令全社会对嫖宿幼女罪的反感。
二是嫖宿幼女罪入罪门槛高,导致实践中时不时发生行为人因嫖宿幼女而逃避法律制裁的案例。如就在最高检于2001年颁布以“可能明知”入罪的解释后,2002年仍然有人以“不知道对象是幼女”为由而逃避法律的制裁。*2000年2、3月间,被告人周某、张某因多次嫖宿幼女刘某被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法院以嫖宿幼女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和3年,两人以“不知道刘某是不满14周岁的幼女,其行为不构成嫖宿幼女罪”为由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被告人以相同理由继续申诉,2002年8月6日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撤销(2001)常刑终字第72号刑事裁定和武陵区人民法院(2001)武刑初字第53号刑事判决,改判周某、张某无罪。参见熊选国:《组织 强迫 引诱 容留 介绍卖淫罪——刑法罪名适用指南》,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0页。事实上贵州习水的嫖宿幼女案,如果不是引起了全国关注,这5名公职人员很可能同样以“不明知”为由逃避法律制裁,能否构成嫖宿幼女罪都是未知数。原因在于:嫖宿幼女罪中对幼女年龄的明知,通常理解为“知道或应当知道”,由此加大了控方的证明难度。
三是最高法不承认“可能明知”的解释受到学者和社会各界的批评。如针对上述司法解释有知名学者发表批评性文章,认为“这一解释是错误的,不仅这一解释理论违背法理,而且违背保护14岁以下少女这一相对弱势群体的基本公共政策。”*苏力:“一个不公正的司法解释”,2007年5月22日,http:∥www.chinalawedu.com/news/16900/176/2004/2/zh443187341212400239728_83126.htm,2015年3月20日。此文在学界引起较大反响,也促进了学界和司法界对明知内涵的反思。
四是面对社会各界要求给予未成年幼女以特殊保护的呼声,最高院开始作出积极回应。如全国人大代表孙晓梅从2010年开始持续提出取消嫖宿幼女罪的建议,至2013年7月30日,最高院在《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3939号建议的答复》中表示,完全赞成孙晓梅代表提出的废除嫖宿幼女罪的建议,并表示希望能够与社会各界共同推动全国人大法工委尽快立项废除该罪名,最高法个别领导还表示“无论从法理上,还是从未成年人保护层面,废除嫖宿幼女罪都有充分理由。”*邱伟:“最高法表态:赞成废除嫖宿幼女罪”,2013年12月8日,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3-12/08/c_118466865.htm,2015年3月18日。
五是嫖宿幼女罪被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废除。2015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沈跃跃和多名委员纷纷提出取消嫖宿幼女罪的建议。*人民网:“人大常委呼吁取消嫖宿幼女罪刑法修正稿未采纳”,2015年7月9日,http:∥news.china.com/domestic/945/20150718/20035893.html,2015年7月20日。2015年8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6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其中第四十三条正式废除嫖宿幼女罪。
嫖宿幼女罪成为众矢之的并被成功废除的背后,是普通民众、学者、民意代表等社会各界对幼女身心健康的特殊关切。这股主要来自民间的法益诉求,是推动“可能明知”入罪的强大动力。
(三)2013年10月最高法等机关正式颁布司法解释,确认所有性侵未成年人的犯罪均适用“可能明知”
就在最高法向全国人大作出上述《答复》后不到两个月,2013年10月13日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颁布《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其中第19条第3款规定:“对于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被害人,从其身体发育状况、言谈举止、衣着特征、生活作息规律等观察可能是幼女,而实施奸淫等性侵害行为的,应当认定行为人‘明知’对方是幼女”,第1条则规定,“本意见所称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包括强奸罪,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猥亵儿童罪,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引诱幼女卖淫罪,嫖宿幼女罪”。
该司法解释有两个核心内容:一是正式确认对未成年幼女年龄的明知,仅需达到“可能明知”的程度,二是“可能明知”的适用范围不限于已废除的嫖宿幼女罪,所有性侵未成年人的犯罪均适用。显然,该解释的适用范围比十年前最高检只适用于嫖宿幼女罪的解释范围更宽,从而回应了近十年来社会各界要求对未成年人予以特别保护的呼声,这也是“可能明知”入罪的社会基础和时代背景。
三、“可能明知”存在的理论基础
通过司法解释,“可能明知”解决了被承认的问题,但“两高两部”提出“可能明知”的解释正确吗?符合刑法的内在精神吗?可见,还需要解决“可能明知”存在的正当性问题。笔者认为,“可能明知”的正当性来自其理论基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刑法的严格责任理论
严格责任理论来源于英美刑法,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先是在特殊侵权行为领域出现绝对责任或无过错责任,规定行为人无论故意或过失,都要负赔偿责任,随着工业革命时期社会风险和危害后果的增加,无过错责任蔓延至刑法领域。早期英美刑法的严格责任实行的是绝对责任,随着社会的进步,严格责任由绝对责任向相对责任转变。由于严格责任的举证责任由公诉方转移到被告方,即实行举证责任倒置,故我国学者认为英美法的严格责任是一种推定责任。*刘仁文:《刑法中的严格责任研究》,《比较法研究》2001年第1期;李恩慈:《刑法中的推定责任制度》,《法学研究》2004年第4期。
目前,英国成文法中有大量规定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的立法,这些成文法主要针对公共福利犯罪、道德犯罪、环境污染犯罪等等,如《1861年侵犯人身权法》第55条规定诱拐不满16周岁的女孩脱离父母的监管构成诱拐少女罪。*根据《1861年侵犯人身权法》,1875年普林斯(Prince)被指控诱拐不满16岁的女孩脱离父母监管,该女孩名叫安妮·菲利浦斯,自称18岁,相貌也象16岁以上,但女孩的父亲证明其未满18岁。根据该法规定,该罪为绝对禁止之罪,被告人即使有合理根据相信他诱拐的女孩在16周岁以上,也不能成为抗辩理由。因此,陪审团以15:1的多数裁定被告人普林斯有罪。又如《1953年预防犯罪法》第1条规定,如果在公共场合携带武器一旦被证明,被告人有责任以盖然性平衡的证明标准证明自己获得合法授权或具有可信的免责理由。*Davis v Alexander (1970) 54 Cr App R 398.(“……if possession in a public place is proved, the onus is on the accused to prove on a balance of probabilities lawful authority or reasonable excuse for the possession.” )再如《1956年的性犯罪法》第30条规定一个男人故意以妇女卖淫收入作为全部或部分生活来源的,构成控制妓女卖淫罪等。这样的成文法还有《1875年的公共健康法》《1916年防止腐败法》《1953年预防犯罪法》等等,都规定了被告人的说服责任。据统计,目前英国至少制定了约29部有关控方证明责任例外的法律,此类犯罪有三个特点:一是危害不特定的多数人,二是主观要件的证明标准降低,三是实行证明责任倒置。
美国刑法典也有专门一节规定“损害道德罪”,规定了通奸罪和私奸罪,乱伦罪和诱奸罪等等适用相对严格责任。*储槐植:《美国刑法》,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20-231页。再如日本《儿童福利法》第60条第3款规定关于不知道儿童年龄方面的无过失也适用严格责任。*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刘迪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227页。可见公共福利犯罪、道德犯罪等领域,适用相对的严格责任和举证责任倒置,是目前法治国家的普遍做法。
“可能明知”虽然与严格责任并不完全相同,但严格责任理论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缓解控方对行为人主观方面的证明压力的本意,正好与“可能明知”的精神实质相一致。因此,刑法的严格责任理论构成“可能明知”的理论基础之一。
(二)刑法故意理论的“认识说”
关于犯罪故意的构成要素,大陆法刑法理论先后有“意欲说”“认识说”以及“容认说”等理论。*马克昌:《比较刑法原理——外国刑法学总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38-242页。在德国,一百多年来一直存在认识论与意欲论两种故意理论的争鸣,20世纪中叶以前,德国的古典刑法理论一直以意志因素作为故意的核心。但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认识说”逐渐取代“意志说”成为故意内涵的核心。*许玉秀:《客观的故意概念?——评德国的间接故意理论》,《政大法学评论》(台北)第48期,第51-54页。
德国故意理论的重大转变,与其证明制度的转变有深刻联系。自二战后,随着纠问式诉讼模式逐步让位于现代职权主义,一系列有关人权保障和程序公正的诉讼原则与制度,如无罪推定、沉默权、辩护权等得以确立,口供中心主义逐渐从德国刑事诉讼中隐退,从而增加了主观要件的证明难度。在此情形下,德国古典刑法理论发生重大调整,传统的“意欲说”这种强调行为人内心意欲、主观要件难以证明的理论,逐渐被强调客观外在表现的“认识说”所取代,如德国学者福利许(Frisch)认为:“具有对法所不能容忍的风险的认识,即有故意,不必要有意欲。”*许玉秀:《主观与客观之间——主客观理论与客观归责》,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第52页。德国的“认识说”有三个特点:一是强调行为人对不法后果发生之可能性的认识(“知”);二是承认“知”的程度存在差异性,其故意类型分为间接故意、不确定故意和未必的故意等等;*许玉秀:《主观与客观之间——主客观理论与客观归责》,第38页。三是有利于摆脱口供中心主义,更贴近诉讼证明。
再从日本刑法理论看,由于战后从英美法中吸收了大量的对抗制元素,又受德国刑法理论变革的影响,故“认识说”逐渐成为日本故意理论的主流,其中又进一步分为可能性说和盖然性说。可能性说认为,为了成立故意,只要认识构成要件的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就足够。盖然性说则是对可能性说的进一步修正,认为为了故意的成立,仅仅认识结果发生的可能性是不够的,认识它的盖然性是必要的。根据结果发生盖然性的高低,以此来区别间接故意和有认识的过失。*马克昌:《比较刑法原理——外国刑法学总论》,第242页。
德、日故意理论从“意志说”向“认识说”的转变,使明知取代意欲成为大陆法故意理论的核心,而“可能明知”正好相当于日本明知理论中的可能性说和盖然性说。可见,“可能明知”获得了大陆法故意理论的支持。
(三)“明知”内涵的层次性理论
随着明知成为英美法和主要大陆法国家构成要件的核心,明知的内涵也成为故意的核心。为何“明知”?“明知”需要“知”到什么程度?这些问题,催生了明知内涵的层次性理论。
明知内涵的层次性理论最早是英美学者提出的。由于英美对抗制诉讼构造向来不依赖口供定罪,其“双层构造”理论对明知的要求近似于今天大陆法的“认识说”,为方便明知的证明,英美法最早提出明知的分层理论,如美国学者珀金斯通过一个案例来阐释明知的不同程度:假设A以虚假陈述诱使B购买了一处不动产,对于A的陈述,B的心态有5种:(1)他意识到A的陈述可能是假的;(2)他也许相信A的陈述是假的;(3)他不能确定A的陈述是真的还是假的;(4)他也许相信A的陈述是真的,但理由不充分;(5)他相信A的陈述是真的,并且有合理理由。*罗林·M·珀金斯:《犯罪意图的理论基础》,孙潇洁、刘仁文译,《哈佛法律评论》,刘仁文、王桂萍编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52页。这段描述充分体现了英美学者在明知问题上的层次性思维。
明知的分层理论与美国刑法的明知理论又是一脉相承的。据储槐植教授介绍,美国刑法的“知”分为两类:一是有认识,二是无认识;其中有认识又分为三个亚类:即必然性认识、较大可能性认识和较小可能性认识。*储槐植:《美国刑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76页。可见,“较小可能性认识”显然正是“可能明知”。由此表明,我国司法解释刚刚被确认的“可能明知”,正是美国刑法理论关于明知的三种法定形态之一。
受英美法明知的层次性理论所启发,我国刑法学者也开始以层次性理论分析我国刑法中的明知,如有学者认为:“主观上的认识因素,存在‘确知’(肯定知道)和‘确实不知’两极。在这两者之间,根据认识程度的由强到弱,还分别存在‘实知’(事实上知道)、‘或知’(可能知道)、‘应知(应当知道)3种类型”。*周光权:《明知与刑事推定》,《现代法学》2009年第3期。还有人认为,他人对行为人主观认识的判断包括:“(1)肯定知道,(2)很可能知道,(3)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4)很可能不知道,(5)不可能知道”等五个层级。*张少林:《刑法中的“明知”“应知”与“怀疑”探析》,《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3期。无论对明知如何分层,“可能明知”都是其中的组成部分。这次“两高”司法解释对“可能明知”的认可,正是明知的层次性理论向司法实践的转化。
综上,“可能明知”并非无源之水,也不是我国最高司法机关的“独创”,而是刑法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的存在具有理论正当性和实践必要性。事实上,相比于法治发达国家,我国承认“可能明知”已经太晚了,为此已放纵了许多狡辩“不知”的犯罪分子。尽管由于我国至今没有确立沉默权,侦查机关仍然可以较为轻易地获取嫌疑人的认罪口供,故明知的证明问题可能尚未达到使诉讼证明难以为继的程度。但是,随着人权保护呼声的高涨,口供越来越难以获取,承认“可能明知”、降低主观要件的证明标准,也是大势所趋。
四、“可能明知”的证据法内涵
明知作为主观要件,其证明标准可以低于其他客观构成要件,这一点在证据法学界已取得共识。而“可能明知”作为明知的特殊形态,其证明标准更低,控方仅需证明至“可能”“大概”的低盖然性程度,即可满足定罪证明标准。相反,被告人如果要否认明知,则应当承担证明自己“不知”的证明责任。可见,“可能明知”对控方而言意味着转移证明责任、降低证明标准。由此引出一个重大问题:“可能明知”是否侵犯了无罪推定原则?是否不当加重了被告人的证明责任?
为了澄清这个问题,需要全面检视我国证明责任理论、审视证明责任与实体法的关系、并考察证明责任在实体法里的表现方式。
(一)“可能明知”丰富了诉讼法视角下的证明责任理论
我国诉讼法学界存在一个认识误区,以为证明责任理论是诉讼法学的专属“领地”,故在讨论证明责任问题时,难以跳出诉讼法视角来考察证明责任问题。而诉讼法视角往往就是无罪推定的单一视角。如刑诉法教科书普遍认为,被告人基于无罪推定原则“一般不承担证明责任,仅在法律有特殊规定的例外情况下承担证明责任”,*卞建林主编:《证据法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48页;樊崇义主编:《证据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282页。或者认为“控方要对犯罪构成要件承担证明责任,被告人无需对否认犯罪构成要件的消极抗辩承担证明责任,但需要对积极抗辩事由承担证明责任。”*纵博:《刑事被告人的证明责任》,《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等等。
这种平面的、单一视角的证明责任理论,往往很容易否认“可能明知”的存在,并轻易地给“可能明知”贴上侵犯无罪推定原则的标签。
但该证明责任理论存在这样的局限性:一是该理论仅仅是无罪推定原则的逻辑延伸,体现的是证明责任分配的总体性和原则性要求,故大多数情况下它难以具体指导个案的证明责任分配;二是该理论仅仅是在诉讼法的范畴内讨论证明责任分配,忽视刑事实体法中蕴含的大量证明责任分配的内容;三是在司法实务上,该证明责任理论往往不当加重控方的证明责任,不利于打击犯罪。
事实上,我国刑事司法难以摆脱口供中心主义,与我国证明责任理论长期与刑事实体法和司法实务严重脱节密切相关。由于证明责任理论的不发达甚至对实务的误导,导致我国刑事司法长期不得不依靠口供,使庭审流于形式,这也是对抗制庭审目标在96年刑诉法修改后难以实现的原因之一。因此,虽然研究证明责任理论的文章汗牛充栋,但现行证明责任理论确实存在局限性,难以具体指导司法实践中的证明责任分配,需要在新的视角下重构。
而“可能明知”深刻反映了刑事政策,更加贴近司法实务,其减轻和降低控方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的内涵,是对现行平面视角的证明责任理论的重要补充。
(二)“可能明知”促使证明责任理论转向刑事实体法
无罪推定只是规定证明责任分配的原则,而具体的证明责任分配的内容,则存在于刑事实体法之中,立法者也是通过证明责任在实体法中的具体表现来贯彻其意旨。因此,单一的无罪推定视角难以窥视证明责任分配的全貌,因为证明责任分配除了基于无罪推定原则外,还有其他因素诸如公平、政策、证据距离、诉讼效率等诉讼价值需要考量。虽然并非所有刑法分则条文都需要考量这些诉讼价值,但这些价值的存在确实使刑法规范中的证明责任分配不尽相同。刑法具体条文一旦考虑了这些价值中的一种或多种,对控方而言就意味着转移证明责任、降低证明标准,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证明责任“倒置”。
可见,“可能明知”中证明责任的倒置现象,是刑事实体法固有的规范技术,它本来就存在,与无罪推定无关,它甚至根本不考虑后者。如果从无罪推定的单一视角责难“可能明知”的证明责任倒置,反而是脱离实体法的本末倒置。因为包括无罪推定在内的整个证明责任理论的内涵,都要以刑事实体法的规范为前提。只有当刑法条文不需要考量上述诉讼价值时,才是无罪推定发挥作用的空间。
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存在先于实体法的证明责任分配,所谓的证明责任分配,其实就是对实体法的理解和适用。脱离实体法讲证明责任分配,既与证明责任理论的渊源不符,也与司法实务脱节。正如罗森贝克所言:“证明责任理论是法律适用理论的一部分,不仅仅证明责任分配原则源自于法律适用的方式,而且证明责任的具体分配同样源自于法律适用的方式。”*莱奥·罗森贝克:《证明责任论》,庄敬华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第12页。可见证明责任分配在本质上就是准确适用刑法。
虽然刑事证明责任与民事证明责任不尽相同,前者受无罪推定原则等多元诉讼价值所制约,但在尊重这些诉讼价值的基础上,并不妨碍刑事证明责任由刑事实体法来作出规范,这一点与民事证明责任的“规范说”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也正是在实体法层面上,证明责任理论才会显得纷繁复杂,责任分配的标准难以统一,如李学灯先生所言:“证明负担之分配……公平仅为重要理由之一,此外尚有其他法则上及政策上之原因。至于其如何分配,依各地之法律、及各家之学说,至为复杂纷纭。权威学者如维格摩尔等人,亦谓无统一不变之标准,且不能执一简单之法则以解决一切之案件。”*李学灯:《证据法比较研究》,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2年,第364页。此话才深谙证明责任分配的真谛,可见,证明责任分配主要由刑事实体法作出规范。
(三)“可能明知”是刑事实体法里证明责任的暗示性转移
诉讼法学界对证明责任的另一个重大误解,就是仅承认实体法中法律明确规定的证明责任转移或倒置,即所谓的法律推定。如有学者认为,“在无罪推定和控方承担证明有罪责任的原则之下,证明责任转移应当有法律依据。只有法律明确规定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时,才出现责任倒置或转移的情况。”*龙宗智:《推定的界限及适用》,《法学研究》2008年第1期。据此,认为我国刑法典里明确转移证明责任的法律推定只有两条,分别是刑法第282条非法持有绝密、机密文件资料物品罪和第395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笔者认为,这种对推定和证明责任转移的理解是不全面的。如果推定仅指法律推定,那么推定理论的复杂性与罕见罪名之间的反差也太大了,推定的研究性文章同样不计其数,如果仅有这两个罪名才是真正的推定,那整个学术界也未免小题大做。事实上,除了法律以明示方式转移证明责任的法律推定之外,实体法中还大量存在暗示性(by implication)转移证明责任的规范。理由如下:
首先,证明责任理论本身蕴含了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的内涵。如英美权威证据法学者彼得·墨菲(Peter Murphy)提出了这样一组概念,他认为:“证明责任(burden of proof)有两种基本分类,一种是‘法定性负担’(the legal burden),另一种是‘证据性负担’(the evidential burden)。法定性负担也就是证明责任,这种责任要求一方提出与争议事项有关的一个事实或一组事实。在一些案件中,与案件有关的一部分事实的法定性负担由一方承担,而另一部分事实的法定性负担则由另一方承担。”*Peter Murphy, editor-in-chief; His Hnour, consultant editor, Criminal Practice, Oxford UniversityPress, 2005, p.2165.(“There are two principal kinds of burden, the legal burden and the evdential burden. The legal burden is a burden of proof, that is a burden imposed on a party to prove a fact or facts in issue. In some case the legal burden in relation to some of the facts in issue will be on one party, and the legal burden in relation to anther (or other) will be on the other party.” )可见,墨菲认为证明责任是双方的、双向的,被告人有时对“另一部分事实”应当承担证据性负担,即被告人并非受无罪推定的无条件保护,而是需要根据不同情况,不仅承担行为意义的举证责任,还包括承担结果意义上的风险责任。
其次,英美证据法学者认为,英美法中存在一种证明责任的立法暗示(legislation implication)。如墨菲教授还认为:“成文法不但以明确地方式还以暗示性方式(by implication)把法定的证明责任转由被告承担。”*Peter Murphy, editor-in-chief; His Hnour, consultant editor, Criminal Practice, Oxford UniversityPress, 2005, p.2165.(“A statute can place the legal burden of proof on the accused not only expressly but also by implication”).
澳大利亚学者安德鲁(Andrew)也认为:“在刑事指控和民事诉求中的举证负担的分配,最终都是由立法机关颁布的成文法所决定的。……困难在于:首先,立法并无举证责任分配的明确规定,审理法官在决定举证责任分配时,需要考虑是否存在暗示性(be implied)的证明责任分配的规定;其次,即使表达了分配的意旨,它也是模棱两可或者不彻底的,审理法官必须决定何种分配效果是分配意旨中所要表达的”。*Andrew Ligertwod, Australian Evidence (4th edition), Lexis Butterworths,Austria, 2004,p.417.(“the allocation of the burdens of proof in criminal charges and civil claims brought under statute is ultimately a matter for the legislature .……difficulties arise, first, where there is no express reference to the allocation, in which case courts must determine whether any allocation may be implied from it is drafted; and second,where there is express reference to the allocation but this is ambiguous or incomplete,in which case the courts must decide what effect that express reference has upon the allocation.”)这段话包含三层含义:一是证明责任分配的内容最终是由成文法规定的。二是证明责任分配往往以暗示性的方式作出规定,而且是模棱两可和不彻底的。三是法官在考虑证明责任分配时,需要考虑成文法中的立法意旨。
再次,英美法的法官也承认证明责任的暗示性转移。如英国上议院和高等法院就鼓励并支持下级法院对立法意图中暗示性转移证明责任的解读。如据墨菲教授介绍,虽然权威的观点仍然是爱德华兹案(Edwards)*Edwards [1975] QB.27;[1975]3W.L.R.285.和汉特案(Hunt)*Hunt [1987] AC 352;[1986]3W.L.R.1115.的规则,但包括上议院首席大法官威斯康特勋爵在内的高等法院和上议院法官均支持“明示和暗示(either expressly or by implication)地把法定证明责任转移给被告人的成文法例外”。*Peter Murphy, editor-in-chief; His Hnour, consultant editor, Criminal Practice, Oxford UniversityPress, 2005, p.2165.
安德鲁教授同样介绍了上议院法官的相同态度:“(法院)还推定(assumed)说服责任也暗示性地转由被告人承担,而且上议院也认为这种推定符合伍尔明顿规则(Woolminton rule)。因此,存在通过立法暗示的方式把提供证据责任和说服责任同时转移给被告人承担的可能性”。*Andrew Ligertwod, Australian Evidence (4th edition), Lexis Butterworths,Austria, 2004,p.417. (“……it is assumed that the persuasive burden can be impliedly placed upon an accused, and the House of Lords decide that this assumption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Woolmindon rule. It is therefore possible for either the evidential or the persuasive burden to be placed upon the accused by legislation implication”).“是否存在由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的立法性暗示,这是解释成文法的问题,上议院和高等法院也强调,决定把何种证明负担转由被告人承担需要根据立法的意图,使之在审议立法意图后综合考虑其文字含义和政策内容。”*Andrew Ligertwod, Australian Evidence (4th edition), Lexis Butterworths,Austria, 2004,p.417. (“Whether a burden is placed upon an accused by implication is a matter of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and both the House of Lords and the High Court emphasis the whether any burden is placed upon the accused depends upon the intention under consideration .” )
证明责任的暗示性转移理论说明,英美法的证明责任理论已经不仅仅把目光集中于程序法,而是转而把研究目光转向实体法,并从实体法中重新发现证明责任分配。这对我国证明责任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启发意义,相信证明责任的暗示性转移理论在我国学界的影响会越来越大。
(四)“可能明知”在刑法中的表现
“可能明知”以及证明责任的暗示性转移在实体法中如何表现、如何识别,可以以重婚罪和破坏军婚罪中“明知”的证明问题为例。
——重婚罪:刑法258条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破坏军婚罪:第259条规定“明知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而与之同居或者结婚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从法理看,两罪存在三个不同:一是侵害的客体不同,重婚罪仅破坏一夫一妻的家庭婚姻关系,破坏军婚罪则侵害现役军人的婚姻关系;二是客观方面不同,重婚罪不包括同居,而破坏军婚罪除了与现役军人配偶结婚外,还包括同居;三是量刑不同,重婚罪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破坏军婚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可见,重婚罪和破坏军婚罪虽然同为破坏婚姻家庭的犯罪,但两罪所体现的刑事政策和立法意旨是不同的,对军婚的保护力度明显要大于对一般婚姻关系的保护力度。因此在“明知”的证明标准和证明责任分配上,两罪必然存在差异,其差异性在于:
重婚罪中的“明知”,控方应当承担全部证明责任且必须达到“知道或应当知道”的程度,即提高入罪门槛,否则就违反无罪推定原则,也会扩大打击面,或与偏远地区的社会风俗相冲突。
而破坏军婚罪的“明知”,则应当降低入罪门槛。笔者认为应当与性侵未成年幼女的保护力度一样,即仅需达到“可能明知”的程度即可入罪。否则,破坏军婚的犯罪分子都会轻易地以“不知”为由逃避法律制裁,不能充分体现刑法对现役军人的婚姻关系予以特殊保护的刑事政策。也就是说,行为人如果辩称“不知”,应当承担相应的证明责任。
可见,在破坏军婚罪中,虽然并无明确规定转移证明责任,但其背后隐含的刑事政策,却暗示性地要求法官在适用证明责任分配时,考虑该政策并向被告人分配其“不知”的证明责任。如果否认这一点,就没必要单独设立破坏军婚罪而以重婚罪替代即可。
五、应当扩大“可能明知”的适用范围
通过对“可能明知”法理正当性及实践必要性的分析,笔者认为“可能明知”的适用范围不应仅仅局限于保护未成年幼女的身心健康,而应当把“可能明知”的适用范围扩大至如下犯罪类型之中:
(一)所有体现特殊刑事政策的犯罪
除未成年幼女的身心健康外,刑法典里的很多罪名,都蕴含了刑法对特殊客体和特殊利益优先保护的刑事政策,为贯彻这些刑事政策,就需要降低入罪门槛、降低主观要件之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
1.公共安全类犯罪。如在第138条校舍及教育教学设施重大事故罪中,控方仅需证明责任人对校舍及教育教学设施存在安全风险的“可能明知”,而责任人如表示“不知”,则应承担证明责任。
2.食品、药品安全类犯罪。如在第141、142、143、144、145条销售假药劣药、有毒有害食品、医疗器械等罪名中,控方仅需证明行为人对伪劣商品的“可能明知”,而被告人主张“不知”应承担证明责任。有人甚至建议“行为人只要实施了上述生产、销售特定商品的行为,就可以推定其具有主观的故意”*李恩慈:《刑法中的推定责任制度》,《法学研究》2004年第4期。这种严格责任并非我国刑法的归责原则,还是应当允许行为人举证和抗辩,把“确实不知”排除在外。
3.所有针对未成年人及幼女的犯罪。如在第236条强奸罪、第237条猥亵儿童罪、第262条拐骗未成年人罪、第358条强迫幼女卖淫罪、第359条引诱幼女卖淫罪等等,如被告人主张对未成年人或幼女的年龄“不知”应承担证明责任。
4.危害其他特殊利益的犯罪。如第259条破坏军婚罪,行为人主张对军人配偶的“不知”要承担证明责任。
(二)行为人与证据距离更近的犯罪
刑法里的有些罪名,由于行为人与证据的距离更近,举证能力比控方更强,故可以向行为人转移证明责任,且不会动摇无罪推定原则。主要有如下几类犯罪:
1.持有型犯罪。第171条运输假币罪,第172条持有、使用假币罪,第177条持有、运输伪造的信用卡罪,第312条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赃物罪,第348条非法持有毒品罪,等等,控方仅需证明行为人“可能明知”,而行为人应当对持有对象的“不知”承担证明责任。*张斌:《论被告人承担客观证明责任》,《中国刑事法杂志》2007年第5期。
持有型犯罪在有的国家被直接规定为法律推定,如加拿大刑法典第82条规定:“任何人,如不能证明有合法理由而占有、保管或控制爆炸物品,则构成可诉罪,处5年以下监禁”。法国1810年刑法典第278条规定“乞丐、游民持有价值超过1法郎之物品而未能证实其来源者,处第276条之刑”。英国《1971年滥用药品法》第28条第2款规定,“如果被告人可以证明他没有理由怀疑其占有的物品是受管制的药品,他就应当被宣告无罪。”可见在持有型犯罪中转移证明责任是各国通行做法。
2.腐败型犯罪。如对刑法第382条贪污罪对公共财物的明知,第396条私分国有资产罪中对国有资产的明知,等等,控方仅需证明行为人“可能明知”,行为人需承担“不知”的证明责任。
3.侵犯知识产权类犯罪。如刑法第213条假冒注册商标罪,第214条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罪,第216条假冒专利罪,第218条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第219条侵犯商业秘密,等等,行为人对侵权对象的“不知”要承担证明责任。
4.其他被告人证据距离更近的犯罪。如第152条走私淫秽物品罪、第153条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第360条传播性病罪、第363条第2款制作出版淫秽书刊罪、第350条第2款制造毒品罪(共犯)等等,行为人需对“不知”承担证明责任。
从域外法看,基于证据距离而成立推定的做法也很常见。如德国刑事特别法《反有组织犯罪法》规定,在对贩毒者家中查出的与其收入不相称的大量财产可以成立来源非法的推定。《联合国禁止毒品公约》第18条规定从事毒品非法进口等行为的行为人非法取得巨额财产的,该巨额财产被推定为“非法收益”。
香港地区《危险物品条例》第47条第1款规定,“任何人被证明实质藏有下列物品,除非能举出相反的证据,否则应当被推定为持有毒品:(1)如何装载毒品的物品;(2)任何装载毒品的袋子、公文包、盒子、箱子、壁橱、保险储藏柜及其他类似容器的钥匙。该条例第41条第2款规定:如果一个人被证实或者推定持有毒品,除非能提出相反证据,否则将被定为已经知道该毒品的性质。”
《美国法典》第18篇第27章规定,下列行为都是犯罪,“……4、以欺骗美国的目的故意把应该开具货单而没有货单的货物、商品走私或秘密带进美国;或者以欺骗美国的目的故意开签货单或者故意使虚假的或伪造的货单或其他文件通过海关;……被告人持有这种货物的证据,除非能解释得使陪审团满意,否则就是定罪证据。”
可见,在持有型犯罪中,各国(地区)出于证据距离的考虑均设置了(法律)推定,向被告人转移证明责任。我国由于立法技术和文字表述的原因,明确的法律推定比较少,但基于事实推定同样可以向行为人转移证明责任。
(三)基于诉讼效率而需要降低明知的证明标准的犯罪
1.环境及公害犯罪。如第33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第339条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其构成要件或加重情节中有“严重污染环境”“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此类犯罪的主观方面和因果关系均难以证明,或将导致诉讼的极大延误,因此可以通过降低“明知”及因果关系的证明标准来避免刑事诉讼的过分延误。
例如日本的《公害犯罪法犯罪制裁法》第5条规定,“如果某人由于工厂或者企业的业务活动排放了有害于人体健康的物质,致使公众的生命和健康受到严重危害,并且认为在发生严重危害的地域内正在发生由于该物质的排放所造成的对公众的生命和健康的严重危害,此时便可推定此种危害系该排放者所排放的那种有害物质所致。”
2.高科技及智能化的新型犯罪。此类犯罪不局限于某一类犯罪,其共同特点是犯罪手段采用了高科技或智能化工具,比如利用电信和网络实施的金融诈骗、电信诈骗或利用电商平台实施的制假售假、诈骗等行为,由于此类犯罪地域跨度广、作案过程迅速、隐蔽性强,侦查机关面临取证难、证据固定更难的窘境,再加上受有限的侦查资源制约,故打击此类犯罪相对困难。因此,可以通过在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上适当降低控方的难度,才能有效打击类此犯罪。这正如“911”后美国通过“爱国者法”降低恐怖主义犯罪的证明标准的道理是一样的。
从域外法看,此类犯罪侦查难、指控难、定罪难是世界性问题。在德国,随着科技进步、犯罪手段的日益智能化,导致侦查难度的不断加大;追诉犯罪的困难性不断加剧。以至从20世纪下半叶以来,德国在司法实务中被迫引入了美国式的“辩诉协商”制度,以应对在经济、税务、环境、毒品犯罪中“被告人保持沉默”的案件。*孙长永:《探索正当程序——比较刑事诉讼法专论》,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第526页。而“辩诉协商”其实也是证明标准的降低,故笔者认为,基于诉讼效率而降低主观要件的证明标准是平衡控辩力量对比的方法之一。
(四)基于诉讼公平而需要降低明知的证明标准的犯罪
刑法中有一些犯罪,根据客观情况,如果全部证明责任由控方承担不利于诉讼公平,而赋予行为人适当的证明责任则更有利于实现诉讼公平。
如第191条洗钱罪,行为人需要对自己“不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履行证明责任;第310条窝藏罪,行为人需要对自己“不知”对方是犯罪嫌疑人履行证明责任。由于这些犯罪本身具有隐秘性,由行为人来证明其是否明知,更符合诉讼公平。
当然,诉讼公平是一个比刑事政策、证据距离、诉讼效率更为抽象的考虑因素,在具体指导证明责任分配时,应当注意不可滥用,否则会不当加重被告人的证明责任。
(责任编辑: 魏萍)
作者简介:钟朝阳,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讲师(广州510520)
中图分类号:DF613,DF7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16)04-0150-11
The “Probable Knowing” in Criminal Law
Zhong Chaoyang
Abstract:“Probable knowing” as a special type of knowing means descending the standard of proving. So its meaning, object and scope are special too, and its theory ground includes the strict duty, the “knowledge view”of traditional theory of intent and the layer meaning of knowing. “Probable knowing” has been admitted by the justice interpretation of the “Two-Supreme”. Considering the policy of the allocation in substance criminal law, the distance of evidence, the justice, the efficiency, and so on, the “probable knowing” would be enlarged in application.
Key words:knowing, probable knowing, criminal policy, the standard of proving, the duty to pro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