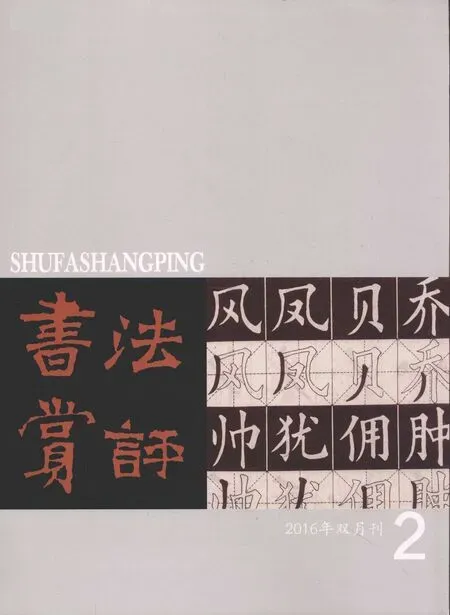“运指”说与“五指齐力”说
——关于包世臣执笔方法的批评
2016-04-04蒋怀坦
■蒋怀坦
理论研究
“运指”说与“五指齐力”说
——关于包世臣执笔方法的批评
■蒋怀坦
包世臣作为清代中后期“碑派”书法的代表人物,在其碑学巨著 《艺舟双楫》中以前所未有的细致和精微对北碑书法给予了高度的赞美和评价。然而,长久以来,人们往往把他局限在这狭窄的一面。有研究表明:包世臣碑学理论的建立是以技法论为核心而展开的。由此可以看出,关于书法技法的论述在包世臣书学思想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一席。其中,尤以执笔方法的论述——“运指”说与“五指齐力”说格外引人注目。包世臣对于执笔方法极为重视,这种重视,可以说已经达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那么,他为什么对这种形而下的执笔方法孜孜以求呢?他关于执法方法的论述又是什么样子的呢?本文试图从他先入为主的学书理念、时代根源、运指说、五指齐力说等几个方面试加分析,以求教于广大同道师友。
一、先入为主的学书理念与时代根源
乾隆四十年 (1775),包世臣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封建地主家庭,虽然生活极为艰苦,但早年的包世臣曾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五岁时便由父亲抱于膝上授以句读,同时开始学习书法,并曾向族曾祖请教过笔法。据其自述:族曾祖槐植三独违世尚学唐碑,余从问笔法,授以 《书法通解》四册。其书首重执笔,遂仿其所图提肘拨镫七字之势,肘既虚悬,气急手战,不能成字。乃倒管循几习之,虽诵读时不间,寝则植指以画席。[1]据金丹先生考证,包世臣这里所说的 《书法通解》,便是清代书家戈守智的 《汉溪书法通解》,此书分为 《执笔图》和 《执笔论》两个部分。[2]暂且不论金丹先生的考证正确与否,仅从包氏本身的论述,便可以看出,此书对执笔方法应该有着较为详细的论述。因为包世臣在这段文字中已经提及“其书首重执笔”,也许正是这种先入为主的学书理念,促使了包世臣一生都对执笔法孜孜以求。
包世臣对执法方法的重视除了与他早年受到的学书理念有关,还有着深刻的时代根源。王世征先生在 《中国书法理论纲要》一书中认为:“清代书法理论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是可观的,而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3]并且进一步指出了清代书法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清代早期,书法理论的发展主要是沿着帖学的路子,思考着如何继承帖学的传统,并且引发了对书法理论的有关问题、书法理论偏重主体的研究,强调做人,强调心的作用。扬雄的“书为心画”,成为人们心目中书法理论问题的中心。清代中期以后,随着金石学的复兴,人们将目光渐渐转移到金石碑版书法,随之而起的碑派书法理论也相应建立起来,它不仅仅强调碑版书法的历史地位,更为重要的是它改变了书法理论研究的立足点,重新将研究的重心带入书法形式的探讨。而到清代后期,经过碑派书法理论洗礼之后,人们开始对两派书法理论的得失进行思考,并从一个新的高度对碑帖两派理论进行汇合。[4]可以说,王先生对清代书法理论发展阶段的概括是极富见解的。通过王先生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在清代中期,书法理论研究的焦点是关于书法形式方面的探讨。这与清初书法理论强调“人”“心”等形而上的研究方式有着根本的差异,它更注重的是形而下的研究,是关于书法最为基础的部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书法艺术最为基础一环的技法必然会成为人们研究的重心。而包世臣书学理论正是形成于这一历史时期,因此,包世臣书学理论中对执笔方法的论述可以说正是这种研究方式最直接的体现。
二、“运指”说
包世臣的一生经历了长期的幕游生涯,足迹遍及楚、蜀、苏、浙、齐、鲁、燕豫等地。在此间包世臣结识了许多挚友,如嘉定钱坫、阳湖张琦、钱鲁斯、常州李兆洛、武进张惠言、黄乙生、朱昂之、荆溪周济、秀水王良士、吴江吴育山、怀宁邓石如等,其中不乏一些著名的书法家、书法理论家。据其自述,包世臣曾向黄乙生、朱昂之、王良士、吴育等人请教过学书之法。但包世臣在听取各家有关书法的讨论之后,并没有死守一家之信条,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进一步的实践经验将其进行了有机的组合,并最终提出自己的执笔主张——运指。
包世臣在 《艺舟双楫·述书上》一文中曾说到:“(余)执笔宗小仲而辅以仲瞿。”[5]我们先来看一段黄小仲关于执笔的论述:“食指须高钩,大指加食指中指之间,使食指如鹅头昂曲者,中指内钩,小指贴名指外拒,如鹅之两掌拨水者。故右军爱鹅,玩其两掌行水之势也。大令亦云飞鸟以指画地。此最善状指势已。”[6]对黄小仲的这一方法,包世臣在 《艺舟双楫·述书中》中曾进一步做过详细的阐释:“今小仲之法,引食指加大指之上,置管于食指中节之端,以上节斜钩之;大指以指尖对中指中节拒之,则管当食指节湾,安如置床;大指之骨外突,抑管以向右,食指之骨横逼,挺管以向左,则管定;然后中指以尖钩其阳,名指以爪肉之际距其阴,小指以上节之骨贴名指之端;五指疏布,各尽其力,则形如握卵,而笔锋始得随指环转如士卒之从旌麾矣。”[7]
透过包世臣的这段解说可以看出,黄小仲关于执笔方法的论述其实并非什么新巧之法,依然是人们常说的“五指执笔法”。然而,除此之外,我们还窥到了一些更为重要的内容——主张“运指”。“五指疏布,各尽其力”,五指并不是仅仅摆出不同的架势,而是有其不同的功用——各尽其力。只有如此才能最终做到“笔锋始得随指环转如士卒之从旌麾矣”。而“士卒之从旌麾”则更为形象生动地说明了“运指”在执笔过程中所起的主导性作用。因此,包世臣所宗尚的这种以黄小仲为主而辅以仲瞿的执笔方法,其主旨便可以概括为“运指说”。而嘉庆丁丑年九月,包世臣在出都的途中所得到的 《王侍中书诀》的石本,则为这一执笔方法找到了理论上的根源。据包世臣记载:“是年 (嘉庆丁丑)九月出都,道中得 《王侍中书诀》石本,有云:‘首务执笔,中控前冲,母左食右,名禁后从。’细心体味,盖以五指分布管之四面,即同此法,古人文简不易推测耳。”[8]包世臣认为,王侍中所说的执笔法,即“以五指分布管之四面”之法。其实,这正为他的“运指”主张,找到了理论上的依据。由此,“运指”就成了包世臣执笔论的中心思想。
包世臣之所以主张“运指”,是因为在他看来“运指”对于书法中的运锋、使毫以及用墨有着统摄性的作用。他在 《与金坛段鹤台明经论书次东坡韵》一文中指出:“锋为笔之精,水为墨之髓。锋能将副毫,则水受摄;副毫不裹锋,则墨受运,而其要归于运指。”[9]包世臣认为,只有通过“运指”这一方法才能使“锋”“毫”“水”“墨”等个体组成一个有机的“序列链”,进而呈现出“笔势无不遒润矣”的艺术效果。然而,长久以来,一些书家学者对此说产生了一定的质疑。其中,对包世臣有着深入研究的祝嘉先生在其所著 《艺舟双楫广艺舟双楫·疏证》一书中说:“包氏一面讲 ‘全身精力到毫端’一面又主张运指,则笔力会打个折扣。”[10]祝嘉先生认为包世臣“运指”的主张与“全身精力到毫端”的理论是互相矛盾的。然而,书法之力的呈现虽然离不开“笔毫”的作用,但全身之力是不可能直接到毫端的,它需要一个由身——肘——腕——指——笔毫,这样一个复杂的传导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指”的运用是不可或缺的,它直接决定着笔毫之力的最终呈现的效果。可见,包世臣主张“运指”的理论非但与“全身精力到毫端”的主张之间没有矛盾,而且有着极为重要的一脉相承的关系。不仅如此,包世臣还进一步提出了“运指”思想的内核——五指齐力。
三、“五指齐力”说——“运指”思想的内核
在 《艺舟双楫》一书中包世臣说道:“王侍中传右军之诀云 ‘万毫齐力’。予尝申之曰: ‘五指齐力’。盖指力有轻重,则毫力必不能齐也。”[11]笔者认为,包世臣力主“运指”的主张以及“五指齐力”思想内核的提出,其目的是为了能够使书法中的“力”之美更好地呈现出来。他试图从书法技法中最为基础同时也是最为重要的“执笔”方法着手,来改变帖学书法软弱、纤细等笔力不足的毛病。这正是包世臣“变革”思想在书法中的显现。
然而,“五指齐力”思想的提出,虽然使得包氏的“运指”理论有了可操作性的依据。但是,笔者认为,包世臣此说曲解了王右军“万毫齐力”的主张。我们先来看包世臣提出“五指齐力”的缘由——盖指力有轻重,则毫力必不能齐也。在包世臣看来,如果要做到“万毫齐力”,就必须使每一个手指的力量保持一致——齐。也就是说,只有手指的力量达到了一致或者一样,才能进一步使得“万毫齐力”。然而,笔者认为,王右军所说的“万毫齐力”的“齐”,应该作“共同”“协调”讲,并非包氏所认为的“均等”“等同”之意。由于五指所控制的区域不同,故所起的作用亦有区别,五指之力理应不尽相同。正因为如此,古人才分别以擫、压、钩、格、抵五字概括之。虽然五指各司其职,但它们并非单独的个体,而是一个有机的组合,其规则即在于“齐”——共同、协调。因此,“五指齐力”并不是五指之力保持一致,而是相互协调后的巧妙组合。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为线条之力的呈现做好阶段性的准备,使整个作品显示出“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的力量之美。由于包世臣并不理解其中的缘由,因此出现了事倍功半的后果。据包氏自述,为了练习指力均齐,他不惜花费了数年之久:“盖作书必期名指得劲,然予练名指劲数年,而其力乃过中指,又数年乃使中指与名指力均。”[12]可以说,包世臣为了练得指力的均齐可谓煞费苦心,但最终的结果却不尽人意:“以迄于今,作书时少不留意,则五指之力互有轻重,则万毫之力亦从之而有参差。”[13]这正是包氏不明就里的可悲之处,认识上的错误,导致了操作上的困难。因而,连他自己在题 《执笔图》时也不得不承认“方知五指齐力难”。[14]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包世臣所崇尚的“运指”的思想,从理论上进一步完善了书法力量由全身之力最终到毫端的传递过程,为书法之力的呈现找到了一个可依的脉点。而他所提出的“五指齐力”的主张,则为这种“呈现”找到了操作上的依据。但同时由于其认识上的曲解,又使得这一“运指”的思想在操作层面上陷入了举步维艰的境况。虽如此,但包世臣“运指”说以及“五指齐力”观点的提出,正是他面对帖学日益靡弱、衰微的局面,特别是清初以来董、赵模拟主义书风流行产生的弊端所做出的一次有意义的探索。这对改变帖学在笔力方面靡弱、纤细的弊病无疑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注释:
[1][5][6][7][8][12][13][14]包世臣 《艺舟双楫》,见 《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644、641、642、644、643、678、678、678页。
[2]金丹 《包世臣书学批评》,荣宝斋出版社,2007年版,118页。
[3][4]王世征 《中国书法理论纲要》,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167、167页
[9][10][11]祝嘉 《艺舟双楫 广艺舟双楫·疏证》,巴蜀书社,1989年版,46、47、46页
参考文献:
[1]崔尔平.历代书法论文选 [A].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641-678。
[2]祝嘉.艺舟双楫 广艺舟双楫·疏证 [M].四川:巴蜀书社,1989年.46-47。
[3]王世征.中国书法理论纲要 [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67。
[4]金丹.包世臣书学批评 [M].北京:荣宝斋出版社,2007年.118。
作者单位:泉州第一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