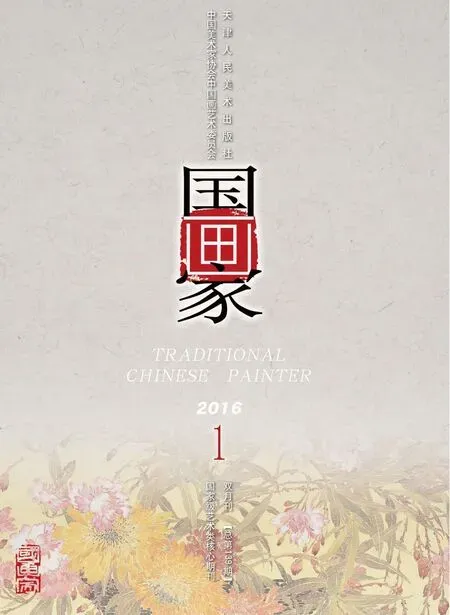经融碑帖 书含诗画——曹柏崑书法艺术浅析1
2016-04-04王智忠
王智忠
经融碑帖 书含诗画——曹柏崑书法艺术浅析1
王智忠
书坛30年,书法艺术经历了由文人书斋的闲情逸致向学科化、专业化转型的历程,而曹柏崑2是这一过程的完整亲历者。书协筹建之初那二十年的工作经历使他始终关注书法发展的前沿,学者型书家的气质又能使其对时风做出科学、理性的思考,大学艺术学院的教学经历更使其对书法的传承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体现在创作上,先生注重传统功力,兼通大楷、小楷、行书、隶书、草书诸体,皆具个人面目,堪称天津书坛的多面手。但其入古深而不泥古,独特的学习门径,加之多方面的学识和修养,涵化了他鲜明的书法风貌,达到了碑、帖、经共冶,书含诗情、蕴画意的艺术境界,他也成为当代极富个性的书家。
一、独特的经味儿小楷创作
曹柏崑以小楷闻名书坛,不同于传统取法晋唐钟王文人书法“在朝”的路子,他独辟蹊径,以写经为法源,走的是“在野”的路子。书法面貌虽与正统书风有异,但又与时代审美不无相合。因为正是“北碑南帖论”解构了唐以后的帖学正统观,使当代书法创作风格走向多元化,写经书法因此大放异彩。先生曾多次著文分析写经的艺术成就,或以经典与之对照,或进行微观评说,皆具有拓荒意义。3
在创作上,曹柏崑始终在写经的富矿中开掘、吸收,不断丰富着自己的艺术语言,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集古为立家,酿蜜不留花”。不同于前辈书家或时人对写经的某种风格的单纯或借鉴性继承,他的小楷于写经更有着集成的意义。他坚持体系化的学习道路,运用“求同、存异、辩证”方法梳理出各种风格的写经。从其个人作品集《临摹写经十二种》中不难看出,首先选择与己意相合者尽量拿来,十二篇写经中六篇为唐人写经,这树立了他尚法的基调,用笔内擫,结字紧艳,平中见奇。其他六种写经为副翼,东晋的古朴含蓄、北朝的雄强刚健、隋人的匀净端秀,或点画或结字尽量追求异质特点的相融,此乃存异也。而六篇唐人写经,或厚重如《唐贤写经遗墨之二》,或柔美如《灵飞经》,或刚健如《金刚经》,又同中显异、异中有同,辩证之理昭然。这样以点带面的学习方式对浩如烟海的写经资料来讲是必需的。而在反复比较、临习中,《议善男子残经》又被他视为集大成者,这是“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的必然,曹柏崑的眼界也在实践中穷极写经的大千世界。学而知止,事半功倍,关键在于系统分析和辨别。
正是“写经”这一晋唐人留下的真迹,赋予了曹柏崑创作上的极大自由、理论上的极大智慧、思想上的极大解放。《柏崑小楷菜根谭》堪称其小楷的扛鼎之作,正如著名鉴定家刘光启先生的评价:“举凡晋人气象、唐人法度、宋人规模、元人风貌、明人方圆、清人步武,与己意合者,与书之规律合者,悉皆拿来,‘集千家米煮一锅饭’,得似之不似,不似之似。”4“写经”这一为传统漠视的经典为曹柏崑大胆地广泛吸纳,与传统经典名家书法笔意同陈一字,使其书法出奇而又得圆融之旨。有着鲜明的辨识度,又无突兀之感,进而跳出了小楷必法晋唐的单一路数,其难度可想而知,难不在学,而在合也。曹柏崑小楷虽取法颇丰,但其艺术风格又是鲜明的。用笔纤毫毕现,爽利而灵动;点画虚实相生,变化无端;格调秀劲中见古雅,鲜活而多趣。这是书家的主体意识使然,才能合众美为一美。正如他在形容八大书法时讲:“百家未能夺其志,造化未能乱其真,他始终是他。”
二、碑帖融合的新尝试
有清以来,汉魏碑刻一直是大字楷书的重要法源。直至当代倡导的“新碑学”,由于过分强调碑石上的刻画美和碑刻独有的笔法技法系统的“挖掘”,“碑学”呈现出强弩之末势,值得深入思考。而曹柏崑习碑的方法采取的是历史还原法,即抓住北碑、写经的一体关系以明确学碑的方法取向。因为,魏晋直至隋唐的写经完整再现了北方以中原古法为主的碑铭楷书发展的全貌,也成为映照北碑书法演变的一面镜子,与北碑虽有书、刻之别,但同源、同步、同风,完整再现了魏晋书法发展的全貌。
先生注重与汉魏名碑同一时期的写经真迹的研究,发现那在写经中若隐若现的北碑笔法,通过“写经”还原北碑的本来面目。从某种意义来讲,写经给碑、帖相融也提供了一种可能。《淳化阁帖》以后,是刻画的问题使书法阶段性地走向低谷,那么一味追求刻画效果的“后碑学”,虽然可以给人带来短暂的新鲜感,但前途又将如何呢?潘天寿先生也曾警示习书者:“倘若先学魏碑是不易学好的,因偏笔临帖较难,易有流弊。”即他所讲的“徒求形似,尤其是去用毛笔刻意地描摹出所谓的‘金石味’,去模仿斑驳的效果,或者要求用毛笔写出刀刻的效果,是吃力不讨好的”。这确为金玉之言,今日书坛有此弊者当引以为戒。文化大发展、印刷水平高超的今天,原来养在深闺人未识的书法真迹名作可以非常真切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近年来,帖学的复兴说明还原书法的历史本真永远是人们追寻的主题,那么,我们更没有理由固守碑板,因为碑、帖本不是平行发展的,二者合流才是书法的全部,写经的艺术价值正在于此,曹柏崑的尝试是有益的。
不仅如此,曹柏崑还以写经为媒介探索书体间的彼此融入。沈曾植《海日楼札丛》言:“篆参隶势而姿生,隶参楷姿而姿生,此通乎今以为变也。”这种“通变”的理论无疑是正确的,因为五体本无清晰的界限分野,诸体相杂的现象在书法史中本就存在。曹柏崑曾创造性地将写经与经典帖学的代表《兰亭序》进行比较,这种楷书与行书的对举比勘本身就打破了书体之限,无疑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他发现了“经生突破传统的工笔小楷的板滞写法复以行书的用笔……似为登《兰亭》之堂,入《兰亭》之室,由楷入行开辟了路径”5。这体现了曹柏崑对书法技法认知的高度,在实践中,他也就能行、草、隶、篆无不纳入楷书其中了。曹柏崑大楷面目与小楷新领域的开拓一脉相承,如果小字彰显的是险而灵动,那么大字则是一派正大气象,碑的厚重、帖的儒雅、写经的生趣一望便知,碑、帖、经的巧妙融合使其大字楷书面目明显有别于当代各家。
20世纪90年代曹柏崑开始习画,宋人小品、李苦禅、潘天寿、齐白石、“四王”、董其昌、黄公望,一路走来,是典型的文人画的路子。绘画方法也在书法创作中得到了自由运用,真正成为一种自觉的追求。笔法的解放、墨法的使用也成为他的书法创作中的亮点。习画后的曹柏崑关注墨法的使用,大大提高了书法的表现力。墨法通过笔法的实施,依情感、字势、字形、章法、书写材料、书写形式、天气等而生变,增加了书法创作的不确定性。但这种不确定性并不是当今书坛某些作品水墨的简单调剂的刻意为之,要听之自然,否则只是浅薄。观其小品用纸兼生熟,因而笔法清丽,线形光洁,色泽清润,且几乎不见晕化之痕迹,又能涩中显润,以去浮滑之气,表现出温和、清润、淡涩的意趣,是董其昌尚“淡”墨法的韵味。大字行草喜用生纸,随用笔起止、停顿、疾徐和情绪的变化而变化,呈现出轻与重的对比、深与浅的安排、块面与块面间的组合,在充满跌宕的纵向性滚动和连绵书写中,自然地表现出晕散、浓润、枯劲的艺术效果,无狰狞之态,达到了“水墨神化,仍在笔力”的境界。
书法与诗(文)的结合,其实是书法文气的体现,而文气则浸透着书家对书写内容的关注和理解。曹柏崑注重自身的文学修养,写诗、著文抒写怀抱,这也直接涵养了他的书法创作。以1998年创作的《学宫碑》《南开中学周恩来纪念碑》《长寿园碑记》《大悲院沿革记》四碑为例,虽为一年内书写,但面貌各有不同,或清秀儒雅,或刚毅卓然,或朴厚中和,或禅意十足,十分耐人寻味。使人感觉书法已超越了个体存在而与文相映成趣,真正做到了书随文动、笔依情驱,这本身就是书法的诗意呈现!
这里还需指出的是,曹柏崑书法所表现出的画意、诗情是对书法艺术本体精准把握后的超然一跃,而非简单的对号入座,更不是时下某些追求书法“美术化”和标举个性大旗的画字、作字者的肆意涂抹。片面强调主观诗意而忽视书、画艺术规律的把握,最终只能是痴人说梦、故弄玄虚。
创新是书法发展的生命力所在,在当代书法内部结构性调整的大背景下,自觉地对古代书法资源进行重新整合、利用,这是书法本体探究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书之妙在于最大限度展现了汉字的固有美的同时,应参天地、尽人事,异类求之于画意、诗情,在跨学科的互动中,重新梳理书法与诗、画之间关系,也成为当代书法发展的另一重要途径。而曹柏崑的书法正是对以上两方面很好的诠释,值得关注。
注释:
1.本文为天津市艺术科学规划项目《曹柏崑书法研究》(D12012)阶段性研究成果。
2.曹柏崑(1947— ),天津人,历任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天津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现为国家一级美术师、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3.先生论文《希望在于继承》《写经书法价值初探》及《写经与兰亭》曾先后入选全国第一、二届书学讨论会及第一届中青年书学讨论会。
4.刘光启.柏崑小楷菜根谭序.柏崑小楷菜根谭[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
5.曹柏崑.书法寻真文论集[M],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P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