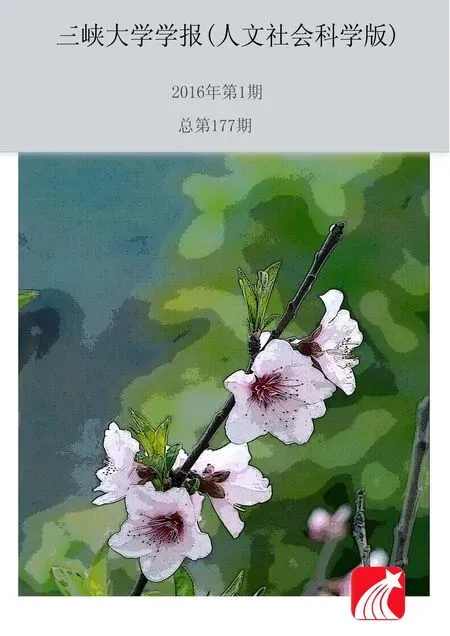“中郎为坡公后身”说考述
2016-04-04张志杰
张志杰
(四川大学 中国俗文化研究所, 四川 成都 610064)
“中郎为坡公后身”说考述
张志杰
(四川大学 中国俗文化研究所, 四川 成都610064)
摘要:“中郎为坡公后身”之说对于进一步认识袁宏道及晚明文坛是一个颇有价值的切入点。此说出现在文化变革背景下袁宏道文人圈的交际活动中,时人对苏轼接受的改变和佛禅思想的盛行构成其特定的文化语境,也由此体现出该说的多重含义,除手足之谊的表达外,此说明显体现出对袁宏道佛禅修为的发扬,更重要者,作为“篇什装点之助”,对袁宏道立言事功尤其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袁宏道;苏轼;后身;佛禅;立言
关于袁宏道与苏轼关系的研究并不少见,但鲜有论者关注到“中郎为坡公后身”之说。笔者以为,此说颇有探讨的价值,自此一孔重新认识袁宏道并进而窥探晚明文坛有一定的学术意义。本文略作考述,以就教方家。
一、滥觞与流布
袁宏道为苏轼后身之说首先引人注目的论述在《识雪照澄卷末》。题注云:“卷中小修有梦中遇老僧,谓余为坡公后身。”文中又称:“东坡,戒公后身也。戒倚柱谭笑而化,当时以为异。……明教曰:‘然则老僧谓公为坡后身云何?’余曰:‘有之。尝闻教典云前因富奢极者,今生得贫困身。坡公奢于慧极矣,今来报得鲁钝憨滞,固其宜也。’”[1]1219-1220考之袁中道《书雪照册》云:“甲辰秋初,予避暑荷叶山房,未几,中郎偕雪照、冷云二禅师及云心居士至。已而寒灰老禅亦至。……是夜,月明如画,诸公谭锋正发。予因假寐,俄至一处,见一庞眉老僧,语予曰:‘公等欲知宿世之事乎?中郎前身是苏公子瞻,公即子由也。”[2]880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系《识雪照澄卷末》于万历二十九年(辛丑,1601),而《书雪照册》载其事在甲辰(万历三十二年,1604),给人理解上造成干扰。任访秋《袁中郎研究·年谱》疑而不定[3]190,马学良《袁中郎年谱》、沈维藩《袁宏道年谱》皆不辨,何宗美《袁宏道诗文系年考订》一书考中郎此《识》时间为万历三十二年[4]291,其说至当,如此则上引两则记述时间上的矛盾可迎刃而解。考察上述两篇内容并参考中道《荷叶山房销夏记》、《书雪照存中郎花源诗草册后》以及宏道《游德山记》诸篇,二者同作于万历三十二年诸人雅集荷叶山房销夏之时甚明。可知袁宏道所谓“小修有梦中遇老僧”之事即为袁中道《书雪照册》所载之事。
据上文所引,袁中道梦中照见“中郎前身是苏公子瞻”,宏道本人对此转生之说也表示了认同,以为“有之”、“固其宜也”。考之当时袁宏道文人圈,此说也见于曾可前、雷思霈等人。雷思霈《公安县志序》云:“余友中郎始有《公安志》,适钱令君属之。……传闻中郎为子瞻后身,嗟呼!子瞻不敢作三国史,而中郎能为一国志,岂隔世精灵乃更增益耶?”[1]1731“传闻”一词说明袁宏道为苏轼后身之说在当时已经流传,至少在亲朋师友间已传开。曾可前的语气更加肯定。据清康熙时孙锡蕃撰《公安县志·袁宏道传》引述:“曾长石云:‘中郎为子瞻后身。乃子瞻不能作三国史,而中郎为一邑志,岂隔世精灵有增益其所未备耶。’艾千子谓:‘以文为戏,坡公不免作俑,而袁中郎为甚。’语虽有间,而中郎之为子瞻无疑矣。”[1]1663引文中曾可前之言与雷思霈几乎相同,孙氏是否将后者错引成前者大可怀疑,抑或二人皆有此语,此处不必细究,要之,此说当时已在流传则很明确。
关于袁宏道为苏轼后身说的最早来源,考之不见于李贽、焦竑等辈。袁宗道《杂说》提及东坡后身之说,云:“《江乡志》卷末记佛日大师宗杲,每住名山,七月遇苏文忠公忌日,必集其徒修供以荐。尝谓张子韶曰:‘老僧东坡后身。’子韶曰:‘师笔端有大辩才,前身是坡耳。’世传东坡为五祖戒后身,然未有称其为妙喜前身者,亦奇闻也。但考杲公生七年,坡公方卒,恐未是。”[5]305言及东坡后身之说而不涉宏道,可见当时亲友之间并无此说。
袁宏道为苏轼后身之说当以前举袁中道《书雪照册》为滥觞。在此之前,他人作品中鲜见以宏道比作苏轼者,更不论以宏道为苏轼后身。就中道自身而言,考之《珂雪斋集》可见此说的形成与明确也有一个过程。
万历十九年(1591)龙湖之会后,中道所编《柞林纪谭》载:“十五夜月色明,伯修、以明、寄庵、中郎并予,坐于堂上饮酒。叟曰:‘今日饮酒无以为乐,请诸君各言生平像何人。’”中郎自言最爱嵇康,而李贽以为不甚像,中道以为像蔡邕,伯修也以为像嵇康[2]1480。可知当时交游诸人并无以宏道为苏轼后身者,倒是宗道素慕白居易、苏轼众人皆知而没有异议。但其后袁中道以苏轼比拟宏道次数渐多,如作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的《听雨堂记》形容其兄弟之间“相爱不啻子瞻之于子由”[2]529,以苏轼兄弟比自己兄弟。此后如《南北游诗序》中以秦少游形容陶孝若,隐然以宏道比之东坡等等[2]457。然而也不难发现,大约于万历三十年(1602)为夏道甫辑李贽遗著所作《龙湖遗墨小序》中,有“龙湖李先生,今之子瞻也”之言[2]474,说明彼时袁中道自身仍然尚未形成宏道为苏轼后身之说,依旧只是将苏轼作为一种称颂他人的比附而已。至万历三十二年(1604)《荷叶山房销夏记》方直接称“嗟乎,予兄真今之子瞻。”[2]548并最终于《书雪照册》托梦中老僧之口道出“中郎前身为苏公子瞻”,袁宏道为苏轼后身之说自此明确。
至于雷思霈“传闻中郎为子瞻后身”与袁中道之说孰先孰后,似乎不成问题。据孙锡蕃《公安县志序》:“公安邑乘,自明万历甲辰(1604)重修于袁中郎先生,闻其编年纪事,一仿太史公体式。乃才如中郎,辑旧志而厘新之,尚自甲徂丙,三易寒暑而高峻,可知其周详而克单行于世矣。”[1]1732则知袁宏道著《公安县志》成当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则雷思霈之序晚于袁中道甚明。
由此,万历三十二年(甲辰,1604)袁中道夜梦老僧告以前身宿世为袁宏道乃苏轼后身说的源头当无疑问。《书雪照册》记载,当时众人集聚荷叶山房“相与激扬第一义”,而中道“以所梦质之,皆跃然,若有忆者。”在场诸人表示认同,此说由此传播开来。雷思霈、曾可前之说也当源于此。稍晚的名僧智旭《净土十要》卷十《评点西方合论序》云:“袁中郎少年颖悟,坐断一时禅宿舌头,不知者,以为慧业文人也。……传闻三袁是宋三苏后身,噫!中郎果是东坡,佛法乃大进矣。”[6]0862可见袁宏道为苏轼后身之说已不单在当时、在亲友间流转了。其后此说仍有所闻,如上文所引《袁宏道传》,孙锡蕃相信“慧业文人应天上生”,并引称曾可前“中郎为子瞻后身”之说,又以为艾南英所言“语虽有间,而中郎之为子瞻无疑矣。”可知至清代此说仍有流传。
二、时代与语境
“中郎为坡公后身”之说的出现与流传有其特定的时代条件和文化语境。
首先在于时人对苏轼接受的改变。
万历中叶,文坛复古思想积弊已甚,不满于此的袁宏道等人起而辟之,力矫“求两汉、盛唐于一字半句之间”[2]1695的复古末流,长期被压抑的宋代诗文逐渐开始被接纳,而作为最有代表性的苏轼所聚注目尤多。文人对苏轼接受的改变,是晚明文学的一个基本事实,也是“中郎为坡公后身”说一个重要的文化语境。对于这一转变,最有说服力的例子莫过于王世贞。身为复古领袖,王世贞晚年转而服膺苏轼,袁宗道称其“晚年全效坡公”[5]234此事尤能说明当时文坛转变情况。而检阅时人著作,崇苏之语俯拾即是,如李贽“对长公披襟面语,朝夕共游”[7]112,袁宗道以“白苏”为斋,易地而名不改,陶望龄“以为少陵以后,一人而已。再读更谓过之。”可见晚明文人尊苏之风殊甚。与此相应,苏轼诗文刻本的盛行直接说明了时人对苏轼的阅读情况。郑利华教授曾对晚明时期苏轼集刊刻的整体情况做过研究[8],文本以袁宏道主要生活的万历时代及万历以前的明代为两个区间,考察四川大学古籍所编《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发现,可确定具体时间的现存明刻本苏集中,刊于万历年间的达30余种,而万历以前较长的时间跨度内刻本仅寥寥数种,可知万历年间苏集刊刻情况远较前期为盛,且其中刻本多集中在万历中后期,正与上述转变相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语境下出现的以苏轼相比拟的习见现象。其例不胜枚举,略如李贽《书<苏文忠公外纪>后》:“余老且拙,自度无以表见于世,势必有长公者然后可托以不朽。焦弱侯,今之长公也,天下士愿籍弱侯以为重久矣。”[7]199陶望龄评王思任诗:“近代诗家尚同工刻,不敢己出一新语、用一新事,而予所见季重《赠客诗》,独广大富有,略类长公。”[9]451袁宏道也多次称其兄宗道为苏轼,如《陶石篑》云:“家子瞻快活殊甚,一冷太史日骑瘦马,走长安市上,不知又有何好面孔,而欢天喜地若此。”[1]267《识伯修遗墨后》称“兄与长公,真是一种气味。”[1]1111而王德完序黄辉《怡春堂逸稿》以黄辉比拟苏轼,雷思霈序袁宏道《潇碧堂集》、曾可前序袁宏道《瓶花斋集》皆以宏道追配苏轼,可见时人以比拟苏轼称颂对方已成为一种潮流。
其次是袁宏道文人圈佛禅之风的兴盛。
与苏轼文人圈相似,袁宏道交游之人也是参禅礼佛,诸人“声气相求,函盖相合”[10]915,而三袁浸淫佛禅尤深。宗道“遍阅大慧、中峰诸录”,终生“精研性命”[2]754,参习佛典“精勤之甚,或终夕不寐。”[2]707中道对“西方之书、教外之语,备极研究。”[1]187尤可重视的是,其作品中所记佛法神异之事甚多,如《袁氏三生传》所叙三生临没前见莲花、五色世界及带宝冠菩萨等异事,陶不退、徐三畏、苏轼外祖程翁等诸异事,以及《次苏子瞻先后事》中记苏轼自悟前身为寺中老僧,《次苏子瞻先后事》、《游居杮录》卷三等记张方平见《楞伽经》手迹知前身是知藏僧等自悟前生之事,折射出中道对佛法的信仰与对转生之事的兴味。
袁宏道交游诸人谈禅说佛中对苏轼转生之说关注尤多。如袁中道所编《柞林纪谭》记李贽之言:“叟问众:五祖戒是法眼嗣,有甚不得力,却出为东坡。东坡到老也不得了,只讲得几句义理禅,向来面目失却了些子,况添了许多文字业、忧国忧民的业,后便不可知矣。”[1]1479袁宗道辨析宗杲为东坡后身之说已如前见,又为中郎《西方合论》作引云:“一念不尽,即是生死之根,业风所牵,复入胞胎。如五祖出为东坡,青草堂再作鲁公,隔因之后,随缘流转。”[5]319袁宏道编李贽《枕中十书》并为之序云:“或说卓秃翁,孟子后一人,余疑其太过。又或说为苏子瞻后身,以卓吾生平历履,大约与坡老暗符。”[1]1634等等,诸人或品评辨析,或彼此标榜,津津乐道于苏轼转生之事。
由上所论可知,晚明文人对苏轼的阅读和接受情况发生普遍改变,并由推崇苏轼而形成一种拟苏的惯常现象。同时,袁宏道文人圈对佛禅思想的热衷又与苏轼接受相结合,对苏轼转生书写发生普遍兴趣,二者共同构成袁宏道为苏轼后身说出现与传播的重要时代条件和文化语境。
三、理由与意义
按照叙事学的观点,一个论点的发出必然有其立足的原由,同时必然表达一定的含义。对袁宏道为苏轼后身说所立足的理由与所体现意义的深入探讨,是全面理解该说更为重要的内容。
1.“坡公后身”说立足的理由
袁宏道与苏轼的关系无疑是密切的。据笔者统计,袁宏道诗文中直接论述或提及苏轼者达60处,远胜于频率也较高的白居易、欧阳修等人。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佛禅与诗文方面着墨尤多,且主要集中在《瓶花斋集》和《潇碧堂集》中,而袁宏道为“子瞻后身”之说正是出现在这一时期。虽然袁宏道阅读并推崇宋代诗文是一贯的,但从万历二十六年(1598)、十二七年(1599)的尺牍中可见,袁宏道开始集中大量地阅读宋人诗文,如作于二十六年的《答梅客生开府》云:“邸中无事,日与永叔、坡公作对。”[1]734《答陶石篑》:“弟近日始遍阅宋人诗文……其中实有超秦汉而绝盛唐者。”[1]743二十七年的《答王以明》:“近日始学读书,尽心观欧九、老苏、曾子固、陈同甫、陆务观诸公文集,每读一篇,心悸口呿,自以为未尝识字。”[1]772《冯琢庵师》:“宏近日始读李唐及赵宋诸大家诗文,如元白欧苏,与李杜班马真足雁行,坡公尤不可及,宏谬谓前无作者。”[1]780此外,不独自己,也建议别人阅读宋代诗文,如《答毛太初》告诫毛太初曰:“古人且熟读韩、苏,余不必读。”[1]764明显可见袁宏道于宋代诸公中对苏轼尤其钟情,言必称东坡,且直赞其“诗文卓绝无论”[1]734、“前无作者”。这一时期,袁宏道不仅阅读、批点苏轼手不释卷,而且遥和苏诗,《花朝和东坡韵》三首、《和东坡梅花诗韵》三首、《和东陂聚星堂韵》等全部作于这一时期。
2.“坡公后身”说对袁宏道的意义
由上可知,在时人拟苏的文化语境与袁宏道本人的崇苏前提下,袁中道抛出“中郎为坡公后身”之说有着充分的理由,同时也带有明显的意义指向。
首先是佛禅修为的发明。袁中道《书雪照册》中小修问老僧曰:“诸人前后了然,独两苏与予兄弟,尚觉有异同处。”老僧曰:“子瞻息机也迟,而中郎息机也早,迟则蹶,早则无咎,其有所惩而然。”[2]880“息机”即息灭机心之意,为佛教常用术语。对应的《识雪照澄卷末》中袁宏道答张五教“然则老僧谓公为坡后身云何”之问,曰:“尝闻教典云‘前因富奢极者,今生得贫困身。’坡公奢于慧极矣,今来报得鲁钝憨滞,固其宜也。”[1]1219-1220此处所谓苏轼之“慧”为“无漏三学”的戒、定、慧之慧,指苏轼开悟的能力,与自己“钝”的不悟相对。袁宏道曾称“龙华分座,子瞻当踞诸禅首席。”[1]1527作为南岳下十二世东林常总法嗣,苏轼在丛林中有很高的声望。而袁宏道遍参华梵诸典,“亡食亡寝,如醉如痴”[2]754,有方外之交如无念、雪照、冷云、寒灰、常觉、如愚等不下十数人。其创作也多与佛禅有关,据周群教授《佛学与袁宏道的诗歌创作》中的统计数据,笔者合计袁宏道诗文中与佛教有关者达423首(篇)[11],而其早年所撰《金屑编》深受李贽推崇。他本人对此颇为自负,曾与友人说:“仆自知诗文一字不通,唯禅宗一事,不敢多让。”[1]503尤其中年转向净土后所撰《西方合论》更成为净土信仰的重要著作。中道此说,正是对宏道佛学修为的称颂与对其影响力的塑造。
其次,手足之谊的表白。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是,袁中道是“中郎为坡公后身”说的首倡者和积极鼓吹者,其《书雪照册》中后身之说,其实兄弟二人俱在。老僧曰:“公等欲知宿世之事乎?中郎前身是苏公子瞻,公即子由也。”即是说“小修为子由后身”是与“中郎为子瞻后身”同生的,其中明显包含了中道对于兄弟之情的彰显。考察中道作品,其将宏道比作苏轼,多会带出自己与苏辙。如《南北游诗序》:“有一时即有一时之名士……昔子瞻兄弟,出为名士领袖云云,文中将陶孝若比之于秦太虚,以自己兄弟比之苏轼兄弟。”[2]457《听雨堂记》中记述更可谓深情绵邈:“乙未,中郎令吴,念兄弟三人或仕或隐,散于四方,乃取子瞻怀子由之意,扁其退居之堂曰‘听雨’。十月,予往吴省之,见而叹曰:吾观子瞻居宦途四十余年,即颠沛流离之际,家室妻子潇然不在念,而独不能一刻忘情于子由,夜床风雨之感无日无之,乃竟不得与子由相聚也。”又曰:“夫孰有子瞻与子由两相知者?以两相知之兄弟,而偕隐于山林,讲究性命之理,弹琴乐道,而著书瑞草、何村之间(见苏轼《与王元直》),恐亦不大寂寞也。”“今吾兄弟三人,相爱不啻子瞻之于子由。”[2]529又,《荷叶山房销夏记》:“嗟乎,予兄真今之子瞻,予媿子由,然其不欲相舍同也。……予遂退而援笔记之,使见之则忆此乐,毋如苏家兄弟阳羡、许下事也。”[2]548中道在《次苏子瞻先后事》也有表见。中道多次满含深情叙述子瞻和子由“兄弟散于官途”的“离合之感”[2]919,表达自己与宏道“兄弟之间彼此慈爱,如左右手不能相离”之情,其所谓“中郎前身是苏公子瞻,公即子由也”之说也出于同样之意。
最重要者,此说的意义还在于“篇什装点之助”。宋人周煇《清波杂志》卷二“诸公后身”一节针对历代文人的转世书写表达了自己的认识:“房次律为永禅师,白乐天海中山……苏东坡戒和尚,王平甫灵芝官。近时所传尤众,第欲印证今古名辈,皆自仙佛中去来。然其说类得于梦寐渺茫中,恐止可为篇什装点之助。”[12]56毫不客气地戳破了后身说神秘的窗户纸,从而更接近了事情的实质。考诸当时文坛,虽然比附苏轼已成风潮,但鲜见有直接标榜为东坡后身者。袁中道抛出此说,重要原因即在于以此超出时流的方式推扬宏道立言的事功,塑造其时代风气扭转者的地位。正如苏辙之推扬苏轼,中道对宏道的推扬是一贯的。如称“中郎力矫弊习,大格颓风”,救“剿袭格套”、“黄茅白苇”[2]451的诗坛于既倒,认为其所论“真天授,非人力也”[2]521、“非独文苑之梯径,傥亦入道之津梁。”[2]451又如所谓“有一时即有一时之名士,以为眼目,若凤麟芝菌,为世祥瑞。”推宏道为名士领袖、时代骄子,[2]457甚至目为冠绝有明一代的人物:“本朝数百年来出两异人,识力胆力迥超世外,龙湖、中郎非欤?然龙湖之后不能复有龙湖,亦不可复有龙湖也;中郎之后不能复有中郎,亦不可复有中郎也。”[2]1047以至径直谓中郎“与世人有仙凡之隔。”[2]1650
袁宏道本人的态度可作为支撑此论的重要旁证。袁宏道对于诗文的态度是认真的,并不是表面给人的侣山友水、流连光景而不务立言的假象,实质上,袁宏道“好为难首”[1]1663,时出惊人之语,当然不是“信心而谈,信口而出”,而是一种有意的诗学策略的选择。如所谓“世人喜唐,仆则曰唐无诗;世人喜秦汉,仆则曰秦汉无文;世人卑宋黜元,仆则曰诗文在宋元诸大家”等[1]479,有意与时人南辕北辙,这种惊世骇俗的刻意态度,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个自视甚高而又位卑言轻的文人在求名心理下引人侧目的一种方式。关于这一点研究者已有关注,如李瑄教授曾从袁宏道早期《述怀》诗中的“无孔锤”和“珊瑚网”两个意象入手,对其诗学策略有过分析[13]。袁宏道诗学旨趣上虽破但不立,其明确目标是致力于抨击复古之弊,并不在倡导被后世放大的“性灵说”。其创作上无理路可循,刻意以俗化与戏谑等方式否定、嘲弄复古派倡导的典雅和规范,甚至作律诗故意不对仗、不合律,这些态度与实践实际上都是其有意的策略上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中郎为坡公后身”之说无疑对其文坛形象的塑造有重要价值。袁宏道交游诸人中,如袁中道、曾可前、雷思霈诸人皆以此转生之说作为一种话头,推扬袁宏道在文学上的成就,展示出此说在交际话语与形象建构中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2]袁中道.珂雪斋集[M].钱伯城,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3]任访秋.袁中郎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4]何宗美.袁宏道诗文系年考订[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5]袁宗道.白苏斋类集[M].钱伯城,标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6]智旭.净土十要[M]//卍续藏经(第108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7]李贽.焚书,续焚书[M]//李贽全集注(第1,3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8]郑利华.苏轼诗文与晚明士人的精神归向及文学旨趣[J].文学遗产,2014(4).
[9]陶望龄.歇庵集[M].台北:伟文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76.
[10] 王元翰.凝翠集[M]//丛书集成续编(第117册).上海:上海书店,1994.
[11] 周群.佛学与袁宏道的诗歌创作[J].南京大学学报,1998(1).
[12] 周煇.清波杂志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7.
[13] 李瑄.手提无孔锤,击破珊瑚网——禅学思维与袁宏道的诗学策略[J].中山大学学报,2011(5).
[责任编辑:杨勇]

中图分类号:I 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219(2016)01-0046-04
作者简介:张志杰,男,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5-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