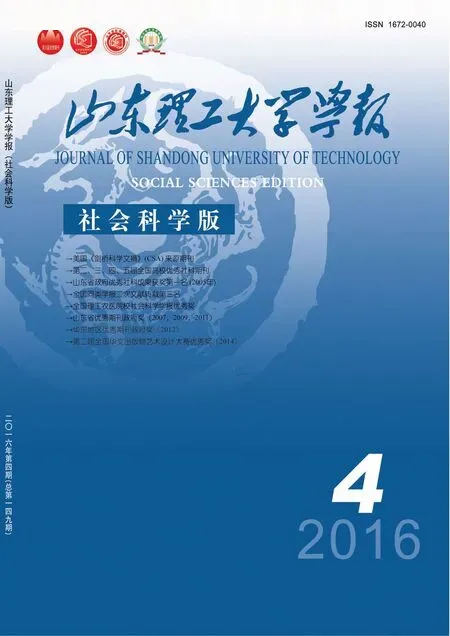《管子》情性论
2016-04-04张杰
张 杰
(山东理工大学《管子学刊》编辑部,山东淄博255000)
《管子》情性论
张杰
(山东理工大学《管子学刊》编辑部,山东淄博255000)
[摘要]《管子》以治国为核心的人性论是以人生而就有的本能即情性为人性,可称之为情性论。《管子》情性论以满足君主、百姓情性,即以治国安邦为核心。它与孟子、荀子、告子等人性论思想相比,具有鲜明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其一,《管子》情性论关注的重点是君主、百姓所拥有的与生俱来的本能,并非探讨人性的善恶,属于西周、春秋时期传统的人性论;其二,《管子》情性论以治国为核心,并非以提高道德、实现理想人格为重点。
[关键词]《管子》;情性论;君主;百姓;治国
《管子》人性论的内容比较丰富,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以治国为核心的情性论,一是以《管子》四篇为代表的稷下道家人性论。在黄老研究兴起之前,很少有人关注《管子》的人性论。随着学者对黄老道家思想的高度关注,很多学者开始研究以《管子》四篇为代表的道家的人性论,进而论及《管子》的情性论。如有学者认为《管子》四篇的人性论属于道家的人性论[1]81,并且把它作为《管子》人性论的代表;又有学者认为《管子》人性论除《管子》四篇之外,其余自成体系,以趋利避害为基本内容[2]13;还有学者认为《管子》四篇与《管子》其他篇章的人性论是一个紧密的整体[3]9,等等。本文认为以《管子》四篇为代表的道家人性论固然特色鲜明、独树一帜,但其人性论的主体仍是以人生而就有的本能即情性为人性。它以满足或实现君主、百姓的情性为主体,即以实现统治阶级富国强兵的治国策略为核心,可称之为情性论。《管子》情性论属于春秋以来传统的人性论。具体来说,《管子》的情性论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管子》以君主、百姓所拥有的与生俱来的本能为人性
学者在论及人性论时多关注孔子、孟子、荀子、告子、周人世硕以及老子、庄子等诸子的人性论。这些人性论大多有其共同的特点:第一,探讨人性的来源及善恶。如孟子以心言性,主张人性善;荀子以情言性,认为人性恶;老子、庄子以创生万物的道德言性,认为人性超善恶[4]24;告子以食色言性,主张人性无善无恶;另有周人世硕认为人性有善有恶,等等。第二,探讨人性的目的大多是为了提高道德修养或成就理想人格。唐君毅对此有详细论述,他说:“至于中国古代思想之克就人之自身而言人性,则又始自即就人之面对天地万物、与其人生理想,以言人性。由此所言之人性,在先秦诸子中,或为人当谋所以自节,以成就而与天地参者,如在荀子;或为人当谋所以自尽,以备万物,上下与天地同流者,如在孟子;或为人当谋所以自复自安,以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者,如在庄子。”[5]7这说明战国时期以孟子、荀子、庄子为代表的人性论探讨的重点是人性的善恶以及如何在人性的基础上成就其理想人格。《管子》的情性论关注的重点是如何满足君主、百姓的情性,即实现他们与生俱来的本能,而不是讨论人性的善恶。
《管子》的情性论非常关注君主、百姓的情性。《管子·禁藏》载:“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源”应为“渊”,因避唐高祖讳而改。之下,无所不入焉。”[6]1015《管子》以求利避害为人的本性,但不同阶层所求之利不同,并以商人、渔人为代表来进行详细说明。《管子》又认为求利大致可分为两大阶级,一是统治阶级,他们以保持富贵、长治久安为利。如《管子·形势解》载:“贵富尊显,民归乐之,人主莫不欲也。”[6]1177《管子·明法解》载:“富贵尊显,久有天下,人主莫不欲也。令行禁止,海内无敌,人主莫不欲也。蔽欺侵凌,人主莫不恶也。失天下,灭宗庙,人主莫不恶也。”[6]1216二是百姓,他们以饮食、侈乐为利。《管子·侈靡》载:“百姓无宝,以利为首。一上一下,唯利所处。”[6]677“饮食者也,侈乐者也,民之所愿也”[6]652。《管子·形势解》载:“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于四方无择也。”[6]1175
但《管子》认为人的性情本非仅限于此。《禁藏》载:“凡人之情: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远之不能勿忘,人情皆然。”[6]1012《管子·形势解》载:“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恶死,莫不欲利而恶害。”[6]1169《管子·国蓄》载:“夫民者信亲而死利,海内皆然。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6]1259《管子·小称》载管仲说:“人情非不爱其子也,于子之不爱,将何有于公?……人情非不爱其身也,于身之不爱,将何有于公?”[6]608可见《管子》中人的性情包括好恶之情、喜怒之情、“亲信死利”、爱子、爱身、爱亲,等等。
上述《管子》性情包括的内容,如食色之欲、求利本能、好恶、喜怒之情,以及珍爱自身、亲近父母、保护后代,等等,这些都属于人们生而即有的能力,故而有学者称之为“生”[7]510,有学者则称之为本能[8]4。而以“生”或本能释性是孔子之前的人性论的传统。如《尚书·召诰》中的“节性”[9]186,《诗经·大雅·卷阿》中的“弥尔性”[10]440,乃至《吕氏春秋·重己》中的“节乎性”[11]35,这些“性”的原义都可称之为“生”,或指“人生而即有的欲望、能力等而言,有如今日所说之‘本能’”[8]4。其实不唯这些,《国语》《左传》中的“性”大多也是这种含义。如《国语·周语》记载的“先王之于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12]1。《左传·昭公十九年》载:“吾闻抚民者,节用于内,而树德于外,民乐其性,而无寇仇。”[13]1405无论“厚其性”,还是“乐其性”,其“性”的原义都可称之为“生”,或者说都是以维持百姓生存的本能欲望为其最主要的含义。由此可见,以“生”或“本能”释“性”是春秋以来中国先秦人性论的传统。《管子》的情性论正是继承了这一传统。
二、《管子》情性论以实现君主、百姓的情性为中心,即以治国为核心
《管子》论述人性内容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君主、百姓的情性。它既主张顺性情以治理国家,又主张反性情以安定社会。然而无论是顺性情,还是反性情,都是为了最终实现统治者国泰民安、长久拥有天下的性情。
(一)“顺人心,安情性”以治理国家
《管子》要求统治者“顺人心,安情性”[6]565,以达到“以情伐天下者帝”[6]1027的最高治国境界。这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有明显体现。
其一,政治方面,《管子》主张顺应人们的情性以治世,主要包括顺百姓四欲以治世,顺百姓之情以立法,驱逐违背人情的佞臣以安国等内容。
《管子·牧民》载:“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6]13《管子》认为所有的政治措施都应该建立在顺应民心的基础上,百姓普遍讨厌四种事物:“恶忧劳”“恶贫贱”“恶危坠”“恶灭绝”,统治者应当顺应民心,当使百姓“佚乐”“富贵”“存安”“生育”时,百姓自然“近者亲之,远者归之”[6]1204。管仲言行也证明《管子》的这一治国理念。《管子·戒》记载管仲认为百姓患劳、患饥、患死,但齐桓公却“使民不时”、厚征重敛、急刑重法,这非常违背百姓的情性,国家危在旦夕,并且认为明君应该顺应百姓情性,使民以时、薄赋敛、宽刑罚。齐桓公不但虚心接受了管仲的意见,并且付诸实施。《管子·大匡》也记载:“桓公践位十九年,弛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赋禄以粟,案田而税。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岁饥弛而税。”[6]368这充分说明齐桓公确实接受了管仲顺应民心以治国的建议,并以此为其富国强兵、称霸中原服务,还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在《管子》《国语》《史记》等典籍中都有记载。
《管子》还主张在立法、任能方面以人的情性为基础。《管子·法禁》载:“凡民从上也,不从口之所言,从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则民轻死,上好仁则民轻财。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则民不从,彼民不服法死制,则国必乱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6]312《管子》认为上行下效是人之常情,故有“上之所好,民必甚焉”之语。因此贤明君上在立法时应该以身作则,即“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这说明《管子》的立法是建立在百姓人性的基础之上。《管子·小称》记载管仲在病危之时,劝谏齐桓公远离易牙、竖刁、卫公子开方三人,其理由是三人的所作所为违背人之常情。“夫易牙以调和事公,公曰惟烝婴儿之未尝,于是烝其首子而献之公。人情非不爱其子也,于子之不爱,将何有于公?公喜宫而妒,竖刁自刑,而为公治内。人情非不爱其身也,于身之不爱,将何有于公?公子开方事公十五年,不归视其亲。齐、卫之间,不容数日之行”[6]608。易牙杀子做成美味以献给齐桓公,竖刁不惜自残身体以替齐桓公管理后宫,卫公子开方为官十五载而不回家探望双亲,他们三人的行为严重违背人情,因此管仲认为他们并非治国的忠臣,而是祸国的佞臣。这是管仲劝谏齐桓公远离他们的最重要的原因。齐桓公起初听从管仲的建议,逐易牙、竖刁、卫公子开方,但后来又因种种原因被迫召回并重用他们,但齐桓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最终身死国亡,霸业中衰。这在《管子》《史记》等典籍中都有详细记载。
其二,经济方面,《管子》主张利用人们的饮食、侈乐之情以发展经济,利用百姓予喜夺怒之情以富国、富民。
《管子·侈靡》载:“饮食者也,侈乐者也,民之所愿也。足其所欲,赡其所愿,则能用之耳。今使衣皮而冠角,食野草,饮野水,孰能用之?伤心者不可以致功。故尝至味而罢至乐。而雕卵然后瀹之,雕橑然后爨之。丹沙之穴不塞,则商贾不处。富者靡之,贫者为之。此百姓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独自为也,为之畜化。”[6]652《管子》认为饮食乃至侈靡之欲是百姓的性情。不过,不同阶层的人们表现不同。品尝最上好的美味佳肴,欣赏最动听的音乐,把蛋雕画了纹饰再煮食,把木柴雕刻了图案再焚烧……这是富商大贾梦寐以求的奢侈生活;饥时有食,寒时有衣,能够维持日常生活,则是贫困百姓的愿望。因此《管子》提倡富者侈靡,贫者则利用此机会做工以维持生计。“积者立余食而侈,美车马而驰,多酒醴而靡,千岁毋出食,此谓本事”[6]673。《管子》主张富人应大量消费余粮,尽情驰乐车马,纵情享乐于酒醴之中,这样做不但富人满足了侈靡之欲,穷人也因此找到了工作,《管子》称之为“谓本事”。“谓本事”,赵守正注曰:“谓,通‘为’,治理之意。‘谓(为)本事’可引申为促进了农业生产。此言侈靡消费反而有利于生产。”[14]466这说明富人侈靡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贫、富两大阶层的性情。
《管子·国蓄》载:“夫民者信亲而死利,海内皆然。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故民爱可洽于上也。”[6]1259“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赵守正注曰:“意即给予人民以有形的利益,而在剥削、夺取时不露痕迹。此种赐予时务求明显,剥夺时不露真情的明予暗夺政策,几乎贯穿在本书《轻重》各篇之中。”[15]350《管子》认为信任亲近的人、拼命追求财利以及喜欢赐予、厌恶掠夺都是百姓的性情,无可厚非。统治者应该利用百姓的这种性情,在赏赐时务必做到人人皆知,在掠夺时务必做到不露痕迹。这同时也是《管子》轻重诸篇的理论基础。如《管子》要求统治者少收掠夺财富明显的租税,而要多通过控制、调节物价的方法以获得巨额钱财,即多运用轻重理论谋取重利。《管子·国蓄》记载:“夫以室庑籍,谓之毁成;以六畜籍,谓之止生;以田亩籍,谓之禁耕;以正人籍,谓之离情;以正户籍,谓之养赢。五者不可毕用,故王者遍行而不尽也。故天子籍于币,诸侯籍于食。中岁之谷,粜石十钱。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岁凶谷贵,籴石二十钱。则大男有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子有四十之籍。是人君非发号令收穑而户籍也。彼人君守其本委谨,而男女诸君吾子无不服籍者也。”[6]1272-1273《管子》认为向百姓征取苛捐杂税,如同时征收房屋税、六畜税、田亩税、人丁税、门户税等做法是不可取的,会引起百姓的反抗。高明的办法之一就是通过提高粮食的价格以获暴利。这是因为每人天天都需要粮食,哪怕每石粮食加价十钱,国家所得的财富远远超过征收诸种杂税的总和。而如何调节物价,这其中既包括国家垄断粟币、盐铁、矿藏等重要物资,又包括利用市场、行政等手段调节乃至控制物价,还包括“采取轻重敛散之术,调节商品供求关系、地区之间的差异,打击富商大贾势力以调节贫富差异,引进别国的物资以及控制本国重要物资外流”[16]92等措施。这是《管子》“轻重十九篇”(自《巨乘马》第六十八至《轻重庚》第八十六,其中佚亡三篇,有目无文)[14]例言1所探讨的核心问题。
其三,外交方面,利用诸侯国君及其百姓恶危坠、恶灭绝及贪利的心理普遍施惠于各诸侯,为其称霸中原争取盟国。
《管子·牧民》告诉我们恶忧劳喜佚乐、恶贫贱喜富贵、恶危坠喜存安、恶灭绝喜生育不但是齐国百姓的本性,而且也是其他诸侯国百姓的本性。齐桓公正是利用人们的这种性情,平鲁乱、封卫、迁邢,从而争取了众多的盟国。《管子·大匡》载:“桓公忧天下诸侯。鲁有夫人庆父之乱,而二君弑死,国绝无后。桓公闻之,使高子存之。男女不淫,马牛选具。执玉以见,请为关内之侯,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邢,桓公筑夷仪以封之。男女不淫,马牛选具。执玉以见,请为关内之侯,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卫,卫人出旅于曹,桓公城楚丘封之。其畜以散亡,故桓公予之系马三百匹,天下诸侯称仁焉。于是天下之诸侯知桓公之为己勤也,是以诸侯之归之也譬若市人。”[6]439齐桓公在位之时,中原正处于“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17]213的危急时刻。中原诸侯国饱受内乱、战争之苦,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齐桓公深深忧虑百姓之苦,因此平定鲁国内乱,帮助鲁国君民摆脱内乱之苦;救助因戎狄入侵而亡国的邢、卫两国,并给予妥善的安置,使“邢迁如归,卫国忘亡”[13]273,这既是周王朝存亡国、继绝世的优良传统,又是齐桓公利用人们恶危坠喜存安、恶灭绝喜生育造福于各诸侯的体现,因此“诸侯称仁”“诸侯之归之也,譬若市人”。
《管子·霸形》载:“桓公曰:‘寡人以定三君之居处矣,今又将何行?’管子对曰:‘臣闻诸侯贪于利勿与分于利。君何不发虎豹之皮、文锦以使诸侯,令诸侯以缦帛、鹿皮报?’桓公曰:‘诺。’于是以虎豹皮、文锦使诸侯,诸侯以缦帛、鹿皮报。则令固始行于天下矣。”[6]456《管子》认为求利不但是普通百姓的本能,同时也是中原诸侯国君的共同意愿。管仲正是利用中原诸侯国贪利的本性在外交中厚施薄取以赢得中原霸主的地位。《管子·小匡》载:“桓公……使轻其币而重其礼,故使天下诸侯以疲马犬羊为币,齐以良马报。诸侯以缦帛布鹿皮四分以为币,齐以文锦虎豹皮报。诸侯之使垂橐而入,綑载而归。故钓之以爱,致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是故天下小国诸侯既服桓公,莫敢之倍而归之。喜其爱而贪其利,信其仁而畏其武。”[6]439可见齐桓公采取的平定内乱、封卫、迁邢、在外交上施惠于盟国等称霸中原的措施都是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因而赢得了中原诸侯国的衷心拥护,这是齐桓公能够称霸中原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反性情,以安定社会
《管子》在论述如何利用人的性情以治国时,不但注重顺应百姓的性情以治国,而且也重视反性情以安定社会。《管子》反性情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劝谏统治者违反好利的性情、节制欲望以求国家安定。《管子·禁藏》载:“夫众人者,多营于物,而苦其力,劳其心,故困而不赡,大者以失其国,小者以危其身。”[6]1012《管子》认为好物利乃至被外物所迷惑是一般君主的性情,但此种性情容易造成身死国亡的悲惨结局。《管子·七臣七主》载:“昔者桀、纣是也。诛贤忠,近谗贼之士,而贵妇人,好杀而不勇,好富而忘贫,驰猎无穷,鼓乐无厌,瑶台玉圃不足处,驰车千驷不足乘材。女乐三千人,钟石丝竹之音不绝。百姓罢乏,君子无死,卒莫有人,人有反心。遇周武王,遂为周氏之禽。此营于物而失其情者也,愉于淫乐而忘后患者也。”[6]989商纣王虽贵为天子,但他纵欲享乐,不顾百姓死活,最终被周所灭。这是典型的被外物所惑、沉溺于淫乐而忘掉祸患的君王。为此《管子》主张君主应在一定程度上节制自己的欲望,这样既有利于自身健康,又有利于社稷安定。《管子·禁藏》载:“立身于中,养有节。宫室足以避燥湿,食饮足以和血气,衣服足以适寒温,礼仪足以别贵贱,游虞足以发欢欣,棺椁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坟墓足以道记。不作无补之功,不为无益之事,故意定而不营气情。气情不营,则耳目穀、衣食足。耳目穀、衣食足,则侵争不生,怨怒无有,上下相亲,兵刃不用矣。”[6]1012-1013《管子·五辅》也载:“凡人君之所以内失百姓,外失诸侯,兵挫而地削,名卑而国亏,社稷灭覆,身体危殆,非生于淫謟者,未之尝闻也。何以知其然也?曰:淫声謟耳,淫观謟目,耳目之所好谄心,心之所好伤民,民伤而身不危者,未之尝闻也。”[6]201从衣食住行各方面控制奢欲,君主的思想感情就不会被外物所迷惑,同时,百姓也会安心生产,社会稳定、诸侯亲近,可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
其二,主张君主使用百姓时,在一定程度上反其情性而富国强兵。《管子·侈靡》载:“为国者,反民性然后可以与民戚。民欲佚而教以劳,民欲生而教以死。劳教定而国富,死教定而威行。”[6]661“反民性”,即违反民性。百姓欲佚恶劳、欲生恶死,但《管子》认为统治者应在满足百姓性情的基础上,可以使他们辛劳,使他们慷慨赴死。《管子·牧民》载:“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6]2百姓只有衣食充足,也就是说,只有满足了他们维持生活所必需的条件,他们才可以接受礼仪教化,才可以为国家任劳任怨乃至出生入死。这可从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中原的历史中得到证明。《管子·大匡》载:齐桓公即位后,忙于扩充军备以同其他诸侯国争夺中原霸主。当时齐相管仲劝谏道:“不可。百姓病,公先与百姓而藏其兵。与其厚于兵,不如厚于人。齐国之社稷未定,公未始于人而始于兵,外不亲于诸侯,内不亲于民。”[6]350管仲认为齐桓公即位之初百姓困苦,齐国内部矛盾重重,齐桓公应内亲百姓外附诸侯,这才是争夺中原霸主的正当途径。但齐桓公表面答应,实际上仍然发展军事力量,意图以武力迫使中原诸侯服从。但经过若干次失败后,齐桓公终于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接受了齐相管仲“内修政而劝民,可以信于诸侯”的劝谏,并付诸实施。《管子·小匡》明确记载了管仲辅佐齐桓公“内修政”的措施。他们实行“参国伍鄙”制以“定民之居”,使国、野中的百姓能够安心居住;实行“四民分业定居”制以“成民之事”,使士、农、工、商四大阶层能够世代乐业。齐国百姓安居乐业之后,又在“参国伍鄙”“四民分业定居”的基础上,实行“作内政而寄军令”,使齐国军事力量激增,齐国霸业得成。齐国百姓在“参国伍鄙”“分民分业”定居制度之下,安居乐业,加之“作内政而寄军令”制度以“参国伍鄙”制度为基础,因此由齐国百姓组成的齐国士兵才能够为齐国霸业出生入死[6]400-420。
可见《管子》对待君主、百姓的性情,不是一味的肯定或者否定,而是根据治理国家的需要而定。《管子》顺从君主、百姓的性情,目的是让百姓的生活得以保障、君主长享国运的愿望得以实现;其违反君主、百姓的性情,同样是为了君主的长生、国运的昌盛而服务。这说明《管子》中的顺性情、反性情都是为了治国的需要。
总之,《管子》人性论的主体是以治国为核心的情性论。这种情性论认为人性包括饮食之欲、好恶喜怒之情、“亲信死利”、爱子、爱身、爱亲等本能。《管子》认为要实现君主、百姓为代表的人性,既需要统治者在治理国家时顺应人性以治理国家,又需要在满足人性的基础上违背人们的好恶、喜怒之情,以达到安定社会的目的。另外由于《管子》的主体成书于战国中后期黄老学派盛行的稷下学宫,因而《管子》的人性论又带有鲜明的稷下道家人性论的时代特色。这种人性论在继承老、庄人性论的基础上,又有所完善。如提出了“心”在人性论中的重要作用,吸收了儒家的某些思想,认为仁、义、礼、法、诗、书、乐等世俗制度或典籍不但是“道”的产物,而且能够帮助回归自然的本性。《管子》人性论的这些内容及特征表明了人性的复杂性,及战国时期人们对人性的深入探讨所取得的丰厚成果,非常值得我们进一步学习和研究。然而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论证了《管子》中以治国为核心的情性论思想,其稷下道家人性论思想有待以后专篇论述。
[参考文献]
[1]匡钊,张学智.《管子》“四篇”中的“心论”与“心术”[J].文史哲,2012,(3).
[2]隋建华,吕海霞.谈《管子》人性论特色[J].齐鲁师范学院学报,2013,28(5).
[3]陈世放.《管子》人性论思想初探[J].社会科学辑刊,1997,(4).
[4]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5]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6]黎翔凤.管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
[7]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二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
[8]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9]王世舜.尚书译注[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10]周振甫.诗经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
[11]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
[12]韦昭.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1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M].中华书局,1990.
[14]赵守正.管子通解:上册[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15]赵守正.管子通解:下册[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16]尹清忠.管子研究[D]. 曲阜:曲阜师范大学,2009.
[17]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公羊传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李逢超)
[收稿日期]2016-01-12
[作者简介]张杰,男,山东荣成人,山东理工大学《管子学刊》编辑部副主编、副编审。
[中图分类号]B26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40(2016)04-0043-06
On the Theory of Natural Instincts inGuanzi
Zhang Jie
(EditorialDepartmentofGuanZiJournal,ShandongUniversityofTechnology,Zibo255000,China)
Abstract:The theory of human nature in Guanzi is to administer the state affairs well, which people are believed to be born with, thus, in this book, the theory of natural instincts is equal to that of human nature. Guanzi takes it as the core of the theory of natural instincts to meet the natural instincts of both the monarch and its subjects, that is, to run the state well and bring peace to its subjects. In contrast to the theory on human nature from Mencius, Xuncius and Gaozi, the theory of human nature in Guanzi has the following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firstly, the theory in Guanzi focuses more on the ability that the monarch and its subjects are born with, rather than on distinguishing evilness from kindness, which is in the sphere of conventional theory of human nature that flourished i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and the Spring and Warring Period; secondly, the theory on natural instincts in Guanzi centers around the running of the state affairs instead of around the morality improvement and achieving ideal character.
Key words:Guanzi; the theory of natural instincts; monarch; the subjects; run the state affai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