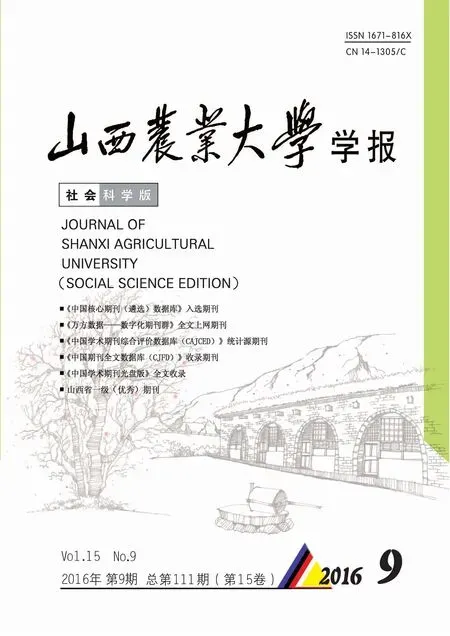当代农村社会变迁中的道德背反现象及重建
——以南京浦口侯冲社区为例
2016-04-04姜姝
姜姝
(南京农业大学 政治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当代农村社会变迁中的道德背反现象及重建
——以南京浦口侯冲社区为例
姜姝
(南京农业大学 政治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当代中国农村的社会变革发生在较短的时域之内,却带来了影响深远、作用深刻的社会效应。如果说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经历了变革的话,那么最重要的一点是——农村生活方式和农民的精神风貌有了异常丰富的形态。这种新形态的文化观念又对农村社会的发展施以复杂多变的影响。这些富于新形态的文化观念的变革反过来又作用于农村社会,对农村的政治秩序和道德秩序产生作用。以农村社会变迁中的道德背反为研究对象,结合对南京浦口区侯冲社区“支部+协会”制治理模式的实地调研,指出超越道德背反的关键在于构建法治秩序、培育政治文化和重建新乡情。
农村社会变迁;道德背反;侯冲社区
当代农村的社会变迁是十分剧烈而影响深远的。根据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报告,农村一直被看作是中国传统文明的根基和源头,乡土文化在新形势和新时期不能遭受断层和分裂,农村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和记忆中的故园。鉴于城镇化的急速建设和农村社会关系的极有力扩展,它们的综合效应怎样?如何在尽可能大的程度上防止或制止道德体系中心与物的背反,同时培育富于现代性的秩序意识?如何争取将社群关系中的新乡情和中国传统社会的情感内涵较为平衡起来,应对“陌生人社会”、“公共秩序”、和各种各样的“集体行动困境”?2015年9月,南京农业大学政治学院“江苏农村政治文明发展报告”课题组赴南京市浦口区侯冲社区展开调研,具体调研主题包括研究当代农村传统道德观念所经历的变迁和调整、所面临的挑战和困惑、所进行的拣择与重建。
一、群体关系的剧烈变迁
根据熟悉村史的计生专员吴主任*吴主任,女,1963年出生,复兴村人。自1992年开始担任复兴村妇女主任,主管妇女工作和计划生育。2008年村庄合并后,除了将计划生育的工作交给社区计生专干外,继续担任妇女、老人和儿童的工作。同时,作为党员和村委委员,吴主任负责联系劳动就业协会,并担任复兴片区片长。吴主任经常和助弱协会联系和沟通。事实上,据别人介绍,吴主任由于工作关系,对社区大部分协会和成员都承担工作任务,因此她对社区的情况比较了解。她的访谈纪要,尽管是一面之词,却显得更加重要。介绍,侯冲社区的人际关系正在经历着一个由“熟人体系”向“陌生人体系”剧烈变迁的过程。所谓的体系,既是一种这样的一种变迁,既印证了全球化和工业化环境对农村社会造成的震动和冲击,也呼唤着一种新型的道德关系来调节乡村社会的人际交往和共同记忆。
所谓的熟人体系,是在一种历史性的乡村文化环境之下,人与人之间形成的较为简单的、稳定的、影响有限的、作用因素相对单一的社群关系,这样的人际关系因 “熟人体系”相联结,并且受到当地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制约。群体成员间的主体性和独立性都局限在一定的区域或者地区之内,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或者“舆论”,因此具有浓厚的区域或者地区色彩。道德感,或者是表现为道德观念的人际关系是固定和稳定的,其中的道德主体成员具有固定性,变动性和流动性都局限于一定的范围之内。同时,传统文化的道德因素具有延续性,不同个体在群体中承担的角色和享受的资源都是固定的,具有显而易见的继承性和延续性。
侯冲社区符合以上的基本代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特征,并且承受了这些关系纵向与横向的叠加。比如,侯冲社区在合并了几个大的自然村之后,其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但仍然保持着原有乡村的乡情风貌。在社区结构中,侯冲居民的生活仍然是富于地方性的,人口的流动不是很频繁,相互之间也仅仅是熟人乡邻之间的交往,保留着各自相互独立的、整体看又是差序分明的社会格局。据吴主任描述“这样的稳定、相似与和谐的乡村生活让人感觉安全、踏实”,由此看出,传统稳定的乡村社会,是一个“看惯了”的社会,“熟悉的社会”没有多少陌生人的社会。这使得传统的道德标准和道德习惯具有非常重大的权威性。中国的农村是聚村而居,与国外的农村情况不同,因此中国农村的道德纽带具有多方面的、经常的熟悉和亲密的感觉,这可能来自于处理种种社会纠纷和社会摩擦的必然结果。这样的一种处理方式,可能不是最民主和最法治的,但是它却是大家都能接受的公平公正,因而是有效和重要的。早在六十年多前,费孝通先生即对这种通过“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而成的“差序格局”的农村社会结构进行了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革以及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加快,中国的社会结构及其成员个体角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经济关系的变化必然引起农村社会道德的变化。因此恩格斯断定:“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1]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农村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革,特别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重大背景之下。这种变革是与城镇化建设的步伐同步的。农村的社会结构和成员角色也因之改变。
侯冲在由村变社区的历程中,传统的旧道德观念在“陌生人体系”中是无法应用的。社区已经形成了侯冲高效设施农业基地、侯冲工业园、侯冲生态都市产业园、永宁镇农民资金专业合作社等产业结构,新的经济模式带来社会关系的调整。人们的收入增加了,且精神、心理、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都经历着巨大的改变,因此构建的社会关系也是崭新的。整个社会,从熟人社会进入到陌生人社会,从静态社会过渡到动态社会,附着于此的社会关系发生了新的震荡和调整,成员之间的道德关系也出现了新的模式和新的形态。
这种道德关系变迁的背景,是当代社会剧烈的社会变革,是由无所不在的“社会性”带来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全球化的生产方式给农村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压力。由此引发的道德关系不再是建立在地域、血缘和情感之上的社会关系,而是一种以现代工业为基本背景,因城乡人口流动(城市拆迁、农村工进城、新农村建设和区划调整)为动力形成的新道德关系。这样的道德标准和道德要求是建立在一定区域内大量、快速和多样化聚集的人口流动之上的。根据吴主任的介绍,侯冲社区的外来人口数已经达到了总人口的六分之一。数量上的更替足以表达转变,即传统农村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农村人口向城镇居民的转变、农业生产向工业生产的转变以及乡村经济向区域经济的转变。
简言之,这种道德变迁的背景是社会结构的急剧变革,影响了新型道德体系及其评价方式。在这样的社会变迁中,侯冲社区的变革仅仅是沧海一粟。很多情况下,社会的道德承受力还不够强大,人们的道德心理还没有准备好,但与此同时,这个社会的变革和生活方式的演进正在悄悄地聚集力量。这种心与物的背反,总会导致群体成员之间道德生活的背反。一旦新旧的道德体系的某些准则、原则和信条发生冲突,或者同一道德体系中的新旧观念和概念发生冲突,道德生活就不再显得那么完整和谐,诚如凯尔森所言:“自古以来,什么是道德这一问题是永远存在的,不知有多少人流了宝贵的鲜血和痛苦的眼泪,不知有多少杰出思想家,从柏拉图到康德,绞尽了脑汁,可是现在和过去一样,问题仍然未获解决。”[2]如果说,道德背反因为自相矛盾而丧失了是非标准和价值导向,道德的社会调节功能和社会价值功效将无法实现。这也是当前农村政治文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一个难题。
二、乡情流失的诸多背反
道德背反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便是乡情的背反。在侯冲社区的社会结构重组过程之中,对于乡情的渴念、对于真诚的诉求成为每一位社区成员的心理期望,但当经历了剧烈变迁的社会环境、错综复杂的群体关系、新型多样的人际关系之后,对于乡情的理想期望值与实际现实相距甚远。不少村民在访谈中表示“从土里长出来的孩子,也会受到土的束缚,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土是我们的命根,但现代社会要择地而居”。中国农村的乡情背反变化着自己的特色,除去其中的时代性和进步性,仍然有一些问题值得重视与思考。
第一,原有的乡情关系中存在的经济调节功能,在新时期成为决定一切道德行为的主导,并且锻造了道德模式的功利化特质。
在传统农业社会的秩序建构进程中,礼教和宗法作为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施加影响,并且维护了传统社会关系中的尊卑有序和社会和谐。在费孝通先生看来,传统的“差序社会”网络的“每一个结都附着一个道德要素”[3],道德的背反影响着差序格局中的社会关系,并且使得在一个盘根错节、相互制衡的“熟人社会”才会具有实质性的功能。
改革开放之前的侯冲社区,人际关系的调整与处理往往可以依据一种简单的“善恶”原则,比如村民之间的纠纷调节、村民利益受到侵害时的补偿诉求、村民之间的交往原则和行为规范,往往并不是通过政府和社会的力量(村干部和媒体)进行裁定,而是借助于“熟人社会”中的道德力量进行调节维权。在熟人社会的框架之下,有一些处理方式可能不是最接近于公平公正(或者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原则),但却是所有人都心悦诚服地接受和配合协调的。
在经济产业规模化与组织化之后,侯冲社区的经济实力有了很大的提高,村民对高品质生活有了更高程度的期许。在剧烈变迁的社会关系中,群体成员不断进行流动和变动,成员之间也由之前的“熟人体系”进入到“陌生人体系”。昔日道德的调节和教化功能,往往只有运用于熟人社会,才直接有效。在新的“陌生人体系”中,道德传统的自律和监督功能都会相对弱化,曾经作为粘合剂将人群联系在一起的乡情也会出现背反。传统的善的力量无法完成这样一种调节,因此这种复杂的人际关系会由现代社会中的经济关系所主宰,并且最终走向一种功利主义的交往。并不是说功利主义本身存在问题,而是说过去的乡情和道德已经无法完成新时期人际关系的调整功能,旧的道德规范和行为标准容易造就一种群体无意识的现象。
在社会的剧烈转型期,过去的旧道德难以适应新的人际关系调整。弗洛伊德曾经把人性的某些痼疾和缺陷称为“破坏性的本能”(destructive nature),这些本能包含了潜意识中暴戾、反抗、报复、嫉妒和贪婪的有害冲动。随着社会关系的急剧调整,这些个群体无意识现象就会表现为对既有秩序和规则的无视、挑战或破坏,而且这些现象往往是非预警的,具有突发性和偶然性。因为争抢公共汽车上的座位而引起的哄抢踩踏事件、在某些公共场合抽烟或喧哗的不文明行为、乘车不按照车票制定座位任意地乱坐或换座。这些群体事件在某种情势下会造成冲突,甚至是斗殴群架,造成的人身伤害和不良社会影响十分严重。
据吴主任介绍,侯冲社区也存在某些群体性事件,比如说拆迁问题、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问题、低保名额分配问题等等,村民与村民、村民与村委会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所幸事态都得到了良好的控制。回顾总结起来,村民之间、村民与政府之间没有能够形成一种稳固持续的调解机制,原本调节人际关系的乡情出现了背反,是冲突状态的本质属性。
群体关系中经济纽带的主导性,往往会导致村民参与政治的供应不足。按照亨廷顿的说法,国家的稳定与政治制度化存在着正相关关系——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稳定。如果国家制度化的水平能有效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民主需求,国家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就得以维护;反之,国家秩序就会紊乱甚至产生动荡。当一国公民政治参与需求增加时,如果政治体系无法给个人或团体的政治参与提供渠道,个人和社会群体的政治行为就有可能冲破社会秩序,给社会带来不稳定。[4]根据“江苏农村政治文明课题组”的调研结果,许多村民在面临人际关系和社会交往剧烈变迁带来的困惑与困难时,往往会对社区原本需要共同完成的公共职能产生冷漠和敌视。他们宁可信任至亲好友,也不采纳村干部或者调解者的意见。这一点,在某些基层民主的创新机制——比如江苏各地积极探索的村民协商会、公道会、百姓议事堂、民主听证会、政策咨询会等协商民主形式中,都出现了类似的民主参与度下降的现象。
第二,在新的社会组织关系中,交往对象复杂多变,传统社区的交往行为不再适应于旧乡情和亲情的制约。
在传统的熟人社会中,亲情和乡情作为一种联结的纽带,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润滑作用,能够调节乡村社会关系中的排他性行为或者利益。侯冲社区调研中村民经常提到的“乡里乡亲”一词,即是此意。如果说因为亲情和乡情的调节,使得某个群体事件的处理结果虽然不符合最大程度的公平公正原则,却是大家都可以接受并且同意的。
当代社会是一个由“陌生人体系”建构的社会,以快速流动、复杂多样的陌生人群为基本的交往对象,活动空间也不局限于一个固定的区域,而具有陌生性、变动性和多样性。在传统的代际关系之中,区域之间的继承已经不再是主导,跨区域或多区域和国际性的邻里关系、同事关系或者客户关系才是当今社会活动的主流方向。在崭新的社会变迁塑造的乡村结构中,村民之间的交往对象变得更加多样、丰富、复杂,在人际交往中必然存在着更多更为复杂的排他性行为或利益分配。
当社区中的人群遭遇到了新人际环境,联结工业生产和城市生活的物质力量会以一种功利化的色彩呈现和表现出来。曾经在熟人社会中赖以作为发展基础的道德自律、道德监督、责任意识都会变得相对弱化和淡化,在变动社会中的个体和人群的关系需要由新的纽带来调节,特点是复杂多变和变动不居。
据吴主任介绍,越来越多的居民反映出对原有乡村文化和乡情的依恋与怀念。他们怀念一家一户、有水有花、乡里乡亲、岁短情长的逝去时光。民众虽然并不富裕,却因共同的乡情文化有着较强的凝聚力和村庄认同。而如今,原有的乡情交往变成了一种功利主义的交往,侯冲社区的人际关系也变得更加复杂和脆弱。在由传统亲情和乡情建构的熟人社会向现代新型的社群关系转变时,社区的人情往来显得更加易变。这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原有的人际关系纽带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断裂,而新的乡情意识和情感认同还没有相应地建立起来。在除旧迎新的历程中,旧乡情会相应地失去有效的约束性和现实规范性。
三、超越背反的道德重建
转型期的乡村社会具有高度的复杂性,以此为背景的新型社群关系也显得具有那么多的易发性、多发性和非预警性。在追问“为什么需要道德”这个问题时,乡村社会中的道德问题需要更多的本质和目的。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人性自我完善”、霍布斯的“理性追求自我利益”和边沁的“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我们必须对社会剧烈变革下的农村道德拣择以及重建提供某些说明和辩护,以便对道德和道德建设的本质达到进一步的理解。
第一,提升道德建设内涵,构建良好的法治秩序。
提倡道德不是为了空洞的道德,而是为了建立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我们需要重视熟人社会中的善,更要建设陌生人社会中的善。
提倡道德建设并不是为了实现空洞的道德目标,而是为了由此建构一个秩序良好的乡村社会。在熟人社会中,道德所创造的“善”的秩序是重要的,而在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陌生人社会,“陌生体系”中的善更为关键。这种善,表现为农村社会秩序建构之中,则是公共秩序的建构与实现。
侯冲社区已经积极发展了“支部+协会”的治理模式,以充分调动群众参与地区公共秩序建立的积极性。根据工作需要、农民需求,由社区党组织牵头,把党员和部分群众组织起来,领办一些社会事务管理类协会。由于侯冲社区着力打造旅游景点,因此对社区范围内的卫生状况极为重视,公共卫生协会因此从2013年开始对社区一些小组进行整改。例如,2013年对复兴村牛王殿小组进行卫生改造,主要任务有重修水泥马路、公厕改造计划和猪圈整理计划,主要针对牛王殿小组垃圾乱堆乱放的现象,现已完成。同时,公共卫生协会也完成了对侯冲村6组的卫生改造计划,专门进行雨污分流计划,着力打造生态居民点,现已改造完成。公共卫生协会还负责其他一些日常工作,例如扬尘管制、例如路灯维修等。
从上述协会的公共职能来看,如果没有良好的法治秩序作导引,熟人社会中的道德之善,容易转化成为一种乡愿之善。比如侯冲社区村东头的空地,就曾经堆满了垃圾,这是村民普遍认为“公地是公共事务,与我无干”的典型代表。就推己及人而言,陌生人社会更加需要这样的一种道德精神,正如孟子曾说过的,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
事实上,某些社会秩序的挑战者,甚至是某些群体事件的责任者,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具有非常恶劣的道德品质。他们大多具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甚至在邻里之间、工作单位中都有着出色的表现。在某些恶劣情绪或者不良沟通现象的影响下,一旦无序行为造成了严重的问题,会造成追悔莫及的结局出现。比如,农忙季节,侯冲社区往往会出现村民因为争水而大打出手的情况。这些村民,平时也是打成一片,友好相处的,但在缺乏公共秩序的管理和引导之下,不讲秩序的善容易转化成一种恶。没有秩序的善即是一种“乡愿”之善,是对善的一种背叛。如果没有良好的法治秩序作保证,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坏事的帮凶。
第二,建构农村政治文化,创建制度场域文明。
阿尔蒙德对政治文化和道德建设有过这样的论述:“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由经验信念、表达符号和价值系统组成,它赋予道德的运作以秩序和意义,限定了道德行为所发生的情势,为道德提供了主观导向。”[5]。十八大报告也指出:“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政治文化的培育,对于解决乡村社会的道德背反问题,建设和谐稳定的农村社群关系,具有基础性的调节作用。
农村政治文化的健康培育需要“乡域”政治制度文明的建设。在乡域的空间里,既包含了政治权力的运作,也包含了不断争夺的社会空间。乡域中的不同单元有能力利用种种策略进行竞争博弈,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利益、社会利益相互调节、竞争博弈的网络空间,也存在着“权力场、政治经济场”等元场和“科学场、艺术场和宗教场”等非原场。[6]这样的场域构建充满了空间的开放性、实践的延展性和政治的多维性,呈现出异样的网状化特征。
通过创建制度场域文明,可以通过一个崭新的视角来观察中国农村道德秩序的重建问题。正如邓小平曾经深刻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7]乡村制度场域文明包含着降低交易成本和缓解信息不对称等一般场域的基本要素。
比如,侯冲社区“支部+协会+合作社”治理模式的制度构建,能够为人们的行为创造大量的调节性规则,成为调节新型社群关系的一项行为标准。在乡域创造的制度框架下,契约、准则以及准协议提供着信息,形成某种合理而又有效率的制度,降低交易成本,实现权利让渡,促进农村群体关系中政策的协调,不再出现彼此阻止对方目标或利益实现的行为。侯冲社区成立的农家乐专业管理合作社,有助于促进农家乐管理规范化,把农家饭店、农家旅社的经营者召集起来,形成一个行业团体,通过行业自律、提供信息、促进交流来规范群体之间的交往行为。
第三,培育乡域情感内涵,留住幸福家园之梦。
传统农业社会中的道德因素,已经难以调节、约束或化解现代复杂社会中“陌生人体系”的复杂关系。随着熟人体系向陌生人体系的转化,高度复杂的社会需要完成一种良好秩序的建构。所以,如果说道德建设在调节熟人社会中还有一定作用的话,在保留传统文化和乡土意识的同时,在新的社会关系之中,更需要一种新的乡情培育,丰富乡情内涵,以超越简单的亲情纽带联结。
所谓的新乡情,表现在新的社群关系之中,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宗族、血缘和地域因素,将扩展后的地域和新兴经济生产方式带来的感情与道德因素加以变革。这样的新乡情具有开放性、多元性和可调性。当经济发展代替政治斗争,当人际协调代替阶级矛盾成为调整日常社会生活的主要任务,当我们将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今后的奋斗目标时,道德背反的重建与超越即是对这一变化中的社会生活的积极适应,是用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指导道德生活的创新性伦理成果。[8]构建新乡情的这一转换扩大了道德的主体范围,在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多样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农村的道德关系趋向于开放、多元和易变的情况下,需要进一步“引导人们在遵守基本道德规范的基础上,不断追求更高层次的道德目标”(《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加强新乡情培育,丰富乡情内涵,也蕴含了“中国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充满正能量的“中国梦”,意味着个人的前途命运和国家息息相关。让乡情真的有情,就是实现农村道德建设的“中国梦”。快速推进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中国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推动着农村人的心灵家园的变迁。生产方式的改变是主动适应,生活方式的改变是被动适应,亲情与乡情、家庭与宗族、历史与现实、区域依恋与迁徙冲动的能量转移,是一次文明嬗变,意味着人类历史上最为漫长而又饱经沧桑的农业文明正在大踏步赶上时代潮流。在城市辛苦劳作的农民工们,梦回故乡,依稀是红砖青瓦、绿柳白杨,小院矮墙、大豆高粱。城镇化和现代化留下的心理痕迹,不仅存在于这一代人,还会在今后几十年影响几代人,改变几亿中国人的人生轨迹。培育新乡情,是一个几亿农村人口顺利融入城镇生活和现代文明的漫长过程。城镇化说到底是中国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和家园的变迁,要有高楼、更要有人气,要有一定城镇规模、更要有较高幸福指数。
就侯冲特色而言,助弱扶贫协会是侯冲开会最多的协会,因此也是最为重要、承担社会任务最多的协会之一。首先,每年组织社区老年人开展免费体检,提供老年人的生活补助,开设老年人活动中心例如广场舞和老年棋牌室,同时还为老年人协调家庭纠纷。其次,承担暑期亲子活动,例如开展暑期校外免费辅导班,学习剪纸手艺和文化科目学习,同时助弱协会有时候也负责调解家庭感情纠纷和妇女感情问题。第三,关注儿童教育和奖励高考的事务,针对那些困难儿童、残疾儿童以及家庭突发性困难的儿童,助弱协会每年定期为他们提供学费资助,以便他们能够继续接受教育;奖励本社区考上本科和专科的高考生,以鼓励他们的努力学习。从上述活动中可以发现,助弱协会为侯冲社区承担了大部分的民政和村庄社会事务,为侯冲社区新乡情的培育奠定了基础。
在城镇化带来不可阻挡的农村社会变革中,道德背反现象渗透在农村社会生态的每一个角落,对农村道德风尚、政治结构和社会发展都有着忽明忽暗而又如影随形的影响。通过南京浦口侯冲的例子我们可以发现,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法治秩序建设、培育新的乡情文化等等,这些道德重建的举措应当被广泛地应用于当代中国新农村文化建设领域。在此语境之中,农村的道德建设也正在经历着一种有力的现代化转向,成为一种越来越具有现代性内涵的社会文化形态。
[1]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7.
[2][美]凯尔森.什么是正义.[J].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7(1):32.
[3]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27.
[4][美]塞缪尔·亨廷顿著.李盛平译.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29.
[5]G Almond.Comparative Politic System[J].The Journal of Politics,1956, 18(Aug.): 396.
[6]杨善华,谢立中主编.西方社会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48.
[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7.
[8]黄明理.社会主义道德信仰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9.
(编辑:武云侠)
Moral antinomy phenomenon and its reconstruction in the social change of rural China——an example of Houchong Community
Jiang Shu
(CollegeofPoliticalScience,NanjingAgriculturalUniversity,Nanjing210095,China)
The contemporary rural China is experiencing great social change. With the change of production style and life style, the moral connotation of the rural people has taken on a new form. Such new type of cultural identity has great effect on the rural societ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moral antinomy in theruralsocial transformation,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research on "communist party+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mode in Houchong community in Nanjing Pukou Zone, so as to point out that the key elements of going beyond moral antinomy is to construct the rule of law order, cultivate political culture and reconstruct new nostalgia.
Social change in rural China;Moral antinomy;Houchong Community
1671-816X(2016)09-0623-07
2016-05-06
姜姝(1988-),女(汉),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政治理论思想方面的研究。
2015年度南京农业大学人文社科重大招标项目(SKZD2015004);南京农业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新农村研究专项(XNC2012008)
D267.2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