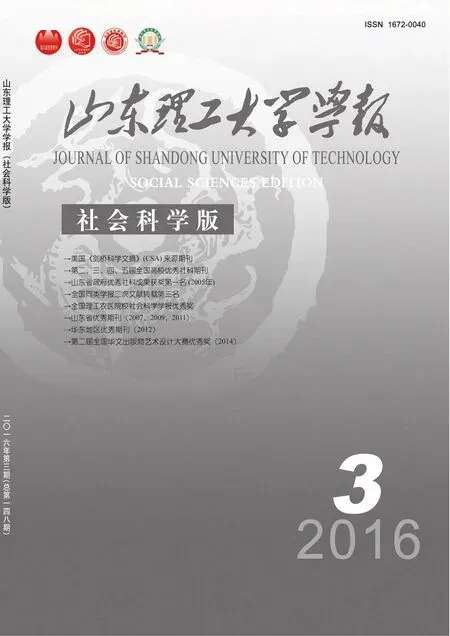重访灰色地带:策略实践与文化政治
——从《双城故事》看华莱坞电影书写
2016-04-03洪长晖
洪 长 晖
(浙江传媒学院文化创意学院,浙江杭州310018)
重访灰色地带:策略实践与文化政治
——从《双城故事》看华莱坞电影书写
洪长晖
(浙江传媒学院文化创意学院,浙江杭州310018)
上海从孤岛到完全沦陷,再到重回国民党统治,抗战时期共计八年,整个上海电影界呈现出错综复杂的面貌。这一时期的电影作品在传统电影史书写中被置于二元框架下的归属,因而处于一种消声失语的状态。傅葆石博士的研究专著《双城故事》有助于我们重新读解这段历史。在那个复杂的场域里,借助电影剖解、阐发那个特殊语境下的社会生存状况,电影人及其作品呈现出的策略实践、反映出的文化政治,值得重新书写。
《双城故事》;电影文学;中国早期电影;华莱坞
20世纪早期的中国电影,不仅伴随着坎坷的现代性进程,而且由于相伴相随中华民族的抗争历史,从而额外具有突出的民族主义样态。这种多变姿态和多元格局在抗日战争期间就显得更为明显,又反过来增加了读解和品味这段历史的难度。长期的回望实践中,二元对立的框架被简单化地定型为认知图式,英雄与汉奸、“自由中国”与沦陷区、抗争与附逆,一系列的标签,既构建了整个电影世界的政治分野,也推演成对不同区域生产的电影作品的质量判断。而显然地,这样的认知一方面显示了当时的社会语境下权力的分配,一方面则意味着大量的模糊地带被忽视,存没于其间的人和事则成为被侮辱与被损害,且无力发声的牺牲者。
傅葆石博士的《双城故事:中国早期电影的文化政治》(刘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以下简称《双城故事》)就试图再现流动于上海和香港两座城市间的“灰色地带”,描摹出中国电影在当时特定的国家政治环境中腾挪闪躲、左支右绌的姿态。
一、如何理解沦陷区电影?
中国电影事业的起步与发展都和西方尤其是好莱坞电影紧密勾连,而作为十里洋场的上海则是这种联系和纽带的见证及体现,即使是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1938年上海沦陷之后,这种联系也没有中断。于是乎,当我们审视沦陷区电影时,也就没有理由忽视这层关系所带来的深层影响,甚至于,因为沦陷区的独特地位,以及因之而来的复杂纠葛,这层关系就更为微妙、多元和动态,考察它则更见阐释者的想象力与洞察力。
傅葆石博士所瞄准的就是沦陷区电影在动态的历史进程中所呈现出的复杂面貌。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经提出“同情之理解”,以求从诠释者的自我心性休养为基础,对诠释对象(文本)视之为人的生命表达方式,从而达致内在共通*关于“同情之理解”可以参看周可真的《中国哲学诠释方法——“通情之理解”的源流及其限制》一文。该文见《河南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5至9页。陈先生原话为“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傅葆石的研究在这里就可以印证了陈寅恪先生的警语。
《双城故事》中特别剖解了沦陷区电影的诸般样式。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本文提到的“沦陷区电影”并不是一个严谨的时空概念,它既包括孤岛时期(1937-1941)的租界区域,也包括上海完全沦陷的时期(1941-1945)。而之所以不做这样严格区分,是因为在笔者看来,这些时空区域里的电影作品与实践都具有相当一致的策略性,处于这些时空中的电影人(和其他普通知识分子)均普遍地在心灵上被动割裂了与“自由中国”的联系,并且由此而来产生极大的愧疚、纠结乃至幻灭。尽管在程度和方式上不同个体会存在各种区别及变体,不过并没有给研究者的观照造成根本性障碍。
那这种策略究竟如何?傅葆石用了一段略显拗口的话,精准地涵括了其内在精神:无关政治的娱乐通过有意地非政治化具备了重要的政治意义(apolitical entertainment that was deliberately depoliticized became significantly political)。对这句话的理解可以从两个层面上来看,首先,作为一种现代大众媒介,电影本身就是“充满这戏剧化的感性和思想的浓汤”,从其诞生之初就更多地是扮演着娱乐大众的角色,这样的功能定位在战前中国尤甚。李欧梵先生在《上海摩登》一书里就已经指出,早在上海沦陷前,电影院已经成为充满现代因素的公共场所,而电影文化——无论是看电影,还是翻阅影院装潢杂志和影迷刊物——已经是现代生活的点点滴滴了[1]118。另一方面,而且也是更重要的一层,刻意地将电影作为娱乐,并限定于此,既是沦陷区电影的生存策略,也是一种“非暴力不合作”的姿态。傅葆石在书中讲得非常透彻,“沦陷电影并不完全是相对于自由中国的国民党官方电影的汉奸文化工具,相反,它建立了一种新的公共空间,让沦陷区的民众在这个空间内参与构建一种娱乐文化话语,逃避日本帝国主义操纵和建立的‘大东亚’侵略文化”[2]163。
众所周知,在沦陷后的上海,由于日伪合作提出所谓的“国策电影”运作方式,强行要求电影人进入中华电影股份公司(简称“华影”),否则就面临生存危机。因而以非此即彼的“忠奸”二元模式(即杀生成仁的“英雄”与为虎作伥的“汉奸”)来看待沦陷区电影人及其实践,显然是不合适的。在傅葆石看来,“沦陷电影提倡中国的民族传统和民众的欲望和想法,而沦陷区的统治者则视这种形态的电影为庸俗不堪和毫无价值:也就是说,这仅仅是娱乐!换句话说,沦陷电影一方面和日本人妥协,一方面又抵抗了他们的文化统治”[2]163。
质言之,每一个处于沦陷区的人都是鲜活的个体,他们各自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承受战争带来的苦难或冲击。这种回应的途径纷繁多样、五花八门,而其指向又殊途同归,意图在逼仄的现实空间里寻求生存乃至生活,所差者或为尊严、或为物质,虽说求仁得仁,但总体上则组成一个规模可观的“灰色地带”。
二、沦陷区电影对谁重要?
十里洋场的上海无疑是民国时期最具现代性的中国都市,这种“现代性”识别甚至在内地和东南亚都具有超高的影响力,“外地人一有机会到上海,就会迫不及待地去看好莱坞电影或到南京路购物,寻找融入大都市的感觉”[2]41。而在20世纪20~40年代的中国电影版图中,上海电影一方面形成与“以北京为中心的非商业化的政治教化电影或称京派电影”相对应的“海派电影”,这“海派电影”既指一种“与特定文化形态密切相关的电影流派,同时也指中国电影发展的一个阶段”[3]7,它是以现代大众商业文化为基本特征的。另一方面,上海电影还在商业驱动力作用之下,向外拓展,从而在香港乃至东南亚一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然,这种作用是一种双向的过程,在时事格局变动之下,香港以后来居上的态势最终取代了上海成为亚洲电影的又一中心。这也正是傅葆石在其论著中所着力勾勒出的演变图景。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上海电影在整个抗战时期的位置不仅没有由于战争而削弱,反而成为各方角力和争夺的舞台。换言之,上海电影的重要性越发突出,这也就很好理解为何日方开始时试图建立像“满映”那样以生产殖民电影为目的的“宣传机器”,后来虽然放弃这一企图,但仍然整合中国电影生产机构成立中华电影公司(1939年于南京成立)、中国联合制片厂股份公司(1942年上海川喜多长政主事,张善琨等参与其中),在后期更是直接以控制胶片等资源的方式尝试掌控和导引上海电影的方向。而一旦这一目标未能完全实现,日方则会大加指责,认为“中联”电影既没有教导沦陷的人们“新东亚秩序”,也没有教育人们去认识“大东亚战争”的本质[2]174。
日方的这些不满与指责恰恰提供了从另一视角审视沦陷区电影的可能。可以稍显化约地说,日方控制电影生产的意图非常明显,就是要为其殖民政策服务,强化的是电影的政治宣导功能,因而绝不满足于“让人们沉浸在娱乐传统”中;而对于沦陷区的电影人来说,电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这也是他们为什么没能丢开电影(这是他们的生计所系)前往“自由中国”的最重要原因,由此,如何在这样的日常生活实践中,既能够巧妙地传递出他们的无奈与不甘,以求化解或冲淡他们不能“坚决抵抗”的道德焦虑,又不至于挑战殖民者的底线导致生存可能的湮灭,就成了电影人的策略应对。
法国社会学家德赛图就非常明确地指出,日常生活就是“透过以无数可能的方式利用外来的资源来发明自身”,他将日常生活看成一个在全面监控之下的宰制与抵抗的斗争场域,职是之故,人们的日常生活并没有在技术专家政治的规训网络之中趋于同质化,人们亦非毫无抵抗能力[4]182。无独有偶,詹姆斯·斯科特也在对东南亚农民的“怠工”研究中提出“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隐藏的文本”(Hidden Transcripts)这样的概念,尽管斯科特分析的对象是农民在面对生产压力时所做的各种隐性抵抗,但是显然,它也同样适用于对沦陷区上海各色人等的生存策略和文化政治的分析。也只有充分考虑这些日常的潜行于生活中的抵抗,才能够避免萨义德所批评的那种“抽离历史时空的文本世界”,回到沦陷区电影的“灰色地带”,因为正如斯科特所说,在侵略强权下的空间中,“不公开的异议”是能够被安全的表达出来的[5]4。
正因为借助电影的“表达”,上海电影人不仅使生产电影或从事与电影有关的工作变成个人维持生计之道,而且还成为他们承担和减少(看似矛盾,其实恰是合二为一)身处殖民统治的焦虑与愧疚的一种自我宣称。亦即是说,与作为殖民者的日方将电影看做殖民宣导的工具不同,上海电影人不仅将电影视为物质意义上的,更是文化政治意义上的,而如其宣称,之所以选择了娱乐化的表达,其实只是特定殖民情境下的策略实践,一种煞费苦心的策略实践。
“娱乐不仅仅是娱乐”。但是处在“自由中国”的国统区人则不会这么认为,毫无疑问,国统区也非常看重电影,尤其是看重电影的战斗动员价值。不过,也正由于战争的缘故,国民党失去了对上海这一“东方好莱坞”的控制,而后方薄弱的产业基础、贫乏的物质条件、短缺的资金供给,都直接制约了高品质的抗战电影的生产可能,于是乎,寄望于“孤岛”时期的上海电影自是应有之义,而面对滔滔的娱乐电影又自然是“恨铁不成钢”——因为,对于战争动员,电影太重要。
三、个案重审:《木兰从军》“遭焚”事件
如上所示,沦陷区电影成为一个多方力量角力的场域。而1939年由新华公司(张善琨所有)拍摄的《木兰从军》上映前后的遭遇则恰恰是一个极佳的分析案例。
张善琨成立的新华公司可以说是淞沪抗战结束后,上海电影迅速恢复的一个标志。在个人影响力、与日方暧昧关系等多重因素作用下,新华公司很快成为上海电影界最大的公司。数据显示,1939年新华公司共生产了24部电影,超过当年全上海电影总产量的一半,而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由陈云裳主演的《木兰从军》(卜万苍导演,欧阳予倩编剧)。
《木兰从军》是一个典型的借用中国传统故事编排的电影,在当时的特定语境下,木兰替父从军的传奇就成为一个充满隐喻的象征,影射着空前的民族危机,木兰本身也演化为一个洋溢着爱国激情的英雄符号。正如当时剧作家阿英的评论所言,“在民族危亡之际,所有的人都必须团结起来,奋战救国,这是男人和妇女都应该做的”[6]33。这样一个绝佳的电影选题,再加上张善琨高超的运作技巧,将木兰的扮演者陈云裳塑造成一个既有现代观念又有传统美德的女性形象。这样的形象一方面迎合了上海市民的欣赏需求,一方面又淡化了陈云裳外来者(陈云裳来自香港)的反差,使陈云裳成为当时炙手可热的巨星。而电影也同时取得史无前例的成功,自首映之日起,《木兰从军》连映83天,打破了上海电影的一切票房纪录,也正因为《木兰从军》的成功,进一步奠定了张善琨在上海电影业的不可撼动的霸主地位。
对于这样一部古装剧,上海评论界一片溢美之词,如有评论就这么写道,“《木兰从军》告诉我们,对外国入侵我们应该如何回答,怎样回答”。与此同时,该片还引发了一波古装片风潮,根据胡菊彬的研究,1938~1940年间发行的影片中有一半都是历史古装片,而1939~1940年更是被称为“古装年”,此类影片远超50%[2]163。以讲述古代故事来书写当下,几乎成了上海电影业的一种套路,而此间的电影人也以此作为自己不忘国仇家恨的佐证,他们自述为“电影的话语资源、框架、剪辑和舞台布置都越来越和叙事目的相融合”[7]120。可以说,《木兰从军》的拍摄如果不是让上海影人重新站到民族大义的制高点的话,至少也荡涤了他们心头的屈辱感与愧疚感。
可惜这恐怕是一厢情愿的自我感觉良好。因为在国统区的人看来,并不存在可以苟延残喘的“灰色地带”(在忠奸二元的对立格局中,他们是不可能承认有这样的可变空间的),抗日文艺是整个社会主流的思想,只要不是为抗日服务的,那就是投敌的,所差者间接与直接、程度深浅而已。尽管整个抗战时期,“自由中国”生产的电影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乏善可陈,重庆在七年间仅仅生产了20部故事片和63部记录片(显然与上海不在同一量级),可是这并不妨碍他们能愤怒地声讨上海电影界,当时的中央电影制片厂厂长罗学濂有一段话很有代表性:“电影从业员除了部分优秀的投奔内地,和部分投机的赴港掘金或躲避外,留在上海毕竟还是少数……孤岛的极少数电影人落水,有少数的虫豸蜷伏在黑暗的角落里投机买卖,更聪明的则摄制意义相异两种拷贝,甚至巧立名目的影片,在变相的出卖灵魂……穆时英、刘呐鸥之流已被‘诛伏’……中央政府还会有更多的制裁。简单说,上海电影正处在忠贞无耻的生死斗争时刻。”[8]431
在这样的愤怒声浪中,上海电影界的骄傲《木兰从军》就在内地遭遇了“焚禁事件”。1940年1月,经历了重重波折和关卡之后,《木兰从军》在重庆公映,引起轰动的同时也带来各种非议,当月27日下午场放映该片时,有人爬上舞台叫喊,指出该片导演卜万苍是上海伪市委党部执委,因此该片是一部用爱国主义的名义去替日本人宣传的汉奸电影,强烈要求烧毁该片,群情激奋之下不仅将该片胶片焚烧,还引发现场一片混乱,不得不靠军警维持秩序。
尽管事后调查发现这是一起暗中精心策划的事件,可是恰恰也折射出重庆方面的文化人对忠奸分隔的敏感——事实上,他们对《木兰从军》的声讨也聚焦于导演制作人、公司等的背景,而不是电影内容本身。焚烧《木兰从军》,可以看做是“自由中国”对那些身处上海的电影人的一次敲打和警告,而包括张善琨在内的上海影人都深感屈辱,他们再次意识到没有旗帜鲜明地向日本人抵抗、宣示,就不可能被民族主义阵营所容纳和接受。这种屈辱感既让上海电影人越发谨小慎微,又不得不游走在“灰色地带”,等候黎明到来。
四、华莱坞影史书写——另一种可能?
时经七十余年,当下的中国电影正面临着一个全新的发展契机。如果让当年的民族主义者看到这一切,不知当作何感想。历史不能假设,但却需要不断地书写。自国内传播学者邵培仁先生提出“华莱坞”的学理概念以来,有关的论述就成为一个热点话题。其中讨论较为突出的是“华莱坞”的概念界定与内涵指向(关于此,笔者也有自己的浅见,在此不再展开),不过,有一点邵培仁先生已经讲得非常清楚,提出“华莱坞”概念不是要向“好莱坞”宣战,而是一种“竞合多元”的关系。
事实上,当我们回顾中国电影史的时候,就可以发现好莱坞一直是中国电影的对话对象。这也是一个显见的事实,只是另一个史实却容易被忽视了。那就是,好莱坞作为一种电影力量几乎从未停止过对中国电影的影响,可在这层影响之下还有其他的力量曾经作用于中国电影——如果说这些其他的力量没有改变中国电影的进程,至少也曲折地形塑了中国电影的风貌。换言之,华莱坞电影无疑要回溯过去,在时空中成就现在与未来;而在这种回溯的过程中,或许要发掘出潜藏着的“灰色地带”,析出曾经曲折影响中国电影的日本力量(也许还有之后的苏联、东欧力量)。
傅葆石先生的著作显然没有从这个层面上来讨论,他自己也说得很明确,《双城故事》不应当被视为一部电影史作品,而是借助电影剖解、阐发那个特殊语境下的社会生存状况,作为“人”如何应对外来力量形成自己的策略实践,而这种策略实践又该被做出怎样的文化解读。但是,正因为傅葆石对“灰色地带”的描摹,我们可以看到历史脉络中的华莱坞电影在抗战语境中的多元光谱,忠奸背离下的“灰色上海”。华莱坞电影史的写作除了关注那些影响深远的电影事件之外,还需要在一种日常生活观照的范式中,去审察那些一个个的鲜活个体在各种作用力的冲击之下如何腾挪闪躲,他们又有着怎样复杂的心态?这样的华莱坞电影史书写将是丰富、细腻和动人的。
[1]Leo Ou-fan Lee.ShanghaiModern: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1930-1945[J].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
[2]傅葆石. 双城故事——中国早期电影的文化政治[M].刘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3]盘剑.选择、互动与整合:海派文化语境中的电影及其与文学的关系[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4]吴飞.“空间实践”与诗意的抵抗——解读米歇尔·德塞图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J].社会学研究, 2009,(2).
[5]傅葆石.灰色上海,1937-1945:中国文人的隐退、反抗与合作[M].张霖,译.刘辉,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6]阿英.关于木兰从军[J].文献杂志,1939,(6).
[7]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8]重庆市文化局电影处. 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电影[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杨爽)
Revisiting the Grey Zone: Tactics Practice and Cultural Politics——Huallywood Film Narrative fromStoriesofTwoCities:CulturalPoliticsofEarlyChineseMovies
Hong Changhui
(SchoolofCulturalCreativity,ZhejiangUniversityofMediaandCommunications,Hangzhou310018,China)
From being isolated to being totally occupied and to being under the reign of Kuo-Min-Tang, the city of Shanghai underwent complex changes together with its filmdom during the 8 years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The movie products of that period of time were subjected to dual frames of attribution in traditional film narrative, and thus stay silent and invisible.StoriesofTwoCitiesby Fu Baoshi serves as an effective way for people to re-interpret that period of history. Confined to such a complex situation, film-makers depicted and interpreted the social existence situation in that special context, and the tactics practice presented in their works, the cultural politics reflected by the works all deserve reconsideration.
StoriesofTwoCities; movie literature; early Chinese movies; Huallywood
2016-01-29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梦影视的创作与传播策略研究”(15ZD01);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传播研究院重点项目“民族现代性的历史影像呈现与国家认同研究”(Z431Y16516)。
洪长晖,男,安徽绩溪人,浙江传媒学院文化创意学院副教授,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博士后,传播学博士。
J905
A
1672-0040(2016)03-006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