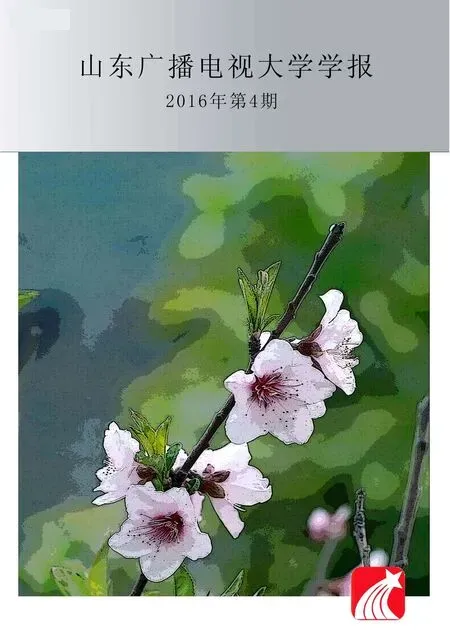倪瓒题画诗刍议
2016-04-03景惜颜
景惜颜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倪瓒题画诗刍议
景惜颜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倪瓒是元代画坛名家,同时也是诗坛名家。通过对倪瓒题画诗种类、内容、风格的分析研究,展现其题画诗的清简之美,隐逸之志,以及诗与画的和谐互补。希望能揭示诗与画两种艺术门类高度融合之魅力,亦可为尚显薄弱的元代诗歌研究添砖加瓦。
倪瓒;题画诗;元代诗歌
一
题画诗是中国古代诗歌园圃中的一朵奇葩,它是诗歌与绘画这两种不同艺术结合的具体体现。诗人因画生思,遂而援诗入画,由是达到“诗中见画意,画里见诗余”的艺术效果。广义上的题画诗可追溯至《诗经》里的图赞诗,由于宋元文人画之兴盛,题画诗在元代诗歌里成为一大门类,在数量与质量上都蔚为大观。
元代诗歌的研究方兴未艾。近年来,元代题画诗的研究正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如王韶华之专著《元代题画诗研究》,徐翔之硕士学位论文《“元四大家”题画诗研究》等。清人顾嗣立所编《元诗选》中收录340位诗人所创作的题画诗2000多首,可见题画诗在元代文坛之盛。然究其盛行之缘由,主要是因元代绘画以“写意”为主导精神,基于此元代画家的题画诗尤其值得我们关注。本文选取著名画家倪瓒的题画诗为研究对象,对之进行探讨,希望能为尚显薄弱的元代诗歌研究添砖加瓦。
倪瓒(1301-1374),初名挺,字泰宇,后字元镇。别号荆蛮民、净名居士、东海瓒、懒瓒等。因为家有“云林堂”,又号云林子。无锡梅里抵陀村人(今江苏无锡东亭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倪瓒诗歌的意趣、风格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他“诗文不屑苦吟,而神思散朗,意格自高,不可限于绳墨。”[1]倪瓒作为画坛元四大家之一,其绘画历来备受追捧,古往今来的大师学者都对之作了诸多研究,不吝笔墨地大书特书。然作为一位诗书画三绝的文人,其诗歌成就却存在被低估的事实。据目前粗略统计,倪瓒有题画诗398首,题画诗在其诗歌中的重要地位自不待言。本文旨在通过对其诗作文本的具体解读,其题诗与绘画、书法三者关系的探讨,以求对其题画诗的内容、创作特色予以介绍分析。
二
倪瓒一生题画诗创作颇丰,我们可据其诗作内容将之归为四大类:山水、人像、花鸟竹石、画技品评。
在倪瓒关乎山水的题画诗中我们能通过其所描绘的简远澹寂之景,感受到一种隐逸情怀。如这首《题画》:“甫里林居静,江湖远浸山。渔舟冲雨出,巢鹤带云远。漉洒松肪滑,敷茵楮雪间。春风一来过,似我武陵湾。”[2]诗人为我们呈现了一幅清远寂寥的早春图景:茅屋在林,湖山相映,渔船披雨,云伴鹤远,松路湿滑,草匿雪间。作品流露出一种道家所追求的审美倾向。尾联中的“武陵湾”化用陶潜的桃花源典故,指隐居之地,抒发其隐逸之志。在其《用王叔明韵题诗》这首诗中有“陶潜宅畔五株柳,范鑫湖中一叶舟。同煮获菩期岁暮,残生此外更何求”之句,将诗人对隐居生活的向往思慕予以更为直接地表露。
在倪瓒的题人像画诗作中,大多是题高士图、真人画像以写道人高逸绝俗之生活,表自己求仙慕道之志向。如这首《奉和虞学士赋上清刘真人画像二首》其一:
君向积金峰顶住,长年高卧听松风。蓬莱云近瞻天阙,剑佩春明下汉宫。归去长谣紫芝曲,翩然远挹黄眉翁。摽名合在诸天上,何事置身岩壑中。
“积金峰”“蓬莱”“紫芝曲”“黄眉翁”等都是神话仙传中的名物,契合高士道人之身份,突出仙道的浪漫色彩。颔联与颈联通过丰富的想象塑造高人道者高蹈飘逸之姿容。不同于郑思肖(其有为一百二十幅人物故事图作的题画诗,人物有各代隐士、高人、神仙、历史人物等)的叙事传画意,倪瓒更多是通过想象夸张以烘托出画中人的超凡脱俗,高妙莫测。
除却题高人真士画,倪瓒还有数首风格与之迥然相异的题仕女图,在这些诗作中诗人对女性情态与内心进行了生动传神的描摹勾勒。如:“画图常识春风面,云雾衣裳楚楚裁。为问人间春几许,石栏西畔牡丹开。”(《看花仕女图》);月鸾削破翠团团,六月人间风露寒。谁觅东陵故侯去,但知华屋荐金盘。(《仕女剖瓜图》);凤钗斜压鬓云低,望断羊车忘欲迷。几叶芭蕉共憔悴,秋声近在玉阶西。(《题芭蕉仕女》)。”在这三首诗中,倪瓒化用了诸多典故和诗句,无论是仕女们赏花探春意的娇俏,月鸾破团翠的欢快,还是听碎芭蕉雨的哀怨,诗人对女性的各类情思心绪都表现得很细致到位。
《题寂照蒋君遗像》这首诗很特别,因之为倪瓒哀悼亡妻之作。我们可从中见得倪瓒作为一名普通男子深情的一面。这首诗如是写道:
幻形梦境是耶非,飘渺风鬟云雾衣。一片松间秋月色,夜深惟有鹤归来。梅花夜月耿冰魂,江竹秋风洒泪痕。天外飞鸾惟见影,忍教埋玉在荒村。
故人音容飘渺,入得梦来,然梦境终究虚无,在“明月夜,短松岗”式的现实环境中那种失却伴侣,独行于世的悲痛之情被浓重的夜色清冷的江风晕染开来。诗人通过松林、月色、梅花、江竹、秋风等意象营造出凄清孤寂之境。在这首诗中我们能依稀看到苏东坡《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的影子。
在题花鸟竹石类的诗作中,诗人皆是借画中之物抒情言志。或赞高洁之行,有如《墨竹》“明月临虚幌,疏篁舞翠鸾。独吟苔石上,霜叶媚天寒”者;或叹当世之事,有如《题郑所南兰》“秋风兰蕙化为茅,南国凄凉气已消。只有所南心不改,泪泉和墨写《离骚》”者;或言怀古之意,有如《松雪马图为原道题》“今日鸥波遗墨在,展图题咏一凄然”者。寄情寓志于物是中国一大文学传统,讲求物我两照,借所咏之物言胸中之情思心志。以《题松雪墨竹》为例:
缘江修竹巧临摹,惨淡松烟忽若无。乱叶写空分向背,寒流篆石共萦纡。春渚云迷思鼓瑟,青崖月落听啼乌。谁怜文采风流意,漫赏丹青没骨图。
作者先描绘画中竹远观之景:修竹缘江而立,松烟迷蒙。再写近看之态:枝叶散乱随意,溪流矶石萦绕其侧。至颈联时则笔锋一转,诗人开始触景生情,江渚生烟云脚低,令人心生感慨。月落青崖乌鸟啼,更是叫人倍感凄清。面对如此孤寂惨淡之景诗人在尾联不禁感叹文采风流无人识,只能揽画自嘲之。由物及景再转而思及自身处境,从而抒发自己孤寂无人解之情。
关于画家画作品评,在《题大痴画》中诗人以“大痴胸次多丘壑,貌得松亭一片秋”来赞扬黄公望对景物的超凡感受。在《题黄子久画》中诗人以“本朝画山林水石,高尚书之气韵闲逸,赵荣禄之笔墨峻拔,黄子久之逸迈,王叔明之秀润清新……”来品名其时各家之长。关于绘画技法,诗人在《题画竹》中提出“下笔能行萧散趣,要须胸次有筼筜”的“逸气说”。
另外,就题画方式而言,有自题诗,如《题画赠九成》《为唐景玉画丘壑图因题》《画竹寄王彝斋》等。也有题他人之画作,如《题方厓墨兰》《为方厓画山就题》等,这其中也包括文人间的和诗,如《题吴仲圭诗画次韵》《用王叔明韵题画》等。当然也有无法从诗题上辨别的作品,如《龙门茶屋图》《题画》者,因画作已不存,绝大多数题画诗都本无诗题,全赖后人拟定,由有心人抄录成籍。
三
从倪瓒的各类诗作内容中我们不难发现其简约自然的创作风格。明人陈继儒曾这样评价倪瓒的诗歌:“余读先生之集,所谓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独大,独先生足以当之。”[3]该评价确有过矫之嫌,不过“文约辞微、言近旨远”用于形容云林先生之诗倒也贴切。周南老对倪瓒诗歌风格特点曾如是说道:“(元代)诗法既变,而以清新尚,莫克究古雅。处士之诗,不求工而自理致冲淡萧散。”(《元处士云林先生墓志铭》)钱溥有“予谓其清新典雅,迥无一点尘俗气,固已类其为人,然置之陶、韦、岑、刘间,又孰古而孰今也耶”(《清閟阁全集序》)之句。而王樨登也在《清閟阁全集序》中言:“先生诗风调闲逸,才情秀朗,若秋河曳天,春霞染岫,望若可采,就若可餐,而终不可求之于声色景象之间。” 总之,后人评倪瓒及其诗,总免不了用一个“逸”字。
倪瓒诗歌中这种简逸萧散的美学倾向其来有自,他在《题赵孟頫诗稿卷》中提出反对过分追求文辞渲染的主张,谓:“今人工诗文字画,非不能粉泽妍媚,山鸡野鹜文采亦尔斑斓,至其神韵则与孔翠殊。”[4]于他而言,诗文最贵自然平淡,要讲求“逸气”,只要能体现神韵情思,就不必使用过多的修饰。另外其自身的道家隐逸气质也是造成诗歌风格的重要原因。他曾在诗中述怀道:“人事匪予忖。得时宁足夸,失势焉用愤,富贵真应羞,功名意何物!”我们不妨再从具体诗作观之,“桐露轩前月满窗,竹声树影落春江。青苔石径无人迹,坐待归来白鹤双”(《题画赠王允同》),“却坐西岩双树下,玉笙云里度清风 ”(《用陈子贞韵题画》),不难发现诗人喜用月、竹、石、鹤、林、云等意象营造一种清幽淡远、萧索孤寂的境界。而在色彩选择上诗人偏爱青色与白色等冷淡色调,如“青苔”“白鹤”“青山”“白鸟”之属。
四
题画诗是诗书画三者结合的艺术,要言论倪瓒如何做到使诗书画融为一体,相互衬托,我们需要了解其诗书画三者的各自特点。有评家说道:“云林在胜国时,人品高逸,书法王子敬,诗有陶韦风致,画步骤关全,笔简思清,……后虽有王舍人孟端学为之,力不能就简而致繁劲,亦自可爱,林之画品,要自成家矣。”(石田《论山水画》)由此可见倪瓒虽诗书画各有师承,却有同一核心指向——萧散简逸。其诗如前所述,至于其画,后世评述实为多矣。倪瓒之画素以平淡天真为后人推崇,大多用墨极少,且不置人物。董其昌称之:“倪迂画在胜国时可称逸品……独云林古淡天真,米痴后一人而己。”(《画旨》)其书法者简远萧疏,在元代崇尚柔媚浓妍的时风中显得风格独具。因笔法的严整有矩,行气茂密,被徐渭赞曰“古而媚,密有疏”[5]。
怎样使诗与画达到完美统一,是诗人写就题画诗时所必须思考的问题。诗与画虽形貌不同但在艺术本质上是相通的:诗重寄性抒情,也需要状物存形;画重应物相形,也不能废达心寓兴。郭沫若先生曾说:“诗歌、音乐等空间艺术和绘画、雕塑等时间艺术虽有直接和间接的差异,但两者所表现的同是情绪的世界。便是两者之间,所不同的只是方法上的问题,不是本质上的问题。”[6]而题画诗正是诗“宣物”和画“存形”的有机统一体,周积寅认为 “(将诗)通过书法表现到绘画中,使诗、书、画的美极为巧妙地结合起来,并相互映发,丰富多姿,增强了作品的形式美感”[7],其实这就是题画诗作为一种特殊诗体所具有的独特魅力。为了使诗与画互为衬托,在内容层面,倪瓒遵循袁桷“诗中传画意,画里见诗余”的原则。以诗传达作者对画中景物所蕴涵之深意的体会见解,而图画则起到与诗相辉映与补充的作用。在形式层面,倪瓒特别注重诗与画的“位置经营”。他会依据画面留白的多少选取适宜的诗体,少则五言甚至四言,多则七言,以求得图画的布局协调。其题款构图更是追求一种诗文辅助画面,使整幅图画达到不空不满的艺术效果。如在《雨后空林图》中,因山势西高东低,画面右侧余有大量空白,所以倪瓒将题画诗书于图纸右侧,并使之与峰顶处于同一水平线,从而令整个画面均衡整齐。又如在《幽涧寒松图》中,左侧远山山势略低,近景寒松于画面偏右处高伫,倪瓒将诗题于画的左上角,让画面整体排布显得匀称美观。
为让诗书画三者和谐配合,互增美感,无论是在诗体选择、书体张弛、题诗位置还是诗作内容,倪瓒都经过精心考量,由是今天我们才能得见在萧瑟荒寂的山水图景上,带有隶书的波磔,却又不失秀雅可爱的别致小楷书写着一行行幽淡萧散的诗句。在倪瓒完整题画诗作品中常可见一河两岸式构图的山水,近景坡陀上杂树数株,远景一抹云山,中间隔着广阔的水面,画面上方留白处以秀雅的小楷题诗其间。就如李泽厚先生所言,“然而在这些极其普通常见的简单景色中通过精练的笔墨,却传达出闲适无奈,淡淡哀怨和一种地老天荒式的寂寞和沉默”[8]。赏其画,读其诗,审其字,我们确实能感受到作品所传达出的那种飘逸却寂寥的心境,以及诗与画这两种艺术门类高度融合的魅力。
[1]永瑢等编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3557.
[2]杨镰主编.全元诗[M]. 北京:中华书局,2013.
[3]温肇桐.倪瓒研究资料[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15.
[4]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692.
[5]徐渭.杂著·评字[M].北京:中华书局,1983:35.
[6]郭沫若.文学的本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74.
[7]周积寅.中国历代题画诗选注[M].杭州:西泠印社,1998.
[8]李泽厚.美的历程[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298.
2016-05-08
“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资助项目”(PPZY2015A008)阶段性成果。
景惜颜(1994—),女,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I206
A
1008—3340(2016)04—006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