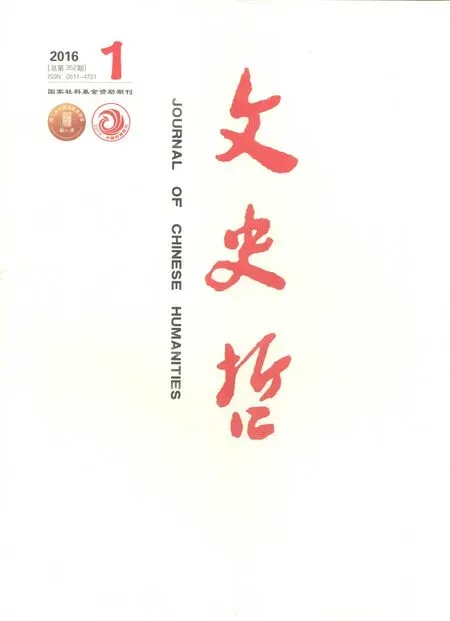权利政治与责任政治
2016-04-01谢文郁
权利政治与责任政治
谢文郁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暨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教授,山东济南 250100)
这里要提出两种政治的划分,即:权利政治和责任政治。在当代政治学范畴中,我们有两个基本概念:权利与责任。简单来说,权利常常称为自由,指的是一个人拥有自主权进行独立的判断选择;责任指的是一个人在进行判断选择时必须考虑并接受外在因素制约。关于这两个概念在界定上的详细讨论,可参阅我的一篇长文《自由与责任:一种政治哲学的分析》*谢文郁:《自由与责任:一种政治哲学的分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在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阴影中,人们往往只是从权利出发谈论权利与责任的关系(即:没自由,则没责任),并在政治上以权利为基础(通过宪法设定基本权利)来建构政治制度。这种“权利在先责任在后”的说法及其实践,可以称为“权利政治”或“宪政”。然而,我们还可以从责任出发谈论责任与权利之间的关系,强调人是在一定的责任意识中行使权利的,因而首先需要培养人的责任意识,以便融入社会,并在社会生活中尽职尽责。这是一种“责任在先权利在后”的政治模式,可以称为“责任政治”。
观察当下政治类型,大致可作如下划分:西方发达国家目前基本上属于权利政治(即西方宪政);中国的传统儒家则采用责任政治(也称为儒家仁政)。受西方宪政和儒家仁政的双重影响,当今中国政治仍然在变化过程中。本文在此只是提供一种相关的概念分析,或许有助于我们认清当今中国政治现状,并进一步思考其未来走向。
我们先来追踪权利政治的观念史。权利政治是在自由主义引导下设计出来的。近代以来,西方思想界出现了两种自由主义形态。一种是古典自由主义,由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提出的权利概念所主导,并在密尔的《论自由》中得到较为完整的表达。古典自由主义更多的是政治学理论。在此基础上,罗尔斯的《正义论》试图为当代社会提供一个完整的政治治理蓝图。另一种是当代经济学上的自由主义。从亚当·斯密的《财富论》重视“劳动”和信奉自由市场中的“看不见的手”开始,西方经济学一直企图在私有制观念基础上寻找合适的经济秩序。经济学上的自由主义是以政治学上的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这两种自由主义都对当代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影响。这里的讨论仅限于后者。
理解古典自由主义需要处理两个概念,一个是洛克的“基本权利”,一个是卢梭的“人权”。洛克在他的《政府论下篇》中提出了基本权利概念。我们知道,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把人的生存状态分为两种: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进而认为人是在自然状态中通过契约而进入社会状态的,即:为了保护生存和某些更为重要的权利而交出一些权利。洛克在这种契约思路中进一步提出基本权利问题,即:人在契约中有一些权利是绝不可能交出的,比如财产权和人身自由权,这些权利必须在宪法中加以规定和保护。不过,这里的财产权(私有制的基础)的原始性一直受到诘问。在洛克的思路中,任何一种权利,一旦被确认为基本权利,就必须受到宪法的保护。但是,如何确认基本权利呢?
卢梭在基本权利思路中发现,人在契约中进入社会,原则上,他可以放弃任何权利,包括财产权和人身自由权。但是,他注意到,有一个权利绝对不可能交出,那就是他的契约权。如果他缺乏这个权利,他就无法在契约中交出他的其他权利。这个契约权,卢梭称之为“人权”。正是因为拥有这个权利,人能够放弃其他任何权利,也能够回收其他任何权利。人无法交出这个交出权利的权利。不过,人们往往不知道自己拥有这个权利,因而闲置不用。比如,奴隶不知道自己仍然拥有这个权利,因而甘愿继续做奴隶。因此,关键在于让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拥有这个无法剥夺的权利。这个想法乃是启蒙运动的杠杆。就政治而言,在卢梭看来,宪法必须首先确认并保护这个权利。进一步推论,为了让它能够充分行使,宪法需要进一步保护一些必要的权利如言论权、财产权等。
在自由主义的权利意识推动下,西方开始走上以宪法规定基本权利,以法律保护这些基本权利的宪政实践。宪政的着眼点是权利保护,特别是要防范政府或强者对个人权利的侵犯。维护个人的宪法权利是这种政治运作的中心。近代以来,这种权利政治在西方社会中的运作相当成功。
我们还需要注意西方社会治理的另一个基础性因素。权利是中性的,是由那些拥有一定责任意识的人来行使的。比如,在美国宪政实践中,行使权利的主体是在基督教教会中成长起来的信徒,他们的责任意识是在教会中建立起来的。美国基督教教会,不仅提供了公民从小到大的责任意识培养机制,而且还对现任政治家进行道德监督和咨询,继续培养他们的责任意识,规范他们的道德行为。美国政治上强调权利,而道德意识的培养则依赖于教会。两者合力是美国社会治理的关键所在。再次强调:人在行使权利之初就已经拥有一定的责任意识。同样一个权利,比如言论自由,拥有不同的责任意识,可以有完全不同的使用,对社会造成的影响也会完全不同。
过去一百多年来,中国精英们面对强势的西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偏激地认为儒家仁政在体制上不及西方宪政,从而一而再,再而三地努力取消这种责任政治。然而,百年宪政实践表明,取消儒家仁政无异于自毁根基。1905年的清朝开始实施宪政;1919年的五四运动进一步企图通过文化运动启蒙中国人的权利意识;1980年代开始盛行的自由主义进而推动所谓第二次启蒙,试图引进西方宪政实践;等等。这些做法追求用西方宪政取替儒家仁政,就其愿望而言,赤子之心,日月可鉴!然而,过去一百多年的宪政实践把中国社会政治引入混乱,时至今日,困局犹在。我认为,原因就在于我们对权利政治与责任政治之间的内在差异缺乏基本的认识,从而导致西方宪政在中国政治土壤中水土不服。因此,有必要深入分析这两种政治的基本思路,考察其中异同,进而在此基础上探索当前中国政治路向,布局未来世界政治秩序。
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国社会的政治治理是如何进行的?我们注意到,中国人拥有一种天下情怀,强调在人情中建立天下秩序。其基本思路是,基于血缘关系的孝、悌、慈是人人皆有的基本情感;它们是群体生活的原始情感,因而也是政治生活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朋友之间的信任情感渐发,成为连接非血缘关系的人和人的情感纽带;而幼者对长者、下级对上级的尊敬情感渐长,则推动建构稳定的社会尊卑结构。与此同时,由此成长起来的长者和尊者必然拥有仁者情怀,并在处理人和人的关系上展示仁爱之心。这种以情感为基础的政治思路,我称为责任政治思路。它要求在上执政者对孝、悌、慈、诚信、敬畏、体恤等情感有深刻体会,并对自己所处位置的职责有深入认识,在情感和知识上不断培养自己的责任意识,做好本职工作。于是,在这个社会关系网络中,每一个人都占据一个位置,尽职尽责。这种责任政治思路也称为儒家仁政思路。
社会是有秩序的。每个人在社会秩序中都占据一个位置。每个位置都包含着社会赋予的职责。找到适合自己本性的位置,并培养相应的责任意识,做好本职工作,乃是一种天然的要求。在这种政治生活中,每个人从小开始培养某种责任意识(家教),接受群体的调节和培养(礼教),在成年时即会拥有一定的与社会期望相向的责任意识,并进而在这种责任意识中处理人际关系,为人处事。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其位则谋其政,不在其位则不谋其政”,“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等等,这类说法其实都是在谈论责任政治中的人的责任意识。
这种政治强调责任意识的培养,注重在礼教中修身养性。这种思路对人的权利有压抑和排斥的倾向。一个人抱怨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人们会解释说,这个人的修养不足,需要继续提高。人融入社会,就当如鱼可以在水中游行自如而不觉受限一样。因此,传统儒家仁政在政治体制上对个人权利不设保护机制。换句话说,它要求个人不要强化自己的权利意识,而要不断培养自己的责任意识,使自己对自己的社会地位有更加明确的认识,并尽职尽责。
儒家仁政对于财产权、言论权、结社权这些在西方权利政治中十分强调的基本权利似乎并不太关心。比如,关于财产权,中国传统社会实行使用占有权(谁使用,谁占有)。至于言论权,慎言慎语是修身养性的基本要求;在语言上过于表现自己,被认为是不合适的做法。在政治上虽然任命谏官,但谏官的权利并没有得到绝对保护。关于结社权的态度则是分化的。如果结党营私,那是受批评和压制的;如果只是兴趣爱好,则随意而行。这些权利大多以自然法的形式得到肯定,并没有法律明文保护。然而,儒家仁政十分强调在修身养性中追求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鼓励并保护人追求“三不朽”的平等权。每个人都拥有天命之性,究竟一个人的天命之性是什么?——这只能由当事人自己在修身养性中将它彰显出来。因此,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寻求自己的位置,包括取得官位和皇位。政府则对任何愿意接受王道的外族人,采取无歧视的教化同化做法。这一点与西方权利政治中的平等权是相吻合的。而且,儒家仁政还十分强调自卫权,指责任何伤害人身的动作。但总的来说,儒家仁政并不鼓励固化人的权利意识(这与西方权利政治的做法相反)。而且,即使人们对一些权利拥有共识(基本权利),但却并不在法律上加以规定和保护。
更为重要的是,在儒家仁政中,权利(包括基本权利)不是绝对的。随着人的责任意识的变化,人对自己的权利的使用会发生变化,对待他人权利的态度也会发生变化。比如,对于一个在责任政治中的官员来说,他在任职时就已经拥有了一定的责任意识;而在任职期间,他还需要不断地发展和丰富他的责任意识。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从他的责任意识出发,责任被置于优先地位。当然,他在相应的位置上享受某些权利;但是,这些权利都是附属于责任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官员的责任意识愈是成熟和完整,他就愈发无视自己的权利。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为了大局,他可以放弃自己的权利,由己及人,他还可能开始轻视他人的权利。这位官员这样做时,并不认为自己做了什么错事;反而,他认为自己在为社会做一件善事。就历史教训而言,在责任政治中,践踏人权现象往往都出现在领袖人物的理想追求过程中。就此而言,责任政治容易走向极权专制。
作为比较,在权利政治中,宪法明确规定了公民的一系列权利。公民的宪法权利受到法律的绝对保护。法官为了保护公民的权利,甚至可以无视负面的社会后果。比如,一个杀人犯的权利如果在被起诉时未能在程序上得到应有的保护,法官可以完全不顾他是否杀了人这个事实而当场释放他。在这种权利政治中,权利是至上的,而责任是随后的。对于那些顽固坚持自己的权利而不顾社会后果的人,权利政治仍然必须严格予以保护,因而常常显得束手无策。
再次强调,任何权利的使用,都是在使用者一定的责任意识中进行的。缺乏相应的责任意识的辅助,权利政治寸步难行。这也是许多国家在引进权利政治后并没有给社会带来福祉的根本原因。在一些重大社会事件中,如果坚持个人权利必将危害社会,那么,解决的办法只能是:或者唤起当事人的责任意识而让他主动放弃权利,或者破坏当事人的权利而强行实施。然而,这两种做法都是违反权利政治原则的。美国的权利政治之所以得以成功运行,关键就在于这个社会一直得到基督教教会的全力支持。教会源源不断地输出行使权利的责任意识。显然,健全的权利政治需要一种辅助性机构,独立地培养公民的责任意识,从而让公民自觉地制约自己的权利行使。
考虑到传统文化对政治运作的巨大惯性力,笔者认为,一方面,中国的未来政治,就其现实运作而言,将走向一种儒家式的责任政治,培养社会成员的责任意识因而仍将是政治的主要导向。另一方面,我希望这个政治能够包容个人的权利意识,并在法律和制度上设置基本权利保护机制。我们期望,未来中国政治能够拥有充分而平衡的责任意识和权利意识。这应该是一种健康的责任政治。
[责任编辑曹峰邹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