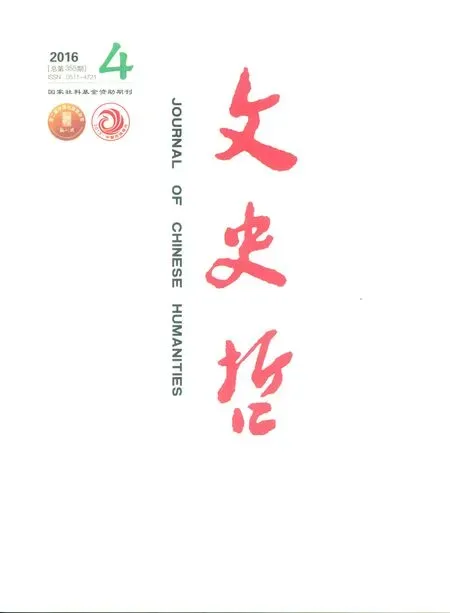我们如何共同行动?
——“同意理论”的当代境遇
2016-04-01张乾友
张乾友
我们如何共同行动?
——“同意理论”的当代境遇
张乾友
摘要:“同意理论”是启蒙思想家们关于我们如何共同行动的经典解释。一方面,同意理论让自主的个人之间得以形成一种共同的秩序,当他们彼此同意建立或接受这种秩序时,就共同进入了一个拥有权威的共同体,并得以在这一共同体的框架之内开展有序的共同行动。另一方面,同意理论又造成了自主与自由、民主与正义的矛盾,因而受到了当代政治哲学家们的集体拒绝。对同意理论的拒绝在实践中意味着某些行动者可以无须其他行动者的同意而开展共同行动,其结果是让社会的边缘群体与世界的边缘社会承受了共同行动的代价,进而造成了今天人类的共同行动困境。在日益多元的社会中,对“我们如何共同行动”的回答需要重新思考同意与拒绝的关系。
关键词:自由;民主;正义;同意;拒绝;共同行动;权威;义务
近年来,随着人们之间、社会之间以及国家之间交往的加深,也随着社会事务、政治事务以及公共事务的形成与解决牵涉到越来越多的方面,我们的生活中出现了许多道德上务要的目的(morallymandatoryaims)*Thomas Christiano, “The Legitimacy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rei Marmor, ed.,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Philosophy of Law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389.,并要求我们通过共同行动来实现这些目的。然而,另一方面,随着共同行动成本与风险的不断增加,随着社会信任的断裂与搭便车心态的盛行,也随着从组织到国家的各个层次上不平等的加剧,正在进入一个“地球村”的我们越来越难以开展共同行动,越来越难以通过共同行动去实现共同的道德上务要的目的。如果说现实中人们之间、社会之间以及国家之间愈演愈烈的冲突与对抗宣布了我们必须诉诸共同行动来改善我们的生存境遇,在行动无力的现实面前,我们如何共同行动就成了理论家们必须加以回答的问题。众所周知,近代早期,启蒙思想家们通过同意理论解决了人们如何共同行动的难题,同时也让人们之间的共同行动陷入了同意与拒绝的紧张之中。而当人们再次陷入了共同行动的困境时,20世纪后期以来,学者们重新将目光转向了同意理论。不过,与启蒙思想家们不同,这一次,他们对同意理论作出了集体性的拒绝。然而,如果说启蒙思想家们通过提出同意理论而使我们陷入了同意与拒绝的紧张的话,当代政治哲学界对同意理论的拒绝也并没有让我们走出这种紧张,在某种意义上,关于“如何共同行动”的问题,我们仍需在同意与拒绝之间寻找答案。
一、同意理论及其紧张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归纳出洛克式同意理论的基本内容:第一,国家是个人之间集体同意的产物,因而是以个人的自由与自主为前提的,那么,在理论上,出于保护和实现其自由与自主的目的,个人就可以集体地对国家表示拒绝,当然,在现代政治实践中,这种拒绝通常只适用于政府,而不适用于国家*个人可以通过移民来拒绝他原来所属的国家,群体也可以通过诉诸全民公决来拒绝他们认为被强行纳入其中的国家,但这两种拒绝都不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正常政治实践,虽然第一种拒绝可能已经具有了某种程度的普遍性。;第二,同意确立了合法权威——也就是政府——以及人们服从这一权威的义务,进而,人们就可以围绕并通过政府来开展共同行动;第三,同意服从政府的权威在实践中意味着同意服从大多数人的决定,也就是同意让大多数人来决定我们共同行动的目标、方式与内容,并且,只要政府本身的存在仍然是合法的,那么,尽管少数可以对大多数人的决定表示反对,却不能拒绝服从这一决定,这是现代政治义务的实质性要求;第四,同意是个人之间集体行使其自由与自主的一种方式,那么,在同意实际上意味着接受政府权威与接受多数决定的意义上,在作出同意的决定时,人们有着选择政府形式的自由,也就是说,只要他们都自由地表达了同意,就可以通过多数决定来建立起一种合法却不自由的政府。

对自主与权威矛盾的化解是启蒙思想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因为它回答了在自主被视为人的首要义务的前提下人们如何还能共同行动的问题,而这也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在理论上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革命是一种颠覆旧秩序的行动,但又不仅仅是颠覆旧秩序的行动,而且也必须是一种建构新秩序的行动,否则,它就只能被称为造反。任何革命性的行动,如果不能提供和确立一种新的政治秩序,就要么演变成换汤不换药的政权更替,要么使人们陷入无政府主义的状态。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试图推翻西欧中世纪的等级秩序,而代之以一种以自主的个人为基础并保障个人自主的秩序,首先就必须证明自主与权威的兼容性,否则,如果自主的个人不需要服从任何权威,如果自主意味着每一个人都自行其是,那就不可能有任何秩序,不可能有有序的共同行动,当人们不得不一道应对共同的问题时,就只能走向冲突和争斗。所以,同意理论让自主的个人之间得以形成一种共同的秩序,当他们彼此同意建立或接受这种秩序时,就进入了一个拥有权威的共同体,并得以在这一共同体的框架之内开展有序的共同行动。

同意理论造成的另一大紧张是合法性与正义的紧张,或者说民主与正义的紧张。同意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合法性取决于后来成为了它的从属者的自然状态中的每一个人的同意。并且,这种同意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同意赋予国家统治的权利,而是说他们都同意接受由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所作出的同意赋予国家以统治权利的决定。换句话说,一个国家的合法性取决于其从属者对多数决定也就是民主原则的同意。在同意这一原则的基础上,多数作出了同意接受国家统治的决定,那么这个国家就获得了合法性。由于这一同意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民主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建立起来的国家也就获得了民主的合法性,虽然它本身可能没有采取民主的政府形式。也就是说,自主的个人可以通过集体表决同意于一种不民主的政府,但这种政府则拥有民主的合法性,也就拥有要求其从属者基于民主原则服从它的权利,对这些从属者来说,服从这一不民主的政府也是他们自由选择的民主义务。这是同意式民主观的内在矛盾,它可以使所有不民主的政府形式都得以合法化,虽然并不是每一个不民主的政府都实际地得到了合法化。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在民主制度于西方社会已经根深蒂固的背景下,20世纪后期以来,学者们开始更多地用正义的理念来校正同意式民主,甚至要用证成性(justification)来取代合法性的地位*A. John Simmons, Justification and Legitimacy: Essays on Rights and Oblig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这一思潮的最重要代表就是罗尔斯。
罗尔斯认为,民主——同意——是一个程序性的概念,如果一个政府是通过民主程序建立起来的,如果它的法律与政策是经由民主程序而得以制定的,那么,这个政府及其法律、政策就都是合法的,但同时,它们也可能是不正义的,并且,当这种不正义达到某种限度,就可能削损政府及其法律、政策的合法性。这意味着,“合法性是一个比正义更弱的概念,因而也对我们能做的事施加了更少的限制”*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Reply to Habermas,”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92, no.3 (March 1995), 175.。进而,“默认甚或同意显然不正义的制度就不能产生义务。人们一致认为,勒索来的许诺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种许诺。但是,不正义的社会安排本身同样是一种勒索,甚至是一种暴力,对它们的同意是没有约束力的”*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343.。所以,如果人们发现他们同意的是一种不正义的制度安排,那么他们就可以拒绝服从这一制度,拒绝依据这一制度来开展共同行动。至此,同意作为共同行动基础的地位遭受到了否定,在自由民主制度似乎已经牢不可破的前提下,“我们如何能够共同行动”的问题被“我们如何更好地共同行动”的问题所取代,而这自然意味着对那些不好的行动方式与方案的拒绝,且这种拒绝的核心即是对我们曾经对这些方式与方案作出过的同意的拒绝。由此,对同意的拒绝就成了当代政治哲学研究中的一个核心议题,而这种拒绝也使人类的共同行动陷入了新的困境。
二、我们能否拒绝同意
在某种意义上,同意理论制造了“我们如何共同行动”的问题。或者说,在此之前,“我们如何共同行动”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显见,同意理论是一种虚构,这种虚构掩盖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我们并不是因为同意才进入了一个共同体,而是生来就处于某个共同体之中,并通过在这个共同体中的生活而习得了它的共同规范,也就学会了基于这些规范而共同行动。在这里,我们并不需要思考我们如何共同行动,因为我们生来就处在了既定的共同行动模式之中,我们也不需要同意这种共同行动,因为我们事实上无法拒绝这种行动。在这个意义上,同意理论其实是一种拒绝理论,当它说只有同意才能加予我们承担某种共同行动之后果的义务时,实际上是说我们拥有拒绝一切我们想拒绝的共同行动的权利。在这里,同意是通过拒绝而得到定义的,判定一个人同意了一项行动的标志,与其说是他明确作出了同意的表示,不如说是在他(1)清楚知道正在发生的事以及他的同意意味着什么,(2)有明确时限表示拒绝并被告知可接受的表示拒绝的方式,以及(3)被告知从何时开始就不再接受拒绝的前提下,没有表示拒绝的事实*A. John Simmons, “Tacit Consent and Political Obligation,”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vol.5, no.3 (Spring 1976), 279.。换句话说,只有拥有了拒绝一切想拒绝的行动方式或方案的权利时,一个人才是自主的,因为只有这样,他才真正拥有同意的自由。而随着人们获得了拒绝的权利,“我们如何共同行动”就成为了一个问题,同意理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同意,只要我们同意或者说没有拒绝一项行动方案,那么我们就可以依据这一方案来开展共同行动,同时有义务承担这种行动所造成的后果。
洛克清楚地认识到了同意与拒绝间的辩证关系,并提出了“默示同意”(tacitconsent)的概念来解释这一关系,即只要一个人没有明确地拒绝一个政府、权威或行动方案,那他就以默示的方式同意了这个政府、权威或行动方案。如前所述,对于历史而言,同意理论完全是一种虚构,因为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是通过所有人的同意建立起来的,但通过引入“默示同意”的概念,那么只要人们没有明确表示过拒绝,则所有国家都可以被视为同意的产物。由此,洛克就得出了“就历史来看,我们有理由断定政权的一切和平的起源都是基于人民的同意的”*[英]洛克:《政府论》下篇,第70页。这一完全不符合历史的结论。这一结论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它意味着同意理论得到了历史事实的支持,因而反对者就不能以历史上找不出明确同意的证据为由而否定其解释力;另一方面,它为现代国家提供了一种更广泛的合法性基础,无论在国家的建立阶段还是在国家的日常运行中都是如此。对于现代国家的正常治理而言,后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代表型民主制度下,同意直接表现为投票,一位选民参与了投票并不只是意味着他同意某位候选人作为他的代表,更意味着他同意了以投票为内容的代表型民主制度。那么,在政治冷漠日益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的背景下,在投票人数尤其当选者所获得投票人数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越来越少的条件下,我们怎么能够认为这个当选者以及民主制度本身是得到了整个社会同意的?显然,“默示同意”的概念可以在逻辑上解决这一问题,因为当选者虽然可能没有获得大多数人的明示同意,但所有没有明确拒绝他也就是没给他的竞争对手投票的人都可以被认为对他作出了默示的同意。同样,所有没有参加投票的人,只要他们没有明确拒绝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如通过双重国籍参与另一国家的投票,就也默示地同意了这个国家及其民主制度。可见,根据同意理论,只要我们没有明确拒绝彼此,那我们就可以共同行动,只要我们没有明确拒绝一种制度,那我们就可以在这种制度下共同行动,而这两点得以成立的前提则是,只要我们想拒绝,那我们就可以拒绝。
拒绝不同于反对,正如同意不同于共识。反对与共识是民主的一体两面,民主一方面赋予了每一个人反对另一个人的权利,另一方面又施加给所有人服从共识的义务,而这里的共识就是多数的决定。所以,在民主过程中,每一个人都可以尽情地反对彼此,但只要多数作出了决定,他就必须服从这一决定,这是他的民主义务,且民主制度的存续高度依赖于这一义务。如果他不服从这一义务,那他就不是在表达反对,而是在表示拒绝,并且是通过对民主义务的拒绝而表达的对民主制度的拒绝。同意理论本质上是一种拒绝理论,但它却不允许对同意本身的拒绝,否则,如果所有人都拒绝同意,那么他们之间就无法形成任何的共同体,也无法开展任何的共同行动了。作为一种拒绝理论,同意理论主张个人可以拒绝一切他不同意的事情,而作为同意理论,它又要求个人必须同意一件事情,这就是他必须服从多数的决定,而无论他自己是否属于多数的一分子。这里的问题在于,如果国家真的是同意的结果,如果每一个人在创立国家的过程中都真的表达了他的同意,至少是对服从多数的同意,那么,作为一个自主的政治行动者,他的确不能否决自己的同意,不能拒绝因同意而产生的义务。但在现实中,这样的同意通常并不存在,很少有人曾经有机会表达他们对国家的同意,尤其在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许多少数群体甚至是被强行整合进民族国家框架之中的,同意理论能够要求他们履行只能因同意而产生的义务吗?显然不能。既然如此,拒绝这些义务也就没有什么不对的了。可见,同意理论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如果它不能让人们相信他们曾经作出过同意,也就不能加予他们任何的义务。如果说在洛克的时代人们还愿意相信同意理论所赖以存在的这一假设的话,到20世纪后期,在民主制度四处开花的同时,同意理论则越来越失去了市场,以致让布坎南(AllenBuchanan)感叹道:“如果同意真的是政治权威的一个必要条件,那就没有也绝不可能有任何实体能够拥有政治权威。”*Allen Buchanan, “Political Legitimacy and Democracy,” Ethics vol.112, no.4 (July 2002), 699.结果,近些年来,所有民主国家内部都兴起了拒绝权威及服从权威之义务的浪潮,使民主社会变得越来越支离破碎,也让人们之间的共同行动再次成为了一个问题。


三、无须同意地共同行动?
由于同意理论的失效,过去几十年来,权威与义务成了政治哲学研究中的一对核心概念,罗尔斯与拉兹则成了人们在重新回答“我们如何共同行动”的问题时绕不开的两个人物。比较而言,拉兹的理论蕴含了一种直接的不平等关系,因为权威掌握了关于我的行动的正确理由,虽然我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理由,却只能通过服从权威来更好地顺应这一理由。在这里,我与权威的关系显然是不平等的。克里斯蒂亚诺将这种不平等的权威观称作工具主义的权威观,他认为:“对政治制度进行工具主义评价的基本标准不是人们作为平等者彼此提出的方案,而是优等者出于劣等者的利益而强加于他们的特殊真理。而这是与正常成年人之间的平等不一致的。”*Thomas Christiano, The Constitution of Equality, 236.所以,“这种权威观所具有的工具主义和零星主义的性质使它可以赋予严重不正义的政权以合法权威”*Thomas Christiano, The Constitution of Equality, 233.。在这一点上,一般证成论有似于儒家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从表面来看,这样一种权威观既是自由的,也是平等的,但如何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呢?答案就是“存天理,灭人欲”,因为没有欲望自然也就不会逾越规矩。在这里,权威掌握了“天理”,也就是正确的理由,而这一理由的要求则是“灭人欲”,即它的从属者只有通过“灭人欲”才能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样一种关系显然是不平等的。所以,作为对同意理论最激烈的反对,拉兹的一般证成论也受到了同意理论所有反对者的激烈批评。克里斯蒂亚诺就认为“这种权威观必须得到拒绝”*Thomas Christiano, The Constitution of Equality, 236.,而不能成为我们共同行动的依据。
与拉兹不同,罗尔斯通过假定每个人都负有一种自然正义义务而证明了我们可以通过选择正义的制度来开展共同行动。并且,在“无知之幕”的设置中,他重申并更新了自由主义的中立性原则,从而让人们对“作为公平的正义”的选择呈现出了不偏不倚的特征,也使基于“作为公平的正义”的共同行动本身具有了正义的性质。在这里,中立性被罗尔斯表述为讲理(reasonableness),它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理性(rationality),因为理性的人不是一个中立的人,他首先倾向于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制度,而不是正义的制度,只有一个讲理的人才会愿意选择一种正义的却可能对自己不利的制度。单从逻辑上讲,在已经设置了原初状态与无知之幕的前提下,讲理这一条件其实有些多余,甚至是不合逻辑的,因为理性选择已经足以保证每个人选择“作为公平的正义”了。但问题在于,无论原初状态还是无知之幕,在现实中都是不存在的,正如同意从来不曾真实存在过一样,而在不存在原初状态与无知之幕的条件下,理性的人们肯定不会选择“作为公平的正义”。所以,罗尔斯就以牺牲其理论在逻辑上的严密性与简洁性为代价而换来了它对现实的更强解释力。这是他超越了同意理论家的地方,他在事实上构建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逻辑体系,却并不仅仅是在玩逻辑游戏。然而,讲理的引入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它究竟是否一个中立的范畴?在罗尔斯看来,或者说,在罗尔斯所代表的西方主流社会看来,答案是肯定的,如果说现实中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讲理的人的话,至少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讲理的人。但在社会中处于弱势或边缘地位的人与群体看来,答案则是否定的,相反,“在西方社会,这样的人通常是白人、男性和中产阶级”*Alison Jaggar, “Feminism in Ethics: Moral Justification,” Miranda Fricker and Jennifer Hornsby ed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Feminism in Philoso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231.。那么,就算每一个讲理的人都愿意选择“作为公平的正义”,在社会中事实上存在着不讲理的人——无论他们为什么不讲理——且他们就是不愿意选择“作为公平的正义”的情况下,所有这些讲理的人与不讲理的人如何能够共同行动?
在国内政治的层面上,罗尔斯不承认这样一种可能性,因为在存在国家这一事实权威(defactoauthority)的前提下,无论人们讲不讲理,他们都必须在国家所提供的制度框架下共同行动,这是最基本的公民义务。对罗尔斯来说,这一义务意味着,“一位自由社会中的公民需要尊重其他人的整全性的宗教、哲学与道德学说,只要这些学说符合于一种合理的(reasonable)政治正义观”*John Rawls, “The Law of Peoples,” Critical Inquiry vol.20, no.1 (Autumn 1993), 37.,这种合理的政治正义观就是“作为公平的正义”。换句话说,作为自由社会中的公民,每一个人都需要让他的整全性学说与“作为公平的正义”相符,只有这样,他才能在保有其差异的同时与他人达成一种重叠性的共识,而只要他们能够达成重叠共识,他们就都是讲理的人。可见,罗尔斯实际上预设了,在自由社会中,每个公民都是讲理的人,或者说,自由社会已经将它的所有公民都变成了讲理的人,所以,他们就可以在选择“作为公平的正义”上达成重叠共识,进而依据这一共识开展共同行动。但从现实来看,在自诩为自由的西方社会中,许多边缘化的社会运动表现出了日益强烈的不讲理甚至无理的特征,它们不是通过理性的协商寻求与其他社会成员的重叠共识,而是要从根本上拒绝它们不想要的但所有自称讲理的人都会赞同的正义观念与政治制度。并且,这种拒绝已经超出了“公民不服从”的范畴,因为它们不是在拒绝特定的政治义务,而是在拒绝所有公民义务的前提,即作为一种事实的公民身份。这些运动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我们并没有同意建立一个国家或一种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如果我们承认我们都负有一种自然正义义务,那我们是否有权拒绝一种特定的正义观念以及相应的政治制度?
对于这一问题,罗尔斯式的回答是这样的:什么叫自然正义义务?它是我们承认与保护每一个人所拥有的自然权利的义务。那么,什么叫自然权利?它是我们每一个人作为自然人所拥有的那些权利,也就是人权。所以,自然正义义务就是承认与保护每一个人的人权的义务。如果说正义观念本身是开放的与多元的,那么,通过在它前面加上一个“自然”的定语,正义就变成了一种封闭的和排他性的观念。至此,所有不以人权为内容的正义观都不再被视为正义观,而所有支持或信奉这些正义观的人也都不再被视为讲理的人,因此,他们的所有不讲理的主张与诉求都应当受到拒绝。这就是马塞多(StephenMacedo)所说的,“我们必须摒弃或放弃我们不能与讲理的同胞公民一同分享的立场。我们寻求可以达成具有公共性的合理共识的共同立场,我们不接受、权衡和就信念与观点上的持久的和不可消除的差异讨价还价”*Stephen Macedo, “The Politics of Justification,” Political Theory vol.18, no.2 (May 1990), 295.。而如此一来,人权就变成了拉兹所说的正确理由,它意味着讲理的人掌握了共同行动的正确理由,不讲理的人则必须服从这种理由,否则他就无法正确地与他人共同行动。在逻辑上,这种服从关系不能被认为是不平等的,因为平等是人权的基本要求,所以,服从人权的理由就是在实践平等。但它一定是褊狭的和排他性的,在实践上,它意味着讲理的人可以拒绝不讲理的人的无理要求,反过来,不讲理的人则必须在讲理的人向他提供的框架或限制中开展行动。所以,只要承认每一个人都负有自然正义义务,那么每个人就都必须讲理,都必须在相互论理(reasoning)中共同接受以人权为内容的正义观。对于罗尔斯之后的自由主义者来说,只有这样,自由社会与自由制度才是可能的,进而,符合自由价值的共同行动才是可能的。


显然,罗尔斯为国际行动所设置的条件过于苛刻,如果守法社会完全拒绝与法外政权共同行动,那么,除非通过战争,否则它们之间就不可能有任何共同行动。而如果它们之间现实存在着某些共同行动,这些共同行动也一定是不符合万民法的。就此而言,罗尔斯的万民法理论具有一种现实批判的功能,它指出了当前所谓守法社会施加于法外政权的所有渔利活动的不合法性质,甚至,从一种理想标准来看,与法外政权的任何共同行动都是守法社会对其人民所犯下的不义。显然,对现实世界的评价是无法采用这样一种理想标准的。因此,与罗尔斯总是致力于构建理想理论不同,在思考国际行动的问题时,布坎南采取了一种现实主义的路径,从全球治理机构入手思考国际行动的合法性基础问题。在这样做时,布坎南旗帜鲜明地反对同意理论,他认为:“很难相信国家间的同意如何能够赋予全球治理机构以合法性,因为许多国家是不民主的,甚至蓄意侵犯其公民的人权,并因此本身就是不合法的。在这些情况下,国家的同意是不能让渡合法性的,因为根本就没有可让渡的合法性。”*Allen Buchanan, Human Rights, Legitimacy, and the Use of For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111.国际关系同意理论的一个论点是,同意可以制衡强者,使弱者可以拒绝强者的不正当干预。但在布坎南看来,“仅仅因为不是所有国家都同意了全球治理机构而无论它们多么有价值就拒绝赋予其合法性,是以放弃对暴政的合法否决权为代价来保护弱小的国家。而这一代价未免太高了。在多边关系中,弱国占有数量上的多数。一般来讲,它们受全球机构中强国支配的危险要远比受那些强国在全球机构之外的行动的威胁小得多。”*Allen Buchanan, Human Rights, Legitimacy, and the Use of Force, 111.言下之意,如果不同意由强国主导的全球治理机构的支配,那就只能接受强国在不受任何全球治理机构限制的条件下的支配,那么,“两害相权取其轻”,弱国就没有任何理由不同意以人权规范为基础组织起来的全球治理机构,反过来,这些全球治理机构的行动也就完全无需弱国的同意。只要是出于人权的理由,这些全球治理机构就可以采取合法行动,这体现了自由人民的一种坚定的自然正义义务(RobustNaturalDutyofJustice),“一种帮助确保所有人都能享有正义制度的义务”*Allen Buchanan, “Political Legitimacy and Democracy,” 704.。
可见,20世纪后期以来,主流政治哲学研究中出现了一股拒绝同意理论的趋势,无论在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层面上,学者们都不再承认同意作为政治义务来源与共同行动前提的地位。这反映了多元社会兴起的现实。多元社会的基本特征在于,这个社会中一定存在不愿同意的人。而且,如布坎南所看到的,这些不愿同意的人虽然处在社会的边缘,却可能是社会中的多数,所以,要能开展共同行动,多元社会中的人们就必须拒绝同意理论,否则,不愿同意的人就可以正当地拒绝一切义务,同时理所当然地享受搭便车的好处。但另一方面,对同意理论的拒绝在逻辑上又导向了人们不能拒绝与他人共同行动、不能拒绝权威的结论,而这在实践中就造成了排他性的甚至不平等的后果,使社会内部的边缘群体与国际社会中的边缘国家不能拒绝它们不愿参加的共同行动,并不可避免地承担了这种行动的不利后果。虽然这种行动似乎得到了哲学上的充分证明,但在实践中,它注定是不可持续的。无论一项行动有着多么正确的理由、多么正义的目的,只要我不愿参加,那我就一定会想方设法反抗这种行动。这正是今天的政治世界中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启蒙思想家们通过同意理论证明了自主的个人之间如何能够开展共同行动,同时也让人们间的共同行动陷入了同意与拒绝的紧张之中。而在今天,随着多元社会的形成,虽然同意理论已经受到了普遍的否定,但在无须同意地共同行动已经造成的现实悖论面前,我们能否无须同意地共同行动?我们是否应当无须同意地共同行动?以及更重要的,无须同意地共同行动是否正确?则成了所有试图回答“我们如何共同行动”的问题的人都必须加以深思的根本性问题。
[责任编辑刘京希]
作者简介:张乾友,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江苏南京 210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