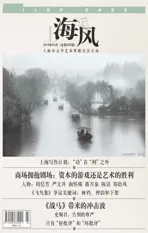为内参片“打补丁”的人——记著名指挥陈传熙
2016-03-31孙渝烽
文/孙渝烽
为内参片“打补丁”的人——记著名指挥陈传熙
文/孙渝烽

陈传熙与白穆
但凡喜爱电影的观众,特别是中老年电影爱好者,对于陈传熙这个名字必然十分熟悉,稍注意一下字幕就会发现“指挥陈传熙”。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发祥地,解放后更是中国电影事业的半壁江山,拍摄了无数人们喜闻乐见的电影,其中很多影片的音乐就是陈传熙指挥完成的。他指挥的配乐影片多达六百多部,在这里我仅举几部:《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李双双》《林则徐》《聂耳》《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天云山传奇》……美术影片《牧笛》《金色的海螺》《小蝌蚪找妈妈》《大闹天宫》……还不包括他完成的大量科教片、电视剧。
陈传熙解放后出任上海交响乐团指挥,他指挥演出的交响乐也多达六百多场,是我国著名的指挥家。他的风格清晰、流畅、严谨、准确,在音乐界享有好名声。
电影艺术是一门综合艺术,除了编导演,也离不开“化(妆)服(装)道(具)摄(影)录(音)美(工)”的和谐成功配合,再加上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有打动人的音乐(作曲)旋律,让人们为之动情,这中间就离不开乐队和指挥的功劳。还有插曲,如电影《英雄小八路》中的“少先队员之歌”,《红日》中的“谁不说俺家乡好”,《红色娘子军》中的“向前进”……有多多少少的电影插曲成为家喻户晓的流行曲,陪伴着几代人成长,至今人们还在传唱。而就是他,陈传熙,用他那熟练的指挥棒,把这些歌曲和音乐带给人们,成为鼓舞人们奋发向上的精神食粮。
陈传熙能有这样出色的成绩,和他从小喜爱音乐、奋发努力是分不开的。1916年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是广西南宁人。当时家里有一架风琴,兄弟姐妹都不感兴趣,而他特别喜爱,这架风琴陪伴他成长,从小就练就了他十分敏锐的听力,辨音的悟性特别高。
1921年,七岁的陈传熙随父亲在越南凉山居住,当时法国驻军有一支管乐队,经常会集体演奏,调剂军中生活。那深厚、雄壮、华丽的乐声不仅把小小的陈传熙带进了一个美妙、广阔的音乐天地,更使他迷上了音乐。每当军乐队走出军营演奏时,他跟在队伍后面,不管多远都跟着听着,嘴里哼着,他记住军乐队演奏的进行曲,他能模仿不同的乐器哼出不同的声响,他能哼出乐曲的很多片段,那些旋律扎进他幼小的心灵之中。
1927年,因为随父亲移居海防市,陈传熙有幸进了一所华侨开办的中学。这个学校十分重视音乐教学,这给他打下了扎实音乐的基础知识,学会了五线谱,学会了吹小号,成为学校管乐队里最小的演奏员。由于他痴迷音乐,学得十分认真,小号能吹奏出不同的旋律,能掌握不同的声部。优美的音乐素养又形成了他一种十分平和的性格,心态特别好,所以他学习特别踏实,特别有成效。
1934年,19岁的陈传熙终于遇到了他人生中的伯乐。上海国立音专的校长萧友梅来到偏僻的西南,在这里招收官费待遇的音乐专门人才。陈传熙以第一名的成绩叩开了“上海国立音专”的大门。国立音专当时有20多名学生,酷爱音乐的陈传熙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坚持了下来,他以出色的成绩毕业于音专的钢琴系,双簧管又吹奏得特别出色,他的优异成绩使他很快进入了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任双簧管演奏员,并且还在国立音专教课,后来又成了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就这样他靠着自己的勤奋努力,加上他的音乐天赋、潜质和对音乐的执着热爱,终于成为中国的音乐人才。解放后,作为新中国的交响乐团他曾多次出国参加演出,回国后不久就担任上海交响乐团的指挥。1958年由于电影发展的需要,他正式调进上影乐团任指挥,一直干到1992年退休,退休后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有闲下来。
陈传熙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只要看到总谱,就能根据影片的长度准确制定出乐曲主旋律的节奏、时值,使乐队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影片的配乐任务。很多电影导演和作曲家和他合作都十分愉快,他常常能在配乐过程中给作曲、导演提出一些极为宝贵的建议。这和他丰富的生活阅历有关,他看到电影画面会产生很多联想,从而充分发挥音乐的感人效应。他能给配唱电影插曲的歌唱演员以充分展示美妙歌喉和动情的乐感,从而帮助演员达到神情并茂的效果。著名歌唱家任桂珍曾对我说,和陈传熙指挥合作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情,“他总是那么和蔼可亲,在录音棚里十分耐心,给我们充分酝酿的时间,让我们情绪十分饱满时才录唱歌,即使时间非常紧,他总为演员创造条件,尽力帮助我们完成最佳的录音状态”。任桂珍提起陈传熙总是十分动情。
真没有想到,我这个晚辈也有幸和陈传熙这位老前辈合作了一把,让我不能忘怀。1987年是上译厂成立三十周年(上海译制片其实在1950年就成立了,当时附属在上海电影制片厂下属的一个翻译片组,直到1957年才独立建厂),为庆祝建厂三十周年,我写了一首长诗发表在《文汇电影时报》上。老厂长陈叙一看后决定让我在庆祝大会上朗诵这首诗。那天我去厂长办公室,老厂长对我说:“我现在打电话给上影乐团,请他们帮忙让乐团为你的朗诵诗伴奏配乐。”第二天我接到陈老(陈传熙,我以后一直称呼他陈老)的电话,让我把诗稿寄给他,他来设计配乐。我问陈老有《文汇电影时报》吗?就最近一期上发表的,他说有,别寄了。等哪天排练我再通知你。
排练那天,我骑车去上影乐团,一进排练厅让我大吃一惊,陈老指挥着六七十人的大乐队为我的朗诵伴奏,真让我又紧张,又兴奋。陈老让我歇一会儿,递给我一杯水,说:“呆会儿你先轻轻地给大家朗诵一次,让我们乐队感受一下。”我朗诵完陈老带头为我鼓掌,给我自信。他很快对乐队作了一些小小调整,我们就合作排练了。我诗中的内容回顾了译制片厂走过了三十多年的辉煌历程,表达了我们译制工作者对译制事业的热爱。我在音乐伴奏声中听到了我们译制的很多影片的音乐主旋律,不断地激发我朗诵的激情。排练很顺利,最后陈老向我提了些建议,中间有一处让我停顿略长一些,让音乐有个抒发的机会,最后结尾让我可以更昂扬些,音乐也将跟着我的情绪推向高潮,真让我受益匪浅,他的认真让我十分感动。庆祝大会是在上海美琪大剧院举行的,那天演出的节目都很成功,陈老指挥着乐团演奏了好些译制片的插曲,有《简爱》《红菱艳》《音乐之声》……在观众的不断掌声中连连加演。
那次演出后我和陈老的交往更多一些。他十分平易近人,每次影协活动,我们总会有很多的交谈,让我记忆最深的是他跟我讲述“文革”搞内参片时期为好多部译制片配音乐,“打补丁”的事儿。
“文革”时,我们译制厂完成了一大批内参片,其中很多影片是没有音效带的,音乐效果带都得重新制作,只有完成音乐效果带后才能和对白声带混合录音,完成译制片的配音工作。当时有很多影片,我们把片头片尾没有对话的那些音乐片段剪辑下来,重新制作一条音乐带。我和剪辑师多次合作过,音乐要连贯衔接好,这是件费时费工、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很多段的音乐,我们都在混录过程中采用淡入、淡出的蒙太奇手法来过渡,免得出太大的洋相。可是有好几部影片,中间缺的音乐在影片中无处可挖,这些重场戏必须有音乐,老厂长陈叙一只好求救于上影乐团,根据原片音乐风格配上去。先是请陈老来厂听原片的音乐,陈老很快记下总谱,回乐团后把乐曲分别用到各种乐器演奏上,重新组合乐队演奏。在陈老的指挥下,把影片中缺的音乐补了上去,当时我们听了觉得非常好,补得天衣无缝。陈老把这项工作称之为,用音乐为影片“打补丁”。这是一项很艰苦的工作,老厂长陈叙一知道只有陈传熙能完成。陈老音准、节奏、力度都会把握得十分准确,又能完成得和原片风格相一致。特别是陈老经验丰富,对长度把握得十分准确,大家称他是“指挥家的秒表”。
有一次影协活动,我和陈老坐在一起吃饭,又聊起当年“打补丁”的事儿,陈老对我说:“小孙,这种为影片音乐‘打补丁’的事情只有我们中国人干,国外的指挥是绝对不会干这种事情的。你想,每个乐队的乐器音质都不相同,演奏员的手法也各不相同,内行仔细一听就能听出来,而且每部交响乐的风格、细微之处都有所不同的。这种为影片‘打补丁’的活,严格讲是不可以的。‘文革’那时候我要提出来不干,肯定会挨批斗,工军宣队不会放过我,不扣大帽子才怪哪!我可不能自找倒霉,也不给你们老厂长陈叙一添乱,我们老哥儿们是多年的好朋友。说心里话那个年代生活多么枯燥,能参加这种工作才有机会看原版片,在当时可算是一种文化享受,你说对吗。”
“陈老你说得对,很对。当时我们根本不会想那么多,只要能完成影片译制任务就行,而且十分佩服你补丁打得天衣无缝,帮我们解决了大困难。对了,陈老,我觉得你身体特别棒,都耄耋之年了,还那么有精神,有什么养生之道可传授?”
“什么养生之道,自然灾害那会儿吃都吃不饱,后来又实行粮食定量,我是知识分子,每月只给28斤定量,我说我是指挥,是体力劳动,每月给32斤定量,我还是吃不饱。要说养生之道只有两条:一是心情好,以平和之心过平常生活。二是甩手疗法,我几十年的指挥生涯,就是每天甩手疗法,不停地在运动,所以至今还活的挺自在!”
这就是我们的指挥家,一个心态平和,干了一辈子电影,一辈子和音乐打交道的老艺术家。我深深地怀念他,凡是对中国电影事业作出努力、作出贡献的人,我们都应该怀念他们,他们的事迹都应该载入史册,让我们后辈们知道他们为中国电影事业所作出的辛勤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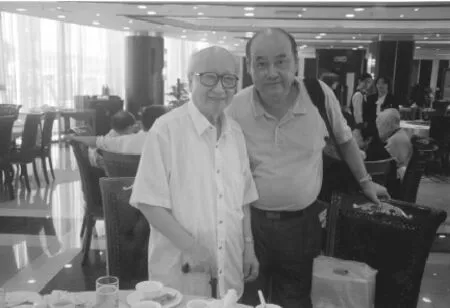
作者与陈传熙(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