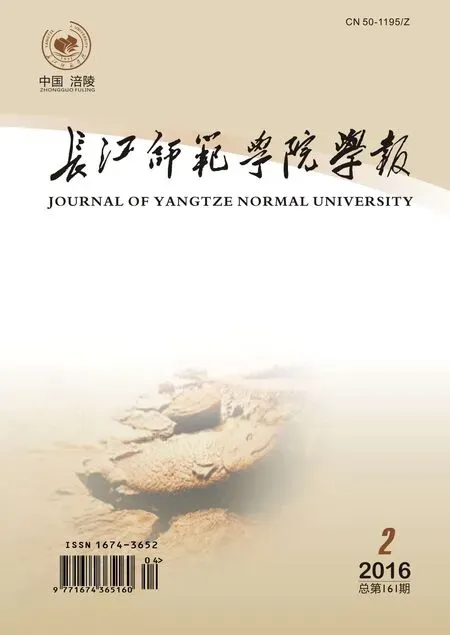泡沫?还是先机?
——2010年以来国内 “非虚构”文学写作研究综述
2016-03-29汪贻菡南开大学中文系天津300071
汪贻菡(南开大学 中文系,天津 300071)
□文学研究
泡沫?还是先机?
——2010年以来国内 “非虚构”文学写作研究综述
汪贻菡
(南开大学中文系,天津300071)
[摘要]虽然有着近一个世纪的写作史,本土 “非虚构”文学却始终作为边缘文类与虚构文学并存;2010年以来 《人民文学》“非虚构”栏目的设置让该写作模式重回聚光灯下,也一并引发了持续近5年的批评与论争。5年后媒体关注度趋于平稳,非虚构写作在各大主流文学杂志中已趋于常态化,批评界的思考也在逐步地深入。梳理2010年以来关于非虚构文学写作的研究,综述其命名之争、兴起缘由、意识形态与写作悖论等几个主要胶着点,以期回答关于何为真实、如何在场等文学本体论的基本问题。
[关键词]非虚构;《人民文学》;在现场;虚构;综述
“非虚构”是否是一个伪命题?自2010年2月 《人民文学》开设 “非虚构”专栏以来,“非虚构”“梁庄”“人民—大地”等一跃而成为媒介热词,并引发了近5年来在严肃的文学领域有相当规模的一次写作与讨论热潮。在CNKI数据库中设 “非虚构”为检索词,1980年至2015年2月期间可检索相关论文390余篇,2010年2月以后的论文约225篇,其中约有180篇 (包括硕士论文2篇)直接以 《人民文学》提出的 “非虚构”为讨论对象。然而,“非虚构”并非一个新名词:1980年,学者王晖就提出 “非虚构”的本土概念;也非新的写作现象:同样是1980年,作家刘心武就宣称正在大量尝试非虚构性的纪实写作。然而迄今为止,当我们提到 “非虚构”时,多数读者分不清其与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的区别;在文论领域对其阐释,则会发现其内涵模糊、外延不清;因跨界写作、涉及文本过多,作为研究对象则歧义重重。这不由引起我们的好奇:1989以来以报告文学为代表的 “非虚构”写作的公众影响力已然大幅下降,但为何在 “国刊”的一次并非炒作的号召下再度崛起?其提出背后关涉了、又将引发哪些当代文学创作的悖论或机遇?在2010年以后的相关论文中,对 “非虚构”提法持坚决否定态度的并不少见,但也有不少论者客观友好地讨论 “非虚构”命名的合法性、兴起缘由及其在当前创作中的悖论与不足。假设 “非虚构”只是又一次 “媒体先行”的泡沫式写作,那么随着这场写作热潮的渐趋平缓与常态化,关于从 “非虚构”写作中延伸出来的关于文学真实观的变迁、中国文学的 “非虚构叙事”传统、作家 “在现场”之如何可能、文学与现实间怎样的距离才是合适的等重要而有趣的文学本体论问题的讨论,或许并不只是一场学术泡沫吧!
一、命名之争:作为文本,或者方法
2010年2月,为发表韩石山的 《既贱且辱此一生》,《人民文学》单辟 “非虚构”专栏,以收纳那些不同于小说、散文、回忆录等传统文体范畴的文学,编者为此做了专门的陈述:“何为非虚构?一定要我们说,还真说不清楚……先把这个题目挂出来,至于非虚构是什么、应该怎么写,这有待于我们一起去思量、推敲、探索。”[1]这样的宽容姿态果然使 “非虚构”成为一个 “乾坤袋”,诸多似是而非的跨界文学都可往里装;然而也正是这种意味深长又愁肠百结的表述,引发了关于 “非虚构”命名及其合法性的种种争议。
就我们所能搜集到的资料而言,“非虚构”的提法最早来自美国华裔作家董鼎山。1980年,他将非虚构小说介绍到国内。随后南京师范大学的王晖将其与国内在此时大兴的报告文学相关联,并展开了长达30多年的持续关注。在1987年 《对于新时期非虚构文学的反思》(《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7年1期)一文中,王晖等极富远见地指出:随着新媒体的发达,非虚构写作必将随电子媒介的发达而勃兴。随后外国文学与新闻学的论者开始介绍美国新新闻主义写作和非虚构小说。1988年,约翰·霍洛韦尔的 《非虚构小说的写作》(春风文艺出版社,2011年)有了中译本,这是国内第一部介绍西方非虚构小说的著作。1999年,徐成淼对20世纪末的非虚构倾向问题做了精细的梳理,并发表了 《当前文学的 “非虚构”倾向》(《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5期)一文,详解其与报告文学之别,其文字字精当,绝无被媒介炒作起来的短暂兴奋。然而彼时关注者始终寥寥,直至10多年后 《人民文学》的非虚构专栏设置,这一并不新鲜的名词才重获关注。
梳理2010年以来对 “非虚构”持赞同态度的重要文章,如龚举善的 《“非虚构”叙事的文学伦理及限度》(《文艺研究》,2013年5期)、关军的 《不仅非虚构,而且写作》(《南方都市报》,2011年5月13日)等,大抵未出王晖与徐成淼的早年观点,即将非虚构与虚构视为写作的两大类,其中 “非虚构”囊括了非虚构小说、新新闻报道、报告文学、传记、回忆录、口述史、纪实性散文、游记等多种文类,其内核是田野调查、新闻真实、文献价值和跨文体呈现。对于 “非虚构”与报告文学的区别,王晖认为,前者是文体,后者是文类,文类包含于文体当中。这就意味着小说既可以是虚构的,也可以是非虚构的;非虚构写作既可以是文学的,也可以是非文学的。在2005年出版的论文集 《现实与虚构——当代文学文体批评论》(作家出版社,2005年)一书中,王晖重提并丰富了他在1987年提出的观点,即将非虚构写作划分为 “完全非虚构”和 “不完全非虚构”两大类。其中,“完全非虚构”包括报告文学、传记、口述实录体、新新闻报道、纪实性散文;“不完全非虚构”则包括非虚构小说、纪实小说、新闻小说、历史小说、纪实性电影、电视剧剧本等。这就进一步扩大了 “非虚构”的外延,从而与国际文学fiction和nonfiction的文类区分惯例趋于一致,其特点是模糊内涵、扩大外延。
与上述论者不同,也有不少研究者对 “非虚构”采取了见怪不怪实则暗自抵触的姿态,认为 “非虚构”不过是用来拯救因台阁化而沦陷的报告文学,是 “大报告文学”的一种新鲜提法,是反对不纪实的纪实文学而已。这些论者大抵是报告文学的长期研究者,其观点不能说没有说服力,其所谓 “文学当然是虚构的”“报告文学的底线就是真实”等,凸显出他们严格的文类训练功底。然其短板也显而易见,且不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虚构写作的弱新闻化、主题私人化、写法个性化等已然与传统报告文学大相径庭;一厢情愿地将文本日趋壮大、写法极富多样化的非虚构写作强行纳入传统文类当中,却对大众媒介勃兴后纷纭的跨界写作现象视而不见,也不能说是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吧!当 《纽约客》记者彼得·海勒斯融游记、新闻、散文于一炉的 《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风靡读者,摄影家陈庆港以10年追踪、近100幅摄影为基础的 《十四家——中国农民生存报告(2000-2010)》(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同时震撼文坛与新闻界时,再固守传统的泾渭分明的文体分类似乎有点吃力不讨好。蒋蓝曾在 《非虚构写作与踪迹史》(《作家》2013年19期)一文中阐明 “非虚构”与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和私人写作的区别;《人民文学》非虚构专栏写作主题的鲜明倾向性也不动声色地否定着自由写作者蒋蓝的一厢情愿。
事实上,这种概念术语方面的缠夹不清,都是在文本层面对 “非虚构”的界定,若我们进入到思维和方法层面,则对 “非虚构”的理解就豁然开朗了。在这方面,马建辉、张文东、霍俊明、祝勇等论者提供了极其开阔的思路。他们认为,“非虚构”不仅是一种文学文本,更是一种写作策略,是为文学和非文学所共同遵守的一种原则。该原则强调文学对现实的介入和对真实的凸显,与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一脉相承。因此作为写作策略,“非虚构”还意味着一种求真务实的写作方法与思考方法。“在新闻的维度上,它是一种探究式的社会学方法;在文学的维度上,它是一种复合型的思维方法;在二者综合的维度上,它又是一种跨文体的写作方法。”[2]无论这种写作或思考具有怎样的名分,其目的是获得表达上的自由。这就一举打破了我们对 “文学”概念长期以来的狭隘视野,从而以一种中间性的、内涵模糊的、新的叙述界定来给予当下向四面八方蔓延着的具有泛文学性的写作现象以极大的创作空间与可能,于是我们就在文本和方法两个层面接近了 “非虚构”。但问题仍未解决:倘若 “非虚构”被认可为一种写作方法和写作姿态,那么其所面对的文本就是一个庞大到难以估量的对象,也因此迄今为止尚没有对本土非虚构写作现象的完整梳理,而报告文学、纪实文学、记事散文等却可以做清晰的年鉴。作为一种文本方法,“非虚构写作”是可以被理解的;但作为一种文学文体,“非虚构文学”的提法仍有待更为精确的内涵界定。在种种对 “非虚构”的拒绝姿态背后,是否存在着 “纯文学”文类因长期占据文学史主流而产生的 “纳喀索斯情结”?归根结底,如果我们真正关注文学在当下社会的生存前景,或许就不好否定 “非虚构”吁请文学回到生活的努力和尝试,也不应基于泾渭分明的文类传统和跨学科时代的文体认同焦虑而对其渐趋繁荣的创作现状视而不见。在媒介的繁盛时代,“回到生活”也意味着回到从未隐匿的、文学的跨界写作实况。保持这种跨界朦胧状态,究竟是斜径还是正途?或许只有等待文学文本的创作实绩才能证明吧。
二、兴起缘由:文学的危机?抑或现实主义的危机?
当 “非虚构”的经典文本尚未沉淀,命名亦未厘清时,讨论兴起缘由是比较稳妥的切入点,也因此论者甚众,观点也很集中。不少论者都将20世纪60年代美国非虚构写作兴起的缘由与当下的中国进行比照,于是有两点得到共识:其一是社会现状的光怪陆离超出了文学的想象;其二是大众电子媒介的勃兴。当比虚构更精彩的生活随时随地在全球传播时,传统纸媒便由此进入到一场 “灾难”之中。约翰·霍洛韦尔的 《非虚构小说的写作》一书被频繁地提及,该书指出上述两点正是新新闻主义写作兴起的成因。在经济高速发展、电子媒介无孔不入的当下中国,是文学而不是新闻举起了 “非虚构”的大旗,以与可视新闻争夺越来越少的文字阅读者。但即便是非虚构写作,又何以能与读图、读屏时代的电子化力量相抗衡呢?擅长自省的文学批评者们并没有单纯地指斥快速发展的现实的荒诞,而是以 “想象力的绝望”来逼迫作家向事实转身,并由此进入一场对虚构时代和文学现实主义表达危机的反省。在此基础上,2010年以来的论者提出了如下几点关于非虚构写作兴起的中国缘由。
首先是有所提及但尚未讨论充分的西学影响与东方传统。自20世纪60年代 “走出美国”开始,“非虚构”写作引发了一场席卷世界的文学革命,fiction与nonfiction的分类即便在欧美乡村的儿童图书馆也为读者所熟知,非虚构作品的出版势头已然高出虚构作品。在与欧洲文学界交流的的过程中,作家邢军纪发现他们对非虚构文学的重视让人吃惊;就连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有着25部非虚构作品的文学大师奈保尔也表示:虚构小说的时代已成过去,只有非虚构写作才能抓住今日世界的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3]。电子媒介更使这种非虚构趋势从文学文本蔓延至一切电子文本。2001年,龚举善指出,在全球化时代,一个正努力迎现代化潮流而赶上的发展中国家,想要对世界范围内的 “非虚构”纪实倾向视而不见,似乎不太可能[4]。当然,如若完全没有内生的 “非虚构”可能,作为纯粹舶来品的 “非虚构”在中国,也不会如此迅速地得以蔓延,这就涉及到中国是否有非虚构传统的问题。
在这方面有两种观点值得关注:其一是汉学家宇文所安提出的中国文学具有非虚构的诗学传统;其二是华人教授吴琦幸从海外华人移民故事研究中提取出来的中国小说的 “亚纪实”传统。我们对此并无太多的注意,但这种跨文化视野给我们带来的启发往往是出乎意料的:比如当我们放弃纠缠 “非虚构”与报告文学的区别时会发现,报告文学乃是新闻与小说的嫁接,非虚构文学则是文学向历史的跨界。在一个拥有上千年史传传统和百年现实主义传统的小说国度,偏是虚构文学长期占据主流而 “非虚构”成为配角,则与 “纯文学”以拨乱反正的方式将自己定位为合法化的文学史姿态密切相关。当然,若需真正厘清这个问题,需单辟文章,逐步地追踪非虚构写作在中国的百年书写轨迹。这当中,20世纪初新闻对于中国现代小说兴起的意义、20年代苏俄革命通讯和30年代 “左联”倡导的西欧报告文学对中国报告文学的深刻影响,乃至缘起于日本的 “私小说”秉承的非虚构传统等,都是极具探讨价值的非虚构写作踪迹。
其次是虚构的危机与文学理想的重提。早在1991年,吴炫就在 《作为审美现象的非虚构文学》一文中指出:“非虚构文学的诞生,主要是建立在虚构文学与我们之间的一种过于长久的理性关系之上。”[5]当事实比虚构更精彩、当真相一再打破我们对于生活本质、人性本质的既定见解,文学如何能够再保持理性精神?如何能够允诺虚构与生活本质间的理性关联?如果所谓本质都是一团漆黑的不稳定的话?曾经的文学以对本质的深层批露而自傲,勃兴的商品经济和后现代主义则教会我们质疑充满主观主义偏见的所谓 “本质”,更质疑文学对 “本质”的再现能力。因此所谓 “虚构的危机”“想象力的绝望”折射的正是文学现实主义的危机。消费经济对文化和文学的冲击是如此的猝不及防却又顺理成章:一方面文学高于生活的神话正在无声地被消解,另一方面热辣滚烫的生活事实则让我们先是反思,逐渐地反对虚构文学的 “不及物”状态:无论是旧的写实还是新的写实,都不如投入生活本身 “写实”。先锋小说也因此在该层面上被霍俊明、张文东等论者再度审视。在20世纪80年代,他们曾开启文学新风,却又以对文学审美与虚构本质的过度把玩而导致文学的异化,“即不断使自己在虚构的意义上成为一种语言的游戏”,从而 “以虚构消解掉了真实的生活及生活的真实。”[6]论者闫海田不无启发性地将近年大行其道的穿越、盗墓类幻想小说与 “非虚构写作”的盛行作为一组对立而又相生的文学组象进行思考,只因在这两种繁盛的写作现状背后,是对消极写实和文学 “不及物”状态的共同反驳[7],于是有理想的知识分子作家重提文学的野心与理想,以拯救文学和作家的双重边缘化。作为 “纯文学”衰落的自然结果,“非虚构”呼唤高高在上的作家重回生活、改变自己对现实和读者的疏远以求更新乃至重获话语权,而这也是李敬泽一再强调的非虚构栏目的设立动机。尽管 《人民文学》及其编者并未鲜明地喊出 “重振文学公众影响力”的口号,但当其强调 “以吾土吾民的情怀……深度表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层面,表现中国人在此时代丰富多样的经验”(《人民文学》2010年第6期 “人民大地&行动者”非虚构写作计划启事第二条)时,其希望通过作家在场的方式重新唤醒文学社会效应的考虑却是显而易见的。在此基础上,“非虚构写作”成为一种行动诗学和介入诗学,霍俊明随之质疑:“这是否是 ‘干预生活’和 ‘写真实’在另一种时代的翻版?”[8]霍俊明所未能指出的是:背负了拯救电子媒介时代文学生存重任的 “非虚构”,因此陷入了用 “写实的现实主义”拯救 “虚构的现实主义”的循环悖论中。
其三是私人阅读时代的到来。该点同样与电子媒介的扩散密切相关。在一个每秒都可以上传心事与全世界共享的可读可写时代,读者的沉默一去不复返了。关于生活本质和时代英雄的宏大叙事被关注私生活和个体隐私的 “小叙事”消解,精英知识分子所传递的人文精神与公共经验在具有民粹主张的大众审美趣味的成熟中被质疑。在罗斯福的轮椅奋斗史和克林顿的内裤之间,更多的读者会首先选择后者。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 “私人化写作”、帝王宫闱历史探秘、名人日记出版等就已然透露出该种倾向,自媒体 (微博、微信空间)时代的到来更是将 “私人精神”全面张扬。在这种基于人类窥视本性和中国文学史传传统的 “小叙事”的熏陶下,读者的深度阅读动机与作者的原创能力一齐衰退。当本雅明哀叹讲故事的艺术被新闻传播当头肢解的同时,听故事的能力也一并消逝在滚滚到来而又飞速逝去的信息轰炸中。大众借助媒介可自由地掌握真相,精英发言人对真理的话语权从此被消解;抽象的宏大叙事便再也满足不了读者胃口大开的窥私欲望;大历史所追求的逻辑理性也早已在新历史主义的解剖下呈露虚妄的本质。诚如尹均生在分析历史性纪实文学热的成因时所指出的:“当代人们不再甘心于担任从属于他人的角色……人们的参与意识有了增长……作家与读者都渴望……更大的真实,更现实的真实,非纯然虚构的真实。”[9]如果说上述拯救文学边缘化的努力和文学忧患意识的返场动机过于宏远的话,那么投合读者的阅读心态从而拯救图书出版的动机则更为切实而恳切了。
值得玩味的却是,《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在深谙这些缘由后得出的结论是:“倡导非虚构写作,是一种争夺的姿态,争夺什么?争夺对真实的发布权,发表权!”作为被纸媒启蒙又伴随电子媒介成长的我们这一代,面对这种高亢的文学宣言,我们不由怀疑:在一个鼠标认识世界的时代,想要把那种通过文学认识生活的古老权力争夺回来,这究竟有多大的胜算?也同样是基于这一怀疑,在讨论了非虚构命名与兴起缘由的基础上,伴随媒体热潮的回落,在近两年的讨论中,论者们更多地进入了对其写作合法性的质疑与写作悖论的反思。
三、悖论与反思:人文精神困境与写作悖论
在对非虚构写作悖论的反思中,有几篇文章是特别值得提及的,如李丹梦的 《“非虚构”之 “非”》(《小说评论》,2013年3期),葛丽娅的 《作为 “他者”的农村形象——“非虚构”农村文本的写作之反思》(《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5期)、龚举善的 《“非虚构”叙事的文学伦理及限度》(《文艺研究》,2013年5期)以及林秀琴的 《“非虚构”写作:个体经验与公共经验的困窘》(《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11期)等。无论是理论的高度、视野的宽阔还是思考的深入,这些文章都令人耳目一新。其提出的问题大抵包括这么两个方面。
(一)非虚构写作的人文精神悖论
李丹梦敏感地发现,2010年以来的非虚构作品热衷于负面题材、敏感故事和边缘人群。作为对台阁化报告文学的反拨,非虚构写作当然应该回到严肃的批评视野,直击当下中国的苦难与疼痛,似乎非如此,便不足以够上 “非虚构”的档次,更不能反映作家对吾国吾民的忧患意识。对此,李丹梦指出:这是以死亡、苦难和暴力为噱头,来投合大众的猎奇心理和浅尝辄止的民生关注,其根源在于叙述主体的膨胀,在这种貌似庄严真实的写作姿态背后,一种急功近利的叙述主体自我神圣化动机呼之欲出。负面与边缘题材固然是真相的一部分,但并非真相的全部;“非虚构”若执拗于推介这些题材,是否会在加重不良公众导向的同时,落入从政治化走向台阁化的报告文学的窠臼?
葛丽娅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非虚构叙述主体的膨胀导致了被叙述者 (多数时候是农村)始终作为 “他者”的形象而存在;知识精英、权力精英和资本精英用不同的方式叙述农村,在满足写作圈子内部游戏规则的基础上,借助农村和农民的苦难来开辟自己的突围阵地。王晖曾指出非虚构写作处在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交汇点上,今日看来,这正是 “非虚构”用大众文化思维炮制和兜售所谓精英文本的营销智慧之所在。知识分子渴望以公知形象返场,重建文学的公众影响力,大众希望通过点到为止的“深刻”来满足自己猎奇和自我神圣化的内心期许,多方利益合围,“非虚构”遂大行其道,因此李丹梦得出结论,“非虚构的出炉,乃意识形态、知识分子、大众在文学领域的一次成功合作,利益的 ‘交集’或曰合作基点…… 《人民文学》于此看中的是 ‘正统’风格的延续,对文坛的干预;知识分子则趁机重建启蒙身份,投射、抒写久违的启蒙情致;大众在此欣然领受有 ‘品位’的纪实大餐。三方皆大欢喜,‘吾土吾民’就这样被 ‘合谋’利用了。”[10]
该结论气势磅礴又一针见血,所不足的是:李丹梦没有指出文学批评者也参与了这场利益角逐,事实上文学的边缘化引发的不只是作家,更有文学批评者的困境。当 《人民文学》以 “吾土吾民”“人民—大地”“困顿与疼痛”等大词征募非虚构写作计划时,长期苦于无法介入生活的文学批评者遂抓住此良机重新标注文学的精神高地,一同参与到新时期 “中国叙事”的宏大构建当中。面对膨胀的叙述主体,如若批评主体没有同样膨胀的批评野心,他们便不会始终停留在对梁鸿的 “代言”、慕容雪村的 “良心”、萧相风的打工者身份上的津津乐道,却对蒋蓝、李娟等功力深厚、文学性、趣味性与思想性皆难得的作品少有关注;同时这也部分地解释了当下的非虚构研究为何多是围绕非虚构概念及其主题的探讨,而极少进入到对文本的文学审美批评当中。
(二)“非虚构”之 “非”的困境
该问题其实囊括了两个小问题:非虚构的 “真实”是怎样的?“在现场”如何可能?关于真实,龚举善、马建辉等人从文论角度充分论证了 “非虚构”所强调的真实只能是文学真实而绝非生活真实或科学真实;衡量文学真实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读者的感觉真实,也即合理真实与想象真实。对此,李敬泽有清晰的认知,他指出非虚构之 “非”是一种求真的写作姿态,号召作家消除身心内外的懒惰、走进生活、回到现场。
关于 “在现场”,李丹梦指出,在叙述主体膨胀的启蒙惯性中,作家无法摆脱他那高高在上的预设理念和无处不在的镜头式人格,这就使得 “在现场”根本不可能。如幽灵般盘旋在 “非虚构”上空的 “看”的意识注定了作家要将被看者纳入到写作主体和阅读主体的 “期待视野”中而对真正的真相视而不见;从慕容雪村深入魔窟23天的 “伟绩”和蒋蓝深入田野山河10数年的写作努力可以看到,缺少文学神圣感与谦卑态度、匮乏田野调查专业知识与社会学传统的非虚构写作,终究只是 “伪在场”,他们很容易用知识分子的廉价同情取代被叙述者的自我发声,更会迷失在叙述主体和阅读主体的自我崇高幻觉中,从而消解文学应有的真正的个体关怀。
这种情况就带来了如下的矛盾,一方面如李丹梦所言,非虚构以强化国家与民族叙事对走向疲软的个人化写作予以纠偏,但另一方面,当下非虚构叙述的私人性、回忆性、情绪性、人物塑造的非典型性,尤其 “伪在场”特性,都使其宏大的国家叙事成为一种不切实际的努力。作为凝结多方利益主体的合作基点,“中国叙事”不过是在文学理想的高扬下引发的关于 “中国形象”的一场非虚构想象——《梁庄》距费孝通的江村或陶行知的晓庄还有一定的距离;纵然李娟、王族等关注了游牧民族的消亡问题,但那些利益牵涉更多、根源植入更深广的如食品安全、雾霾、医患、养老等宏大命题,却绝非以私人化视角切入并自傲的非虚构写作者们所能把握的……这些想象不仅损害了 “非虚构”之真实,最终还将损害到非虚构写作的文学本质:当写作者过多地以启蒙话语替代审美话语、批评者对其宏大主题的关心超过对其文本价值的关注时,非虚构写作的诗性品质和美学精神也就一并被剥落了。所幸,该点已得到学者徐肖楠、申赋渔[11]等论者的密切关注。作为一种虽非新鲜但正在崛起的文本与写作策略,其跨文体写作特征使得它在媒介时代更容易吸收、整合,进行文体更新,其在文学、新闻、历史等诸种文体间徘徊的特征应当成为它兼采众家之长的契机,而非用新闻性取代文学性、用社会学意义涵盖文学价值。但徐肖楠所没有指出的是:在文学性泛滥、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私阅读、自媒体时代,致力于 “非虚构”的文学究竟要以什么来吸引更广大的读者呢?若缺少真正有分量的审美文本,非虚构写作是无法走得长远的。而基于如此宏大、殷切的实用性写作动机,作为非实用的非虚构文学将会走向何方呢?
四、当下 “非虚构文学”研究的不足与反思
在对非虚构写作研究的梳理中,我们常陷入困惑:这究竟是不是一个有价值的论题?如此既不新鲜、文体归属不明、又缺少优秀文本的写法,究竟能走多远?与此同时,“非虚构”所牵涉的千头万绪则使论者很容易踏入理论的漩涡而纠缠不清,比如关于非虚构的 “国家叙事”问题,所要讨论的不仅有叙述主体的自我膨胀,还有批评者的启蒙惯性、读者的忧患自觉,乃至 《人民文学》的国刊传统;又比如关于“在现场”如何成为可能的问题,其实关涉了底层文学始终悬而未决的 “代言”危机和叙述主体不可能摆脱的 “看”者姿态;再比如作为多方利益的妥协产物,讨论 “非虚构”就理应同时关注叙述主体、阅读主体、批评主体、传播媒介以及被叙述者等多方观点,如此才能集中讨论何谓真实、如何真实的问题。如此,对中国文学变动不居的真实观的嬗变之梳理就是应有之意了。如果非虚构文学坚守其对真相的发布权,那么它就应当被视为一种传播,而对非虚构文学写作的研究就因此需借助传播学、信息学、经济学等多维视野而全方位地铺开。或许也正是这种极具发散性的跨界写作与跨界批评模式,既让人困惑,又充满未知、危险和迷人的理论魅力。
与此同时,2010年以来的非虚构写作研究始终匮乏对文本的直接的审美分析,仅有的文章也大多集中在对 《梁庄》《打工记》等名篇中,其关注点也多为作家的动机访谈、作品主题的社会价值等,能够从文本本身切入的仅有刘亚美的硕士学位论文 《论 “非虚构”写作 〈梁庄〉的作者主体性》(广西师范学院,2013年)一篇,然其结论仍是社会学、伦理学意义上的。究其因,不仅与非虚构写作缺少有力的审美文本有关,也与非虚构写作的文体归属不明有关,比如对李娟、刘亮程等的研究还只是限于散文领域,但缺少文本批评的文学研究终究是隔靴搔痒,没有 “贴肉的批评”,便无法真正理解当下非虚构写作的现实意义,更无法对其写作提出有价值的批评和引导,这就使 “非虚构”极易陷入短暂的话题消费狂潮中,并最终淹没于追新逐异的媒介批评。事实上,全面的阅读还会揭示出迄今为止的非虚构写作究竟给文坛带来了哪些正面影响。比如借助 “非虚构”这个热词,可以将蒋蓝、李娟、陈徒手等优秀的写作者纳入更多的普通读者视野;而经由虚构文学半个多世纪的审美熏陶,更高层次的读者已经有能力深入欣赏兼具文献色彩、特写实录、史学、社会学价值的非虚构作品了。这就接近了非虚构文学想要更多地介入生活的写作初衷,不是吗?
同时,由于非虚构写作的内涵始终悬而未决,其研究对象无法确定,遂使对本土非虚构写作史的梳理和发掘只能停留在想象之中。只发掘百年来 “非虚构”提法的历史和西方非虚构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轨迹,并非全无可能;前文提及的中国文学的史传传统与非虚构的内在关联以及现代以来相对于虚构文学的 “非虚构”写作的边缘化亦是值得反思的;王晖与青年论者张莉都曾提及的女性写作中的非虚构倾向也颇值得深入探究。理论的缺失或许是非虚构研究的短板,受刘亚美、蒋蓝等论者启发,我们以为,叙事学与民族志或许可以成为近身思考非虚构叙述主体膨胀问题的途径之一。
归根结底,非虚构写作在这个时代大行其道,并不意味着它仅仅是这个时代的衍生物[12],作为一种并非短期存在、且能引发如此繁复的理论问题的写作现象,阶段性地思考 “非虚构”,或许不只是一种追逐热点之举。在文学无可挽回的衰落中,回到作家何以在场、真实如何可能、文学何以 “有用”等文学本体论问题,也不是全无意义的吧!
参考文献:
[1]编者留言[J].人民文学,2010(2).
[2]马建辉.非虚构文学的三个维度[J].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5).
[3]董鼎山.非虚构著作胜于虚构小说——奈保尔讨论伊斯兰教与今日世界[J].彼岸,2006(1).
[4]龚举善.全球化背景下纪实文学的文化回应——兼及比较文化视野中的非虚构写作[J].伊犁教育学院学报,2001(1).
[5]吴炫.作为审美现象的非虚构文学[J].文艺争鸣,1991(4).
[6][12]张文东.“非虚构”写作:新的文学可能性?——从《人民文学》的“非虚构”说起[J].文艺争鸣,2011(3).
[7]闫海田.当下小说“情节荒诞”与“消极实写”的两极倾向——关于“穿越”“魔幻”及“非虚构”现象的思考[J].文艺评论,2012(7).
[8]霍俊明.“非虚构写作”:从文学“松绑”到“当代”窘境[J].文艺争鸣,2012(1).
[9]贾文清.非虚构文学研究的新视角——读尹均生的《国际报告文学的源起与发展》[J].中华文化论坛,2010 (3).
[10]李丹梦.“非虚构”之“非”[J].小说评论,2013(3).
[11]徐肖楠.非虚构文学如何突破媒介包围[N].文艺报,2012-07-30;申赋渔.非虚构:在新闻达不到的地方生成力量[J].传媒观察,2012(10).
[责任编辑:丹兴]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652(2016)02-0077-07
[收稿日期]2015-11-11
[作者简介]汪贻菡,女,安徽合肥人。博士生,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与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