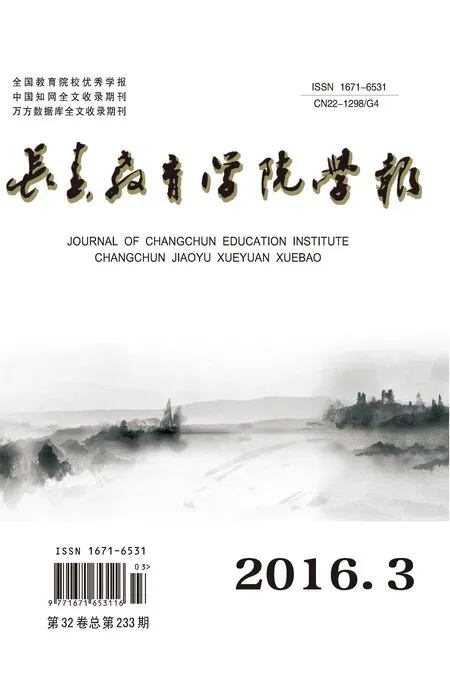陈廷焯与王国维对贺铸词评价的比较研究
2016-03-28朱庆林
朱庆林
陈廷焯与王国维对贺铸词评价的比较研究
朱庆林
摘要:北宋名家贺铸的词,历代褒贬不一,备受争议。其中陈廷焯、王国维两人的评价相差最为悬殊,陈廷焯赞之过高,王国维则贬之过深。陈廷焯提倡“沉郁”,而贺铸词极具沉郁之风且变化多端,所以受到陈的推崇;王国维讲究词的境界,反对用典、因袭前人,贺铸词用典过多,因此受到王的排斥。由此可见,陈、王二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都有各自的理论依据。然而,由于二人对贺铸词没有进行深入地挖掘以及受评判标准的局限,使他们的观点暴露出明显的不足。陈、王二人为读者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去分析贺铸词。
关键词:贺铸;东山词;陈廷焯;王国维
朱庆林/扬州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江苏扬州225000)。
贺铸,字方回,北宋著名词人,著有《东山词》。历代对贺铸词评价颇多,或褒或贬,没有定论。清代词论家陈廷焯在《词坛丛话》中说,古今词人众矣,余以为圣于词者有五家:北宋之贺方回、周美成,南宋之姜白石,国朝之朱竹垞、陈其年也。[1]陈廷焯对贺铸赞赏有加,并将其词推至北宋乃至整个词坛的巅峰。然而,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不苟同于前人看法,在《人间词话》删稿中直言不讳:北宋名家以方回最为次。其词如历下、新城之诗,非不华赡,惜少真味。王国维此论又将贺铸其人其词的地位降至谷底。陈廷焯与王国维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和评论与他们的理论观念、评说标准有直接关系。
一
宋人张耒对贺铸词的评论言简意深:“文章之于人……是所谓满心而发,肆口而成,虽欲已焉而不得者。若其粉泽之工,则其才之所至,亦不自知也。夫其盛丽如游金、张之堂,而妖冶如揽嫱,施之袪,幽洁如屈、宋,悲壮如苏、李,览者自知之,盖有不可胜言者矣。”充分肯定并赞赏了贺词有感而发、不矫揉造作的写作态度和多变的特色风格。陈廷焯在吸收前人观点的基础上,融入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昔人谓方回词妖冶如揽嫱,施之袪,幽洁如屈、宋,悲壮如苏、李。此犹论其貌耳,若论其神,则如云烟缥缈,不可方物。可见陈廷焯较之张耒,对贺铸词评价更加全面。为了突出贺铸在词坛无可撼动的顶尖地位,陈廷焯大胆地将其与北宋一流词作家进行比较并表明优劣,他在《词坛丛话》中写道,昔人谓东坡词胜于情,耆卿情胜于词,秦少游兼而有之。然较之方回、美成,恐亦瞠乎其后。[6]苏轼、柳永和秦观都是词坛周知的大家,他们的名气、才气高于贺铸,陈廷焯却标新立异,将其立于苏、柳、秦三人之上。此外,他还在《云韶集》中说:易安词骚情诗意,高者入方回之室,次亦不减叔原、耆卿。认为李清照优秀的词作可与贺铸词相提并论,次一等的作品也不亚于晏殊、柳永的词作,对贺铸词的喜爱和推崇不言而喻。
陈廷焯对贺铸词定位如此之高,与他的词学观有很大关系。“沉郁顿挫”原本是指杜甫的诗歌风格,陈廷焯借用“沉郁”二字,作为《白雨斋词话》的核心理论,并赋予了其全新的内涵:作词之法,首贵沉郁,沉则不浮,郁则不薄。其自序尝称《词话》曰:本诸《风》《骚》,正其情性,温厚以为体,沉郁以为用,引以千端,衷诸一是。陈廷焯评贺铸词:“方回词,胸中眼中另有一种伤心说不出处,全得力于楚骚而运以变化,允推神品。”“方回词极沉郁而笔势却又飞舞,变化无端,不可方物,吾乌乎测其所至”。他认为贺铸词继承了《风》《骚》传统,又极具沉郁之风,因此对其倍加青睐。
陈廷焯对“沉郁”词的写法也有相应的规定,如“意在笔先,神余言外”“若隐若现,欲露不露”“终不许一语道破”等等,这与历史相沿的比兴手法极其相似。贺铸正是第一位自觉运用《离骚》比兴之义的北宋词人,他注重对内心世界的描写,运用比兴手法,力求深隐曲折,营造朦胧迷离的意境,从而表达出词人的“心志”。如《芳心苦》表面是咏荷花,事实上是用拟人手法,塑造了洁身自好、孤芳自赏的“骚人”形象,表明自己的旨归和理想,这正如陈廷焯所说“骚情雅意,哀怨无端,读者亦不自知何以心醉,何以泪堕”。
陈廷焯认为,“沉郁”不仅是为词的基础,更是至高无上的法则,“若词舍沉郁之外,更无以为词”。他赞贺铸词“方回词笔墨之妙,真乃一片化工,离骚耶?七发耶?乐府耶?杜诗耶?吾乌乎测其所至”。由此可见,贺铸词不仅善用比兴手法,还颇具沉郁,变化多端、风格多样,离骚、七发、乐府、杜诗精华兼而有之。由此可见,陈廷焯推举贺铸词为词坛之圣并非空穴来风、无稽之谈,存在一定的合理性。
二
王国维对贺铸词的评价与陈廷焯大为不同,他称贺词“如历下、新城之诗”,甚至将贺词归同于李攀龙、王士祯的诗。他评王诗说“若国朝之新城,岂徒言一人之言而已哉,所谓‘莺偷百鸟声’者也”。认为贺铸词“非不华赡,惜少真味”,不能够“感自己之想,言自己之言”,否定的态度非常明显。他曾在《清真先生遗事尚论》中说:“故以宋词比唐诗,则东坡似太白,欧、秦似摩诘,耆卿似乐天,方回、叔原则大历十子之流……。”大历十才子诗风寒冷萧瑟,追求清雅闲淡,后世对其评价不高,王国维又将贺铸词比作大历十子之诗,可见讽刺意味十足。刘体仁在《七颂堂词绎》中写道:“词有警句则全首俱动,若贺方回非不楚楚,总拾人牙后慧,何足比数。”贺铸词的缺点是喜用唐人的成句,词境不高。王国维认为词的境界最为重要,他明确表示: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所以,贺铸词缺少意境的短板自然成为王国维贬低的依据。
贺铸词中使用唐人成句、多用典故,是其意境不高的主要原因。王国维主张白描,反对用典。他在五八则《隶事与诗才》中说:“以《长恨歌》之壮采,而所隶之事,只‘小玉双成’四字,才有馀也。梅村歌行,则非隶事不办。白、吴优劣,即于此见。不独作诗为然,填词家亦不可不知也。”所谓“隶事”即为“用典”,王国维将白居易《长恨歌》和吴伟业《圆圆曲》进行比较,权衡其能不隶事、少隶事、非隶事不办的高下优劣,对白居易“能不使事”的才华极为赞赏。可见,他不主张隶事。贺铸词中的大量用典导致了一些词作不是有感而发,更像是一场文字游戏。贺铸词中许多句子直接截取于唐诗或者稍加改编,而且还消逝了原诗本来的美感,没有完全释放作者自己的情感,因而王国维给予了“惜少真味”的评价。如贺铸词作《晚云高》,词云:
秋尽江南叶未凋,晚云高。青山隐隐水迢迢,接亭皋。二十四桥明月夜,弭兰桡。玉人何处教吹箫?可怜宵。
该词的典故出自杜牧的《寄扬州韩绰判官》:“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贺铸只是稍加改动,便成《晚云高》一词,沿袭成分十分严重,作品失去了真情实感,因而这种创作并不成功。贺铸不少词存在着上述毛病,过多用典,必然要牺牲词作最真实的“味道”,消殆词的意境,站在这个角度考虑,王国维看低贺铸词,并非没有道理。
三
陈廷焯、王国维将贺铸在词坛中的地位推向了两个极端,陈廷焯赞之过高,王国维则贬抑太甚。他们的论断虽然有充分的证据和一定的说服力,但是各自所处的视角过于狭隘,难免会有盲点,考虑自然缺乏全面性。陈廷焯标榜贺铸词,是因为贺铸词符合他的“沉郁”理论。他曾如此点评贺铸词:“方回词,儿女、英雄兼而有之。词至方回,悲壮风流,抑扬顿挫,兼晏、欧、秦、柳之长,备苏、黄、辛、陆之体,一时尽掩古人。两宋词人除清真、白石两家外,莫敢于先生抗行。”陈廷焯认为贺铸词婉约、豪放两种风格
兼备,又集宋代众大家之长,“悲壮风流、抑扬顿挫”,自然具备“沉郁”之风。他对“沉郁”的理解,是“意在笔先,神于言外”,“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与一草一木发之”,但“终不许一语道破”。由此观之,“沉郁”只是词作所表现的外在之美,不是重点。而词作最为关键的是作者是否“用情”。反观贺铸词,陈廷焯虽说“方回词,胸中眼中,另有一种伤心说不出处”,不假思索地肯定了贺铸词“温厚”“含蓄”的情感。然而,翻看全部贺铸词,事实并非如此,陈廷焯的这种结论不免过于武断,不够严谨。贺铸词作善于用典,不是所有作品都表“温厚”之情,有的纯粹是改前人作品“翻诗为词”,并没有真实情感可言,如前面提到的《晚云高》,正是王国维所说的缺少真味。因此,陈廷焯对贺铸词有过誉之嫌,其原因是陈廷焯没有以辩证的态度深入归纳总结贺铸每一首词,没有给出全面客观的评价;王国维对贺铸词的看法,虽有洞见,但依旧存在很大局限。他十分崇尚意境高远的词,排斥用典,贺铸词自然难以让他赞赏,排在北宋大家之末。然而,王国维认为贺铸词蹈袭前人语仅仅是为追求形式的华赡,而完全忽略了贺铸词作的情感内蕴,这也是非常片面的。以贺铸最著名的豪放词《六州歌头》为例,此词虽多处用典,却也抒发了作者矢志不渝的豪情壮志和强烈真挚的报国情感,并不是王国维认为的“华而不实”,“华赡”其实与“真味”在词作中是可以共存的,两者并不矛盾。
综上所述,对于贺铸词的评价,陈廷焯、王国维发表了各自的观点,虽大相径庭,但其实也并不矛盾,更没有谁是谁非之分。不仅如此,他们的观点也能起到相互指正的作用,从而印证对方观点的不足之处。最重要的是,根据陈、王不同视角的评论能启发读者更为客观地给贺铸及他的词一个公平公正的评价。
参考文献:
[1]唐圭璋.全宋词[M].北京:中华书局,2011.
[2]贺铸,钟振振.东山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3]陈廷焯.白雨斋词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4]王国维.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5]王国维,施议对.人间词话译注增订本[M].湖南:岳麓书社,2008.
责任编辑:贺春健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531(2016)03-002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