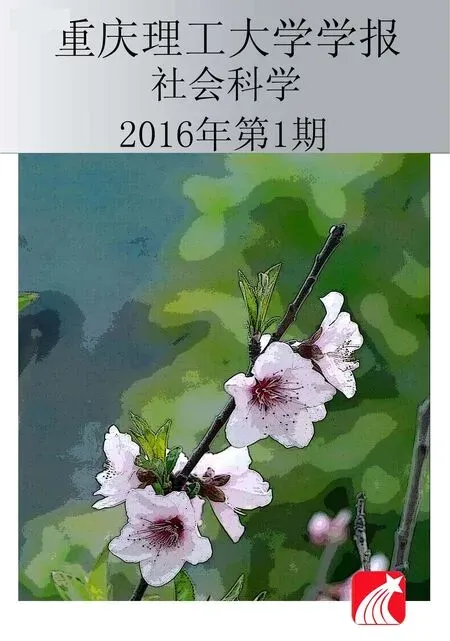从经济体需求方和供给方看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
2016-03-28张晓波
张晓波
(重庆行政学院 经济学教研部,重庆 400041)
从经济体需求方和供给方看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
张晓波
(重庆行政学院 经济学教研部,重庆400041)
摘要:近年来论及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使用频率最高的概念非“新常态”莫属。新常态实质上是经济运行规则、结构和发展特征等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变化。而对经济发展新常态背后的逻辑基础和形成机理的学理性分析是解读新常态主要特征的必然要件,因此,主要从工业化进程、后发赶超和经济转型3个维度阐释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形成机制和客观必然性。从经济体的供给面来看,中国经济新常态呈现增长放缓趋势,生产率和增长质量的关键作用愈加凸显,低碳增长模式导引下的结构变动以及创新愈发重要。从经济体的需求面来看,消费支出渐成经济增长的关键推动力,步入绿色增长理念导向下消费需求升级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关键阶段,步入一个消费需求推动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催生新的消费需求的良性循环的新阶段。
关键词:新常态;需求侧;供给侧;工业化进程;后发赶超;经济转型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指出,“要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1],这种平常心态体现在国家发展所具有的长远眼界、长效目标和长治久安的战略思维中[2]。在7月份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习总书记再次用“新常态”概括了中国经济发展特征变化和发展趋势;紧接着8月初的《人民日报》连续3天刊登了《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系列评论,阐释了新常态的内涵和政策含义,指出新常态下至关重要的对接工作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3]。在11月份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凝练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3个关键要素,即经济中高速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创新驱动发展[4]。在我国经济向中高速增长演变的过程中,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和明确宏观经济的合理区间渐成宏观常态[5]。与此同时,有学者指出应注意防止中国和美国两种新常态经济的周期错配深度恶化[6]。在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方向演进[7]。
针对习近平总书记用新常态描述正在变化中的中国经济以及对中国经济发展特征变化的洞察,国内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就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和引领新常态进行了论述。但是大多数文献往往缺乏对新常态的学理性分析,这是其一。其二,新常态是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变化的事实描述和理论概括。经济发展新常态作为中国经济的发展特征,可以从多重视角、领域和层面来描述,平心而论,对中国经济发展特征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变化比较恰当的解读是早些时候提出的3期叠加,即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3期叠加和经济新常态存在哪些关联?其三,除了从时间序列对新常态进行考察外,还需从横向的国际视角进行比较。按照世界银行标准,中国已迈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国际经验显示,当一个经济体迈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存在两种发展情景,一种是国家成功迈入高收入国家,而另一种则是经济持续放缓、停滞并长期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因此,有必要从国际视角比较这两类国家和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才能历史地和辩证地洞察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关键特征。文章旨在从上述3个方面审视和考量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主要特征。
一、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内涵及其经济学要义
“新常态”这一提法最早出现于2001年的美国,主要指美国在面临新经济危机和恐怖主义威胁之下,发展格局可能长期化,进而发展成为一种常态。随后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在2010年一个题为“Navigating the New Normal in Industrial Countries”的发言中,重新用“新常态”归纳和刻画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西方经济体特别是美国经济运行低迷的态势和缓慢而痛苦的复苏过程。他归纳出西方经济体特别是美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为:增长乏力和失业率高企;危机前高杠杆率、不合理的债务负担和信用扩张等结构性问题致使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修复其资产负债表需要较长时间;收入、财富和机会等的不平等加剧,弱化了协调治理机制,增大了经济脆弱性;危机改变了金融系统放任、自由的理念,强化了政府监管职能[8]。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运行的实际轨迹不幸被埃里安所言中,从而使得新常态的概念逐渐被学界和政界所关注和认可。经济发展新常态从实质上是指经济发展特征和经济运行规则、机制、模式从一种经济形态向另一种经济形态的变化。如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确实改变了金融市场的运行规则和模式,强化了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对金融市场的监管,美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来自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变化,共同塑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9]。在中国语境下,经济增长告别两位数,迈入中高速增长,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首要表现[7]。如何认识和理解中国经济新常态背后的逻辑基础和形成机制,对把握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极为重要。经济新常态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特征变化的高度概括,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解读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关键形成机制。
从工业化进程维度来看,经济新常态揭示和洞察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和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根据国际经验和发展经济学理论,各国经济发展显示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农业经济发展到工业化经济,各国大致经历了不发达的农业经济、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等阶段。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这本颇具争议但影响深远的著作中,基于长期的数据收集和分析,得出一个关键结论:经济高速成长是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关键特征[10]。根据托马斯·皮凯蒂的估计,从远古时代到工业革命和工业化以前的人类发展历史进程中,全球人均产值年均增长率接近于零,只是由于全球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为0.1%,这才使得全球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0.1%。工业革命和工业化进程开始以后,1700—2012年全球人均产值和人口的年均增长率同为0.8%,从而使得全球总产值的年均增长率为1.6%。
各国发展经验表明,工业化后期和工业化中期相比,其发展特征的一个典型差异是,在工业化中期依靠投资和重化学工业驱动经济高速成长的经济形态难以为继。之前推动经济快速成长的基本要素、规则等在后工业化时期显得不那么有效,随着潜在增长率的下降,经济快速成长的动能将自然回落。2010年中国的工业化综合指数为66,标志着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迈入了工业化后期[11]。中国也存在类似的发展阶段,经济新常态是工业化发展内在规律的客观表现,同时也是跨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传统路径和向低碳经济发展转型的必然要求。
从后发赶超的维度看,后发优势是赶超国家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在赶超的初始阶段,后发赶超经济体的市场空间大、与技术前沿经济体技术差距大,结合低价劳动力成本和丰富资源等禀赋比较优势,依靠引进国外技术和资金,能比较容易地驱动经济快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得益于以下结构因素支撑,我国经济才实现了高速增长。一是人口红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市场的力量激励着劳动力从生产效率较低的农村部门向生产效率较高的城市工业部门转移,劳动力的再配置效应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TFP),进而推动经济高速成长。二是技术引进所形成的经济辐射效应。由于我国经济赶超阶段技术水平与技术前沿国家存在较大差距,技术引进空间较大,因此,技术的较易获得性以及引进的技术都是国外成熟的技术,企业很容易组织生产并扩大生产规模。三是全球化红利。与舒尔茨共同分享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亚述·路易斯爵士在颁奖大会上以“增长引擎转速下降”为题发表了演讲,阐述了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格局。他认为发展中世界经济增长与发达世界经济增长存在密切联系,两者之间存在着趋同倾向。他指出:“过去几百年中,发展中世界的产出增长速率依靠发达世界的产出增长速率。发达世界增长迅速时,发展中世界增长也迅速,而发达世界速率下降时,发展中世界速率也下降。”[12]而发达世界控制发展中世界的增长动能所依赖的主要环节是贸易。
然而,上述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结构性因素,蕴含着我国经济增速结构性趋缓的必然,并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结构转型、增长动力格局的演变而日益凸显。一方面,从20世纪以来各国发展经验来看,在其经济高速增长的工业化过程中或多或少存在人口红利。以日本为例,日本在1956—1973年的黄金增长时期也捕捉到了快速增长的人口红利,至此以后,尤其是1990年以后,伴随着老龄化问题的凸显和劳动年龄人口增速的下降,增长趋于低迷。相似的趋势在中国也逐渐显现。一是近年来“民工荒”和“用工荒”现象在东部沿海地区凸显,二是过去农民工工资长期处于低水平的旧常态难以为继,三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出现拐点,我国在国民未富状况下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另一方面,随着我国技术水平接近全球技术前沿,获得国外先进技术的难度增大,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干中学”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动能减弱,导致投资减弱及生产效率减弱。
从经济转型的维度来看,在过去2个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期,人均收入的增长和结构变化处于常态。按照世界银行标准,我国已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根据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2008年发布的报告,在二战后全球经济增长长期记录中,仅有13个经济体的GDP保持了30多年的7%及以上的年均增长率。而其中只有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少数几个国家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并成功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13]。像巴西、阿根廷等拉美诸国以及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诸国,在保持了较长时期的快速增长记录后,其制造业并没有实现向产业价值链高端的攀升,而继续锁定低收入阶段的增长引擎,进而造成在阶段性快速增长之后出现增长疲弱,长时间徘徊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在低收入阶段,依靠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有效动员能力和再配置,利用与世界经济接轨,依托贸易和投资等关键环节,可以有效把技术前沿国的技术、管理、经验等与国内生产要素协调起来,促成本国生产率的提高,进而驱动经济高速成长。但是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和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劳动力工资上涨的压力使其无法与低收入国家低工资的禀赋优势竞争,也无法在技术进步和创新能力方面与发达经济体竞争,从而造成经济增长在低水平上徘徊。从更深层面来看,其根源在于没有实现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更多关注消费需求、基于消费需求升级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等关键经济转型。经济发展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发展特征的高度概括,揭示了以上经济转型的内在规律。
二、经济新常态供给侧的主要特征及国际比较
分析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主要特征,既要考虑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路径,也要考虑中国经济局势的演变和阶段性变化,同时也要进行国际比较。
(一)增长趋势性放缓,凸显生产率和增长质量的关键作用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1978—2014年),我国GDP增长率一直保持年均9.8%。即使受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外生冲击,之后(2009—2014年)也达到年均8.8%。但是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率呈现与这30多年高速成长期不同的发展特征。GDP增长率从2010年的10.6%下降到2011年的9.5%、2012年的7.7%和2013年的7.7%,2014年再跌为7.4%。从GDP的季度增长趋势来看,我国已经连续11季度(2012年2季度—2014年4季度)增长率低于8%,这是从1992年开始GDP季度增长统计以来未曾出现过的状况。
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趋势发展,可以从两个方面认识。一是从长期视角看增长率。二战后日本、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在保持了高速增长后都出现了明显的增长放缓过程。新加坡从1961年开始保持了37年的年均8.6%的高速增长,韩国从1963年开始保持了40年的年均8%的高速增长。从极长视角看,公元0—1700年全球产出年均增长率为0.1%,1700—1820年该指标为0.5%,1820—1913年该指标为1.5%,1950—1980年该指标为2.5%,1980—2012年该指标为1.7%。欧洲的年均增长率1950—1970年为3.8%,1980—2012年则为1.8%。由此可见,经济增长的加速和放缓是经济发展中的常态。
二是从潜在增长率的趋势来看。从理论上看,潜在增长率是由资本、劳动和技术等长期因素决定的。如果潜在增长率呈现下降趋势,则经济增长率也存在着类似趋势,也会随之降低。Louis Kuijs认为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在1978—1994年为9.9%,1995—2009年为9.6%,2010—2015年为8.4%,2015—2020年为7.0%[14]。近年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并面临着严重的资源和环境问题,此外,与技术前沿国家的技术差距逐渐缩小,这些因素的多重作用压低了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根据理论依据和国际经验,拉动经济稳态增长的关键举措是结构变动、关注增长质量和提升生产率。
(二)结构变动和服务化
近年来,理论界和政策界都认识到了高投资和出口双轮驱动的增长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在政策驱动框架下,开始将聚焦点从依靠生产要素粗放投入、生产规模的扩大转向生产要素集约使用、提高增长质量和生产效率上。在新常态下,需要把握好总量和增量的关系、潜在增速和实际增速的关系[15]。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11月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所强调的,新常态下经济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的和没有水分的增长,是有效益、有质量的增长。近年来,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些结构性的改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GDP增长放缓的同时,就业总量及其发展局面保持良好态势。这说明中国经济增速回落不是周期性波动的产物。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14年统计公报,2014年城镇净增就业人数为1 070 万;又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2014年中国城镇新增就业1 322万人,同比增加12万人。这说明在中国经济增长率趋缓的状况下也能创造与过去相当的就业局面。
二是外贸增速和顺差大幅度收缩的同时,服务业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这意味着经济再平衡进程取得初步成效,中国经济发生显著结构变动。此外,人口红利逐渐耗竭,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动,劳动力短缺带来工资上升,从而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劳动报酬份额逐渐提升将是中国经济未来很长时期的一种新格局。这有利于提高经济的整体消费购买力,有利于实现以消费者为基础的消费驱动型发展模式,有利于促进服务业的发展。相对而言,服务业所具有的低碳的内在发展特征,作为新的增长领域在新常态下受到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的关注是必然的。
三是在产业方面,随着资源和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以工业特别是制造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发展空间愈发有限。2012年中国第三产业占总产值份额为45.5%,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所占份额。2013年和2014年继续保持这种发展势头,两者占比差距由初始阶段的0.5个百分点提高至2014年的5.6个百分点。其实,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所占份额将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而逐渐下降,第三产业所占份额上升。从各国发展经验来看,这是经济增长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是一种常态。
(三)技术创新愈发重要
迄今为止,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低价格推动着中国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但是,随着中国劳动力供给的放缓,土地、能源和环境约束的加大,以往依靠扭曲土地成本、能源成本和环境成本以及源于存款利率上限和贷款利率下限的资金扭曲等形成的特殊比较优势逐渐消失。从国际经验和经济发展理论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必须转向通过创新提升生产率以支撑经济持续发展的路子上来。
为了加快创新,不仅要从国外引进技术,更重要的是积极开展研究开发活动。2013年中国研发(R&D)支出占GDP比重为2.08%,首次突破2%的发达国家研发支出平均水准。但是与德国2.92%(2012年)、日本3.39%(2011年)、美国2.79%(2012年)、新加坡2.23%(2011年)、韩国4.04%(2011年)的研发支出所占份额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若再加上研发资金的使用效率和创新能力,则我国技术创新的经济绩效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三、经济新常态需求侧的主要特征及国际比较
(一)消费支出渐成经济增长的关键推动力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始终保持高速成长,但是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中断了这一进程。从GDP季度同比增长来看,2008年GDP增速从第3季度的9.0%跌至第4季度的6.8%,2009年第1季度增速再跌至6.1%,尽管后来出台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促进了GDP增速的回升,但中国GDP增长的急剧下降亦折射出中国经济对出口,特别是对发达国家外部需求的过度依赖。对中国经济需求侧的一个共识性的特征是增长主要依赖于投资和国外需求,而投资又主要集中在制造业。
2001—2008年,投资和净出口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58.5%。这个占比数字高于G7国家16%、欧元区30%的同期平均水准,也高于以高投资为主要增长动力的其他亚洲经济体35%的同期水准。
2011年,中国经济需求侧出现了一个显著变化,即: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升为56.5%。这是近10年来首次出现消费支出超过投资对生产总值的贡献。消费支出所占份额回升的态势,折射出了消费支出正在替代投资和出口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关键推动力。
(二)发展进入消费需求升级带动结构变动的关键阶段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中断了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基本面,同时也给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重要的结构性变化:一是国民总储蓄率和国民总消费率到达至关重要的结构性拐点。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国民消费率为50.3%,高于国民总消费率0.3个百分点。二是危机过后农民工收入连续几年保持两位数增长。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劳动报酬随着生产率提高而稳步增长。三是伴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份额不断提高。与此同时,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也呈现多样化特征,更加关注产品质量、差异性。消费支出迈入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需求。四是历史经验表明,每次危机过后,都会出现重大的技术突破和科技成果的大规模商业化,从而支撑人类不断向前发展。处于全球技术前沿的发达国家,正依托新能源和低碳技术的重大技术突破,培育新的增长点和创造新就业。
中国城乡居民在满足衣、食、住、行等基本消费需求后,对医疗保健、文化娱乐等发展型、享受型消费需求的支出能力将逐步释放。根据国际经验,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人类生活方式的多样化,服务业约占全部就业人数70%~80%的份额是发达国家经济运行中的一种常态。在这种经济常态下,医疗和教育所占份额为20%以上,零售、酒店、餐饮和文化娱乐业所占份额为20%,交通运输、会计、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所占份额约为20%,其他服务业所占份额约为10%。2013年中国服务业所占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服务业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经济产出的主要贡献因子,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又一至关重要的特征。
参考文献:
[1]新华社.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强调 深化改革发挥优势创新思路统筹兼顾 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N].人民日报,2014-05-11(01).
[2]金碚.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5(1):5-18.
[3]贾康.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1):4-10.
[4]习近平.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演讲[EB/OL].[2014-11-09].http://news.xinhuanet.com/2014-11/09/c_1113174791_2.htm.
[5]洪银兴.论中高速增长新常态及其支撑常态[J].经济学动态,2014(11):4-7.
[6]汪红驹.防止中美两种“新常态”经济周期错配深度恶化[J].经济学动态,2014(7):4-11.
[7]习近平.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EB/OL].[2014-12-11].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4-12/11/c_1113611795.htm.
[8]EL-ERIAN M.Navigating the new normal in industrial countries[R/OL].[2010-10-10].http://www.imf.org/external/np/speeches/2010/101010.htm.
[9]李杨.提质增效 适应增速新常态[N].人民日报,2014-06-11(10).
[10]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M].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4:39-110.
[11]陈佳贵.工业化蓝皮书: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1995—2010)[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1-60.
[12]王宏昌,林少宫.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讲演集(1978—2007)(修订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38.
[13]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增长报告:可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发展的战略[M].孙芙蓉,译.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8:1-29.
[14]KUIJS L.China through 2020-A macroeconomic scenario[R/OL].[2010-06-18].http://www-wds.worldbank.org/external/default/WDSContentServer/WDSP/IB/2010/06/18/000333037_20100618003219/Rendered/PDF/55104
0WP0P11751um1term1scenario1eng.pdf.
[15]余斌,吴振宇.中国经济新常态与宏观调控政策取向[J].改革,2014(11):17-25.
(责任编辑许若茜)
Main Characteristic of the New Normal of China’s Economy from
the Demand and Supply of the Economy Entity
ZHANG Xiao-bo
(Economics Teaching Research Department, Chongqing Institute of Administrative, Chongqing 400041, China)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when it comes to the new trend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oncept of the most frequently used must belong to the “new normal”. The new normal is the changes of the economic operation rules,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from one state to another state in essence.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 of analysis the main characters of the interpretation is the new normal is the rational analysis of the logic basi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behind the new normal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is article mainly interpreted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new normal and objective necessity of China’s economy from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the coma to catch up with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upply side of economy, the new normal of China’s economy presents a slowing growth trend, the key role of quality and productivity is increasingly highlighted, and the structure change and innovation is increasingly important under the guidance of low carbon growth mod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mand side of economy, consumer spending grows into the key driver of economic growth, and we have steped into the key stage that consumer demand’s upgrade promotes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and optimiza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concept of green growth, and steped into a new stage of virtuous cycle that consumer demand promotes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reates new consumer demand.
Key words:new normal; demand side; supply side;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catch up with and surpas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文章编号:1674-8425(2016)01-0062-06
中图分类号:F120.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4-8425(s).2016.01.010
作者简介:张晓波(1983—),男,贵州毕节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宏观经济分析。
收稿日期:2015-05-12
引用格式:张晓波.从经济体需求方和供给方看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6(1):62-67.
Citation format:ZHANG Xiao-bo.Main Characteristic of the New Normal of China’s Economy from the Demand and Supply of the Economy Entity[J].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2016(1):6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