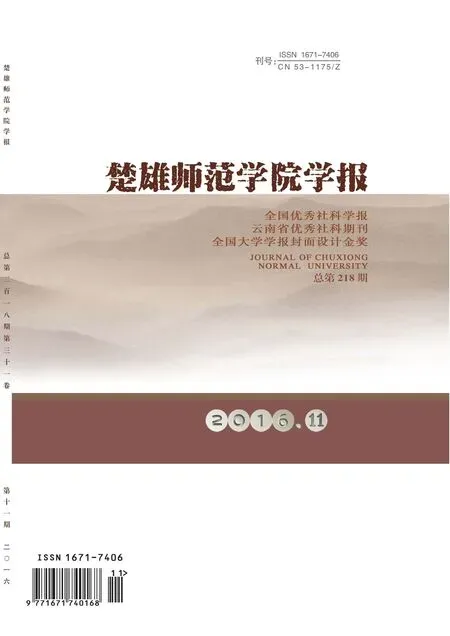王昶《金石萃编》以金石证经史方法述论
2016-03-28龙野
龙 野
王昶《金石萃编》以金石证经史方法述论
龙 野
清代金石学与考据学联系紧密,在乾嘉时期体现得尤为明显。王昶《金石萃编》注重用石经文字及纬书材料来考证校勘板刻儒家经书,用石刻文献补充、纠正史书,碑史互证,体现出以金石材料考证经史的学术观念,代表着清代金石学的主流,是乾嘉考据方法在金石学领域运用的例证。
王昶;《金石萃编》;金石学;考证经史;乾嘉学术
清代学者尚朴学,注重金石文字与经史研究的关系,形成了以金石材料考证经史的共识。这种学术方法首先体现在史学考证上,后来逐步拓展到经学领域。学者们或强调金石之文“其事多与史书相证明,可以阐幽表微,补阙正误”。[1](P77)或指出“金石之学,与经史相表里”;[2](P414)“金石之学,上必本于经,下必考于史”。[3](P658)在这种思潮之下,清代产生了数量众多的金石学著作,影响广泛。王昶编《金石萃编》是其中集大成的著作,体现出以金石材料考证经史的思想,与乾嘉考据学关系紧密。以下尝试对其方法进行梳理,或有助于更完整地认识乾嘉学术的面貌。
一、以金石证经学
(一)石经与板刻经书的校勘
因年代久远、语言文字演变等原因,儒家经书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错讹。因此,较早的石经就颇受学者重视。清初学者顾炎武、朱彝尊、万斯同等均利用石经对板刻儒家经书进行校勘。乾嘉时期,这种方法被更广泛采用,成为金石学、考据学的主流,《金石萃编》中就曾大量采用。如卷一六收《石经残字》六种,王昶有校勘:
《公羊传》昭公二十五年云:“人以为灾。”何休注云:“灾,周埒垣也。今太学辟雍作‘则’字。”即指太学石经而言也。《易·系辞》“洗心”,《经典释文》云:“京、荀、虞、董、张、蜀才作‘先’,石经同。”《诗·淇奥》“绿竹”,《释文》引《韩诗》作“音徒沃切,石经同”。《广韵》上声四十五厚,“斗”字,注云:“《说文》作‘’,有柄,象形。《石经》作‘斗’。”此皆据汉石经而言也。[4](P106)
王昶以《公羊传》、《经典释文》中引及经文与熹平石经相校勘,发现多能相互印证,由此证明《石经残字》保留有儒家经典的早期面貌。因石经刻于东汉,是官方定本,包含了今文经学的资料,有着重要的校勘价值。尽管它只残存少量文字,但对研究汉代经学仍有较大的意义,王昶认为不能因其残缺而不予重视。
又如,《金石萃编》收有《石刻十二经并五经文字九经字样》,王昶撰有《石刻十二经跋》三卷,对唐石经文字与明国子监及毛氏汲古阁所刊“十三经”进行了校勘,同时校以《经典释文》、《说文解字》、《尔雅》、《玉篇》等书所引相关经文,在跋文中一一罗列其文字异同。如《周易·乾卦》:
乾上乾下。……“闲邪存其诚”(郑康成作“以存其诚”)。“君子进德修业”(今石经“脩”作“修”,下“脩辞”“脩业”并同)。“可与几也”(李作“可与言几也”)。“欲及时也,故无咎”(郑作“及咎时,故无咎”)。“圣人作”(马融作“起”)。“穷之灾也”(“之”,郑作“志”)。[5](P395)
王昶先列唐石经《周易·乾卦》经文,并在小注中遍举《说文解字》、嘉庆石经、明代国子监本、毛氏汲古阁本、刘歆父子本、京房、荀爽、董遇、孟喜、马融、郑玄、李鼎祚、王肃等诸本的文字差异,详考其异同。实际上是通校诸本差异,以见其优劣。其他经也仿此校勘。《尚书》后王昶还附录《史记》所采《虞书》、《夏书》、《商书》诸篇文字,以见其文献价值。
又,唐《石刻十二经》中收“御删定礼记月令”,为李林甫注,与《新唐书·艺文志》所载悉合。今传宋椠本《礼记·月令》多用郑玄注,不用玄宗本。王昶梳理了唐玄宗所删、李林甫所注的《礼记·月令》篇与《五经正义》本郑玄注《月令》篇的流传情况,通过文字校勘,考知其与郑玄注的差异,进而推断从五代至南宋时仍流行唐玄宗删定本。这对于了解唐玄宗删改经文、唐代至宋代《月令》的接受状况有着较大的意义,对考察《礼记》篇目的顺序的变化也有价值。
王昶将《石刻十二经》与《经典释文》所引石经之文相校勘,充分意识到了唐《石刻十二经》与后世通行板刻差异的校勘价值:
是刻十二经,以校陆氏《释文》,颇多异同,盖如《易》《书》《诗》《三礼》《三传》,多用《正义》本。《正义》与《释文》已有字句不同之处,故石刻亦然。然《正义》成于唐,自宋以来,绝鲜善本,今世所行,庸有踳驳。惟石刻历久不易,虽经后人凿改一二,而唐时诸经真面尚存,得以考知古本,良可宝也。[5](P393—394)
尽管经部著作的校勘在四部中最为严格精审,但因时间流传久远,记载经典的工具由竹简变为纸笔、雕版,其书写的书体,也经历了蝌蚪文、篆书、籀书、隶书、楷书,其传写过程中难免舛讹。且汉魏间,出现了较多增删甚至伪造经典的情况,尤其是北朝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中国时使用了一些俗字,使经文出现了差异。唐贞观间,孔颖达等奉敕撰《五经正义》,对儒家经典进行了订正,形成了官方定本;后世《易》、《书》、《诗》、《三礼》、《三传》文字多以《正义》本为准,与《经典释文》存在差异。王昶认为《五经正义》自宋以来就绝少善本,沿至清代,文字难免踳驳,唯独石刻文字历久不易,虽偶经后人凿改,但唐代诸经的真面目尚存,比宋以后以木刻翻印的《五经正义》的错误要少,具有较高的校勘价值。
鉴于一些学者如顾炎武等批评唐石经文字讹误的做法,王昶并不赞同。他说:“若夫石经文字既多,卷帙孔富,且镌勒时看书上石之人更代不一,摹刻偶误,或未能免。但当择善而从,不可刻意吹求,亦毋庸曲为回护。而后人磨改凿刻之字,仍复是非参半,至明人补字,则纰缪已极,收藏家往往于装裱时顺文羼入,考古者一时不察,遽认以为原刻,转生异议。昆山顾氏、秀水朱氏正坐此失,最足疑误后来。”[5](P394)他认为石经刻石,卷帙巨大,镌刻时看书上石,非出于一手,摹刻偶误也属正常。并且经人磨改凿刻,明人又有补字,纰缪颇多,收藏家往往在装裱时顺文羼入,顾炎武、朱彝尊等大家皆一时不察,以为是石经原刻的面貌,实际上这并非石经的错误(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已指出这一点)。
王昶认为石经文字可与古书所载的一些经书传注文字相印证,能够纠正明代国子监本、汲古阁《十三经注疏》中注疏部分的舛误,具有重要的价值。他博引《经典释文》及汉魏典籍所载有关儒家经典的“传注”文字有差异者进行校勘辨证,并将其与传世经典如明监本《十三经注疏》及汲古阁所刊诸经注疏,乃至史书、诸子所引传注进行校勘,详列其异同。这实际上是将石刻十二经中传注文字与传世经学注疏文字进行通校。在经学研究上,有时经文与注疏的一字之差,往往会引起阐释上的巨大差异,王昶这种注重石经传注异文的校勘方法,在经学阐释上具有重要意义。后来的一些学者组织校刻儒家经典,集大成者如阮元《十三经注疏》即采用此方法校勘,可能就受到过王昶的影响。
(二)以纬书印证经书
王昶以金石证经学还表现在他充分利用到石刻中的谶纬资料,尤其是用“纬”对经学典籍进行印证。谶纬一词常联称,实际上二者有别。四库馆臣在《易纬坤灵图》提要中指出:“儒者多称谶纬,其实谶自谶,纬自纬,非一类也。……后人连类而讥,非其实也。”[6](P47)在有汉学背景的四库馆臣看来,纬与经相表里,在经学阐释上有其价值,故而反对将谶纬一并排斥的做法,这是对纬书学术价值的一种肯定。
吴派汉学家注重以纬书资料证经,其中以东吴“三惠”最具代表性,其影响波及到浙江一带。刘师培在《南北考证学不同论》中指出:“吴中学派传播越中,于纬书咸加崇信。”[7](P245)比如,惠栋治《易》引纬书,信纳甲、爻辰之说,《易汉学》就参用《周易·乾凿度》等书。王鸣盛引纬书以申郑学,张惠言治《易》宗虞氏之说,孙星衍撰《岁阴岁阳考》等文杂用纬书,沈涛以五纬配五经,且引纬书证经等等,皆是重视纬书的例子。但是,将纬书资料进行条列疏释以明确标举其解经价值的是王昶。钱穆在指出苏州学派多信纬术时,强调“王昶《孔庙礼器碑跋》谓纬书可以证经”,[8](P273)这是对王昶“以纬书证经”理念的归纳。
王昶在《韩敕造孔庙礼器碑》跋文中大量引用了经史、碑文中的“谶纬”材料,认为用纬书去参验六经,能够广闻见。并举《史记》、《汉书》、孟喜注《易》、贾逵注《左传》、赵歧注《孟子》、许慎《说文解字》、郑玄注《周礼》、《毛诗》皆大量使用纬书的例子,证明谶纬不被大儒所弃;又博引汉以来的碑碣所载纬书资料的百余条例子,以印证汉代社会颇重“内学”、“谶辞烦于汉末”的说法,证明纬书材料对于考证经书的重要性。同时,王昶指出谶纬之学衰亡在于宋儒的排斥,并对此结果表示惋惜:
盖自汉以来,博古之士多喜习之,即有不能深信者,亦未竟斥为异端。自欧阳氏有《论九经请删除〈正义〉中谶纬札子》,而魏了翁作《九经正[要]义》,尽削去之。自是厥后,学者同声附和,而纬书遂致散佚,仅有存者,良可叹惜也。[9](P609)
唐代学者在注释群经《正义》时,尚保留、遵信谶纬,《艺文类聚》等征引纬书材料也屡见不鲜。但自宋代欧阳修、魏了翁开始,在经书的注释中大量删除谶纬之言,后来的学者同声附和,以至纬书散佚,仅有少量条目散存于各书中。这导致了后来儒家经学阐释上重要材料的缺失。
王昶认为纬书所载资料与经书多有符合,对于阐释经书有重要的补充作用,不应对纬书资料存有偏见。他说:“汉时碑刻多用谶纬成文,论金石者概讥其谬,不知纬与经原无大异,经所不尽,政当以纬补之。若以纬书荒渺,则六经之言,其似纬书所云,曷可胜纪?将尽删之,可乎?”[9](P612)这实际上是肯定了纬书在阐释、考证经书上的价值。王昶《示长沙弟子唐业敬》云:“《公羊》、《谷梁》间有别解,何休承之,亦皆出自孔门弟子,义深文奥,墙仞难窥,不可以偶涉谶纬,辄仿陋儒指斥。”[3](P659)可见他在接受儒家经典时对谶纬并不排斥,与其重视金石谶纬材料的做法相一致。
这种重视纬书的治学理念,在王昶的后辈学人中得到了延续。如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孙氏周易集解》在治学思路上就与王昶颇为接近。在杭州诂经精舍求学的徐养原、汪继培、周治平、金鹗、李富孙等均写过《纬侯不起于哀平辨》,[10](P346—353)可能就是山长王昶、孙星衍命题。这表明王昶等对纬书与经书关系的看法得到了第二代、第三代汉学家的继承,意义深远——这实际上是在学术研究方法上对宋儒过分歧视与排斥谶纬的一种反驳。他们将纬书视为一种历史材料,相对客观地加以分析,对清代经学的阐释、经学研究观念均产生了影响。
当然,在汉学家重视以纬书材料证经的风气下,姚鼐、方东树等人对此提出批评。方氏的《汉学商兑》就批评王昶表彰谶纬“皆驳杂之说,无一语一事足明圣道政教之用,足资人事身心之益”。[11]方东树在清朝经世致用思潮渐成主流、汉学流弊日显的背景下提出这样的批评,未必能完全领会到王昶等汉学家重视以纬书考证经学的用意。
二、以金石考证史学
《金石萃编》在史学上的价值已有学者关注到,如唐长孺利用《金石萃编》卷三〇《神静寺刹前铭敬史君之碑》撰有《跋敬史君碑》一文,资以考论魏晋南北朝士族的构成、兴衰、演变等。[12](P110-118)高敏利用此碑文对东魏、北齐的中央、地方僧官制度进行研究皆是代表。[13](P14-17)以金石考证史学,是乾嘉考据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王昶对此颇为留意。以下论述《金石萃编》以金石考证史学的方法与成就。
(一)以金石补史书之阙
古代史书限于具体的编纂体例,在详略取舍上有其标准,书传主生平履历时摘要着笔,子孙所附者也需有较大影响,不可能一一详述。而碑文则一般会详列墓主生平履历、子孙情况等,往往可与史书相辅而成,多能补史书所略。
《金石萃编》注重以金石材料补史书之阙。如卷八四《裴道安墓志》王昶跋:“此碑书者族叔礼部员外郎裴朏,两《唐书》无传。《宰相世系表》:洗马。裴有裴朏,重晈之子,官礼部郎中,当即其人。碑叙裴氏先世已详《裴光庭碑》,其述稹事,惟《新唐书》附《裴行俭传》,所载甚略(旧史无传)。但云光廷(旧史作‘庭’)子稹以荫仕,累迁起居郎,后授祠部员外郎,卒。碑则云开元初,举孝廉,授左千牛备身,转太子通事舍人,补太常寺主簿,迁京兆府司录。丁太师忧,服除,拜起居郎,迁尚书祠部郎。视史较详也。”[14](P557)就是注意到了碑文所载裴稹历官等比史书记载更详,可以补充正史的不足。
王昶在《金石萃编》卷二九《司马昞墓志铭》跋文中指出《魏书·司马叔璠传》不载景和袭爵,也未载景和之子,都是正史的疏漏。而参看《司马昞墓志铭》及《司马景和妻墓志铭》,可知其所袭爵位是“宜阳子”,这表明墓志“可以补史之疏”。[4](P326)又卷一二《高阳令杨著碑》后王昶跋云:“石经立学,《水经注》以为光和六年,《后汉书·灵帝纪》《蔡邕传》并以为熹平四年,释云:‘盖诸儒受诏在熹平,而碑成则在光和。’今此碑年月已泐,然著卒与沛相同时,定为建宁元年无疑。则所谓受诏定经者,乃桓帝时事,尚在蔡邕、堂溪典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之前,可补范史所阙。”[4](P31)石经立学的时间,《水经注》与《后汉书》记载有异,王昶根据杨著卒与沛相同时,定碑所刻时间为建宁元年(168)。又考证受诏定经是汉桓帝时事,在蔡邕、堂溪典奏请正定六经之前。这能够补范晔《后汉书》记载的不足。这样的例子尚多,如《段志玄碑》、《令狐德棻碑》中所载均可以补《旧唐书》、《新唐书》的疏漏等。
(二)以金石纠史传之误
《金石萃编》注重以金石材料纠史传之误。如卷一五《太尉杨震碑》后有王昶跋:“碑称‘长子牧,富波侯相’,而《世系表》称‘牧,荆州刺史、富波侯’。考杨氏二侯:太尉孙赐临,晋侯;曾孙众先,封宜阳侯,更封蓩亭,未闻侯富波者。又考王霸以建武二年封富波侯,十三年改封向侯,而《郡国志》称富波侯。国永元中复,则牧实相非侯,《新唐书》误也。其称牧荆州刺史,殆亦承传中‘高舒至荆州刺史’之文,皆当以碑为正。”[4](P70—71)《太尉杨震碑》中明确记载其长子“牧,富波侯相”,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牧,荆州刺史、富波侯”。大概是《新唐书》中富波侯后脱漏了“相”字,王昶据碑文纠正了《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错误(按:范晔《后汉书》卷五四《杨震传》中明确记载“震五子。长子牧,富波相”,王昶未引以为据)。
又如卷二三《上尊号碑》,王昶跋中指出碑文记载的黄初年间诸臣的历官与封爵均与史传所载有异,碑文记载更详细,可补正史。同时,碑文还可纠正史之误:“惟《公孙瓒传》书鲜于辅虎牙将军,阎柔渡辽将军;《夏侯尚传》书迁征南将军、领荆州刺史、假节都督南方诸军事;《常林传》书迁少府;《许褚传》书迁武卫将军;《曹休传》书迁征东将军、领扬州刺史,进封安阳乡侯,并在文帝践阼后,是则陈寿纪事之误,读史者所宜知也。”[4](P221—222)王昶认为黄初诸臣封爵的时间当是在魏文帝称帝后,陈寿的记载是错误的。
此外,如《温彦博碑》记载罗艺授予温彦博的官职为“通□舍人”,而《旧唐书·温大雅传》附载温彦博的官职中有“中书舍人”。据《隋书·百官志》,隋时尚未设中书舍人,因此王昶认为《温彦博碑》碑文中“通□舍人”所泐之字应是“事”字,这就纠正了《旧唐书》记载温彦博官职的错误。又《贞和上塔铭》中记载李皓的官职为吏部尚书,而《旧唐书》本传载其任工部、兵部尚书,并未记载其任吏部尚书。《新唐书》载其以奉使称职,转吏部尚书,与塔铭中内容相符。王昶据碑文及《新唐书》,认为《旧唐书》记载有误。这也是以碑正史的例子。
(三)“以碑校史”与“碑史互证”
《金石萃编》注重碑文与史书互校互证。如卷三八《赵芬碑》王昶跋文据《魏书·赵逸传》、《北史》与碑文的差异,指出宾育是赵煦的字,而非名。并认为史书称赵融为赵逸十世祖是误载,应据碑文纠正为七世祖,就是“以碑校史”的例子。王昶跋云:
(芬)除蒲州刺史,史不详何年,碑则云开皇五年。史但云归第后数年卒,碑于‘卒’字泐,不能辨。参考碑史,则当在开皇五年以后之数年,约略在十年左右也。以碑校史,彼此详略,皆可以互证矣。[4](P467)
王昶据碑文所载与《隋书》之详略差异,考知赵芬于开皇五年(585)除蒲州刺史,约卒于开皇十年(590)左右。这显示出碑文可以用于校勘正史,正史所载也可以纠正、补充碑文缺泐。“以碑校史,彼此详略,皆可以互证”的方法为乾嘉治史者所重,实际上这对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也有影响。
在一些跋文中,王昶将碑文与史传所载异同详列,如《唐俭碑》原文约有三千三百字,因残泐,只存一千二百余字。钱大昕已有跋文,据碑文以考证《宰相世系表》载唐俭之父唐羲封“安富公”等错误。王昶在此基础上,以残存碑文为底本,取《旧唐书》、《新唐书》中相关传记之文详列之,以互相参证,使读史者能更多地使用到碑文中的信息,这也可以视为碑史互校互补的例子。
此外,王昶还重视对金石中政治史、制度史资料的考证与梳理。如《郎官石柱题名考》先列官名,将其设立时间、人员、品秩、所经负责掌管之事等条列于下,并考证官员的生平履历。“其姓名之在新旧两《唐书》有传者,考其历官与碑合否,又参以唐书《宰相世系表》及《全唐诗》小传,补两书所未备”。[5](P632)王昶以两《唐书》、《宰相世系表》及《全唐诗》小传等对郎官的生平、历官等进行考证,对其有异者进行揭示,碑史互校,以备后来人详考。这对唐代职官志研究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唐宋诸碑系衔并食邑实封》则是对唐宋诸碑刻的标题及撰人、书人、篆额人中官位显赫者的系衔、食邑实封与史书所载制度并不相符现象的具体考察。如系衔之例有“功臣”、“检校”、“散官”、“职事官”、“勋官”、“封爵”、“鱼袋”、“食邑实封”等,王昶详取有关正史职官志、政书等记载此职衔设立的时间、何官可称该衔等材料进行排比,实际上是对唐宋官制中高官职衔较为详细的梳理。如“检校”下,王昶引《宋史·职官志》、《文献通考》、《朱子语录》等关于检校设立的记载后,复引碑传所载论证“检校之缘起”源于隋朝, “其用以入衔,则始于唐初”, “唐之检校不尽加之于尊官”, “检校二字,宋南渡后尚用以入衔”,[4](P522—523)对检校的起源、演变以及南宋时仍以入衔的梳理与考证,援据精博,对于研究唐宋官制均有意义。后来,汪士铎在《历代官制特进诸吏检校行守试判知答龚伽生》[15]一文中就加以引用。其他关于“散官”、“食邑实封”等的考证也与此相似。《金石萃编》中关于此类考证唐宋官制设立及其流变问题的按语,淹贯经籍,考证精当,实为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王昶注意到碑刻所载诸人系衔、食邑实封与正史职官志的规定有出入,虽未找出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但他有意识地进行资料的整理汇编,对于研究唐宋政治制度史颇有助益。
此外,王昶撰有《元祐党籍碑姓名考》、《元祐党籍碑本末》,对元祐党籍碑的始末进行了较详细的梳理,对研究元祐党禁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样的例子还有一些,如《碑文避讳字》对历代碑刻中避讳例的揭示与归纳;《昭陵陪葬诸碑总考》对唐代陪葬制度的详细考察皆是。这种通过校勘异同发现问题的方法,是王昶以金石考证经史的实践,“皆本本原原,极为赅洽,为考据之渊薮”,[16](P1059)获得了后人赞许。
综上所述,本文从以石经考证木刻儒家经籍、以石刻中谶纬材料考证经学、以金石文字纠补正史、碑史互证等方面探讨了《金石萃编》在经史考据中的意义。这种以金石考证经史的学术思想与方法对后来的金石学、考据学走向,乃至中国近代的史学研究方法均产生了巨大影响。对王昶《金石萃编》以金石考证经史方法的梳理,有助于我们更完整地认识乾嘉学术的面貌。
[1](清)顾炎武.亭林诗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2](清)钱大昕.潜研堂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3](清)王昶.春融堂集[M].清代诗文集汇编(358)[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4](清)王昶.金石萃编[M].续修四库全书(第887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5](清)王昶.金石萃编[M].续修四库全书(第889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6](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北京:中华书局,1965.
[7]刘师培著,万仕国点校.国学发微(外五种)[M].扬州:广陵书社,2013.
[8]钱穆.国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9](清)王昶.金石萃编[M].续修四库全书(第886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0](清)阮元.诂经精舍文集[M].丛书集成初编[C].北京:中华书局,1985.
[11](清)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中)[M].清光绪十一年(1885)刻本.
[12]唐长孺.山居存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3]高敏.从《金石萃编》卷30《敬史君碑》看东魏、北齐的僧官制度[J].南都学坛,2001,(3).
[14](清)王昶.金石萃编[M].续修四库全书(第888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5](清)汪士铎.汪梅村先生集(卷三)[M].清光绪七年(1881)刻本.
[16](清)李慈铭撰,由云龙辑.越缦堂读书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3.
(责任编辑 徐芸华)
(Schoolof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s,NanchangUniversity,Nanchang, 330031,JiangxiProvince)
(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1)
On the Method of Using Chinese Epigraphy to Verify Confucian Classics and Historiography inJinShiCuiBian
LONG Ye
In Qing Dynasty, the Epigraphy is close connected to the Textology, such tendency is extremely obvious in Qianjia epoch. Wang Chang’sJinShiCuiBianpays attention to use the characters in the classics engraved on stones and materials from the latitude book (纬书) to examine and collate the Confucian classics, to use the literature engraved on stones to replenish and rectify the official history. His method of employing the stone tablet and official history to verify each other reflects the academic idea that using the materials from bronze and stone to research the classic historical texts, showing the main stream in Qing Dynasty, which is an application that uses the Qianjia Textology in the epigraphy study.
Wang Chang;JinShiCuiBian;Epigraphy;Verifying the classic historical texts;Qianjia Academy
2016年度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青年博士基金项目“王昶与乾嘉文学演变研究”,项目编号:16BJ39。
2016 - 09 - 27
龙 野(1982―),男,文学博士,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清代学术史。
K877.43
A
1671 - 7406(2016)11 - 0028 - 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