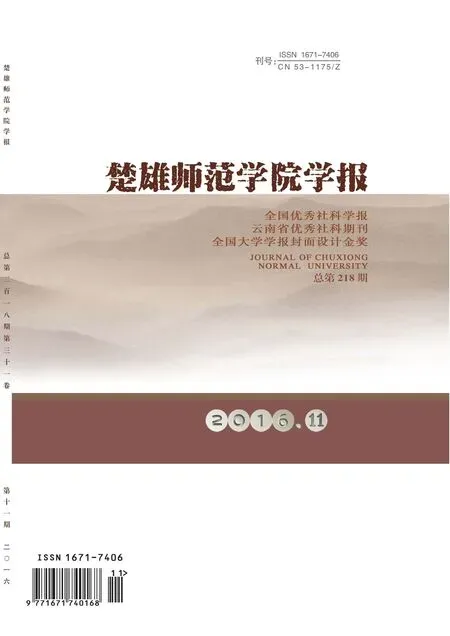20世纪80年代末诗歌“黑夜”意象群的镜像解读
2016-03-28周俊锋
周俊锋
20世纪80年代末诗歌“黑夜”意象群的镜像解读
周俊锋
20世纪80年代末,以北岛、顾城、海子、戈麦等人为代表在诗歌中对“黑夜”意象群的集中关注和表达,既能够凸显探索诗歌理想的紧张感,也隐现着诗人把握社会现实复杂关系的思考能力与认识角度。围绕“黑夜”意象群的象征性、否定性、隐微性写作,80年代末汉语诗歌将审视自我与反思时代紧密联系起来,“黑夜”的抒写成为一种自我认识的手段。以“黑夜”意象群构造的特殊情境作为考察对象,阐释“黑夜”艺术母题的内涵,从诗歌技艺角度分析呈现“黑夜”作为精神书写的矛盾体所具有的丰富复杂性。
“黑夜”;意象群;诗歌结构;镜像;自我
诗歌是技术化的产物。诗人在诗歌创作时的意象选择,因为复杂心理因素的参与,使得某一类诗歌母题得以强化与定型。闻一多在《诗与批评》一文谈道:“一篇诗作是以如何残忍的方式去征服一个读者。诗篇先以美的颜面去迷惑一个读者,叫他沉迷于字面、音韵、旋律,叫他为这些奉献了自己,然而又以诗人的偏见深深烙印在读者的灵魂与感情上。”[1](P223)诗人是乐于行使自己的“偏见”的,这种“偏见”植根于特定的时代文化背景,以及诗人自身业已形成的思维观念与知识结构。诗人在进行诗歌意象选择时,将个体的价值观念结合白描、隐喻、象征、通感、戏剧化等意象加工手法,强化瞬时感受与精神的张力,融入进诗歌作品;反过来,诗歌意象既反映社会现实,同时又折射诗人的性格形象和精神主张,这就为重新解读20世纪80年代末汉语诗歌“黑夜”意象群的内涵提供重要依据。
一、“黑夜”意象原型与诗歌镜像游戏
汉语诗歌的书写技艺发展至20世纪80年代渐已成熟,诗歌意象世界与作者精神心理的契合度越来越高,诗歌艺术表达上形成更具普遍性的原型意象和艺术模型。“窗户”、“镜子”、“骨骼”、“睡梦”、“旅途”、“黑夜”、“迷宫”、“时间”、“枪箭”、“影子”、“墓碑”等诗歌母题,在意象空间结构下诗人的心理活动得到外化,母题性意象可以作为“客观对应物”成为诗人自我精神世界的映射。吴晓东谈诗歌母题时强调,“可以通过艺术母题的方式考察一个派别或者群体的共同体特征,考察他们之间具有共通性的艺术形态、文学思维乃至价值体系。”[2](P3)重新切入一些在意象和结构上较为稳定的诗歌母题,能够直截揭示特定时代文化、一代诗人内心深处的精神冲突、心理焦虑、理想激情。诗歌在精神探索与自我认识的道路上,现实人生与自我心灵的矛盾无处不在,以“黑夜”为代表的诗歌意象群,从个体性的书写行为上升为现代汉语诗歌创作者共同分享的公共意象,“黑夜”原型能够承载更为复杂的精神内容。
“黑夜”意象群表面上呈现的是否定性范畴,但却内在地赋予肯定性的积极意义。诗歌意象世界与社会人生现实是一组镜子的互照,镜子中的“自我”与镜像相互叠加与映射,这一镜像游戏在诗歌技艺与文字表达过程中有着光怪陆离的呈现。诗歌意象表达是象征的艺术,镜像世界中关于现实与自我的“真实反映”是诗人们对现实存在的抽象提取,围绕“黑夜”意象群的写作具有象征性、否定性、隐微性特征。象征性植根于现阶段汉语诗歌的技艺发展水平,隐微性则与整体时代文化的氛围息息相关,否定性则强调构建二元对立的冲突来呈现复杂深刻的精神内涵。弗里德里希在《现代诗歌结构》一书中重点分析了否定性范畴,如“碎片式的、混乱的、图像的单纯堆积、暗夜、聪明的简略涂画、摇摆不定的迷梦、颤抖的交织物”[3](P7)等等,指出这类否定性范畴的内涵不是用来贬损指责,而是用以描述和定义。“黑夜”意象群呈现为一种异质表达和抵抗书写,反思与理性成为思想认识的利器,这样一种书写的“偏见”最终发展为共识性的诗艺追求。
诗歌创作是一种语言的镜像游戏。从诗歌创作心理或诗歌接受角度看,诗人反抗性的“偏见”客观存在并且衍生至诗歌的意象结构体系。诗歌对现实的关注表达,不只停留在表层上朦胧暧昧的模糊介入,而是时刻保持警惕性与危机感,以“黑夜”为代表的语言符号传递着诗人对政治文化语境的独立思考。诗歌的意象体系是对诗歌理想的一种想象性建构,既要剥离与现实痕迹相勾连的生搬硬套,又要放弃简单意义上的猜测臆想。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末汉语抒情诗歌中对“黑夜”的集体性书写,享有一种共通的历史氛围与知识文化背景,为诗歌表达提供了情绪饱满的抒情场域,这一公共场域同时像巨大的幕布遮蔽了特殊历史时期的思想纷争和价值混乱。“黑夜”意象原型恰恰指向严峻沉郁、充满危机的公共场域,成为镜像阶段下想象性思维的起点。“黑夜”意象群的总体特质是一种理性自觉的文化反思,“黑夜”意象成为北岛、顾城、海子、戈麦等人用诗歌打开社会历史内容的一个隐蔽的切口,诗人的历史主体性与诗歌的文本审美性得到内在的融合。
诗人历史主体性的获得,随着自我认识程度的不断加深而日益强化,诗歌的文本结构充分呈现诗人对自我认识的努力。拉康在《助成“我”的功能形成的镜子阶段》谈及猴子一旦明了镜子形象的空洞就中止了“辨认”,而孩子“要在玩耍中证明镜中形象的种种动作与反映的环境的关系以及这复杂潜象与它重现的现实的关系,也就是说与他的身体,与其他人,甚至于周围物件的关系。”[4](P90)对于婴儿阶段,孩子兴奋地将镜中影像归于自己,在拉康看来是一种在典型情境中表现的象征性模式。当“语言”代替“镜子”,这种认知模式延续并贯穿于个体生命的一生,充满着“你即如此”的欣喜若狂,现实世界和自我本身的奥秘得以部分显现,“认识自我”的价值追求得到部分实现。20世纪80年代末,北岛、顾城、海子、骆一禾、戈麦等人的诗歌作品中“黑夜”意象群的反复使用,理性反思成为思想的利器,“自我认识”从镜子阶段的误认发展而成为一种主体自觉,充分显露出诗人对历史时代命运与自我主体价值的思考与关切。
二、书写范式:“黑夜”作为一种自我认识的手段
“黑夜”书写成为文学表达的理想范式,突出原因在于“黑夜”意象自身具备着内涵丰富的隐喻和象征意义,因此使诗歌语言的表现力有着更为丰富的可能性。拉康提出“回到弗洛伊德”的口号实则是给人以假象,力求对弗洛伊德学说进行新的阐释。从婴幼儿开始,人们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开始于对自我形象的迷恋,也即镜中影像的认同,并以此开始从镜中的自我向社会中的自我过渡,从婴儿时代开始构建的想象性“自我”得到不断丰富与完整。实际上,这也成为20世纪80年代末汉语诗歌“黑夜”意象群隐喻和象征意义的生成方式。“黑夜”提供一面认识自我的镜子,个体第一次从镜中影像获得心理上的认同,精神探索的旅程便依次展开。考察80年代末汉语诗歌,诗人的主体性姿态是异常孤寂而桀骜的形象,力图构建更具有完整性和想象性的“自我”。
“黑夜”书写作为一种自我认识的手段,首先体现在对自我意识的唤醒,重新认识价值和评判价值。婴儿首次在镜子中注意到自己,“自我”得到辨认,在与他人、与社会的相互认同过程中不断加深自我辨识,加之社会话语的习得以及语言的加入,进一步深化“我之所以是我”的主体性功能建构。拉康延用弗洛伊德“理想我”的概念,有关“自我”的不断习得这一途径的认识,拉康认为:“重要的是这个形式将自我的动因于社会规定之前就置在一条虚构的途径上,而这条途径再也不会为耽搁的个人而退缩……不管在解决我和其现实的不谐和时的辩证问题的成功程度如何。”[4](P91)镜像世界的认知模式客观存在一定的虚构性,更重要的是从一开始,“自我”不断习得的认知方式被“置在一条虚构的途径上”,因此注定认知的虚构性结果。自我认同是一种想像性投射,“自我是在主体与自己的身体之间所建立的想像性关系之上形成的……作为异化的镜像中的整体性和完整性实际上是无法获得、实现不了的理想。”[5](P25)伪现实的镜像、伪自我的认同,最终加剧误认的扭曲、变形、失真,导致幻象与异化的结局。诗人的诗歌创作,同样是一种文化体认道路上检视自我、获得自我认同的艰难旅途。主体在习得语言以后,语言逐渐代替镜子成为认识工具,客观上改变了前期镜像阶段主客不分的模糊认知状态,进而向整体性、完整性的自我建构更进一步,这恰恰是诗歌认识自我的功能所在。
“黑夜”意象的书写,作为诗人的一种自我认识的方法,首先呈现的是复杂历史境遇下人的历史主体性。人是通过某种类似于“自我”的形象,比如镜子中的影像,产生自我认同的功能,而镜像的复杂性使得主体重新辨识“真相”的难度愈来愈大。“黑夜”首先提供一种特定的公共场域,并呈现不同人群对于时代社会的思考判断与价值观念,自我的概念因此变得明朗化,个体进而形成自我,并且建立“我之为我”的主体性。“黑夜”成为一面自我观照的镜子,在明暗光线的倏忽之间辨认主体的存在。按诗人王家新的说法,北岛显示出一种“逆拉康式”的主体建构,“拉康式的主体的生成过程是从想象界进入象征界进而进入到现实界的过程,而北岛呈现的是一个相反的过程,即从现实界回到象征界又回到想象界,回到拉康所谓的镜像阶段的过程。”[6](P285)而事实上,诗人在诗歌创作中主体的生成方式是常规意义上的镜像阶段的再发展,而非幻象的误认。象征的参与使得镜像主体的辨识难度加大,象征的游移使得把握主体建构的方式愈加变得不可能,因此诗歌“主体性”最终呈现出来的面貌往往杂糅多副面孔,具有复义朦胧的特点。
自我认识还包含着对自身所处时代的认知,北岛、顾城、海子、骆一禾、戈麦等诗人的诗歌作品中对特定历史时期的权利话语有着清醒的思考认识,“黑夜”意象群的反复使用,焦灼、忧虑、冲突凸显出复杂历史境遇下主体性建构的艰难。如果剥离时代,只通过诗歌作品获取对于诗人主体“自我”的认知,在某种意义上是虚假的镜像,是一种“伪自我”。通过“黑夜”意象结构来反观主体性,“语言作为代替了镜子的他者使主体性完全地建立了起来,从而克服了前期镜子阶段主客不分的混沌状态。”[7](P96)“我是他者”,语言既构成了人的主体性,同时客观上限制着思想的表达方式,通过与他者的认同过程中的辩证关系,从而确证“自我”的客观化。20世纪80年代末汉语诗歌创作深受时代历史语境的影响,北岛、顾城、海子、骆一禾、戈麦这一代诗人热衷于历史文化的反思,更加敏感于时代气息的脉搏,“黑夜”书写最适宜这一精神主题的深入。
三、“黑夜”情境:现实与自我的精神裂隙和博弈
幼儿时期的镜像阶段,人的“自我”形成的第一步是建立在平面上的一个虚像;当平面镜像开始走向立体,走向更为复杂的社会历史情境之中,镜子里的影像重叠交错,使得镜像世界更加错综复杂,对“自我”的认知因此带有朦胧性、偶然性。而这恰恰符合“黑夜”的情境,也即在面对现实与自我的精神裂隙和博弈时,不可能的境遇孕育着无限的可能。北岛、顾城、海子、戈麦的诗歌创作,在特定历史时期坚持追寻“自我”与诗歌理想,客观上形成一种对外部世界的“疏离”。自我是他者的疏离,“即‘我’在成为自己本身之际认同的对手其实并非自己,而是他者,我为了成为真正的自己而必须舍弃自己本身,穿上他者的衣装。”[8](P46)这种“疏离”姿态有着诸多变化,特别是以沉默对峙、怀疑反思、趋避逃离等为代表,力求填补现实与理想二者的裂隙,来构成80年代末汉语诗歌“黑暗”意象群的感情倾向和思想深度。
作为黑夜之中的主体,“自我”必然是无所依傍的。以北岛诗作《黑色地图》为例,“寒鸦终于拼凑成/ 夜:黑色地图/ 我回来了——归途/ 总是比迷途长/ 长于一生/ 父亲生命之火如豆/ 我是他的回声”。[9](P305)个体在重走父辈的道路时不断追寻自我,“黑色地图”成为认识自我、体验社会人生的象征符号。“归途”所寻觅的祖国、故乡、母语、父亲,是以夜幕下的“回声”而存在的,正因为如此,“归途”成为夜路,充满艰辛与磨难。北岛诗歌着意书写“黑夜”“镜子”“影子”,构成精神内涵丰富的“黑夜”意象群,抒情主体多为孤独、强力的精神漫游者,穷其一生追寻灵魂的栖居地。再例如:“即使明天早上/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 让我交出青春、自由和笔/ 我也决不会交出这个夜晚”(《雨夜》);“亿万个辉煌的太阳/ 呈现在打碎的镜子上”(《太阳城札记》);“一个来自过去的陌生人/ 从镜子里指责你”(《不对称》);“尽管影子和影子/ 曾在路上叠在一起/ 象一个孤零零的逃犯”(《明天,不》)……同样地,这类表达与熟悉度较高的《回答》《宣告》《结局或开始》等诗篇一样,北岛诗歌中的“我”“太阳”“敌人”“陌生人”是主体变幻的复杂镜像,与诗人追寻的自我认同、价值理想相互纠缠,“黑夜”情境成为自我与现实博弈的标志性符号。
“黑夜”情境成为一代人的最初遭遇和生命底色。“童话诗人”顾城,较为被读者熟知的是其22岁作于1979年的《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10](P26)从顾城整体的诗歌创作历程以及诗歌追求来看,童话王国、完美主义、孩童视角共同编织成诗人的诗歌理想。顾城诗歌中的“黑夜”有着泛化意义,区别于北岛和海子的诗歌类型,“黑夜”意象群不是针对一种现实人生的映射,而是一种知识背景和生存状态,对精神内在而言,“黑夜”是一种“他者”的存在。作为他者,“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黑色”是由“黑夜”赋予的无可辩驳的原色,而个体和眼睛所能观感的世界是外在的,“自我”的价值层面始终无法洞悉。黑夜拒斥光明的同时,也引领诗歌精神探询的方向。当主体真正处于开放敞亮的“光明”背景之下,才能够逃离虚伪的镜像,逃离“他者”最初强加赋予的自我认识。
而“麦地诗人”海子则延用“黑夜”意象群的表达,历史性与文化内涵更为丰富深刻,与顾城诗歌中的浪漫性和理想性有共通之外,更加凸显庄重与肃穆。因为海子诗歌中“黑夜”意象群侧重关注的是集体性的缺失状态,着力传达的是对生命状态和生活理想的痛苦质询,例如“我今夜难以入睡是因为我这双黑过黑夜的翅膀”(《黑翅膀》);“黑夜,你就是这巨大的歌唱的车辆/ 围住了中间/ 说话的火”(《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火回到火 黑夜回到黑夜 永恒回到永恒/ 黑夜从大地上升起 遮住了天空”(《献诗》)等。考察诗歌文本不难发现海子笔下的“野花”(《无名的野花》)、“鸽子”(《野鸽子》)、“酒杯”(《酒杯》)等无不以“黑色”示人,被赋予凝重与孤寂的感情基调。回到“黑夜”本身,也即阐明抒情主人公的精神指向,审视自我与反思时代在“黑夜”极端情境下成为可能。海子写“我何时成了这一朵/ 无名的野花”和“野鸽子是我的姓名/ 黑夜颜色的奥秘之鸟/ 我们相逢于一场大火”,[11](P187)诗歌主体的“自我”形象与现实中的自我被搁置于一种折射、共鸣、区隔而又相互挣扎分裂的境遇,乃至否定和毁灭的精神状态。对比海子逝前(1989年1―3月)写作的给“黑夜”/“黑夜的女儿”的献诗,其感情内核高度一致,“黑夜”情境与集体性的民族自我认同联结在一起,诗歌镜像愈是繁杂玄奥,穿透虚假和遮蔽的镜像世界而获取的自我认识才更加接近价值与真理。
现实与自我的紧张性关系,成为诗人戈麦重点思考和表达的题旨,戈麦诗歌呈现出极致的分裂意识和精神强度。蓝星诗库出版的《戈麦的诗》全集收录戈麦诗歌200首(不含轶诗10首),戈麦对“黑夜”意象群进行描写刻画的诗歌有近50首,较有代表性的是《风烛》和《献给黄昏的星》。以后者为例,“黄昏,是天空中唯一的发光体/ 星,是黑夜的女儿苦闷的床单/ 我,是我一生中无边的黑暗”。[12](P116)诗人将“黄昏的星”作为“这个世界,最后的一件事情”,高度抽象化的黑暗意象成为辽阔时空下对抗精神荒芜的唯一武器。诗歌用“艰难的时刻”“最后的时刻”重复强调精神探索与认识自我的艰难性,星星成为荒芜境遇仅剩的一粒种子,希望渺茫而孤寂无边。“黑夜”意象群的表达,试图将静止的自然意象转换成为普遍性的公共场域,在精神自剖和审视的道路上,“唯一的”“无边的黑暗”则成为人们共同的心理遭遇。“黑夜”书写,切入并放大现实与自我的精神裂隙,但同时以更加严苛、决绝的方式重新进行着历史主体性的建构,确证自我的存在意义。以北岛、顾城、海子、戈麦为代表的80年代末诗歌,将“黑夜”意象群的精神强度和诗歌张力发挥到极致。
四、明与暗的对峙:诗歌理想的困厄和出路
“黑夜”意象群作为否定性范畴,背后传递的则是价值探索层面肯定性的意义。现实与自我的裂隙,使“黑夜”意象群的诗歌表达更加青睐于象征性、否定性、隐微性书写,集中强调诗歌的情感张力和思想深度。黑夜与星光的并置,在20世纪80年代末汉语诗歌“黑暗”意象群书写中成为稳定的表达范式,通过明与暗的对峙来突出对诗歌精神探索的坚持以及对诗歌价值理想的守望。而事实上,现实人生则往往为诗歌精神探索道路设置多重阻隔,诗人对理想、价值、自由、爱情的追寻处于焦灼、挣扎、矛盾、分裂之中,“黑夜”意象群的诗歌写作范式因此得到固化。
“黑夜”为代表的诗歌意象体系,一方面积极探询获取自我认同的途径,同时也警惕着异化的危险。认同和异化是密切相关的,从一开始镜中影像,在零碎片段中形成了对自我身份的整体性认知,异化已经开始悄然发生,并且成人镜像阶段遭遇的他者影像加剧了异化中的认同。张一兵谈拉康镜像理论的实质时说:“从狭小的镜子影射开始,伪自我在场于外在于我的虚假镜像格式塔,接着,可怜的镜像自我在众人的面容之镜和非言传的意会行为之镜中滑入了自我异化的深渊。”[13](P153)因此想象性“自我”便渐渐从想象域过渡至象征域之中。更应该注意到,当镜像期趋于结束时,镜像转换为一面语言媒介构成的巨大的镜子,人、事、物在这面巨镜中相互折射、相互映照——构成拉康所谓的“大写他者”。回归80年代末的历史文化语境,“黑夜”意象群的书写模式一定层面上体现出特殊时代诗人群体性认识的思维方式,自由的呼声愈是高昂,来自现实层面的紧张和压迫感则愈加强烈。“黑夜”的象征符号,决定一代人精神探索道路上的诸多可能性,叛离、流浪、自由、迷途、返乡、归栖、打破等一系列激情迸发式的诗歌母题,构成80年代末诗歌理想的精神内核。
考察80年代末的诗歌群体,文化反思与自我审视成为一种共通性的价值追求。80年代处于思想解放的井喷期,同时也遭遇着传统文化的断裂层,因此迫切要求诗人们确证自我身份的认同。“黑夜”意象群的书写关注“黑夜”的底层,探询的是打开文化反思与自我审视的缺口,寻找“我之为我”存在的价值意义。诗人呕尽心血对“黑夜”意象群的精神内核作痛苦的质询,“有门,不用开开/ 是我们的,就十分美好/ 早晨,黑夜还要流浪”(顾城《门前》);“我把黑夜托付给黑夜/ 我把黎明托付给黎明/ 让不应占有的不再占有/ 让应当归还的尽早归还”(戈麦《最后一日》);“你是灯/ 是我胸脯上的黑夜之蜜/ 灯,怀抱着黑夜之心/ 烧坏我从前的生活和诗歌”(海子《灯诗》);“诗的内部一片昏暗”(北岛《黑盒》)……“黑夜”意象群,在诗人这里试图通过诗歌与现实世界之间构建一种拉康式的镜像关系。借助于镜像,诗人把外部世界内在经验化,浸入生命的激情、理想、痛苦、沉思,同时诉诸语词形式呈现出来,获得精神与现实对话的可能。对“黑夜”的诠释,北岛、顾城、海子、戈麦等诗人竭力穿透虚假的镜像获得自我认同,诗歌的精神探索充满着沉郁、紧张、分裂、痛苦的思想意识。北岛的漂泊之思、顾城的童话王国、海子的麦地太阳、戈麦的黄昏暗夜,不同的书写笔触和情绪背后,共通的是身处“黑夜”情境下对个体身份认同的焦虑与隐忧,并从自我认同上升至时代命运、文化自信相关联的集体性自我认同。
明暗的对峙和相互抵抗,使得“黑夜”意象群富于矛盾和冲突,1984年3月卧轨的海子在逝世前写于1、2月的几首献诗较为典型,诗歌集中对“黑夜”意象进行总结性思考,《最后一夜和第一日的献诗》中写道:“黑夜比我更早睡去/ 黑夜是神的伤口/ 你是我的伤口/ 羊群和花朵也是岩石的伤口”;[11](P240)另一首《黑夜的献诗》则写道:“黑夜从大地上升起……黑夜从你内部上升/……黑夜一无所有/ 为何给我安慰”。[11](P241)“黑夜”是自我探询过程中无法止歇的精神伤口,身处“黑夜”镜像中追寻自我认同而始终没有答案。“黑夜”本身包裹着无尽的死寂与晦暗,是探求价值理想和追逐自我认同的彻底溃败。诗人称“我在丰收中看到了阎王的眼睛”,给黑夜的献诗无疑是哀恸与深刻的,认识“黑夜”的同时也深化着对自我与时代的认识。自我呈现、自我指涉在北岛、顾城、海子、戈麦等人的诗歌中频繁出现,恰如吴晓东所言“自我由自我来确证”,“黑夜”意象群的精神书写最终指向主体确证主体的悖论,矛盾和冲突成为镜像诗学的直观写照。
“黑夜”是一面巨大的镜子,在镜像世界和他者的视域下,对自我的认知只能够在误认与确证之间徘徊不前。个体获取自我身份的认同,在20世纪80年代末诗歌书写中始终充斥着“黑夜”情境下的痛苦焦灼,甚至衍生成为死亡书写。正因为有北岛、顾城、海子、戈麦等充满生命力的诗歌关怀,现实黑夜才留省下星光的闪烁,诗意栖居也才成为可能。诗人的自我探询,观照的是时代集体性的精神生存状态,在80年代末的特定时期释放抒情诗强烈的情感张力。客观上“黑夜”意象群作为象征性、否定性、隐微性的诗歌写作,以“黑夜”作为现实和人生的象征,这种曲折和隐喻性表达实际上代表着异质和抵抗的书写姿态。恰如欧洲浪漫派诗人最初的不被理解,“文学重复了革命对既存社会的反抗,成为了反动派文学或者一种‘未来’文学,最终成为了一种疏离的文学,因其孤独而日益骄傲。”[13](P17)诗歌与时代之外独有的警惕性和抵抗性,最终会成为时代精神文化的宝贵财富,“黑夜”意象群的诗歌书写正是以否定和反抗的姿态走向当代精神生活的底层,咀嚼痛楚以获得经验的超拔,确证自我身份的认同,并引领诗歌理想的未来指向。
[1]闻一多.唐诗杂论·诗与批评[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2]吴晓东.临水的纳蕤思:中国现代派诗歌的艺术母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3](德)弗里德里希.现代诗歌的结构[M].李双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4](法)拉康.拉康选集[M].褚孝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5]刘文.拉康的镜像理论与自我的建构[J].学术交流,2006,(7).
[6]吴晓东.文学的诗性之灯[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
[7]邵文硕.拉康镜像理论的理论来源及其理论建构[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1,(3).
[8](日)福原泰平.拉康——镜像阶段[M].王小峰,李濯凡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9]北岛.北岛作品精选[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
[10]顾城.顾城的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11]海子.海子的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12]戈麦.戈麦的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13]张一兵.不可能的存在之真——拉康哲学映像[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责任编辑 王碧瑶)
(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Interpretation of the Mirror Image of the “Dark Night” Image Group in Poems of the Late 1980s
ZHOU Junfeng
(CollegeofLiterature,CentralChinaNormalUniversity,Wuhan, 430074,HubeiProvince)
In the late 1980s, Bei Dao, Gu Cheng, Hai Zi, Ge Mai and other China’s lead poets paid much attention to the image group of “dark night” in their writing. While highlighting the sense of urgency of exploring poetic ideas, their effort also showed their ability to reflect on and know about the reality and complicacy of our society. By revealing the symbolism, negation and evasiveness of the image group of “dark night,” Chinese poetry at that time combined examination of the poets themselves and that of the time they were in. Writing about the “dark night” thus became a way to show your knowledge about yourself. The present paper first attempts to interpret the connotation of “dark night” as an art motif from departure of the special context of “dark night” as an image group before proceeding to analyze the concrete varied and complicated spiritual content of “dark night”.
“dark night”; image group; poetic structure; mirror image; selfness
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创新创业基地项目“现代汉语诗歌的黑暗书写与心理疗救”,项目编号:NO2015650011。
2016 - 10 - 12
周俊锋(1990―),男,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诗歌。
I207.25
A
1671 - 7406(2016)11 - 0053 - 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