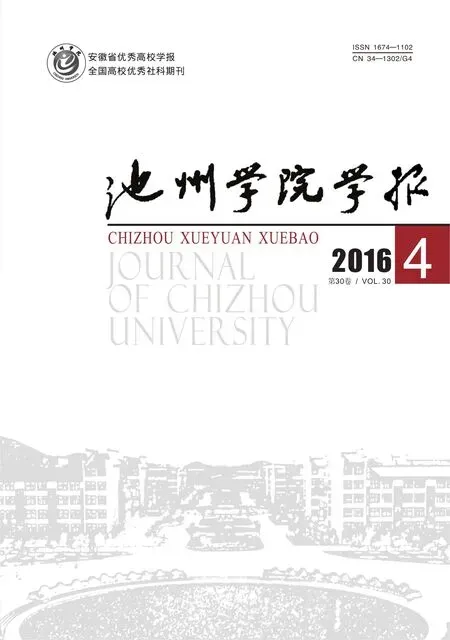社区矫正制度的性质定位
2016-03-28章璐璐
章璐璐
(华东政法大学 法律学院,上海 200042)
社区矫正制度的性质定位
章璐璐
(华东政法大学 法律学院,上海 200042)
社区矫正的性质界定决定了其开展工作的模式。现行法律将其性质规定为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存在着定位不准确、报应思想痕迹较重的问题。而在分析社区矫正的理论基础上,即刑法谦抑主义、深化的复归理论、刑罚目的的变迁以及人道主义思想之后,并结合社会的发展的现状,社区矫正的性质应发展为“行刑、矫正和福利性质”的综合性矫正方法,在此前提下开展工作。
社区矫正;理论基础;性质界定
伴随着刑罚文明的不断发展,刑罚执行方式也在不断改进,近代以来更是涌动着一股轻型化和非监禁化的潮流。社区矫正制度便是在这股潮流的影响下产生的。脱胎于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实践,再加上联合国刑事司法规则的发展,这一制度逐渐流行于发达国家。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社区矫正制度已经日趋完善,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比如“中途之家”、宵禁令、社区惩罚令、社区恢复令等,惩罚方式发生了深刻的转变。
社区矫正制度作为轻型化的一大标志,对于节约司法资源、降低重新犯罪率、增进社会和谐以及转变我国的刑罚执行方式具有重要意义。在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过程中,矫正主体混乱、矫正效果不理想的现象层出不穷,在学术界学者关于社区矫正的概念、理论基础等问题也是争论不休。
诚然,这些问题都是我们不能忽视的,而在这之前还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需要解决,否则这些争论将永无止境。性质问题是有关社区矫正的所有问题的基础,只要能够准确地界定,社区矫正的概念以及形式问题便可迎刃而解,而社区矫正的工作方向也会日渐明朗。因而笔者认为在讨论社区矫正的完善之前必须要对其性质进行界定。
1 现行法框架下社区矫正的性质及问题分析
1.1 现行法框架下社区矫正制度的性质界定
从两高两部发布的《通知》来看,社区矫正被官方界定为是与监禁矫正完全不同的行刑方式,是一种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有学者在此之外,从其他角度对社区矫正的性质进行了界定,即双重性质说。比如为了平衡社区矫正的监管、矫正和服务这三个方面,避免重监管轻矫正的现象,史柏年教授认为社区矫正应同时具备刑罚执行性质和社会福利的性质[1]。再如,刘永强博士和何显兵博士认为社区矫正是社会系统工程,其性质是专门机关工作与社会工作的结合体,是融合社区刑罚执行、监狱行刑社会化和出狱人社会保护等多方面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制度[2]。
在现行法有规定的情况下,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是社区矫正确定的唯一的法律性质。而双重或多重性质说只是从不同角度赋予了其不同的性质,但这些都没有被法律所认可。
1.2 社区矫正官方性质的问题分析
尽管在当前的法律背景下,我们必须在坚持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的前提下开展社区矫正活动,但社会是不断发展的,法律是不断进步的,我们不能只满足于现状,否则社区矫正的功能便不能完全发挥,而设置社区矫正制度的现实意义也会大打折扣。因此,我们不能忽视当前社区矫正的性质定位所存在的问题以及带来的种种隐患。
1.2.1 定位不准确 众所周知,管制是刑法规定的独立的刑罚方法和刑种,因此“对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的规定与社区矫正的性质相符。然而,缓刑与假释都不是独立的刑罚种类,具体来说,缓刑是作为一种量刑制度而存在的,而假释则是刑罚执行制度,对这两种罪犯实行社区矫正,则社区矫正变成了刑罚执行方式的执行方式,是比刑罚执行方式更加下位的概念,显然与官方给予社区矫正的性质是相矛盾的。
1.2.2 报应思想挥之不去 两高两部的《通知》将社区矫正定位为与监禁矫正相对的刑罚执行方式。古往今来,不管人类文明如何发展,刑罚始终带着“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报应思想,官方定义的社区矫正只是改变了刑罚的执行方式,把封闭的监狱搬到社会中来,使社会变成了犯罪人员服刑的大监狱。这就使得为保障人权而诞生的社区矫正又跳回到报应的圈子里。而在官方的宣传下,也使得学者以为社区矫正本就应与传统刑罚异曲同工。如周湘斌认为社区矫正制度应当体现报应的正义目的,如果毫无惩罚意义的话可能会使更多的人走上犯罪的道路[3]。这些观点显然没有正确理解社区矫正设立的理论基础与最终目的,仅仅着眼于其惩罚机能,而忽略了其更为重要的矫正功能。
2 社区矫正的理论基础
要给社区矫正确定一个合理的性质,必须首先厘清其理论依据。国内外有关于此的著述繁多,至今仍无定论,“四大理论”、“七大理论”等等莫衷一是。关于各家理论,本文不再赘述。考察所搜集的资料,笔者认为其理论基础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2.1 刑法谦抑主义思想
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刑罚也在不断发展,人类的刑罚从以死刑、肉刑等残酷刑罚为中心发展到以自由刑为中心,体现出了刑罚由重向轻的转变,充满了人道主义的光辉。在人权的份量不断加重的今天,人们普遍意识到犯罪人也有人权,试图寻找一种更有利于社会,有利于罪犯的刑罚措施。
“刑罚的谦抑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用最少的社会支出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对罪犯进行改造,以达到有效地抑制犯罪的目的”[4]。该理论认为刑法是保护合法权益的最后屏障,只有当其他手段不能有效保护合法权益时,才能够启动这最后一条防线。刑法不是万能的,而且由于刑法条文力求简洁,所以刑法不能事无巨细地规定社会生活的所有内容。尽管刑罚作为一种必要的“恶”,但必须重视其人道性、正当性和合理性,如果这种“恶”被允许,则是为了制止更大的“恶”[5]。在刑法谦抑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刑罚目的也发生了变化。原来以报复罪行为重点的格局悄然改变,矫正罪犯,帮助其重返社会逐渐占据上风。长期监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遏制了罪犯再次犯罪的可能性,但由于长期失去自由,也可能导致罪犯逆反心理严重,此外,罪犯长期与社会脱离,不利于其回归社会。而短期自由刑的威慑效果有限,而且容易导致服刑人员交叉感染,交流犯罪经验,其弊端也早已为人诟病。因此西方国家采用了诸如暂缓起诉、不起诉等措施代替监禁刑,可以较好地集中司法资源,将刑事政策的重点放在罪行重大的罪犯,而把犯罪情节轻微的罪犯交给社会矫正。
2.2 深化的复归理论
复归理论认为:社区是治疗罪犯的中心,不把罪犯隔离而置于社区环境中,能够避免罪犯在服刑完毕接触到一个全新的世界时的不适感,帮助其更加容易地回归社会[6]。
复归理论认为每一个罪犯都是可以重返社会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不必拘泥于监禁刑这一种刑罚,如果将社会作为罪犯矫正的场所,让其在未脱离社会的情况下改造自我必定事半功倍,更加容易回归社会。而且该理论认为犯罪不能仅仅归责于犯罪人,社会因素在其中也应负一定的责任,在矫正罪犯时必须出力。同时,汇集社会各界力量的社区矫正也有更多的资源来帮助罪犯重新做人。
2.3 刑罚目的的变迁
“惩罚性是刑罚的永恒的属性,而教育性则是近代刑罚的属性”[7]。刑罚目的的变迁是社区矫正的另一个理论基础。
刑罚目的的变迁经历了报应主义、功利主义和折衷主义这样一个过程。报应主义否认预防犯罪是刑罚的目的,认为刑罚是对罪犯过去所实施的犯罪行为的责难与报复,刑罚的轻重取决于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刑罚的目的是使犯罪人遭受痛苦。然而在报应主义控制下的刑罚并没有有效地遏制犯罪,人们开始质疑这一理论,转投功利主义的怀抱。该理论主张惩罚犯人带来的实际利益是刑罚的立足之本,因而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包括一般预防与个别预防。社区矫正的理论基础来源于其中的个别预防。
然而这两种理论都不尽完善,各有不足,综合了二者的折衷主义刑罚目的也就应运而生。折衷主义主张将犯罪分为已然和未然,分别赋予刑罚以惩罚和预防两种不同,而在预防未然的犯罪人上,刑罚的目的既包括防止犯罪分子再犯罪的特殊预防,也包括预防一般社会民众犯罪的一般预防[8]。在对犯罪分子判处刑罚时应以其罪行轻重为依据,这体现了报应主义的主张。然而由于适用报应主义的刑罚理论并不能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所以这里要引入功利主义的观点对其进行教育改造,从根本上消除其人身危险性。当然,对于罪行重大的犯罪人还是要采取监禁的方式改造,对于罪行轻微的犯罪分子则选择应该适用的社区矫正措施。因此折衷主义主张社区矫正与监禁矫正相互配合,有条件地选择适用。
2.4 人道主义思想
矫正的概念是基于刑事社会学派的理论而产生的。刑事社会学派认为犯罪不仅仅是犯罪人个人的原因,而且更应该重视社会在里面所起的作用。人是社会动物,其一系列行为都是其对社会生活的反应,所以社会因素在犯罪中也具有可谴责性。正如有学者所言在一定程度上罪犯属于社会中的特殊的弱势群体,因为刑罚的执行使得其与社会隔绝造成社会功能弱化而难以为生[1]。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为犯罪人员提供福利,帮助其回归社会的思想,社区矫正应运而生。纵观国外社区矫正工作的先进经验,对人格的尊重在社区矫正的开展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以及社区服务中培养罪犯的劳动技能为日后的就业做准备也是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人性的光辉。这也说明了社区矫正虽然不可避免地也具有惩罚的功能,但教育矫正等社会福利功能才是其更为重要的意义。
3 社区矫正性质的新界定
在分析社区矫正的理论基础之后,能够总结出这样一个结论:社区矫正是适用于犯罪情节较轻的罪犯的,同时在惩罚功能之外应兼具教育性、帮助罪犯复归社会,重复体现人道主义的制度。王顺安教授指出,未来我国社区矫正的性质应定位为“行刑、矫正和福利性质”的综合性矫正方法。学者吴海峰将其概括为综合性的与监禁处遇相对的非监禁处遇方式[9]。“社区矫正是由专门矫正机构在社会力量的配合、辅助下,对非监禁刑和其他非监禁措施罪犯予以行刑、矫正及服务的活动,是与监狱矫正相对的行刑与矫治工作,但其性质更倾向于矫正与福利性质”[10]。理由如下:
3.1 国外经验借鉴
在民法法系国家,社区矫正被称为“社会内处遇措施”,其主要内容是缓刑、假释和监禁执行过程中的开放性处遇措施与方法,以及对刑满释放人员的监护与帮助[11]。可以看到,在大陆法系国家,所谓社区矫正既要针对服刑人员的犯罪行为进行惩罚,同时也要对其犯罪心理予以矫正,并在其陷入困境时伸出援助之手,防止其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再次走上犯罪的道路。尽管像家中监禁之类的半封闭性矫正措施似乎惩罚力度较大,但在另一方面可以说这是一种保护性的管束。
而就我国而言,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充斥着重刑主义思想的刑罚设置并没有有效地减少犯罪率。因此,在轻刑化的潮流中,我们引进的社区矫正制度也必须将重心转移至矫治和提供福利。根据人道主义思想理论,罪犯也是犯罪行为的受害者,犯罪一方面侵害了社会利益,另一方面也毁灭了罪犯的未来。单纯的惩罚除了给予被害人精神慰藉以及罪犯以痛苦外,在其他方面收效甚微。而将社区矫正的性质更倾向于矫正与社会福利的话,一方面可以帮助罪犯复归社会,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罪犯对被害人进行补偿,弥补被其破坏的社会关系。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想法。我国封建时期的历史较长,在封建社会中刑法主要惩罚的是犯罪人而非犯罪人的行为。只要有了危害社会的结果就要受到惩罚而勿论其主观方面。罪犯应该受到与被害人同等的痛苦,这种粗暴的报复心理至今还在支配着人们思想。将罪犯放回社区不剥夺其自由,而且还要全社会来帮助罪犯,这种做法是传统的中国人民难以接受的。这种观念是亟需改变的,而改变的契机或许就是社区矫正的发展。
3.2 理论基础导致的必然结果
前文已论述过社区矫正的四种理论基础,从中可以看到社区矫正不能仅仅局限于刑罚的执行方式,否则我国的刑罚体系改革只是原地踏步。
仅仅关注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方式性质,会致使矫正人员的工作重心错误,过分重视对矫正对象的监督,忽略了对矫正对象心理的矫治以及工作技能的培训。同时也造成矫正机构在挑选工作人员时仅仅着重于矫正人员的监管技能。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主要是司法所的工作人员)、社会工作者和社会志愿者是我国社区矫正队伍的主力。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社区矫正的参与人员中应当涵盖各个专业的人才,尤其不能忽视工作人员在心理学和社会学方面的修养,比如日本开展的社区矫正工作中专业、科学、人格审查、保护观察等措施都是经过精心设计论证的[2]。就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组成来看,很少具有上述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员。这种性质定位错误不仅严重阻碍了矫正工作的开展,而且极大地阻碍了其功能的有效发挥。而当将社区矫正的性质确定为“行刑、矫正和福利性质”的多元化矫正方法时,矫正人员就能很清楚地认识到工作的重点,以便有效地开展工作。而且这样的性质定位还可以扩大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以便最大限度的发挥其作用。
首先,可以将刚刚出狱的人员并入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中。应该明确的是,这并不是要加重其刑。刑释人员因其犯罪被监禁而被打上烙印,并由此回到社会面临失权状况,表现为无法维持正常的生活、被周围的人孤立以至于感到自卑和无助[11]。由于长期与社会隔离导致的陌生感和无措,刚出狱的刑释人员极易再次误入歧途。将这部分人员纳入社区矫正的范围,为其构建一个过渡场所,向其提供一些就业和生活上的帮助,可以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而且一对一的社区帮扶也可以及时发现刑释人员的心理变化,纠正其不良思想,帮助其充实责任感和自信心。
其次,可以将具有依赖或滥用毒品的人员纳入社区矫正。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维护合法利益。毒品消耗是无底洞,需要花费大量金钱,“瘾君子”在无力购买时往往会铤而走险,走上不归路。而且大部分吸毒人员都是精神空虚、无所事事的人。将这部分人纳入社区矫正工作,组织其参加社区服务,可以增加其归属感。为这部分人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增加就业的机会,可以填补其空虚的心灵。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丰富的时候,吸毒的可能性也会变小。
再次,将犯罪情节较轻的罪犯纳入社区矫正。情节较轻的初犯通常犯意较轻,人身危险性小,对社会的危害不大。将这部分人放到监狱矫正和放到社区矫正没有多大区别。但是在监狱矫正却有使这部分人员被交叉感染的可能,在被传授犯罪方法、坚定犯罪思想的情况下很有可能再次犯罪。因此这部分人不应继续在监狱服刑,而是应该放回到其所在社区。面对社区居民以及社会各界的“以德报怨”,这部分人更易于矫正成功。而且这样也可以减轻监狱的压力。
最后,本文认为对于部分犯罪情节轻但非监禁刑不足以惩罚其罪而监禁刑又过重的罪犯(尤其是盗窃类罪犯)可以将两种刑罚结合适用。但这又不同于假释。我们可以借鉴西方的中间性惩罚的方式,如果这类罪犯的悔改表现较好,可以将他们刑期的最后几个月改为半监禁性。即白天可以恢复自由,可以自觅工作,但晚上必须回到监狱或者是其他的固定场所居住。这样既可以让服刑人员不至于与社会脱节,也可以防止其再次犯罪。
4 结语
作为一种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并迅速普及的刑罚执行方式,社区矫正体现了轻刑化以及刑罚社会化的趋势,对于我国行刑方式的转变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笔者认为在当前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各项配套措施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可以暂时按照现行法律的规定将社区矫正仅仅局限于刑罚执行方式的范围内。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必须逐渐完善其性质的丰富的内涵,最终确立“行刑、矫正和福利性质”兼容的综合性矫正方法的性质。只有这样才能转变我国传统的刑罚观,进一步完善社区矫正制度,同时让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充分发挥其作用。
[1]史柏年.刑罚执行与社会福利[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2009(1):22-37.
[2]刘永强,何显兵.关于社区矫正工作者的定位及其队伍建设[J].河北法学,2005(9):97-99.
[3]周湘斌.社会工作充权视角下的释犯社区矫正政策分析[J].刑事法学,2006(2):45-52.
[4]陈兴良.刑法哲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6.
[5]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M].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216.
[6]彭亚楠.论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及其完善[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2010:10.
[7]赵秉志.刑法争议问题研[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66.
[8]陈兴良.刑法适用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132.
[9]吴海峰.论社区矫正的性质定位及改革[J].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3(3):34-55.
[10]王顺安.社区矫正的法律问题[J].政法论坛,2004(3):102-109.
[11]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M].陈钟林,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370.
[责任编辑:周芳]
D924
A
1674-1102(2016)04-0034-04
10.13420/j.cnki.jczu.2016.04.011
2015-10-19
华东政法大学2015年度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015-2-088)。
章璐璐(1991-),女,浙江丽水人,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刑法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