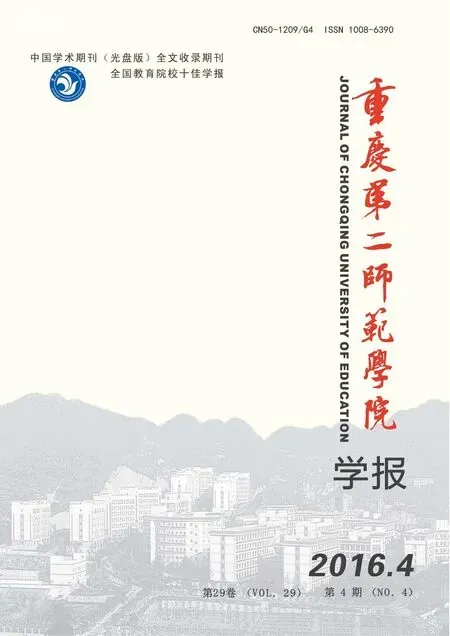网络文学的基本特性
2016-03-28孔令斌
孔令斌
(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文理科学系,合肥 230051)
网络文学的基本特性
孔令斌
(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文理科学系,合肥 230051)
界定网络文学,应具有技术性和文学性的双重视野,从互联网的本质入手,结合文学活动的主要特征,找到两者之间的交互点,即网络文学具有网络性、复制性、互动性、大众性、颠覆性、多媒介性和商业性等七大特性。网络文学可以界定为一种全程在互联网平台开展,以复制作为创作和传播的主要特征,阅读体验具有互动性和浅俗性,主观上不断进行解构和自我解构,客观上由商业利益驱动,可供多媒介共同参与的文学活动。
网络文学;复制;互动;大众
何谓网络文学?对此问题的认知往往走向两个极端,要么进行狭义界定,将其与网络小说混为一谈,要么进行广义扩展,认为互联网上出现的文字形式皆是网络文学。虽然网络文学仍旧属于文学的范畴,却在表现形态和精神内涵上迥异于传统文学。从文学的角度来看,狭义界定忽略了文学的多样性,而广义扩展则淡化了文学的独立价值,两者均无助于厘清网络文学的真实面目。有学者指出:“在网络文学还处于‘命名焦虑’时就试图对其做学理阐释,无论在知识谱系还是在意义范式上,都有太多悬置话题期待解答。”[1]界定和研究这一新兴文化现象,只有从互联网的本质入手,结合文学活动的主要特征,才能发现文学与技术之间独有的媾和关系,即网络文学的七个特性。
一、网络性与复制性:网络文学的创作特征
毋庸置疑,网络文学具有网络性。首先,互联网要参与文学活动的全过程,无论是传统文本被上传网络,还是网络文本在线下传播,只要某个环节脱离了网络,就不能称为网络文学。其次,互联网要在文学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成为创作、传播和阅读的驱动力。
我国网络文学的创作热潮是空前的。互联网逐步降低门槛,赋予人们越来越多的发声权利,为创作热情的释放提供了一个公共平台。“创作自由”的主张由来已久,在很多时代被提倡,也被不同程度地践行,但没有传播和阅读的自由,创作的自由就无从谈起,只能是体制默许下主流精英们的孤芳自赏。网络时代以前,大多数人的创作冲动只能通过私人渠道进行宣泄,流通的圈子较为有限,而在网络空间里,草根与精英至少享有了表面上均等的权利,所发布的信息在理论上既可以向任何人开放,也可以限制开放的范围,成本却十分低廉。互联网激发了创作源源不断的生命力,使文学在体制性生产、推广之外,向下扎根,向光生长,找寻自在呼吸的广阔空间。
网络文学依靠互联网进行传播,而传播过程本身也参与了创作。传统的文学作品讲求一次成型,无论创作历时多久,无论在读者心目当中会产生多少个哈姆雷特,一旦原作者划下句点,作品便宣告完成;后世虽有改写或续作,如《西厢记》之于《莺莺传》,《荡寇志》之于《水浒传》,却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独立文本。而在网络文学的传播中,网民通过一次改编或一句评论,就可能完成从读者到作者的身份转换,如因《后宫甄嬛传》流行开来的“甄嬛体”;甚至可以将非网络作品改编为网络文学形态,如2009年因韩寒、王珞丹电视广告在网上走红的“凡客体”。网络文学只要继续在网上传播,其创作就不能主动宣告终结,一切有关的改写就不是独立的文本,而是依附于网络原作,成为“1”后面无数个“0”。在这样一个动态过程中,原作者往往置身事外,眼睁睁地看着作品一步步背离自己的初衷。
对阅读而言,网络是把双刃剑。一方面,相对来说,纸质书存在价格昂贵、容量有限、携带存储不便、阅读过程单调等缺点;网络阅读费用低廉,既能在线浏览,亦可下载保存,选择范围较大,疲倦时可随时跳转至其他娱乐方式进行放松。这种便捷化和智能化降低了阅读的难度,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阅读的兴趣。另一方面,因创作门槛降低和传播围墙拆除,网络文学总体上不再追求文本的严谨、雕琢,转而走向轻“质”重“量”,注重秒杀读者眼球,迎合宣泄的需要,弱化了阅读的教育功用,使之愈来愈浅。
网络也为复制提供了巨大的便利。瓦尔特·本雅明曾说,工业机械时代生产出来的许多艺术作品丧失了独一无二性,如摄影、电影,成为可供不断复制的产品[2]。复制即拷贝(copy),不仅指复印机的复印功能,而且一部影视剧被重复播放,一张照片在不同刊物上出现,一条生产线上成千上万辆同型号汽车分批下线等,均可称之为复制。可以说,复制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涵盖广泛,已经成为大众文化的重要属性。对于网络文学来说,复制既是创作方式,又是传播形态。
怎样理解网络创作中的复制?网络文学创作中的复制并非简单的“抄袭”,这种复制也不是“仿作”,更非盗版之类的非法行径。如果原作是网络作品,那么每个复制品都是原作的组成部分。例如“哥吃的不是面,是寂寞”,原本只是网民一句调侃或一首内心独白的小诗,没有随后海量的排队跟帖改写,不可能发展成为如此著名的网络文化事件。如果原作是非网络作品,复制就是一次重构,如著名的《悟空传》,就是以今人的观念来演绎《西游记》中的经典情节,对原作进行了原创性的复制。
那么,究竟怎样理解网络传播中的复制呢?技术通常会赋予人类两种权限:学习和使用。阅读亦即学习的过程,与之相比,使用才是互联网技术赋予我们的最大权限。电脑上的复制、粘贴操作简便,与手动抄写没有本质差别,只在效率上有高低之分,所包含的意义却不是传统的手抄那么简单。2014年3月14日,“白色情人节”当天,某网民更新了一条微博:“两只蜈蚣谈恋爱了,他们手牵着手手牵着手手牵着手……”随即,这条微博引发了转发和评论的热潮,出现了众多改编版本,如“约会结束了,两只蜈蚣挥手拜拜挥手拜拜挥手拜拜……”、“蜈蚣先生向蜈蚣小姐求婚,给她戴上钻戒戴上钻戒戴上钻戒……蜈蚣先生破产了”,再到结婚、生子及各种生活场景,共同将这句冷笑话变成一场网络狂欢盛宴。网络文本的轻质化使阅读和改编变得容易,为复制转发提供了市场,在网络传播中,哪怕一字不改,转发就是阐明态度,而改写就是继续创作。
二、互动性与大众性:网络文学的接受特征
在传统文学创作中,读者对文本的参与度几近于零,思路框架在作者动笔时已了然于胸,内容结构在书斋中基本定型,即使有所改动,那也多是付梓前与出版方商榷的结果。坊间流传蒲松龄为作《聊斋志异》,在家门口摆茶摊请路人讲故事。此说出自邹弢的《三借庐笔谈》,即使真有其事,也无法佐证作者与读者之间交流的存在,因为提供素材的路人对作者的创作意图毫不知情,也不一定会成为《聊斋志异》的读者。随着创作终结,读者意图已无法融入,所谓的作品研讨会、读者见面会,不过是版权方的宣传策略,其意义更多在于单方面的促销,并非互相的影响。而在网络文学当中,作者与读者、读者与读者、读者与文本之间,互动随时发生,“越界”成为常态。
网络文学作者与读者的界限本来就很模糊,读者能够转换身份参与创作,还能对处于创作状态中的作者施加影响。互联网看似纯技术手段,实则是人际关系的技术显现,网络产品须关注用户感受,才会受欢迎。在这种意义上说,网络作品与“淘宝”商品没有区别。作者借着网络便利,通过聊天软件、论坛空间聚拢读者群体,既为从中汲取灵感,又可获得第一手反馈信息,以便随时调整创作方向,赢得佳评。至于那些不经意间走红的案例,是因为其中的某些元素暗合了读者意图,同步于市场的脉搏。
读者彼此间的交流历来都不少见,但在传统经验中,除去小圈子里的面对面交流,大多数读者之间只存在“柏拉图恋爱”式的精神共鸣,缺少同一时空内、物理意义上的互联互动。而在互联网搭建的平台中,读者们可以根据共同话题自建讨论空间,可以一起“坐等更新”,还可以互相参与,对灵光乍现的“神回复”展开热炒,制造网络热点。有人担心随着网络实名制的全面实施,这些繁盛景象将不复存在。事实上,虽然眼下实施实名制的现实条件尚不完备,但实名制不足以抑制正常的网络交流,相反还能保护网络生态的健康运行,促进阅读群体的良性互动。
在网络文学中,作品为不可更改的完成态,文本则是开放的未完成态,等待读者来填充和解构。读者的阅读、转发、改编可以影响文本发展轨迹,而以上行为可能被文本记录,最终成为作品形态的组成部分。反过来,一些题材新颖、结构独特的网络文本迅速走红,开辟了全新的阅读市场,从而引领新一轮的创作风尚。从2006年3月开始,《明朝那些事儿》在“天涯论坛”连载,这条以“历史可以写得很好看”为旨趣的网帖因其演义色彩、轻巧笔触和权谋心术,受到网友的青睐和鼓励,继而结集出版。作者“当年明月”名利双收,直接刺激了《汉朝那些事儿》《唐朝那些事儿》《慈禧那些事儿》等跟风之作的涌现,这股热潮至今仍未消退。传统文学其实也能做到这点,但因种种客观限制,市场反馈较网络文学明显滞后。
互动性增强,能够提升大众参与的热情。人群的普及率和使用频率反过来又决定了互联网所能发挥作用的大小,想提升这两项指标,立竿见影的方法是降低使用门槛,让成本低廉,操作简便。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5年7月发布的《第3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达到88.9%,网民结构呈低龄、低学历趋势,平均每周上网时间持续增加,上网地点更加多元。科技不仅使网络阅读日益便捷和大众化,而且在挑拣阅读群体,把未养成阅读习惯、好奇感强烈的年轻人群吸纳进来;而对虽然具有良好阅读习惯,但消化新生事物的能力和冲动双双退化的老年群体缺少吸引力。这一现象说明,网络文学正以其简单化和娱乐化,重新划分阅读势力范围,蚕食传统阅读市场。
简单化体现在阅读设备和文本内容两方面。从庞大到微小,从固定到移动,是互联网终端一贯的进化方向,而智能手机作为最新成果,将候车、课间、睡前等碎片时间一网打尽,使之渐变为人们主要乃至唯一的阅读时间。阅读方式往往能够影响阅读的深度,为适应时间和场合的散碎,文本内容必须浅露直白,便于浏览。早在拨号上网时期,所谓“轻松读史”、“水煮历史”已蔚然成风,用笑书闲谈或麻辣酷评的方式,把严肃纷繁的历史人物和事件重新编排,套以当代人的思维模式,确实能消除阅读中的阻拒感,但这种一味将社会生活简单化的做法,省略必要的推理论证,除了在逻辑上难以自圆其说之外,还会产生误导大众的危险。
至于娱乐化,并非文学趣味的升华,而是感官刺激的加强,让阅读更适宜日常消遣,以戏说新解、穿越架空来规避社会责任,不再承担唤醒功能。“恶搞”是网络娱乐化的惯用手段,如“船撞桥头自然沉”类的经典戏仿,《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类的移花接木,“芙蓉姐姐现象”类的审美颠覆,“赵赶驴系列”类的小白奇遇,均以恶俗趣味迎合大众的逆反心理,深究下去,实是“反智主义”在网络空间的大肆蔓延。反智萌发于“社会普罗大众对一小部分精英意图掌控社会话语权的反抗”,“在传媒文化生产层面,表现为悬置知识、误读通俗和弱化知识分子身份”[3]。人类的历史屡受其扰,直至今天甚嚣尘上的“读书无用论”,鄙夷形上学问,追捧“世故哲学”。世故与唯利是图、虚假伪善的市侩习性有本质区别,它反崇高但不作恶,重功利但不逾矩,是一种实用至上和圆滑处世的生活态度。在网络文学中,反智主义老于世故而不囿于世故,不放弃对良知的恪守,只不过在表达方式上略显矛盾,用威权来惩治市侩,用市侩手腕来戏耍精英,个中细节虽经不起推敲,且有越轨嫌疑,却能激起草根大众快意恩仇的普遍赞赏。
三、颠覆性、多媒介性与商业性:网络文学的意识形态特征
网络文学表现出的生命力不是创新,而是颠覆。在传统经验中,科技通过颠覆旧有知识体系,来获得直线式的飞跃发展,烙有鲜明的时代印记。相比之下,文学则显得犹豫徘徊,无论怀旧还是激进,写实抑或写意,都不能用“先进”和“倒退”来衡量,只能以新创的独特性来凸显审美主张。在互联网平台上,随着技术对文学活动的持续参与和日渐主导,两者间达成媾和:技术获得文学授权,将自己装扮得温情脉脉,直抵人心;文学借助技术手段,将审美元素量化、解析之后拼贴重组,面目全非却又似曾相识。
网络文学的颠覆性最先体现在对话语权的争夺上。文学自产生之后,就逐步分为精英和平民两条发展轨迹。从巫术崇拜到辞赋浪漫,从建安风骨到诗律文理,精英阶层牢牢掌控着文坛走向;从劳动记录到诗经国风,从竹林隐逸到传奇词曲,随着文学管控的加强,本是平民发声的文学阵地被招安收编。而网络文学则展现出扫除一切的面貌,便是草根们另辟空间,力图建立一套新的话语体系来对抗主流传统,“传统文学经典网络化之路,也就是被解构之旅”[4]。
但是,这种草根霸权显得外强中干。在幕后,互联网技术的实际掌控者不可能将权力拱手相让,于是到了台前,网络话语开始转向对自我的不断颠覆。互联网为信息传播搭建了多元畅通的桥梁,信息在爆炸的同时也在加速淘汰,受众应接不暇的快速阅读倒逼了快速创作,那么与其费时费力地新创,还不如在已有经验上做文章。通过打破重构,既可以针对传统经典进行改写,也能够对网络文本进行反复挖掘。前段时间,“蓝翔技校”因黑客流言引发网络热炒,而后风向很快转到了“学挖掘机哪家强”的全民娱乐,而你根本无法预见未来一段时间,“蓝翔”又将以何种面目呈现于网民眼前。除此之外,网络的“复制”行为本身就包含颠覆的动机,网帖回复中常见的复制点赞、“保持队形”,都是一种改变原义的行为,将一句空泛的牢骚过度阐释为人生至理,将无心插柳变成绿阴成片,将个体无意识的无聊变成集体有意识的无聊至极。
多种媒介在网络空间的并存,又为这种颠覆提供了新的维度。对传统文学来说,同一文本可以通过不同平台来展现,如小说改编为话剧、影视剧等,但绝不可能同时共存于一个平台上,读者只能分别进行阅读。而网络平台因其强大的技术兼容性,为各种媒介都保留了一席之地。于是,文学的一元传统开始被打破:一是创作手法上的混搭风格,将图文、声情杂糅一体;二是阅读环境的立体包围,当我们在线欣赏音乐的时候,可以一边阅读网络小说,一边打开即时通讯软件与好友聊天。在以往的技术条件下,以上场景并非完全无法实现,只是互联网让这一切更加便捷,更重要的是,它能够轻易地改变固有习惯,让我们接受甚至依赖这样一种喧嚣的文学体验。
在这片喧嚣背后,商业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互联网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美国,其规则也最先由美国制定,商业需求促使互联网在90年代初从军事和科研领域挣脱出来,开始民用,融入并加速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让区域经济难以自给自足,必须依附于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尽管欧元和人民币相继崛起,眼下仍然无法推翻美元在国际外汇结算中的统治地位。金钱作为商业利益最直接的体现,与互联网缠绵缱绻,结成了天然的同盟关系。
全球化以国家和地区为单位,编织了一张巨大的社会关系网,把美国文化和美式价值观裹挟到世界各地,而互联网将网眼的密度细化到个人之间。这张网表面上兜揽了这个时代的文化特征,深层里却由经济活动维系着。现实生活中的一切,落在网中皆可成为被交易对象,由此进化产生的网络营销比传统交易更具隐蔽性。网络营销如今已发展到无孔不入的地步,网页弹窗、软文写作及广告植入比比皆是,连文化产品自身的宣传有时也无所不用其极,各种消息真伪难辨,炒作手法游走于法律和道德的边缘。在文化领域,娱乐精神和消费主义已成为大众文化的主导特征,日渐开放和多元的文化环境造成大众审美口味的变换不居,商业资本借助互联网捕捉到这些细微改变后,能够及时做出调整,我们才得以看见影视剧中一股审丑潮流的逆袭。从美学角度来看,审丑是一种猎奇式的审美,主角搭配从俊男靓女到女神“屌丝”,女性形象从温柔贤淑到霸气癫狂,衣着格调从大方得体到混搭另类,故事背景从地球爱情到外星之恋,犹如一针针兴奋剂注入我们疲惫的审美神经,被重复燃起的娱乐和消费欲望,通过互联网急速扩散,引发资本市场的新一轮狂欢。
四、结语
作者与读者界限的模糊,意识形态立场的游移,都指向网络文学鲜明的动态特征。网络文学与其说是一种形式,毋宁说是一种状态更为合适。如果尝试为其做一个更加准确的界定,那么网络文学就是一种全程在互联网平台开展,以复制作为创作和传播的主要特征,阅读体验具有互动性和浅俗性,主观上不断进行解构和自我解构,客观上由商业利益驱动,可供多媒介共同参与的文学活动。
[1]欧阳友权.网络文学论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432.
[2]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王才勇,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7-9.
[3]陈伟球.传媒民粹化背景下的反智亚文化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21(4):104-113.
[4]孙书文.解构:网络时代传统文学经典的“命运”——以《西游记》的网络改编为例[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5(3):85-90.
[责任编辑于湘]
2015-01-25
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支持计划重点项目“网络文学基本问题研究”(gxyqZD2016483)
孔令斌(1981- ),男,安徽合肥人,讲师,研究方向:网络文学和大众文化。
I206.7
A
1008-6390(2016)04-010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