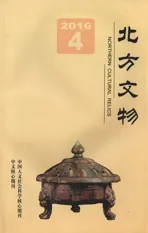元朝皇帝与星命、相术之关系新证
2016-03-27周思成
周思成
元朝皇帝与星命、相术之关系新证
周思成
星命 相术 民俗信仰 元朝皇帝
从星命和相术两方面探讨了蒙元统治者与被征服地域民俗信仰的关系。蒙古大汗和元朝皇帝,普遍采用一种“生辰占星术”为即位大典推算吉日,此外,元宪宗蒙哥和元世祖忽必烈也曾亲自采用观察“行步”和“目睛”的相术来品评甄选人物。这些信仰形式,大都能在其时帝国疆域内的各种本地信仰中找到渊源。这些事实说明,蒙元统治者对帝国疆域内本地“小传统”(通俗文化)的接纳,是既深入又微妙的;与汉化相比,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涵化”或许更适合描述这一过程。
对于13~14世纪的蒙古帝国统治者,特别是元朝皇帝同各种宗教文化及其他信仰形式的关系,学界的关注迄今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突厥—蒙古民族秉承自先民的萨满巫术,另一方面则是他们在征服扩张过程中广泛接触甚至接纳的,一般具有教会、信众组织和成熟教义体系所谓“世界性宗教”,如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等等①。其实,在蒙古帝国的广大疆域之内,介乎原始宗教和教会宗教之间,尚有多种形态的民俗信仰存在,它们表面上仿佛与蒙古统治阶级或其宫廷生活无甚纠葛,若仔细检视史料,却可发现某些本土化的民俗信仰其实与之关系甚深——根据人的相貌推断其祸福寿夭的相术,以及根据生辰推断其大运流年的星命就是其中的两种。包括元朝皇帝在内的蒙古统治者与这两种民俗信仰的互动,此前很少有学者留意②。笔者拟在蒐集若干新史料基础上对此问题略加考证,虽非数术之学的专家,或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 星命之术与元朝皇帝的即位仪
“有问皇帝之命,敢于应答者,皆邪僻应罚之辈,因星者亦不可窥探或妄言此事。”——古罗马星占家Firmicus Maternus③
若欲了解星命在蒙元宫廷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意义,就必须先考察波斯文史料《史集》中关于蒙古大汗即位仪礼的一组有趣记载。拉施特在叙述蒙哥汗登基时(1251年)提到,正式即位典礼举行前,先由“星占家们选出了一颗吉星”(波斯文:munajjim tāli’-i mas’ūd ikhtiyār karadand),“恰好在星占家选作天象观察的那个时刻,照耀世界的太阳,从乌云后面露出来了”,于是“星占家们便容易地测定了[行星]在地平线上的高度”④。在伊利诸汗纪中,这位波斯史家还先后提到,回历663年9月3日(1265年6月19日),阿八哈就是按照著名天文学者纳昔剌丁·徒昔择定的吉日,“在室女星座照耀下”(bi tāli’-i sunbuli)在彼剌罕地区察罕—纳兀儿即位;阿八哈之子阿鲁浑在回历683年5月27日(1284年8月11日)即位时,据说也是“在人马星座的吉照下”(bi tātil’-i mas’ūd-i burj-i qūs)⑤。对于另一些蒙古大汗,如元成宗铁穆尔,拉施特则只简单地记载:“他在吉星高照下(bi mubārak va tāli’ sa’d),顺利地被扶上合罕之位。”⑥
这些多属古代天学中黄道十二宫的所谓“吉星”,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另外两条记载或有助于我们解释这一疑惑。《史集》还提到,阿鲁浑之子合赞是于“回历670年3月29日”(1271年11月4日),在“天蝎星座的吉祥兆临下”(bi tāli’-i mas’ūd-i burj-i ’aqrab)诞生的,并且在他诞生之时,“在场的许多高明的星占家编制出星占表,极为慎重地作出结论,发现他是在十分吉祥的星的照临下诞生的。他们之中每个人念着诗说:‘我观察你的吉星,见到你的封地有十万人口’”⑦。又据宏达米儿(Khwandamir)的《旅行者之友》,阿里不哥之乱中,海都为与察合台后王阿鲁忽作战,向术赤后王别儿哥请求钱粮军队。别儿哥召所属之星占家,令他观测海都的本命星辰(natal star)以确定吉凶。星占家回奏说,天象显示海都的本命星辰极有威势,故他将击败一切敌人并统治长久,别儿哥遂决意在战事中协助海都⑧。这两条史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显示,蒙元统治者作为即位及重大事件决策依据的星占,应该就是源自巴比伦,陆续传入希腊罗马、波斯和伊斯兰世界的“生辰星占术”(horoscope astrology)。这种星占术大抵依据某人出生时刻的天象(涉及黄道十二宫、五大行星及日月的相对位置)排出天宫图并预言其一生命运⑨,其中又有特别重视“命宫”(即在诞生之时黄道十二宫中恰好在东方升上地平线的那一宫,又称上升星座)的一类讲究。
在中古时期的中国,人们对这种生辰星占术就有所了解。明人《星学大成》收录的《西天聿斯经》,据说源自唐代⑩,其中歌诀有云:“人命生来秉星算,历数幽玄妙难断。须识西天都例经,理义分明有条贯。但问生时日宿宫,加向时辰迥视东。天轮转出地轮上,卯上分明是命宫。”据此不难推断:《史集》提到合赞诞生时出现的“天蝎星座”,应该就是他的“命宫”或“上升星座”,与《旅行者之友》记载的海都“本命星辰”,实是指同一事物;前引《史集》记载大汗即位仪时常见的“在某宫照耀/照临下”一类辞令中,照耀/兆临(tāli’)这个借自阿拉伯文的波斯文词语原意,实是指星辰“上升”或“出现在地平线上”,故室女星座和人马星座也极有可能分别指阿八哈和阿鲁浑的“命宫”。
责成星占家为即位典礼择定吉日,确保自己在“命宫”的吉兆下登基,蒙古大汗对此有时是颇为严肃和虔诚的,甚至情愿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史集》记载,回历690年7月24日(1291年7月23日),阿八哈汗之子乞合都取得哈敦、异密和诸王的推戴即位,次年7月12日(1292年6月29日),他“第二次依照惯例登上王位,照例举行了欢娱、宴饮和庆祝”。据《瓦撒夫史》,乞合都将正式即位礼延迟一年的原因,居然是“诸星者言天象不利,故改期于还自罗姆时行即位礼”。重复举行即位仪的结果是汗廷库藏被赏赐一空,乞合都后来不得不仿效元朝发行钞币,以缓解严重的财政危机。有不少迹象显示,采用类似“生辰星占术”为即位择吉的习惯,也在元朝得到了延续。大德十一年(1307年)正月,元成宗驾崩,后嗣未立,卜鲁罕皇后欲援引安西王阿难答入继大统。《元史》记载,“成宗崩,内旨索星历秘文”,时兼掌秘书监的西域人爱薛“厉色拒之”。卜鲁罕皇后索取星历秘文,应是为自己临朝听政和阿难答即位选取星命吉日作参考。据程钜夫《拂林忠献王神道碑》,爱薛保管的“星历秘文”属“非御览不启”,很可能是记载太子、诸王生辰星命的高级机密文件。既然《旅行者之友》记载别儿哥可以遥知海都的星命,那么蒙古宫廷中保存有这类图籍也并不奇怪。元文宗至顺三年(1332年),文宗后与权臣燕铁木儿谋立元顺帝,但燕铁木儿疑心顺帝即位后将于己不利,于是“帝至京,久不得立。适太史亦言帝不可立,立则天下乱,以故议未决。迁延者数月,国事皆决于燕铁木儿,奏文宗后而行之”。燕铁木儿嗾使掌管天文历法的太史院官发布对顺帝即位的吉凶预测,干预皇位继承,恐怕也是在名义上利用了以星命推算皇帝即位和运祚的蒙元王朝传统。
从上述分析可暂得出两点结论:(1)蒙古大汗和元朝皇帝,普遍采用过一种“生辰占星术”为即位典礼推算吉日;(2)采用这种生辰占星术择吉,或应讲求当事人“命宫”中显示的吉兆。马可波罗观察到的、流行于元大都的占星术,须先得知问卜者诞生之年月日时,再将其人“诞生时之天象”与“其问卜时之天象,比较观之,夫然后预言其所谋之成败”,应该就是这种占星术。它与北宋以来趋于发达的、依据人生年月日时(“四柱”)起干支八字推算禄命的命理学(子平学)不同,却与中国古代使用星盘和安星法的“七政四余”、太乙和紫微斗数颇有些相似。若带着这两点结论,重新审视一些史家早已十分熟悉的史料,还可发现某些新的解释途径:己丑年(1229年)秋,以数术闻名的耶律楚材为窝阔台汗择定八月二十四日为即位日期,由于宗室诸王有持异议者,皇子拖雷示意耶律楚材“再择日”,楚材则坚持“过此日皆不吉”,即位大典最终如期举行。张帆师在《元朝皇帝的“本命日”》一文中曾附带指出,若从中国古代传统择日术来考虑,楚材择日的主要依据可能是日期干支或至少包括日期干支。不过,楚材既以星占术(“太乙数”)知名,据传“以甲火乙孛丙木丁金戊土庚水辛气壬计癸罗推命,曰天官五星法”。从前文考证看,关系窝阔台帝王运祚的即位仪,或更可能是通过某种生辰占星术、从当事人生辰年月日时推算决定举行日期的。此外,学者同样耳熟能详的“武仁授受”中的一则插曲:为调停武宗和仁宗争位之局,答己太后“以两太子星命付阴阳家推算,问所宜立。对曰:‘重光大荒落有灾,旃蒙作噩长久。’‘重光’为武宗生年,‘旃蒙’为仁宗生年。太后颇惑其言,云云”。无需赘述其中的政治斗争内幕,值得指出的是,我们解读这条史料的通常方式是将岁星纪年还原为辛巳、乙酉两个干支名称,对应武宗和仁宗的生年。这种做法自有所本,然而,联系前文讨论,推算武宗和仁宗星命,可视作是为迫在眉睫的即位典礼及确定之后的帝王运祚作准备。自蒙哥汗以来以至成宗,生辰占星术就在此类场合频繁得到应用,此处生年干支的单独出现,更可能是因为与八字命理学相比,带有生辰占星术色彩的推命术更加重视生年太岁干支的缘故。
二、 忽必烈的相人二术
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荀子·非相篇》。
对元世祖忽必烈的用人之道,史家历来多有褒辞。当然,也有学者发现,在权衡任用人才的某些场合,忽必烈偶尔也让相士侧身其间,相士甚至或多或少影响到他自己的判断。黄溍撰《答禄乃蛮氏先茔碑》言,中统元年(1260年),别的因入朝,忽必烈“密敕相士从后扪其胁,公不为动”,忽必烈呼为“壮士”,继而相士言其“大胁,非极贵之相”,忽必烈 “愕然”,遂不加显擢。其实,有元一代的史籍中尚颇有材料表明,不仅忽必烈,甚至在他之前的蒙哥汗,就亲自采用一种观察“行步”的相术来品评选拔人物了。《元史·忙哥撒儿传》记载,断事官首领忙哥撒儿举荐西夏人和斡于蒙哥,“帝召和斡,命之步,曰:‘是可用之才也。’和斡由是知名”。至元十六年(1279年),淮东道宣慰使也速儿奉中书省檄奏报边事:
入对便殿,出牍于怀。上大奇之,召近臣知文墨者使进读,而左右适无其人。王拜而言曰:“臣亦粗知文墨。”乃诵其文,而释以译语,音吐明畅,辞旨精切。上悦,令纵横行殿中,而默察之,知为伟器,谕宰臣俾与共政,遂以参议中书省事。
注意到这一有趣现象的是清末学者屠寄。在《蒙兀儿史记》的《忙哥撒儿传》和《也速儿传》相应的史料下方,他分别添加了小注,一曰“蒙兀人相法,忽必烈汗亦以是相人”,一曰“蒙格汗相西夏人和斡亦如此”。除屠寄明示的两则史料外,关于这种颇为独特的相步法的记载,其实还有数种。黄溍的《资德大夫陕西诸道行御史台御史中丞董公神道碑》提到,至元十八年(1281年)前后,董士恭朝觐忽必烈,“至上前,命返往行于庭中,见其气宇凝粹,正色敛容,周旋中度,大奇之,自是出入禁闼无间”。《元史·方技传》记载,数术家田忠良初会忽必烈,“帝视其状貌步趋,顾谓侍臣曰:‘是虽以阴阳家进,必将为国用。’”《康里脱脱传》则言其献猎物于忽必烈,“世祖见其骨气沉雄,步履庄重,叹曰:‘后日大用之才,已生于今。’即命入宿卫”。有意思的是,藏文史料中似乎也存在类似记载——《汉藏史集》提到,萨迦派喇嘛八思巴应忽必烈邀请出席大都的一次宫宴,他观察“伯颜朝见皇帝时的仪态、行步,启奏时能言善对,知其有大功德,向皇帝说道:‘英杰中之英杰,正是此人。’皇帝知上师此言之意……命伯颜留在朝中”。“行步”即藏文的‘gro lugs(步态),这“仪态”与“行步”,无非就是汉文史料中的“状貌步趋”。
这种观察行步姿态的相术,究竟是否如屠寄所言,是一种古代蒙古族的相法呢?据现有的史料难以得出定论。不过,“步相”确是中国传统相术的一支,四库馆臣推断出自宋代的相书《太清神鉴》专辟有“行部”,称“贵人之行,如水而流下,身重而脚轻。小人之行,如火炎上,身轻而脚重。故行不欲昂首而躩,又不欲侧身而折……周旋不失其节,进退各中其度者,至贵人也”,等等。元代刻印的日用类书《事林广记》所收“人伦风鉴”就有“行步”门,略言:“沉重者主荣贵,轻骤者主贫贱,移拽者聪明,跳跃者孤独,行步不低昂者主富贵两全。”笔者更倾向于认为,或是汉地传统中认为步态反映穷通祸福的民俗信仰,经由元朝皇帝身边的数术家,传入了蒙古宫廷,为某些皇帝所熟稔。
反过来说,元代究竟是否可见真正意义上的“蒙兀人相法”呢?其实也是有的。《元史》言,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以近臣举荐,召刘哈剌八都鲁于白海行宫,“世祖谓其目有火光,异之,遂留侍左右”。相似的还有成吉思汗夸赞畏兀儿人孟速思“此儿目中有火,他日可大用”的记载。类似说法,早见于《蒙古秘史》第62、114和149节。如德薛禅老人见到年少的成吉思汗,即称赞他“眼明面光”,蒙古语作nidun-tur-iyan qaltu,其实就是“目中有火”之意。罗伊果(Igor de Rachewiltz)在他译注的《蒙古秘史》中认为,这种说法“描述一种显示某人极其聪慧能干的非凡目光,是蒙古族口头文学中的习语”。刘迎胜先生最先注意到《秘史》中这一说法与《孟速思传》及《刘哈剌八都鲁传》记载的关系,指出“目中有火”是“实际存在的且广为使用的蒙古谚语”。
罗、刘两位先生的观点均是成立的。不过,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指出,民俗习语往往并非凭空创造,而多是现实生活中某种社会活动的反映。“目中有火”之所以成为元时期以来蒙古族形容聪慧独具之貌的习语,或许恰是因为其时通行一种注重从双目或眼神推断其人个性及能力的蒙古习俗。《元史·杨赛因不花传》记载,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播州土官杨氏子汉英随母亲朝觐忽必烈于上都大安阁,“帝呼至御榻前,熟视其眸子,抚其顶者久之,乃谕宰臣曰:‘杨氏母子孤寡,万里来庭,朕甚悯之。’遂命袭父职,锡金虎符,因赐名赛因不花”。似乎忽必烈素来就颇为留心此术。《元史·洪君祥传》也言君祥,“年十四,随兄茶丘见世祖于上京,帝悦,命刘秉忠相之,秉忠曰:‘是儿目视不凡,后必以功名显,但当致力于学耳。’令选师儒诲之”。“目视不凡”是否可看做“目中有火”?虽然中国传统相术传承中也存在“相目”的内容,甚至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如署名金人张行简撰、元人薛延年注的《人伦大统赋》就强调“欲察神气,先观目睛”,又称:“目光明媚,才秀聪明,积德之人。目无光彩,短命。牛虎视者,贵。黑睛大而端定,有寿。目圆无角,作事错拙,多后悔。”清代的一部相学总论《相理衡真》也强调“凡人之相以头为主,以眼为先,以鼻为权”,等等,然而,在忽必烈宫廷中,刘秉忠这位“聪书记”更像是在娴熟地借用汉地传统相术的语言,说着蒙古大汗最容易听懂的话。此外,在《元史》中,涉及忽必烈因为“伟其貌”或是“奇其貌”而招揽人才入值宿卫或是加以越次擢用的例子尚有不少。不过,单纯从这些记载中,无法看出忽必烈判断的依据究竟是眸子或是行步,或究竟不过是碑传作者的妙笔生花了。
三、 结语:汉化还是涵化?
在前揭关于元朝皇帝“本命日”的研究中,张帆师谈及学界对蒙元统治者汉化的研究稍有重“大传统”(精英文化)而轻“小传统”(通俗文化)的倾向,其实元朝皇帝对阴阳数术一类的迷信内容感兴趣更早,接受程度更高,并存在“选择性倾向”,值得深入研究。我们选取星命和相术这两个切入点来探讨蒙元征服者与被征服地域的民俗信仰间的关系,可以说是沿着这一方向作出的一点尝试。
对于现代人类学家而言,“文化”或“习俗”只是在一个范围内观察到的连续出现的现象,而对于历史学家而言,这些习俗出现的概率更是受到了千百年来种种必然和偶然的历史—文化因素对历史记录的干扰、扭曲与过滤,故本文所论两点,实未敢遽指为历史的本象。然而,对现有史料的分析毕竟揭示出,蒙元统治者对帝国疆域内本地“小传统”的接纳,既全面深入又错综微妙:元人朱思本在《星命者说》中描述了当时的数术家圈子中,“列十二宫,定太阳躔次,以人之生时”,从太阳宫推知命纬之所在,又推而知限之所至的“星命”,与“以人之生年月日时,配以十干、十二支,由始生之节序先后,推而知运之所值,五行生克,旺相死绝,而知吉凶祸福焉”的“三命”并行其道,且目睹了“挟斯数以游于通都大郡”、“名动公卿者数人”的真实情形。然而,不知是否因为长生天信仰的影响,蒙元统治者在即位仪这类重大事件上似乎总对星占一流的推命之术青睐有加。相似的,在金元以来的相学著述中,眼目作为面部“五官四渎”之一,一直是远较“行步”重要的主题,而这一大一小两个主题同时浮现在关于元代宫廷生活历史记载中,看起来更像是历史的巧合。“北方民族的天文星象学走着一条文化开放的道路,构成北方民族在文化上的开放性、容纳性与空前的文化活力。”蒙元统治者与这些属于“小传统”的文化因子的接触,可能正是这样一个杂糅了抗拒、接纳、改造甚至创新的复杂过程,其最终结果也必然是非均衡且非对称的。与其把这样一个过程及其结果描述为“汉化”(sinicization),我更愿意借用文化人类学的“涵化”(acculturation)的概念。涵化是指不同文化集团在密切接触过程中发生的文化特征的相互借鉴和改变,这种改变是部分的,不妨碍这些文化集团保留各自的文化特质。这一转换绝非是概念上的文字游戏,而是希望指出,当研究对象(比如,异族统治阶层)的某些行为模式发生了看似熟悉的改变时,我们不应过于仓促地将之单纯归因为“汉化”所代表的因素的推动。在这种情形下,与具有明显指向意义的“汉化”相比,涵化似是更加客观和富于启发意义的描述。
注 释:
① 关于古代蒙古族及元代蒙古统治者宗教信仰的综合讨论,可参见Jean-Paul Roux, La religion des Turcs et des Mongols, éd. Payot, Paris, 1984;〔意〕图齐、〔德〕海西希著,耿升译:《西藏和蒙古的宗教》,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邱树森:《元代文化史探微》(卷3《元代伊斯兰教研究》、卷4《元代基督教研究》),南方出版社2001年;近年出版相关著作主要有陈高华等:《元代文化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42~92页、第176~207页;李鸣飞:《蒙元时期的宗教变迁》,兰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
② 关于元代以算命、相面和占卜为代表的民俗信仰的一般讨论,参见陈高华、史卫民:《中国风俗通史(元代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关于元代的本命年信仰,参见张帆:《元朝皇帝的“本命日”——兼论中国古代“本命日”禁忌的源流》,《元史论丛》第十二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 33~34 页。关于伊利汗旭烈兀对星占学的兴趣和赞助,参见George Saliba: Horoscopes and Planetary Theory: Ilkhanid Patronage of Astronomers, in : L. Komaroff, ed., Beyond the Legacy of Genghis Khan. Leiden / Boston:Brill, 2006, pp. 357~368. 其他相关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元代所谓“阴阳人”和“阴阳学”方面,参见叶新民:《元代阴阳学初探》,《蒙古史研究》2000年第6辑;贾陈亮:《占卜与元代政治》,《黑龙江史志》2011年第13期;关于元代的阴阳学,西方学者的研究还有Elizabeth Endicott-West: Notes on Shamans, Fortune-tellers and Yin-Yang Practitioners and Civil Administration in Yüan China, in: Amitai-Preiss and Morgan (eds)The Mongol Empire and its Legacy, Leiden: Brill, 2000,pp.224~237.
③ Julius Firmicus Maternus: Ancient Astrology Theory and Practice:Matheseos Libri VIII, Trans. Jean Rhys Bram, Astrology Classics,2005, p.69.
④⑥〔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等译:《史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42页;第376页。波斯文见Rashīd al-Dīn, Jāmi’al-Tawārīkh, ed. by Muhammad Rawshan, Tehrān:Nashr-i Alburz,1953, p.829; p.938.
⑧ Khwandamir, Habibu’s-siyar, Tome Three: the Reign of the Mongols and the Turks: Genghis Khan-Emir Temur, Trans. Wheeler M. Thackst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41. 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和刘迎胜先生《察合台汗国史研究》都根据宏达米儿祖父米儿洪德的《洁净园》引述了这则故事,然其辞较简略,未提及占卜海都的“本命星辰”(参见张锡彤等译:《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570页;《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69页)。
⑨ 关于西方古代占星术的历史,参见江晓原:《历史上的星占学》,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5年。
⑩ 参见陈万成:《杜牧与星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8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1~80页。
〔责任编辑、校对 王孝华〕
周思成,男,1984年生,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列部编译一处主任科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15级博士生,邮编100032。
K247
A
1001-0483(2016)04-009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