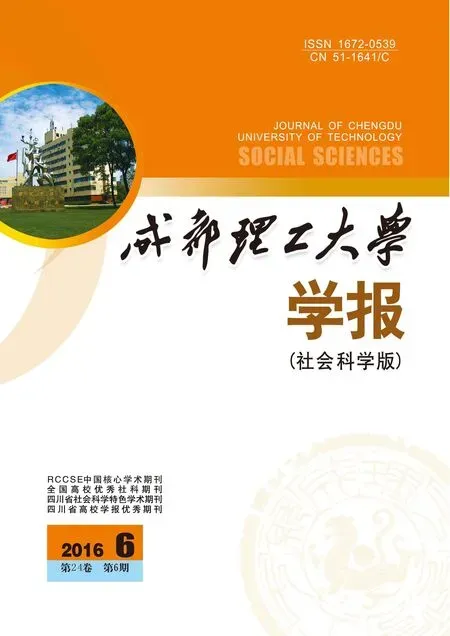《聊斋志异》的崂山道教形象书写
2016-03-26梁思媛
梁思媛
(广西大学 文学院,南宁 530004)
《聊斋志异》的崂山道教形象书写
梁思媛
(广西大学 文学院,南宁 530004)
《聊斋志异》中书写崂山的篇目都是关于道教的,蒲松龄通过对崂山人、仙、物、空间的构建,展现了崂山“神异”、“神仙”、“神圣”的不同形象。崂山篇目对道教的强调和对佛教的忽略,显示出崂山本土的“道盛佛衰”以及蒲松龄本人在道教影响下的新创举。
《聊斋志异》;崂山;道教;蒲松龄
崂山是我国著名的道教圣地,它僻处海隅,清静幽深,自古就被视为“神仙之宅,灵异之府”,在明末清初,更被冠以“道教全真天下第二丛林”(1)的称号。著名道士丘处机、刘志坚、张三丰等均曾在此修道。同时,崂山与佛教亦颇有渊源,《华严经》中记载:“东海有处,名那罗延窟,是菩萨聚居处”,此窟即在崂山。法显、憨山等高僧也选择崂山作为弘扬佛法之地。崂山兼具佛教与道教之土壤,然而在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直接书写崂山的篇目,即《劳山道士》、《成仙》、《龁石》、《香玉》四篇(2),却都是道教化的,这为《聊斋志异》以及关于蒲松龄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聊斋志异》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在艺术上代表了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其与佛教、道教有着广泛联系。“据粗略统计,在《聊斋志异》492篇作品中,直接与道教有关的就达157篇之多,几占全书作品的三分之一(间接受道教影响的尚未计入)。”[1]315“《聊斋志异》中三分之一写到因果报应,除此之外,还有近四十篇作品写到僧侣生活或涉及到僧侣的有关活动。”[2]51但迄今为止,国内学者有关《聊斋志异》宗教方面的研究基本还局限于全作与宗教的宏观梳理与把握,或者对单独篇目做文本细读,偏重于解读宗教影响下的文学思想与创作。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大视角与小视角,是否形成了研究的空白区域,以及忽略了某些篇目创作时独特的历史语境与作者情怀?笔者通过对《聊斋志异》中书写崂山的篇目进行细读,试图把崂山、道教与《聊斋志异》作为三个关键词放在一起作深入考察,归纳出蒲松龄书写的崂山形象,并探讨形成这些形象的原因。
一、神异、神仙、神圣——多方化的形象特征
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民族宗教,在其形成过程中,大量吸收了中国文化的各种因素和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固有的精神和心理特质,呈现出“杂糅多端”的特征,而在杂糅中又能见其结构的稳定统一。因此,落实到具体文本的书写上,指涉道教的形象必然也是多方化,又自成一体的。《聊斋志异》中书写崂山的篇目,就从人、仙、物、空间等不同角度,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完整的道教仙境,其总体特征可以用“神异”、“神仙”、“神圣”概括。
(一)人——从“神异”到“神仙”的脱胎
“长生”与“成仙”是道教成立前就扎根在先人心中的原始梦想,《庄子·天地》中就有“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3]129之句,帝王声势浩大的出海寻仙活动亦将这一梦想广泛散布。道教成立之后,这一梦想借由神仙方术、鬼神崇拜得到强化。唐代时,诸帝与贵族文人仍有服食仙药的习惯,社会上亦出现慕仙风尚。到了明清,这一梦想连同某些道教思想已经深深扎根于民间,可以说成为了整个民族的一种集体无意识[4]2。《聊斋志异》中许多关于求仙问道的篇目,其主人公就是书生、平民,而精确到书写崂山的四篇里,人的形象又可以根据得道的多寡划分为三类。
第一类人是由于自身原因“不入道”的,以《劳山道士》中的王生和《成仙》中入道前的周生为代表。《劳山道士》的开头,就提到王生的求道原因是“少慕道,闻劳山多仙人,负笈往游”,王生所慕之道实为道术,他把道教的“神异”一面误认作其终极——从刘勰在《灭惑论》中总结出的道家三品“上标老子,次述神仙,下袭张陵”[5]802来看,王生所慕之道仅为末流,虽是主动地求,却在最开始时就入了歧途。而在具体的求道过程中,面对日复一日的身体劳作,王生“不堪其苦”,屡有归志,始终不能理解和适应道教中“禁欲苦修”、“动静双修”的原则,仍旧一味“忻慕”道士所作的法术。他离开崂山时仍不忘让道士“略授小技”,最后落得求道不得、贻笑大方的下场。而相比王生的“慕道”和主动入山,《成仙》里的周生却是被迫的,他心中并没有给“道”留下位置,对求道丝毫不感兴趣,而是耽于现状。面对想规劝自己一同归隐的成生,周生因“溺少妇,辄迂笑之”,只是在与成生人神互换后,才不得不进入崂山以求帮助。虽然周生在山中见识了种种世间没有的“神异”景色,“然尘俗念切,无意留连”。他不像成生能敏锐地洞察人世,对现实更没有清醒的认识,当妻子背叛的真相近在眼前时,周生仍旧不愿相信,反而“窃疑成诪张为幻”。但明伦点评周生有云:“周先以牧佣之微嫌,不能自忍,几坏身家;继则人己弃予,而犹溺之而不忍弃;颠倒至此,何从识自己面目乎?梦者以为真,真者乃以为梦。幸有良朋,反复警唤,半生懵懵,乃忽焉醒耳。”[6]160王生的“慕术”、“中途而返”,周生的“被迫入山”、“思归”,崂山在他们生命中不过是停留数日数月的暂时性场所。延伸来看,实际上隐喻着崂山所象征的道教仙境与他们是“异质”的,即使身在其中,他们也并未沾染“仙气”,而仍是流于世俗。对于崂山来说,王生和周生这类人恰恰也代表着数量最庞大的芸芸众生,他们或因崂山的美景、或因道教的盛名而来此作短暂停留,但终归只能做个过客,不能深入真正的道教仙境。
第二类人是带有“仙根”,与道有缘的,以《龁石》中的王姓马夫和《香玉》中的黄生为代表。《龁石》篇幅精短,对马夫的求道经过没有细致的刻画,只写到他“幼入劳山学道”,而侧重于展现他得道回归时,崂山加诸于其身的种种“神异”之处,如“遍体生毛”、“啖石如芋,知其甘苦酸咸”,而其母离世之后,他选择复入崂山,“今又十七八年矣”,隐含着一种可以永不归尘世的超然。而《香玉》中的黄生,以往研究、评论多言说他的用情坚贞、感人肺腑,却忽略了其在崂山中生成的“仙根”。黄生本是舍读在崂山下清宫的一介书生,性情里不乏风流,对香玉和绛雪两位花仙有过“坐拥双美”的心思,然而这种心思却随着故事进展渐渐隐去,最终荡涤。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经年之后的黄生已然不复当初,他的言行中很明显地表现出深受以绛雪为代表的崂山仙境的影响,无论是弥留前对其子说的话(“此我生期,非死期也,何哀为!”),还是对自己身后事的预测(“他日牡丹下有赤芽怒生,一放五叶者,即我也”),都可以让人感觉到他已经“脱出凡胎,步入仙境”了。马夫和黄生身上,都运用了“入山—归家—入山”的叙事模式,这一模式隐含着最初他们与道的“异质”关系,即他们并非天生的“仙胎”,因此会带着世俗的习气。这在他们归家时体现得最为明显,马夫的“渐复火食”、黄生的“腊归过岁”都展现了他们作为凡人的一面。而关键的转化在于叙事的终点,即选择以“入山”作为终结。从这里可以看出,一方面,崂山作为二人最终的回归之地,表现出他们与尘世的主动断绝,另一方面,崂山亦是他们“脱凡入仙”的重生之地,他们在此处求得了道,并将自己也转化为道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最初的“异质”关系被“同质化”了。
第三类人是深谙道教义理,不仅自身修成大道,还能引导他人,以《成仙》中的成生和《劳山道士》中的道士为代表。成生虽然与第二类人一样来自尘世,但他在尘世时就能够深刻洞察世间,显示了自身的与众不同。劝阻周生不要冒进行事时,成生再三而泣曰:“强梁世界,原无皂白。况今日官宰半强寇不操矛弧者耶?”。友人落狱后,成生亦奔走为之脱罪。“是予责也,难而不急,乌用友也!”,但明伦评此为“大义凛然,仙根在此”[7]30。《成仙》中用了极大篇幅叙述成生得道后劝度周生,可以看到,成生践行了道教“惩恶行善”、“求无为,先避害”(3)的教义,行事风范中也带有道家所推崇的“上善若水”(4)的气质。对周生而言,他既是友人,更是良师。而《劳山道士》中的老道士,可谓是仙缘最深的“崂山中人”。他从开始时就身处崂山,未曾离去,可以说自成道教仙境的一个部分。道士的神,不在于他“素发垂领,神观爽迈”的外表和酒水不绝、遨游月中的“神异”道术,而在于其“去神异化”的艰苦修习与朴实良言。王生与道士初见时,道士就已洞察出王生“娇惰不能作苦”的本质,但却从未呵斥,而是循循善诱,作法让王生感受得道之后的超凡,言下之意即是只要他坚持修习,总有一天也能得道。对于道士来说,真正的道在于坚持日复一日的身体劳作,即使前一晚快活畅游,也要“足宜早寝,勿误樵苏”。笔者认为,倘若《成仙》描写成生助力周生,拔剑击仆,断其臂的字句还带有一丝血腥感的话,那么崂山高道从头至尾都是一派仙风道骨,与尘世全无粘连,真正地从“神异”到达了“神仙”的境地,我们可以说他身为人而实为仙,已经“同质”于崂山道教仙境的图景之中。
(二)仙——高洁“神格”的彰显
道教的神仙观认为,尊神皆道气所化,道气是无限的,无限的气可以化生出无数的神人,人也能得道成仙,神又是无所不在,无所不存的,掌管着自然界的万事万物[8]4,26。这与《聊斋志异》中的世界观是吻合的,在《聊斋》的故事中,人、神、妖等常常也没有明显的界限,他们是可以互通互联的一个整体。书写崂山的《聊斋》篇目里,仅有《香玉》篇涉及香玉和绛雪两位花仙,她们虽然都“艳丽双绝”,但性格迥异,反映出《聊斋》对神仙刻画的不同面。
香玉可与《聊斋》中蕙芳、竹青等爱慕凡人的女仙归为一类。从描写香玉的字句中就能清晰地读出她的单纯与痴情,她被黄生的诗句邀来,稍作交谈后便许下终生,经历了生离死别,仍初心依旧。但明伦在总评香玉时说:“种则情种,根则情根,苞则情苞,蕊而情蕊,‘忍风雨以待君’二句,无限深情,一时全绽。”[7]170可以说,香玉身为花仙,但言行、性格都与人无异。这在道教的神仙谱系中是得到承认的(5)。而此篇故事虽以“香玉”为名,但在笔墨功夫上,绛雪却要比香玉多得多,笔者也认为,绛雪才是《香玉》篇的真正主角,而她亦是故事中最具“仙气”的角色。故事开头先刻画了绛雪的真身——耐冬树的形象:“高二丈,大数十围”,颇有迎风斗雪的风姿。世人对此树多有赞许,如清嘉道间翰林尹琳基,在游崂山时作诗《冬游太清宫诗》:“灼灼耐冬花,孤芳自高洁。道人取琴弹,冷冷音清越。”[9]90直言耐冬的高洁、艳丽。绛雪性情疏落,却是个重情的人,在故事中多次为香玉恸哭,她素爱清净,却又能“代人作妇”,陪伴黄生。绛雪与崂山仙境最为相合之处在于她清净自爱又坚贞不移的“神格”,这在与黄生的相处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如她与黄生初次见面时就表明了“妾与君交,以情不以淫。若昼夜狎昵,则妾所不能矣”的立场,与黄生的交往也只限定在“宴饮唱酬”。而彼时的黄生还是风流俗人,面见美人时难免升起欲望。因此,在“生欲与狎”时,绛雪回答“相见之欢,何必在此”,字字掷地有声,“神格”尽显,让黄生为之汗颜。但明伦评此情节曰:“香玉之热,绛雪之冷。一则情浓,一则情淡……淡者能寡欲而多疏;疏则可以长守,情之所以有节也。”[7]169冯镇峦转引金圣叹评曰:“遇绝世人,急索登床。”都是以香玉的痴情、黄生的俗情来衬托绛雪的圣洁,也正是受到了绛雪的影响,黄生才能够渐渐地脱俗入仙。当香玉恢复真身后,绛雪来辞曰:“旧日代人作妇,今幸退而为友。”一位静穆、圣洁、进退有度、不染尘俗的耐冬花仙跃然纸上。绛雪之于《聊斋》中构建的崂山仙境是不可缺的,除她“神格”的相合外,某种程度上也冲淡了其他篇目中以男性仙真为主的格局,达到了一种阴阳的平衡,这同样是道教所提倡的(6)。
(三)物——玄妙“道气”的汇聚
天下名山僧道多,名山洞府是求玄问道之人选择居住、修习的上佳所在。道教认为,“非宫宇则无以示教,非山水则无以远俗”,崂山上道教宫观众多,最胜时达到了“九宫八观七十二庵”。《聊斋》中的《香玉》、《成仙》,就是依托崂山上清宫、下清宫而作,而《劳山道士》中出现的道观没有明确写出名称。这些篇目中穿插描写的涉及花、鸟、宫观等崂山之“物”的字句,虽然精短,却也隐含着深刻的道教思想。
与道家一样,道教也信奉着“道法自然”的思想。所谓“自然”即自然而然,意为事物“自己如此的”、“非人为的”,道是自己如此的原则,道的法则就是维护世界生长变化过程的自然本性,维护宇宙整体的和谐与平衡,而从不用人为的强制方式破坏这个过程的本来面貌[10]98。《香玉》篇中的两处关键情节,正是对这个道理的生动阐释:故事开头就提到生长在下清宫里的“耐冬高二丈,大数十围,牡丹高丈馀,花时璀璨似锦”,展现了花木在自然中生长的优美体态。而牡丹被即墨蓝氏掘移至家后,就“日就萎悴”了。同理,黄生想移植重生的香玉归家,以免再生祸患时,香玉亦劝阻道:“物生各有定处,违之反促年寿”,字字在理。同时,道教教义中也有教人珍爱自然,不要无辜伤害生命的。意在让世人有限的个体生命能与生生不息的自然之道合一共融,实现其对自我心性的超越[10]99。在《成仙》中,“异彩之禽,驯人不惊,声如笙簧,时来鸣于座上”这句话以神奇夸张的笔调,描写了珍禽异兽见人不惊,愿与人同坐的景象,暗含着人善待自然,与自然和谐相生的道理。
《香玉》、《成仙》在一定意义上书写的都是崂山仙境实存的景物,我们可以称其为“现实物”。而《劳山道士》中道士与二客共饮一段,当中所出现的物,皆由道术幻化而成,可以称其为“道化物”,如剪纸为月、壶酒不绝、掷箸化美等。可以看到,“道化物”是对现实事物的“化”,即生于现实物(纸、筷子),又对现实事物有所超越;虽是虚幻的,却又能体现现实物的功能作用。“夫道本虚无,因恍惚而有物。”道教的哲学思维是动态思维,其核心就是这个“化”字,宇宙由“道”而化为万物,人得道而羽化成仙……没有“化”,道教的很多东西都无从谈起[1]327。再仔细研读便可发现,整个故事中除了王生是有来历的,道观和道士都没有名号。从这个层面上可以说,道观和道士也是崂山仙境道气的“道化物”,崂山的物都有特有的精神性依归,即归于“道”。
(四)空间——超越中见“神圣”
道教对于修行空间的言说,具有“世外”的神圣特质,体现在道教建构中神仙居住的地方叫作仙境,人修炼成仙的地方称作洞天福地。崂山空间作为崂山篇目中包罗最多事物的存在,其构建本身由文字承载,有其“虚化”性,是作者的文学想象,从中更隐含着从“器”空间到“道”空间的转化与超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11]797有形的器用之物组成了崂山的第一层空间即“器”空间,故事中崂山外人听闻到崂山的“神异”,看到虚幻道术中的美酒、美人、美景和加诸于人身的种种奇相而欣之、羡之,所涉的都是这一层空间。“器”空间是通过“道化”的途径升华为“道”空间的,而崂山空间的“道”空间是“不可说”的,充分彰显了大道无形,或许我们只能从故事里崂山高道那淡然少言、笑而不语的风姿中窥探一二。大道的“无形”落实到空间上,也说明了“道”空间是“有其虚”的。在这种“虚”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12]96,无形才变化为有形。蒲松龄在《会天意》序中也认为,最初的天地是“空空静静,冥而守之,与元始合其真”,天地的形成是“太乙之精,孕而为气,一气熏蒸,温良初判,二气交旋,结而成形;形结为山海大地,气耀为日月星辰。”[13]30,可看作是对此“道”之理的认同。也只有在超越了“器”空间的“道”空间里,神仙才能居其中,空间中的一切事物才有其神圣化的一面,这是上文的人、仙、物都不具备、不能给予崂山的。人、仙、物也只有在这样的空间中才能与“道”相融无间。由此,崂山仙境形象通过如此的构建,达到了一种纯粹的、理想化的、道化的神圣状态。
二、崂山形象道教化缘由猜想
本文开头即指出,《聊斋志异》中书写崂山的篇目都是道教化的,笔者通过分析篇目中所涉形象也证明了这一点。那么,蒲松龄在书写崂山时偏重其道教化一面,而空缺其佛教化一面,其原因何在?
考察道教在清代的发展可知,道教的信仰在清代转入了萧条,满清统治者在宗教上信仰萨满教,入关后又接受了佛教(7),对道教的信仰则较为缺乏。由史料知,自康熙后,朝廷对道教渐不重视,如“对于张天师,始但许称正一真人,由二品降为五品,后又不许朝觐,令礼部带领引见。乾隆四年,又禁止正一真人传度。”[14]232道教因而流向民间寻求发展,渐渐地与普通民众的生活和信仰融于一体,演变成民间信仰、社会习俗和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对乡土之民的影响比佛教要“大得多,也深得多。”[15]89蒲松龄的家乡淄川,就深受道教的影响,从他文集的一些碑刻和题词中,也可以看出他参与了道教活动。
然而,在道教信仰总体萧条的政治大环境下,崂山道教却拓展了自明代嘉靖以来的中兴局面,尤其以崂山龙门派高道王常月于顺治十三年(1656),“奉旨主讲白云观,赐紫衣,凡三次登坛说戒,度弟子千余人,道风大振。”[16]717为代表。回溯崂山历史,道教的信仰就盛于佛教(8)。从周至元编《崂山志》中记载崂山可考的道观、释刹、仙道、高僧来看,道教在质量和数量上都远胜于佛教。且崂山道观修真庵在康熙十年时仍得到过重建[17]117,正是蒲松龄游崂山的前一年。蒲松龄在康熙十一年与七人同游崂山,唐梦赉《志壑堂杂记》中有简略记载:“壬子之夏,游劳山,见海市。时同行八人。初宿修真观,历上清、下清庵,登八仙墩,水尽山穷,连天一碧。再宿青玉涧,观日出。”[18]323可以知道一行人途经了修真庵、上清宫、下清宫等道观,而文字中并未提及佛刹。由此可推知,《聊斋》中崂山篇目的书写,是受到了蒲松龄游崂实际情况的影响,但文字记载过于简略,途中所遇所见,亦不能妄下断言。不过,蒲松龄对崂山的书写,落实在具体篇目中,确实是全盘道化的。我们可追问,这是他的无意为之,还是自觉构筑呢?
自名为“留仙”的蒲松龄自幼喜读《庄子》、《列子》,深爱庄列恢诡谲怪的文风,认为“千古之奇文,至庄、列止矣。”[13]26但对于庄列之欣赏,并不直接等同于对道教的完全认同。蒲松龄对道教的推崇,表现在现实生活中,他是个“天性伉直、不阿贵显”[6]283的人,这与道教教义中贵清主静、全性保真的思想相契合。同时,蒲松龄一生不得志,道教与道士在他身心困顿之时,不失为医治他精神创伤的一剂良药。蒲松龄本人即与平江道士沈坚白交好,认为他“瘤然而形清,端然而净莹,洒然而出尘也。……超然有卓识,浩乎莫测其津涯。韵士也,抑逸人也!”[19]37而道教中的法术、神鬼之类,对佛教而言皆是“邪伪”,是“惑乱心生,迷于体性”[20]475-476的。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称自己“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6]275,这就与佛教的精神相背了。蒲松龄对佛道两家的态度反映在《聊斋志异》的人物形象塑造上,可以看到道士大多善良仁慈、惩凶扬善,而与之相对,僧人则大多是恶僧、凶僧[21]93-94。其实,蒲松龄对于真正的佛教教义是不排斥的,《聊斋》和《聊斋自志》中也不乏对“六道”、“业”、“恒河沙数”等佛教概念的运用。但作为一位有气节的文士,蒲松龄希冀的是佛门的纯化和净化,而当时佛教与统治阶级的权力挂钩,僧侣中不乏追求“酒、色、财、气”的现象,而道教因为深入民间,反而更显其“纯粹”。因此,蒲松龄在《聊斋》中对道士大加赞扬,而对僧侣更多的是进行辛辣讽刺。
事实上,道教直接影响到《聊斋志异》的笔墨文体(包括行文布局、文字风格、语气措辞等),其启迪性当不可抹杀。由此可溯至庄子之文——清人赵起杲称《聊斋》“其事则鬼狐仙怪,其文则庄、列、马、班。”[6]313而就崂山篇目来谈,蒲松龄已自觉将庄子汪洋肆恣、微言见义的书写方式融于奇异故事中,其中也连带着对庄周之梦的重新演绎。在庄子那里,梦是一个有意创制的发言媒介,也是他阐发“大圣大觉”与“愚人不觉”思想的方式。《齐物论》云:“……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而愚者自以为觉,窃窃然知之。”[22]54在此,“庄子离开梦的原意而取其比喻意,即把人生喻为一场大梦,把看不透人生的人称为不觉的愚者,把能看透人生的人称为大觉的圣人。对于前者,庄子讥其‘自以为觉’,批评他们斤斤计较于什么君臣、利害、生死,都不过是一种固陋的偏见,对于后者,庄子则赞其为万世一遇的楷模,要人们效法之。在两相对照下,阐发其爱恶褒贬。”[23]22据此而观,崂山篇目中的故事不也正是这样吗?崂山空间因其文字构造与神圣性质,与梦之虚幻性有相通之处,其中的人、仙、物,不正是蒲松龄对庄子梦之世界的化用吗?故事中亦有周生入梦、绛雪借梦传话的情节。而崂山中人与崂山外人的两相对照,亦是对“大觉”与“不觉”的形象演绎,尤以周生及王生为代表。但蒲松龄所处的时代、面临的问题与庄子终归不同,他对于王生、周生这样认识不到自己的人并没有给予尖刻的批判,而是在逗笑、自问的话语中弱化了这种倾向,其中饱含着对世人深深的关切与同情。正如松龄之子蒲箬所说:“(《聊斋》)可参破村农之迷,而大醒市媪之梦也……其救世婆心,直将使男之雅者、俗者、女之悍者、妒者,尽举而匋于一编之中。”[6]282再联想其艰辛一生,不禁让人唏嘘(9)。
三、结语
《聊斋志异》是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集大成者,其中的崂山篇目呈现出道教化的单一倾向。蒲松龄自觉从道教中汲取营养,加之以丰富的艺术想象与奇诡笔法,书写出崂山外人与崂山中人由“神异”转向“神仙”的不同面孔、崂山女仙不染尘俗的神格风度、崂山之物超脱现实的玄妙、崂山空间“有其虚”的“神圣”特质,最终建构出一个以“神异”、“神仙”、“神圣”为特征的崂山道教语境,“虽事涉荒幻,而断制谨严……非漫作也。”[6]286在崂山的视野中,诸多关于《聊斋》、关于蒲松龄的问题都因其具象化而更加凸显。据此我们也可以追问:在《聊斋》涉及的其他空间域中,是否也存在着这样统一严整的构建,它因何而生,又是怎样的形态?此疑问,正有待于有识者思之、察之、省之。
注释:
(1)关于此称号于何时获得,史籍并无明确记载。白如祥认为随着明嘉靖、万历年间崂山全真道的中兴,宫观大兴,此称号遂于此时获得,见白如祥:《明清山东全真道概况》,牟钟鉴等:《全真七子与齐鲁文化》,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第309页;任颖卮在《崂山道教史》中亦主此说,见任颖卮:《崂山道教史》,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第44页。
(2)《聊斋志异》中还有《海公子》、《罗祖》、《安期岛》等篇都与崂山有渊源,但并未直接提到崂山,因此本文不做讨论。
(3)《云笈七签》中有云:“欲求无为,先当避害。何者?远嫌疑、远小人、远苟得、远行止;慎口食、慎舌利、慎处闹、慎力斗。常思过失,改而从善。”见张君房:《云笈七签》,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年,第329页。
(4)老子《道德经》第八章有云:“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见释德清:《道德经解》,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3页。
(5)道教的神仙谱系十分繁杂,除尊从天神、地祇外,也尊从关羽岳飞等人鬼之神。
(6)道教传习不避女子,女道士称道姑,世称女冠。崂山也不乏女道观。唐明两代,均有公主妃子出家入道,如明朝末年宫廷妃子蔺婉玉、养艳姬等就先后在崂山出家。
(7)佛教对清统治者的影响深远,如顺治帝笃信佛教,册封达赖,他是清朝历史上唯一公开皈依禅门的皇帝,允许满族人出家当僧人,“无论男女,皆可随意”。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下)》,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169页。
(8)崂山素以道观著称。宋太祖为华盖敕建道场,而官观始立。嗣后王重阳之徒邱长春、李志明踵事增修,益臻完美;一时有九宫八观七十二庵之多,诚极盛矣。元明以迄于今,虽其间迭有废兴,而道现之存于焉未替。惟佛刹除华严一寺足称庄严,禅刹余不甚盛,而海印寺之旋筑旋废,洵二崂之一大憾也。见周至元:《崂山志》,济南:齐鲁书社,1993年,第82页。
(9)蒲松龄从道教启迪中生发出新的创造并不局限于此,与他总体的文化、信仰等是联结在一起的。单以本文篇幅,不能一一展开,仅能具体就崂山形象做出分析与把握。
[1]吴九成.《聊斋志异》与道教[J].蒲松龄研究,1995,(3).
[2]黄洽.《聊斋志异》与宗教文化[D].济南:山东大学,2005:51.
[3]杨柳桥.庄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29.
[4]王利器.道教问答·序[M]//朱越利.道教问答.北京:华文出版社,1989:2.
[5]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802.
[6]朱一玄.聊斋志异资料汇编[G].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
[7]但明伦.《聊斋志异》新评[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5.
[8]杨桂婵.《聊斋志异》与道教神仙信仰论析[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03:4,26.
[9]周至元.崂山志[M].济南:齐鲁书社,1993:90.
[10]毛丽娅.道教生命观与自然环境[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8).
[11]陈玉森,陈宪猷.周易外传镜诠(下)[M].北京:中华书局,2000:797.
[12][明]释德清.道德经解[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96.
[13]盛伟.蒲松龄全集[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
[14]傅勤家.中国道教史[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9:232.
[15]刘笑敢.道教[M].陈静,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89.
[16]完颜崇实.昆阳王真人道行碑[M]//李养正.新编北京白云观志.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717.
[17]苑秀丽,刘怀荣.崂山道教与《崂山志》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117.
[18]唐梦赉.志壑堂杂记:卷8[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323.
[19]路大荒.蒲松龄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37.
[20]释延寿.宗镜录[M].北京:北京广化寺印行,2005:475-476.
[21]陈庆纪.从《聊斋志异》看蒲松龄宗教观的价值取向[J].蒲松龄研究,2001,(2):93-94.
[22][明]释德清.庄子内篇注[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54.
[23]傅正谷.中国梦文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22.
编辑:鲁彦琪
On the Description of the Image of Laoshan Taoism inStrangeStoriesfromaChineseStudio
LIANG Siyua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Guangxi University,Guangxi Nanning 530004,China)
The chapters about Laoshan are all Taoism inStrangeStoriesfromaChineseStudio. Through building a four-layer structure of Laoshan people, immortals, objects and space, Pu Songling presented different images of Laoshan characterized by “Mystery”, “Immortals” and “Sacredness”. In the chapters about Laoshan, Pu Songling laid stress on Taoism but lost sight of Buddhism, which revealed the reality of “the rise of Taoism and the decline of Buddhism” and the new creation of Pu Songling himself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aoism.
StrangeStoriesfromaChineseStudio; Laoshan; Taoism; Pu Songling
10.3969/j.issn.1672-0539.2016.06.016
2015-11-30
梁思媛(1992-),女,广西桂林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化批评研究。
B958
A
1672-0539(2016)06-008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