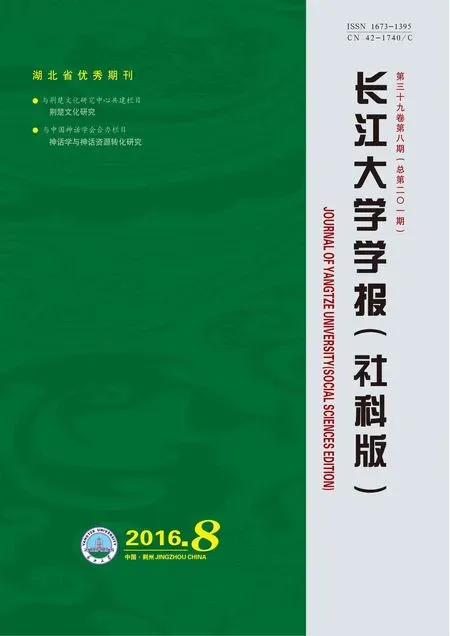内省与超越:宋代士人的价值取向
2016-03-23袁咏心
袁咏心
(长江大学 期刊社,湖北 荆州 434023)
内省与超越:宋代士人的价值取向
袁咏心
(长江大学 期刊社,湖北 荆州 434023)
宋代文化的全面繁荣,与宋代士人主体意识的高扬息息相关。在理学风行,禅学大盛,赵宋皇室重文轻武的时代背景下,宋代士人在从“外王”转向“内圣”,从“平天下”的追求转向“修身”趋向的同时,重新开启了返身向内,审视自我价值的门径。在内省意识的自觉张扬中,宋代士人不断提升其反思能力,走上了一条既超越前人,又超越自我的自觉之路:在承传传统中不断开拓以超越前人,在内心营构的理想境地中放飞心灵以超越自我。宋代士人这一自觉的价值取向,不仅深深地影响到了后世士人的审美倾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整个封建社会末期的文化走向。
宋代士人;内省;超越;价值取向
在中国文化史上,宋代文化是一个特殊的存在。这不仅因其文化之盛,远迈前代,诚如朱熹所谓“国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1](P291);更因“从文化形态上来说,宋代是中国历史‘近世’的开端”[2]。特定背景下发展成熟起来的宋代文化,以其特有的繁富多样,精致内敛,迥异于唐代文化的奔放磅礴。在这一文化转型过程中,宋代士人的价值取向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由唐代士人的汲汲于世功,一变而为内省与超越。宋代士人的这一价值取向,不仅深刻地影响到了宋代文学的品格,使其由唐之前的以进取为雅演化为以退隐为雅;而且也深深地影响到了此后的文学思潮,由苏轼开创的以出世为武器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经由李贽、汤显祖一直延续到曹雪芹,贯穿了整个封建社会末期。从这一意义上说,探讨宋代士人这一价值取向的成因及其具体表现,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宋代文人的审美情趣、宋代文学的独特面貌,亦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整个封建社会末期的文化走向。
目前,学界有关宋代士大夫精神的探讨,大抵集中于宋代士大夫先忧后乐的入世情怀[3],亦或“以天下为己任”的伦理精神[4]上;而对其经由理学的涵养,从“外王”趋向“内圣”时所引导的内省意识,以及在承袭前人基础之上迥异于前人的超越精神等的相关探讨,尚未之见。有鉴于此,本文拟探讨宋代士人内省精神的形成,及其超越的具体途径,以更为深入地考察宋代士人的价值取向。
一
内省本为儒家的道德修养之法。《论语·学而第一》:“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5](P9)郑注以“省”训“察”:“思察己之所行也。”[5](P9)《孟子》则称其为存心:“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6](P595)焦循曰:“盖以在为察,在心即省察其心。”[6](P595)这里的“省察其心”,显然是以仁为前提,以敬为旨归,即《大学》所言之正心,而“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7](P3),“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7](P5),故程颢直承其言,以诚敬二字径代内省:“诚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则诚。”[8](P61)本文所言的内省,则为本于上述相关含义的拓展:既指一种基于诚敬的自我审视的道德观,也指一种本乎察己的俯仰世间的方法论。
宋代士大夫内省道德观的张扬,得益于理学的日渐涵养。由周敦颐、张载、邵雍、二程创立的理学,本为传承于子思、孟子一派的心性儒学。其在高扬儒家人伦礼法的过程中,使儒学更为心性化。在理学家眼中,许多哲学范畴如天、命、性、心等,均可统于理的范畴予以诠释。这些哲学范畴均服从于理,并体现了理的存在,所谓“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8](P99)。毫无疑问,天命也好,性理也罢,所有这些哲学范畴,实乃出自理学家对人类一切活动的认知,即本于人之心,此即所谓“心即性也……天下更无性外之物”[8](P99)。由此而言,在某种程度上,对“心”这一哲学范畴的强调,可以视为理学建构其哲学体系的基点。惟此之故,理学家在建构其哲学体系时,都不约而同地强调了心的作用。周敦颐重养心,为此,其专作有《养心亭说》一文,曰:“养心不止于寡焉而存耳,盖寡焉以至于无。无则诚立、明通。诚立,贤也;明通,圣也。是圣贤非性正,必养心而至之。养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9](P52)在《孟子》“养心莫善于寡欲”[5](P1017)之说的基础上,周敦颐进一步申发,不仅将其推进到“无”的极致,且在养心与圣贤性正之间直接划了等号。张载则推立心:“未知立心,恶思多之致疑;既知所立,恶讲治之不精。……求立吾心于不疑之地,然后若决江河以利吾往。”[10](P376)在张载看来,唯有立心才能精一,而立心的根基则在于不疑,即“存意之不忘”[10](P376)。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张载发出了振聋发聩的时代最强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10](P376)这一承载理学家之庄重使命,彰显宋代士人之高迈情操的响亮口号,正建基于立心之上。二程则推重静心。在二程看来,明理的首要之患,在于“学者心虑纷乱,不能宁静……学者只要立个心,此上头尽有商量。得之于心,谓之有德”[8](P72)。其静心主张,与其诚敬之说一脉相承。延至朱熹,则承袭以上诸子之说,以求放心为省察工夫:“学者为学,未问真知与力行,且要收拾此心,令有个顿放处”[11](P201),“学者须是求放心,然后识得此性之善”[11](P203)。在朱熹看来,为学之道之所以在求放心,是因为“自古圣贤皆以心地为本。圣贤千言万语,只要人不失本心。……心若不存,一身便无所主。……人只有个心,若不降伏得,做甚么人”[11](P199);而求放心的前提则是存心:“存得此心,便是要在这里照常照管。若不照管,存养要做甚么用!”[11](P203)在朱熹这里,存心便是涵养之功,所谓“平日涵养之功,临事持守之力。涵养、持守之久,则临事愈益精明”[11](P204)。在朱熹看来,只有在涵养的基础上存心,进而求放心,才能最终达至“存天理,灭人欲”的境地,亦即达至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从周敦颐的养心,到张载的立心,再到二程的静心,直到朱熹的求放心,我们不难看出,在理学的演进过程中,对心的重视,贯穿了宋代理学的始终,而宋代理学对心的重视,又与元典时代的儒家内省精神一脉相承。换言之,无论养心、立心,还是静心、求放心,如若舍弃了自我省察的道德观照,都是不可能完成的。由是之故,随着理学的日趋发展,宋代士人的内省道德观便得到了不断的强化。
而作为方法论的宋代士人内省观的形成,亦与时代风气息息相关。宋代禅学大兴,理学也借助了禅宗的修炼之道,成为一种“渗透禅机的新儒学”[12](P147),而其所倡导的“凝神静气、摒弃杂念,达到内心通透、感悟天理的修养方法,与禅宗所倡导的如出一辙”[12](P150)。禅宗本是一乘顿教,由佛陀“以心传心”[13](P25)而来,以顿悟佛心为宗旨,明见自心佛性为依归。禅宗所谓的自心佛性或心性,又称本心,所谓“唯有一心,故名真如”[14](P82)是也。其显现为世间出世间一切法。五蕴、六入、十八界乃至戒定慧,皆从本心起用。而本心只可自见自悟,即裴休《黄檗断际禅师传心法要》所云“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因此,禅修之人,“但用此心,直了成佛”[13](P4)。从二祖慧可的求安心,到六祖慧能的用此心,再到周敦颐的养心、张载的立心、二程的静心、朱熹的求放心的演进过程中,我们不难见出理学与禅宗心法的一脉相承。如果说,禅宗拓展了庄子“乘物以游心”[15](P160)的认知法门的话,那么,理学则在其演变过程中,不断地强化了宋代士人返身向内的意识,使“务外游,不如务内观”[16](P128)日益成为宋代士人的自觉。这一过程,又与宋代“内圣”经世路线的高扬相呼应。“在原始儒家那里,内圣外王是真正的儒者应该身体力行的奋斗目标。从秦汉以降直至宋初,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们的赫赫武功盛极一时,相比之下,‘内圣’之学偏于晦暗”,“理学的产生使‘内圣’的经世路线得以高扬”。[12](P152)唐宋间所发生的这种变化,与宋代的重文轻武政策息息相关。赵宋皇室惧武将专权,于是防备武将,重视文官,最终致使其军力不振,在对外战争中屡受重创。这种“外王”受挫,使得宋代士人想像唐代文人那样“勋业在临洮”[17](P246)变得不可能,于是,宋代士人转而“内圣”,即从“平天下”的追求转向“修身”的趋向。这一价值取向的转变,在促成理学风行的同时,为宋代士人再次开启了一条重新审视自我的门径,最终使内省观得以凝练为宋代士人观照世界的方法论。
二
内省意识的自觉张扬,使宋代士人在自我审思中,不断地提升了其反思能力。这一反思能力,不仅体现在宋代士人对以伦理为本体的哲学体系的建构中,更体现在其自我实现的人生追求之中;而当宋代士人以自我实现作为其人生的基本设定之时[18](P318),“孔颜乐处”的推崇,理想人格的鼓吹,便自觉地涵养了宋代士人放眼宇宙的博大胸怀,锻造了宋代士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使其由此走上了一条超越前人并自我超越的自觉之路。
宋代士人对前人的超越,体现于其对历史的反思以及对传统文化的承传与开拓上。宋代士人反思历史的最为直接成果,便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的诞生。这部由北宋司马光主编,历时19年编纂完成的294卷编年体史书,是继《春秋》之后,中国最重要的编年体史书。其叙先秦至宋前长达1362年的中国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及反思,以为统治者提供镜鉴。在《资治通鉴》的直接影响下,李焘撰成中国古代私家著述中卷帙最为浩繁(原本980卷,今存520卷)的断代编年史《续资治通鉴长编》,断自宋太祖赵匡胤建隆,迄于宋钦宗赵桓靖康,记北宋9朝16年事;而袁枢则改易《资治通鉴》撰写方式,撰成汉民族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通鉴纪事本末》。由《资治通鉴》引发的这股反思历史的风潮,在成就宋代史学辉煌的同时,也带来了宋代文化的全面繁荣。在对唐诗以诗为诗的深刻反思中,宋代文人上承《诗经》自然艺术的本色,接续《楚辞》人为艺术的传统,高扬“以文为诗”的创作理念,使宋诗得以成为相较于《诗经》、汉乐府而言的更高层次的自然艺术。宋诗创作理念的这一转变,又直接催生了宋词的繁荣。宋人“以文为诗”的创作理念,使诗溢出了词,继而又溢出了曲。词、曲就其实质而言,本就是“以文为诗”的特殊形式,加之由于传统审美思潮的惰力,其一直不被传统文人承认为诗,而成为“别是一家”的文学体裁,因此,词与文的联姻——“以文为词”便成为必然。宋人的这一努力,不仅使词更切合风雨飘摇的时代际遇,更能表达文人的内心世界,真正意义上做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19](P108),且极大地提升了词品,终至使宋词成为能与唐诗相提并论的“所谓一代之文学”[20](P1)。除此之外,宋代文化之所以能取得这些超越前人的成就,也与宋代士人对传统文化的承传与开拓紧密相连。太宗不仅组织文臣校订《五经疏义》《史记》《汉书》《后汉书》等经史群书,并编纂了大型类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真宗则子承父志,又编定了《册府元龟》。“宋汇部四大书”的问世,在将中国类书编纂规模推向空前繁荣的同时,也为后人的相关研究保存了重要的资料。此外,我们所能读到的宋以前的总集、别集,亦多含宋人的收集整理、校勘笺注之功,如欧阳修、苏辙、范处义、王质、吕祖谦、杨简、魏了翁等都有论《诗》注《诗》专著,而朱熹不仅有20卷《诗集传》,且有8卷《楚辞集注》行世;此外,乐史裒集有《李翰林集》、苏舜钦编有《老杜别集》、王洙编有《杜工部集》、方崧卿校正了《韩昌黎文集》,等等。很显然,如果没有宋代士人本于内省的历史反思,以及由此而来的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就不会有宋代士人对传统文化的自觉承传;而宋代士人在自觉传承传统文化时的这一开拓之功,更使宋代文化在泽惠后人的同时,全面超越了前代。
如果说超越前人是宋代士人的内在追求的话,那么,超越自我则是宋代士人的必由之路。这是由宋明理学所具有的“为己之学”的本质所决定的。宋代士人的自我超越,与前人一样,也指向心性的自由与解脱,但在超越路径的选取上,宋代士人却与前人有所不同。在追求人格自由的过程中,宋代士人既没有选取庄子、陶潜式的辞官归隐之路,也没有因袭王维式的亦官亦隐之道,更没有效法李白式的求仙之举;而是巧妙地出入于儒释道之间,在内心深处,营造出一方属于自我的理想净土,以此寄顿自我灵魂,进而超越现实的苦痛。苏轼所选取的,正是这一自我超越之路。苏轼早年“奋厉有当世志”[23](P1117)。乌台诗案后,苏轼深刻地反省了前期的生活道路:“谪居无事,默自观省,回视三十年以来所为,多其病者,足下所见皆故我,非今我也。”[22](P1432-1433)于是,其精神寄托的对象,从名利事业而暂时转移到了东坡,并开始重新评价人生的意义,而其对人生、社会问题的认识和思考,最终归结到了“人生如梦”四字之上。这一人生归结,不仅是苏轼黄州时期作品的主旋律,也是苏轼整个后期作品的主旋律。对于苏轼而言,梦幻已不再是补天济时的幻想,而是返归虚无、皈依大自然的陶然一醉:“身外傥来都似梦,醉里无何即是乡。”[24](P476)由于苏轼前期的儒家进取精神实在太过强烈,因此,其一生都不可能完全忘却兼济天下,也不可能完全归隐。于是,苏轼从儒家的内省出发,以庄禅之游心为依托,引陶渊明为同道,选取了一条托身现实,寄心梦幻的自我超越之路。其所着意营造的梦幻之境有二。一为其意念中的黄叶村:“扁舟一棹归何处,家在江南黄叶村。”[23](P1525)有关李世南所画《秋景》图,宋人邓椿在《画继》中提及,李世南之孙李皓曾告知作者:“此图本寒林障,分作两轴。前三幅尽寒林……后三幅尽平远,所以有黄叶村之句。”[25](P40)由此可知,黄叶村并非实有村名,而是苏轼虚构出的理想所在。一则为其梦幻中的仇池:“至扬州,获二石。……忽忆在颖州日,梦人请住一官府,榜曰仇池。”[23](P1880)而仇池本为道藏所言通昆仑山之道,非人间实有,故此,其乃苏轼所着意营造的梦幻之境无疑。从此以后,“我坐华堂上,不改麋鹿姿”[23](P1885),就成为苏轼自觉的人生追求。需要指出的是,苏轼最终的这一价值取向,应该还受到了韩愈的影响。韩愈“既排斥佛老又出入佛老的双重品格直接影响到宋明理学的架构”[12](P146),而苏轼更明言与韩愈身世相类:“退之诗云:‘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乃知退之磨蝎为身宫,而仆亦以磨蝎为命,平生多得谤誉,殆是同病也。”[26](P44)由此而论,其步武韩愈,在承续儒家道统的同时,悠游于佛老之间,以寻求自我超越之道,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在内省中走向超越的苏轼,以其自身的杰出成就与人格魅力,得以成为宋代文化最为伟岸的一座丰碑。苏轼与宋代其他杰出士人所共同开创的这一内省与超越之路,不仅给宋代文化烙上了特殊的时代印记,自此而后,士人主体价值的极力张扬,以及对带有士大夫情致的风雅品格的追求,便成为宋代文化的主旋律;而且,其更在深深影响后世士人审美倾向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整个封建社会末期的文化走向。惟此之故,在中国文化史上,宋代文化才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
[1]朱熹.楚辞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2]谢贵安.从宋明时期家庭经济的经营看中国文化的转型[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1).
[3]诸葛忆兵.宋代士大夫的境遇与士大夫精神[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1).
[4]王泽应.宋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伦理精神述论[J].道德与文明,2015(4).
[5]刘实楠.论语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90.
[6]焦循.孟子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
[7]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8]程颢,程颐.二程遗书[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
[9]周敦颐.周敦颐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0.
[10]张载.张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8.
[11]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2]冯天瑜,杨华,任放.中国文化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13]坛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14]普济.五灯会元[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5]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1.
[16]杨伯峻.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7]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8](美)杜维明.杜维明文集(第3卷)[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2.
[19]刘熙载.艺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0]王国维.宋元戏剧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0.
[21]苏辙.苏辙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0.
[22]苏轼.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3]王文诰.苏轼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4]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
[25]邓椿,庄肃.画继·画继补遗[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
[26]苏轼.东坡志林[M].北京:中华书局,2007.
责任编辑 韩玺吾E-mail:shekeban@163.com
Introspection and Transcendence: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Scholars in the Song Dynasty
Yuan Yongxin
(PeriodicalPress,YangtzeUniversity,Jingzhou434023)
The overall prosperity of the Song Dynasty cultur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main body of the Song Dynasty scholar in consciousnes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popularity of neo-Confucianism and Chan,stresses the civil arts over the military arts in the Song Dynasty,the Song Dynasty scholars from “positive in actions” to “virtues in mind ”,from “the land great governed” to “self-cultivating” at the same time,re-opened turned inward and examine the self-value method. In the conscious publicity of introspection consciousness,the scholars of the Song Dynasty constantly improve their ability to reflect on the past,walking on a path that is not only beyond the previous,but also beyond self:In the inheriting tradition constantly open up to go beyond the previous,in the ideal situation of the self-inner construction flying the heart to go beyond the self.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scholars in the Song Dynasty not only deeply affected the aesthetic tendency of the later scholars,but also to a certain extent,it affected the cultural trend of the end of the feudal society.
the scholars of the Song Dynasty;introspection;transcendence;value orientation
2016-06-18
袁咏心(1984—),女,湖北大冶人,硕士,主要从事国学研究。
I207.22
A
1673-1395 (2016)08-008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