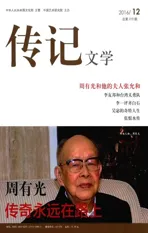周有光和他的夫人张允和
2016-03-22文|屠岸
文 | 屠 岸
周有光和他的夫人张允和
文 | 屠 岸

1953年,周有光、张允和夫妇在苏州
中国当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大师周有光,是我的表嫂(我的表哥屠模的夫人)周慧兼的弟弟,生于1906年1月13日。屠、周两姓都是江苏常州的望族,我们两家过从甚密,亲如一家。我称周有光为“有光大哥”,他比我大17岁,但是和我同一辈分。有光大哥的妻子张允和,是沈从文的妻子张兆和的姐姐,我称她为“大姐”。有光有一次忽然问我:“你是我的长辈吧?”我说:“不是,是小弟。”
1946年3月10日,在上海,我到当时英租界亚尔培路昌厚新村4号去向我的姻伯母、即有光的母亲拜寿。告别时我说:“耀平哥,你别送了。”有光本名周耀平。他还是送我出了大门口。那时我22岁,他39岁。他仪表堂堂,倜傥潇洒而又风流儒雅。
有光曾告诉我,他研究语言文字学是出于爱好。有一次,我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徐志摩译诗集》带了去,请有光看徐志摩译英国诗人柯勒律治(S.T.Coleridge)的诗《爱》(Love)的第二节。其中,徐志摩把When译成“其寺”,是把“其”和“寺”合起来新创的字,意思是“其时”,即“那时候”。有光很感兴趣,把徐的这首译诗抄了下来。他说,这种自创的汉字,公开印出来的很少。可能有人造字,但不一定能见天日。

1977年夏,周有光、张允和夫妇在北京景山前街
每次到有光家,他对我总是非常热忱,总要留我吃饭。2001年2月的一天我去他家,那时有光95岁,允和大姐92岁,但从外貌看,两位只像六七十岁的人。允和拿出通讯录,翻开一页,是屠姓亲戚的地址,上面有屠岸、章妙英的地址,只缺电话,我填上了。她问起我的妻子妙英的消息,我说,她已于1998年故去。两位叹息。
那天,允和赠我三本书,有光送我一本书,并说另外还有一本要等再版后送我。这些都是他们的著作。
不久,我收到了有光赠我的那本书,上面扉页上有题字:“屠岸大哥指正 周有光2001-2-23。”此外还有一封信:
屠岸大哥:
驾临小谈,屋内欣快!
我还只看了您的译诗的一小部分,就钦佩得五体投地!我要慢慢看,每天看一小部分,细细咀嚼。
这里送上拙作《比较文字学初探》,请指正。这本书已经作为北京两所大学的教材。这是一个国内的缺门学科。
目前胃肠道微生态与AP的关系在动物模型及人体的研究中报道偏少。虽有在人体中补充胃肠道微生态治疗AP的报道,但缺乏前瞻性的研究。
敬祝
健康、快乐!
周有光2001-2-23
信是用电脑打字,而在打字的“周有光”三字上面,还有一个手迹签名。“五体投地”显出他的幽默,“请指正”暗含着诙谐。称我为“大哥”,更奇!他比我大17岁。从这本《比较文字学初探》就可见这位老人学富五车,我望尘莫及。而他自己说这门学问是大海,这本“初探”只是“一个观望大海的人在海边留下的足迹”。学,然后知不足。学问越多的人越谦逊。
有一次,允和大姐说,怎么屠岸那么久不来了?“你这个老表应该经常来,我们好好聊聊。有许多话要跟你讲。”2001年3月的一天,我早餐后出门去她家。允和大姐起身,见了我即热情洋溢,要我吃早饭,我说已吃过了。她拉我到卧室,说:“不要紧的,你进来!”此时有光大哥还睡在被窝里,允和把他唤醒,他急忙起来,穿衣,下床。他对我说:“你的译诗极好。我每天看一点,可以补补精神。”
允和大姐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是她的开朗、乐观、豪爽的性格。每次到有光家,一进门就听到屋子里充满了允和爽朗的笑声。允和曾跟我说卞之琳先生年轻时追求四妹充和的事,终未成;而沈从文先生当年追求她的三妹兆和成功,有情人终成眷属。当沈从文的求婚得到张家姐妹的父母同意时,她给沈从文发了一份电报,只有一个字:“允”。双关!允和讲到这里,哈哈大笑起来。
允和逝世时,有光96岁。虽然遭遇剧痛,但心态终于渐渐平静下来。他对我说,西方有一位哲人说过,人的死亡是给后来人腾出生存空间,使人类可以生生不息。所以,我们要以平静的心态对待人的死亡。
2005年4月19日,我去看有光,他正在电脑前工作。他热情非凡,让我稍等一分钟。他关了电脑就跟我聊天,聊了一个多小时。我告辞前,请他给我写一句格言以留念。他立即用钢笔在纸上写:“历史进退,匹夫有责。”
我说:“这是从顾炎武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变化出来的吧?”有光说:“顾亭林只提到一个国家,我们的眼光应该放大些,要关注到整个人类。”
2006年,有光送我他的新著《学思集》并题字。这本书卷首印着两行字:“学而不思则盲,思而不学则聋。”有光说,他把《论语》上的原话“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改了两个字——“原来那两个字一般人不认识,哈哈!”
2007年1月6日,我提前一周带着两个双胞胎外孙女到有光家,为他祝寿。这已是多年的惯例,我有时带儿子,有时带女儿,有时带外孙女。这一次,有光满面笑容,神采奕奕。我把带去的花篮送给他,花篮上系着两条红绸带,我事先用金粉写上字,上款是“有光大哥一百○二岁大寿志庆”,下款是“愚表弟屠岸率建、宇、燕、海、霖、露、笛同贺”。我说:“祝大哥百二大寿!”有光笑着看了看花篮和绸带上的字,道了一声谢谢之后,说的第一句话是:“上帝把我给忘了——不叫我去!”他看着我和我的两个外孙女,说:“你是三世同堂。”我连忙说:“您是四世同堂。”因为他已有重外孙。他笑说:“不,我是四世同球。”原来他的孙女和重外孙现居美国,他隔天就用“伊妹儿”和他们通信。
有光曾说,他90岁之前感觉与60岁时无异,精力充沛。过了90岁之后才觉得体力差了。我问他有什么疾病,如高血压、冠心病等,他说没有,能吃能睡能工作(在电脑前),只有耳朵稍聋。因此不能出门,出门要麻烦别人相伴照顾;就更不能出国了,航空公司对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是不提供人寿保险的。
我只要到人文社去,就到“一表五十米”的有光家去看望他。他104岁了,依然容光焕发,神采奕奕,腰背直,脚步稳,仅耳朵有点重听,但不用助听器仍能与人自由交谈,没有半点老迈之态、衰惫之容。这真是个奇迹,难怪他说“上帝把我给忘了”!
2010年4月春光明媚时
写于北京寓所萱荫阁
以上是我六年前写的文章。今年,我又拜访了有光大哥,他已是111岁高龄,身体比过去稍弱了些,但思维依然清晰,精神依然矍铄。据国外某位人类学者称,与世间一切生物(动物)的年龄相比,人的正常寿命应该是140岁到160岁。有光大哥到这个年龄,大有希望啊!
责任编辑/胡仰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