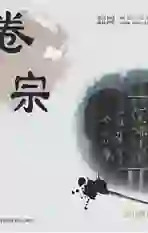中国的人口危机与化解对策
2016-03-21盛蕾
盛蕾
摘 要:人口问题始终是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人口的趋势性变化,能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全面、深刻、长远的影响。当前中国人口形势严峻,人口结构扭曲危机初露端倪。全面两孩的实施效果事关中国发展大业和中国梦的实现,如果失去目前调整人口结构的最后较佳窗口期,中国人口安全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全社会要清醒认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树立新的人口理念,,科学调整人口政策,努力化解人口危机。
关键词:人口结构;人口政策;人口危机;老龄化;少子化;低生育率
我国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这一政策旨在控制国家人口,解决人口过剩问题,但也导致了我国人口危机的出现。进入21世纪,特别是“十二五”时期以来,我国面临异常严峻的人口形势,人口总量增长势头明显减弱,劳动年龄人口和育龄妇女明显减少,老龄化、少子化程度不断加深。这种严峻的人口结构扭曲形势,已危及人口可持续发展和国家人口安全,将对民族前途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造成冲击[1-3]。
1 中国进入“人口危机”时代
(一)人口老龄化急速发展
国际上通常以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来衡量一个社会的老龄化水平[4]。据统计,2014年全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达到1.37亿人,占总人口比例为10.1%。在1990年,中国这一比重只有5.6%,低于世界水平6.2%;2010年,中国的这一比重为8.87%,已超世界平均水平。国家统计局2016年1月1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2.22亿人,占总人口的16.1%;65岁及以上人口近1.44亿人,占10.5%。按照人口统计学标准,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到7%即为进入老龄化社会。可见,中国已经处于深度老龄化阶段。目前每10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是65岁以上的老人,每6个国人中,就有将近1个人年龄在60岁以上。
中国人口的老龄化不仅体现为程度高,还体现为老化速度快。尤其是1960年代第二次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口进入老年后,老龄化更是加速推进。据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2050年,中国将有35%的人口超过60岁,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5-7]。目前,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的比例是15%,在未来数十年内将会直线上升至40%左右。根据联合国人口展望(2012)的相关人口预测,未来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依然将明显快于世界平均水平,世界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从14%升至21%需要50年,而中国只需11年左右。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领衔的研究团队预计,到204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25.62%。这意味着,届时1/4的中国人在65岁以上。到2050年时,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将达到3.75亿人,这个数字超过美国现在全国的人口总数[8-10]。
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预测,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将进入三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人口老龄化急速发展阶段(2015年—2035年),我国老年人口从2.12亿增加到4.18亿,年均增长一千万人左右,老年人口比例由15.5%提升至28.7%。到2035年,老年人口比例将占总人口28.7%。
第二阶段是人口老龄化缓速发展阶段(2036年—2053年),老年人口从4.18亿增加到4.87亿,年均增长380多万人,老年人口比重从28.7%提升到34.8%。在这个阶段,人口高龄化特征明显,80岁以上的高龄人口从0.6亿增加到1.18亿,新增老年人口超过八成是高龄老人。
第三阶段是人口老龄化平稳发展阶段(2053年—2100年),老年人口与其他年龄段人口共同减少,从4.87亿减少至3.83亿,老年人口比重在32%-34%区间浮动,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重度老龄化高峰平台。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有一个和“未富先老”一样重要的特点,就是“未备先老”。所谓“未备”,不仅表现在养老服务体系、养老保障体系等没有准备好,也包括极其重要却在庞大人口总量的表象下常常被忽视的年轻人力资源储备的不足上。我们必须认识到,仅仅有钱不足以保障老年人的需要,还必须有强大的年轻人力资源的支撑,包括创造社会财富的人力,也包括为老年群体提供服务的人力。不久的将来,中国将为“年轻人口战略性储备不足”付出代价。
有人认为,发达国家也进入老龄化社会了,他们不是过得挺好吗?所以人口老龄化并不可怕。但实际上,中国的老龄化与发达国家的老龄化有三点不同:第一,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时,人均GDP一般在5000-10000美元,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有能力解决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而中国在本世纪初进入老龄化时,人均GDP仅1000美元,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大,应对老龄化的能力也大不相同。第二,发达国家的老龄化是逐渐形成的,社会压力也是逐渐出现的;中国的老龄化是短时期形成的,中国只用了20多年就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一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才完成的人口老龄化转变。第三,发达国家的生育率是缓慢下降的,最低时每对夫妇平均差不多有两个子女,而中国实行的是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因此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将比发达国家严重得多,与老龄化相关的各方面问题也会因此而严重得多[11-12]。
(二)少子化的速度超过老龄化
与老龄化相对,少子化是中国人口结构扭曲的另一个问题。查阅国家统计局历年的人口调查数据可以发现,我国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1982年为33.6%,2014年只有16.5%,下降了17.1个百分點。大大低于世界27%平均水平,不仅远低于金砖国家印度的34.0%、南非的32.0%、巴西的28.0%,甚至比美、英、法等发达国家水平还低(美、英、法分别为21.0%、18.0%、18.0%)。同时0-14岁人口总量也大幅下降,1982年为3.4亿人,2014年只有2.2亿人,比1982年减少了1.2亿人。按照人口统计标准,我国已处于严重少子化水平,且少子化的速度超过了老龄化,说明中国人口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潜力堪忧[13-15]。
根据人口统计学标准,一个社会0-14岁少儿人口占总人口比重15%-18%即为“严重少子化”。少儿人口是潜力人口、朝阳人口和希望人口,具有人口的生育潜力、支撑潜力和创造潜力。比较而言,老年人口则是余力人口、夕阳人口和负担人口,潜力随着时间的推延而减少。中国作为刚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发展中大国,合理的人口结构水平应该是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20%-23%,可以测算出需要新增6000万人以上少儿。从当前情况看,即使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也难以实现这一目标。为确保实现十八大提出的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我国人口结构改善目标的底限是,0-14岁人口所占比重应该由现在的16.5%调到18.5%,这至少需要新增3300万人以上少儿。
少子化的危机有别于老龄化,这是两个既彼此联系又相对独立的问题。年轻人口持续亏损,老年人口就会严重缺乏年轻人口的生产性、服务性和依靠性支撑。少儿人口的减少,意味着人口的生育潜力、支撑潜力和创造潜力将受到严重损害(0-14岁人口的生育潜力、支撑潜力和创造潜力将在成年阶段表达出来)。老龄化比重一旦超过少子化,就会形成危险的倒金字塔人口结构,人口关系倾斜、失衡甚至断裂。严重的少子化(0-14岁少儿人口比重低于18%)将使人口失去平衡能力、发展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庞大的人口总量和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将人口少子化问题完全淹没和遮蔽。如果说少子化是人口之本,那么老龄化是人口之末。少子化关乎人口的生机和活力,老龄化则彰显人口的负担和保障。不遏止少子化,老龄化将陷入无解困境。微观上,一些独生子女因为入学、就业或者婚姻离开自己的父母,造成“老年空巢”和“赡养脱离”,儿女养老有心无力,家庭养老形同虚设。宏观上,护理人员、家政人员短缺以及普遍的用工荒已经从不同的方面证实了劳动力转移“刘易斯拐点”的到来[15-17]。
(三)低生育率趋势难以逆转
决定未来人口趋势的关键因素是总和生育率(简称生育率),即各年龄别生育率的总和,可通俗理解为女性平均生育孩子数。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人口要保持既不增加也不减少,总和生育率要保持在2.1,这就是人口学上的世代更替水平。直观来看,年出生人口大致相当于当年的生育率乘上处于育龄旺盛期的年均女性数量。孩子的数量与父母辈持平,意味着生育率处于更替水平。按照人口统计标准,2.1为世代更替水平,2.1以下为低生育水平,1.5以下为很低水平,1.3以下为超低水平,1.0以下为危险水平。如果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人口总量将不断衰减。2010年“六普”后国家统计局对外发布的总和生育率是1.18,统计过程中肯定有漏报,或因“黑户”等原因导致数据误差,经过修正后全国的总和生育率应该在1.4-1.5左右,这远低于2.1更替水平,大大低于世界2.5的平均水平,甚至比发达国家水平1.7还低。
从历史和国际的经历看,总和生育率1.5水平是一个高度敏感警戒线,一旦滑到1.5以下,就进入了低生育率陷阱,很难回升。除了瑞典和法国外,目前还没有别的国家在跌破1.5之后重新回到1.5水平,更没有一个国家回到2.1的世代更替水平。中国的生育率自1990年代初期就一直低于更替水平,年出生人口在1990年代更是直线下降超过40%。目前出生于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的育龄妇女处于生育高峰期,但是2014年出生人口仅增加47万人,几乎没什么反弹,10年前国家有关部门预判的出生高增长量并未出现。2014年1月开始,全国各省陆续放开单独二孩政策。按照事先的预计,2015年,单独二孩的政策效应将明显出现,年出生人口估计会持续增加到1700万,甚至1800万。国家统计局2016年1月19日公布的数据,大大出乎此前各有关机构的预料,2015年出生人口总数为1655万人,比2014年减少32万人。去年出生人口不升反降,说明我国已掉入低生育率陷阱[18-21]。
在未来一二十年,随着生育旺盛期女性数量的急劇减少,中国出生人口将再现1990年代那样的断崖式下跌,可能从目前的约1600万急剧萎缩到1000万以下。中国出生人口已经历了1970年代和1990年代的两次台阶式下跌,现在正在进入第三次下跌。这种趋势从全球比较来看,更是触目惊心。虽然目前中国人口占世界19.0%,但年出生人口仅占世界12.0%,而这还是中国的生育高峰期。在未来十年,中国23~28岁的生育旺盛期的女性数量将萎缩至目前的55.7%,而中国生育率则仅有世界平均的一半。在这两种因素叠加的趋势下,只要一代人,也就是25~30年的时间,中国年出生人口将萎缩到世界的3.3%。即使能幸运地将生育率相对提升50%也只能保持世界的5%。更关键的是,低生育率具有巨大惯性,并不是放开甚至鼓励生育就能恢复正常。即便大力鼓励生育,要把中国生育率最终提升到世界平均水平,可能需要两三代人;等到最终稳定下来时,中国人口占世界的比例可能不足3%。如果不能逆转这种趋势,人口急剧萎缩可能持续达百年之久。
(四)人口“三难”危机将全面爆发
我国是至今全球唯一尚未进入发达经济体就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国家。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受现代化快速推进和长时间实行一胎化为主生育政策双重叠加的影响。在这种双重影响下,人们的生育观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再加上长期低生育率会加重未来社会的老龄化,导致养老负担沉重,育龄家庭不堪重负,这反过来也会抑制生育意愿,降低实际生育率,这又是一个恶性循环。高生育率时,降低生育率马上能缓解压力;但低生育率时,提升生育率短期内却会加大压力。人口学者预计,2020年后中国社会将出现“三难”[15,19-22]。
一是招工难。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大陆16周岁以上至60周岁以下(不含60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91096万人,比上年末减少487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6.3%,较上一年占比又下降了0.7个百分点。2013年,国家统计局将劳动年龄人口的统计范围调整为16~60岁。统计结果显示,16~60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91954万人,比2012年末减少244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7.6%;2014年,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比2013年末又减少了371万人。2012年至2015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连续4年下降,表明我国劳动力供给高峰已经产生并出现拐点,劳动力短缺已拉开序幕。2021年之后,随着1982年后的0-14岁人口大幅减少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三次人口高峰出生劳动力的陆续退出,劳动力供给将急剧下降,中国将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2021年后,20-34岁的青年劳动力将呈悬崖式下降,2022年至2025年4年间,每年将净减1100万人以上,到2030年将比2010年减少1.04亿人、降幅达32%,总量只有2.21亿人。到2030年,20-59岁劳动年龄人口只有7.64亿人,将比2010年时减少6900万人,降幅达8.3%。由于后备劳动力急剧大幅减少,将遇到严重的劳动力危机,中国劳动力缺口将超过8000万人。届时招工难将成为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将促使工资大幅上升、产业竞争力急剧下降,从而制约经济增长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二是养老难。2015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2.22亿人,占总人口的16.1%;65岁及以上人口近1.44亿人,占10.5%。据预测,到2050年,中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4亿,占总人口将超过30%。1966年-1973年,是中国人口生育高峰期,一共出生将近5亿人。意味着到2033年,这5亿人都会变成60岁以上的人口,全部退出工作岗位,再加上2亿的被抚养人口,也就是7亿人被7亿人抚养,这是非常沉重的话题,人口学里抚养比1:1的时代。加上人口的贡献率问题,还要乘70%的系数,也就是其实只有70%的有效贡献率,还有30%的无效贡献率,这时候大约是5亿人在养活9亿人。在目前这种“四二一”家庭结构中,需要赡养老人增多,中青年将不堪重负。尤其是2030年后,届时供养一个老年人所用的劳动力将由目前的近5个演变成2个。面对老龄化提前来临,整个社会从物质到心理等方面都没做好准备,现有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水平低,养老资金缺口较大,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发育严重滞后,社会保障面临相当压力。
三是娶妻难。众所周知,我国男丁情结较严重,和许多亚洲国家一样,中国有重男轻女和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这加剧了人口性别比例失衡的问题。其次,由于我国社会养老机制尚不健全,靠儿养老的传统家庭模式占据一定的社会主流。在正常的自然情况下,出生性别比一般介于103和107之间,也就是说,每出生100个女婴,相应有103至107个男婴。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在1980年代之前基本正常,在1982年为107,但之后迅速攀升,1990年达到111.3,2000年升至116.9,到2004年更高达121.18。一般来说,造成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性别比失衡有两大主要原因:移民和出生性别比失衡。由于我国移民比例很小,中国人口性别比失衡的根本原因是出生性别比失衡。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大陆总人口137462万人,男性人口70414万人,女性人口67048万人,总人口性别比为105.02(以女性为100),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3.51。通过计算,我国男女人口差在2015年已经达到3366万,这意味着约有3000余万的男性人口在面临“打光棍”的局面。到2020年,娶妻难将拉开序幕:以22-26岁代表女性的初婚年龄,以24-28岁代表男性的初婚年龄,到2020年,初婚年龄男性有4900万人,而初婚年龄女性只有3900万人,男比女多了1000万人,只能向低年龄女性中去择偶。由于低年龄段男女失衡持续产生、一直处于高位态势,因此这一问题将非常棘手。或会导致婚姻错位、代际争夺及婚外情、第三者插足、非婚生育、性犯罪、反社会等社会现象增加。娶妻难成为社会和家庭的一个重要难题,易与其他社会矛盾相交织而引发社会动荡。有人认为,女性婚龄人口的短缺,可以通过拉大婚龄差来解决。然而,婴幼儿人口持续下降、性别比持续上扬,这种情况下是根本不能奏效的。因为低龄女性人口本来就越来越少,挤压的结果使低龄男性婚配机会更少,这样婚配竞争会愈演愈烈。
2 人口政策调整迫在眉睫
(一)修复人口结构已步入最后“窗口期”
“窗口期”是一个医学术语,之所以说现在已经进入人口政策调整的最后“窗口期”?是因为中国人口形势异常严峻,但就像感染病毒一样还没被检测出来,现在可能是最后一段尚未顯露的“窗口期”。中国人口发展已进入了关键的历史节点,当前及”十三五”是人口政策调整的最后“窗口期”,修复人口结构、缓解人口危机正与时间赛跑。从大的背景来说,2015年是改革的关键年。补偿性生育是所有改革中一项最大的改革红利,其受益面最广,改革成本又较低,不仅惠及当代,而且泽至子孙,并且将有助于推动其他各项改革。当前人口发展困局也是一个重要战略机遇。如果全面放开二孩后,能够实施积极的鼓励扶持政策,将带来2000万人左右的补偿性生育,将有效改善人口结构,并有效扩大内需,为发展提供新动力,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一招。
现在应该担心的是补偿性生育量太小的问题,而不是生育堆积。如果错过了当前的最后“窗口期”,即使以后鼓励生育,由于育龄妇女急剧减少,恐怕也将于事无补,难以促进人口结构回升到正常水平。但二孩全面放开,并不意味着生育率就会有明显提升。在经济和社会观念快速发展变化之际,年轻一代生育观念已发生重大变化,而购房、医疗、养老和教育等重重压力,更是让年轻人生育意愿和动力大大减弱[3,5]。
(二)姗姗来迟的“全面二孩”政策
提高国家生育率的意义深远,从其他国家的经验而言,人口政策应当有的放矢,寻找恰当的措施方能保证人口红利和劳动力的市场出清。韩国的经验与中国颇为相似,20世纪60年代,韩国人口增长率在2.9%以上,采取计划生育政策后,80年代人口增长率降至1.53%。80年代中期韩国采取更严厉的“一孩政策”,直至90年代末生育率已经降到1.7,彼时韩国的生育率开始持续低迷,政府从控制人口改为维持生育率,可惜21世纪以来生育率仍低于1.5,从此韩国陷入低生育的陷阱,社会老龄化压力非常大。比韩国老龄化更为严重的国家是日本,其65岁以上人口数量是14岁以下人口数量的两倍,占总人口比例达到26%。俄罗斯与日本相同,从二战以来常年推行鼓励生育的政策,然而收效甚小,直至2013年才首次出现人口自然正增长。这些都说明一旦全社会生育率低于某个水平后,再依靠人口政策来刺激增长已有些为时过晚[23-27]。
2015年1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全面二孩政策于2016年1月1日起实施。这意味着,从1978年“计划生育”正式写入《宪法》后,中国的人口政策迎来第一次重大调整。此次调整,不仅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要求,也符合人口结构优化的社会进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全面二孩”放开后,专家预计每年新生儿数量可达1900至2300万左右,从长期而言,这是解决劳动力困境的唯一途径,从短期而言,其蕴藏的消费力每年达到900至1500亿。
全面二孩的实施效果事关中国发展大业和中国梦的实现,如果失去目前调整人口结构的最后较佳窗口期,中国人口安全将面临严峻的挑战。根据最乐观的估算,即使2016年全面放开,但不鼓励生育,从2030到2070年的40年内中国人口将萎缩30%。这种衰减在人类历史上将是空前的。由此可见,当前推进全面放开二孩不是早了,而是已经严重滞后了[22-24]。
(三)全面放开两孩生育后的人口趋势
要预测全面放开生育后的人口变化,需要估算无限制下的、不含生育堆积的自然生育率。假设因为放开限制,在35岁及以下的母亲中,有一孩的人中有80%最终多生1个,7%最终多生两个或更多,平均多生2.5个;有二孩的人中有7%最终多生一个或更多,平均多生1.5个。基于此,35岁及以下女性对“增值”的贡献,在农村不超过0.188,在城市不超过0.204,全国平均应在0.2以下。再考虑到自1980年代以来总和生育率中,来自35岁以上母亲的贡献最高不到15%,加上35岁以上母亲的贡献,放开后的生育率“增值”应不到0.236。上述估算每一步都放宽了。比如,中国近年的各种调查显示,愿意生育二孩、三孩的比例分别都小于上述估算过程中使用的80%和7%[21-25]。例如:2013年11月26日《中国青年报》报道的该报一项调查显示,如果不考虑政策限制,62.5%的受访者选择二孩,5.9%的受访者选择三孩或以上。此外,由于各种原因,实际生育率通常低于意愿生育率。
为确保实现经济新常态、实现十八大提出的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我国人口结构改善目标的底限应是0-14岁人口所占比重由现在的16.5%调到18%,这是一条人口安全红线,这至少需要新增2500多万人口。由于生育观念转变及育儿成本提升,全面放开二孩甚至立即鼓励生育,年平均总和生育率难以由现在的1.4至1.5升到1.8以上,2020年人口总量也难以突破14.5亿人,人口峰值也难以突破14.8亿人。
3 生育政策下一步应该怎样调整?
全面放开二孩以后,我国下一步的生育政策应该怎样调整呢?本着学术研究无禁区的理念,结合部分人口研究者的学术观点,谈几点不成熟的看法,供学术界同行商榷[27-29]。
下一步应该争取用3年时间消化释放二孩生育堆积,并随后立即转向全面鼓励生育。目前真正需要担心的不是放开后出生人数的短暂反弹,而是生育旺盛期的女性数量将急剧萎缩,导致几年之后新生儿数量再现1990年代那样的雪崩。因此,应该趁着现在生育旺盛期女性数量还未开始锐减,立即完全放开生育并尽早鼓励生育。国家要考虑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为《人口发展法》,废除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暂停征收超生子女社会抚养费,研究和借鉴世界各国鼓励生育的措施。要推动社会回复正常的人口观与生育观,特别是对教科书的相关内容进行全面核查和修改,促进科学、健康的生育文化。同时,要把0-14岁人口所占比重由现在的16.5%的严重少子化水平提升到18%以上纳入“十三五”规划目标,并成为“十三五”规划核心战略目标、硬约束目标。也把新生儿性别比向103比107的正常值回归纳入“十三五”规划目标。应该清楚,如果不能在“十三五”期内修复扭曲人口结构,则“十三五”之后由于育龄妇女急剧减少,修复的难度就更大了,这将导致存在难以实现中国梦的重大战略风险。
中国人口危机早已积重难返,要扭转这种人口颓势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强势的决断力、高效的执行力和伟大的历史担当[18,29]。要有危机感,让全社会要清醒认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要树立新的人口理念,破除生育率越低越好、人口越少越好的思维,树立人口是宝贵资源的观念;要树立人口结构优先、兼顾人口数量的发展理念,人口的结构规模要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要与资源环境相协调;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强化人力资源投入,全面提高人口素质;要加大人口形势宣传,形成人口改革社会共识。
参考文献
[1]何亚福.人口危局: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3 年5月第1 版.
[2]王霞. 中国人口结构变动与老龄化问题研究[J].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25(2):66-69.
[3]梁建章, 黄文政, 李建新. 人口危機挑战:中国放开生育刻不容缓[J]. 决策与信息, 2015(4):10-61.
[4]穆光宗. 人口优化理论再探——新人口危机和国家安全[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4):111-122.
[5]刘忠良. 中国崛起与新人口危机[J]. 决策与信息, 2014(10):31-35.
[6]张锐. 老龄化:中国新人口危机[J]. 中国证券期货, 2011(8):80-83.
[7]蔡茜, 向华丽. 我国农村老龄化现状和发展趋势分析--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J].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3(1):99-104.
[8]李军.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及战略选择[J]. 老龄科学研究, 2015(3):73-81.
[9]王桂新.我国“潜在”的人口危机及其应对之策[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2(2):30-39.
[10]宋宝安, 于天琪. 关于规避人口老龄化引发社会危机的思考[C]// 中国社会学会2010年年会——“社会稳定与社会管理机制研究”论坛论文集. 2010.
[11]吴玉韶. 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与应对策略[J]. 中国国情国力, 2015(4):29-31.
[12]穆怀中, 陈曦.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农村家庭子女养老向社会养老转变路径及过程研究[J]. 人口与发展, 2015, 21(1):2-11.
[13]王谈凌, 郝福庆. 适应新常态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J]. 宏观经济管理, 2015(6):7-8.
[14]董晓琳, 王伟平. 后人口红利时代人力资源危机治理研究[J]. 经营管理者, 2014(18):141-141.
[15]穆光宗. 人口少子化是最大战略危机[J]. 中国经济报告, 2014(11):49-51.
[16]杨琳. 中国已步入“少子化”时代[J]. 瞭望, 2012(30):50-51.
[17]陈澍. 中国“少子化”问题初探[J]. 南方论刊, 2013(07):60-62.
[18]王增文. 人口迁移、穆光宗. 人口优化理论再探——新人口危机和国家安全[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4):111-122.
[19]范洪敏. 中国低总和生育率分析[J].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1):8-11.
[20]靳永爱. 低生育率陷阱:理论、事实与启示[J]. 人口研究, 2014(01):3-17.
[21]汤梦君. 警惕“低生育率陷阱”[J]. 决策探索月刊, 2015(2):54-56.
[22]翟振武, 张现苓, 靳永爱. 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J]. 人口研究, 2014(2):3-17.
[23]陈爱珍. 现阶段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可行性的统计分析[J]. 经济视野, 2014(10):389-38
[24]戴玉. “全面二孩”,放开只是一个起点[J]. 南风窗, 2015(23):26-27.
[25]庄亚儿, 姜玉, 王志理,等. 当前我国城乡居民的生育意愿——基于2013年全国生育意愿调查[J]. 人口研究, 2014(3):3-13.
[26]石智雷, 楊云彦. 符合“单独二孩”政策家庭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J]. 人口研究, 2014(5):27-40.
[27]覃民, 李伯华, 齐嘉楠. 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对生育行为影响的纵向追踪研究[J]. 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 2010, 18(9):519-521.
[28]魏益华, 迟明. 人口新常态下中国人口生育政策调整研究[J]. 人口学刊, 2015, 37(2):41-45.
[29]穆光宗, 张团. 十字路口的中国人口:危机与挑战——《公开信》前后的人口问题和中国道路[J]. 思想战线, 2011, 37(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