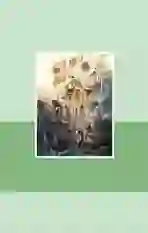陈集益:想象力能把故事推向极致
2016-03-21陈集益梁帅
陈集益 梁帅
陈集益,1973年生,浙江金华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迄今在《十月》《人民文学》《钟山》《花城》《大家》等刊发表小说近百万字,有作品收入多种选本,获《十月》新锐人物奖、浙江省优秀文学作品奖等。著有小说集《野猪场》《长翅膀的人》。现居北京。
梁帅,笔名梁坏坏。1979年出生,著有长篇小说《补丁》,中短篇小说《水漫蓝桥》《白日梦》《马戏团的秘密》等。现居哈尔滨。
梁帅:我听你说你有八年在外打工的经历,然后才开始写作,我想知道这八年你都经历了什么,这些经历的生活直接促使你写小说吗?
陈集益:打工八年是针对我来北京之前的说法,其实我到北京以后仍然在打工。我没有上过大学,户口还在老家村子里,说穿了我的身份是一个农民,想找一份正式工作很难,所以我在北京也是给出版社、杂志社等等地方打工,相对那些“体制内”人而言就是单位最底层的临时工。但是比起当年,在一些私营企业、家庭黑作坊做苦力,情况稍微好了一些。我19岁就离开家乡走向社会了,种种原因命运多舛,一直处于半漂泊状态。二十出头那些年,我大部分时间在温州打工,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对新兴的老板阶层好像没有什么法律上的约束,许多老板肆无忌惮地剥削工人,克扣工资,这样一来,我就经常生活困顿,也经常跟老板打架,不断地失业。我最穷时半个多月身无分文,挨饿,在公园与马路边广告牌后面过夜。我那时愤世嫉俗,精神抑郁,思想有些激进,平时爱听崔健等人的摇滚乐,梦想是组织一支摇滚乐队,为底层呐喊是当时最大的理想。那时候听歌得买磁带,拆开封皮,歌词就印在背面。我的写作就是从听崔健、何勇、黑豹乐队、唐朝乐队等等磁带模仿写类似歌词的文字开始的。
梁帅:我们还是有一点共同经历的生活的,比如说摇滚乐,我在二十岁左右的时候也接触过摇滚乐,并深爱至今。大学毕业后,我和朋友还搞过几次摇滚音乐节,我真心觉得摇滚乐对我们现今文化有很大的影响。
陈集益:是的,摇滚乐非常有魅力,它对像我这样生活过的人特别有感召力量。他们的歌词就像诗歌一样令我着迷。时间一久,我仿写“歌词”的过程等同于最初的文字训练。
我真正接触“文学”,是在1998年。当时我结束了温州杭州的打工生涯,待在自己家乡金华某工厂当炉工,因为闲暇时间比较多,加上由我哥哥带路,认识了金华市文联的一位作家叫蒋启倩,她看过我写自己打工经历的文字有些感动,出于对我的帮助,推荐我去杭州的一个文学讲习班学习。我那时除了在语文课本上读过小说散文,对其他文学作品一无所知。所幸在班上,我听到了王彪、洪治纲、吴亮、盛子潮、任峻等人的讲座,简直脑洞大开,回来后就去图书馆借文学书看,看了一两年开始尝试写小说,但是小说风格还是受摇滚歌词的影响比较大。或者说我的小说最初类似摇滚的嚎叫,是我内心情绪与价值立场直接的体现。后来,写作慢慢变得内敛规范了一些,它引领我从狭隘的愤世嫉俗走向更广阔的悲天悯人。
梁帅:苦难是我们的写作资源,但说到苦难,我们这一代,也很难切肤体验到经历过改革开放前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苦难,但社会在前进,精神生活中的“苦难”也随之而来,这一代作家在解剖精神磨难的时候,做出了不少努力,其中也包含您的作品。您对苦难的理解,是怎么样的,自己切身经历过吗,无论肉体还是精神方面的。如果有,又是怎么表达出来的?
陈集益:苦难不是计量单位,不能简单比较,应该说每代人各有各的苦难,都很沉重。就我而言,我想起贫穷的童年,洗脑的教育,理想的破灭,被故乡驱逐,在城里受难,前途无望,无力抗争,那种压抑绝望,至今想起来都让我感到窒息、暗无天日。有时候我想,苦难施加于人的程度可能跟受难者采取应对的态度有关。比如说,有一种苦难是社会迫害,一个人(或一个群体)被迫卷入其中,假如他(他们)采取默认、屈服甚至主动奴化,可能苦难于他(他们)就会削弱了许多。你提到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苦难,我确实没有体验,但是至少其中有一部分人是顺从了国家意志的。鲁迅有一个著名的“铁屋子”隐喻,借用这个隐喻,我们旁观同处“铁屋子”中的人们,会以为他们身处一样的苦难中,但是具体到屋中的每个人,承受苦难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再比如同处于当下吧,有些作家面对社会现实会感到良心不安、灵魂疼痛,但是也有些作家审势度局、阿谀奉承,不是混得很好吗?所以,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直面苦难。甚至有些苦难是我们自己主动选择的结果。作家应该是那种人,哪怕生活优裕婚姻幸福事业有成,他的内心深处还是会有“苦难”存在,或因为“选择站在鸡蛋那一边”,或因为无法解决人类某些永恒的精神困惑,即你所说的精神上的“苦难”……
我的小说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现实苦难与精神苦难的双重压迫。我从事写作主要跟我反抗苦难、不甘屈服有关,所以我的小说情绪一般是激愤的,主题是外露的,风格是悲怆的,某种程度上,这样的表达方式有点像当年的摇滚歌曲《一块红布》的风格,比如《洪水、跳蚤》《野猪场》《城门洞开》《吴村野人》《第三者》等等,我希望小说能反映出一个大时代的征候,时代裹挟下人的普遍的生存状态。当然,这样的表达方式是否适合,是否有损于小说的艺术质感,我也一直在怀疑,但是心中有话要说时,喊,依然是我选择的手段之一。
梁帅:中国曾出现过轰轰烈烈的先锋小说写作,但我们开始写作的时候,先锋的潮流已经过去,先锋作家后来写出来的作品似乎也不那么先锋了,但先锋小说对我们的影响还在,马原、苏童、孙甘露这些作家的作品我都仔细阅读和喜欢过,你感觉先锋小说是否也影响过你的写作?
陈集益:我无疑受到过先锋文学的影响。可能我们这个年纪的人都有这样的文学经历。并且内心会有一个情结(好比一个人的初恋情结),那就是总想写出跟目下流行的现实主义不一样的小说,不甘与主流文学随波逐流。可是文学界不见得就欢迎有探索性或者创造力、想象力的作品,于是较长一段时间,一些没有赶上趟儿、坚持先锋写作的后来者被文坛冷落一边。更让人尴尬的是,当年我们追随的那些所谓的先锋派作家,他们自己都改旗易帜放弃先锋了,弄得我们这些追随者们有点儿茫然无措、很想骂娘。但是不可否认,一个人于写作之初受到过先锋文学的滋养,是幸运的。因为先锋文学在当时社会背景下的反叛精神,孤独偏执的姿态,已经影响了我们的文学立场。真正的先锋应该是精神层面上的,是一种审美上的前瞻,是敢于对世界发出不同的声音,或者敢于直面严峻的社会现实,“越雷池一步”,这是一笔有利于我们将来成为“大作家”(假如你有这个雄心的话)的文学遗产,至少格局不一样了吧。
具体到先锋文学与我,以及当年的先锋派作家继不继续先锋,并不影响我未来的写作。我到今年才总结出我为什么热衷先锋文学,或者说为什么会有人说我的小说写得有点怪诞,貌似先锋?主要跟我的写作背景有关:一是我的文字训练最初脱胎于摇滚歌词,摇滚乐是一种打破常规、破坏秩序的音乐;二是我的小说表现手法早期受卡夫卡影响较大,卡夫卡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鼻祖,他对我影响深远;三是目前的报刊审查制度逼迫我采取“先锋文学”的样式伪装文本,将敏感题意匿藏或弱化——这第三条理由听起来或许有点费解,其实不然,我们知道现在还有很多题材是书写的禁忌,为了小说能够顺利发表也只能采取寓言式的写作,将真相以象征的、隐喻的方式表达出来。其中《青蛙》《天堂别墅区》《特命公使》等小说是这方面的尝试。所以,先锋文学在马原他们那一代,可能更多的是单纯的文本形式的革命,小说内容往往与现实离得较远,而在我这个年龄的后来者的创作中,开始将它转变为为表达内容服务的文学手段。不如此,我们很难书写历史。
梁帅:我看到有评论说你的“父亲系列”的小说中,有集权和强权的阴影。强权会对整个社会产生压抑、扭曲和把一些事物变形,你怎么体现这种压抑。
陈集益:“父亲系列”我好像写了《洪水、跳蚤》《离开牛栏的日子》《城门洞开》《哭泣事件》,可能还有其他,相对我自己某些荒诞色彩比较浓的小说,它们有相对扎实的写实主义功底,故事背景都与吴村有关。那是一个极度封闭的小山村,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它被一个巨大的水库人为地封锁在大山里。在水库建造之前,山里人主要靠贩卖木材为生,当洪水来临,预先扎好的木筏竹筏顺流而下,最远能漂流到钱塘江直达杭州——因为那时候钱塘江上游的新安江水库(现在叫千岛湖)同样不存在——所以我们山里人也都是见过世面的,日子也过得富裕。无奈等我出生时,水库阻断了一条河流的流淌,没有公路,不通电,出不去,进不来,粮食难以自产自足。在那种恶劣的环境里,大队干部、生产队长、地痞、莽夫、无产者等等人物,控制了这个村庄。我写父亲,是因为“父亲是一个家庭与社会的纽带,社会生活可以通过他反映在家庭生活上”。另外,由于我在小说中对那个封闭环境一次次反复书写,可能容易让人产生“集权和强权”的印象吧。我愿意将吴村看作是整个社会的缩影。在这个封闭的村子里发生的一切,我曾亲眼目睹:血腥,愚昧,蛮横,强权,阶级斗争,窝里斗,等等,都客观真实,但是我采取的体现方式,其实我在上面那个问题中已经谈到,是“寓言式的写作”。
梁帅:我感觉《野猪场》《吴村野人》还有《长翅膀的人》就是颇具隐喻意味的“寓言式”作品。那么如何在一个现实故事里,产生出一个大的隐喻或者象征,让故事升华为寓言呢?
陈集益:我个人经验是将一个你要书写的故事借助想象力推向极致,随着想象力持续推进,故事情节不断地向现实的边界扩延,在即将跨越写实的那个临界点上,现实好像要展翅飞翔起来,这时就自然而然地产生隐喻、象征等等效果。不论是你提及的隐喻、象征或思考,都会伴随着想象的推进而产生。其最关键之处,是要把握一个推进的度,不能让小说失去真实与虚构的平衡。
梁帅:目前为止,您对您的写作满意吗?请谈一下您最满意的作品?
陈集益:我对自己的写作谈不上满意。原因很简单,因为我在试图表现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时,采用的什么隐喻之类的手法,多少是没有勇气直接揭示真相的无奈之举,这种旁敲侧击终究是旁敲侧击。当我在书架前面对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那样的作品,感觉自己如此渺小,简直无地自容。当然,相比国内某些没有底线、歌功颂德的作家,我无疑还是有所坚持的。我有一小部分作品,它们没有给我丢脸。不过由于工作忙碌,最近两三年我都没有怎么写作了。以前的作品已经基本被人遗忘。最近的作品就一个《人皮鼓》还拿得出手。这个小说是我第一次直面自己的打工生涯,对我自己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在这之前,我已经为写作的出路问题苦恼很久,在创作思路比较矛盾的情况下,我的作品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现象。即:在写作时,比如我认为这篇东西是想写出来发表的,就力图让它四平八稳的,之后又觉得自己太势利了,就会写一篇不想发表的东西来补偿,这时就会用力过度,小说面目狰狞、难读。通过这篇小说,我重新调整了写作的心态:我要做的就是遵循自己的内心,竭尽所能写我自己想写的小说,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写作领域和创作技巧,写我认为能靠近甚至超越心目中“经典”的小说,如此,就足够了。
梁帅:你其实一直是那种“离群索居”式的作家,你有自己的写作套路,不跟从主流。但是,就算你能做到背对文坛,你的文学却是要面对读者的,这个没有办法回避。读者往往喜欢从小说中看到“故事”“主题”,您有多年的写作经验,您觉得故事和主题这种东西,对小说来说很重要吗?
陈集益:在西方小说中,特别是后现代小说,好像就没有什么故事和主题。国内先锋文学盛行时期,很多探索小说都不讲故事,也摸不清它的主题。这些小说中,有非常优秀的传世之作,当然也有故弄玄虚的伪作。总的说来,“条条大路通罗马”,什么样的写法套路都能产生伟大的作品,传统与先锋,这个流派与那个流派,本质上没有优劣之分,就看你写得好不好,对文学这门艺术有没有提供新的贡献,哪怕提供一个别人没有写过的人物,一个思想,一段精美绝伦的文字。我自己的写作,还基本保留了人物与故事,可能有些故事讲得不那么顺溜,或者为掩盖主题故意颠来倒去,但是我确实很少写没有主题的小说。倒不是为读者考虑阅读习惯,而是没有主题,不知道怎么组织几万字的文字。假如你也像我这样,那么动笔之前我还是劝你为小说设定一个或多个主题吧。
梁帅:也有作家强调过有中国味道的小说,今天的小说,是从西方发展过来的,小说使用的语言虽然是汉字,但也是改造过的中国文字,我们在看民国一代的作家作品的时候,很多小说的语言,包括鲁迅先生的语言都很有中国味道,后来的作家,阿成的小说也有中国味道,你觉得中国味道,除了语言上的味道,还会有哪些体现?
陈集益:我不太喜欢官方舆论倡导的“中国经验”、“中国故事”之类的提法,人类的经验与艺术的方法应该都是互通的,没有必要鼓励大家穿上唐装、抹上胭脂、端起一副架子,倒是你提到的“中国味道”好像更亲切、也更包容一些。中国人骨子里有自己的“味道”,这是与生俱来的,所以不必担心穿西装的中国人有一天变成了白种人,但是也好像没有必要特意将它拎出来说吧。我个人比较推崇文学风格的多样化,每个作家都是独立的个体,各写各的就行,一旦过分强调某一种需要你去趋同的东西,特别是一阵风一样刮过来的概念或者口号,就值得警惕。
梁帅:你最近在阅读什么书,给推荐几本啊。
陈集益:说来惭愧,我因为工作实在太忙,加上年轻时没有养成阅读习惯,读书不是很多。跟一些朋友聊天,他们说早在二十岁之前,就读了上百本名著,可我到现在也没有读完《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名著,总是被打断。今年我一口气读完的是拉什迪的《午夜之子》,我认为这是一部可以与《百年孤独》《铁皮鼓》相媲美的巨著。我如果在有生之年能写出这样一部巨著,那么死的时候就无憾了。
责任编辑 白荔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