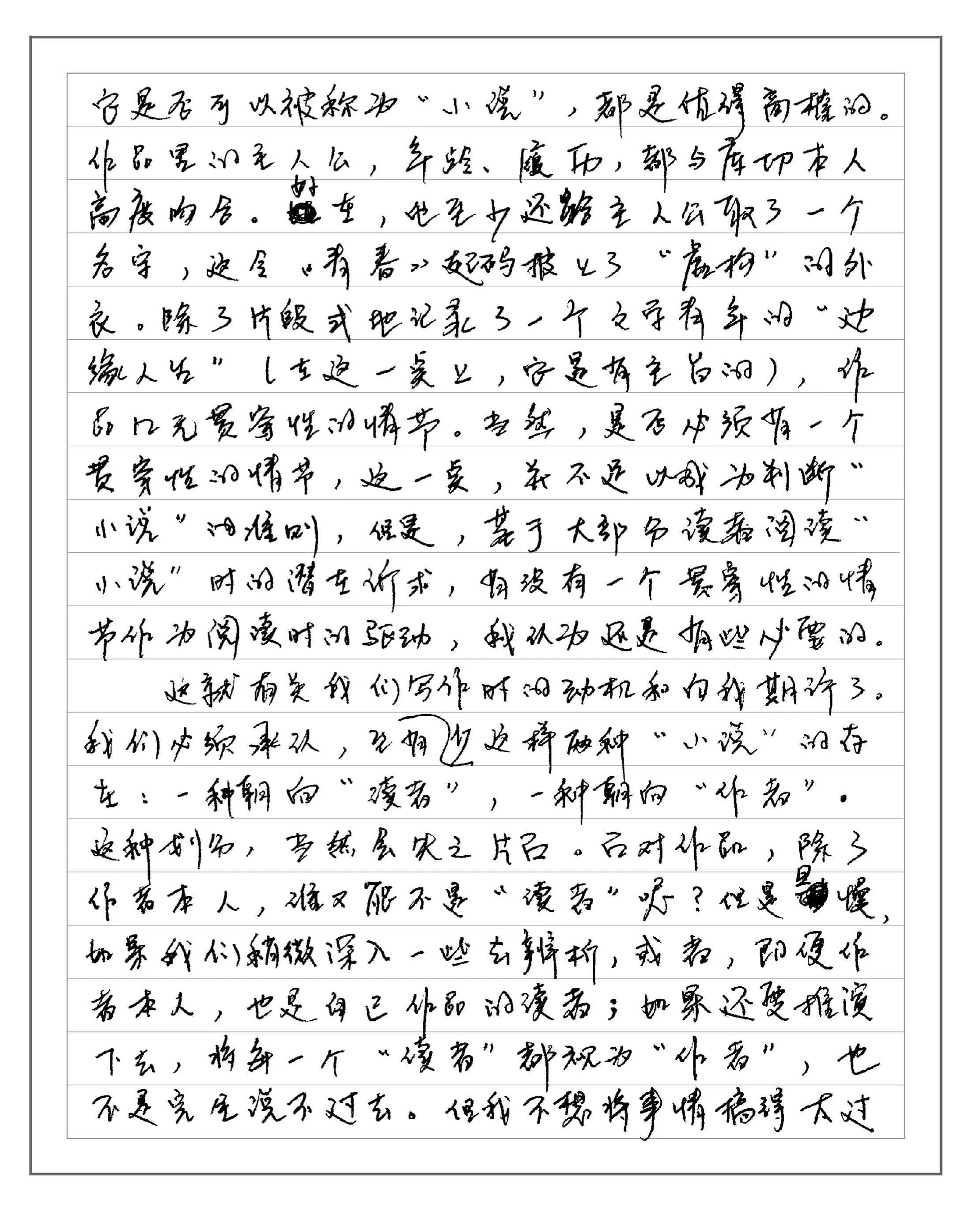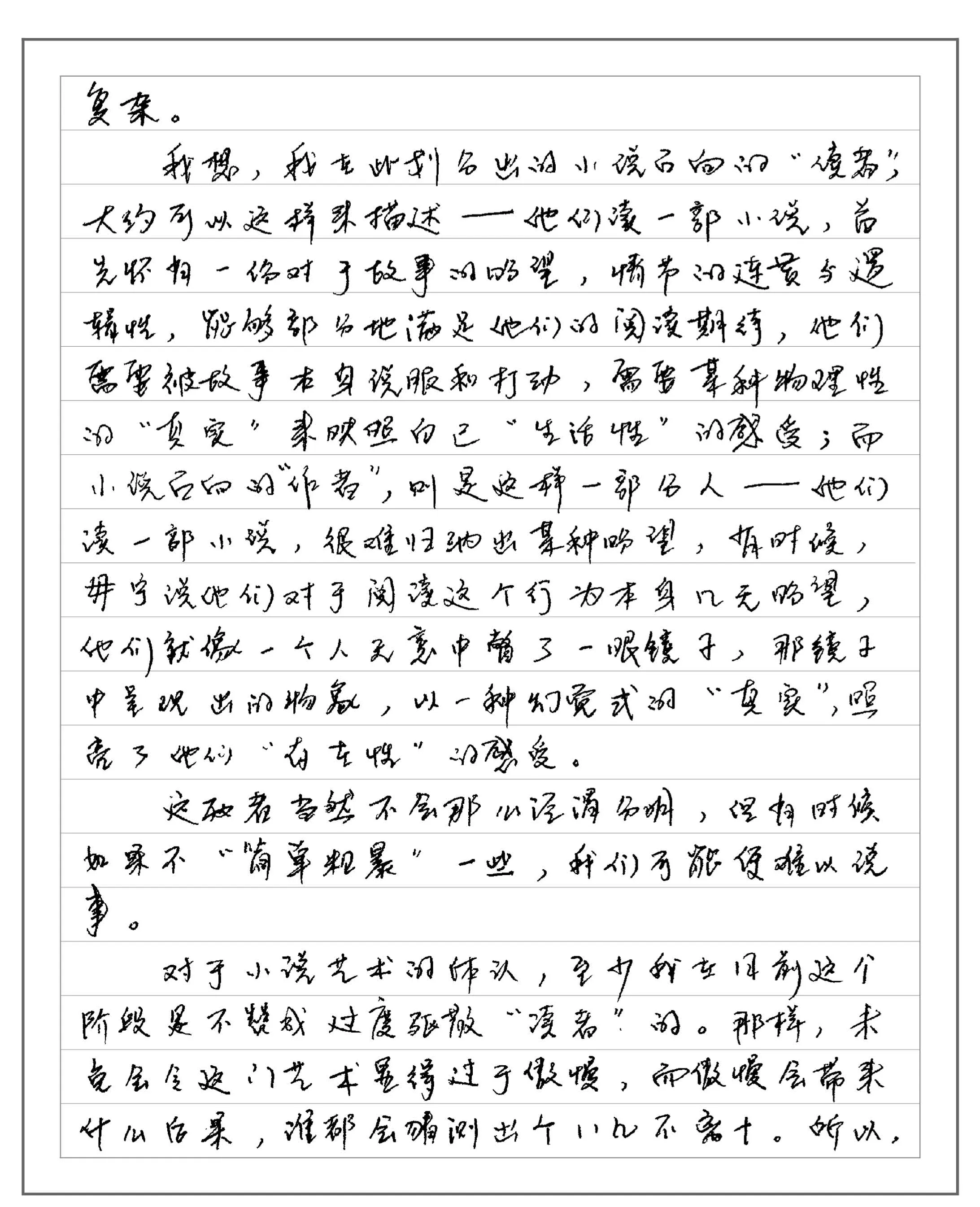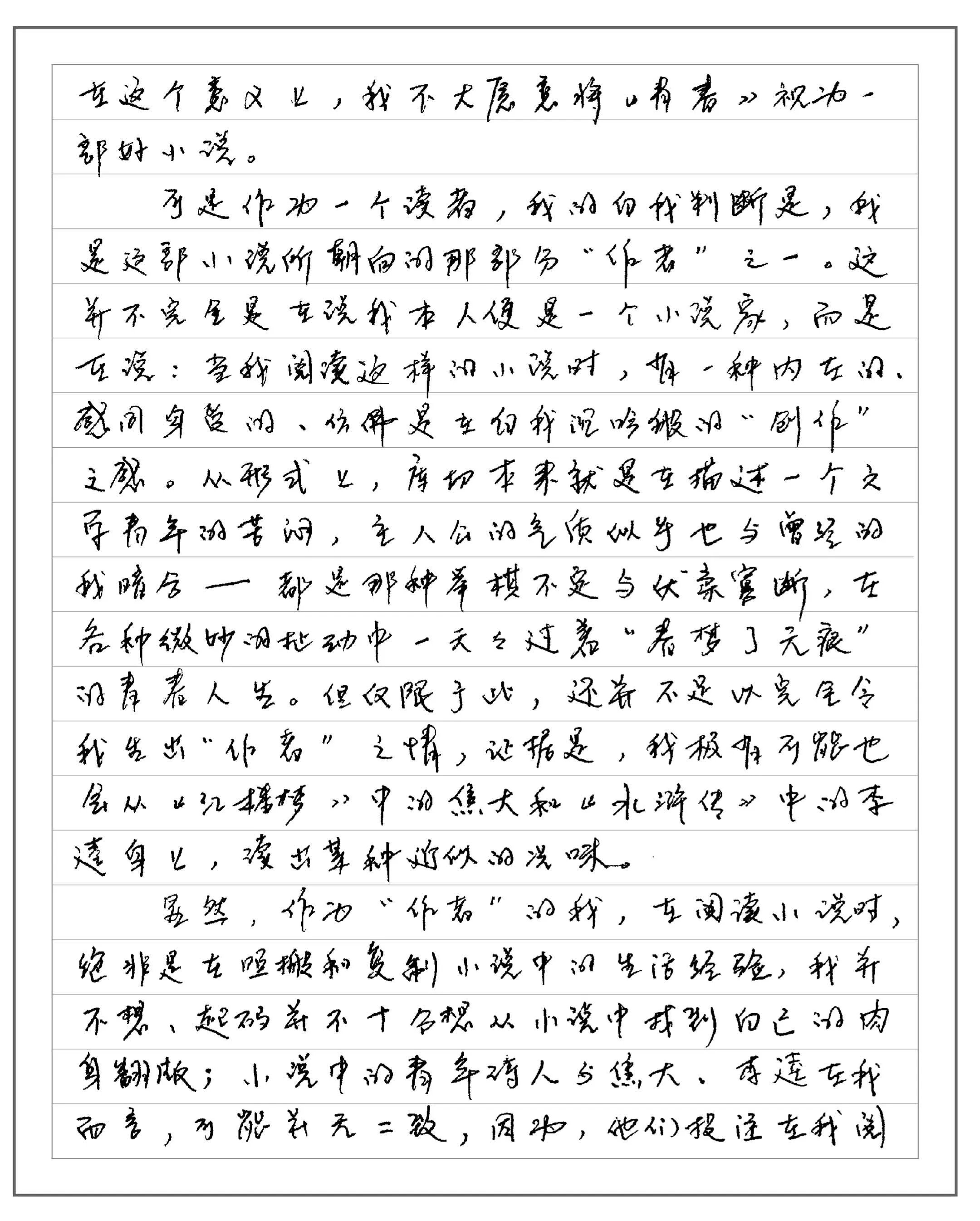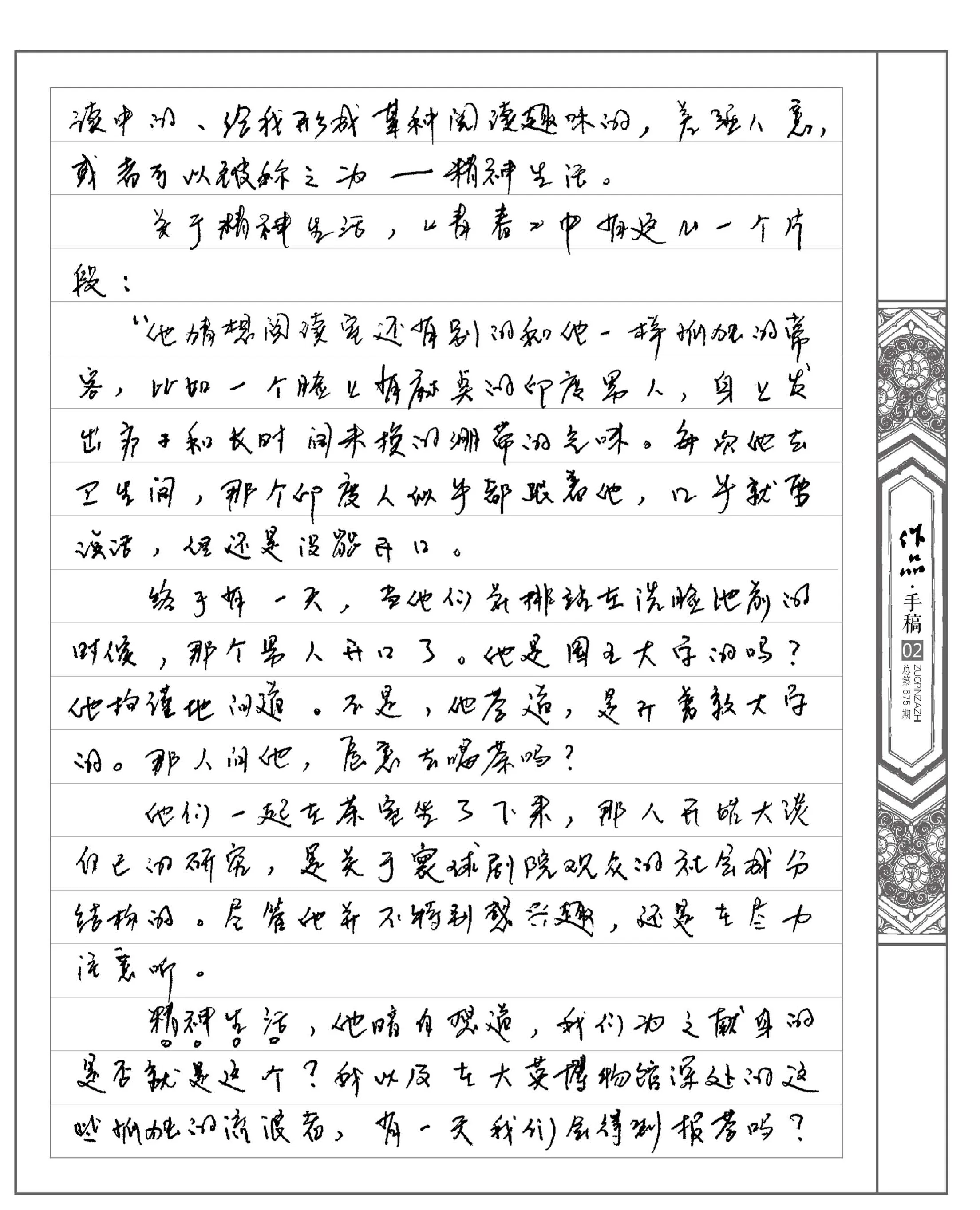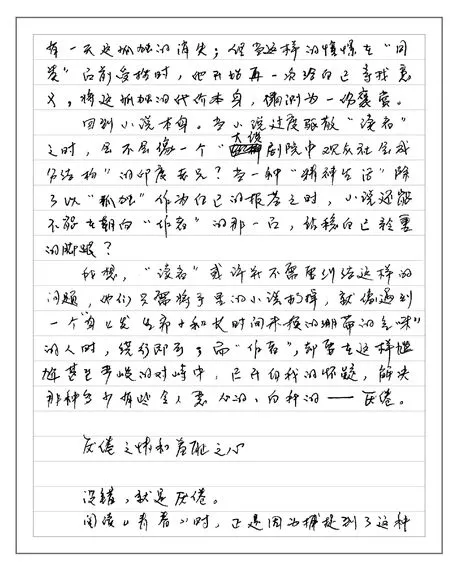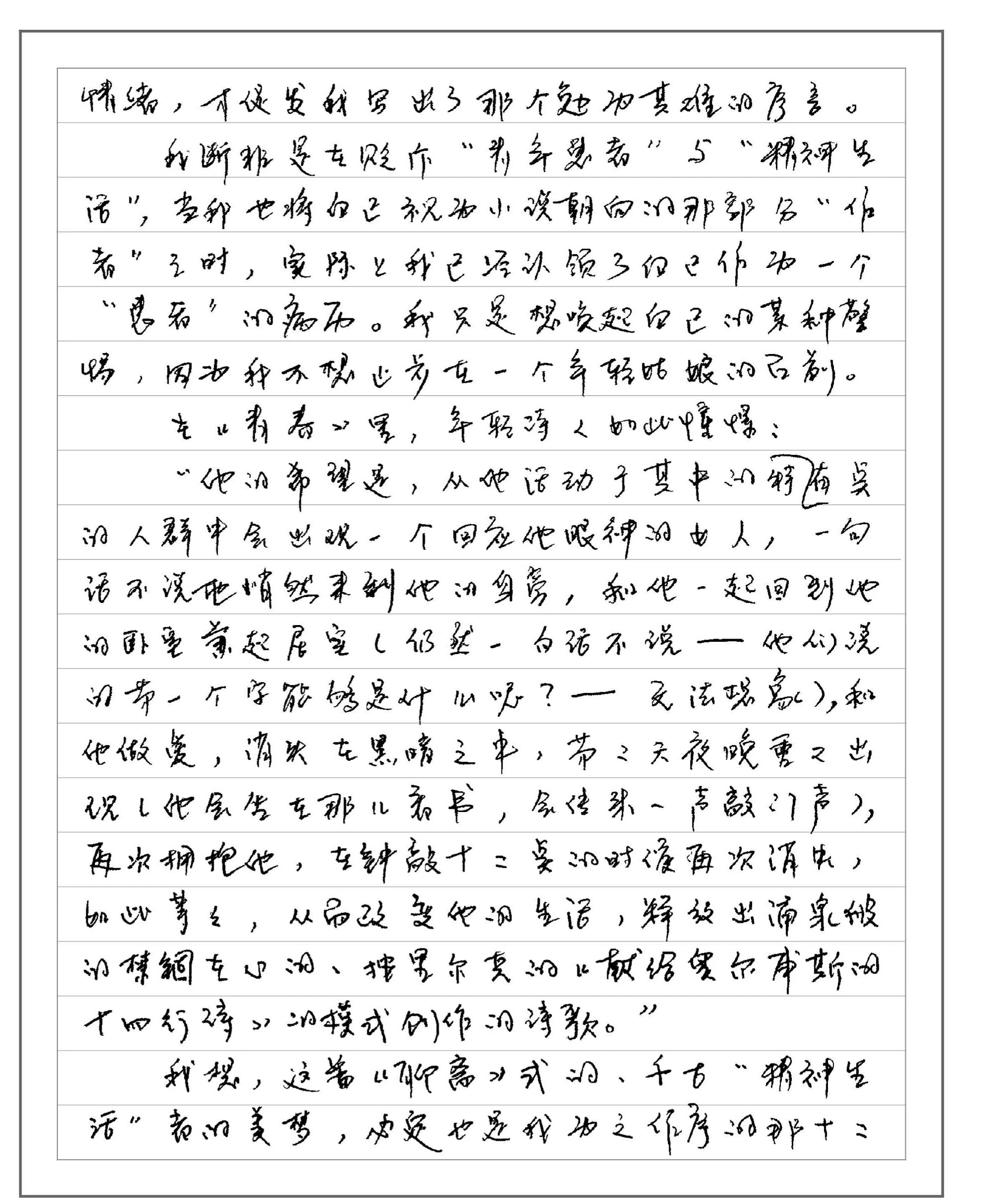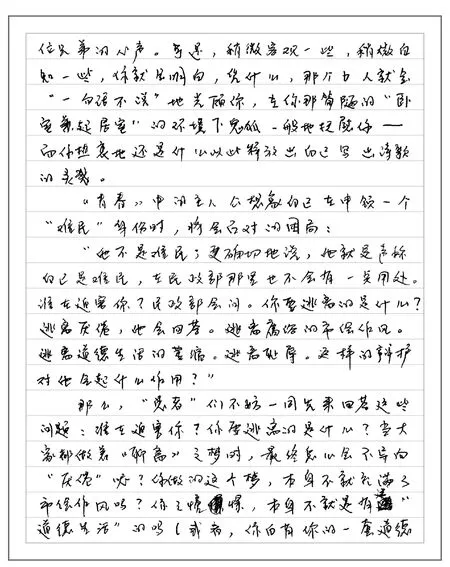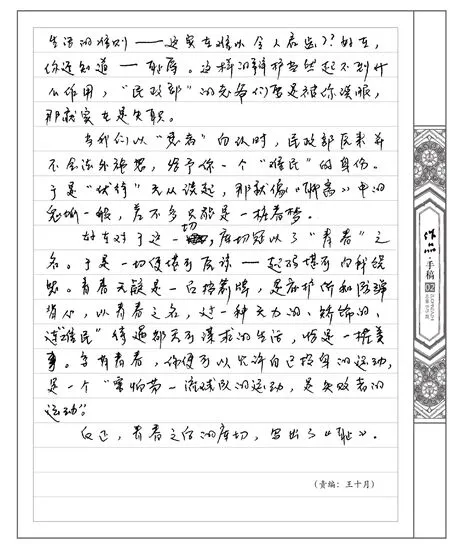名窑精神
2016-03-21沈荣均
文/沈荣均
名窑精神
文/沈荣均
沈荣均在场主义散文成员,新锐作家、批评家。在数十家报刊发表诗歌、散文、文学评论百万字,入选十多种权威文学年选。出版散文集《倾城的土著 》、《斑色如陶 》、《内心的花朵 》。获二十四届、十八届孙犁文学奖散文奖、2006年滇池文学奖提名奖、首届四川散文奖、在场主义散文奖新锐奖。
汝 窑
古瓷讲究出身。官窑和民窑,在普通人的概念里,相当于贵族和平民,身价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甚至就不只是价格的问题。比如,北宋汝窑(汝官窑)。已知的文献和考古发现证实,宋官窑从汝窑开始。对于今人,汝窑的名字绝对如雷贯耳。很多人也只是听说而已,看一眼的机会都不曾有,更别说拥有了。可能土豪们说,我有钱,我买。有一点是明确的,汝窑这玩意,虽不像柴窑仅存于传说,市场上偶尔也得见,但就是买不着,即便有很多很多钱。为啥,太稀少了!
汝窑的烧造,我们已无法看到明确记载。有人推测,大致20年左右,具体说是在11世纪末到12世纪初,期间经历了哲宗、徽宗两朝。从文化上讲,正值王朝顶峰。从政治上讲,又暗藏外敌入侵的危机。文物专家把这20年定为汝官窑的烧造时间,没有争议。一座烧造条件和标准极其苛刻的官窑,仅烧造20年左右,又历经千年的战火和变迁,你说保存到现在能有几件?有人统计过,记录在案的不过67件,几乎都藏在顶极的博物馆里,真正的稀世之珍!可能有些土豪不服气,我去拍卖场举牌呵。这也许是个办法,问题是迄今为止,汝窑在拍卖上露面的机会寥寥,价钱高得让你心跳。20多年前,美国拍过一个盘子,154万美金。当时,这价格是包括元青花、永宣青花和釉里红、成化斗彩、清三代珐琅彩在内的顶极官窑,远远不能及的。如今,所提到的这些官窑都卖上亿了,你说买汝窑,得烧多少银子?
不过,买不了,不影响我们对于汝窑的情感。我们可以去博物馆看看,去窑址走走。看那天青色,一泻而下,烟云一样袅绕。去摸摸曾经焙烧过汝窑器皿的窑泥,余温不在,凉意袭来,那是岁月的冰凉,穿透一千年。有心的,看看走走时,再拍拍照,买本图册放在书房也好。宋代顶极知识分子的书房,许是要放置汝窑的。我们只是小书生,没有汝窑可玩,但有天青色可观,可聊,可遐想,可述说。一屋子的氤氲,静如天籁。
汝窑的珍稀,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一问世,就步入青瓷的颠峰。这在陶瓷烧造学术问题上,很难解释的。后来的元青花也是如此,暂且不提。
汝窑水平有多高呢?南宋人叶寘(音置)在《坦斋笔衡》讲:“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这话可以理解为,在汝窑成功烧造后不久的南宋,汝窑与各大青瓷窑口器皿比,算第一名,受到贵族和读书人的追捧。南宋人周密还在《武林旧事》中专门记录了一件有趣的事情:“高宗幸张府节次略。奉汝窑 ,酒瓶一对、洗一、香炉一、香合一、香球一、盏四只、盂子二、出香一对、大奁一、小奁一。”这则笔记大致说高宗赵构,一日到清河郡王张俊家巡幸,张俊一激动,送了16件汝窑器皿给主子。周密为啥要在自己的笔记里,一五一十地记载得这么详尽,只有一个说法,东西太贵重了!今天我们在各大博物馆里看到的汝窑,有几件或许就是记载中的那些。汝窑第一,一直保持到明清。明人王世懋在《窥天外乘》对“第一”有个明确的诠释:“宋时窑器以汝州为第一,而京师自置官窑次之。”大画家徐渭《墨芍药》云:“花是扬州种,瓶是汝州窑。注以江东水,春风锁二乔。”把汝窑与美女偶像二乔并提,可见它在读书人心目中的地位。清人孙灏有诗云:“青瓷上选无雕饰,不是元家始博殖。名王作贡绍兴年,瓶盏炉球动颜色。官哥配汝非汝俦,声价当时压定州。皿虫为盅物之蠹,人巧久绝天难留。金盘玉碗世称宝,翻烂泥土求精好。窑空烟冷其奈何,野煤春生古原草。”注意,清人孙灏对汝窑的赞美是以慨叹的形式,“窑空烟冷其奈何”。为啥慨叹,因为明清两朝,官家以举国之力,都不能仿造,只能空对寂寥的古窑,兀自嗟叹——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呵!
汝窑烧造的20年后,金人打到了汴京。徽宗赵佶被虏。
汝窑从颠峰跌落。中世纪东方读书人的眼,迷离,湿润。
天青色,四下弥漫。
汝窑逐渐远离读书人的生活,成为割舍不掉的感伤。记忆飘去,或隐到黑夜背后,星子一样暗光闪烁,或逐于风中,碎片一样流浪。
今天我们讨论汝窑,都没人能准确讲出它的整体印象。明代曹昭在《格古要论》里说:“汝窑器,出北地,宋时烧者。淡青色,有蟹爪纹者真,无纹者尤好,土脉滋媚,薄甚亦难得。”这话透露出的一些基本信息,也只是作者本人的片段体会,很难读懂。读不懂没关系,记住天青色就行了。记住天青色,你就记住了中国古陶瓷最顶极的审美标准——朴素、去感官刺激、内心化、闹中取静、最终归于沉寂,记住了那个让读书人无限向往,又无限纠结的时代。
官 窑
历朝皇帝中,艺术造诣高的,乾隆算一个。乾隆对艺术品的鉴赏能力,非同一般,当朝读书人中,没人能比,放在历史长河里,也是十分了得。他的诗文水平就一般了,不过特能写,有几万首,算以量取胜。几万首诗词作品,我唯一能深刻记得的只有:“李唐越器久称无,赵宋官窑珍以孤。色自粉青泯火气,纹犹鳝血裂冰肤。”是什么样的稀世珍奇让阅宝无数的乾隆皇帝发出“珍以孤”的感叹?
宋官窑粉青贯耳方壶呵!
五大名窑中,官窑次及汝窑,排第二。这也与宋朝皇帝特别是宋徽宗的艺术喜好有关。宋徽宗是否烧造了官窑,官方文件并无明确记载。南宋人顾文荐在《负暄杂录》中提到:“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这是学术界比较公认的关于宋官窑存在的说法。顾式说的官窑,可以认为烧造于宋徽宗后期,应稍晚于汝窑,窑口在京都汴梁(今河南开封)。这个时期的官窑(“北宋官窑”),又称“汴京官窑”或“旧官”。汝窑除有文献记载外,近年也成功发现了窑址,发掘了大量可以对比的文物资料,已成铁论。北宋官窑的真实存在与否,迄今还是学术公案。黄河古道变迁,窑址早淹没得不见踪迹,连传世的宋代青瓷作品中,也难明确其出身。靖康之变,北宋灭亡,汴京官窑随徽宗被虏,成为历史烟云。宋室南迁临安(今浙江杭州),高宗先后新建了官窑“修内司”和“新窑”。南宋叶
寘的笔记《坦斋笔衡》明确记载道:“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釉色莹澈,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亦曰官窑,比旧窑大不侔矣。余如乌泥窑、余杭窑、续窑,皆非官窑比,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修内司”和“新窑”,就是南宋官窑,学术界又称之“新官”,文物专家已于上世纪在杭州发现了窑址——老虎洞修内司官窑和郊坛下官窑。
引发乾隆皇帝作诗盛赞的那个粉青贯耳瓶,究竟是徽宗还是高宗时烧造的呢?连故宫专家都说不清。说不清楚就对了,神秘感还在,历史的魅力还在。民国时期资深的古董商崔仲良和洪玉琳,据说就买卖过一件北宋官窑彝炉,注意还是让人欲罢不能的“据说”。民国早年,崔仲良在北京城开了个“保粹斋”,买卖古董瓷器。“九·一八事变”前,北京人都在传小宣统跑到了东北。一天,宫里一位老太监到保粹斋,说要卖个物件。包袱开。锦匣露。匣里还个软囊。搞得挺复杂的。看来送货人很看重手里的宝贝——仿青铜器造型青瓷彝炉。锦匣的黄绫签上书有楷文:“北宋官窑翠绿双耳彝炉”。好家伙,北宋官窑!我们能想象,那一刻崔仲良定是眼睛一亮,既而心中又几下扑腾。之后,行里就传出崔仲良买了件北宋官窑,花了一千大洋,也有说花了两千的。东西的来路,说法不一了,有说在窜货场上窜来的,有说没落晋商送来典当的,有说从某王府后人手里倒腾来的,等等。任大家传闻,崔仲良不表态。有一回听人说,那玩意是龙泉窑,不是啥宋官窑。这不是在质疑他在业界的眼力么!忍不住了,他就很坚决很高调地放话——肯定是“宋官窑”。宋官窑谁见过啊?它可是跟传说一样神秘,古董商们对它的知晓,仅限于“紫口铁足”。崔仲良对他的宝贝彝炉深信不疑。没人认识,就不给人瞧了。他就等,等有钱又懂行的大买家。终于有这么一个人来了。洪玉琳,上海古董界四大天元(戴福葆、张仲英、仇焱之、洪玉琳)之一。洪玉琳也没见过北宋官窑。但他看懂了炉子的包装——团龙锦匣和黄绫题签,皇家独有的气质。就冲这副无法造假的包装,洪玉琳狂砸一万银洋,下了个大赌注。后来的事情证明了,冲包装就敢下大注买宋官窑的洪玉琳,眼力和胆识的非凡。一年后,古玩界传出他发了大财,转手宋官炉子得利数万美金。有的说他卖给了大英博物馆,有的说卖给了美国博物馆。不管怎样,这件翠绿双耳彝炉再无确切的去向了。甚至有人认为,崔仲良和洪玉琳买卖宋官窑,就是古玩界一提振人气的闲话。
也许,北宋官窑彻头彻尾就是个猜想。猜想总有着神秘的诱惑。因为诱惑,我们好奇,并试图设法证实这诱惑。就像科学命题。一些命题或许会有个终极的结果,更多的仅是不断地接近,再接近。
“官窑器,宋修内司烧者,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色好者与汝窑相类。有黑土者谓之乌泥窑。伪者皆龙泉所烧者,无纹路。”(明·曹昭《格古要论》)读曹昭这话,我们可以想象南宋修内司官窑“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或许就是北宋宣和官窑的模样。“所谓官者,烧于宋修内司中,为官家造也。窑在杭之凤凰山下。其土紫,故胎如铁,时云紫口铁足。紫口乃器口上仰,釉水流下,比周身较浅,故口微露紫痕,此何足贵?维尚铁足,以他处之土咸不及此。哥窑烧于私家,取土俱在此地。”(明·高濂《遵生八笺》)高濂此话,又告诉我们南宋官窑烧造的大致环境 ,于是,我们又猜想,汴京的官窑烧造大致如此吧。“官、哥、汝窑,以粉青色为上,淡白次之,油灰最下。纹取冰裂、鳝血、铁足为上,梅花片、黑纹次之,细碎纹最下。”(明·文震亨《长物志》)文震亨是个文人,文人重视觉感受,对宋代青瓷的深刻印象,一是青色,一是冰裂开片。文震亨对官窑的理解,大致与我们今人谈论宋代青瓷审美标准接近。冰裂纹——宋代读书人内心的纠结就在于此。青色,半片江山,一片烟云。不管它是宣和官窑,还是临安修内司,都是宋人内心。其他已不重要了。尤其是那天青色。当我们再一次目睹宋代官窑,真的会有一种“天青色在等你”的情怀,在弥漫,在荡漾。弥漫十一世纪,荡漾一千年。
一千年后,我们看到某件南宋官窑纸槌瓶,它正摆在香港苏富比的春季拍场里。这一天是2008年4月11日。整个专场仅有两件拍品:一只瓶,一幅画。一瓶一画,日本茶道里叫“床之间”——颇有意境的组合:极为简朴的茶室,任何扰乱内心的饰物被拒绝。“床之间”,一个唯一可置器物,向后凹、再凹的空间。有点类似壁龛或神坛,只是不放佛造像,现在它被主人允许,置放两样物事——瓶花与墙画。也有用书法替代画作的。瓶花协调了书画的情绪——那近乎严厉与苛刻的素朴,游丝一样充盈和弥漫。官窑的美,简略得只剩得线条。金丝铁线,稀疏开满釉面,像春天的冰河,在朝着温暖解冻。喀嚓之声,仿佛谁的呐喊,那么轻,轻得了无声息,却又那么有力。冰河倒影天空的青色。游丝一样的青色。游丝一样的呐喊。青色无边。呐喊无声。是天青氤氲了呐喊,还是呐喊感动了天青。春阳也含蓄了。窗外的弥漫。弥漫过窗。床之间。阳光随意地抹在瓶花上——这个季节,最淡然也是最丰盈的春色。有人说,那春色叫“禅意”。做为某种高级的精神审美,我的叙述也许过于饶舌。叙述终究是苍白的。此刻,拍场从未有过的宁静。没人试图表达和解释,自言自语也是多余的。就让那画,那瓶花,那一片天青色,兀自弥漫,再弥漫。
接下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南宋青瓷瓶是一个叫坂本五郎的日本瓷痴送拍的。二战的时候,他在日本的南部遭遇了它,从此得藏。瓶底刻有“玉津园”三字。玉津园是南宋高宗皇帝的御花园。南宋人周密在他的笔记《武林旧事》中,记载有“北使到阙……四日,赴玉津园燕射。”也许一千年前,这件天青色花瓶,曾摆放于宋高宗花园的书房一角。现在,它摆在“床之间”,以艺术商品的形式被拍卖了6752万港元的高价。人们追捧他,不惜抛掷千金,去制造喝彩——喧闹或许也是动听的。要多动听的喝彩,才能动摇它?!既不能动摇,那就绚烂吧。绚烂之极。后是平淡和宁静。平淡宁静之极——天青色兀自讲述千年前的北宋传说,南宋故事。
哥 窑
美丽从来带有理想的色彩。然十全之美,一直在路上——那么切近,又那么遥不可及。遥不可及也阻挡不了我们对于美丽的渴求——既然不能十全,那就退而求其次吧。很多时候,我们遭遇的不是理想化的“十全”,是缺陷。缺陷随处可见。我们不能因为缺陷的太多存在,放弃了审美的理想。于是,又一个命题产生了:美的常态或许是缺陷。苏东坡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阴晴圆缺是月亮的常态,悲欢离合是人生的常态。杨玉环的肥胖,赵飞燕的瘦削,西施的孱弱,这是美人的常态。林黛玉算是大观园里头号美人,缺陷不是一两处,身体欠佳,小心眼,说话刻薄,多愁善感……哪儿都不顺眼。不顺眼就对了,要是“太顺眼”,我们就不会关注她和宝哥哥绝世的爱情了——那种脱离生活的“高大上”,其实我们并不感兴趣。
我们对于缺陷感兴趣,源于内心的纠结——渴望绝世的美丽,又希望它真实存在。如此纠结,宋人也是有的。他们在烧造青瓷的时候,因为工艺的原因,不小心把釉给烧炸了,开窑后一看,釉面噼哩啪啦开了一大片。开片是瓷器釉面的断纹,本来是宋代青瓷的一个病态,宋人却把它当另类的个性来推崇。哥窑就是个典型。哥窑的开片,叫“金丝铁线”,也有叫“百极碎”的。“哥窑则多断纹,号百极碎。”(明·王圻《稗史类编》)“哥窑,白断纹,号百圾碎。”(明·陆深《春风堂随笔》)金丝铁线,是说大片套小片,大片铁线,小片金丝。百极碎,描述开片的形状,细小,多边形,走势没有任何规律可循,缠绕,流畅,类似冰河之裂或田土皴裂。有人猜想哥窑百极碎可以人为控制,金丝铁线是染色。就想了很多法子仿作,所仿的开片,死板,无生机,与真正的哥窑开片相距甚远。现在比较公认的说法,哥窑的开片,原本胎、釉和温度恰到好处的偶然碰撞结果。明代《处州府志》记载有个传说:“章生二,不知何时人,尝主琉田窑,凡器之出于生二窑者,极青莹,纯粹不暇,如美玉。然一瓶一钵,动辄十数金。”传说大意是,宋时在龙泉那个地方,有兄弟俩章生一、章生二,一人管一青瓷窑口——哥窑和弟窑。老大水平高,“紫口铁足”就是他的成就,自然名满天下。老二小心眼,嫉妒了,就使坏,趁老大不注意,抓了把黏土扔到哥哥的釉缸。老大施用掺了粘土的釉,烧成后一开窑,眼前一片裂纹,有的像鱼子,有的像柳叶,有的像蟹爪。他傻眼了,一气之下,把一杯浓茶水泼在刚出窑的瓷器上,没想到那些裂纹顿时染上黑和金两种颜色,很美。来购货的商家一看,喜欢得不得了。后来的研究证明,这个传说归传说,从开片工艺角度看,釉里加黏土,出窑后泼茶水,都是不得要领的猜想。但传说也证明了一点,那就是本来偶然而为的青瓷烧造病态,逐渐成为人们追求的一个工艺标准。这就像作文,灵感本是偶然而为的智慧奇葩,因为可遇而不可求,总害得我们为寻觅它的痕迹,“为伊消得人憔悴”。
瑕疵上升为灵感,这是哥窑被人们追捧的身份标识。主导宋人审美标准的是读书人。读书人讲境界,抱朴守素,愈寂寥,境界愈遥远。今天我们叫寂寥美——仿佛现代社会高端的审美话题。从素色,到寂寥美,中间的时间跨度是一千年。青瓷以寂寥的素色为主流。汝窑、官窑——寂寥的长天一色。钧窑——寂寥的半山烟霞。定窑——寂寥的月色满地。龙泉窑——寂寥的五月陌上。耀州窑——寂寥的九月秋水。建窑——寂寥的长夜弥漫……一种色调的审美,到了老百姓那里,还是觉得调子低了,委婉,含蓄,欲罢不能。宋朝又是个市民文化特火的时代,素色终究藏不住内心的跃跃欲试——美的端倪从寂寥开始,有了多种可能性。那红,钧窑烟霞关于夕阳的可能性。那花,定窑月色关于霜草、耀州秋水关于莲池的可能性。那梅,龙泉五月关于爱情的可能性。那天目,建窑长夜关于黎明的可能性……
到宋末元初,到哥窑,“百极碎”有了更为丰富的可能性:二月,南方的溪水开始解冻。寂寥一个冬天的封水,没有谁去扰动它。似有呐喊从冬天传来,开窑了……呐喊掷地。第一处冰烈。哗!那是谁按捺不住的悸动。又一处冰烈,噼啪!悸动传递。接下来更多的冰烈,唏哩哗啦……既已发生,那就让它继续吧。江南的生动,接连不断地演绎,我们不知它止于何处。永无止境的可能性,超越想象。最不可揣摩的线条走势,暗合了我们对于青瓷更多的审美诉求。纠结也好。悸动也好。都让我们起了荡漾,仿佛初春的江水。荡漾之后,是荡气回肠(在宋代青瓷中,汝、官、哥、钧都有开片,惟哥窑以开片为第一审美元素,也最为典型)。冰河初开!满目的纠结和激动!嗓子眼终于忍不住有了隐隐的冲动——哥!我的亲兄呵……
钧 窑
人们追求哥窑,是寻求完美中的那一丝遗憾美。但十全十美,毕竟还是中国人的主流观念。凡事讲究圆满,最好该有的都有,能有多好有多好。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这不仅是一句广告词,它道出了我们每个人的心底——有谁能拒绝那极致美的诱惑呢。
就像钧窑。钧窑本来属于青瓷。青瓷追求素,汝官哥求天青,定窑求月白,龙泉求粉青和梅子青。一色之青。青一色好,安静,低调,有定力。钧窑的窑工呢,对青瓷的素色审美标准并不那么执着。他们一直在试图制造点啥氛围——长时间的安静,忽生血液的温暖和浪漫。于是,铜红釉被发现了。宋时,以铜为呈色剂,烧出的红釉,不算鲜艳,只能叫暗红。就是这个暗红,已属相当了不起的成就了。钧窑之前,中国的陶瓷艺人一直想烧出类似太阳、火焰和花朵的红色——因为红太夺目了,它在很远的角落,也能抓住你突发的情绪——心跳加速,血液在体温,创造的激情在燃烧……还有,北方瓷土粗糙,釉色对瓷土瑕疵的覆盖能力,也是陶工们不懈努力追求红色的一个客观原因。烧出红,是所有钧窑人的梦想。梦想归梦想,梦想从来与现实有距离。用铜呈现红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高温之下,能提供给铜呈现颜色的温度区间很窄,低一点,颜色出不来,高一点,颜色又飞了。要准确地控制窑温,抓出那稍纵即逝的一抹红,在当时属于高科技了。好在窑工们有理想。有理想就有创造力。长沙窑的窑工最终抓住了那一点红——只是一点,或是偶而为之,也是耳目一新。宋代的窑工们追求完美。随后又成功地在青瓷地上,烧出了得心应手的钧红——可控的带图形或满身的红。“元瓷之紫聚成物形,宋均(钧)之紫弥漫全体。”宋代的钧窑花盆,浑身上下着红衣,很好看。故宫博物院有件玫瑰色的钧窑花盆,红得有些隐约,却也艳丽不俗。台北故宫有件海棠红渣斗式花盆,虽然还不能算真正的大红,但已经很厉害了。“钧窑挂红,价值连城。”“钧瓷不带红,一辈子都受穷。”宋代的钧窑也有其他颜色的。但带红的钧瓷,遗传基因最纯粹。金元的钧窑,窑工们可以随意烧出各种带笔触的红色图案。有件叫“三潭映月”的盘子,盘边三笔,共同朝向中间滴落的一小点,虚实之间,营造了美好的意境。似乎有意,又似乎不是。
按理说,钧窑的陶工们,成功地控制窑温,烧出了太阳、火焰和花朵的颜色,可以很满足,很敖视了——说前无来人,后无继者,一点也不为过。然钧窑陶工们的红色理想,不,应该叫梦想,一直在路上。玫瑰红也好,海棠红也好,三潭映月也好,都没有超过窑工们对于生活中红色的认知。我相信他们还怀揣着一个梦——更为绚丽,更为遥远,只能心领神会——冥冥之中某种不可琢磨的瓷色。
做梦的窑工叫钧生。禹州(今禹州市,古阳翟城)有很多叫钧生的后生。他们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他们年轻,十五六岁,十七八岁,无一不是眉清目秀,相貌堂堂。他们与父母一道,白天去窑厂打工,或做些陶瓷小生意为生。到了晚上,就做梦。钧地月色好,清凉,有诗意。有诗意的月夜,钧生们的梦也恍惚。恍恍惚惚梦见一长者飘来,白发苍苍,布衣翩翩,安详和蔼。说话的声音也极高古了。老人说,他是几千年前的虞舜,上古的帝王呢,原来在颍河之滨,制陶烧陶。这么多年过去了,他掐指一算,如今阳翟城该烧出一种天下第一的宝瓷了。这些日子,他来故地,考察了很多的钧窑人家,最终选定钧生来完成这个任务。老人还约钧生明天到城东北隅见面,手把手教他怎么烧造传世的宝贝。钧生好奇怪,就问,是件有啥稀奇的宝贝呵,要你老人家惦记几千年。老人说,你的梦有多美,宝贝就有多美。钧生更奇了。他在梦里从来都是天马行空的。就连钧瓷的颜色,也被他折腾成了一大堆的颜色,有像太阳,有像月亮,有像星星,有的像云霞,有的像火焰,有的像各种花朵,数都数不过来,这些个颜色能烧么。长者就笑,数不过来就对了。说完,一闪不见了。钧生的梦也醒了。
第二天早上,钧生来到城东北隅。是块野蒿地,夏朝的遗迹古钧台,就在正西不远处。钧生问,你是舜王吗。来人说,是的。钧生赶紧跪地拜师,请老人家赐我烧造宝瓷的手艺吧。舜王说,古钧台是地之中心,在此造瓷,一定会瑰丽无比,名扬四海。两人就开始忙碌。先清理一空地,挖坑造窑。正南方掏个大洞,洞后墙上,又通个烟道。向北开出窑门和窑膛。所有的程序简单,又神秘莫测。窑造好后,舜王带钧生到阳翟城的西北,翻九道岭,到了一座叫“鸠”小山上,采回了陶土——“五彩石”,舜王说这是女娲氏补天遗弃的宝土。接下来,两人又造“碾盘”、“石磙”,用来捣料,造“陶钧”,用来拉坯。拉坯可是陶工的细活。钧生随大人们在窑厂见过好多回了,有些心得,上手自然快,盘、碗、瓶、炉,拉什么像什么,舜王很满意。坯阴干后,该上釉了。上釉也见过,钧生就毛里毛糙地把坯往釉浆里蘸,捞起来放地上,可是没过多久,坯就塌成了一堆烂泥。这下傻眼了,又讨教。舜王说,烧这宝贝,不能跟烧普通瓷器一样,要先烧一次,再上釉呵。钧生就照舜王传授的经验做,上釉前素烧,一下成功了。但这只是完成了一半。大功还没告成,梦想中美丽宝贝还没有来。钧生对烧窑最关键的环节——入窑技术,还不会。他在村里窑厂打工的那些日子,大师傅们根本不可能让他见识入窑的,那可是人家看家的本事,保守着呢。今天,他却要亲自领教舜王传授的独门手艺了。两人从山里砍回松枝和杉条,劈成一尺长短的小块,堆得像小山似的。这天,舜王说,点火吧!钧生一把火就把窑点着了。带香的浓烟,很快弥漫了古钧台。夜里,城东北人家,看见了美丽的烟云在天空里缭绕。那些天,舜王一个人安静地端坐,极少说话。钧生丝毫不敢怠慢,按舜王吩咐,不断地往火炉里添减柴火,一会多几块,一会少几块。烧了三天三夜,从小火烧到旺火,最后一块松柴也烧光了。炉火散发出纯净的青色。舜王说,火候已到,停火!第二天,钧生有些急不可耐地开了窑门。开窑的瞬间,钧生看见了冥冥之中的那一幕:满窑的五彩和宝光,红的像玛瑙,红里透紫;紫的如水晶,紫里藏青;青的似翡翠,青中寓白;白的像丹桂,白里透红……钧生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绚烂的瓷色,这分明人间罕见,梦中才有的缤纷呵!
钧生的故事本是传说。但钧窑不是传说。窑变成就了钧窑人关于瓷色的美好梦想——青瓷之上诞生红(“绿如春水初生日”),红地之上诞生绚烂(“红似朝霞欲上时”)。从青瓷到绚烂,钧窑可谓脱胎换骨。窑变让钧窑的瓷色审美具有了多种可能性。“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高山云雾霞一朵,烟光空中星满天;峡谷飞瀑兔丝缕,夕阳紫翠忽成岚。”同一种釉,千万种变化,已非人力可为。钧窑的窑工们宁愿相信这是神的授意,把自己的手艺创造,附丽于上古帝王传说。手艺人就是本份呵。
最近有部电视剧《大河儿女》很火,也是讲钧窑传说的。故事发生在抗战前后,河南禹州一个叫风铃寨的地方。大致说的是,烧钧窑的贺家掌门人贺焰生和叶家掌门人叶鼎三,两人虽然是手艺人,骨子里还是自私心重。后来两人发生了质的蜕变——从明里暗里斗艺,到团结斗寇。斗艺,窝里斗。斗寇,同仇敌忾。这变化了不起。手艺人,内心往往都比较封闭。饭碗嘛。你盯到我的碗,我盯到你的碟,几十个手艺人,几十门心思,也理解。要是有人来抢大伙的饭碗,又该怎样的心思?我相信编导讲这个故事时,内心很强大。电视剧双主角由陈宝国和赵君担当,二人的表演,升华了钧窑艺人内心的强大。还真要佩服两个老戏骨。奔放,浓烈,但不夸张,表面上的粗枝大叶,暗藏过经过脉的细节处理。有点像钧窑的窑变,恍惚之灿烂,细微之精妙。故事之一讲的是窑变龙凤盘。贺焰生有个原型——当代钧瓷传人任星航。国宝龙凤盘就出于任大师之手。凤盘现珍藏在他的博物馆里。美妙绝伦的凤凰纹,给到此采风的编导高满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任大师低调,本来龙盘也烧出来了,但不是很成功,就没放馆里展示。电视剧里讲述的龙凤盘,是完整的一对稀世珍宝。现实与故事相比,多少有些遗憾。作家高满堂发现了龙凤盘的故事,并把它作为基本元素,讲述钧窑的现代传奇,从某种意义说正好契合了钧窑的审美精神——让梦想照进现实。窑变就是钧窑人的梦想。一寸青釉一窑色。钧窑人就是国人的梦想。今天钧窑作为奢侈品牌,同茅台一起走出国门,让多少人的眼睛为之一亮。我们喜欢青瓷的低调。但该出手时还得出手。套用一句最近流行的话作为钧窑之旅的结尾——给我一米阳光吧,我还你灿烂。
定 窑
中国陶瓷史上,有两种白瓷最深入人心。一是永宣时代的甜白,一是宋时的定白。甜白,从字面上看,偏重内心的美好感受,甜甜的纯洁美。定窑的白,有点像牙的白,更讲究釉色的品质。作为白瓷系的代表作,定窑也因其一流的品质,被列入五大名窑。
虽然青瓷占据了宋瓷的大半部江山,但是陶工们一直没有放弃对白的追求。从工艺的角度,要把青瓷中的杂色一点点去掉,烧出纯净的白色并非易事。从黑陶开始,到青瓷,陶工们一直在挖空心思地琢磨如何提纯——把釉上的杂色斑点去掉。由黑而白的过程,大约经历了一千年。到了唐时邢窑,窑工门就已掌握了这一核心技术。可以说,在定窑以前已经做到了最白——如银似雪。
定窑的工匠们很郁闷。唐时邢窑的窑工门,给后来的定瓷陶工们设置了一道很高的槛。技术上的白,已经不可逾越。定窑的工匠们,需要重新寻找突破口。好在有了宋词和文人书画——可以向内抒写,也可以向外放纵——审美仪式的日常化。工匠们受到启发,另辟蹊径。既然通向白色的路,已经走到尽头,那何不往两旁横向拓展。新的风景区被发现。他们看见了石雕。定州的曲阳,盛产汉白玉。被压抑亿万年的生命,按曲阳玉工的理解,被重新修饰,焕发出花草虫鱼的生机,以及神灵的光彩。定窑陶工们找到了灵感——在白地上作文章。以泥胎为石为玉,以竹木为刀,或塑,或刻,或印……大朵的牡丹和莲菊,各种飞鸟、鸣禽和游鱼……他们不仅把生活中的日常细节,一刀刀复制到瓷胎上,还把关于生活的幸福理想——那种纯精神性的表达,以陶艺的形式,予以再现。
他们崇拜真龙美凤与生俱来。那是家族的梦想,虽然梦想遥不可及,但一直在坚持,历经千年也未曾动摇。
他们一直在努力做精神的贵族。端庄的莲瓣,“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一重莲花就是一重佛呵。
他们渴望世俗的欢娱。游水双鱼,两条青年的鱼,携手戏水,你看我,我看你,彼此欣赏和追慕。一条河都流淌爱情。
他们或许还没有养育孩子。“栓(拴)娃娃”,“抱娃娃”,今天造个瓷娃娃,明天生个胖娃娃。唱歌谣的是北宋定州的陶工,男的叫“赵刚”,是培烧的高手,女的叫“美霞”,专事描画。定州的赵刚和美霞们,烧了一窑又一窑的孩儿枕,生下一屋子的会吃会跑的娃。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们生育的梦想。他们让娃娃们穿“百家衣”,吃“百家饭”,盼着他们能长大,成家,立业,继续把家族的梦想繁衍下去。
定窑娃娃枕,寄托了定州窑工们世俗的梦想,也造就了定窑。《饮流斋说瓷》对定窑的工艺有很高的评价:“北定,其质极薄,其体极轻,有光素、凸花、划花、印花、暗花诸种,大抵有花者多,无花者少,花多作牡丹、萱草、飞凤、盘麶等形,源出泰镜,其妍细处,几疑非人间所有,乃古瓷中最精丽之品也。”用“非人间所有”,来评价民间色彩浓厚的定窑日常器皿,可见定窑的魅力。
“定瓷娃娃(定赐娃娃)”,本是老百姓世俗的美梦。世俗就像草根,地位越卑微,生命越绵延。就连历朝历代的帝王也羡慕之极。坐江山,要一代一代坐下去,直至万世。帝王们差不多天天做江山梦。他们大多数是不缺子嗣的。有一大通老婆在帮他生养,东宫不亮西宫亮。延续子嗣,需要靠很多的老婆来帮忙,看来帝王们还是不自信。乾隆皇帝似乎就不自信。在他钟爱的器物中,就有好多件定窑孩儿枕(估计自己枕一个,皇后和妃子们一人还要枕一个)。有一次,他又搞到了一件,高兴得不得了。乾隆有个癖好,就是一激动就来诗兴。他抚摩孩儿枕,题下几行诗:“瓷枕通灵气,全胜玳与珊。眠云浑不觉,梦蝶更应安。”老实说,诗一般,基本上就是一枕头功效说明书,没怎么拐弯子。不过比打油诗还是要稍好,毕竟或多或少寄托了乾隆的人生理想——渴望在夜里睡个好觉做个好梦。啥才算好觉好梦呢,我估计乾隆大多数时候,还是希望像宋时定州的窑工夫妇那样,也梦个娃娃啥的,明天早上一觉醒来,哪个妃子肚子又报喜了,多好。世上有谁能够不怕死呢?死意味着梦想到此终止。现在流行一种说法——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是,人死了,钱还没花完。没花完,就得找个子嗣继续花。普通人家,家业小是小,但还是家业,得有人继承。何况帝王家那么大的基业,要多少子嗣来接呵!娃娃越多,王子王孙越发旺盛,江山或才更稳当。还有啥理想比江山稳当重要?这恐怕是封建帝王们共性的忧虑。帝王们不能免俗。乾隆也不能。我们普通人等亦是。
(责编:张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