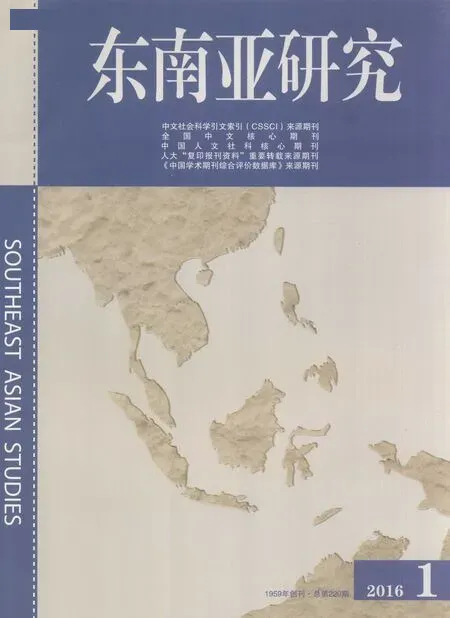新加坡妇女权利与国家父权制关系试析
2016-03-19范若兰
范若兰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广州 510275)
新加坡妇女权利与国家父权制关系试析
范若兰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广州 510275)
[关键词]妇女权利;国家父权制;新加坡
[摘要]新加坡是典型的国家父权制,奉行国家至上、家庭为根、好政府和强政府。新加坡政府对妇女定位是“贤妻良母”和“好劳动力”,妇女既要承担照顾家庭培养孩子的传统角色,也要为国家经济增长作出贡献。政府的妇女政策围绕着这两个有点矛盾的定位不断调整,新加坡妇女权利因应国家父权制的需要而变化。政府是从国家利益和家庭利益的视角,而不是从性别平等和妇女利益的视角来提倡妇女权利,所以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升妇女权利。
Abstract:National patriarchy remains entrenched in Singapore, which believes in the primacy of the nation, the fundamental value of the family, thus pursues a good and strong government.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positions women as “virtuous wive and caring mother” and “good labors”, in which women are not only supposed to bear the traditional role of taking care of the family and children, but also to make a contribution to national economic growth. Therefore, government’s policy on women adjusts constantly around these two somewhat contradictory positions, and women’s rights change in the light of the need of national patriarchy as a result.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government promotes women’s rights for the sake of national interests and family interests, rather than gender equality and women’s interests, so it is impossible to enhance women’s rights fundamentally.
国家父权制是父权制的延伸,是一种等级制的社会结构,呈现为国家/家庭、中央/地方、富人/穷人、主体民族/少数民族、男人/女人的等级秩序。在国家父权制主导下,不同阶级、族群、性别的政治权力、资源分配均不平等。“国家作为这一切的反映,其本质只能是男权的。”[1]新加坡是典型的国家父权制,奉行国家至上、家庭为根、好政府和强政府,人民行动党政府就像一个充满威严的大家长,事无巨细管理和控制一切,因而,妇女权利变化维度和走向也处于政府的掌控之下。
学术界对新加坡妇女的研究以妇女就业、婚姻家庭、人口政策、女性参政为主①参见Phyllis Chew, The Singapore Council of Women and the Women’s Movement,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No.1, 1994;Aline K. Wong and Leong Wai Kum, eds., Singapore Women: Three Decades of Change,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3;Lenore Lyons,A State of Ambivalence: The Feminist Movement in Singapore, Leiden: Brill, 2004;M. Shamsul Haque, “Representation of Women in Governance in Singapore: Trends and Problems”,As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8, No.2, 2000;〈新〉苏瑞福著,薛学了等译《新加坡人口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对国家父权制与妇女权利的关系则鲜有论及[2]。其实,目前世界上的民族国家都属于国家父权制,研究这一议题对于深入分析父权制的形态及其对妇女权利的形塑方式颇有裨益。本文以新加坡典型的国家父权制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其国家父权制特征,探讨其对新加坡妇女权利变化的影响。
一国家父权制特征及对妇女角色的定位
新加坡是一个1965年才独立的城市国家,由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等种族构成,建国之初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经济落后、种族隔阂、资源贫乏、缺乏国家认同。为了使新加坡能在外部敌视和内部纷争的困局中生存下来,人民行动党建立高效而廉洁的强政府,大力发展经济,力促种族团结,强调秩序和稳定,建构国家认同,最终使新加坡成为东南亚最富裕、繁荣、稳定的国家。新加坡国家父权制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 国家至上,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为了新加坡的生存和发展,为了建构国家认同,人民行动党政府强调国家利益至上。早在独立之初,人民行动党就提出“生存的意识形态”:(1)无论如何,决定国家利益的是人民行动党,新加坡的生存就等于人民行动党的生存;(2)为了新加坡的生存,国民要不惜奉献一切,甚至为国家牺牲自己;(3)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的人力资源,当须实行能力社会主义[3]。第一条将人民行动党与国家的生存联系在一起,第二条则强调国家利益重于一切。1982年,李光耀总理提出用儒家的“八德”(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作为治国之纲,其“忠”就是要忠于国家,国家利益第一,加强群体意识[4]。当新加坡已取得较高的发展成就时,1991年政府又提出“共同价值观”,即: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5]。第一条就是“国家至上”。实际上,在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大旗下,人民行动党将“新加坡的生存与人民行动党的生存结合在一起,为人民行动党威权统治提供了合法的意识形态”[6]。新加坡是党国合一,人民行动党=政府=国家,人民行动党是国家权力中心。
第二, 家庭为根,稳定社会。新加坡政府强调家庭的重要性,因为这是社会稳定的基石。李光耀总理一再指出:“家庭是绝对重要的社会单位。从家庭,到大家庭,到家族,再到国家。”[7]这个稳定系统是建立在父权制基础之上的,李光耀努力维护这样的家庭系统,“我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加以避免的,就是决不能让三代同堂的家庭破裂……这是一个家庭结构、社会结构、把家庭单位连成一体的伦理关系和结合力的问题。”[8]1982年的治国之纲的“孝”就是要孝顺长辈,尊老敬贤。1991年共同价值观的第二条就是“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家庭是承担养育孩子、照顾老人、提供亲情的场所,家庭稳定则社会稳定。正如1994年吴作栋总理在国庆节庆典上强调,传统家庭观念是“价值基石”,提供了新加坡在21世纪生存的基础,“我们必须高举这些价值,稳定家庭和我们的国家”。所以政府要加强新加坡传统家庭观念,政策要确保一家之主的权利、利益和特权,以便他能规范家庭成员的责任和义务[9]。可见,家庭在国家父权制中处于重要地位,体现了家国同构理念。
第三, 好政府与强政府,尊重和服从权威。新加坡是威权政治,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实行精英治国。精英们毕业于名校,历经层层选拔,进入政府,内阁基本上是由军官、律师、医生、工程师、银行家和教授组成。人民行动党政府高效而廉洁,是干预能力极强的强政府。这个强政府不仅要捍卫国家主权、促进经济发展、控制政党和选举,还要控制和指导国民的行为、言论、婚姻和生育。实际上,国家是放大的家庭,政府及领导人是扩大的一家之长,自然有权力将其控制触角深入到家庭和个人的方方面面。
第四, 等级社会结构。新加坡的等级无处不在,从体现阶级的“富人—中产阶级—穷人”,“精英—草根”,体现在种族方面的“华人—印度人—马来人”,到语言的“英语—华语—方言”之分以及性别的“男人—女人”,等级结构深入政府管理和人心,小孩子从小经历的学校分流制,就使他们认识到人是分等级的,而不断进行的等级划分要伴随他们一生。新加坡媒体人李慧敏指出,新加坡政府 “似乎非得要用很复杂的分类法把学生和国民分等级才能进行管理”[10]。而等级是父权制的主要表现之一。
国家父权制确立了等级制权力结构,性别与阶级和种族一起,构成这一等级制结构的要素。在国家父权制下,“国家不仅难以平等地对待妇女,而且它还不同程度地构筑了男性与女性的关系。在许多方面,国家权力的使用是为了强化对妇女的控制。”[11]国家父权制其实是将妇女角色从家庭、家族控制上升到国家掌控,它与家庭(私人)父权制既有继承,也有区别,正如沃尔拜精辟指出的,私人父权制的特征是家庭中父权关系的主宰地位,公共(国家)父权制则为雇佣和国家所宰制。前者的剥夺模式是个人的,是丈夫或父亲的剥夺;后者的剥夺模式则是集体的,是许多男人的共同行为的结果。前者的主导策略可以归纳为排拒,即将妇女排拒于公共领域活动之外,从而将她们限制在家庭之内;后者的主导策略是隔离,即允许妇女进入所有领域,但就在这领域内被隔离并处于从属地位。”[12]
从性别视角来看,新加坡国家父权制所推崇的“家庭为根”部分继承了家庭父权制,这个家庭建立在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男主女从等性别秩序基础之上。正如政府强调的“丈夫是家庭的支柱和核心,而妻子则是丈夫的辅助者”[13]。所以,新加坡政府对妇女的第一个定位就是“贤妻良母”,照顾好孩子和家庭,辅助丈夫。而“国家至上”又区别于家庭父权制,要求为国家奉献一切,所以新加坡政府对妇女的第二个定位是“好劳动力”,为国家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可以说,政府从现代和传统两方面塑造新加坡妇女,她们既要成为贤妻良母,承担照顾家庭培养孩子的传统角色,也要成为好劳动者,参与国家经济发展。
二国家父权制与妇女权利的变化
本质上,“贤妻良母”与“好劳动力”这两个定位是矛盾的,有时难以兼顾,因此新加坡政府的妇女政策围绕着这两个有点矛盾的定位不断调整,妇女权利因应国家父权制的需要而变化。
1.新加坡妇女的教育权得到大力促进。
妇女要成为“贤妻良母”与“好劳动力”,都需要接受至少中学以上的教育,这样她们才能更好地培养孩子和辅佐丈夫,承担职业所要求的技能,所以新加坡政府积极促进女子教育,并取得显著成绩。1957年新加坡女性识字率仅为33.6%,1990年上升到84.4%[14],2001年为88.7%[15]。受过中学以上教育的女性大幅度增加,1960年新加坡女中学生占中学生总数的39%,1980年达到51.5%,以后一直占一半左右[16]。1980年女大学生占大学生总数的32.2%,1990年上升到43%[17]。男女教育机会平等,但所学专业却有较大差别,女生在人文社科和师范专业比例较高,而在理工专业人数较少。以新加坡国立大学为例,1991年女生占该大学学生总数的53.9%,其中在人文社科专业占69.2%,在法律专业占50.7%,在财会专业占49.2%,但在机械专业只占15%,计算机专业占39.5%,在医学专业占34.9%,在牙医专业占20%[18]。这组数据显示,父权制所规范的性别分工反映在学生的专业选择上,女生倾向学习所谓“适合”女性的专业。新加坡政府非但不致力消除专业上的性别差异,反而加以鼓励,如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鉴于女生过多,1979年规定招收的女生不得超过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无论她们成绩多高,这一歧视性政策的依据是许多医学院毕业女生在结婚和生子后会放弃医生职业,“浪费”了她们的医学教育,因此限制女生可以降低政府和大学用在她们身上的资源*这一歧视性政策直到2003年才被取消。。这其实深刻体现了贤妻良母定位与职业和专业选择的冲突。
2.新加坡妇女的就业权得到大力提倡。
新加坡政府一直将经济发展放在首位。自独立以来,新加坡抓住国际大分工的机遇,实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促进了经济起飞和高速增长,新加坡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发展经济需要劳动力,因此促进妇女就业也是新加坡政府的关注重点。1957年新加坡女性就业率只有21.6%,1966年为24.2%,1974年为37.4%,随着经济发展和政府的大力推动,女性就业率大大提高,1984年为44.3%,到1994年高达50.9%[19]。
新加坡妇女在就业上面临的主要困难之一是如何兼顾家庭和职业,通常她们在婚前就业,生育后退出职场。1984年新加坡有51.4%的职业女性因照顾家庭和孩子而中止就业,有24.1%的妇女因结婚而中止就业,同年因上述两个原因中止就业的男子只有0.4%和0.1%[20]。政府还实行弹性工作制以促进妇女就业,也鼓励私人部门多设灵活工作时间,方便妇女参加工作。但弹性工作制作用有限,因为70%的妇女想要灵活就业时间的工作,但只有2.8%的职位是半职的[21],远远满足不了需要。
3.新加坡妇女的参政权得到有限鼓励。
新加坡宪法规定妇女有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参与政治的权利,但长期以来妇女政治参与程度不高。表现一是妇女非政府组织不活跃,只有1985年成立的新加坡妇女行动与研究协会(Association of Women for Action and Research,AWARE)比较活跃,提出很多性别议题和建议。二是女议员比例长期较低,直到21世纪后才有较大增长。新加坡1968年大选国会女议员比例只有1.7%,1972年、1976年和1980年大选议会中的女议员人数为零。1984年大选女议员占3.8%。在21世纪之前,新加坡历届国会女议员比例从未超过5%。2001年大选有较大突破,人民行动党推出10位女候选人,全部当选,女议员比例达到11.8%。2006年大选女议员达到21.2%,2011年大选女议员比例为22.2%*参见新加坡大选网站http://www.singapore-elections.com和国际议会联盟网站http://www.ipu.org/wmn-e/world-arc.htm。三是女性担任行政官员的比例较低。迄今新加坡最高权力职位中没有女性,总统、总理、副总理都是由男性担任,在部长一级,迄今只有两位女性,即2009年、2012年出任总理公署部长的陈惠华和傅海燕。即使在中下级行政职位中,女性比例也不高,90年代末女性在社区中心管理委员会占11.3%,在居民委员会中占18.5%,在市民咨询委员会只占5.6%。她们担任这些机构领导职务的人数更少,如在81个市民咨询委员会中只有1位担任主席职位的女性,在401个居民委员会中只有50人,在109个社区中心管理委员会中只有3位[22]。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对妇女的定位是贤妻良母和好劳动力,而不是充当政治家去参与政治和管理,所以人民行动党虽然建立了妇女团,但目的是让其动员女选民支持该党,而不是加强妇女参政权,人民行动党也就不积极推出女候选人。1980年记者提问为什么议会中没有女议员时,当时任人民行动党竞选委员会主席的吴作栋回答,找不到合适的候选人,“你能不能找到一位女性,她拥有像男性一样的品质,和男人一样能干,她的丈夫或未婚夫或男朋友会同意她从事这样一份危险的职业。”[23]在吴看来,政治是危险的职业,不适合女性,女人只有像男人一样能干,还要得到丈夫或男友的同意,才能从政。随着民主化浪潮发展,要求增加女性议员的呼声渐高,李显龙总理表示愿意推举更多女候选人,但他又一再说,“我思考了很长时间,吸纳女性融入政治会比男性更困难,加上她自己的事业和她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责任,女性很难应对作为议会议员的要求。”[24]也就是说,贤妻良母的角色定位阻碍了女性参与政治的机会。
4.新加坡妇女的生育权受到直接控制。
新加坡是小国,人口规模与其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因此女性的生育一直是政府关注的重点,换言之,国家父权制取代家庭父权制,直接干预妇女的生育。20世纪60、70年代政府认为人口过多,开始实行家庭计划,宣传“两个孩子恰恰好”,妇女是避孕、绝育的主体,承担起减少人口的重任。80年代政府开始注重人口质量,鼓励高学历母亲多生多育,1984年颁布政策规定生育三个孩子的高学历母亲有为所有子女选择最好学校的优先权,这项政策引发众怒,政府不得不取消这一政策,代之以规定生育三个孩子的高学历女性可获得奖励,每一个孩子可获得每年5%的额外收入,另外她的子女可享受税款减免,第一胎为5%,第二胎为10%,第三胎为15%。与此同时,政府采取措施使贫困和低学历夫妻不要生育太多孩子,如生育一到两个孩子实行绝育者获得一万新元补助,生育三胎以上者分娩费用提高,目的是“通过对学历较低的女性施加更大的经济压力来迫使她们减少生育”[25]。1987年新加坡政府重新调整人口控制政策,改为增加生育,允许妇女生育三至四个孩子,为此改变个税减免政策,还改革带薪产假制度以鼓励生育。2001年政府规定生育第三胎的女性也可以享有八周带薪产假,2004年这一规定进一步放宽,女性雇员生育第四胎时也享有带薪产假,而且产假时间延长到12周。
需要指出的是,所有家庭计划几乎都是针对女性,有学者指出:“对于出生率下降,政府指责新加坡华人妇女,尤其是高学历女性,因为她们自私、职业狂,不愿结婚,而新加坡华人男性的自私、工作狂、大男子主义却不被讨论或被认为是‘问题’的一部分。”[26]
5.新加坡妇女的婚姻家庭权利得到维护
人民行动党政府重视家庭,早在1961年就通过《妇女宪章》(Women’sCharter),规定所有非穆斯林家庭都应为一夫一妻制;结婚必须进行登记;已婚女性有权保留本姓;女性有权从事任何职业;女性有权管理和处置在其名下的财产;在孩子的照顾和赡养问题上,妻子和丈夫具有同等权利,并有权从丈夫处获取赡养费。通过实施《妇女宪章》,国家父权制成功介入私人领域,极大地冲击了家庭父权制,正如彼得森指出的:“通过加强对婚姻、儿童监管、财产及公民权继承的立法,国家控制了国家成员/公民身份的再生产。”[27]
政府强调稳定的婚姻家庭,所以对高学历女性不婚现象忧心忡忡。1983年8月14日李光耀总理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发表鼓励高学历女性生育和结婚的讲话,他认为基于优生学,高学历的男性应该娶高学历的女性,才能生出聪明的孩子,而男性囿于传统文化,只愿意娶各方面低于自己的女子,使得高学历的女子嫁不出去[28]。为此政府还建立社交发展署(Social Development Unit,SDU),为在政府部门、国企工作的高学历男女提供社交、联谊、婚介服务,后又建立社交俱乐部(Social Development Service,SDS)为非大学学历的大龄青年提供上述服务。也就是说,由政府充当红娘来促成单身男女的婚姻。
家庭暴力影响到家庭的稳定,也受到新加坡政府的关注。早在1980年政府就对《妇女宪章》进行修订,对遭受家庭暴力或暴力威胁的配偶或儿童进行救助,法庭根据“个人保护令”和“家庭禁制令”发出逮捕令,警察可依此逮捕[29]。但妇女组织认为修订后的《妇女宪章》在处理家庭暴力时还有许多不足之处,如家庭暴力更多被认为是家务事,警察不应过多干预。1995年官委议员苏英(妇女行动与研究协会前主席)提出“家庭暴力法案”(Family Violence Bill),被议会所接受。1997年议会通过《妇女宪章修正法令》,明确规定了家庭暴力的定义,还规定了相应的处罚,这个修正案基本接受了妇女组织的建议,为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提供更多保护[30]。
国家父权制要求妇女既能成为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同时也能成为发展国民经济的“好劳动力”,所以提倡和维护妇女的教育权、就业权、参政权和婚姻家庭权,并掌控女性的生育权,极大地冲击了家庭父权制。但不论是在国家父权制还是在家庭父权制之下,女性的首要角色仍是“贤妻良母”,李光耀虽然优先发展经济,但他对女性的定位首先是母亲和妻子,当“贤妻良母”与“好劳动力”冲突时,后者要为前者让位,“我们必须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政策,……从而使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生育更多的孩子。……我们需要提供平等的工作机会,但是我们不能让女性去从事那些不能让她们兼顾母亲角色的工作。……你们(女性)不可能内外兼顾,即完成一个诸如医生、工程师等全日制的辛苦工作,又照顾好家庭和孩子。”[31]
三国家父权制与妇女权利关系解析
新加坡经过多年发展,已迈入发达国家行列,新加坡政府提倡性别平等,女性的教育权、就业权、参政权、婚姻家庭权利得到维护和提升。但是,新加坡的性别平等还有较大差距,决策中的性别主流化程度也较低,与其发达国家的地位并不相称。其根源在于新加坡国家父权制的“国家至上”、“家庭为根”、“好政府和强政府”、等级结构等特征,决定了政府是从国家利益和家庭利益,而不是从妇女利益来提倡妇女权利,所以政府尽管宣称支持性别平等,但在实际上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升妇女权利。
“国家至上”决定了妇女权利变化取决于是否有利于国家利益,符合国家利益时,妇女的相关权利才能获得。女子教育有利于母亲培养合格的下一代,有利于培养合格的劳动者,所以妇女的教育权得到大力促进;妇女就业有利于经济发展,所以女子就业权得到大力提倡,与之相应,政府实行带薪产假和弹性工作制等,女性的工作权益得到一定程度的维护,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在就业上有与男人同等的权利。事实上,当新加坡劳动力短缺时,政府大力促进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但当失业率高时,妇女第一个被解雇,如1974年新加坡经济不景气,年底有16,900人被解雇,其中79%是女性[32]。女性的生育权也完全取决于国家的需要,人口多时,政府鼓励妇女节育,人口少时,政府鼓励妇女生育,带薪产假制度和弹性工作制只是因为要平衡母亲和职业角色,也就是生育和经济发展才受到重视。甚至新加坡妇女的公民权也因国家的人口需要才能得到平等对待。新加坡宪法规定,对于出生在新加坡之外的人,如果父亲是新加坡公民,他(她)可取得公民权,如果母亲是新加坡人而父亲是外国人,他(她)不能取得公民权;外国籍妻子嫁给新加坡丈夫可申请公民权,但新加坡女子嫁的外国籍丈夫不可申请公民权。这是一种性别歧视条款,妇女组织多次要求修改,无果。但当政府为了增加人口吸引海外人才到新加坡工作时,这种歧视条款就被修改了。1999年议会通过修订的《公民身份法》,允许新加坡妇女的外籍丈夫申请新加坡公民身份,2004年议会修订公民身份法,规定新加坡母亲在国外生育的孩子有资格获得新加坡公民身份[33]。
“家庭为根”决定了妇女权利取决于是否符合男外女内、男主女从、一夫一妻的性别规范。在新加坡政府看来,“在一个家长制社会中,由于男女之间的不对称性,要求男女平等是不可能和不明智的,因此任何对男人是一家之主的传统结构的改变都是不现实的。”[34]新加坡一些政策存在性别歧视,如妻子没有工作,丈夫可以声称为妻子每年少交1500新元的收入税,但如果丈夫没工作,只有妻子工作,她却不能要求为其夫减少交税,因为这不符合男人是养家者的性别观念。此外,男公务员的家庭成员可以享受医疗或其他福利,而女公务员的家庭成员却不能享有同样待遇。妇女组织对此提出批评,吴作栋总理回应说:“妇女组织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改变公务员条例中有关女公务家庭成员的医疗福利的规定……但是这将改变男女在家庭中的责任。亚洲社会总是男人负起责任,他是最重要的养家者,而不是妻子,如果……丈夫能依靠妻子的医疗福利,新加坡男人将变成一个不重要的角色,像在英国一样。”[35]由于这不符合男主女从的性别规范,所以政府一直坚持公务员条例中的这一性别不平等规定,直到2004年才修改。还有《妇女宪章》规定离婚时丈夫必须向妻子支付赡养费,却没有妻子向丈夫支付赡养费的条款。而妇女组织认为时代已经改变,一些家庭是妻子出外赚钱养家,丈夫在家照顾孩子,所以《妇女宪章》修正案也应包括妻子向丈夫支付赡养费。但这一建议因与男外女内、男主女从的传统性别规范不符,未被接受。
政府强调稳定的一夫一妻制婚姻家庭。家庭暴力破坏家庭和社会稳定,所以反对家庭暴力得到政府的支持,多次修改相关立法。政府对不婚现象忧心忡忡,甚至由政府充当红娘来促成单身男女的婚姻。政府反对未婚生育和单身家庭,认为这是对传统婚姻家庭的破坏,所以不批准未婚母亲和35岁以下单身人士申请组屋。正如传达政府意志的《联合早报》的一篇社论《维护传统婚姻观念刻不容缓》所述,如果批准这些人的组屋申请,就是“鼓励”这种风气,所以政府“必须同时通过政策和公众教育,对维护传统的家庭结构和婚姻观念有所动作,最重要的是传达,政府固然同情单身者的处境,但是,不能因此而鼓励更多年轻人选择单身。”[36]对于处于贫困中的未婚母亲,新加坡政府不愿提供救助,因为她们违背传统婚姻伦理,正如新加坡一位代部长林得恩指出的,“年青的未婚妈妈确实需要我们的帮助,她们需要我们的理解。……但是在面向未婚妈妈建立援助体系的时候,我们要十分谨慎,以避免其他年轻女孩们仿效。因为这样会弱化家庭的作用,并削弱个人责任感。”[37]
“好政府与强政府”决定了政府以效率、发展、稳定为先,以公正、民主为后,压制了包括妇女在内的民众的政治参与权。李光耀总理明确提出:“国家要发展,纪律重于民主。民主发达导致无纪律和紊乱的行为,这对发展根本不利。”[38]他认为追求民主不能带来秩序,追求平等不能带来发展,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只能导致混乱,建立平等社会违背了等级秩序。新加坡政府不致力于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所以女性政治参与也长期处于低水平。李光耀认为新加坡发展最好的年头是1965年到1981年,因为“在这一段时间里,新加坡享有历来最高的经济和社会进步,也正是在这些年里,我们政治稳定,在国会里没有好斗、吹毛求疵的反对党,这并不是偶然的事。”[39]而恰恰是在李光耀眼中最好的年头,新加坡女性政治参与水平最低,没有活跃的非政府妇女组织,议会中没有一个反对党议员,也没有一位女议员,世所罕见。人民行动党政府奉行精英治国,政府强调能力是获得提名推荐的最重要条件,不愿采取促进妇女参政的配额制,尽管妇女组织为了增加女议员人数,建议在新加坡实行的集选区选举中,除了一定要有一位马来人或印度人候选人外,还要有一位女候选人[40]。而且在2006年和2011年大选中集选区的竞选团体几乎都有1至2位女候选人,但政府拒绝将其法律化或制度化,因为这与精英治国相悖。
建构主义的教学设计是自上而下地展开教学进程,即首先呈现整体性任务,让学习者尝试解决问题并发现完成整体任务需要事先完成的各级子任务及其所需的知识技能。而传统教学设计则是自下而上,从小单元到整体知识。
在等级结构下,权利与等级联系在一起。精英享受更多的机会和奖励,“差生”则被早早分流。即使是生育权也分了等级,高学历母亲被鼓励多生,而低学历母亲则被迫少生。
新加坡政府对妇女权利和性别平等的推进具有极强的功利性,提高妇女权利的出发点和目标是国家利益,而不是性别平等。所以新加坡尽管已进入发达国家,但其政治民主和性别主流化却落在后面。有学者精辟地指出:“事实上,这种强调对妇女的需要而不是权利,在新加坡各级部门都能看到。要理解女性在政治、公务员队伍和地方管理中的代表性,这种区分十分重要。一方面是妇女的权利,另一方面是经济、政治和管理的需求。当代表性是基于后者的需求,它就是不确定的,因为这些需求是不断变化的。当代表性是基于妇女的民主权利,它就是更真实的,因为它基于进步的公正原则,是不能改变的。”[41]
新加坡国家父权制决定了妇女权利从属于国家,这种基于国家利益而不是基于性别平等的原则,不利于真正提高妇女权利,也不利于性别主流化。
【注释】
[1] 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三联书店,1995年,第229页。
[2] Stephanie Lawson, “Patriarchy and Resistance in Singapore”,in Maja Mikula, ed.,Women,Activism,andSocialChange, London: Routledge, 2005.
[3] 〈日〉田村庆子著,吴昆鸿译《超管理国家——新加坡》,台北:东初国际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第56-57页。
[5] White Paper,SharedValues, Singapore National Printers, 1991.
[6] 卢正涛:《新加坡威权政治研究》,第174页。
[7] 李光耀:《新加坡的改变——李总理向国大与南洋理工学生发表演讲全文》,《联合早报》1988年8月30日。
[8] 〈新〉《联合早报》编《李光耀40年政论选》,新加坡:现代出版社,1994年,第411页。
[9] Goh Chok Tong, “Moral Values: The Foundation of a Vibrant State”, National Day Rally Address, 21 August 1994.
[10] 〈新〉李慧敏:《成长在李光耀时代》,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51页。
[11] 〈英〉罗宾·科恩、保罗·肯尼迪,文军等译《全球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30页。
[12] Sylvia Walby, “Women and Nation”, 载陈顺馨、戴锦华选编《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80-81页。
[13] 孙小迎主编《东南亚妇女》,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9-60页。
[14] Mark Grace C. L,Women,Education,andDevelopmentinAsia:Cross-NationalPerspectives, New York: Garland Pub, 1996, p.147.
[15]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3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国财经出版社,2003年,第322页。
[16] Mark Grace C. L,Women,Education,andDevelopmentinAsia:Cross-NationalPerspectives, p.137.
[17] Singapore Ministry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WomeninSingapore:ACountryReport, Singapore, 1995.
[18] Mark Grace C. L,Women,Education,andDevelopmentinAsia:Cross-NationalPerspectives, p.148.
[19] 范若兰:《香港和新加坡妇女就业模式比较》,《港澳经济》1996年第11期。
[20] Hoeleen Heyzer ed.,DaughtersinIndustry:WorksSkillsandConsciousnessofWomenWorkerinAsia,Asian and Pacific Development Centre, Kuala Lumpur, 1988, p.363.
[21] M. Shamsul Haque, “Representation of Women in Governance in Singapore: Trends and Problems”,AsianJournalofPoliticalScience, Vol.8, No.2, 2000, p.76.
[22] Seet Ai Mee, “Singapore”,i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UN, ed.WomeninPoliticsinAsiaandPacific,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1993, p.152.
[23] Jenny Lam-Lin, “Voices and Choices, The Women’s Movement in Singapore”, Singapore: Singapore Council of Women’s Organisations and Singapore Baha’I Women’s Committee, 1993, p.122.
[24] Wil Burghoorn, Kazuki Iwanaga, Cecilia Milwertz and Qi Wang, eds.,GenderPoliticsinAsia:WomenManeuveringwithinDominantGenderOrders, Copenhagen: NIAS Press, 2008, p.204.
[25] 〈新〉苏瑞福著,薛学了等译《新加坡人口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20页。
[26] John Clammer, “Reinscribing Patriarchy: The Sexual Politics of Neo-Confucianism in Contemporary Singapore”,JASO:JournaloftheAnthropologicalSocietyofOxford, No.3, 1997, p.253.
[27] V. Spike Peterson, “Gendered Nationalism: Reproducing ‘Us’ versus ‘Them,’” in Lois Ann Lorentzen and Jennifer Turpin, eds.,TheWomenandWarReader,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8, p.43.
[28] 〈新〉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经济腾飞路》,外文出版社,2001年,第128-130页。
[29] Aline K. Wong and Leong Wai Kum, eds.,SingaporeWomen:ThreeDecadesofChange,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3, p.262.
[30] 《新加坡重视解决家庭暴力问题》,2007年11月28日,http://news.sohu.com/20071128/n253608588. shtml,2013年7月30日。
[31] Lenore Lyons,AStateofAmbivalence:TheFeministMovementinSingapore, Leiden: Brill, 2004, p.30.
[32] H.C. Chan, “Notes on the Mobilization of Women into the Economy and Politics of Singapore”, in Wu The-Yao, ed.,PoliticalandSocialChangeinSingapore, Singapore: ISAS, 1975, p.26.
[33] 〈新〉苏瑞福:《新加坡人口研究》,第267-268页。
[34] 孙小迎主编《东南亚妇女》,第59-60页。
[35] Goh Chok Tong, “Moral Values: The Foundation of a Vibrant State”, National Day Rally Address, 21 August 1994.
[36] 《联合早报社论: 维护传统婚姻观念刻不容缓》,《联合早报》2012年10月16日。
[37] Lenore Lyons,AStateofAmbivalence:TheFeministMovementinSingapore, Leiden: Brill, 2004, p.34.
[38] 〈美〉 约翰·奈斯比特著,蔚文译《亚洲大趋势》,外文出版社,1996年,第64页。
[39] 〈新〉《联合早报》编《李光耀40年政论选》,新加坡:现代出版社,1994年,第172页。
[40] Jill M. Bystydzienski and Joti Sekhon, eds.,DemocratizationandWomen’sGrassrootsMovement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81.
[41] M. Shamsul Haque, “Representation of Women in Governance in Singapore: Trends and Problems”,p.77.
【责任编辑:郭又新】
Women’s Rights and National Patriarchy in Singapore
Fan Ruolan
(School of Asian Pacific Studies,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Keywords:Women’s Rights; National Patriarchy; Singapore
[中图分类号]D733.98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099(2016)01-0004-0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东南亚女性政治参与研究”(10YJA810006)。
[作者简介]范若兰,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导。
[收稿日期]2015-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