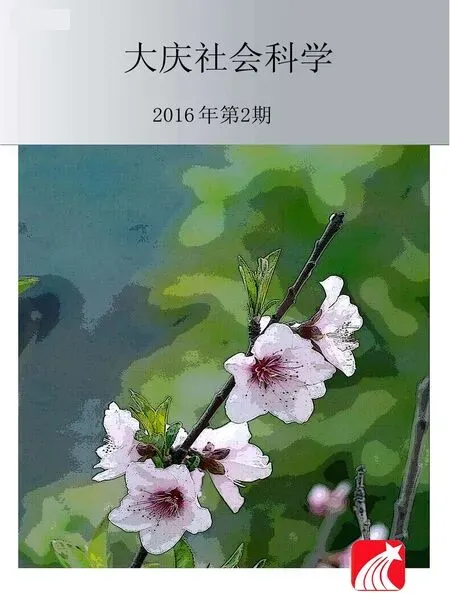社会治理视阈下的负面社会心态研究
2016-03-19王真卓
王真卓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北京 100091)
社会治理视阈下的负面社会心态研究
王真卓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北京 100091)
社会心态反映社会现实,又会反作用于现实。不良的社会心态折射了现实社会存在的问题,又会对社会的发展稳定和良性运行产生不利影响。社会治理的应有之义包括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社会稳定的内涵、社会心态状况与社会治理的实际效能密切相关。为此,重视并积极引导负面社会心态是加强社会治理的必然要求。
典型负面社会心态;社会焦虑;社会仇视;社会戾气
社会心态是指一定时期内社会群体普遍具有的代表性的心理特性和心理倾向。社会心态是反映现实人民生活状态的晴雨表,还是社会未来变化走向的风向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5)》中指出:较之2014年的网民情绪指数,2015年网民的情绪主要集中在社区民生类话题,并且负面情绪较为明显[1]。这一预警也提醒我们更加重视研究社会负面心态。
一、典型的负面社会心态及其成因
社会焦虑。社会焦虑是社会群体成员普遍性焦躁、忧虑、困惑迷茫,甚至抑郁压抑的心理状态。社会焦虑不同于个体层次的焦虑情绪,它已经成为一种微观层次的社会通病。社会焦虑已经几乎覆盖整个人群,无论是处境好与坏的各个阶层都存在着焦虑心态[2]。中国青年报一项社会调查(2134人参与)数据显示:34.0%的受访者经常产生焦虑情绪,62.9%的人偶尔焦虑,只有0.8%的人表示从来没有焦虑过。据报道,相比5年前,有47.8%的人更焦虑,这表明焦虑已经成为现代中国人的一种生活常态[3]。
究其社会焦虑的原因,根本还是源于对现实生活和未来风险的不安全感、不确定感和不可预期感。这与当前我国社会的快速转型期和改革的深水期背景密不可分。一位西方评论家曾感叹:“西方社会100年内的现代化转型,在中国被压缩在30年内进行着”。社会变化之快,新事物、新观念、新行为方式的不断涌入,让人们心理“无法承受之快”,从而出现价值性焦虑。人们不知道什么价值可以相信,可以皈依,可以坚持,在精神生活领域处于虚空状态。更重要的是,焦虑与人们的切身利益有关,人们为自身基本的生计和健康担忧。“新的三座大山”即“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是当下不少人的头等忧虑,还有为自身社会流动机会上升滞缓的忧虑。总之贫富悬殊的强烈反差压力以及改变自身现状的无力、无助、无奈感,使人们不能以平和的心态坦然处之而忧虑忡忡。
社会仇视。社会仇视心态主要表现为仇富、仇权,一般是因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悬殊而引发的穷人对富人和权力阶层的抵触或仇视心理。“官二代”“富二代”“富家子”“红二代”,这些标签化的词语就隐含着低收入阶层“羡慕嫉妒恨”的情结。现实生活中许多实际案例,如“杭州飙车案”“郭美美事件”“我爸是李刚”等,这些涉事者一定被“口诛笔伐”为“有钱有势者”,他们的肇事行为往往会激起一片民愤民恨。根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进行的关于“青年人眼中的中国富豪”(3990人)的调查显示:近七成人认为中国富人的整体品质是“很差”或“较差”,认为中国富人身上最缺失的三种品质是:社会责任感、合法致富和有爱心。另外,人们仇视权力阶层主要表现为“仇腐”,仇视权钱交易、以权谋私、损害人民利益。
人们仇视情绪背后根本原因是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社会分配结构不均衡。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成员个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都在不断拉大。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9,超过国际公认0.4的贫富差距警戒线[4]。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巨大的贫富差距直接引起低收入群体的仇视心理。其次是相关的社会保障机制和公共服务的不完善。一些社会成员的基本利益没有得到保障甚至受损,影响了其基本生存发展条件,引起民怨和不满。除外,富人的“非法致富、为富不仁、过分炫耀,追求奢侈”和权力阶层的“贪污腐化,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中饱私囊”,这些行为招致民恨。一些富人阶层先富起来后,鲜于回馈社会,对慈善事业也漠不关心,不能体恤“民生之多艰”,甚至损害弱势群体利益。而部分权力阶层的“在其位,不谋其政”,滥用权力,与民争利,腐败行为招致民众不满、仇视。
社会戾气。社会戾气是指少数社会成员情绪的极端化和暴戾化,“遇到事情即爱使狠斗勇取径极端的心理,会以多种暴力形式体现出来,如话语暴力、行动暴力以及其他各种隐性的暴力与强迫”[5]。因琐事相争,就拔刀相向;因心怀怨恨,就伤及无辜;甚至因“人群中多看了一眼”,就怒发冲冠。摔死孩子、公交纵火、商场砍人等,这些极端暴力行为在现实生活中频频上演。而在网络虚拟社会,一些网络暴民利用网络社会的匿名性,因观点不和,即会言语激进,人身攻击,话语暴力层出不穷,《一代宗师》掀起的网络骂战就是暴戾心态的典型事例。现实生活还是网络社会中,这些不顾后果,暴力发泄私愤的不理性行为充分说明民众中累积的戾气之重、戾气之浓。
戾气从何而来,与当下社会价值观的迷失和异化密切相关。社会快速变化,社会新的规则和价值体系还没有完全确立,社会成员缺乏明确的价值导向而无所适从,做出极端的失范行为。其次是由于生活重压下社会成员的情绪失衡。长期快节奏的生活状态和巨大的竞争压力,对于抗挫折能力较弱的社会成员,一旦遇到精神刺激,又无法排遣心中的抑郁不满,挤压的负面情绪就可能转向社会泄愤。如厦门公交纵火案的陈水总就是负面心理积累导致暴力事件发生的典型个案。此外,社会戾气与社会公平正义的缺失及民意表达的渠道受阻相关。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呼声得不到重视,权益得不到维护,问题得不到解决,诉诸无门的失望感、无助感会让一些人铤而走险,做出极端行为。
实际上,以上这三种社会心态都具有广泛性、传染性、复杂性、交织性的相似特征,三者之间又是可以相互传染、相互交织、相互转化的密切关系。焦虑不安的情绪可以催发极端的冲动行为,仇视、暴戾之气又可以加剧情绪不安的程度。学者王俊秀曾指出:“情绪具有动力特性,也称为‘情绪能量’,社会负向情绪的积累可能对社会产生破坏性影响。”[6]因此,若这些负面社会心态的并存、交织,无疑会对社会良性运行造成影响,而且影响广度、强度之大、破坏烈度之强是显而易见的。
二、负面社会心态的正负功能
负面的社会心态是伴随社会发展和转型的副产品和代价。需要辩证、客观地对待我国社会心态的现状。正如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提出,冲突对维护社会的团结和统一,疏通社会中的不满情绪有积极的方面。[7]负面的社会心态也有其正功能的体现。不良社会心态是折射社会问题的一面镜子,所反映的社会问题会有助于我们了解社情民意,知民众之所难,解民众之所需。这也是一种矛盾倒逼改革,促进政府及时发现问题和化解社会矛盾的窗口。但是我们不可忽略负面心态的主要负功能。
社会关系层面——加深群体、阶层之间隔阂。尤其是社会仇视心态和社会戾气,对于加剧阶层分化和阶层固化现象更为明显。两者心态产生的共同根本原因,源于贫富差距的扩大,向上流动通道的堵塞。改革中的受益者越来越富,其社会地位和占有的社会资源更有优势,改革中利益受损者越来越穷,形成贫富差距拉大,“富贵绵延”和“贫困世袭”的阶层固化严重。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指出:合理的社会流动缩小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缓解由社会地位差异而产生的隔阂和冲突”[8]。而跨阶层流动率低甚至停滞,社会资源占有的多寡、利益分配的失衡,这不可避免引起阶层间的相互摩擦和冲突[9],加深阶层裂痕,产生阶层隔阂和歧视,不利于形成以中间阶层为纽带的橄榄型的理想社会结构,影响社会健康活力、和谐有序的发展。
社会稳定层面——激发社会矛盾,甚至引起群体极化的群体性事件。这三种负面社会心态都会催化群体性事件的产生。斯梅尔塞的累加价值理论认为,集合行为的产生是由利于社会运动产生的结构性诱因、社会结构衍生出来的怨恨、剥夺感或压迫感、一般化信念、触发社会运动的因素或事件、有效的运动动员、社会控制能力的下降[10]这六种因素构成。而具有负面心态的群体本身具有被剥夺感、压迫感、一般化信念,若再加之事件的诱因和事件控制力的减弱,群体性事件就由此产生了。如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指出的“群众等同于无意识集体,因为无意识,所以力量强大”。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急剧增加、频率不断增大,与背后民众的负面心态密切相关。而群体性事件一般参与人数多、持续时间长、冲突程度剧烈、破坏性大,会给人民生命或财产带来巨大损失。贵州的瓮安事件就是值得我们警醒的典型案例。
社会发展层面——减弱社会凝聚力,抵触消解改革发展进程。社会良好的心态是促进民生改善,推动社会健康稳定发展的前提保障和动力之源。社会心态也关乎社会整合、社会团结、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积极的心态能激发社会成员活力,使其各尽所能。不良心态的蔓延则会影响社会成员的积极性、能动性、创造性,降低社会的合作合力和社会认同度,影响社会发展的效率和质量,甚至影响整个民族精神面貌和国家软实力。古语“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就表明“人心所向”的极其重要性。[11]“人心齐,泰山移”,在中国改革发展的新征途,更需要万众一心,凝聚合力,共铸中国梦。
三、培育积极社会心态的必要举措
社会心态问题其实早已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弘扬科学精神,加强人文关怀,注重心理辅导,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也提出要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的要求。而负面社会心态是多种社会病的交织,培育健康的社会心态需要开复方药。
(一)弘扬主流社会价值观,凝聚共识感
社会心态反映了人们的价值取向。负面社会心态存在的背后原因与价值观和信仰的多元和紊乱、迷失相关。社会成员缺乏共同遵守和认同的核心主流价值观,就会无所适从,随心所欲。主流社会价值观念是个人价值观念和行为标准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参照系数,对个人价值观和行为标准起重要引导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了进一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的倡导和建设。我们需要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弘扬友善文明、诚信友爱、充满活力的主流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传播与强化主流价值观,使正确的道德价值观外化为公民的行为规范,内化为公民的信仰信念。良好的社会心态还是一种心理资源,充分利用心理资源的能动作用,化负能量为正能量,才能凝聚共识,凝聚人心,凝聚力量,共谋发展。
(二)着力改善民生,增进获得感
贫富差距的拉大,不断增强相对剥夺感是促使民众负面社会心态形成的重要因素。增进人民安全感和幸福指数,必须从关乎人民切身利益的民生开始。首先,需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发挥社会保障的保基本和兜底功能,使广大人民能够“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满足人民基本的物质保障和精神需求。其次,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们的需求是从低层次到高层次的。保障民众基本的生存权益后,还需要不断地改善和满足多样化更高层次的需求,如人身财产安全需求,人格尊重和价值实现的需求。因此,今后还应致力于社会事业机制的完善、社会流动机制的畅通和生态环境的改善。进行教育、就业创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领域的民生改革,“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让老百姓过上更有保障、更有尊严的幸福生活”[12]。如习近平在2016年新年贺词中提到的,“让农村贫困人口、城市困难群众等所有需要帮助的人们都能生活得到保障、心灵充满温暖”[13],让人民更有获得感。
(三)推进民主法治,实现公平正义,增进认同感
公平正义是影响社会成员心态的重要元素,公平正义是培育社会心态的土壤,是创造积极社会心态的前提条件。公平正义的制度化保障就要通过民主法治的推行。故而我们要积极推进发扬民主、厉行法治、依法治国的进程。首先,要不断扩大公民对社会事务的积极参与,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还要保障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依法公正解决社会矛盾和纠纷,做到科学民主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平公正[14]。其次,还要加强公权力的规范和约束。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必须以规范和约束公权力为重点,加大监督力度,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廉洁政府、服务型政府,增强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营造风清气正的廉洁社会氛围。最后,对于针对危害社会公共安全,向社会宣泄戾气的极端暴力行为,需要严厉打击和惩处,创造一个安定、安全的社会环境。厉行法治,彰显公平正义,增进社会认同感,社会心态才会越来越健康。
(四)畅通民意表达方式,疏导负面心理
利益诉求渠道不畅是恶化社会心态的罪魁祸首,畅通的民意表达渠道和完善的民意表达机制是疏导社会情绪的重要通道。“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提出要“注重心理疏导”。构建制度体系化的渠道,让人民群众充分表达诉求,反映意见,才能化解民众心中不满,疏解社会情绪。首先要发挥传统社情民意表达渠道,比如进一步完善和强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会议制度、信访接待制度以及其他发挥民意代表制度,使其充分体验民情,代表民意。其次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时效快、覆盖广的优势,开辟诸如“网络论坛”“民情邮箱”等,为熟悉互联网的群众提供便捷的表达渠道。[14]另外,还不能忽视媒体的喉舌作用。媒体机构要树立社会责任感,做坚持贴近群众生活、倾听民声、反映群众诉求的传播人。焦虑、怨恨、戾气消极心理情绪,需要及时释放和疏导,否则会积聚危害社会秩序的巨大能量。建立规范有效的心理疏导机制,有利于把积累的负面心态得到无危害的宣泄与释放,从而维护社会稳定。
四、结语
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不可避免会引起社会成员思想观念、社会心态的深刻变化。我们在把握主流积极社会心态的同时,不可忽略负面社会心态的负面影响。社会心态直接关乎社会局势的安定、社会关系的和谐。对社会心态的准确把握和有效引导,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及时调节社会负面情绪,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乐观包容、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才能提高人民幸福指数,保障社会稳定有序和良性运行,才能凝聚共识,齐心协力,推进改革,共促发展。
[1]王俊秀.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社会心态蓝皮书-2015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2]吴忠民.透视社会焦虑症.商周刊.2011,(17).
[3]林金芳.缓解社会焦虑应有制度化渠道[N].组织人事报,2007-04-24.
[4]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
[5]熊培云.社会戾气的文化解读[J].中国图书评论,2011 (08).
[6]王俊秀.当前社会心态的新变化[N].北京日报,2015-12-03.
[7]刘易斯.A科塞.社会冲突的功[M].华夏出版社,1989.
[8][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56-58.
[9]杨文伟.转型期中国阶层固化研究[D].中共中央党校,2014.
[10]王小章,冯婷.集体主义时代和个体化时代的集体行动[J].山东社会科学,2014(05).
[11]李培林.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社会心态影响[J].经济导刊,2005,(01).
[12]巴音朝鲁.主动适应新常态 满足人民新期待[J].求是,2005(07).
[13]习近平.《二○一六年新年贺词》党建网2016年第1期http://www.dangjian.cn/gbbd/xxhtwx/201601/t20160106_3069810. shtml
[14]刘武俊.良好的社会心态来自民主法治[N].法治日报,2005-05-06.
〔责任编辑:宋洪德〕
C912.6
A
1002-2341(2016)02-0102-04
2016-03-03
王真卓(1990-),女,河南驻马店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社会学理论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