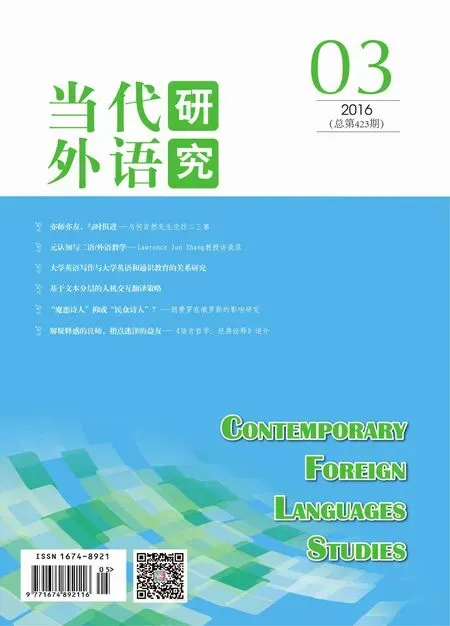解疑释惑的良师,指点迷津的益友
2016-03-19刘龙根朱晓真
刘龙根 朱晓真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200240)
解疑释惑的良师,指点迷津的益友
——《语言哲学:经典诠释》述介
刘龙根朱晓真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200240)
McGinn, C. 2015.PhilosophyofLanguage:TheClassicsExplained.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ISBN: 978-0-262-02845-5. pp. x +225.
1. 引语
众所周知,语言哲学是20世纪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哲学的主流。进入21世纪后,虽然语言哲学或许不再独执西方哲学之牛耳,但这并不意味着语言哲学业已走向终结。相反,语言哲学研究无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正在获得空前的拓展。不仅是许多传统语言哲学论题的研究进一步得到深化,而且语言哲学研究的领域也愈加广阔。有志从事语言哲学研究或对之怀有浓厚兴趣者人数之众更可谓今非昔比。
学习研究语言哲学的第一步往往离不开阅读该领域的经典名著。但是,对于许多初涉语言哲学的人来说,读懂哲学巨匠的经典名篇无疑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即使对于母语为英语的读者而言,这些思想大家的原著也往往令其望而却步。这不啻由于哲学家原创性思想之深邃,而且因为他们富有专业性且不乏个性特点的语言表达更增加了理解的难度。虽然或许可以通过修学语言哲学课程,在教师带领下研读,但这对许多学习者来说,依然是远水不解近渴。更何况他们之中能够有幸亲耳聆听到像Colin McGinn(以下简称CM)这样具有38年讲授语言哲学经验的教授诠释经典名作的比例恐怕小之又小。这样,由MIT出版社出版的《语言哲学:经典诠释》(以下简称《经典诠释》)一书有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缺憾。
CM所著的《经典诠释》形式独特,不同于通常的语言哲学专著或文选,也有别于常见的语言哲学教程,而旨在与诸如马丁尼奇《语言哲学》这种权威性文选配合使用。作者选取了语言哲学领域十部经典文献,着力对之做出清晰明了、深入浅出的阐释。因此,本书并非围绕语言哲学论题的普通导论,而是聚焦于上述经典文献各个作者之代表性思想观点做出导读性诠释。实际上,本书的酝酿过程也颇为奇特,肇始于作者一个学生的建议,真可谓应读者之需而萌生。学生之所以渴望能有这样一本诠释经典的书籍在手,主要是希望借助于这种详尽系统的导读性诠释,能够克服阅读这些经典文献中所遇到的重重障碍。书的胚胎是这位学生将其对CM讲课内容的录音转写而成的文字材料。转写出的文字又经本书作者字斟句酌的修改加工,最终成稿。因此,除了声音转成文字过程中常见的缺损之外,即无法完全复原作者课堂上声情并茂的生动形象,但本书却再现了他所讲述的基本内容,不仅能为学生指点迷津,也为教师减轻单调讲解的负担提供了可能。
2. 内容梗概
本书共包括十章(后加一个附录),每章详细讨论一部经典文献。现按章概述如下。
第1章聚焦弗雷格的论文《论涵义与指称》。这是本书诠释的唯一一篇发表在19世纪末的经典文献,剩余九篇均发表在20世纪。但是,这篇文章非但没有因为发表年代久远而被学界淡忘,相反,其学术影响却由于该论文对意义研究的独特贡献而历久弥新。弗雷格号称世纪转折处的哲学巨匠,虽然在有生之年影响平平,但在他身后乃至今日,其学术思想却愈加熠熠生辉。
在诠释该论文之前,CM首先扼要阐述了语言哲学的总体目标。对于这一目标最为普遍的表述是,语言哲学研究意义的基本性质。可是,CM认为这个定义对初学者帮助不大。为了更加具体地阐述语言哲学的基本目标,CM连续提出了十多个问题,诸如,语言如何能够与现实相联系?人们如何指称事物?语言中的一切都是名称吗?不同类型的表达式指称方式是否不同?不同类型表达式在意义上有何差异?语句如何同其意义相关联?如何理解成真性概念?意义如何与成真性相联系?语句意谓与言者意谓存在何种关系?其中某个(些)问题正是由本书诠释的经典原作所发现并试图做出回答的。
弗雷格发表于1892年的论文《论涵义与指称》标志着现代语言哲学的开端。在这篇论文中,弗雷格论述了句子与句子表达的命题之间的关系,探究了不同的句子如何表达相同的命题、构成命题的成分是什么以及词的意义是什么等问题。这些问题导致人们探究句子如何可能有意义以及意义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但是,弗雷格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并不直截了当,有些地方显得含糊其辞。他采用数学上的同一性概念,阐述命题同一性的内涵。以包含指表金星的两个专名“长庚星”与“启明星”的命题为例。“长庚星是长庚星”(a=a)是一个复言式,属于分析性命题;“长庚星是启明星”(a=b)则是一个综合性命题,陈述了一个重大的天文学发现。这个例子表明,了解到两个名称指称同一个对象不只是了解一个语言学事实,而且理解了某种关于世界现实与事物的重要知识。
“涵义”是弗雷格引入语言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他将涵义解释为与指称的呈现方式相联系。例如,在上述“a=b”中,名称“a”和“b”具有相同的指称,两者的涵义却不同。因此,仅仅囿于句子本身或者句子中词语的指称,不足以阐释句子表达的命题。要想对表达的命题做出充分阐释,必须考虑涵义这个层面。弗雷格强调,必须赋予名称以呈现其指称的一个特定方式。指称的呈现方式表明了名称的真正定义。名称的真正意义并不源于指称对象,而是源于呈现方式。他进而提出,语义理论不能仅有指称,还必须包括涵义。
就“指称”而言,弗雷格认为,一个指称可以与许多涵义相对应,可以与许多符号相对应。但是,一种涵义不可能对应于几个事物,涵义独特地决定指称。在他看来,指称不决定涵义,相同的指称可能有许多不同的涵义。相反,涵义确实决定指称,涵义必须始终具有一个特定的指称与之对应。而且涵义也不由符号决定,所以语言中存在很多没有指称对象却具有涵(意)义的表达式。
弗雷格还将词语的涵义、指称同语言使用者心中的想法区分开来。在他看来,使用者的想法实质上同涵义和指称毫不相干。这样的想法也许对于掌握涵义十分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将涵义与想法混为一谈。想法是个体的,不为众人分有,而涵义是社会的,为公众分有。涵义不随个体心灵消失;涵义同指称对象一样具有客观性与心理独立性。
当然,弗雷格在这篇论文中提出的原创性思想不仅限于如上所述。正如CM所指出的那样,尽管他关于句子的指称是句子的真值以及真值是一个客体这些主张似乎有悖直觉,他的有些论述也不够清晰明了,但其理论富有的魅力远远超过所存在的不足。
第2章集中探讨克里普克的《命名与必然性》。假若按照一些熟谙语言哲学史的读者的期待,紧随论述弗雷格的第1章之后的这一章应当专论罗素语言哲学思想。CM之所以没有这样安排,他的主要考虑是,主题的延续性胜过时间的延续性。鉴于源自弗雷格的描述语理论长期在哲学界流行,但在1972年克里普克在《命名与必然性》中对之提出了空前激烈的批评,CM将关于克里普克理论的阐释作为了第2章。
描述语理论利用有定描述语概念,这种描述语适用于某个特定个体而不适用于任何其他个体,讲话者借由有定描述语以指称该个体。按照这种理论,诸如“亚里士多德”这种专名以与有定描述语同样的方式做出指称;名称事实上与描述语同义。为了方便实际使用,人们将有定描述语简略成一个同义的名称。名称只是缩略的有定描述语,名称与描述语具有相同的指称方式。名称也可以看作是伪装的有定描述语。由此可见,描述语理论是关于如何才算理解名称、掌握名称意义的理论。在克里普克提出挑战之前,这种描述语理论在哲学界业已流行了70多年。
克里普克的挑战振聋发聩。他声称,描述语理论是完全错误的。根据描述语理论,名称“A”与描述语“theF”同义。这样,句子“A是F”就有几个性质:(1)先验地成真;(2)必然地成真。一个成真性如果是分析性的,就在所有可能世界中成真。既然这两个表达式在命题中是同义的,该命题就必然地成真。据此推论,在每个可能世界中A是F,正是因为“A”意谓“那个F”。针对描述语理论蕴含的结论,克里普克提出的质疑是,并不存在一个或者一组描述语,常规性地与一个具有分析性地必然成真特征的名称相关联。所以,他认为名称的描述语理论从根本上是错误的。例如,在某些可能世界中亚里士多德并不一定是柏拉图最好的学生。这只不过是现实世界中的一个偶然事实。但是,假如“A=那/这个F”不是必然的,那么,名称“A”与描述语“那/这个F”的意谓就不同。由此看来,描述语理论就是错误的。
克里普克区分严格指称语与非严格指称语的概念。前者在每个世界指称相同客体,而后者在不同世界可能指称不同的客体。他进而认为,专名是严格指称语,而有定描述语则是非严格指称语,所以两者在语义上不同,因而主张在语义上相同的描述语理论就是不正确的。克里普克主张以历史-因果链理论取而代之。在他看来,同描述语理论所表明的相比,命名在更大程度上是互动的社交现象。但是,克里普克的认识论辩只是对驳斥个体论形式的描述语理论能够奏效。而可以认为有定描述语确定社团中名称的指称,因为人们可能在语言上是顺从的。所以,当描述语理论作为社团语言的理论提出时,克里普克的认识论辩就无法将之驳倒。
第3章集中阐释罗素的(有定)描述语理论。这一理论实际上影响了整个20世纪的分析哲学。
关于有定描述语的性质,罗素与弗雷格观点相左。弗雷格认为有定描述语与专名属于同类,均为“单称词项”,用于指表特定客体供句子其余部分做出评述。有定描述语既具有涵义又具有指称。但罗素却主张,有定描述语不属于类似专名的单称词项,而属于完全不同的语义类型。若将描述语混同于专名则可能是受了有定描述语表层语法结构的误导。罗素通过分析无定描述语的逻辑性质,建构有定描述语理论,以论证一个核心的观点,即有定描述语不是名称,而是一个限量词语。借此,罗素解决了涉及有定描述语的诸多难题,尤其是阐释空无指称对象的有定描述语之难题。
针对诸如“(当今的)法国国王”这种空无指称对象的有定描述语,弗雷格理论的解释是这种表达式有意义但没有指称。但是,罗素并不接受弗雷格关于涵义与指称的区别,罗素坚持意义指称论,主张表达式的意义必定是其指称。按照罗素的观点,每个专名或者单称表达式都有一个由其指称决定的意义。他认为,由于自然语言的缺陷,“(当今的)法国国王”这种表达式表面上是指称性,而实际并非指称表达式,因此其空无指称性不成其为问题。实际上,认为“自然语言能够满足于实际使用的需要,而对于逻辑目的则是不充分的”这种观点长期流行。所以,这场关于描述语的争鸣具有广泛的哲学意义。
罗素还以“是”的歧义性佐证其关于日常语言在逻辑上具有误导性的观点。具体而言,他论述了述谓中的“是”与同一性陈述中的“是”存在着重要的差异。同一性陈述中的“是”用于可以转述为“a=b”的句子。但人们并不总在同一性意义上使用“是”。例如,在“这朵花是紫色的”这个陈述中,花的颜色为紫色,而其同一性却并非紫色。在罗素看来,“这朵花是紫色的”中的“是”为述谓的“是”。而用于“亚里士多德是人”中的“是”与“亚里士多德是一个人”中的“是”完全不同。
罗素还对逻辑专名与日常语言中的名称做了区分。在他看来,逻辑专名通过指称而具有意义,而日常语言的专名并不借由指称具有意义。所以日常语言中的名称表面上是名称,实际都是假名称,都是伪装的描述语,这些描述语都可以用描述语理论分析掉。罗素认为,专名是无法再分成更小部分的简单符号。专名借由其指称而意谓所意味的东西。由此而论,有定描述语不是专名,因为将名称与描述语互换,所表达的命题就会发生变化。
罗素理论中的另一个重要结论,涉及处理真值的路径。按照他的观点,“法国国王是秃子”这个句子成假,原因是法国国王不存在。这一结论遭到斯特劳森的反驳。斯特劳森提出这样一个陈述非真非假:使该陈述成真的唯一情形是法国国王秃头,使之成假的唯一方式是法国国王头上长着浓发。既然这两种情况都不存在,这个陈述必然非真非假。
第4章探讨唐奈兰针对描述语做出的区分。前文介绍的弗雷格与罗素关于描述语的不同理论,唐奈兰都不完全接受。在他看来,有定描述语可以有两种不同的作用方式。在有些陈述中,有定描述语以罗素阐释的方式发挥作用,而在其他陈述中,则依照弗雷格与斯特劳森论述的方式起作用。这两种理论中无论哪一种都未能囊括全部有定描述语的语义特征。
至于真值,唐奈兰认为存在第三种可能性。罗素认为,空洞的描述语导致句子成假。弗雷格提出,这导致句子非真非假。唐奈兰则主张,空洞的描述语可能导致陈述成真。他论证这一观点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区分了描述语的两种用法,即指称性用法与归属性用法。在指称性用法中,讲话者使用描述语以使听者能够识别所谈论的对象;而在归属性用法中,讲话者就符合该描述的对象做出某种断言。唐奈兰通过一个思想实验例示两者的区分。假设在一个聚会上,某人看上去在饮马提尼酒,他是著名的哲学家。看到这个人,你说道:“在饮马提尼酒的那个人是著名的哲学家。”然而,假定尽管那个人是著名的哲学家,但他在用马提尼酒杯喝水,而不是饮马提尼酒。但你依然使用描述语成功地指称了你意在指称的对象。反之,假设主办聚会者不想让客人喝酒,问道:“那个喝马提尼酒的人是谁?”她并不意在鉴别特定的个人,而是试图弄清喝马提尼酒的人是谁。假如结果证明,看上去在饮马提尼酒的人喝的是水,她就不会担心。她使用描述语意谓“饮马提尼酒的任何人”,心目中并没有特定的个人。这就是一种归属性用法。区分归属性用法与指称性用法,是唐奈兰论证的核心所在。唐奈兰认为,正是由于忽略了描述语用法的这种双重性,罗素和弗雷格/斯特劳森的理论都不足取。
在论证中,唐奈兰还进一步区分了“指表”与“指称”两种概念,前者是一个语义学概念,是对描述语做出的严格的字面理解;后者是讲话者使用描述语进行指称的语用概念。实际上,唐奈兰的主要兴趣在于讲话者如何在特定场合将信息传达给听话者这种语用问题。他认为,描述语本身在语义上指表符合描述的任何客体,因而起着“归属性”的作用。讲话者则可以使在语义上指表某个特定对象的描述语,在语用上指称另一对象。由此也许可以认为,唐奈兰对罗素理论的批判并不中肯,因为他试图将语用区分应用于语义问题。
就指称性地使用空洞的描述语而言,唐奈兰认为斯特劳森将包含这种用法的陈述判断为非真非假的做法是错误的。按照唐奈兰的观点,讲话者使用没有指称的描述语可以说出某种真话。例如,假若史密斯根本不是被谋杀的,而是死于车祸,如果讲话者高喊“史密斯的谋杀者疯了!”以指称琼斯,斯特劳森就会认为,这句话既不真也不假,而唐奈兰则提出,假定琼斯确实疯了,讲话者会就琼斯做出了成真的断言。但是,正如会话含义理论所揭示的那样,不应将使用语言所传达的信息同词语本身的意谓混为一谈。有时可以用词语意谓实际上并非词语本身的意谓,这是自然语言的本质特征。
第5章专题探讨开普兰关于指示词语的研究。为此,必须对可能世界语义学做一了解。可能世界语义学家把意义阐释为从世界到真值的函数。这个思想可以扩展到有定描述语这样的句子成分。有定描述语的意义是从世界到外延的函数。两者的差异在于,就句子而言,外延是其真值,而对描述语来说,外延是一个客体。外延随世界而变,而内涵则固定不变。
鉴于语言中存在指示语,开普兰不接受可能世界语义学对意义做出的阐释,主张以一种十分不同的意义概念来表征指示语的意义。指示词语是指示语的一个小类,是像“这”或“那”这种通常伴有指示手势的词语。指示语则包括“这儿”、“我”和“现在”这样的词语。与名称和有定描述语不同,指示语典型地用于特定语境之中,依赖于语境确定指称对象。因此,开普兰强调指示语的两个特性:语境依赖性与直接指称性。包含指示语的句子所表达的命题是单称命题。指示语的指称关系并不以独特鉴别客体的描述概念为中介。
开普兰还对严格指称与直接指称做出了区分。严格指称是模态概念,而直接指称则是语义概念。对应于直接指称词项的命题是单称命题;对应于严格描述语的命题是普遍命题,因为描述语不是直接指称性的。严格指称性只是在每个世界都具有相同指称的思想,而直接指称则涉及什么构成相应的命题。
为了进一步阐述严格指称与直接指称的区分,开普兰论述了使用语境与评价境况的区别。使用语境包括可能说出给定句子的人、时间与地点。评价境况则指某个命题可能成真或者成假的可能世界。在不同的语境中使用同一个指示语,做出的指称不同,从而产生不同的真值。那么,这是否同一些描述语的情形相同呢?这些描述语在不同的可能世界中具有不同指称。开普兰强调,不应当混淆语境依赖性与世界依赖性。例如,倘若某人说出“我不存在”这个句子,这句话永远无法成真地说出,因为这句话不可能由某个不存在的人说出。在任何使用语境中,这句话始终成假,因为语境包括讲话者。在任何某人说出“我存在”的语境中,这句话始终成真。但是,说出“我存在”的讲话者存在,这并不是一个必然成真的命题,因为存在这样的可能世界,在这种世界中,说出“我存在”这句话的人可能并不存在。
在开普兰看来,另外一个区分对于阐释指示性话语的全部意义十分重要。他认为,不存在弗雷格“涵义”的简单的单一实体,指示性话语具有两个不同的语义维度:系统意义与场合意义。CM认为,这是他理论的核心所在。所谓“系统意义”是指示语在语言系统中所具有的意义,亦即其词典意义。系统意义不同于弗雷格涵义,涵义决定指称,而系统意义必须与语境相互作用,方能确定指称。系统意义本身不包括指称,包括指称的是场合意义。开普兰将句子所表达的命题称作场合意义。场合意义是系统意义与语境两者互动的产物。场合意义是在不同的可能世界中具有真值的东西,而系统意义本身则不可能具有真值。
第6章阐释埃文斯关于指示词语的理解。正如上一章所示,开普兰以对于指示语的阐析驳斥弗雷格意义理论,认为其涵义概念并不适用于指示语。但埃文斯对这个结论提出质疑,主张对指示语做出弗雷格式阐释是可行的。但是,要想创立涵义决定指称的指示语理论,就不能将涵义认同为指示词语的规约意义,必须为指示语寻觅一种超越指示语规约意义的涵义。
埃文斯在阐述指示语时,区分了“例型”与“类型”两个概念。在特定场合说出的指示语称作该指示语的例型。从其所有例型中抽象出的共同形式称作类型。例如,你说出“我”时所使用的与我说出“我”时所使用的是同一个词的类型,但你与我说出了那个类型的不同例型。
就指示语的处理而言,一种可能的弗雷格方式是借由指示语例型之涵义的描述语理论。指示语的语义可能包括三个成分:系统意义、场合意义与揭示例型涵义的描述语。在这种理论阐释中,指示语不是直接指称性的。指示语同描述语同义,而描述语具有独立于语境的内涵。语境的作用只是不同个体使用相同的指示语类型,它们将不同的描述语同指示语类型相关联,指示语的指称对象由这些描述语决定。指示语在不同的使用中具有相同的系统意义,但其涵义却因语境的改变而改变。这样,最终的语义理论就包含系统意义、涵义与指称三个要素。
指示语的涵义既非系统意义又非指称,涵义也不可能是描述语。为了阐明这个观点,埃文斯论证了涵义如何同指称相联系。他认为,表达式的涵义通过说出表达式的指称是什么而得到规定。通过陈述指称提供涵义,但只有某些指称性陈述成功地提供了涵义。涵义是思考客体的一种方式。但唯有通过谈论客体,才能对涵义做出具体规定。因此,埃文斯的语义理论兼收并蓄了罗素理论与弗雷格理论的特点,主张涵义是指称依赖性的;没有指称,就不可能有涵义;但涵义又不等同于指称,而是某种超乎指称的东西。
然而,就空名的阐释而言,埃文斯认为,空无指称的名称之涵义是有缺陷的,这种名称仅仅具有准涵义,即模拟涵义。所有恰当的涵义皆依赖于指称,但不恰当的模拟涵义则可能不依赖于语境。
但是CM认为,埃文斯并未能成功地阐述一种融贯理论,以替代涵义之描述语理论,从而可能为指示词语的阐释提供一种可行的弗雷格式路径。他由于相信指示性涵义的描述语理论必定是错误的,所以试图建构一种不同的非描述性弗雷格理论,但尚不能说他已经获得了成功。
第7章诠释普特南语义外在论。前面关于指示性的讨论有助于理解普特南的论点。对于指示性表达式,正像开普兰论辩的那样,决定外延的传统描述性内涵理论是行不通的。指示语在特定场合中使用时的意义并不等同于所指称客体的有定描述语。指示性指称由使用语境外在地确定,而不由言者心中的东西主观地确定。这不同于描述性指称;描述性指称独立于语境,言者的内在概念足以确定其所指。因此,对于指示性指称外在论是正确的,而就纯描述性指称而言内在论是正确的。
普特南专注于自然类词项。他想弄清这些词意谓什么,尤其是这些词如何确定指称。在他看来,自然类词项的语义特征体现指示性表达式的语义特征。这种词不符合有定描述语及其指称的经典弗雷格理论。人们并不是通过理解内涵而理解这种词的,而是以理解指示语的相同方式理解这种词。在理解指示语中,语境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他认为内在心理状态不决定讲话者的指称,因而拒斥言者指称可以从其讲话时心中所想的东西中抽取这一传统观点。
普特南通过双子地球思想实验加以论证。假设双子地球上没有水,却有一种液体尽管不是水,却具有与水表面上相同的许多特征。普特南规定这种液体具有XYZ的化学构成。再假定双子地球上存在我们的孪生子。他们说的“水”指称双子地球上的液体XYZ,而非地球上的液体H2O。这个词在两个星球上具有不同的外延。我们的“水”不指称XYZ,只指称H2O。他们的“水”不指称H2O,只指称XYZ。双子地球人与我们处于同样的心理状态,但其用词的外延不同。普特南据此认为,心理状态不能决定指称或外延。讲话者使用词语时的意谓不由其内在心理状态决定;而由其外在环境决定。关于各自指称的液体,两组讲话者会对之做出相同的描述。但是,由于使用语境不同,指称也就各异。
如假定意义决定指称,就可以推断,“水”在地球上和在双子地球上就具有不同的意义。因此,词具有相同的描述内容,却不具有同样的意义。“水”这个词并非描述语的缩略形式,因为在双子地球人的心中也出现了与我们心中相同的描述语,然而,两者的指称对象不同。假定意义决定指称,那么,意义也就必然不同。普特南推论:“意义不在头脑中”,词的意义取决于外在因素,而不能从讲话者的心理状态推断得出。意义不是心理现象。意义源于世界本身,不以任何人的心理状态为中介。正是言者与身处世界的相互作用决定其用词的意谓。
当然,笼统地说“意义不在头脑中”未免有失偏颇。假如专注于描述语情形,就会认为意义必然决定指称,因为对于有定描述语来说,意义确实决定指称。但是,对于指示语而言则需要更加复杂的语义分析,必须区分意义的不同维度。虽然系统意义确实可以存在于头脑之中,场合意义则不然。
第8章阐述塔斯基的真理论。历史地看,普遍认为塔斯基为真之概念提供了严密准确的定义,使之成为“科学的”。但至于其对意义理论的贡献,学界仍莫衷一是。
关于真之概念,历史上出现过若干不同的理论,诸如融贯论、符合论与实用论。融贯论主张,命题成真,当且仅当该命题与所相信的其他命题相融贯。据此,成真性涉及所相信的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符合论则提出,信念成真,当且仅当该信念符合事实。塔斯基将之表述为,命题指称现实的事态即成真。该理论着眼于命题与世界上的事物之间的关系。第三种理论因为通常与实用主义相联系而称作实用论。按照这一理论,命题成真,当且仅当相信该命题是有用的。成真性即为实用性。在这三种理论中,多数哲学家认为符合论最为可行。它体现了成真性依赖于客观实在的思想。但是,符合论也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回答,譬如,什么是事实,符合关系是什么关系,事实与成真命题有何不同。塔斯基正是试图回答此类问题。
普遍认为,塔斯基以严谨的逻辑理论使关于真之概念得到了澄清,他的理论因此而受到青睐。他提出,可接受的真之理论必须在内容上充分、形式上正确。所谓内容上充分,即指成真性之定义必须揭示“真”这个词在实际使用中的意谓。所谓形式上正确,则是说在关于“真”之定义中不能出现逻辑错误,而且必须具体规定所用语言的形式结构。
塔斯基考察“真”这个词的运用,提出成真性可用于不同的事物,包括:(1)用于信念,信念是心理状态,可判定为真假。(2)用于命题,命题是信念的抽象内容。在将“真”用于命题时,命题不依赖于特定的语言或信念持有者。(3)用于句子,句子不同于命题,是具体的语言实体。句子是可感知的物理实体,是一串符号或声音。塔斯基是在将成真性用于句子时定义“真”的,这正如其双条件句成真性定义所示:“雪是白色的”成真,当且仅当雪是白色的。
第9章探讨戴维森自然语言语义学。戴维森旨在将塔斯基真之理论加以改造,以用于自然语言的语义分析。塔斯基阐释“真”之性质;戴维森利用“真”之概念解释语义性质。
在整个20世纪语言哲学中,关于意义的两种观点颇为流行:(1)意义与成真性联系密切;(2)意义本质上是组合性的,句子的意义由其成分组合而成。这两种观点结合起来就意味着,意义是通过组合而产生成真或者成假句子的东西。简而言之,句子的意义即为其真值条件。
戴维森主张,意义理论应当提供每个有意义的表达式的意义。他认为,首先,意义描述的恰当形式必须以结构为基础,有限地加以陈述并且能够生成无限的输出。为了阐释自然语言无限数量的句子意义,意义理论必须包括一套能够递归性地运用、能产生无限结果的有限公理。在戴维森看来,塔斯基的理论正是这样一种理论,具有正确的形式,将意义(真值条件)有限地、结构地、递归性地赋予句子,并且能够潜在地生成无限的语义归赋,因而有资格作为意义理论。
以“雪是白色的”这个句子的意义阐释为例。这个句子分析成单称词项“雪”和谓项“是白色的”。然后给出“雪”的指称公理:“‘雪’指称雪”;再给出“是白色的”之满足公理:“某个客体x满足‘是白色的’,当且仅当x是白色的。”如此,这个句子就分解为其构成成分,这些成分再被赋予语义性质。依据公理知道,主词“雪”指称是什么,谓项“是白色的”具有什么满足条件,从而推断“雪是白色的”成真,当且仅当雪是白色的。鉴于意义与真值条件重合,也就从句子成分的意义生成了整个句子的意义。
9月2日凌晨3名中国游客赴瑞典斯德哥尔摩旅游,9月15日网络曝出3人指控接待酒店青年旅舍拒绝其“交钱在大堂休息”并报警,随后瑞典警察“强行带离并丢弃至野外坟场”。
戴维森认为,这个理论的优势在于不利用任何未包含在所针对的原初句子里的概念资源。在他看来,意义归赋中不应归赋超出讲话者在知道一个句子的意义时通常拥有的知识。
第10章诠释格赖斯的讲话者意义理论。格赖斯试图回答词汇意义与句子意义如何产生的问题。他认为,使语言成分表达意义的东西,同讲话者意谓事物的方式存在某种关系。语言不能先于讲话者而存在。词语本身只不过是人们发出的声音或手写的符号,词语本身并不内在地具有任何东西决定意谓。词义具有任意性与规约性,意义是被赋予词语的。
格赖斯引入了讲话者意义这一重要概念。不仅词语和句子意谓事物;讲话者也使用词语意谓事物。人们以这两种方式使用“意谓”一词。所以,既可以说“雪是白色的”这个句子意谓雪是白色的,也可以说讲话者说出这个句子时意谓雪是白色的。就两种意义的关系而言,格赖斯提出,句子意义派生于讲话者意义,讲话者意义是句子意义之源。正是由于人们通过词语意谓事物,所以词语才能具有意谓。因此,讲话者的意谓行为创造了语言意义。句子意义是语义意义,同独立于讲话者的词语相关联;而讲话者意义是语用意义,明确涉及讲话者。
格赖斯以区分“自然意义”与“非自然意义”入手,然后重点阐释非自然意义。格赖斯以“这些斑点意谓麻疹”为例,说明自然意义。这个句子可以理解为这些斑点是麻疹的自然症状。相比之下,“公共汽车上的这三声铃响意谓‘公共汽车已满’”则是非自然意义的例子。这两个例子中的“意谓”使用方式不同。在麻疹的例子中,若说“那些斑点意谓麻疹,但他没有得麻疹”就会自相矛盾;而在三声铃响的例子中,假如说“那三声铃响意谓车满了,但车没有满”,则不会相互矛盾,汽车售票员可能搞错了。但仅仅由于某人做出了断言,并且以此意谓某物,这并不意味该断言必然成真。其次,在非自然意义的实例中,可以替代“意谓”之后引号中的表达式,但对于自然意义却不能这样替代。例如可以说,售票员以三声铃响意谓“车满了”,但却不能说斑点意谓“病人得了麻疹”。这实际上就是说三声铃响与“车满了”意义相同,而斑点与句子“患者得了麻疹”意义并不相同。再次,在自然意义的转述中,意义事实中不包括施事者;而在非自然意义的实例中,始终隐含着所涉及的施事者。
3. 简要评述
CM曾长期在伦敦大学学院、罗格斯大学、牛津大学等高校讲授(语言)哲学。《经典诠释》是其多年教授语言哲学课程之经验的结晶。作者不仅熟谙语言哲学经典,而且了解语言哲学初学者在阅读这些经典时的疑难困惑。他以浅显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的方式循循善诱地为所选语言哲学经典文献的读者解疑释惑。与此同时,他在诠释这些经典文本中所迸发的睿智洞见对其他从事语言哲学研究的学者亦不无启迪。正如《语言本能》的作者、哈佛大学教授Steven Pinker所言,即使对那些具有丰富语言知识的人而言,语言哲学也是一个令人生畏的领域:充满了深奥难解的区分与容易误解的陷阱。《经典诠释》为语言哲学的学习者提供了明白晓畅、值得信赖的指导,因而是学界期盼已久的著作。
当然,语言哲学经典名篇浩瀚,CM并未试图对所有经典文献做出诠释,囊括全部经典名作——那实际上无异于黄粱美梦。他也没有奢望对有关哲学家的全部著作做出完整全面的概览,而是着力对所选作者的代表性论著进行详尽系统的阐释,并且就所诠释的理论观点普遍地做出评价与批评。但正如CM本人所指出的那样,这些评价与批评更多地是为了激发学生的思考与讨论,而不旨在对语言哲学做出令同行满意的贡献。其目的始终是在不影响准确性的前提下,使诠释内容尽可能地通俗易懂,而不预设读者已经掌握了语言哲学的基础,以激发初涉语言哲学领域者的探究兴趣,鼓起研读本领域艰深难懂的经典名作之勇气,实现最终与语言哲学巨匠对话的夙愿。因此,《经典诠释》无疑是令语言哲学学习者开卷受益的佳作(Goldstein 2015)。
不过,受本书作者的语言哲学观与视角所限,包括他对“语言转向”的态度以及对分析哲学成就的评判,他对诠释对象及其著作的选择以及对所选文献的阐释,并不能令许多语言哲学界同行所满意。但是,这种现象在哲学界并不鲜见。正像很多有重要影响的哲学观点经常是褒贬不一、毁誉参半的情形一样,《经典诠释》的面世也不可能完全是一片颂扬之声。不仅有人从理论旨趣、行文风格与原作理解等方面对这本书加以质疑,而且也有偏激者对其近乎嗤之以鼻(Piety 2015);更有甚者,有些对之持否定立场的批评者还与对之做出肯定的哲学家大动干戈、论战甚欢(Decker 2015)。
《经典诠释》遭到主要的诟病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遗漏了语言哲学杰出代表人物的著作,比如,号称语言哲学精神教父的维特根斯坦的著作在本书中难觅踪影;言语行为论创始人奥斯汀的论著同样不见身影;书中更没有收录一位女性哲学家的代表作品。但是,窃以为,这一指责似乎过于严苛,囿于本书的编写目的,经典的选择无法求全,难免挂一漏万。况且正如CM本人所言,他更多地考虑所阐释的主题之连贯性。他确实也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全书围绕语言哲学的三个核心论题展开:意义理论、指称理论与真之理论。其次,CM对经典原作的误读,如对罗素描述语理论和普特南意义外在论的表述也许并没有确切地再现原意。这一方面再次证明理解经典原著的不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另一方面,有些原著的理解恐怕本身就莫衷一是。再次,就其行文风格而言,如前所述,本书的原始初稿是从录音材料转写而成的。虽然作者做了精心加工,但是,有些地方依然存在口语表达与书面形式混用的现象。最后,也有读者在《顾客评论》上留言,提出本书的装帧太过普通,但是,考虑到消费群体主要是缺乏经济实力的在校大学生,内容胜于形式,普通的装帧也许是保证他们能够购买得起的良策。总之,虽然本书尚有若干不足之处,但瑕不掩瑜。作为语言哲学的导读性著作,本书无疑不失为一部佳作。当然,正如俗话所说,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就得亲口尝一尝。因此,唯有一读,才能评判本书究竟是否实现了“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传授大量丰富哲学思想”的宗旨。
参考文献
Goldstein, R. N. 2015. What philosophers really know [J].TheNewYorkReviewofBooks62(15):48-50.
Piety, M. G. 2015.What philosophers think they know [J/OL].CounterPunch.[2016-02-20]. http://www.counterpunch.org/2015/09/18/what-philosophers-think-they-know/
Decker, J. 2015. Review onPhilosophyofLanguage:theClassicsExplained[J].TeachingPhilosophy38(4): 463-469.
(责任编辑管新潮)
作者简介:刘龙根,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语言哲学。电子邮箱:wyzxzr@sjtu.edu.cn
朱晓真,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哲学。电子邮箱:zhuxiaozhen@sjtu.edu.cn
*本书中译本近期将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