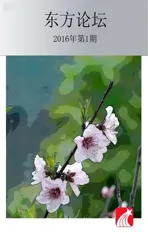朱德发与中国五四文学研究
2016-03-19温奉桥温凤霞
温奉桥温凤霞
(1.中国海洋大学,山东 青岛 266100;2.山东财政大学,山东 济南 250014)
朱德发与中国五四文学研究
温奉桥1温凤霞2
(1.中国海洋大学,山东 青岛 266100;2.山东财政大学,山东 济南 250014)
摘 要:朱德发是新时期中国五四文学研究的引领者和集大成者,为中国“五四学”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五四文学史》是近百年五四文学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五四文学研究深刻影响了朱德发学术个性和学术品格的形成。
关键词:朱德发;五四文学研究;学术个性;学术品格
作为一代著名文学史家,朱德发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其学术研究主要转向文学史学和“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建构,但五四文学研究是他的学术“发祥地”,既是其学术原点,更是其标志性学术存在。自1922年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始,对五四文学的研究已近百年,特别是新时期以来,五四文学研究一度成为学界的“热点”,涌现出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学者,朱先生是其中的集大成者,是最具标志性的学者之一。如果把十卷《朱德发文集》堪称是一座宏伟学术大厦的话,那么,五四文学研究构成了这座学术大厦的根基和基础。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朱先生毕其一生的才力和激情,把中国五四文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学术高度,开创了新时期以来中国五四文学研究的新局面。
作为新时期中国五四文学研究的先觉者和引领者,朱先生在中国“五四学”的创建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朱先生的名字与胡适、周作人、茅盾、赵家璧、李何林、田仲济、王瑶、严家炎、许志英等,共同构成了近百年五四文学研究史。
朱先生的学术生涯发轫于五四文学研究。在《朱德发文集》之“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三十余载有感”中,朱先生把自己的学术起点定位于《论胡适早期的白话诗主张与创作》①最初发表于《山东师院学报》1979年第5期。收入《朱德发文集》第1卷时,名为《评论胡适的〈尝试集〉及其诗论》。,而不是之前参加编写的全国十二院校《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这是因为在朱先生看来,从《论胡适早期的白话诗主张与创作》开始,才真正具有了某种学术自觉,才真正显示了作为一个学者的“独立姿态”。《论胡适早期的白话诗主张与创作》拉开了新时期朱先生五四文学研究的序幕。一时间,一大批五四文学研究的学术论文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思想解放气息和迥异流俗的学术新见,涌现在《文学评论》等全国各大重要学术刊物上,可以说,在20世纪80年代初,在刚刚复苏的五四文学研究界刮起了一股“朱德发旋风”。
朱先生无疑是近百年来五四文学研究用力最勤、著作最丰的学者之一。朱先生对五四文学进行了多层面多视角的研究,既有“史”,也有“论”,既有对五四文学的整体关照,也有对五四文学观念、文学思潮和流派的细密梳理,既有作家专论,也有对具体作品的深入研析,构建了一个丰富多维的五四学术研究世界。朱先生曾把新时期以来的五四文学研究概括为初探—深化—突破三个历史阶段,朱先生完整地参与了这个过程,并在每一个阶段都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从最初的《五四文学初探》(1982)、《茅盾前期文学思想散论》(1983),中经《中国五四文学史》(1986),到《五四文学新论》(1995),完整构成了朱先生五四文学研究的学术脉络。特别是《中国五四文学史》,更是与此后刘纳的《论“五四”新文学》、许志英的《五四文学精神》等,构成了新时期以来五四文学研究最重要的收获,迄至今天,也是研究五四文学无法绕过的标志性著作。《中国五四文学史》虽然是“迄今第一部也是惟一一部重要的五四文学断代史”,但是就其达到的学术创新程度而言,与既往各类文学史关于五四文学的论述相比,《中国五四文学史》确实又是真正意义上的“重写”。《中国五四文学史》的显著特点正如学界早已指出的:“运用历时性与共时性双向建构的考察方式,探讨了五四新文学的来龙去脉与演变范型。其书宏观审视气势博大,微观考查刻度精细,初步显示出了朱先生的文学史思维方式的特点与文学史总体把握的突出能力。”[1]《中国五四文学史》奠定了朱先生在五四文学研究界的地位,是中国五四文学研究史上的标志性著作。
探究历史的“本真面影”,是朱先生走向五四学术研究的初衷,也是激发朱先生学术激情的内在原动力。20世纪70年代末,朱先生为大学中文系学生开设了“五四文学研究”的课程,并参加了田仲济、孙昌熙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之“五四文学革命”一章的撰写,由此,朱先生开始真正走进五四文学,并开始了其贯穿一生的五四文学研究。在这一过程中,朱先生以超乎寻常的毅力,埋首故纸堆,苦研深钻,接触、阅读了大量五四文学的原始史料,“几乎翻遍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编写的所有‘中国现代文学史’,较为广泛地阅读了‘五四文学革命’的有关史料、重要报刊和主要作家作品以及政治经典文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的权威论述。”[2](P2)但困惑也随之产生,那就是文学史论述与历史史料间的巨大背离和矛盾,“还历史一个真实的面目”[2](P3)由此成为朱先生走进五四文学研究的最初也是根本的学术动力和出发点。这段埋首故纸堆的经历,不仅为他后来撰写《中国五四文学史》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更为重要的是,在阅读这些历史原始史料的过程中,重新回到了历史现场,这构成了朱先生五四文学研究的一个鲜明品格:回归原点,立足史料,言之有据,不发空论。
《五四文学初探》和《中国五四文学史》在五四文学研究中的价值和地位,学界已有共识,而对于朱先生的另一重要著作《五四文学新论》的意义,似乎认识不足,这里面有一个客观因素,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文化环境发生了整体性的变化,特别是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彼时学界的兴奋点已经不在五四,故《五四文学新论》的学术价值并未被学界充分认知。《五四文学新论》是对《五四文学初探》的深化和对《中国五四文学史》的理论升华,如果把《五四文学初探》看成是朱先生五四文学研究序曲的话,那么《五四文学新论》则是其辉煌的点睛之笔。如在《生命哲学:五四文学观念的深层文化意识》一文中,朱先生在系统梳理、辨析了郁达夫、郭沫若、周作人、鲁迅的文学观后,指出五四文学观念的深层文化意识既不是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也不是人道主义,而是生命哲学,这是对五四文学的一种全新认知和判断,也是一种新的理论概括。从“生命哲学”的高度研究五四文学,既与五四文学的客观实际相一致,也与朱先生一向秉持的人本主义的学术旨向相契合。在一定意义上,《五四文学新论》不仅标志着朱先生的五四文学研究跃上了一个新的高度,也把中国五四文学研究引向了一个更为深邃和超拔的学术境界。
从“初探”到“新论”,既是朱先生五四文学研究的学术轨迹,也是中国五四文学研究走向深化的标志。
学术研究,本质上是一种精神的对话,而研究对象的选择,则是心灵契合的结果。在长期的五四文学研究中,特别是在与五四文学大师们心灵的对话中,朱先生逐渐形成了鲜明的学术个性。学术个性是一个学者成熟的标志。在第二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队伍中,朱先生是少数具有鲜明学术个性的学者之一。这种学术个性具体表现为:青春气息、创新激情和独立精神。
在学术研究上,朱先生存在着浓重的“五四情结”,在学术个性上,则具有强烈的“五四气质”,五四文学研究不仅“点燃了我的生命激情”[2](P3),而且深深地影响了朱先生的学术品格,而且内化成了某种精神气质。朱先生曾坦言:“通过对五四文学的生命体验与理性感悟,使我的文化人格力注入了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增强了‘诚’与‘爱’的人生内涵,提升了真善美和谐统一的审美境界,激起了学术生命力的爆发力。”[2](P5)虽年逾八旬,但是朱先生仍然对学术充满了浓厚的兴趣,仍旧充满了创造的激情。就在最近一篇文章中,朱先生仍在孜孜思考和探求“创造力”的问题——现代中国文学史教学与提升学生创造力之间的关系问题。[3]他把生命的火焰化成了学术的激情,可以说,五四文学既是他学术研究的对象和领地,也是他生命的润泽和寄托。
作为一代著名文学史家、文学史学家,朱先生始终坚守一个学者的“独立姿态”,始终坚持“根据自己的感受和思考发出内在的声音”,[2](P1)探讨真理、求异追新构成了朱先生的学术关键词。由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独特的政治文化语境,朱先生自登上学术舞台起,即喜做“翻案”文章,从质疑“五四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开始,一路“翻案”——翻“左”的案,翻“定论”的案,翻所谓“正统观点”的案,在质疑中探索,在突破中创新,这一点在最初的《试探五四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一文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即使在今天看来,这篇文章仍闪耀着思想解放的光芒,集中体现了朱先生实事求是、探索真理的精神和超越常人的学术胆识和勇气。在这篇文章中,朱先生对五四文学指导思想这一极为敏感、复杂的问题提出了质疑,通过对大量五四文学史料的爬梳钩沉,特别是通过对五四文学革命产生的特定历史背景、《新青年》的实际思想倾向、五四文学革命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的细密考察和深入辨析,提出:“五四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呈现出一种比较复杂的形态,它是各种‘新思潮’的混合体”[4](P5),但其主要方面是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之前学术界所普遍认为的五四文学运动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定论”。这在当时的确是一种充满了冒险的学术探索,没有一种实事求是、勇闯学术禁区的精神是无法想象的。事实上,朱先生走向五四文学研究之初,都是有意识选择那些在文学史上有争议、被忽视的作家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这既是一种研究“策略”,更体现了朱先生的敏锐的学术直觉和过人的学术胆识。《五四文学初探》以及《茅盾前期文学思想散论》中几乎所有的文章,都是“翻案”文章,如《评五四时期胡适的白话文学主张》《论五四时期周作人的文学主张》等,都极力冲破“左”的反智主义的禁锢,对一些颇具争议的五四时期代表人物如胡适、周作人等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历史主义的评价和分析,没有过多地受政治思想和传统观点的影响,这些充满了探索精神的文章,在一定意义上开启了后来学术界“胡适热”“周作人热”的先河。更重要其实还不是这些文章中阐述的具体观点,而是透过这些“翻案”文章表现出的一种真正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再如《五四文学初探》中关于《尝试集》的评价,打破了既往文学史的成见,客观地指出这部诗集“对于扫荡旧诗坛上的颓靡腐朽的诗风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4](P178)“是一部有进步思想内容的新诗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五四’前后的时代精神。”[4](P182)相反,对鲁迅,朱先生并没有被某些“权威”论述和笼罩在鲁迅头上的光环所吓怕,在《鲁迅五四前后“为人生”的文学观》等文中,朱先生在肯定鲁迅五四“为人生”文学观历史意义的基础上,也实事求是地指出其中的一些矛盾之处和局限性;对于鲁迅的《狂人日记》,当时一般认为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具有“朴素的阶级观点”,而朱先生在《论〈狂人日记〉的人道主义思想倾向》中,朱先生在对《狂人日记》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内容以及艺术描写所体现出来的审美观、艺术观进行深入分析后,认为“鲁迅创作这篇小说的主要指导思想,不是受了马克思主义影响的阶级论,而是进化论、人道主义。”[4](P188)这类“翻案”文章,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乍暖还寒的政治语境中,是具有相当风险的,然而,恰是在这些“翻案”文章中,体现了朱先生不畏权威、坚持真理的学术品格。
学术的使命在于创新。一个真正的学者,既要有打破成见的勇气,也要有敢于超越自己的精神,因为他追求的是真理,而不是所谓对自己观点的“坚守”,时代变了,对五四文学的研究和认识也随之发生转变,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朱先生一直把“创新趋优”看作是其学术研究的生命所在。在《图式结构:五四文学精神新探》一文中,面对五四文学精神这样一个“老话题”,朱先生提出了自己的新见。朱先生透过历史现象对五四文学发生的具体历史文化语境、创作主体的文化心态以及接受主体的期待视野进行了重新辨析,认为五四文学的“现代化程度”与所表现出的文本形态并非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完美,而是“始终纠缠于一个历史与现时、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撞击而又彼此渗透的尴尬局面之中”[5](P45),在这篇文章中,朱先生摆脱了就文学而文学的封闭式研究理路,运用整体论的观点和方法,深入探析五四文学精神与具体“历史发展的内在要求”之间的深层关系,认为五四文学精神“是一个多元的、多层次的图式结构,即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交互多重变奏。”[5](P55)这一观点超越了之前把五四文学精神化为“反帝反封建”“现实主义精神”以及“悲剧意识、自由精神和感性生命特征”等层面,并坦称,之前自己的某些观点,构成了对这一问题的装饰性“误解”。
五四文学研究深刻影响了朱先生的学术价值取向。凡熟悉朱先生的人都承认,在朱先生近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都始终存在着五四的影子。众所周知,五四文学是启蒙主义的文学,是“人的文学”,这是五四文学的核心价值所在,这也正是“五四神话”的魅力所在。朱先生对五四文学这一核心价值理念有着精深研究和深刻领悟,在与五四文学大师鲁迅、胡适、茅盾等的心灵对话中,朱先生不自觉地接受了大师们的“立人”的人本主义思想,并内化成了其学术取向的核心内涵。我认为,朱先生一直是一个启蒙主义者,他通过学术研究,体现和弘扬的是一种人本主义精神,其学术旨归是人的解放。朱先生通过学术研究特别是五四文学研究,参与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思想启蒙运动,参与了那个年代的思想建构。由之,形成了朱先生高远健朗的学术品格。
朱先生认为,一个学者的最高追求和学术使命在于通过学术“维护全面的人性、人类完整的感性”[2](P11)。从五四文学研究到文学史学的建构,虽然具体的研究对象、研究领域几经转换、拓展,但是,五四文学带给朱先生的特有的价值追求、精神品貌并没有改变,而是一以贯之地存在于朱先生整个学术世界中,构成了朱先生坚强的学术支点。例如,《五四文学文体新论》一文,看似是研究五四文学的具体“文体”问题,然而,作者的旨归却并不是“文体”,而是“人”,探讨的是“文体”后面创作主体的个性意识和精神自由,只不过是从“文体”的视角切入而已,朱先生念兹在兹的仍是人的解放,因为,在朱先生看来文体结构与主体精神结构具有同构性,五四文学文体解放是个性和情感解放的一种表现形式:“五四文学文体自觉与人的自觉取得圆满的共振性与同构性,五四文学文体表现出强烈的主体意识,同时体现了人类情感的彻底解放。”[5](P244)即使在一些具体的文本如五四诗人沈玄庐的叙事诗《十五娘》的分析中,朱先生孜孜思考和探索的仍是人的解放和精神自由问题,而不执著于文本主义分析。这种人本主义价值追求使朱先生的学术研究境界高远,气象开阔。
朱先生深知没有对“人”的理解和关注的学术研究,就会干瘪萎缩,就会失去生命活力,并最终走向学术研究的反面。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提出,“史才”须有“三长”即才、学、识。应该说这“三长”朱先生都具备,且都高于常人,然而,这只是朱先生作为一代文学史家的“优先条件”,最主要的还不是这些“优先条件”,而是朱先生一生致力于对“人”的自由和解放的追求。早在“文革”大学“复课闹革命”时,朱先生因给工农兵大学生授课,即开始“思考文学史的书写”,至今已逾40多年。特别是自20世纪70年末期,朱先生参与田仲济、孙昌熙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始,中经80年代末同蒋心焕、陈振国主编《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89),到皇皇三大卷200万字的《现代中国文学通鉴(1900-2010)》(2012),朱先生主编、独撰的文学史著作已逾十余种,在这些文学史著作中,有一个核心的一以贯之的理念,那就是“人”的文学,朱先生又称为“人学文学史观”。从文学史实践到文学史思维学,再到文学史哲学,在这个学术世界中,“人”始终居于中心位置。朱先生指出:“‘人的文学’史观,……它应该被看做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或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的核心理念。”[6]而这正是五四文学的核心价值理念。
人本主义的学术价值观贯穿于朱先生重写文学史、重构现代中国文学学科的所有层面,特别体现在朱先生对文学史建构“价值尺度”问题的思考。朱先生明确提出“人类的普世价值追求应该在文学史的研究或书写中越来越得到呼应。” “需要选择或确立一个带有普适性且能关注所有书写对象价值内涵的大家认可的价值评估体系”[7]这体现了朱先生作为一个大学者的远见和胸怀,更体现了一个现代学者的价值追求。在《现代中国文学史重构的价值评估体系》一文中,朱先生提出了文学史价值评估体系的标准问题即“一原则三亮点”:“以‘人道主义’作为评价现代中国文学的最高原则”[8](P175),同时,将人道主义作为文学史重构的价值评估体系的“最高原则”;“三亮点”则是指以真、善、美作为评估现代中国文学的价值尺度,“这是因为人之生存、发展的最高境界是真、善、美的和谐统一,这种统一既是人类心灵联结的纽带,又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 “对现代中国文学必须以‘人道主义’这一最高原则为前提来重估一切价值,确定其以真、善、美为核心的人的文学的基本内涵。”[8](P176)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新编》时,朱先生就擎起了人本主义的大旗,他明确宣布这部文学史坚持“人学思想和‘文学是人学’的观念”[2](P8);2002年,在《重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意识》一文中,朱先生正式提出了“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概念,标志着朱先生从一个卓有成就的文学史家到文学史学家的转变。从“中国现代文学史”到“现代中国文学史”,不仅仅是语序的变化,而是标志着对现代文学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评判与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一书中,朱先生更是开宗明义,指出重构“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核心理念是“人的文学”。在此基础上,朱先生完整提出了“人本型”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构问题[9]。从上可以看出,“人的文学”的理念,是朱先生一生坚守的学术价值指向。而“人的文学”理念无疑来源于五四。这一点,在《现代中国文学通鉴(1900-2010)》中更是得到了集中体现。在这部恢宏的文学史著作中,朱先生认为,能够把形态各异、差异互现、系统多元的现代中国文学统摄连通起来的一个核心理念只能是“人的文学”的人本文学观,因为只有“‘人的文学’属性就是各种形态或系统文学之间的‘本质联系’”[10](P47)。事实上,恰恰是“人的文学”理念支撑起了这个巨大的开放式全方位的现代中国文学的架构,从而使“现代国家观念”为基石的“现代中国文学”学科框架得以很好建构和体现。
朱先生曾提出“为学术而学术”的问题,这主要是指学术态度问题,即要有一种真正的学术精神,也就是坚守真相坚持真理的精神。朱先生认为,学术研究“旨在探讨真理、创新趋优、言说真话”[2](P5),这几句看似平淡无奇的话,其实做起来又谈何容易?没有一种为学术而献身的精神是很难做到的。例如,在1980年代初“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朱先生关于五四文学研究的一些观点被“揪了出来”,受到批判,遭到“全国共讨之”的厄运,甚至不得不暂时远离自己喜爱的五四文学研究,但即使如此,朱先生仍旧坚持“不会套用现成的公式,不会盲从流行的概念,我相信文学史的真相只存在于原始史料中,绝不存在于公式或者概念中。”“我觉得自己有义务有责任去探究五四文学运动的真实面目。”[8](P311)这是一个“真学者”的发自内心的真实声音。再如,在《朱德发文集》第2卷也即《中国五四文学史》的末尾,朱先生特别注明一句话:“除了错别字可改正外,绝对不要修改原著……哪怕某些观点与当下认识向左或者某些注释格式不符合当下要求也必须尊重历史,总之最大限度地保持原著原文的历史面貌。”[11] (P1)与那些随着时代风气变化不断修改自己观点的做法相比,寥寥数语,体现了一个“真学者”尊重历史、严肃认真的学术态度;同时,也体现了朱先生的一种学术自信。事实上,朱先生的自信源于他一贯的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学术品格。
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在《理念人》中曾说,知识分子是指那些超越了直接的具体工作,向“意义和价值”更普遍更一般去探求的人。作为一个现代学者,朱先生的所毕生追求的“意义和价值”就是“人”的解放,就是人的现代化,就是现代国家的建立。朱先生曾深有感触地说,一个“真学者”不只是把致力于学术研究当成其生存方式和价值根基,具有一种自觉的以身殉业的奉献精神,而且应从骨子里体现出特立独行、耿直率真、光明磊落、刚直不阿的学术人格。无论是在学术成就还是学术人格上,朱先生都出色践行了一个“真学者”的理念和追求,践行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使命,堪称一代学人的楷模。
参考文献:
[1] 谭桂林.从文学史著到文学史学[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 (6).
[2] 朱德发.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三十余载有感(代弁言一)[A].朱德发文集:第1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
[3] 朱德发.现代文学史书写与创新能力培养[J].山东社会科学,2014,(6).
[4] 朱德发.朱德发文集:第1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
[5] 朱德发.朱德发文集:第4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
[6] 朱德发,顾广梅.“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建构的设想与思考——朱德发先生访谈录[J].新文学评论,2013,(2).
[7] 朱德发.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3,(1).
[8] 朱德发.朱德发文集:第9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
[9] 朱德发.人本型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构特征[J].烟台大学学报,2010,(3).
[10 朱德发,魏建.现代中国文学通鉴(1900-2010)(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1] 朱德发.“文集”编选设想及其内容提要(弁言二)[A].朱德发文集:第1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冯济平
Zhu Defa and His Study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May Fourth Era
WEN Feng-qiao1WEN Feng-xia2
( 1.College of Liberal Arts,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2.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Jinan 250014, China )
Abstract:As a famous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writer, Mr. Zhudefa was the leading fi gure of the May Fourth Era and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ies of this Movement. His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May Fourth Era i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May Fourth literary study in the past one hundred years. The May Fourth literary study has exerted great infl uences on Zhu Defa's academic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Zhu Defa; study of the May Fourth literature; academic character
作者简介:温奉桥(1968-),男,山东沂源人,文学博士,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温凤霞(1974-),女, 山东沂源人,山东财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5-01-25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6)01-004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