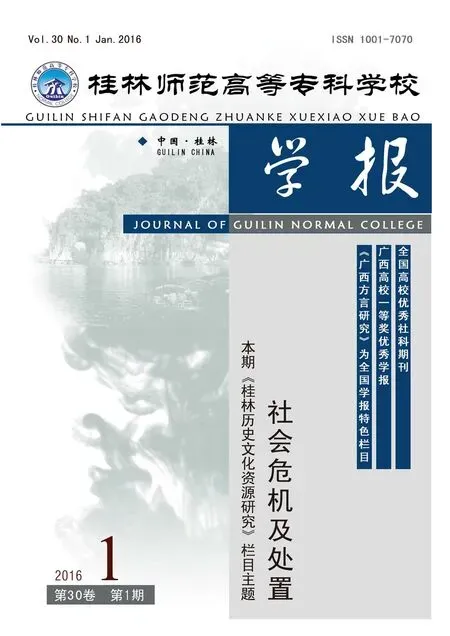魏晋士大夫对佛教大乘思想的选择
2016-03-18侯宾
侯宾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思政部,广西 桂林 541001)
魏晋士大夫对佛教大乘思想的选择
侯宾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思政部,广西 桂林 541001)
佛教在东汉初年从印度传入中国至今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从外来宗教演变为盛极一时的国家宗教,佛教完成了在中国的本土化。魏晋时期中国社会对佛教大乘思想的选择和接受,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士大夫阶层的影响。
大乘佛教;小乘佛教;士大夫
佛教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它起源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印度次大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佛教曾是古印度文化的代表。中国佛教虽然不是直接来源于印度,但却保存了印度佛教的基本精神,它是印度文化在中国文化圈内的移植。但中国佛教有别于印度佛教,经过长期的选择、改造和重构,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融入了中国文化之中。
自东汉安世高译经开始,印度佛教宗派中的大、小乘思想便被陆续介绍到中国。但经过中国文化的吸收和转化,唯有大乘佛教思想在中国北方汉族地区得到了广泛认可和传播。虽然小乘佛教的“六道轮回”“因果报应”思想最早在中国佛教徒中引起反响,但在中国即兴即亡,很快就消退了,而大乘佛教则滋生繁茂,源源不断。佛教大乘思想在魏晋时代获得认可并不是偶然的事件,众多因素影响了中国文化对大乘佛教的选择。作为一种外来宗教思想的移植,大乘佛教思想需要社会主体的认同,魏晋时代的知识分子即士大夫阶层正是这种选择的中坚力量,他们的接受和认可深深影响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一、佛教大、小乘思想的基本内容
佛教在印度产生和传播的过程中曾有过四次集结,先后导致了两次的大的分裂,先是上座部(有部)和大众部(空)的分裂,后来则是小乘教和大乘教的分裂,后一次分裂导致了佛教大、小乘两种思想的独立发展。
“乘”本身有运载、乘坐之义,大、小乘思想是针对佛教涅磐彼岸世界而提出。大乘在印度文中原指“伟大”的车辆或大轿车,小乘则被指为“低劣”的车辆。虽然二者在印文中有褒贬之分,但佛教史著作中沿用的“小乘佛教”“大乘佛教”等称谓,却不存在褒贬之意。在教义上小乘强调“我空法有”和个人涅磐,即以追求个人的自我解脱为主,从生死出发,以离贪爱为根本,以灭尽身智为究竟,秉持着纯粹的出世理念。大乘则强调“我法俱空”和普渡众生,即断除自己一切烦恼外,还应以救脱众生为目标,既出世又强调要适应世间,以大开佛法的方便之门。佛教大、小乘思想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而且两者的差异不仅仅是修行方式的不同,更表现为主导思想的迥异和个体境界的殊胜。在佛教哲学的意义上对两者进行考察,大乘思想更具哲学气息,而小乘思想的宗教意味更加浓厚,小乘思想属于真理认识的初级阶段,而大乘思想则属于真理认识的高级阶段。
二、中国选择佛教大乘思想的社会条件
从外来宗教输入的客观因素来看,佛教思想的传承和传播是一个由西向东的过程,其思想传播的载体即为佛教的各种经典。史籍中记载:“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1]佛教经由中亚首先传入我国新疆地区,再经敦煌地区,通过河西走廊进入内地,史称“佛出西域,外国之神”[2]。由于“佛教为外来之学,其托命在翻译,”[3]佛教的传播与经典的翻译密不可分,译经工作在佛教传入后的千年间一直被当作最主要的事业来完成。早期翻译的佛经并没有大、小乘之分,佛教经典经由西域诸国向中土陆续地输送,而各国信奉的佛教经典并不统一,中原地区接触到的佛经兼而有之。随着译经工作的不断深入,后期所译出的经书则逐渐以大乘经典为主,且其数量远远高于小乘佛教经典,这既是佛教大乘思想被选择的一个缩影,客观上也成为了其思想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从中国接受佛教的思想环境来看,东汉时期的官方儒学已走进了谶纬学的误区,变得空洞烦琐、枯燥无味,儒学的影响逐渐式微并不断衰落。中国道教此时还处于不断形成的初期,宗教的功能还未完全具备,因而无法为现实中人提供一个完美的彼岸世界。从公元254年到公元290年前后的50多年里,富有思辨性的魏晋玄学开始发展壮大,形成了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的一种特定的哲学思潮,并围绕“本末有无”[4]问题探讨了“有”“无”,“体”“用”,“本”“末”,“一”“多”,“名教”“自然”等范畴。这些范畴与佛教思想有部分相通之处,如大乘般若学的基本原理就是讲性空,而道家老庄哲学中也讲无名无为,两种思想虽有差异但都指向了存在这一哲学基本问题,二者都超越了现实存在的实体,去探究一种空灵的存在境界。佛教中人研习老庄,魏晋玄学中的知识分子研究《般若经》和《维摩经》成为一时风气,两种思想在两类不同的人群间产生了互动和交流。
三、魏晋士大夫对中国佛教大乘思想的选择
思想在交流的过程中蕴含着选择,佛教思想中国化的历程就是一个被接受被选择的过程。马克思·韦伯认为:“在社会地位与对不同宗教世界观的接受倾向之间,有着一种显而易见的明确的关系。这种联系主要取决于接受者对宗教教义的选择。”[5]如果把中国佛教的接受者划分为以祈求福运为目的民俗阶层和知识程度较高的士大夫阶层进行比较,后者的政治身份和文化地位对宗教教义的选择则具有明显的优势,更有能力影响社会文化的走向。
(一)士大夫是佛教思想传播的依靠阶层
对于民俗阶层而言,他们对佛教大、小乘教义的选择权不大,甚至也不会太重视。这不是忽视了民俗阶层的重要性,只是说他们很少像僧侣和知识分子那样去把握复杂深奥的哲理,他们只关心“有求必应”的现世利益。道安曾说:“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6]不难看出,获得政治力量的支持与主流文化的认可,是佛教扩大影响和发展的前提条件。
外来宗教作为社会上层建筑需要得到当地上层社会的认可,否则很容易被当作异端邪说来限制。汉末至魏晋的士大夫阶层不仅代表着一定文化地位,也享有一定的政治权利。士大夫阶层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阶层,是知识分子和官僚相结合的产物,很多人兼有双重的社会身份,他们既是文化的倡导者,又是封建政治统治的中坚力量。魏晋士大夫们在文化领域也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历代所谓“正史”中有记载的佛教人物,除《魏书·释老志》外能被列传记载的不过十余人,“正史”中记载与佛教人士有联系和交往的魏晋名士却很多,而且记载描述得十分丰富详尽。从文化选择到政治认可的需要来看,魏晋士大夫阶层既掌握着主导文化的话语权,又具备一定政治的影响力,所以魏晋士大夫阶层自然会成为当时佛教传播所依靠的主要社会力量。
(二)士大夫阶层对佛教大乘思想的选择
从自身的精神需要来看,魏晋士大夫阶层对大乘佛教思想是有好感的。魏晋时代是一个反叛传统的特殊时期,旧的道德规范已演变为缚束人们思想的僵死教条,过去的儒家伦理道德和谶纬宿命之学已招致了士大夫们的深度怀疑与强烈反感。“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检”[7]的风气由此开启,魏晋士大夫阶层形成了以钻研老庄为特色的学风和人生态度。
在魏晋玄学形成发展的过程中,佛教大乘思想的传入为士大夫阶层研究玄学提供了新的路径。谢灵运说:“今孔废圣学之路,而释开见渐悟之径。”[8]从对精神境界的追求来看,要求解脱羁绊、返回自然的士大夫们对佛教追求智慧的直觉方法颇有好感,但肩负圣人使命的现实责任感又促使他们形成一个折中的态度。士大夫阶层对印度佛教所提倡的苦行、戒律、禁欲、禅定等艰苦的解脱方式并不感兴趣,却对于以直觉把握幽玄的奥理,以心灵体验为主的理解方式表现出特别的热情。谢灵运还说:“大而校之,华民易于见理,难于受教,故闭其累学,而开其一极。”[9]超越宗教的仪式而追寻思想的深邃成为了士大夫阶层的选择,大乘佛教思想正是超越于个人修炼之上的追求终极意义的渡世哲学,在逻辑上更为严密也更具有思辨性,从而与士大夫阶层的需要相一致。
另一方面,佛教文化作为古印度文化的代表,与中国本土文化是两种完全异质的文化形态。魏晋士大夫们虽然在一定意义上产生了接受和认同,却难以消除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影响,文化沉淀不会因为佛教传入而消失。从《牟子理惑论》“恍惚变化,分身散体,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圆能方”[10],到宗炳《明佛论》中“虽慈良无为与佛说通流……是以孔老如来虽文训殊路,而习善共也。”[11]魏晋士大夫对佛教的认识就体现出了文化的差异,他们或将佛教理解为神仙方术,或不断尝试打通儒、道与佛教间的障碍,力求获得佛教存在的合法性。既然存在认识和理解上的差异,佛教在传入初期就必须顺应中国本土文化的特点,以期获得最终的认可和传播。
(三)佛教徒对魏晋士大夫阶层的顺应
在佛教思想与中国文化的交流融合过程中,利用中国文化自身的元素阐释佛教思想更有利于佛教的生存和发展,魏晋时期对道家老庄思想的研习之风为佛教徒与魏晋士大夫阶层提供了交流的契机。
佛教思想传播的载体是佛经,传入中国之时皆为外国文字所抄写,故有大量的经典需要翻译。佛经翻译的难度在于“佛之著教,真人发起,大行于外国,有自来矣。追及此土,当汉之末,晋之盛德也。然方言殊音,文质从异,译梵为晋,出非一人,或善梵而质晋,或善晋而质梵,众经浩然,难以折中。”[12]佛经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翻译,而是思想与思想的对话和转译,更是两种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鉴于魏晋时期的文化环境,佛教思想要保持自身的独立性是有难度的,所以佛教徒要把当时流行的老庄思想和佛教思想相融合,从而顺应中土文化的要求。
除此之外,佛教人士更是加入到中土士人的文化圈之中,进一步扩大佛教思想在士大夫阶层中的影响。道安《毗奈耶序》中说:“于十二部毗目部最多,以斯帮人老庄行教,与方等经兼忘相似,故因风易行”。[13]名僧支道林用“致人乘天正而高兴,游于无穷而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则遥然不我得,玄感不为,不疾而速,则逍然靡不适”[14]来展现他对庄子逍遥意境的感悟。佛教徒在老庄思想上做文章,推进佛教思想与老庄思想的交流,不仅形成了“谓滨务逍遥之极,庐岳结般若之台”[15]的文化氛围,还以此来结交士大夫阶层。从“支道林、许(询)、谢(安)盛德,共集王家。谢顾谓诸人:‘今日可谓彦会,时既不可留,此集团亦难常,当共言咏,以写其杯’”[16]中可以看到他们交往的盛况,魏晋士大夫们也通过钻研佛学来提升玄学素养,双方的交流互动成为一时之风。
有学者认为佛教大乘思想与中国传统之思想相融洽,乃是佛教能在中国发展的一个基本因素。[17]佛教徒为顺应中土文化,相应选择了哲学气味胜过宗教气息的大乘教义,以满足士大夫阶层对思辨和义理的需要,形成了佛教层和士大夫层彼此间的交流。虽然佛教所蕴含的思想极为丰富而且自成系统,但在深厚的中国文化面前却无法保持其独立的特性,作为外来宗教必然要经历一段被理解和被选择的过程。在魏晋时期,由于大乘佛教思想本身的价值和士大夫阶层的需求具有了契合点,才促使士大夫阶层对佛教大乘思想由陌生走向了理解和接受。佛教人士与士大夫阶层在持续的交流和互动中,抬升了佛教在中国的地位与影响,以至后来“晋元、明二帝,游心玄虚,托情道味,以宾友礼待法师,”[18]使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获得了封建王权的认可,在政治上获得了最终的确立。
魏晋士大夫对大乘佛教思想的选择不仅仅是一个社会阶层的选择,它代表了中国文化选择的一个缩影。客观来看,大乘佛教思想是社会和历史的产物,是印度进入封建社会后不断走向成熟的,它更加符合封建社会的政治需要。中国虽较早步入封建社会,但中国社会接受佛教思想仍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佛教根据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进行了自身的转变,依靠与士大夫阶层的互动获得了政治与文化的认可,完成了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使命。
[1]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3025.
[2][6]释皎慧.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4:352,178.
[3]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02.
[4]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79.
[5]托马斯·F·奥载.宗教社会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110.
[7]萧统.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692.
[8][9]道宣.广弘明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232.
[10][11]释僧佑.弘明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2,12.
[12][14]释僧祐撰.出三藏记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5:227,1.
[13]李霞.中国佛教解经方法的演变[J].中国哲学史,1998:75. [15][16][18]刘义庆撰.世说新语汇校集注[M].刘孝标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94,211,289.
[17]钱穆.中国文化导论[M].北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39.
The Selection of Mahayana Thoughts by Cao-Wei and Jin Dynasty Scholar-Officials
Hou Bin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 of Guilin Normal College,Guilin,Guangxi 541001,China)
It has been about two thousand years since Buddhism was spread from India into China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Buddhism had localized form external religion to national religion and Mahayana had been finally established in China.The paper draws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selection of Cao-Wei and Jin Dynasty scholar-officials acted important role in this event.
Mahayana;Hinayana;scholar-officials
B948
A
1001-7070(2016)01-0047-03
(责任编辑:韦国友)
2015-09-22
侯宾(1980—),男,陕西西安人,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思政部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