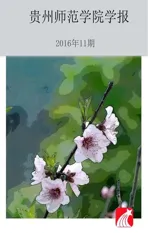论新媒体对本土文化的传播效应
——以贵州文化为例
2016-03-18黎筝
黎 筝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论新媒体对本土文化的传播效应
——以贵州文化为例
黎 筝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密不可分。人类历史上每一次传媒的更新都为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提供了契机。相较于主流的传统文化,本土文化往往因其区域性限制而被边缘化。同时,外来文化的传入也对本土文化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那绝不意味着本土文化的必然衰落。新媒体的产生和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本土文化的传播。它为本土文化创造了有利的媒介环境,产生大量正向的传播效应,带来了更胜一筹的传播优势。
新媒体;本土文化;传播效应
从历史演变的过程来看,文化只有传播才能成为文化,有传播才有文化的产生和传承。单个人类个体的存在不足以论及文化,因为它不能像生物基因一般遗传。文化必然是人们在漫长的群体生活中共同创造、不断累积、彼此交流、普遍认同的。尽管广义上的文化无所不包,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吃穿住用到柴米油盐。但“文化更多地被看成一个受价值观和价值体系支配的符号系统。”[1]这个符号系统蕴含了人类历史的全部信息。而媒体的天然使命正是传播信息,从根本上来讲就是文化信息。人类历史上每一次媒体的更新都为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提供了契机。无论是印刷传媒,还是电子传媒,抑或数字传媒,各个阶段的传播媒体都具备了“承接和传授文化、选择和创造文化、积淀和享用文化”[2]等一系列强大的文化功能。时至今日,人类的文化如璀璨星河般源远流长,媒体的传播功不可没。而对于本土文化来说,新媒体的发展将为其带来更胜一筹的传播优势。
一、新媒体时代本土文化的传播契机
“有别于全民族共同关注的传统文化,本土文化是各区域地方的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携手创造的,包括当地独有的价值观念、风俗信仰、惯例禁忌等文化因子。”[3]相较于主流的传统文化,本土文化往往因其区域性限制而被边缘化。然而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恰恰是这些植根于现实生活方方面面的本土文化滋养了各区域地方的广大人民,创造了覆盖神州大地960万平方公里绚烂多样的文化盛景。仅以贵州为例,始自石器时代的本土文化历史悠久,先后产生了夜郎文化、屯堡文化、阳明文化、沙滩文化、长征文化等独特的地方文化。而18个世居少数民族的文化更是使得贵州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文化千岛”,备受赞誉。在这些异彩纷呈的本土文化中有着大量优秀的文化元素,它们对青年人的爱国教育、道德教育、生态教育、审美教育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在新的历史时期,弘扬本土文化,发掘其所涵养的时代价值和教育功能,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
与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不同的是,今天人类正处于一个极速发展的阶段。社会生活的便捷性优先体现在了互联网络中。从Web1.0到Web2.0,人们架设起了数字化信息高速公路,任意驰骋。而其含义就是“以光速在全球传输没有重量的比特。当一个个产业揽镜自问‘我在数字化世界中有什么前途’时,其实,它们的前途百分百要看它们的产品和服务能不能转换成数字形式。”[4]22-23于是,各种新兴产业大量涌现,许多传统产业也开始了大规模深层次的技术升级。新媒体便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应运而生。从2006年的博客到2009年的微博再到2011年的微信,新媒体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将传统媒体下的沙发土豆们俘获为了网络成瘾者、手机依赖者。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数字化科技所征服,切身体会着如若没有网络、没带手机所产生的那种焦灼感。人类生活与数字化技术紧密地黏合在了一起,就像未来学家尼葛洛庞帝(Negroponte)预言的那样:“计算机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4]15人类已经进入了数字化生存的时代,新媒体是这个时代的一大表征。
关于新媒体概念的产生,最早应追朔到1967年。当时,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网(CBS)技术研究所所长高尔德马克(Goldmark)就将他计划开发的电子录像称为“新媒体”。此后,新媒体的内涵日渐丰富。作为一种媒体的新形态,有人强调它的数字化基础,也有人强调它的非线性模式,还有人强调它的交互功能。众说纷纭之下,人们也渐渐意识到新媒体其实是一个相对概念,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新媒体。印刷传媒主宰的时代,广播、电视是新媒体;而电子传媒主宰的时代,互联网又成为了新媒体。事实上,新媒体之“新”不在时间而在技术性变革带来的质的突破,导致了人们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的巨大转变。它将以往在传统媒体面前被动、沉默的报纸读者、广播听众、电视观众变为了拥有话语权的参与者。借助新媒体传播人类文化,人们将不再是站在文化场域边缘的旁观者。这种积极的推动作用是技术性与人文性的结合。更重要的是,不同于传统媒体大多倾向于主流的传统文化,新媒体的发展能够令长久以来被边缘化的本土文化获益匪浅。
二、新媒体对本土文化的传播效应
“任何技术都倾向于创造一个新的人类环境。”[5]因为新技术将对人们的行为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新媒体的发展为本土文化的传播创造有利的媒介环境,产生大量正向的传播效应。
(一)激活效应
诚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它是“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6]78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建立在物质资料的基础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不过,当人们一心一意地追求物质极大丰富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在工具理性的岔路上渐行渐远。对物质的占有与渴望不仅成为了衡量社会的外部尺度,也成为了反观自我的内部尺度。于是,人性的扭曲、人类的异化在所难免;逐渐物化的人们彻底丧失了主体性。继征服自然之后,人类又一次陷入了生存的危机。这种危机有着深层次的破坏力,直接危及到了人类安身立命的根本——文化。实际上,每个看似独立的社会个体都是人类世界最复杂的集合体,究其本质,都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56,是类的存在物。他不可避免地与其他个体产生交集,彼此交往,相互影响;既实现自我,又尊重对方。这样的交往绝不是任何一方的个人独白,它打破了过去“主体—客体”的传统模式,确立了“主体—主体”的新型模式。双方都具备主体性,这一点至关重要。这也正是倡导“交往行动理论”的哈贝马斯(Habermas)一再强调的“主体间性”。只有在主体间性的基础之上,主体才能凭借已有的文化资源彼此理解,并通过彼此的交流实现文化信息的传播。本土文化以往的传播方式,如刻板的课堂教育、大部头的研究专著、沉闷的文化宣讲、千篇一律的文化节等恰恰忽视了这一原则,沿用的是主客体对位的传播模式,置信息接受者的主体性于不顾,导致文化传播的结果收效甚微。针对主体性缺位的弊端,新媒体的优势集中体现为激活效应的产生,在传播模式上弥补本土文化已有传播方式的不足。它使人们在对话交流时建构起了互为主体的对等关系,激活了原来被动的接受者的主体性,赋予了他们选择文化信息、传播文化信息、共享文化信息的自主性。其实“发生传播的关系看起来是简单的,两个人(或者两个以上的人)由于一些他们共同感兴趣的信号聚集在一起。”[7]关键是二者能否找到彼此的兴趣点,即共通性。这种共通性以突出双方的主体性为前提。缺失掉任何一方都可能造成传播的中断,甚至永久性终止。无疑,新媒体语境下的接受者能够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度,他是文化传播过程中的译码者、反馈者、消费者、参与者。凭借新媒体的激活效应,人们能够积极地探寻本土文化日渐消逝的历史印迹,主动地传播居于边缘地带的本土文化信息。如2013年,贵州就曾依凭“微力量”推出了“发现贵州微风景”系列活动。网友们纷纷借助微博、微信,以随手拍的形式记录下贵州山水的绮丽风光和贵州民俗的多彩风情。活动共产生了11000多幅作品,活动网页浏览量竟高达2亿多次,不但有力地促进了贵州文化的传播,而且带动了更多的人来到贵州、发现贵州、认识贵州。
(二)亲信效应
时间和空间是人类生存的两大维度,超越时空素来是人们孜孜以求的梦想。21世纪最令人骄傲的一点就在于,数字化信息社会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实现了时间与空间的压缩,世界变成了地球村,现代人的生活享受着前所未有的优越感。不过,正如美国学者戴维·哈维(David Harvey)基于全球化进程批判的后现代困境:“资本主义的历史具有在生活步伐方面加速的特征,而同时又克服了空间上的各种障碍,以至世界有时显得是内在地朝着我们崩溃了”[8]。同样,数字化信息技术的发展非但没有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相反使其变得更远。虚拟的符号传播着真真假假的信息,各种光怪陆离的事件层出不穷。活着的人也能被说死了,是真实发生的网络怪相。整个世界的确被无限放大了,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却荡然无存。慢慢地,人们开始产生信息抗体。无论传媒说什么,都有可能被当作魔弹而遭受抵制。这成为了传统媒体致命的传播瓶颈。所幸,新媒体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尴尬的传播局面。它将人际传播的特性植入大众传播,形成高联系性的群体关系。微信上,你的朋友圈是稳定的,又是延伸的;微博上,志趣相投的博客也会互粉,在圈内分享各种信息。这种延伸无限扩展,甚至可能通过哈佛大学教授斯坦利·米尔格兰姆(Stanley·Milgram)提出的六度分隔原理聚合产生一个偌大的人际网络。任何素不相识的人之间,采取朋友传朋友的方式,间隔不超过6个人,便能产生联系。最终,以现实社会关系为支撑,信息的传播变得更流畅,信息的接受也变得更容易,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能够产生强烈的亲信效应。新媒体缔造的世界才是真正的“小世界”,它以美国社会学家邓肯·沃茨(Duncan Watts)的“W-S小世界网络模型”为蓝本,具有“高网络聚集度”和“低平均路径”[9]的显著特征。这些特征非常有利于本土文化的传播。因为本土文化是在一定区域内产生的文化,对地域性有着极强的依赖度。跨区域的人们不仅难于理解这种文化,严重的还会反感、排斥这种文化。例如,从未到过贵州的人往往难于理解当地的本土文化。结果在外乡人眼里,原生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完全变了味,失掉了原有的艺术魅力。不但模拟山水花鸟自然之音的侗族大歌曲高和寡,采用靛蓝染色的苗族蜡染单调乏味,就连展示忠义豪情的屯堡地戏也不过是只知道打打杀杀的戏码。而新媒体的亲信效应无疑将化解不同地域的人们接受本土文化的心理障碍,令本土文化信息的传播更为广泛。
(三)强化效应
尽管文化的传播是人类共同的选择,但就个体而言,它同样重要。任何人的任何行为都不是无缘无故的,都有其内在的动因,反映出个体的需求。换言之,人就是“一种不断需求的动物,除了短暂的时间外,极少达到完全满足的状态。一个欲望满足后,往往又会迅速地被另一个欲望所占领。人几乎整个一生都总是在希望着什么。”[10]20世纪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A.H.Maslow)发表了《人类动机理论》,提出了需求层次论的基本构架,包括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与归属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这些需求隶属不同的层次,逐级增高,高一层次的需求在低层次需求得到一定满足之后便会产生,促使人类形成复杂的需求心理结构。现代社会经济的繁荣与科技的昌盛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激励着人们向着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迈进。文化的传播就是人们在探寻自身存在价值时做出的需求选择。来自不同区域地方的人对本土文化有着强烈的表述需求,需要在文化表述的过程中完成文化身份的确认,实现文化信息的传播。而新媒体的传播模式将会极大地强化个体对本土文化的表述需求,产生惊人的强化效应。过去,在美国传播学者拉斯韦尔(Lasswell)的“5W模式”(Who——Says what——In Which Channel——To Whom——With What Effect)中,我们总认为接受者是被动的“靶子”,媒体的力量之大能够彻底地改变对方的观点。然而,需求层次理论却告诉我们:接受者的接受行为也是基于内在需求的。媒体传播的信息,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成为有效的“魔弹”击中接受者,主要是看媒体如何满足接受者的需求。这是一种极具颠覆性的思维大逆转。新媒体的传播正是以接受者的需求为出发点,令接受者成为了传播活动真正的主角。新媒体语境下,不同区域地方的人传播本土文化的需求会不断增强。依托微信朋友圈、博客粉丝群、SNS网络社区等传播模式,人们很容易在本土文化的感召下聚合为一个又一个特定的文化圈。身处其间的人们享有共同的地域文化偏好,彼此欣赏,彼此认同,维护着自身的本土文化身份,实现个体的归属需求。不仅如此,由于新媒体的开放性,文化圈里的每一个成员还能拥有平等的话语权,自由地发布其所看重的本土文化信息,通过与圈内其他成员的交流与沟通完成文化身份的自我定位。无论这种文化表述最终的结果如何,是获得认可,还是遭到反驳,个体的独立人格都得到了应有的尊重,满足了个体的尊重需求。而当这样的传播活动被人们普遍接纳时,它便能呈现为一种良性的循环,持续强化个体对本土文化的表述需求,使得每一个个体都能成为积极的媒体发言人,主动地传播本土文化的信息。如今,在贵州除了政府的官方网络平台,“多彩贵州”、“贵州山歌”、“文化贵州”、“深爱贵州”等众多民间的微信公众号也在大力推广贵州本土文化。而像范同寿等学者的文化博客更引发了探究贵州文化历史的热潮,吸引了大量网友参与互动讨论。
伊格尔顿曾经说过,文化是英语中两三个最为复杂的单词之一;它包罗万象,通达古今。保护与传承文化,绝不是为了复制历史,而是为了探寻人类生存的根本意义,解答“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的终极命题。本土文化的珍贵之处是它不仅书写了各区域地方的发展与变迁,更直接地影响到了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的每一个人。它构成你的生活环境,决定你的态度立场,塑造你的个性气质。随着时代的改变,外来文化的传入对本土文化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那绝不意味着本土文化的衰落。如何在危机中应对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审美趣味、价值观念的革新,是本土文化急需解决的问题。新媒体的产生正顺应了这个迫切的需要,有力地推动了本土文化的传播。尽管信息失真、可控性差、商业性强等问题常常使得新媒体受人诟病,然而不容置疑的是,它的确衍生出新的人际交往方式,建立起新的社会组织结构,在给予人们更多自由的同时,也引发了价值观念的变革。“媒介是人的延伸”[11],新媒体的发展也促成了现代人的发展,开启了本土文化传播的新篇章。
[1]郑金洲.教育文化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3.
[2]邵培仁.传播学[M].北京:高教出版社,2000:96.
[3]黎筝.论本土文化教育在大学生世界观培养中的优势[J].贵州师范学院学报,2015(12):76.
[4][美]尼古拉·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M].胡泳,范海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
[5][美]理查德·A·斯皮内洛.世纪道德——信息技术的伦理方面[M].刘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1.
[6][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美]维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M].陈亮,周立方,李启,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45.
[8][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M].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300.
[9]廖新媛,陈敦旭.从六度分离理论看网络深度营销价值[J].商业研究,2009(07):11.
[10][美]A.H.马斯洛.动机与人格[M].许金声,程朝翔,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29.
[11][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4.
[责任编辑:袁向芬]
On the Propagation Effect of New Media on Local Culture ——A Case Study of the Culture in Guizhou
LI Zhe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550001)
The inheritance and dissemination of culture are inseparable. In human history, each update of media provided an opportunity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culture. Compared with the mainstream of traditional culture, local culture tend to be marginalized because of its regional restrictions. Meanwhile the introduction of extraneous culture made some impact on local culture. However, this never means the inevitable decline of local culture.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helps to promote local culture effectively. It created a favorable media environment to local culture, and produced a large number of transmission effects, and brought about better communication advantages as well.
New Media; Local Culture; Propagation Effect
2016-09-09
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新媒体发展趋势下贵州本土文化资源的教育功能研究”(项目编号:2016ZC079)的研究成果。
黎 筝(1981-),女,汉族,贵州贵阳人,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文化研究。
G206
A
1674-7798(2016)11-002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