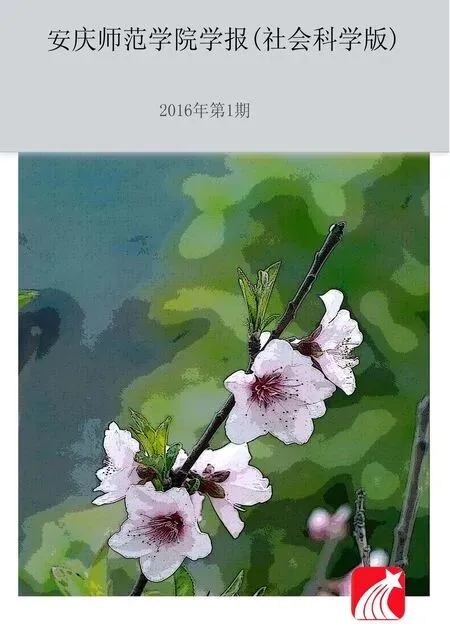《闲情赋》研究献疑
2016-03-18段梦云
段 梦 云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0)
《闲情赋》研究献疑
段 梦 云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芜湖241000)
摘要:《闲情赋》在陶渊明的作品中有着独特的审美意义,对于研究陶渊明丰富的精神世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从而为历代研究者所关注。然而关于此赋的主旨、题材以及创作时间则歧异纷纭。如果综合考察历代学者关于文本的评论、闲情题材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发展演变以及陶渊明的生平和创作,则可以看出,《闲情赋》的主旨既无意于闲情,也不关乎讽谏,只是一次有关爱情遐想的兴致之作;而它的创作时间则应当在陶渊明经历了人生沧桑之后的壮年时期。
关键词:陶渊明;《闲情赋》;创作主旨;写作时间
现存陶渊明作品中与爱情相关者,唯在《闲情》一赋,因此《闲情赋》不仅在陶作中具有独特的审美意义,而且对于研究陶渊明丰富的精神世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从而为历代研究者所关注。然而,关于此赋的创作主旨、题材划分、写作时间等相关问题,学界一直各持己见,聚讼无已。笔者在仔细研习了诸位先贤的研究结论之后,心中仍存有稍许疑问,故本文拟就对这三个问题的理解向先贤们献疑。
一、《闲情赋》主旨探微
陶渊明《闲情赋》究竟表达的是什么主旨,历来饱受争议。萧统《陶渊明集序》曰:“白璧微瑕者,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谏,何必摇其笔端。惜哉,无是可也。”[1]后来苏轼批评萧统说:“渊明《闲情赋》,正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与屈宋所陈何异?而统乃讥之,此乃小儿强作解事者。”[2]遂开后代聚讼的初端。依萧统所言,此赋乃表现爱情之“流宕”无疑。然苏轼拟之以《国风》之“好色而不淫”,或即认为是一首爱情赋,但他同时也认为其无异于“屈宋所陈”,开香草美人“寄寓说”之端。
明代张自烈认为:“此赋托寄深远,……或云此赋为眷怀故主作;或又云续之辈虽居庐山,每从州将游,渊明思同调之人而不可得,故托此以送怀。”[3]清人陈沆认为:“《闲情赋》,渊明之拟《离骚》。”[4]逐渐将《闲情赋》的主旨导向了政治理想的寄托。不过学界最广为认可的还是爱情说,如鲁迅先生《“题未定”草(六)》、曹道衡先生《汉魏六朝辞赋与骈文精品》、袁行霈先生《陶渊明的〈闲情赋〉与辞赋中的爱情闲情主题》等都力主此说。上世纪90年代初,顾竺在《关于陶渊明的闲情赋》一文中,将历代对此赋主题的解读大体归为政治理想说、守礼说和爱情说三类[5]。本世纪初,李世萍《〈闲情赋〉的情蕴和主旨探析》一文又明确提出了“悼念亡妻说”[6]。宋雪玲赞成李说,并认为:“他并没有以极度悲伤和凄惨的语言表达自己对妻子的怀念,而是以华丽的语言和铺排夸饰的风格相结合,以美轮美奂的方式表达了对亡妻的思念之情”,是一种理想化倾向的表现[7]17。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也有一定的文本依据。但如果我们进一步解读文本,能不能得到一种新的而且可能更为合理的解释呢?
首先,赋名“闲情”。《广雅·释诂》曰:“闲,正也。”钱钟书《管锥编》论《闲情赋》说:“‘闲情’之‘闲’即‘防闲’之‘闲’,显是《易》‘闲邪存诚’之‘闲’。”[8]也就是说“闲情”并非闲适之情,而是正邪之情。如王粲有《闲邪赋》,“闲邪”正与“闲情”意同。古人认为情生于爱,爱生于欲,不合礼仪道德规范,故应当发乎情止乎礼。由此可知“闲情”必然与爱情、礼教相关。
当然,解读《闲情赋》创作主旨的关键,还是在于作者的自序。其序曰:“初,张衡作《定情赋》,蔡邕作《静情赋》,检逸辞而宗澹泊,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缀文之士,奕代继作,并因触类,广其辞义。余园闾多暇,复染翰为之。虽文妙不足,庶不谬作者之意乎。”由此可知,《闲情赋》是一篇拟作,即模仿张衡《定情赋》、蔡邕《静情赋》及后代缀文之士而续作。陶渊明自认为“庶不谬作者之意”,那么要探究此赋之义,就不得不梳理一下历代缀文之士的创作内容和创作动机了。
张衡《定情赋》、蔡邕《静情赋》今都不见完篇,最早见于《艺文类聚》,或都经过了编选者的删节。从所存内容看,基本上都是描写美人,表现“荡以思虑”,而无“终归闲正”。《定情赋》描绘出一位华秀无双的美人,并咏叹着对美人愁肠百转的思念。《静情赋》也名《检逸赋》,除了描写美人容貌之丽,又加以“昼骋情以舒爱,夜托梦以交灵”,表达的情感更为逸荡而热烈。关于此二赋的创作宗旨,袁行霈先生曾说过:“从宋玉开始的爱情赋,一直在不断发展,到曹植手里已达到成熟的地步,……可是从东汉张衡开始,插进了另一种声音,以礼教之大防把爱情匡了起来”,“总算是符合了儒家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原则了。”[9]133不知袁先生是另据别本,还是根据《闲情赋》序所作的推断?因为从张衡的作品来看,即使是现存完整的《同声歌》、《四愁诗》似乎也很难找到“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影子。由此推想,《定情赋》也不一定是“以礼教之大防把爱情匡了起来”的。
建安时期,模仿这类作品的很多,甚至多人唱和、同作一题的现象相当普遍。如“赤壁之战次年,王粲、陈琳、应玚共同创作《神女赋》”,“曹丕作有《戒盈赋》,并命阮瑀与陈琳各作一篇《止欲赋》,王粲作《闲情赋》,应玚作《正情赋》,繁钦作《抑检赋》。曹植的《静思赋》大致也写于这个时期。”[10]这些作品都绝少礼教大防的意识,如陈琳《止欲赋》极力铺写美人“色曜春华”之容貌和“伊余情之是悦”的相思;曹植的《静思赋》除表现美人容貌艳冶之外,也表达了“愁惨惨以增伤,悲予安能乎淹流”的求之不得的哀伤;唯有阮瑀《止欲赋》结尾“知所思之不得,乃抑情以自信”能算得上是止乎礼义。而曹植《洛神赋》的确是一篇有寄托的作品,爱情只是理想寄托的对象而已,与此类赋作其实是大不相同的。
概括地说,从宋玉开始,经过张衡、蔡邕的发展,一直到建安前期,在不同时代的模拟和流变过程中,这类赋已经形成了较为固定的模式。在酬唱模拟之中,闲情和讽谏之意是相当淡漠的。防闲情思未必是作者心中真正的主张,而扬诗守礼亦未必是他们写作的主观目的。以一种近乎游戏的笔调描写男人内心对美人的渴望,却是这类赋的基本特点。对其表达的主旨不必人为地加以拔高,陶渊明《闲情赋》亦是如此。所以,陶渊明《闲情赋》更有可能是他在园闾多暇之时,因阅览奕代缀文之士的此类作品,故拟和而为之,并在写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触及和融入了自己的某些情愫,实乃兴致之作,本无意于闲情,亦不关乎讽谏,仅是用文字再现了思绪中一次对爱情的遐想罢了。序所说的“终归闲正”、“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仅仅是文人鉴于礼教的罗网,带上一点面具,虚晃一招而已。岂可信哉!
二、爱情与闲情之分
《闲情赋》是否属于爱情类作品?袁行霈先生《陶渊明的〈闲情赋〉与辞赋中的爱情闲情主题》一文及《陶渊明笺注》中对《闲情赋》之笺注提出了深刻而独到的见解。袁先生在文中系统考察了历代关于《闲情赋》主题的各种重要说法,并予以总结性评说;且区分了“爱情赋”和“闲情赋”之异同,并对二者的源流进行了详细论说,从而确立了此赋的“闲情”主题。袁先生的研究可谓采诸说之所长,集众家之大成,令人如沐春风,受益良多。然而对爱情与闲情之分,笔者尚有一些疑问。
袁先生在论文中说:“爱情与闲情在辞赋中是先后出现的两种主题。……真正以爱情为主题的赋,应当从宋玉这三篇(指《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开始。……继承宋玉的三篇赋,还有另一个分支就是闲情。爱情赋虽然多数以不得交接结束,但双方毕竟发生了爱情,爱情不是自己压抑下去的。闲情则不然,有爱的发生,甚至发展到了不可遏止的地步,但还是压抑下去了。这往往是男方的单相思,就好像《洛神赋》写了一半,写怀疑能否得到洛神对爱的回报便把自己的爱强制地压下去了,文章也就到此打住。《洛神赋》的中段不是有这样两句话吗:‘收和颜而静志兮,申礼防以自持’。这两句话正好可以概括这类赋的主题。”[9]112概括袁先生的意思有四点:第一,情赋划分为爱情和闲情两个分支。第二,爱情赋始于宋玉三赋,而闲情赋则是爱情赋发展过程中流变出来的另一个分支。第三,在爱情赋中,双方发生了双向的爱情;在闲情赋中,虽有爱的发生,但往往是男方的单相思。第四,爱情赋虽多数以不得交接结束,但爱情不是自己压抑下去的,乃是由于外在因素而被迫压抑下去;然闲情赋则是主观上以礼义为大防而将爱压抑了下去,如曹植《洛神赋》。
在这篇文章中,袁先生还将宋玉三赋、司马相如《美人赋》、杨修《神女赋》、蔡邕《协和婚赋》和《青衣赋》、陈琳《神女赋》、应玚《神女赋》、徐干《嘉梦赋》(一作《喜梦赋》)、曹植《洛神赋》及张敏《神女赋》归入爱情赋类。张衡《定情赋》、蔡邕《静情赋》(又作《检逸赋》)、王粲《闲邪赋》和《神女赋》、应玚《正情赋》、陈琳《止欲赋》、阮瑀《止欲赋》、曹植《静思赋》、阮籍《清思赋》、张华《永怀赋》、傅玄《矫情赋》、袁淑《正情赋》及陶渊明《闲情赋》则归入闲情一类。“曹植的《洛神赋》是这类赋中的翘楚,其序文明言‘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可见属于《高唐赋》的系列。”[9]112袁先生在分类时明确将《洛神赋》分入爱情赋一类。然而按照前文所引袁先生的具体论述,似乎又是将《洛神赋》划为闲情赋一类。那么曹植此赋究竟是属于爱情赋还是闲情赋?袁先生对闲情赋的界定和举例是不是有些矛盾呢?
袁先生把《高唐赋》、《神女赋》划归爱情主题,这当然没有疑义。然而将《登徒子好色赋》也归入爱情类就有点难以理解了。《登徒子好色赋》写了登徒子、宋玉及章华大夫三人对待“色”的态度。登徒子妻貌极丑,而登徒子悦之,生有五子;东家之子极美,且属意于宋玉,宋玉却不为所动;章华大夫途遇采桑美女,心有感动,但因恪守礼义而“终不过差”。从文本看,宋玉举登徒子悦其丑妻之“好色”,是为了衬托自己面对貌美的东家之子的挑逗而不为心动。通过夸饰和对比,证实自己乃正人君子,从而打破登徒子攻击他“性好色”的谗言。二者皆非表现爱情。章华大夫对采桑女心有所感,“于是处子恍若有望而不来,忽若有来而不见。意密体疏,俯仰异观,含喜微笑,窃视流眄”,却终是以礼自持,故“迁延而辞避”。然而采桑女是否果真对章华大夫亦萌发了爱情,却并不能确定,章华大夫的“扬诗守礼”则更近于求偶受挫后的自宽自慰,即使从爱情的角度说,也并未发生双向的爱情。更何况文章主旨乃在于阐释“目欲其颜,心顾其义,扬诗守礼,终不过差”,即面对女色时如何以“礼”制“欲”的道德规范问题。司马相如《美人赋》有着明显的模仿《登徒子好色赋》的痕迹。赋中东邻之女和上宫之女的美艳与主动,也不过是反衬男主人公脉定心正之德操的道具,亦难以爱情赋视之。如果按照袁先生对爱情、闲情主题的界定,则此二赋归入闲情赋一类似乎更为妥当。
张华《永怀赋》云:“既惠余以至欢,又结我以同心。交恩好之款固,接情爱之分深。誓中诚于皦日,要执契以断金。”足见男女双方曾经产生过真挚而炽烈的爱情。然而为“天道幽昧,差错缪于参差”,爱情失却的原因是天时的阴错阳差,却绝不是因守礼以闲止。“天道幽昧”、“禄运不遭”的嗟叹呼号而出,男子心中的惋惜、痛苦和无奈几欲喷薄。在此基调下,“长收欢与永已”的决心也显得苍白无力,倒更像是爱情破灭之后故作旷达的自我安慰。依据袁先生的界定,则此赋似又应归入爱情赋一类。
在袁先生所列举的爱情赋中,除前文已作探讨的《登徒子好色赋》、《美人赋》,以及应玚《神女赋》、徐干《嘉梦赋》仅存残篇,结局不可考知外,爱情双方终以“心悦怿而未交接”作结的作品,只有宋玉《神女赋》和曹植《洛神赋》。《神女赋》中双方以动情始,以止情终。神女动之以情,而约之以礼。这种表现似乎又超出了袁先生对爱情、闲情的划分。《洛神赋》中,情感的表白使男女双方心意相通、指渊为期。然而此时,男子却因“执眷眷之欵实兮”而“惧斯灵之我欺”,由“感交甫之弃言兮”而“怅犹豫而狐疑”,于是他“收和颜而静志兮,申礼防以自持”。洛神感受到他的变化而决定离去,爱情因此转向失败。曹植接着以大段的笔墨渲染了洛神的徙倚彷徨、转眄难舍和男子的怅惋流涕、悔恨莫及。究其全篇,确系爱情之赋。但男子心中的静志之思毕竟是使爱情走向终结的根由。这里描写的爱情恰恰“是自己压抑下去的”,按先生的意思似乎又不能列为爱情赋。
在袁先生所列的闲情赋中,阮籍《清思赋》是描写玄思的作品,无论是从内容上、思想上还是形式上都与其他爱情赋或闲情赋有着明显的不同,故暂且不论。其他作品内容多有亡佚,得以留存的唯有王粲《神女赋》、张华《永怀赋》和陶渊明《闲情赋》三篇。《永怀赋》前文已论。王粲《神女赋》和陶渊明《闲情赋》的写作皆遵循“颂扬女子之美——表现思慕之情——未曾展开追求而回意以自绝”的模式而来。赋中皆以大量的笔墨渲染女子的美貌,并倾吐了对女子难耐的爱慕之心。虽皆在卒章称诗言志、以礼防情,但相思之情的酸苦、内心斗争的激烈及心中的遗憾与怅惘却溢于纸面。其他作品虽无法得其全貌,但从残留的文本看,或有倾慕美人之意,或现相思煎熬之苦,或存爱情无望之悲,比比皆是。虽然赋这一文体难免铺排和夸饰,但在这些难销的浓情之后,那些篇末方仓促上演的闲情之语则显得绵软无力,倒更像畏于追求爱情或追求爱情无望后的故作清高。而这类赋的主旨也绝非“闲情”二字足以囊括的。
既然“闲情赋”中的闲情之语往往淡化成渲染爱情之余的小小旁白,而以礼防情又往往成为“爱情赋”中爱情失败的缘由,依笔者浅见,情赋主题之爱情与闲情实在难以明确分离,或者可以不必强分。爱情的发生固然诱发于人的生物本能,但又总是受到深层文化心理的影响,而包涵着“闲情”的成分。所以在古代中国,即便是一个世风开放的时代,文人敢于描写放纵的情欲,也多少会拉着一点礼教的幌子以遮掩真实的内心世界,就连素以色情文学著称的《金瓶梅》也不例外。
三、《闲情赋》的写作年限
关于《闲情赋》的写作时间,历代学者也是众说纷纭,至今仍然未形成统一的结论。
王瑶先生认为:“《闲情赋》大概就是少年时的示志之作。渊明于晋太元十九年甲午(394)丧偶,见《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诗》注;《闲情赋》是抒情文字,或即这年所作。时渊明年三十岁。”[11]483古人二十弱冠,即为成年。王先生前文断言辞赋乃渊明“少年时的示志之作”,后文却强调作于而立之年的丧偶之后。在那个时代,而立之年应该难以算是少年了,所以袁先生的观点前后相互抵触了。因《易》大过卦解“枯杨生稊”为“老夫得女妻”,而陈琳《止欲赋》中有“忽日月之徐迈,庶枯杨之生稊”之句,故林晓光先生推测与《止欲赋》同一谱系的《闲情赋》等“并不是在泛泛表达追求异性以及求之不得的哀愁,而是在描写老年男子对少女的爱慕。”[12]212而认为此赋作于陶渊明老年时期。然而,以笔者浅见,即便陈琳《止欲赋》所表现的的确是“一个老人在爱慕追求美貌的少女”,恐怕也难以因此确保这一谱系下的其他作品也具有这一内涵。袁行霈先生则认为“此赋写爱情之流荡,又序曰‘余园闾多暇’,可见乃渊明少壮闲居时所作。姑系于晋海西公太和五年庚午(370),渊明十九岁。”[13]从袁先生的叙述来看,先生似乎亦不确定此赋即陶渊明十九岁之作,故用“姑系于晋海西公太和五年庚午,渊明十九岁”之语。
《闲情赋》的写作时间,既无可靠的史料记载,也无明确的作品内证,所有结论都是基于《闲情赋》文本和陶渊明生平的推断,诸位先生的推理都可备一说。但无论如何,考察此赋的创作时间,都必须观照到两点:第一,“爱情之流荡”是否只出自于少年之手;第二,陶渊明之“余园闾多暇”最可能在何时?
首先,“爱情之流荡”并非只有年少才可能产生,摹写和表现“爱情之流荡”的作品也绝非只可能出自少年之手。如曹植三十余岁作《洛神赋》,王粲更是四十岁而作《神女赋》[14],成熟的年龄丝毫没有影响二人赋中相思之情的动人心扉。故虽然“此赋写爱情之流荡”,却远不足以将它的写作时间限定在少年之时,或十九岁之际。其次,陶渊明外仕的时间较散且都短,居于园闾的时间则较多。据袁行霈先生考证,陶渊明一生五仕五隐[9]67,且几次仕宦时间皆不长,大部分时间都是居于园闾。所以《闲情赋》的写作未必就在初仕之前,更未必就在少年时期或十九岁之际。再次,从陶渊明的自序看来,“园闾多暇”并非指闲居乡园,而是说躬耕田园、多有闲暇之时,故“复染翰为之”。在园闾多暇之际进行写作,陶渊明俨然已将园闾之事、耕种自资作为人生的第一事业了。这种口吻显然不可能出自十九岁的少年之口。从陶渊明晚年追忆少壮时所作的诗歌看,少壮时的他虽说是“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但“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少时壮且厉”(《拟古》其八),“丈夫志四海”(《杂诗》其四),踌躇满志和意气风发,才是其少年人生的主调。而且据袁先生考证,陶渊明二十岁时逢“家道中衰,经济状况大不如前”[9]270,即所谓“弱年逢家乏”(《有会而作》)。由此,陶渊明为谋求生路而开始了长达九年的游宦学仕生活,直到二十九岁时方为官府正式征聘,起为祭酒[9]275。陶渊明的这段经历也证明,在他少壮时,不仅心怀猛志,并且为之做出过相当的努力。由此推知,十九岁的他,且无田园之志,也无躬耕之任,纵然“性本爱丘山”,也未必能如此志于园闾而安享多暇罢!
另外,从赋的内容看,首先细细体味“悼当年之晚暮,恨兹岁之欲殚”一句,可推知此赋应该是作者的追忆之作。“当年”袁先生训作“壮年”。古时男子二十弱冠,方为成年。十九岁仍未成年,尚且不能算作“壮年”,则更不可能称之为“当年之晚暮”了。这句话前半句为伤逝,悲慨青春不在;后半句乃惜今,痛感时不可追,表现出茫茫的若失之怅,透露出强烈的生命意识。而赋中“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长勤”、“同一尽于百年,何欢寡而愁殷”、“敛轻裾以复路,瞻夕阳而流叹”、“行云逝而无语,时奄冉而就过”等句,也都表现出了对生命流逝的感慨和无奈,心思殷愁沉重,风格哀婉凄切。再者,诗人“十愿”所表达的“爱情之流荡”,似乎充满了青春的理想与激情,然而作者情感抒发的重心却在“十悲”上。抒情主人公希望成为心上人的贴身之物,亲密地陪伴和呵护着她,但是每一个物件最终都逃脱不掉被委弃和替换的命运,从而使诗人热烈的想象转化为不尽的哀伤。前九种事物因时间转移、节令变化等客观原因而被替换,后一种则因女子主观情绪的乐极生悲而受到冷落。万物有时,不变而变,“十悲”所表现的是自然而然的“无事的悲剧”,表达出兴至已悲来、物盛则衰生、“所愿而必违”的人生空寻之叹,情绪悲观而怆然。试想,少年时期正是对爱情和婚姻充满希望和期待的年龄,纵使羞于追求爱情,或苦于相思受挫,亦未必会产生如此沧桑的迟暮之慨和浓郁的生命之悲。而赋中的细微体察、深刻思考与惨淡经营,也绝非一个尚未经历家道衰颓和世事磨难的少年,所能产生的生命体认。
《闲情赋》又有“鸟凄声以孤归,兽索偶而不还”、“徒勤思以自悲,终阻山而滞河”等句,表达孤独无伴之凄、山河阻隔之悲,其哀之切,情不自胜。所以有学者认为此赋乃悼念亡妻之作。钟优民先生《陶渊明论集》认为:“王瑶先生假定本赋作于渊明丧偶的太元十九年,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同时又主张“不应因为是写在丧妻之后,而设想它是悼亡之作了”[15]。即认为此赋作于陶渊明丧偶之后,但并非悼亡之作。此说甚是。渊明诗曰:“始室丧其偏”,知其丧妻在三十岁许。袁先生考证渊明丧妻在三十岁为公元381年[9]295。王瑶先生认为在公元394年[11]483。虽然所考证的时间相差很大,但是由此却可推知,此赋作于陶渊明三十岁之后,或当无疑问。然具体时间已不可考。
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说:“常著文章自娱。”《饮酒诗序》也说:“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他的文学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自娱自乐。因此,当园闾多暇的诗人翻检出异代缀文之士的遥和之作,兴致倏起,摇其笔端,不仅与前辈们进行了一场萧条的心灵沟通,也为自己创造了一场盛大的关乎爱情的美好遐想。
参考文献:
[1]逯钦立.陶渊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10.
[2]苏轼.苏轼文集[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1092.
[3]张自烈.笺注陶渊明集[M].明崇祯刻本.
[4]陈沆.诗比与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78.
[5]顾竺.关于陶渊明的闲情赋[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0(6).
[6]李世萍.《闲情赋》的情蕴和主旨探析[J].贵州社会科学,2006(6).
[7]宋雪玲.《闲情赋》的主题和陶渊明诗文的理想化倾向[J].九江学院学报,2011(2).
[8]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三联书店,2001:1220.
[9]袁行霈.陶渊明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0]赵西尧,马宝记.三国文化概览[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158.
[11]王瑶.王瑶文集 第1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
[12]林晓光.《闲情赋》谱系的文献还原——基于中世文献构造与文体性的综合研究[J].文学评论, 2014(5).
[13]袁行霈.陶渊明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3:452.
[14]王粲.王粲集[M].俞绍初.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80:109.
[15]钟优民.陶渊明论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98.
责任编校:汪长林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730(2016)01-0020-05
DOI:10.13757/j.cnki.cn34-1045/c.2016.01.005
作者简介:段梦云,女,江苏溧阳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4-11-06
网络出版时间:2016-03-09 13:49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34.1045.C.20160309.1349.00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