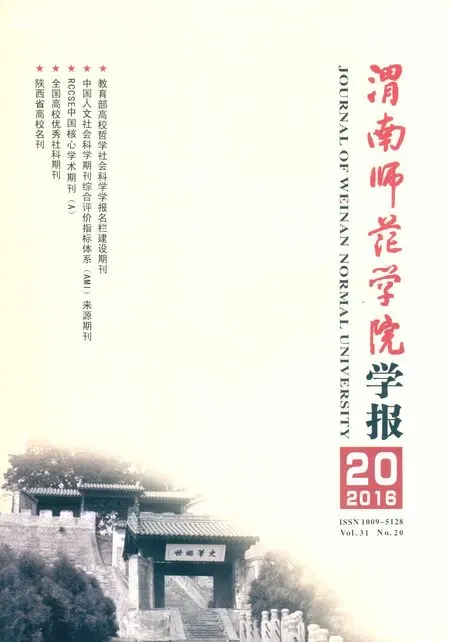在记忆与叙事中寻求生命的意义——论朱利安·巴恩斯的小说
2016-03-17原金利
原 金 利
(渭南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语言文化与文学研究】
在记忆与叙事中寻求生命的意义
——论朱利安·巴恩斯的小说
原 金 利
(渭南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朱利安·巴恩斯擅长用多种写作技巧进行创作,记忆和叙事是作者常用的创作方式。记忆往往是不可靠的,叙事在小说中往往是虚构的。因此,巴恩斯的小说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是虚实结合,亲切自然,诙谐当中不乏深刻的哲理。文章通过分析巴恩斯的多部作品,希望读者从中既能感受到灵活多变的写作风格,也能体会到蕴含其中的深意。
记忆;叙事;自我身份;婚姻;死亡
记忆是人类最重要的生存能力之一,没有了记忆,人类就一直生活在蒙昧与混沌之中。《辞海》对“记忆”的解释是“人脑对经验过的事物的识记、保持、再现或再认”。作为人类最基本的心理过程,记忆是和其他心理活动有着密切联系。比如在知觉中,记忆的参与对人的过去经验产生重要作用,使人能够分辨或确认周围的事物及环境。通过记忆提供的知识经验,可以极大地帮助人类解决复杂的问题。记忆对作家来说,其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的。作家被称作“记忆生产者”,其创作过程离不开记忆对其作品的建构和塑成。作家的记忆可谓是一种对生活的体验,既是对过往生活的追忆,也是对未来生活的憧憬,最终汇聚成其创作的内在动力和经验源泉。
叙事形式主要由纪实叙事和虚构叙事构成。前者是以实录的方式传达真实发生的事情;后者则以虚构想象的途径创造有别于实际发生的故事或者完全没有发生的事件。表现在具体的文本形式上,前者主要指的是历史、传记、自传、回忆录或新闻报道;后者则主要包括小说、戏剧、电影及电视剧本等。小说是以刻画人物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具体的环境描写来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体裁。小说中的典型人物是作者根据现实生活创造出来的,并非基于真人真事,而是综合了生活中的种种人物类型提炼出来的,通过这些典型的人物形象能够更加集中,更加普遍地反映真实的社会生活。小说通过故事情节反映人物性格,表现中心思想。故事来源于生活,小说通过对故事情节的创作、提炼和安排,使得作品比现实生活更加深刻、完整而具有代表性。小说的环境描写包括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两方面,社会环境的描写主要反映当时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历史背景;自然环境的描写主要是为了刻画人物的内心活动或衬托和渲染当时的气氛。因此,小说的整个创作过程都可以说是虚构叙事的过程。
大部分小说都是对过往的叙事,这必然少不了记忆的功能。记忆是不确定的、不牢固的,依靠记忆进行的叙事当然都是虚构的了。作家在创作小说时,依靠记忆提供丰富的素材,通过虚构叙事建构文本。因此,记忆与虚构叙事形成互文的关系,贯穿整个创作过程。[1]49-52
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1946—),是英国当代著名的作家和评论家,他的创作艺术和美学思想代表了当今英国小说的发展方向。其作品具有大胆的创新性、实验性和浓厚的历史与人文主义关怀。自从2011年获得象征英语语言小说的最高奖——布克奖以来,其作品越来越受到国内外读者欢迎,更多的评论家和文学爱好者对其作品的分析和研究也正如火如荼。
巴恩斯的小说大多具有半自传体的特征,小说的创作与自身的经历有密切的关联。所以,小说里的人物描写和情节设置通过小说中人物的记忆及叙事展现在读者的面前,虚实结合,亦真亦假,揭示着生命的意义。人的生命在时间的长河里只是短暂的一段漂流,随着年岁的增长,渐渐会思考自己的人生及功过是非。巴恩斯的小说贴近普通人的生活,通过个人的记忆和叙事体现了具有日常生活价值的个人历史和哲理。因此,每部小说的发表会立刻引起公众的关注和认可。小说的字里行间不乏作家的亲身经历和感悟,引领读者如何在平凡的生活中寻找自我身份;如何在感情或婚姻生活中理解爱的本质;以及在知天命时如何面对衰老和死亡。在某种意义上,作家试图通过小说创作帮助人们度过生命中不同阶段的生存危机,运用记忆和叙事的方式将个人从危机中得到救赎,启发人们洞见生命的意义之所在[2]43。
一、在平庸生活中寻求自我身份
巴恩斯的处女作《伦敦郊区》(Metroland)发表于1980年,具有较强的自传性,巴恩斯正是通过这部小说成就了长久以来寻求的作家身份。作者对小说里主人公克里斯的刻画以及故事情节的安排与其本人的经历极其相似,两人都是从小生活在伦敦郊区,在那儿上学,大学都主修的是现代语言文学专业,都因迷恋法国文化而去法国学习生活了一段时间,职业上都曾是编辑和评论员,结婚后又都搬至伦敦郊区,平凡的生活虽小康稳定但缺乏个人身份的被认同。那时的巴恩斯不甘于长期从事编辑或评论员的工作,于是根据自身的经历,借助第一人称克里斯的记忆和叙事帮助主人公实现了成为驻地作家的生活理想。小说一经发表就大获全胜,并获得了毛姆文学奖,作者同时凭借这部小说确立了一直渴求的作家身份。
2011年,巴恩斯凭借小说《终结的感觉》(The Sense of an Ending)第三次入围代表英语语言文学最具权威的奖项——布克奖,并最终折桂。同年,他还荣获大卫·科恩终生文学成就奖以及其他奖项。可以说,《终结的感觉》这部小说再次证明了巴恩斯的艺术才华和创作成就,确立了他在英国文学甚至世界文学中的显要位置。2008年,巴恩斯的爱妻帕特·卡瓦纳(Pat Kavanagh)不幸去世。其妻生前是著名的文学代理商,对巴恩斯的创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妻子离世后,作者悲痛万分,失去生活的勇气,失去了创作的热情,渐渐在文坛上沉寂。后来,作者感觉到妻子其实并没有离开自己,好像一直陪伴着他,于是每天独自与她进行对话,慢慢走出了悲伤情绪的阴霾,滋生了创作的灵感。
在创作长篇小说《终结的感觉》时,巴恩斯带着丧妻之痛,进入了孤独的老年时期,不由自主地思考个人的历史。此时,作者试图通过小说的创作,摆脱独自终老的生存困境,重构个体的自我身份,重新找寻生命的意义。小说以第一人称托尼的记忆和叙事为线索,与作者的老年经历极其相似的情节设置,再次寻找自我身份,评论个人历史,认知生活。托尼同样生活在伦敦郊区,在那儿上学,大学选择了稍有兴趣的历史专业,毕业后同大多数人一样从事着相关专业的工作,结婚生子,贷款买房买车,妻子后来忍受不了平淡无奇的日子和庸庸碌碌的托尼,选择离婚。从此,托尼过上了自我感觉不错的老年生活,尽管与前妻离婚,但是两人依旧正常往来,关系似乎更为融洽,女儿长大成人并已为人妻母。退休后,经济上有丰厚薪资的保障,生活上有三五酒友和柏拉图式关系的女性朋友的陪伴,为了熟悉以后避免不了要适应医院的环境,志愿做了当地医院图书室管理员的工作。巴恩斯借托尼的晚年生活质疑自己及大多数人的这种生活方式,是不是应该这样平淡,毫无理想、庸庸碌碌地就此一生。作者的答案毫无疑问是否定的,于是借小说里另一正面人物安德里安之口愤怒地谴责道:“我痛恨英国人对于应该严肃的事情一点都不严肃。我真的痛恨极了。”[3]42作者在创作小说的过程中,意识到自己不能就这样让生活得过且过,要坚持自己的文学理想,认真严肃地对待独自终老的日子。小说中的托尼后来意外收到年轻时女友罗维妮卡母亲的小额遗产馈赠和随附的信件,但是部分重要信件仍被前女友保留着,为了索回本该属于自己的东西,托尼想尽一切办法,运用各种手段。“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彬彬有礼、坚持不懈、乏味而友好:换句话说,撒谎扯淡。”[3]108罗维妮卡终被托尼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纠缠所惹恼,先后返还他部分安德里安日记的影印件,还有托尼年轻时写给安德里安的一封信的复印件。打开这封信时,托尼也惊讶于当初自己信中内容的恶毒,语言的粗俗。他无法接受年轻时的自己,愧对昔日的朋友和恋人。托尼开始打探并关注罗维妮卡的生活状况,希望弥补以前的过失,求得良心上的安慰。然而,越是接近罗维妮卡本人的生活,越是感到内心的不安和惶恐,渐渐明白年轻时恋爱失败的原因,妻子与他离婚的根源,以及自己之所以这样平庸而自以为是的根本是从来没有认真对待一生中遇到的人和事,一味地谴责命运或他人,而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价值和应当承担的社会身份。
巴恩斯通过批判像托尼这样的英国人的失败人生警醒自己以及平庸的芸芸大众。作者可不希望自己像托尼那样孤独终老时才恍然大悟,追悔莫及。他认为普通人也应该活得有价值,体现出自己的社会身份,追求自己有意义的人生。在妻子死后,巴恩斯通过坚持与妻子的对话,坚定了生活的信息,总结了人生经验,并通过创作出《终结的感觉》这部力作,重新建构了自己的作家身份,追求人生的美好前景。
《伦敦郊区》和《终结的感觉》都是建立在作家的个人经历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的。后者可以说是前者的续集,前者主要反映了成家立业后,作者不甘于从事收入稳定的平凡工作,向往于能够实现人生价值,体现自我身份的职业目标;后者则评判那些一生平平,甘愿接受命运的摆布的人,总以受害者的身份为自己平淡的人生找借口,随波逐流,从来没有认真审视过自己,没有勇气承担作为个人应有的社会职责和身份,更不懂得思考生命的真正意义。随着《终结的感觉》给巴恩斯带来的无数奖项和荣誉,增强了他本人作为有实力作家的信心,为他日后的创作增添了动力。在2013年出版的《生命的层级》中,巴恩斯直接讲述自己如何从丧妻之痛中走出,他坦言妻子为“ 我生命的核心,我核心的生命”[4]68。 “ 我在一举一动中想她, 我在一动不动中也想她。”[4]81作者勇敢地正视现实生活,重新走上了创作之路。《终结的感觉》和《生命的层级》几乎是作家同时提笔创作的,通过这两部作品的创作,巴恩斯一边疗伤,一边思考人生,更加明确了自我身份和存在的意义,使得这两部小说有力见证了巴恩斯当之无愧位列于英国顶级的作家之一,是巴恩斯“用文字取代白色大理石为妻子铸就的泰姬陵”[5]74。
二、在平淡的婚姻生活中理解爱的本质
爱是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没有了爱,生活将没有了色彩,变得枯燥而乏味。这里所说的爱,并不仅仅指的是爱情,还包括亲情,友情,关爱之情,包容之情等充满正能量,有温暖,有道德,有人性,符合对真、善、美传统价值追求的所有情感。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在《爱的多重奏》里这样阐述:“爱是从某种相遇开始的。这种相遇,我以一种形而上学的方式,赋予一种事件的地位,也就是说无法进入事物的直接规则的某种事物……爱不再是相遇的两个个体之间的封闭关系,而是一种建构,一种生成着的生命。”[6]60-61
巴恩斯的多部作品中,充斥着一方对另一方在恋爱或婚姻关系中情感背叛的恐惧之情。这也是现代人生活当中经常遇到的感情危机,作者通过小说的创作,其中也不乏对私人生活的记忆和叙事,指出在消解情感方面的生存危机时的两种选择:是通过复仇的手段还是采取宽容的态度。
《她遇我前》(Before She Met Me,1982)是巴恩斯的第二部小说。该小说讲述的是名叫格雷厄姆·亨德里克结束了第一段失败的婚姻之后,娶了位名叫安·米尔斯的女演员。由于在年龄上的差异导致两人沟通上存在障碍,男主人公出自对第二次婚姻的珍惜和对妻子的爱,整日担心妻子会在感情上背叛自己,想象着妻子之前当演员时如何与男演员们偷欢。格雷厄姆被无名的嫉妒情绪扭曲了心智,开始对曾与妻子有关系的男人们一一展开秘密调查。好友杰克是写小说的,格雷厄姆通过阅读他的一部小说的过程中,推测出他曾经是妻子的情人并且两人仍然保持着不正当的关系。当所有的猜测最后得到证实,格雷厄姆恼羞成怒,像被恶魔控制了一样杀死了好友杰克,然后当着妻子的面自杀。
《她遇我前》的男主人公格雷厄姆选择用复仇的手段杀死了感情上欺骗过自己的好友杰克,消灭了感情上敌人的同时也毁灭了自己的生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历史老师的格雷厄姆错将虚构猜测的问题当成真实的历史事件去追根问底,忽略了现实婚姻生活里爱的意义,舍本逐末,自作苦吃。如果格雷厄姆能够冰释前嫌,大度地接受自己的妻子并努力经营他们的婚姻生活,也许不会担心妻子不爱自己,更不可能会背叛自己,那么故事的发展会是另外一个全新的结局。
《福楼拜的鹦鹉》(Flaubert’s Parrot)发表于1984年,是巴恩斯的第三部小说。小说的主人公布瑞斯维特,是位退休的外科医生,通过追寻研究法国作家福楼拜的传记,试图探寻亡妻艾伦为何要像《包法利夫人》里的女主人公艾玛那样,生前多次在感情上背叛他,然后因绝望而自杀的缘由。布瑞斯维特一次到法国鲁昂旅行期间,发现两家纪念福楼拜的博物馆分别陈列着一只剥制鹦鹉标本,均声称是福楼拜作品《纯朴的心》里名叫露露的鹦鹉的原型。为了探查清楚哪只鹦鹉才是传说中的露露,主人公对福楼拜的生平故事及作品产生浓厚的兴趣。在研究评论福楼拜本人及其作品的同时,布瑞斯维特无意间会提到自己的妻子,“我的妻子……已经去世。孩子们分散各处。 他们实在感到内疚才会偶尔来封信。 他们也有自己的生活”[7]3。但是每次都是遮遮掩掩,断断续续,令人扑朔迷离。有时,布瑞斯维特对妻子的评价是前后矛盾的,“我那时爱她,我们是快乐的;我想念她。她没爱过我;我们不曾快乐;我想念她”[7]180-183,“我们幸福,我们不幸福,我们相当幸福”[7]186-187。主人公似乎对妻子要做出客观公正的评说很纠结,陷入异常的困惑和苦恼之中。读者对他们的夫妻关系更是感到云雾缭绕,不置可否,无法言说妻子生前他们的婚姻关系到底有没有情感的维系。
布瑞斯维特为了摆脱退休后作为鳏夫的孤独生活,在百无聊赖当中把对福楼拜的研究作为自己的业余爱好。同时通过研究,试图找出妻子对婚姻产生不满,进而感情出轨,最终自杀的源头。主人公之所以对福楼拜的鹦鹉感兴趣,因为那只鹦鹉就像自己的妻子,令他感到神秘而不确定。通过阅读福楼拜的小说《淳朴的心》,布瑞斯维特认为妻子就像女仆全福那样,任劳任怨,对孩子无微不至,尽到了做妻子的职责。鹦鹉“露露”成为全福最后的精神寄托,但是他的妻子的精神寄托是什么,作为丈夫,他无从知晓。所以,他搜索所有的资料,恳请专家帮忙鉴定,希望找到那只真正曾是全福精神寄托的鹦鹉。结果非常渺茫,因为与小说当中描述相同的鹦鹉有五十只,真正的那只鹦鹉或许就在其中,或许早已送至他处,或许早已腐烂。答案是不确定的,或许是不存在的,仿佛对妻子的认知一样模糊,这就是布瑞斯维特每次提到妻子时,闪烁其词的苦衷了。后来,主人公将研究的重点转移到福楼拜的代表作《包法利夫人》,觉得自己就像小说中的夏尔·包法利,妻子背着丈夫与别的男人相好,作为丈夫虽然在某些方面很无能,但也不能成为妻子出轨的理由。布瑞斯维特知道自己当然比夏尔·包法利幸运,至少自己的妻子爱伦还是比较顾家的,也没像包法利夫人那样死后留给丈夫厚厚的账单。因此,在妻子死后,布瑞斯维特还是很悲伤的,认识到自己一直还爱着她,想念着她,并且对妻子生前的出格行为采取宽容的态度。
《她遇我前》和《福楼拜的鹦鹉》分别都牵涉到了婚姻关系中感情出轨的家庭问题。前者是作为丈夫的格雷厄姆在中年时遇到婚姻上的感情危机,尽管很爱自己的妻子,但是对妻子的婚前行为疑神疑鬼,并且鬼使神差地对其所有荧前幕后的男人进行侦查,结果正中下怀,在失去理智的情况下,杀死了情敌的同时也将自己逼上了不归路。所以,以复仇的暴力手段解决婚姻问题是不可取的,爱首先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之上,需要不断地呵护和付出才会变得深厚而经得起考验。后者的故事叙述者布瑞斯维特对于妻子起初不愿提起,但是又不由自主地会提及,表现出对于妻子的评价褒贬不定,自相矛盾。一方面,主人公承认妻子为人善良,尽职尽责,另一方面,也承认自己懦弱无能,满足不了妻子的期望。但是,无论如何不能理解妻子会在感情上背叛自己,并且会对婚姻生活感到绝望而自杀,这给布瑞斯维特留下无尽的苦恼和极大的内在创伤。为了解开这团团迷雾,主人公对研究福楼拜生平和作品产生浓厚的兴趣,试图因此会帮助自己找到问题的出路。遗憾的是,有些问题就像要寻找真正的福楼拜的鹦鹉那样不确定或者没有答案。但是这个研究过程也是自省的过程,布瑞斯维特意识到其实自己一直还爱着妻子,并且原谅了她生前的出格行为。正如巴恩斯在短篇小说集《柠檬桌子》中说道:“爱情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唤醒良心,满足虚荣心,甚至洁净肌肤,但它绝不会带来快乐。爱情里永远有不对等的感情和意图存在。这就是爱情的本质。”[8]1
三、在知天命时从容面对衰老和死亡
衰老和死亡是人类长久以来普遍讨论的话题,每个时代的人们都在思考它,每个人都要经历它,一直也是文学界亘古不变分析探讨的永恒主题。“文学离开对人类自身生命的追问是空洞和肤浅的, 文学的社会价值正是在于对人类生命的终极关怀。”[9]41巴恩斯其实早已关注着衰老和死亡,在他的首部小说《伦敦街区》里,主人公克里斯表达了对丧亡的无限恐惧。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死亡的极大恐惧会出其不意地扑向克里斯,想大声尖叫,可是父母不允许。克里斯只能无助地在黑夜里“浑身颤抖……不是惧怕死亡的过程,而是惧怕已经死亡这个状态”[10]54。巴恩斯集中而深入关注衰老和死亡这一话题是《柠檬桌子》(The Lemon Table,2004)《没有什么可怕的》(Nothing to Be Frightened of,2008)。
《柠檬桌子》是由11个故事组成。故事里的主人公来自不同的社会背景,不同的时代,甚至不同的国家。他们都将面临同样的问题,即衰老和死亡。正如《纽约时报》曾这样评论:这些故事是为逝去的青春、逝去的诺言和逝去的爱而作的美丽的悲歌。相对一向理智的巴恩斯先生的作品,它们展现出一种新的情感深度。下面以书中的第一个故事《美发简史》为例,看看巴恩斯是如何洞悉衰老和死亡的。
《美发简史》由三个章节组成,主人公叫格雷戈里。四次的理发经历浓缩了主人公整个人生的历练过程。第一次去理发,由于刚搬家,母亲带他去理发。母亲那句“后面和两边剪短,头顶略微剪剪”成为他以后理发的语录。[8]1他感觉理发就像被做了一次可怕的外科手术那么可怕。第二次是独自一人去理发的,这是母亲要求的。路上一遍又一遍练着母亲的那句话,像在祷告。内心无比紧张恐惧,但是又得表现的像个男子汉。可是当坐在理发椅子上时,还是不由得紧张起来,似乎要遭受理发师的任理意宰割了。理发师那坚如磐石的大手猛拍他的脑袋,他一动也不能动,只能默默忍受着剪刀冷冷地在头顶上滑来滑去,磨剃刀的声音意味着要被割喉了,电推刀会把耳朵割去一大块,血流致使电推刀导电,会将他就地电死。[8]4-7后来发现其他人临走时都给理发师小费,而他没有多余的钱,格雷戈里猜测这有可能是理发师对他这样的男孩子粗暴讨厌的原因了。
第二次理发时,格雷戈里已是个年轻气盛的小伙子了,大学毕业,恋爱受挫。理发师是位年长他许多的老人,头发花白、瘦骨嶙峋、眼神焦虑,并主动与格雷戈里搭讪。主人公对理发师的问题简短做以回应,或者不理睬,心里只是想着女友艾莉为何与他要分手。理发师聊到婚姻的话题,年轻的格雷戈里不以为然地声称,“对于懦夫,婚姻是唯一的冒险”[8]13。理发师可不这样认为,骄傲地谈到他的儿子和女儿。格雷戈里觉得理发师们都是些唯利是图、粗暴无礼的人,现在他长大了,是该以牙还牙的时候了。当理发师让他照镜子时,虽然内心对理发师的手艺和理的发型很满意,但是并没有表达出来,什么都没有说就离开了。
第三次理发时,格雷戈里显然是位老人。他在理发前,在盥洗室里,自己用指甲剪修了修眉毛、耳毛、鼻毛,并将沾湿了一角的法兰绒布块擦洗了耳朵。然后,他打电话预约了理发。走进理发店里,一位胖乎乎的女孩为他洗头发,她嘴上说了几句体贴顾客的话,但是无法从她手上感受到一丝一毫的关切。[8]21到了这把年纪,格雷戈里在理发店里已经养成了半开玩笑的顺从,他也随身带了足够的小费给她们。为他理发的女孩叫凯莉,一边理着头发,一边两人随意地聊着天。凯莉兴致勃勃地谈到曾经在迈阿密的邮轮上工作过,很轻松,来钱快。但是,作为父辈的格雷戈里不免担心起在那儿女孩子工作的安全性。当他谈起家事时,凯莉只是漫不经心地敷衍几句,心里似乎还在想着迈阿密的情景。理完发,凯莉照例去取镜子让他照后脑勺,这次格雷戈里脸上挂着那惯常宽容的微笑拒绝了。他认为“如果前面好好的,后面也会没问题”[8]28。
四次的理发经历,格雷戈里从一个青涩的小男孩,长成年轻气盛的小伙子,再到圆滑世故的老人。其内心也发生了人生不同阶段的相应变化,由童年时对理发师的紧张惧怕到青年时的反感厌恶再到老年时的委婉抗拒。巴恩斯通过对格雷戈里的刻画,说明每个人都会经历人生的幼稚期,旺盛成熟期和衰老期。人们不能因为自己正处于人生的旺盛期,就可以歧视欺辱其他时期的人。人们应该学会相互尊重,相互扶持,毕竟谁都会有衰老的那一天。
在回忆录《没有什么可怕的》,巴恩斯一改以往针对死亡只是表示无奈和恐惧。这次他勇敢地站出来,鼓励人们直视死亡,克服对死亡的恐惧。作者依据对亲人朋友们死亡时情景的记忆,通过和研究古典哲学的哥哥关于死亡的探讨和叙事,能够进一步洞悉死亡的真相。
作者在这本回忆录当中,采取分散的、简洁的、诙谐的语言风格坦然告诉读者:死亡是可怕的。因为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死亡都是无法预测、不可避免的;活着的人只能作为旁观者,目睹亲人朋友们死亡时的苦痛;死亡是令人异常难堪的,尽管生前人们是多么体面,多么辉煌。但是,人们不能把死亡想象成可怕的魔鬼,不敢在公开场合谈论。相反,应该作为常见的话题去商讨,揭示它的神秘性。另外,人们要敢于想象死亡来临时的境况,做好应有的准备,更加从容地去面对。正如俄国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对死亡的认识: “我们应该时常想到死亡,应该使自己习惯这种对死亡的思考。我们不能让对死亡的恐惧不知何时悄悄地攻上我们的心头……我想如果人们能早点想到死亡,他们就能少犯些愚蠢的错误……对死亡的恐惧是一种最热切的情感。有时,我想,再没有比死亡更深沉的情感了。”[11]27
四、结语
巴恩斯是当代具有人文主义关怀的伟大作家之一,他强调日常生活价值对于普通人的重要性。他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涉及与人们日常生活相关的话题,比如个人历史、记忆、死亡、婚姻、生存危机等方面。尽管在后现代语境下艺术和生活、真实与虚构的界线已经模糊, 巴恩斯仍然坚持认为“人类的内心和情感始终是他作品关注的对象”[12]21。他那机智诙谐、跳跃分散、简洁明快的语言中蕴含着温暖而深刻的哲理。正如2011年,巴恩斯凭借《终结的感觉》被授予布克奖时,评委会主席盖比·伍德(Gaby Wood)这样称赞他:“受困于日常生活的悲剧如此感人、如此敏锐,人们只能几乎盲目地、以片断地形式面对,而这正是真正大师级小说的标志。”
[1] 龙迪勇.记忆的空间性及其对虚构叙事的影响[J].江西社会科学,2009,(9):49-52.
[2] 毛文强.生存危机中的自我与他者——朱利安·巴恩斯小说研究[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5.
[3] [英]朱利安·巴恩斯.终结的感觉[M].郭国良,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4] Julian Barnes.LevelsofLife[M].London:Jonathan Cape,2013.
[5] 张莉.哀悼的意义——评巴恩斯新作《生命的意义》[J].当代外国文学,2014,(1):74.
[6] [法] 阿兰·巴迪欧.爱的多重奏[M].邓刚,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7] [英]朱利安·巴恩斯.福楼拜的鹦鹉[M].汤永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8] [英]朱利安·巴恩斯.柠檬桌子[M]. 郭国良,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9] 陈民.西方文学死亡叙事研究[M].南京:江苏出版社,2006.
[10] Julian Barnes.Metroland[M].London: Vintage Books,2009.
[11] Julian Barnes.NothingtoBeFrightenedof[M].New York: Alfred A.Knopf,2008.
[12] McGrath, Patrick.“Julian Barnes” in Bomb[M].London:Jonathan Cape,Ltd.,1987.
【责任编辑 马 俊】
Exploring the Meaning of Life from Memory and Narration——On Julian Barnes’ Novels
YUAN Jin-li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Weinan Normal University, Weinan 714099, China)
Julian Barnes is very skillful at writing by memory and narration, which are often employed in his works. Memory is not always reliable, and narration is mostly fictional. Therefore, readers’ impression on Barnes’ novels is a mix of being fictional and authentic, amiable and natural, humorous and philosophical. The paper analyzes a few works by Barnes, hoping that readers can appreciate Barnes’ various writing styles and philosophical ideas.
memory; narration; self-identity; marriage; death
I106
A
1009-5128(2016)20-0085-06
2016-05-20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人诗意地栖居——唐代关中生态与文学(12YJC751039);渭南师范学院人文社科重点项目:地方院校英语专业学生思辨能力培养研究(15SKZD03)
原金利(1977—),女,陕西蒲城人,渭南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与英语教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