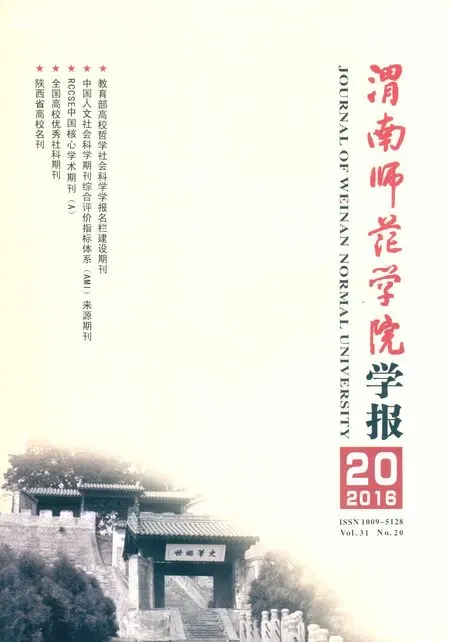精神信仰下的身体资本:再论霍桑文学作品中的身体观
2016-03-17田静,王毅,田苗
田 静,王 毅,田 苗
(渭南师范学院 a.外国语学院;b.体育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语言文化与文学研究】
精神信仰下的身体资本:再论霍桑文学作品中的身体观
田 静a,王 毅b,田 苗a
(渭南师范学院 a.外国语学院;b.体育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霍桑的文学作品大都是在探讨宗教与道德、宗教与信仰、宗教与科学以及宗教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其背后都是围绕精神信仰与身体的核心展开的。以马克思提出的影响身体行为的道德规范是取决于社会的生产关系的视角分析认为,霍桑在文学作品中试图建构起的身体观是在批判的基础上,通过宗教信仰引导与规训,使身体成为原始积累的资本,建构起一种旨在为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服务的资本主义身体观。
身体观;信仰;身体资本;霍桑
霍桑身处的时代,支撑美洲早期移民精神支柱的清教思想逐渐退去,充满个人主义的超验主义思想日渐凸现,一种充满孤独悲观、有幻灭主义倾向的个人主义与资产阶级集体主义思想交织在一起。这一阶段美国国家概念基本确立,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北方科学民主的资产阶级与南部农场主蓄奴制并存。建立起一种什么样的思想体系、道德观念、社会生产关系是霍桑文学作品探讨的主题,而这一切都涉及的一个核心就是身体。因为身体作为一种物质现象,既形塑着它所处的社会环境,又受着社会环境的塑造。[1]7因此,从身体的维度来审视道德价值体系和社会生产关系,对于我们理解霍桑文学作品中宗教与道德及社会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西方哲学史中身体观的产生与演变
柏拉图最早提出灵魂与肉体的二元理论,强调灵魂对于肉体具有主导支配权,肉体对灵魂发展起着消极作用,拖累着灵魂向下运动。当肉体的欲望不能听命于理性的灵魂时,外在表现的人便走向堕落。因此,在古希腊哲学思想中,“肉体”就不是一个没有生命性的中性的词,而恰恰是隐藏着能拖动理性灵魂向下堕落的低级欲望的。[2]11当灵魂离开肉体时,肉体便死亡,而灵魂不灭,它在人的生前和死后永恒存在。灵魂的本质是理性的、思维的。而身体则是其通向真理、知识与智慧之途的障碍与桎梏。因此,“如果我们要想获得关于某事物的纯粹的知识,我们就必须摆脱肉体,由灵魂本身来对事物本身进行沉思”[3]64。基督教中也大量使用“肉体”这一词,但基督教中的 “肉体”概念相对于柏拉图的“肉体”更具有罪恶本源的能动性。《约翰福音》中耶稣就多次提出肉体和上帝的旨意是完全对立的,这个“肉体”按照自己灵魂的本意最终走向死亡。如果按照上帝的旨意行事,就会让肉体得到上帝圣灵,从而使身体重生,灵魂得救,让“肉体”得到永恒的“生命”。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柏拉图二元论中的灵魂不灭,基督教则更多地强调了“肉体”所拥有的自主性灵魂,死亡是灵魂同肉体一起灭亡。因此,基督教中的“肉体”只有在拥有了灵魂后,我们才可以理解为“身体”。因此,在西方哲学体系的两大思想来源中,不管是柏拉图独立于灵魂之外的肉体,还是基督教中拥有罪恶灵魂的肉体,身体都不仅是纯粹理性知识的障碍,更是伦理与罪恶的本源。[4]85
这种身心二元对立的观点到了中世纪,在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教父哲学思想推动下,建立起了一个用理性论证信仰的方针,即本体论、认识论问题。进一步强调精神信仰的本体性,因为从信仰到观察,不存在任何过渡。用肉体的眼睛来判断,信仰实际上是“瞎子”[5]190。而肉体则是“原罪”的容器和邪恶的根源。我们只有把自己从肉体的欲望之中脱离出来,专注于灵魂才能得到上帝的眷顾。灵魂与肉体就是上帝与魔鬼的对决,身体既是上帝与魔鬼斗决的场所也是争夺的对象。
到了15世纪,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作为形而上学的第一原理,确立了近代理性主义哲学,构成了近代哲学的开端。笛卡尔认为身体感觉经验的不可靠性,怀疑客观存在的现实世界,客体必须依赖于主体思维而存在,身体作为客体的存在也是不可靠的。因为“我”是一个有思维而没有广延的东西,“我”对于肉体有一个分明的观念,它只是一个有广延而不能思维,所以这个“我”就是我的灵魂,也就是说“我”之所以为 “我”的那个东西,是完全真正跟我的肉体有分别的,所以灵魂可以没有肉体而存在。[6]82身体只是我的表象,思想才是我的本质,只有通过思想才能意识到我的存在。身体是客体,思想是实体,思想可以脱离于身体而独立存在。身体的有效性和作用只是一架依照自然规律进行运转的精密机器而已。笛卡尔主张的这种“无身思维”,将思维、心灵作为我的本质,完全区分开于我的身体,确立了“身心二元论”。笛卡尔之后的近代西方哲学基本没有走出“身心二元论”的影响。此后,理性和科学是哲学领域的重点,康德进一步将人的知识能力分为感性、知性、理性三种,认为一切知识来源起始于感觉经验为感性的,而后天对感性经验进行加工即为知性的,先天的知识非指离开个别经验而独立自存之知识,乃指绝对离开一切经验而独立自存之知识。当先天的知识未杂有经验的事物在内,则名为纯粹的。[7]30纯粹理性概念之客观的使用,常为超验的,而纯粹悟性概念之使用,则依据其性质且因其仅应用于可能的经验,自必常为内在的。[7]263一切知识来源于经验的基础之上,科学知识具有经验性,但知识还应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这种符合普遍性与必然性的形成上学的理性知识来自于我们的先天就有的,这种先天就有的理性知识康德称之为“先验”。康德的这种抛开身体,仅讨论经验与理性的先验思想来源于笛卡尔的先天观念,既而到19世纪被爱默生等人认为人能超越感觉和理性而直接认识真理,强调直觉的重要性,发展成为了“超验主义”。
二、宗教改革让身体解放成为“资本”
基督教所宣扬的“原罪”思想认为身体的欲望是罪恶的本源,其实质是人类对自身存在及对生存环境的缺乏理性的认识。然而,在奥古斯丁等基督教教父学将宗教哲学化以后,“原罪学说”这些看似神秘的、不合理性的学说恰恰成了人类理性的产物。因此,整个中世纪社会的焦点就在于理性与信仰、理性与权威之间的关系,理性在人类进步历程中的作用,承认不承认个人理性在决断信仰中的权威以及个人理性思维的权利。或者更准确地说,关键在于这些学说背后所反映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所反映的阶级利益。[8]1正是出于这种阶级利益,罗马教廷整个中世纪长达千年利用宗教信仰进行身体规训和理性思维的蒙昧统治及对社会经济的控制,其反映出的本质是阶级集团的利益。直到14—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以后,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进步,新兴的资产阶级形成。反封建、反神权,人文主义的信仰、自由、平等等理性与科学的背景下,16世纪英国的亨利八世、德国的马丁·路德及法国的加尔文等,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因此,中世纪宗教神学的核心问题与其说是人与上帝的关系,不如说是人与教廷的关系。只有在马丁·路德通过《九十五条论纲》对天主教会进行控诉,并提出“因信称义”,加尔文提出的人通过“信仰得救”将人与教廷的关系割裂开来并转变到人与神的直接关系,才使得人通过自身得到上帝的救赎成为可能。它割裂了阶级集团利用宗教对人身体和思想的控制。
德语中的“Beruf”,英语中的“calling”两个反映职业、天职、神召的词,其本意都有宗教概念中上帝安排的任务的意思。新教教义认为个人道德的最高形式应是对世俗事务的评价,就是日常生产的、生活过程,这就让日常的世俗活动具有了宗教的意义。马丁·路德正是基于此提出了“职业”概念,提出新教的教理是日常的生存方式,而不是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道德。个人完成在现实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就是他的天职。只有干好上帝分配的职务为上帝服务,进而得到上帝的救赎。加尔文也认为一个灵魂得救的人一定是一个内心有坚定的信仰,外在有着奋斗敬业精神,做善功的人。干好上帝派你去干的本职工作,让勤奋节俭成为美德,多产生少消费。不管是马丁·路德提出了“职业”概念,还是加尔文让人从关注来生转到关注于现世,都使身体从宗教中解放出来成为自由的身体“资本”成为可能,这在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资产阶级的原始积累提供的巨大的精神支柱和推动力。
因此,德国20世纪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认为,宗教改革在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原始资本的积累,它成了资本主义原始核心精神的杠杆。他在《近代资本主义的概念与先决条件》中认为:“把西方资本主义的特性与其原因结合起来,我们即可发现下列因素:只有西方的资本主义,产生一种任何地方从未有过的合理的劳动组织。”[9]135近代资本主义形成的先决条件包括是自由劳动力之存在。[9]118恩格斯认为加尔文教为自然主义成功的自然阶级提供了一个宗教依据和精神支持,认为加尔文教的信条正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最果敢、大胆分子的要求。
三、对清教及“超验主义”身体观的批判
宗教发展中最伟大的历史进程便是把“魔力”从中排除出去,达到逻辑的结局。换而言之,就是让宗教摆脱巫术和迷信,成为一种信仰。这是加尔文宗教改革对基督教最大的进步。然而,加尔文宗教强调上帝的绝对超验性及“一切和肉体有关的都是堕落”等严酷的清教教义,是对一切感官和情感进行彻底否定的禁欲主义。这种深陷的禁欲主义会让人们脱离于日常的世俗生活,而脱离于现实意义,最终走向自我毁灭。加尔文教徒与上帝的联系是在深深的精神孤独中,这在加尔文宗教思想来源的班扬所著的《天路历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这种孤独感成为有幻灭感及悲观倾向的个人主义的根源。霍桑深受美国清教思想的影响,也认为人是有“原罪”的,人的本性里有恶的存在,这种身体与罪恶,宗教与道德等“原罪”和“内在堕落”是霍桑早期作品的主题,如《罗吉·马文的葬礼》《好小伙布朗》《大地的燔祭》《伊桑·布兰德》《胸中的蛇》《教长的黑面纱》等,都是对人性本恶的描写。但同时,霍桑也对于清教主义对人性的压抑与迫害时行严厉的批判。如《红字》《七个尖角阁的房子》《福谷传奇》等。
17—18世纪为回应牛顿力学对传统神学世界观的冲击,自然神论者以上帝创造了宇宙和它存在的规则后,并不再对这个世界的发展产生影响进行回击。以斯宾诺莎等自然神论者认为“自然即神化身”,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自然神论者卢梭认为,上帝不在自然界中,但上帝依然存在,它在我们的心中。康德继承发展为先理性知识的“先验”性。这一思想到19世纪,被爱默生等人在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下发展为“超验主义”。“超验主义”思想强调人能超越感觉和理性而直接认识真理,强调直觉的重要性。超验主义过度强调人对于宇宙的重要性,宣扬精神世界对于客观世界的主观控制,强调个人主义,认为自然界就是“超灵”与上帝的象征。认为上帝存在于自然及自我的心中,通过无限放大自我达到“人性”与“神性”的互通。“超验主义”打破了清教主义“原罪”和“命定论”思想,对于人性的解放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然而,“超验主义”无限放大个人意愿,让个人欲望无限地扩大,使得“超验主义”明显地烙上资本主义上升期的时代特性,促使殖民资本主义、冒险资本主义在美国的高速发展。这种冒险主义殖民资本主义进行着对自然资源和身体利益的无限疯狂掠夺。如早期的殖民国家开始对美洲进行扩张和殖民活动时,正是重商主义在西欧初兴之际,无不把贵金属的掠取当作首要目标。16世纪30年代在新墨西哥、新格拉纳达、智利等地分别发现了极富开采价值的银矿和金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10]2后来的殖民者对印第安原住民居住地的殖民扩张,再到17世纪开始的非洲人口贩运及蓄奴制度[11]1,无不是在这种极度地充满着个人主义使得超验主义明显地烙上资本主义上升期的时代特性。这种强调人能超越感觉和理性而直接认识真理,强调直觉的重要性,使得个人主义,私人欲望的无限扩大,促使殖民资本主义、冒险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这种殖民资本主义冒险主义、进行的自然资源和身体利益的无限疯狂掠夺在反映了资本主义的罪恶本性。这样的超验主义思想下的殖民资本主义身体观,霍桑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如《胎记》中的科学家爱尔默就是在超验主义思想下认为自己掌握了科学技术,达到了人性与神性的互通的“超灵”,认为妻子的身体和其他自然界的物体一样,只具有物质的本性,自己如同上帝一样拥有绝对的权力对于妻子的身体——这个“尘世的俗物”进行改造。最终他用一双自以为拥有上帝能力手的实验害死了美丽的妻子。《拉帕奇尼的女儿》中描写的医生拉帕奇尼不惜以女儿的生命为代价进行所谓的科学试验。还有后来受到霍桑深刻影响的麦尔维尔的作品《白鲸》,同样也是讲的人类违反神的意愿,仇恨使他丧失理智和人性,成了最孤独最痛苦的人。他以个人意志,无视他人自由,不惜牺牲他人性命,达到与自然的共同毁灭。亚哈、爱尔默、拉帕奇尼医生都是“超验主义”思想者的自助者形象,他们的最终方式都是死亡,这种死亡是精神的、感情的、肉体的死,死是自助论发展成为唯我主义阶段所必付出的高昂代价。因此,极端的个人主义使其灵魂因过于独立而难以得救。《胎记》《拉帕奇尼的女儿》和《白鲸》都是通过披露19世纪标榜民主的美国社会生活中孤独与近乎自杀的个人主义模式,有力地抨击了新英格兰超验主义的个人“超灵”与自助论。[12]374《胎记》中妻子乔治安娜脸上胎记和《白鲸》中白鲸这些上帝自然的造物在爱尔默、亚哈等这些超验主义者看来都是世间一切“恶”的化身,是神的面具。他的满腔怒火实际是冲着上帝进行的灵魂与肉体、物质与精神、天堂与尘世的较量。这一切企图窥探上帝秘密的行为都是对上帝绝对超验性的怀疑与挑衅。同样这种思想来源于加尔文清教对于一切诉于感官和情感成分的彻底否定,这种孤独感成为有幻灭主义及悲观倾向个人主义的一个重要根源。这就是霍桑认为的冒险主义、殖民主义的掠夺资本主义身体观走向灭亡的必然倾向。
四、建构的宗教伦理下资本主义的身体观
清教主义具有强烈的现世主义、禁欲主义和功利主义三大特征,其身体观因严酷的禁欲主义压抑了人的本性,使人脱离了世俗的现世生活。而掠夺资本主义身体观过度强调人超越感觉和理性直接认识真理的个人直觉“通灵”,这是对自然世界的神的窥探与挑衅,及对于感官和情感的彻底否定的带有幻灭主义及悲观倾向的个人主义都必将走向灭亡。霍桑对这两种身体观都进行严厉的批判。那么,当时的美国应当建立起一种什么样的身体观呢?分析其时代社会背景,美国两次独立战争后,彻底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成为独立的国家。1789年《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的通过让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人类对于理性政治的追求变成了现实。更重要的是它是建立在真正契约意义上的宪政与实践。此后,1850至1860年间,北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产阶级和南部蓄隶制农场主一直进行着斗争、妥协与并存。美国在18世纪末为西部扩张开始了西进运动,美国的西进运动实际就是对原住居民的殖民运动。使自己摆脱被殖民后即刻变成了殖民者,然而在他们看来,这一切恰恰是美国的精神。
16世纪,欧洲殖民者开始将西非的黑人贩卖到欧洲及新大陆去,达到了奴隶制度的顶峰。18世纪晚期,欧洲开始的启蒙运动给美国北方的资产阶级带来了人权、自由、平等的观念,而南部农场主蓄积了大量的农奴。而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北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需要大量自由身的劳动者,并进行大量废奴思想的宣传,如晚于《红字》两年,于1852年发表的《汤姆叔叙的小屋》揭露了蓄奴制的野蛮丑恶,引进了巨大的反响,致使大量农奴逃离南部。南北矛盾日益激化,废奴运动日趋高涨,南北冲突日益加剧。霍桑正是处在这个支撑早期移民的精神支柱的清教思想逐渐退去,超验主义思想个人主义日渐凸现,这种充满孤独、悲观有幻灭主义倾向的个人主义与资产阶级的集体主义思想交织在一起的时代。建立起一种什么样的思想体系、道德观念、生产关系这是霍桑文学作品中进行讨论的主题。
马克斯·韦伯分析新教伦理的两种资本主义,一是建立在冒险主义、殖民主义上的掠夺资本主义,二是建立在真正宗教伦理精神下具有契约资本精神的现代合理资本主义。霍桑的文学作品在批判了冒险、殖民资本主义身体观的基础上,试图建构起的正是这种新宗教观念,具有宽容、仁爱、坚强、信仰的合理资本主义身体观。分析整个霍桑的文学作品我们不难看出,1850年《红字》出版以前的早期作品,如《罗吉·马文的葬礼》《好小伙布朗》《大地的燔祭》《伊桑·布兰德》《胸中的蛇》《教长的黑面纱》等都是在讨论人性的善恶、身体的“原罪”“内在堕落”等宗教与道德的关系。1850年的《红字》及1851年的《七个尖角阁的房子》都是讨论人性的解放、摈弃与自我救赎等宗教与信仰的问题,再后的《胎记》《拉帕奇尼的女儿》等,都是讨论宗教与科学的关系。《通天的铁路》《福谷传奇》及深受霍桑影响并用来献给霍桑的麦尔维尔的《白鲸》等主要是对于超验主义这种乌托邦式的幻灭式个人主义的批判,讨论宗教与社会生产方式关系。不管是讨论宗教与道德、宗教与信仰、宗教与科学还是讨论宗教与社会生产关系,其都是围绕着身体的主题讨论宽容,这宽容是对灵魂的宽容,是对身体的宽容,也是科学对于上帝的宽容。整个欧洲正是因为不宽容,通过战争对殉教者、异教徒从身体进行消灭,使得欧洲渡过了几千年的黑暗时代。只有到了文艺复兴以后的宗教宽容才有了科学与民主产生的条件。然而,科学和民主的发展却反身对于上帝没有宽容。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说:“我不得不限制科学,以便为道德留下余地”,科学如果无限地扩大到道德的领地,也就没有了自由。科学认识是有界限的,这一个界限就是道德。因此,康德说:“人是一个有限的理性存在。”尼采说科学的进步让“上帝死了”。所以,科学技术的进步、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不能解决道德、信仰等精神层面的问题。宗教和道德共存于同一社会体系,共生于同一经济基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乃至于互为因果。道德用伦理准则和行为规范来调整人—人关系,宗教用神的意志来神化现存经济关系为基础的人—人社会关系。道德为宗教提供教义的社会内容,宗教把道德抬升为信条律法,这就是道德宗教化与宗教道德化的过程[13]614-615,而这一过程的中间纽带便是身体。因此,霍桑的文学作品不管是讨论宗教与道德信仰、宗教与科学技术还是宗教与社会生产方式都是围绕着身体展开的。
费尔巴哈提出伦理道德体系是建立在“利己主义”的人之本性下,这就把伦理学从宗教学的束缚解放出来,把伦理还原为人本学和社会学,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作为伦理道德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人类社会关系中有三种最基本的关系:一是物质生产;二是需要;三是人与人的社会伦理关系。马克思对一般社会关系进一步分析到社会生产关系,发现社会生产关系才是社会伦理秩序和道德观念的真正基础。社会伦理秩序有不同的形式,它们是由生产关系的性质所决定,随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13]614-615,而生产关系的核心便是身体关系。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待霍桑作品中关于身体和信仰,我们就不难理解了。难怪米歇尔·福柯认为这种对肉体的政治干预,按照一种复杂的交互关系,与对肉体的经济使用紧密相联;肉体基本上是作为一种生产力而受到权力和支配关系的干预;但是,另一方面,只有在它被某种征服体制所控制时,它才可能形成一种劳动力(在这种体制中,需求也是一种被精心培养、计算和使用的政治工具);只有在肉体既具有生产能力又被驯服时,它才能变成一种有用的力量。[14]27-28因此,与其说霍桑文学作品中宣扬的是对于身体的解放,不如说是在对身体进行的重新规训,让身体从清教主义身体观下解放出来的同时,又要去除超验主义身体观的不羁,使身体在精神信仰的引导下,成为资产阶级控制的一种身体资本。尽管这一切霍桑本人可能也不曾意识到,但他却在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身体观与美国精神的建构。
纵观西方哲学史中的身体观,我们不难发现,“历史是身体的历史,而身体则是权力的身体。当灵魂、意识这些实体退去,身体走进前台,却示人以无比屈从与臣服的面目与形象”。“这是一种操练的身体,而不是理论物理学的身体,是一种被权威操纵的身体,而不是洋溢着动物精神的身体,是一种受到‘有益训练’的身体,而不是理性机器的身体。”[14]175这一切往往就隐藏在文化中,而这一过程就是权力与意志的身体隐喻。
[1] [英]克里斯希林.身体与社会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 谢文郁.身体观:从柏拉图到基督教[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11-22.
[3] [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4] 陈治国.论西方哲学中身体意识的觉醒及其推进[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84-91.
[5] [德]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6] [法]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反驳和答辩[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7]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8] 李平晔.宗教改革与西方近代社会思潮[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
[9] 郑乐平.经济·社会·宗教——马克斯·韦伯文选[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
[10] 何顺果.美国历史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1] 董衡巽.美国文学简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12] 聂珍钊.外国文学史:第二卷[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4.
[13] 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14] [法]福柯.规训与惩罚[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责任编辑 马 俊】
Physical Capital Influenced by Spiritual Beliefs Based on Body Concept in Hawthorne’s Literary Works
TIAN Jinga, WANG Yib, TIAN Miaoa
(a.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b.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Weinan Normal University, Weinan 714099, China)
Hawthorne’s literary works are mostly concerned about relationships between religions and morals, religion and beliefs, religion and science, religion and social relations, behind of which they focus on spiritual beliefs and body indeed. The paper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body concept in western philosophy system and analyses body’s role and status in western philosophy system and relations of social production. From Marx’s perspective that production relations in society determines physical morals norm mostly, Hawthorn tried to construct the body concept critically and made body become the capital of primitive accumulation under the guidance and disciple of religions. In Hawthorn’s literary works, capitalism body concept is constructed to serve bourgeois production relations.
body concept; beliefs; body capital; Hawthorn
I106
A
1009-5128(2016)20-0074-05
2016-05-20
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爱默生超验主义和中国儒道思想的跨文化研究(16JK1248)
田静(1978—),女,陕西白水人,渭南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王毅(1976—),男,陕西汉中人,渭南师范学院体育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运动与体质健康研究;田苗(1981—),女,陕西渭南人,渭南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跨文化交际与英美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