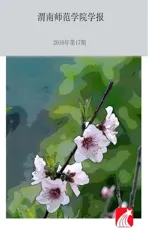论《史记》在跨文化交流中的双重价值
——从主体与客体的视角分析
2016-03-17魏泓
魏 泓
(1.北京外国语大学 文学院,北京100089;2.淮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史记》文献与传播研究】
论《史记》在跨文化交流中的双重价值
——从主体与客体的视角分析
魏泓1,2
(1.北京外国语大学 文学院,北京100089;2.淮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史记》体大思精、内涵丰厚,在跨文化交流中拥有重要的地位。文章从主体与客体的视角探讨了《史记》在跨文化交流中的双重价值。 《史记》描述了中国与周边民族与国家的关系,首次记载了跨文化交流中的民族问题。另一方面,《史记》作为客体被全世界许多国家翻译,在文学、哲学、史学等方面都得到了深入研究,对世界文化的融合、发展与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史记》;跨文化交流;主体;客体;双重价值
在中国历史典籍浩中,《史记》如一颗瑰宝,折射出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个性和民族身份感。它既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也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史记》不仅仅是一部记载史实的史书,而且内蕴极为丰富,梁启超称之为“超史的目的”[1]34。
《史记》不仅是一部叙述中国3000年史事的通史,而且也是一部世界史。当时,中国与外国的交往远到南亚、东亚、西亚一些国家,中国与这些国家的交往都被写到《史记》里了。虽然司马迁时代还没有“跨文化交流”的概念,但司马迁本人在民族史的记载中却以跨文化的视野来观察周边世界的历史,并尽其所知、对自己所知道的世界作了尽可能的描述与思考。他不囿于“中国”一国之内,而以世界性视野来编撰中国历史,表现出开明而深广的跨文化跨民族交流的思想,显示出先进的民族统一观与平等观。司马迁以超时代的民族眼光与世界范围内的跨文化交流视角来撰写史实,而另一方面,《史记》作为跨文化的客体媒介而被全世界诸多国家与民族所瞩目。一般而言,主体是实践与认识活动的承担者,客体是主体实践与认识活动指向的对象,两者是认识论的一对基本范畴。从主体视角而言,司马迁描述了中国与许多其他民族与国家间的关系,所记载的跨民族跨文化交流的内容与其中所反映的思想值得我们学习与探讨,对我国进一步研习与加强民族关系有着重要作用。从客体视角而言,《史记》是中国史学的代表,蕴含着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符码,它作为跨文化交流的客体对象在世界范围内被广为翻译与研究,体现着无尽的客体价值,对世界跨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史记》体大思精,值得发掘和探讨的课题很多。《史记》自问世以来,历代研究它的文章成千上万、不可胜数,有从历史学、文学、天文学角度来进行探讨的,也有从民族学角度进行探讨的,但目前还没有从跨文化交流角度来研究它的世界价值。
本篇尝试着从主体与客体视角来研究《史记》在世界范围内跨文化交流的意义与作用,具体探讨其在跨文化交流中的双重价值。
一、《史记》跨文化交流中的主体视角
气贯长虹的《史记》全面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时期中华民族3000年的历史。其中,《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专门给中原以外的周边民族以及当时与汉朝交往的国外民族立传,这在历史著作中是一个创举。[2]3《史记》开创了正史记录少数民族历史与文化的先河,给后人留下了真实的历史资料,表现出深刻的跨民族交流意识、批判精神以及忧国忧民的民族思想。
(一)《史记》的跨文化民族史
在中国历史上,《史记》第一次为少数民族立传,记录了少数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还记载了邻国的历史。《史记》对跨文化交流中的民族问题做了首次记载,独创了民族史传。
司马迁的《史记》保存了民族史的重要资料。他写了匈奴、南越、东越、朝鲜等少数民族史传,叙述了汉武帝时期各周边民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司马迁不仅记载了既有“和平友好”又有“兵戎相见”的民族史,还表现出民族一统和等列天子臣民的思想。司马迁对各民族的不同生活环境和风俗习惯予以客观真实的记载,丰富了古代历史上关于跨民族跨文化交流的内容。《史记》展现了周边民族与汉朝交往以及众民族逐渐融合发展的历史过程,提供了研究少数民族和世界民族历史的重要史料。“《史记》中所记录的一部分地区和民族,不在今日中国境内,如印度、朝鲜,但这些地区和民族的历史文化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3]66《史记》一书保存了大量民族史料,是研究民族历史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同时又是研究当时社会政治、文化的重要依据。
在民族史传中,司马迁对《大宛列传》的处理最为引人注目,其中记叙了远至中亚的外国史事,被特别列出。《大宛列传》对乌孙、康居、大月氏、安息、大夏等外国的生活习俗有一定的记载,展现了汉民族与其他外国民族的友好交往,有着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像朝鲜、印度临近中国,当时大宛则是远离中国,中国与大宛等西方国家的交往则完全是中国与外国之间的交往。“张骞出使西域”的民族活动让中国人的视野不仅扩大到了中亚、西亚和印度,甚至远达东地中海。司马迁在《大宛列传》中提到西边最远的国家是“條枝”[4]106。條枝位于地中海东岸的叙利亚境内。《大宛列传》记叙了遥远国家的历史事实,所以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作特别说明:“西极远蛮,引领内向,欲观中国。作《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可见,司马迁“用这样的眼光看待历史,正如翦伯赞先生所说‘即以世界规模研究中国历史’,表现了司马迁非凡的识见”[2]4。 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其行程通过北道的龟兹直达乌孙,到达了大宛、康居、大夏、安息、身毒、于阂等地,并进行了一些经济、政治、外交活动。司马迁记载张骞事迹的同时记录了大宛等西域诸国的情况,这些记录表明中国中原地区人民眼界的进一步开扩,国家、民族意识的进一步提升。“《大宛列传》记述西域、中亚乃至更为遥远的西方的民族情况,使中国人第一次将民族研究的目光从汉王朝的辖境放眼到今天的中亚乃至欧洲,从而使《大宛列传》具有了世界史的性质。”[5]69司马迁在《大宛列传》中对西域各民族文化的记述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跨民族跨文化的财富。
《史记》对中国和周边各国,与中亚、西亚的跨文化交流上进行了首次记载,具有开先河的意义。司马迁对民族史实的忠实记录,为后人认识当时的民族关系、中原和西域的关系以及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关系史等都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二)司马迁的跨文化交流思想
司马迁博学多才,拥有丰厚的史实与广阔的跨文化交流视野。司马迁首创民族史传,并区别国内外民族进行立传。在立传中,司马迁表现出超前的跨文化交流的思想,他的民族平等并相互融合的思想为我国提供了宝贵的跨文化交流的资料与处理跨文化问题的理论基础。
在记录跨文化交往的民族史中,司马迁首创“中国人”一词,并加强了“中国人”一词的概念,体现了他的爱国思想,代表他大一统的民族观念。[6]99司马迁有着深深的大中国的观念,在《史记》中,“外国”“外国客”“外国使”等名词多次使用。司马迁把《大宛列传》中的西域各国,如大夏、大宛、乌孙、康居等都当成“外国客”进行记叙。司马迁重视各民族的历史演进过程,写下了许多与汉朝有关的地区与民族的历史文化情况。
司马迁独具先进的民族一统思想。他从心理上把各民族皆视为黄帝子孙,把各民族纳入统一的封建帝国版图之内来进行叙述,承认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并把各民族作为客观存在的民族实体来记叙他们的历史。在《匈奴列传》中,司马迁在记述匈奴与汉朝的争逐中,同时把匈奴民族生活的地域,经济、文化及风俗习惯作了介绍。司马迁写《西南夷列传》时,他侧重于西南夷复杂的地域概念进行论述,同时记述了西南夷内部各部族的特点。司马迁很欣赏汉武帝的“且以其故俗治,勿赋税”的策略,充分尊重各民族的生活习俗。司马迁谴责匈奴民族对汉朝北部边境的掠夺、入侵,对汉武帝发动战争含有批判态度,在民族列传中流露出反对战争、扩张和掠夺的思想。
司马迁拥有跨文化跨民族的统一与融合的思想,这种统一思想贯串于《史记》的始终。他认为中华民族是个统一的整体,中国境内各民族应平等相待,反对歧视和非正义战争。司马迁能站在华夏民族大一统的立场上来对各民族的历史情况进行记叙,并且特别注意汉朝与周边民族的政治、军事等方面的交往。司马迁能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发展情况来看待民族关系,把中国境内各民族看作统一的整体,这是他进步而超前的历史观使然。
司马迁的跨文化交流的民族观、世界观对《史记》影响很大。司马迁在少数民族列传的论述中,渗透着他民族平等、共同繁荣的跨文化思想。司马迁的民族融合观彰显着他先进的历史观,《史记》中的民族观对于中国各民族的大融合、大统一,有着积极影响。
二、《史记》跨文化交流中的客体视角
司马迁所记载的民族内与民族外的内容以及从中所体现出的思想都成为中外学者的研究对象。《史记》作为跨文化交流的客体,在全世界许多国家被翻译、解释与研究,并对所在国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而对世界文化的融合与共同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史记》在西方的流传从最初的译介逐渐向纵深的专题研究发展。美国汉学家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曾总结了《史记》翻译历程的三个阶段:一是20 世纪 30年代的一些零星的翻译;二是 20 世纪50 年代两次大的翻译工作,承担者分别为美国汉学家华兹生(Burton Watson)和中国翻译家杨宪益与戴乃迭;三是20 世纪70 年代到 90 年代所出现的四次重大的《史记》翻译工程:鲁道夫·维阿特基的俄文翻译,吉田贤抗的日文翻译,华兹生修订以前的译本和倪豪士等启动的英文全译工程。[7]可见,《史记》的外译工程日益浩大,而对于《史记》内容的研究文章在西方与东方的诸多国家都大量涌现,越来越多。《史记》的翻译与研究必将使世界更加了解《史记》,了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
(一)《史记》在西方世界的翻译与研究
《史记》在西方世界的翻译与研究大体上始于19世纪,迄今为止已有100多年的译介历史。19世纪中期,奥地利的先驱菲茨迈耶(August Pfizmaier)所翻译的《史记》,是《史记》最早的德文译介。1951年德国的海尼诗(Erich Haenisch)发表译文《公元前209年陈涉起义》,1965年其译著《信陵君:〈战国策〉和〈史记〉中的记载》由斯图加特雷克拉姆出版社出版。[8]303法国汉学家沙畹(Emmanuel-è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所译介的《史记》闻名遐迩,颇具世界影响力。1972年吴德明(Yves Hervouet)撰写的《史记》4卷由法兰西大学联合出版社出版。美国汉学家华兹生(Burton Watson)所翻译的《史记》文采斐然,可读性强,他选译了《史记》中文学性强的66篇进行翻译,华译本被作为世界文学经典译本而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性著作选集。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汉学家倪豪士主导《史记》全译工程,力求再现给读者忠实的学术性翻译。在英国最有名的是道森(Raymond Dawson)的《史记》翻译,他所译注的《司马迁:史记》于1994 年作为世界经典系列丛书之一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苏联学者非常推崇司马迁的《史记》,他们充分借助司马迁的《史记》研究中国古代史和中亚细亚各民族的情况。苏联著名汉学家阿列克塞耶夫(В.М.Алексеев,1881—1951)曾将《史记》许多篇译成俄文。20世纪70年代,鲁道夫·维阿特基开始将《史记》译成俄文,其工程规模宏大,学术价值很高。
随着《史记》在西方的译介,《史记》引起了外国读者们的广泛兴趣,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学者来研究《史记》。《史记》在西方世界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史学、文学与哲学思想上。
1958年,华兹生的博士论文《司马迁: 伟大的中国历史学家》被出版,他指出:“《史记》的形式为中国后世史学典籍提供了范例,其内容和风格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波及中国文化影响下的其他亚洲国家。”[9]761962年弗兰克·克尔曼(Frank A. Kierman Jr.)撰写了《从四种战国后期的传记看司马迁的撰史态度》一书,分析了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思想渊源、资料来源、列传的总体内容与风格等。1978年法国左景权(Dzo Ching-Chuan) 出版了《司马迁与中国史学》一书。顾传习(C. S. Goodrich)在其所译注的《司马迁的吴起列传》中用历史研究方法探讨司马迁的史学思想。[10]1999年侯格睿(Grant Hardy)发表《青铜与竹子的世界:司马迁对历史的征服》一书,高度肯定了司马迁的史学成就。[11]1988年侯格睿的博士论文《〈史记〉中的客观性与阐释问题》指出了《史记》中司马迁的历史观——历史史实具有道德教育意义,并认为司马迁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 《史记》是一部文学与史学价值兼备的杰作。[12]342-3451970年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发表《司马迁语言拾零》一文,系统研究了司马迁的语言特征。[13]306“美国汉学界真正从文学角度研究 《史记》,始于约瑟夫·艾伦 ( Joseph R. Allen) ”[14]62,1981年,艾伦发表了《史记:叙事结构初探》一文,探讨了《史记》的叙事机制及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1990年李乃萃(Vivian-Lee Nyitray)的博士论文《美德的写照: 司马迁〈史记〉中的四位君子的生平》运用法国结构主义、英美新叙事学、电影叙述学及中国传统美学理论分析了《史记》的结构特征。[15]1992年简小斌(Jian Xiaobin) 的博士论文《史记的空间化》从空间角度研究了《史记》的叙事基础。1992、1994年,侯格睿先后发表《司马迁〈史记〉的形式与叙事》与《论司马迁的多重叙事法》两篇文章。1995年,杜润德(Stephen W. Durrant)撰写《模糊的镜子:司马迁著作中的紧张与冲突》一书,对《史记》潜在的文学模式进行了深入分析。[16]1997年英国弗赫尔(Bernhard Fuehere)发表了《宫廷史学家的自画像: 司马迁〈报任安书〉札记》一文,对其中的文学修辞问题进行了分析。1986年杜润德发表《处于传统交叉点上的自我:司马迁的自传体著作》一文,指出西方自传传统与中国自传传统方式之间的关系。1992年杜润德发表了《混乱与缺漏:司马迁对前贤刻画的几个方面》一文,探讨了司马谈、董仲舒对司马迁所起的塑造作用。
(二)《史记》在东方世界的翻译与研究
《史记》在东方世界的翻译与研究以日本与朝鲜最为典型。
据史书记载,《史记》大约在魏晋南北朝时就已传播海外。虽然《史记》传入朝鲜的具体时间难以查证,但可能不会晚于东晋时期。至今,《史记》仍是朝鲜人民喜读之作,在朝鲜王朝政治与日常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史记》对朝鲜史学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入的,朝鲜二大正史《三国史记》与《高丽史》都效法了《史记》的纪传体史书特征,即便在编年体等其他史书中,也能见到《史记》的影响。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韩国出版《史记》译本数10种,其中第一部《史记》韩文译本《史记列传》于1965 年由崔仁旭完成,1973 年李英茂翻译的《史记》是第一部韩文全译本,自1992—1996年,在中国文学研究学者丁范镇率领下,由成均馆大学中文系青年学者共同参与完成七卷本《史记》全文的韩译工作。[17]《史记》在韩国出现了许多译注本,也出现了许多关于《史记》与司马迁的研究论著。
在东亚地区,日本《史记》研究的成果最为突出,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18]《史记》于公元600年就传到了日本。在近现代时期,日本已逐步形成了研究《史记》的庞大队伍,影响较大的专家就有泷川资言、水泽利忠等百余人,仅研究专著和译著就有680多种。一个始于20世纪70年代、并尚在进行中的翻译工程由吉田贤抗承当,他以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和田中笃实的《增订史记评林》为本,兼参考其他版本。1973年他的第一册译文出版,后陆续出版了第二、五、六、七、八册。这几册译本都相当详尽精到。日本对《史记》的研究成果向来最为丰硕,在汉文学、日本文学、中国文学、哲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各领域,都有众多的关于司马迁与《史记》内容及考证的研究成果。
三、结 语
本文以主体与客体的双重视角对《史记》跨文化交流的价值进行了描写与审视。《史记》作为跨文化交流的主体,开创性地给我们提供了二千多年前的跨民族交流史,让我们了解到中国当时和别的民族与国家间的文化交流。同时,司马迁开明的跨文化交流思想也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对我国现在的民族政策与研究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史记》作为跨文化交流的客体,产生了一定的世界影响力。它已被世界上许多国家翻译,并在文学、哲学、史学等方面受到深入研究。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与世界文明的快速进展,《史记》在世界范围内的翻译与研究工作更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的局面。不过,《史记》的研究中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间题,“《史记》研究已经走向世界,但是各国之间的研究很不平衡,国内与国外的交流也不够,这是问题”[19]57。不幸的是,当前跨国际的合作很不充分;中国学者常常忽视日本与西方研究的贡献;由中国、日本和西方国家的学者所共同参与的学术讨论实际上还不存在,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外研究不宜隔离开来、独自进行,应进一步加强《史记》跨文化交流的效果,形成世界范围内跨文化研究《史记》的网络系统,这样会更易于出研究成果,更有助于中国文化走出去,也更将有利于促进世界文化共享与共荣!
[1] 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M]. 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46.
[2] 张新科.《史记》民族列传的价值[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1): 3-5.
[3] 向红.《史记》中的张骞——读《史记·大宛列传》[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6,(3): 64-66.
[4] 杨巨平.“全球史”概念的历史演进[J]. 世界历史,2009,(5): 103-113
[5] 王文光,尤伟琼. 从《史记·大宛列传》看汉王朝对西北民族的治理及对中亚、南亚民族的认识[J]. 学术探索,2013,(2):69-73.
[6][美]吴淑惠.谈 《史记》中的中国人——兼驳近年来西方学者有关司马迁民族观的论述(下)[M]//杨共乐.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7]Nienhauser,W.H.Jr. A Review of Recent Shih Chi Translations[J].Asian Culture Quarterly,1991,(4) : 35-39.
[8] 李秀英. 《史记》 在西方:译介与研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06,(4):303-308.
[9] 吴涛,杨翔鸥. 《史记》研究三君子——美国汉学家华兹生、侯格睿、杜润德《史记》研究著作简论[J]. 学术探索,2012,(9):75-79.
[10] Goodrich , C. S.,Ssu-ma Ch'ien's Biography of Wu Chi[J].Monumenta Serica, 1981,35 : 197-233.
[11] Hardy Grant.Worlds of Bronze and Bamboo: Sima Qian's Conquest of History[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9.
[12]Hardy Grant. Objectivity and Interpretation in the Shih chi[D].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1988.
[13] Karlgren,Bernhard. Sidelights on Si-ma Ts'ien's Language[J].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1970,42:306.
[14] 吴原元. 百年来美国学者的《史记》研究述略[J]. 史学集刊, 2012,(4): 59-68.
[15] Nyitray,Vivian-Lee. Mirrors of Virtue Four “Shih chi” Biographies[D]. Polo Alto:Stanford University,1990.
[16] Durrant,Stephen.The Cloudy Mirror: Tension and Conflict in the Writings of Sima Qian[M].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5.
[17] 诸海星. 近四十年来韩国《史记》研究综述(1971—2010)[J]. 唐都学刊, 2011,(5): 47-57.
[18] 张新科, 李红. 《史记》在国外的传播与研究[J]. 博览群书, 2015,(12): 92-96.
[19] Crespigny, Rafe De. Reviewed work(s): Ssu-ma Ch'ien,The Grand Scribes' Records. Vol. I: The Basic Annals of Pre-Han China;Vol.VII:The Memoris of Pre-Han China[J].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96,59(3):596-598.
【责任编辑梁红仙】
On the Cross-Cultural Dual Value of Historical Record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ubject and Object
WEI Hong1, 2
(1.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2.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 235000, China)
Historical Records being grand in size and rich in thought enjoys high status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ubject and object, this paper makes a probe at the cross-cultural dual value of Historical Records. Historical Records describ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its neighboring nations and peoples, making an initiative in recording national problems concerning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On the other hand, Historical Records has been translated in many countries, and meanwhile received a great amount of studies in the aspects of literature, philosophy, history, etc., making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the whole world.
Historical Records;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subject; object; dual value
K207
A
1009-5128(2016)17-0089-05
2016-06-27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文化软实力构建中的文化翻译与对外传播研究(13YJAZH025);全国高校外语教研项目:生态学视阈下文学翻译本土化“再生”研究(2014AH0042A);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重点项目:生态语言学视阈下的“译语”语言研究(SK2014A373)
魏泓(1974—),女,安徽宿州人,北京外国语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淮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翻译与比较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