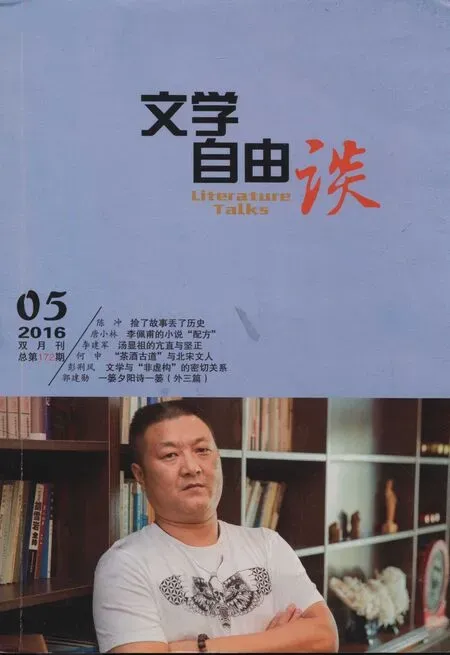一个女性知识分子的文化长廊
2016-03-17李进超
□李进超
一个女性知识分子的文化长廊
□李进超
喜欢上赵玫的作品是从她的《我们家族的女人》开始的。这部小说极具个性化的“女性书写”力透纸背,直达普遍人性的深处,读来令人震撼不已。赵玫的小说,情感丰沛充盈且跌宕起伏,却从不矫情,可谓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每每读来总被带入其中,掩卷则大有净化之感。与此同时,在情感的洪流下面又总能听到来自冷静思考者极富哲理的声音。想辨别清楚这声音当然并不容易,因为它不是直白的说教,何况还被淹没在情感的洪流之中。然而,这正是其魅力所在,也是最让我感兴趣的地方。哲理性构成了赵玫小说的一个潜在的重要维度,而这在她近年来发表的系列文化随笔中则成为了明显的特征。
发表在《世界文化》上,以“赵玫文化随笔”为总题的系列散文有二十余篇,构成了独具一格的文化长廊。这是一个文学家的文化长廊,不仅写人记事大多离不开文学,而且文笔优美,极具文学意味,如对晨光中波士顿的描写:“很早醒来,很美的窗外。看不到太阳,却看到缓缓升起的晨光。那是种令人神往的金色光芒,浸润着波士顿安宁的早晨。慢慢地,远远近近的建筑发出光来,浅浅淡淡地闪出太阳一般的明媚。而此时寂静的波士顿城,依旧沉睡在迷蒙的晨色中。”如此充满感情的描写在“文化随笔”中比比皆是。如果说赵玫的小说是情感的洪流中始终隐含着哲理的思辨,她的随笔则恰恰相反,以文化哲理的分析为主要内容,以绵延不断的真情实感为底蕴,更是一个女性文学家的文化长廊。一方面,在这文化长廊中女性占绝大多数,且位置突出,是为主要形象,她们当中不仅有乔治·桑、杜拉等著名的女作家,更有伍尔芙、波伏娃这样宗师级的女性主义者;另一方面,这些随笔中的确包含着大量极其深刻的女性主义思想。当然,赵玫或许根本就无意于作什么女性主义的阐释,至少“文化随笔”中几乎不见任何女性主义的专门术语,她只是站在女性的立场,以自己独特的洞察力,率真大胆地剖析两性社会的事理人情。只是,读者之心未必不然,特别是对像我这样“前理解”中主要是女性主义视角的所谓的研究者,读来处处都是女性主义思想,而且老实说,这些随笔有时候比那些正宗的女性主义理论文本更能给人以启发。比如赵玫对女作家乔治·桑和沃尔夫的解读。
乔治·桑的一生有过无数次恋情,历来的评论争议很大。赵玫则直率地认为,一个人能够爱许多次,正是强烈激情和强大生命力的象征,乔治·桑更是在情爱中创造了许多伟大的艺术家:“桑便成为这种可以爱很多次的那种人。而且很多次造就了伟人。她让她自己的爱的历程每一次都充满了光彩,她也让她爱过的那些男人每一次都不是一无所获。所以桑夫人不是别人。她是个十分了不起的女性。她能够爱很多次,而每一次都是饱满的,有质量的,充满了波澜起伏、悲欢离合的,也是孕育着伟大和不朽的。”在一个女性动辄被贴上“水性杨花”标签的男权社会,这种“女性的爱可以创造伟大男性”的观点多少还是有点惊世骇俗的,就算现在已经是21世纪。然而细想来,至少对于乔治·桑来说,也不无道理。在沃尔夫身上,赵玫则看到了“知识之美”:“伍尔芙是个美丽的女人。她美丽是因为有思想和知识在她的容貌中驻足。是因为她拥有着知识分子的烙印和立场。”这种美同样见于作为知识分子的波伏娃:“波伏瓦成为了这个最美的女人。她的美是深邃的,是以不停的思考为基础的。没有思考,就不会有波伏瓦脸上的那种独特的味道。无限探究的,那是种与知识和智慧相连的美丽。”“知识之美”或“智慧之美”的提法早已有之,在古希腊哲人柏拉图的美学体系中,智慧的美被置于最高的位置。只是,这种至高的美自古以来就属于男性,就算是在理性主导下的启蒙时期,在康德等美学大家的笔下,女性的美仍只是多少有些贬义的“秀美”,同“知识之美”毫不沾边。事实上,直到今天,又有多少人能够肯定女性的“知识之美”呢?而这不仅是当下女性主义理论的重要议题,也是普遍意义上的社会现实问题。
就女性主义思想来说,“文化随笔”中对波伏娃同萨特之间“伙伴契约”关系的解读真实而新颖,尤其能引发我的思考。众所周知,萨特和波伏娃这对情人曾“约法三章”:只恋爱,不结婚,不生儿育女,甚至也可以不同居,各人保有自己的住处。他们还十分认真地约定互相的性开放,不争风吃醋,亦不嫉妒。他们要求对方的是坦诚和信任,而不是感情的忠诚,尤其不是肉体的忠贞。这种“伙伴契约”关系一直为世人所津津乐道,被视为人类新型两性关系的典范。赵玫对两人之间的这种关系显然也是持肯定态度的:“他们身体力行的‘伙伴契约’难道不是爱的千古绝唱吗?否则为什么多少年过去,关于他们生命的传说总是历久不衰呢?”然而,创作过著名历史小说《武则天》的赵玫,对男权社会中女性无意识深处的悲凉和残忍有过深入的研究,这让她得以进入波伏娃的心灵深处,并读出了“伙伴契约”束缚下的女哲学家的苦楚。
波伏娃著名的小说《女宾》成为赵玫进入波伏娃内心世界的钥匙。《女宾》是波伏娃的处女作,发表于1943年,这时的她已是人到中年,“且已经拥有了她的哲学思想以及她与萨特共同的生活”。小说叙述的是一对情人出于同情接纳了一位年轻的女宾,三人约定和睦相处共同生活。然而,情感永远不可能像理性那样简单,男人喜欢上了女宾,女人出于妒忌,谋杀了女宾,小说在悲剧中结束。按照赵玫的阅读,这部小说几乎就是波伏娃“现实生活的真实的翻版”:“无论是其中的人物还是人物关系,甚至言谈话语、琐屑的细节。事实上《女宾》就是现实,而‘女宾’的原型也就是波伏瓦的学生奥尔加。”只不过,现实中的波伏娃和萨特历经漫漫五十年终得善果合葬一处,奥尔加等“女宾”们也获得了各自的归宿。但是,小说显然比世人眼中的现实生活更能反映波伏娃内心的真实。
赵玫一针见血地指出,《女宾》是波伏娃 “发泄和克制的产物”。在《武则天》的作者赵玫看来,《女宾》中的“三人家庭”同“古老中国的后宫和妻妾成群的家庭”并无二致,不过是改头换面的 “一夫多妻的把戏”:“那是封建社会最典型的特征和糟粕,却被西方的大师接纳了过来。”当然,波伏娃毕竟是现代“坚定的女权主义者”,她对“一夫多妻”的超越以及对新型伴侣关系的探求不可否认:“波伏瓦和她的‘女宾’们之间的关系,正在抵达女人们相互理解的那种超越了‘后宫’的境界。她们彼此努力关心对方,争取在心灵上做朋友。甚至做到在感情上理解对方的爱与恨,做到相互之间喜爱起来。”而更重要的是,波伏娃显然是在借这样的“酒杯”浇自己心中的块垒。《女宾》里在嫉妒中煎熬的“女人”正是波伏娃真实的写照。除却“哲学家”“女权主义者”等等这些华丽的外衣,波伏娃终究也还是个女人,是女人就会妒忌:“妒忌尽管不是一种美好的情感,但却也是人类的一种真实的情感,尤其对女人。而爱情也永远是排他性的。”萨特一生风流,拈花惹草无数,波伏娃严守两人之间的契约,并无半句怨言,但并不代表她不妒忌不痛苦:“波伏瓦还是嫉妒了。或者她不说,但心里的苦楚是存在的,并时时刻刻啃咬着她的心。那种疼痛的感觉她显然清楚。每当她得知她爱的男人被另一个女人所吸引,所诱惑,并放浪形骸,她这个前卫的女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痛苦(这和常人没有什么区别)。”不得不说,赵玫的这种解读非常“真实”。
而“真实”总是残酷的。其一,在现实社会中,男女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这是个由男性主导的社会,男人在各个方面都有着巨大的优势,而女人则始终处于从属的地位,纵使像波伏娃这样出类拔萃的女性也难免成为萨特的“附丽”,而这正是她的悲哀所在:“她毕生附丽于萨特。世间没有真正彻底的女权主义者。她们都只是在提醒你们。她们连自己都做不到。她们也毕生都在寻找着主人。寻找主人身上的父亲的或是君王的影子。想做那一束被管理起来的花。”这其实是男权文化中女性的必然命运。因此,萨特和波伏娃之间看似平等的“契约”恰恰并不平等:这契约对波伏娃是禁锢,对萨特则是自由——是可以随时拥有波伏娃同时又可以滥交的自由。两人之所以能够获得圆满结局,主要是因为波伏娃的隐忍包容:“她总是能忍辱负重地和那些成为萨特情人的女人相处得很好。她和她们一起喝酒,一起看戏,一起交友(很难说这是不是一种变相的自我摧残),是她的聪明、智慧、文化教养以及她的控制能力所使然,或者也因为她从来对自己充满了自信。”
可以说,萨特和波伏娃所倡导的看似公正平等的 “伙伴契约”关系,在男权社会中不过是由男性主导的游戏,只有近乎男性的女性或可赢得胜利。波伏娃的理智丝毫不逊色于男性,且还有着极高的名望。如果说连她都难免悲剧,那么对普通女性来说,更是不可能有好的结果。诗人顾城的妻子谢烨的悲惨结局就是典型的例子。顾城、谢烨和他的情人阿英之间组成了 “三人家庭”,共同生活在激流岛上。“这一次积极倡导 ‘三人家庭’的还是男人”,谢烨则同波伏娃一样宽容、隐忍,只是她没有波伏娃幸运,最终还是惨死在顾城的斧头之下。顾城是名满天下的诗人,而谢烨没有波伏娃那样的名望,她只是一个“无名的女人”,一个“单纯的女孩儿”,没有任何资本同顾城抗争,终落得个死于非命。《女宾》艺术地反映了波伏娃的苦楚,谢烨的悲剧则从现实的角度折射了普通女性的悲哀。在现实和文本的“互文”中,揭示的恰恰是美好爱情面纱下女性的悲剧性命运,一如波伏娃对安徒生浪漫的爱情故事《海的女儿》的解读:“女人,由于承担次要角色和完全接受依附,便为她们自己造就了一个地狱。每一个恋爱的女人都会把自己看作安徒生童话中的小美人鱼。为了爱,用自己的尾巴换来了女性的大腿,然后发现自己竟是行走在针尖和熊熊的炭火之上。”这就是残酷的“真实”,但显然难以为赵玫所接受。如果说之前出于对思想家萨特的尊重还只是隐忍不发的话,那么面对谢烨无辜的惨死,赵玫终于忍无可忍了:“童话的王国。伊甸园一般的。男耕女织。每个人都在涂抹的诗歌。创造着,虚幻的乌托邦式的生活。……所有的女人都想显示出她们是无私的。她们不在乎男人到底爬上了谁的床。唯有男人是自私者。他的全部目的就是得到。两种女人的两种爱。还有大同小异的两个女人的身体。他们是这种畸形关系的最大受益者。而女人得到的却是痛苦的锤炼。”这基于“真实”的控诉可谓笔力千钧。
其二,男女的“本质”不同。如果说男性是理性的动物,那么女性则是情感的动物。这种区别有生理上的原因——女性生儿育女,母爱是为本性,难免天生“多情”;也有后天社会选择的因素,毕竟数千年来社会对男女的定位有别:男人必须理智,而女人则是情感乃至情绪化的。理智与情感的矛盾由此也成为了社会最基本的矛盾之一。问题是,社会终究是由男性或曰理性主导的,情感终究要服从于理性,在两者的矛盾斗争中女性因而难免陷于悲剧之中。诚如赵玫的解读,从小说《女宾》到波伏娃、萨特,再到顾城、谢烨,在所有的“三人家庭”中,女人都为感情(哪怕是妒忌)所控制,真诚地爱着男人,为了对方幸福可以付出一切;相反男人却总是那么多情或无情,永远只想着自己的“自由”和“性福”。在两性关系中,女性总是比男性更容易为情所困,这也正是女性悲剧的根源之一。波伏娃是个“坚定的女权主义者”,她的《第二性》是现代女性主义奠基性的著作。她对两性关系的本质有着透彻的认识,且毕生都在为女性获得平等权利而奋斗,然而又能怎样?她终究还是女人,也难免为情所困,以至于她对塞西尔·索瓦热的话刻骨铭心:女人陷入情网时必须忘掉自己的人格。这是自然法则。女人没有主人就无法生存。没有主人,她就是一束散乱的花。这对一个“坚定的女权主义者”来说该是怎样的无奈!颇能说明问题的是,波伏娃并不孤独。事实上,西方历史上知名的女权主义者似乎都难逃情网,比如沃尔斯通克拉夫特。
1795年深秋的一个黄昏,细雨霏霏,天色阴冷。伦敦城外泰晤士河普特尼桥上一位年轻的女子纵身跳进了浑浊的河中。这个女子不是别人,正是被称为西方现代史上第一个女性主义哲学家的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她为丈夫伊姆雷(一个游戏人生的商人)所抛弃,情难自抑,决心投河自杀。而就在一年多前,她还疯狂地爱上了丑陋的画家福塞利,且尽管对方不过是逢场作戏,她却不能自拔,受尽了创伤。谁能想象,也就在三年前,她刚刚出版了影响深远的现代女性主义的开山之作《女权辩》。在这部伟大的著作中,她曾宣告:“我在这儿扔掉我的手套,反对所谓的性美德,也不在乎什么端庄贤淑。真理是,就我的理解来说,男人和女人必然是同等的。”可谓掷地有声,豪气干云!她坚信女人和男人有着同等的理性:“如果理性出自神性,是造物同造物主之间的纽带,那么它的本质对所有人都应该是相同的。”她对情感的危险性早有透彻的认识:“心灵极易背叛,如果我们没能控制住最初的情感,接下来也不可能阻止它为一些不可能的事情叹息。如果按照通常的方式,两人的结合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障碍,那么就要努力斩断任何危险的柔情,否则它不仅会毁掉你的快乐,还会把你骗上错误的道路。”然而,她非但没能控制住自己的情感,反而在“错误的道路”上飞蛾扑火般地冲向了死亡。为情所困的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完全没有了一个女权主义者应有的独立人格:福塞利娶了别的女子后,她不顾尊严地哀求福塞利和他的夫人允许她参加他们的家庭聚会,请求同他们住在一起;她的丈夫另觅新欢后,她也是恳求三人共同生活——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可谓现代“三人家庭”观念的创始人。历史何其相似,从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到波伏娃到谢烨,她们的悲剧并无二致。女性的理性终究没有男性强大,男性的情感终究不像女性那么强烈,虽说男女两性这种本质差异并不必然导致女性的悲剧,只不过在一个男权社会里就不可避免了。
“总之,”赵玫最后总结道,“男人们说,开始,便开始。他们说结束吧,便结束。甚至波伏瓦这样的倡导女权主义的女人也在劫难逃。这意味了什么?是的,平等的爱情远没有真正建立。要实现波伏瓦的理想还任重而道远。波伏瓦所描述的女人的痛苦至今犹存,这或者就是波伏瓦之于我们今天的意义。”颇多控诉的意味,也有说不出的无奈!而我想说的是,除非彻底改变男权社会,否则永远都不可能真正建立平等的爱情。这就是赵玫解读波伏娃给予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