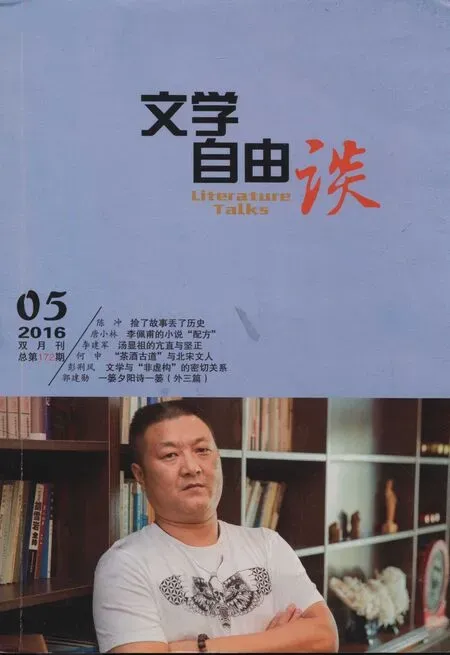我们的写作有如蜀道
2016-03-17周玉宁
□周玉宁
我们的写作有如蜀道
□周玉宁
前一段时间重读雨果的《悲惨世界》,忽然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受,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面对这些世界级的经典作家,我们当下的文学创作缺乏的究竟是什么?是语言技巧还是谋篇布局?笔者以为都不是。我们的写作缺乏的是这些经典大师那颗澎湃奔涌的灵魂、那种不顾一切的理想主义以及强烈的正义感和道德感。为何这样说?我们来看《悲惨世界》。
小说的第一部《芳汀》第一卷的标题是“一个正直的人”,一开篇,就将一个理想主义世界展现在读者面前。卞福汝主教带着一家人过着简朴的生活,他在最穷的教区宣道布教,将财物分给穷人,还对他们进行精神上的帮助。雨果认为,卞福汝这样的人才是正直的人。《悲惨世界》的故事背景发生在法国大革命前后,正是因为看到了太多的底层苦难,郁结在胸,希冀自己理想的社会形态在法国出现,雨果才会写下卞福汝这个形象。卞福汝实际上是一个圣人;普通人或许会有他身上的某种特质,而全部特质只能被雨果笔下的这个理想人物所有。雨果之所以在小说开篇就急急推出他,实际上是在说,这个社会太需要像卞福汝这样的人了。他是用这个人物揭示大革命前后的法国社会上层人物的贪腐,用这个人物警醒他们,也为苦难的底层民众增加一线希望。小说所述完全是一个理想主义的社会模式。雨果在小说的开篇就把这个社会模式推向了读者,正是一种急于表达自己理想社会图景和理想人物的迫切感。
通过接下来出现的主要人物——冉·阿让、芳汀、珂赛特,雨果写了一个施爱与拯救的故事;这是卞福汝式理想主义的一个实施个例。作者安排冉·阿让做这件事,是在表述这样一种观念:如果给这些底层民众机会,他们也可以做市长,可以成为有良心和充满理想主义的上等人,也能进行拯救与施爱。冉·阿让的工厂也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模式,让所有穷人高兴的模式;这是卞福汝理想主义的延续与发展,也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冉·阿让能成为马德兰市长,开办工厂,实际上都是雨果的理想主义与施爱心理的表达。这是一种直抒胸臆的浪漫主义写法,并不是仅仅凭谋篇布局就能结构的。通过芳汀和珂赛特母女这些人物所叙述的拯救故事,我们同样看到了作者通过冉·阿让所体现的人们所应该具有的善良和同情心,以及正直、正派。
《悲惨世界》以小说的方式,描述了法国大革命前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历史。它既是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也是现实主义的。小说对法国社会现状的描述,是那样的真实;芳汀母女、各种主义的革命者、各种各样的底层人物,又具有很强的煽情力量,让人感觉到作者奔涌的灵魂、热烈的救世思想,以及强烈的情感。
《悲惨世界》有结构有情节,但这不是主要的。它是一种激情的抒发,是随着激情而书写的鸿篇巨制,仅仅凭写作技巧很难驾驭。而我们当下的创作问题就出在这里:所有的问题都指向了写作技巧,很多写作都走向了炫技,写作的灵魂问题却不再有人提及,文学究竟是什么也不再有人讨论。文学作品应该用什么来感染人、影响人?其实,作家的感情、立场甚至灵魂,任凭你用多么高超的写作技巧遮掩、矫饰,都会暴露在自己的作品中。就此而言,写作是一种非常残忍的职业:一切都暴露无遗,是非纷争也常常纠缠不已,读者又不停歇地在“拷问灵魂”,而他们的要求和口味又这么高……这足以让很多作家疲惫不堪。但是,作家们也该想想,面对那么多的名篇巨著,读者为什么偏偏要读你的作品?如果你连理想的世界和震撼心灵的人物、故事都不能描绘给他们,你还有什么办法拦住他们弃你而去的脚步?
当下的问题是,我们很多作品站得并不比读者高多少,而真性情、真感情等属于灵魂的东西又都吝啬地隐藏着。我们的作品没有感情、没有血肉,也没有灵魂,很多甚至都没有正义感。文学的边缘化说了很多年,仅仅从社会去寻找原因并不能触动内在的改变。当然,写作技巧也是很重要的;说《悲惨世界》是灵魂之作,并非说它无技巧,而是说它的技巧已经融合在激情与理想之中,属于大师的杰构,我们可以从各个角度去欣赏它。我们的问题主要还是出在理想与情感上,如果作家自身的情感卑琐了,写出来的作品也就会被抛弃了。作家的写作是要引领读者思考的,必须站得高一点。如果说写作是一种职业,那么这种职业的特点,就是要求作家有很高的知识修养和道德情感,而这两项就很折磨人:知识修养不仅仅是读书就行,还要读通;道德情感的要求更是把人常常往火上烤。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写作可真不是个好干的行当,从业者不仅仅要面对自己的同行,也要面对古今中外的前辈和后辈。想到这里,我们不得不像李白一样发出一句“危乎高哉”的感叹:我们的写作,确实如蜀道,“难于上青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