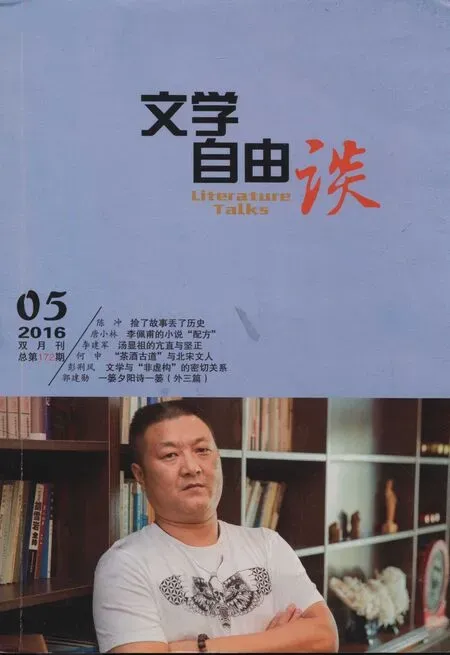李佩甫的小说“配方”
2016-03-17唐小林
□唐小林
李佩甫的小说“配方”
□唐小林
在未获得“茅奖”之前,李佩甫在当代文坛,也算得上是一位颇有影响的当红作家,但尽管如此,我却从未读过他的任何只言片语。我对李佩甫的认知,完全来自于媒体的高度赞扬和圈内的如潮好评,如有学者高度赞扬他的《羊的门》:“是一部改变了五十年来中国乡农文学面貌的作品,一部前所未有地演绎和再现了特定时代风貌和特质的作品,一部对于当代中国史有着社会百科全书意义的作品。”面对这样惊人的评价,好长一段时间,我都在为没有读过李佩甫如此优秀的小说而自责和感到遗憾;我总是担心,因为我狭窄的阅读视野,错过了我们这个时代一位优秀的作家。当李佩甫的长篇小说《生命册》获得“茅奖”之后,我立即买来了此书,以弥补我曾经的“过失”。但读完这部鲜花云集、满身光环的小说,我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难道是我的文学鉴赏和审美眼光出了问题?众多的专家和学者都盛赞李佩甫,作为乡土叙事的卓有成就的实力派作家,其《生命册》有着厚实的根基,浓郁的乡土气息,语言硬实,具有不可低估的分量;而何以我的鉴赏和理解能力,却完全跟不上专家们的脚步,怎么也看不出这部获得“茅奖”的小说究竟“经典”在何处?
2016年这个炎热的夏天,我决心要为心中的疑问找到一个能够说服自己的答案,给自己一个确切的交代。我在深圳火炉般的酷暑中,用了大量的时间,读完了李佩甫被书商和文学批评家们称为“经典”的多部长篇小说和主要中短篇小说,从而获得了冰窟般的“凉爽”感受——我清晰地看到了一个当代作家是怎样自我复制,追寻着一条工业化生产的写作之路的。如:
他(某省委副书记)说:“我一生曾遭遇过六个女人,这六个女人是各有千秋哇。头一个女人,让我懂得了眉毛。从她那里,我才知道人的眉毛是干什么用的。眉毛这东西,可不光是眼的帘子,它的妙用主要在性上,眉毛其实是一种性器官,它就跟花的蕊一样,是性欲的外在反应。你如果稍加注意的话,你就会发现,人的眉毛是千姿百态的。眉毛的形态跟人的性形态是一致的。尤其是女人。女人的外‘好’看脸蛋,女人的内‘好’看眉毛。别笑。女人媚在眉上,柔也在眉上,荡也在眉上,寡也在眉上。床上功夫好不好一看眉就知道了。……凡是结过婚的女人,有过第一夜之后,她的变化首先反映在眉毛上。”(《羊的门》)
邹志刚悄悄对她说:“看他们在那儿胡吹,我也就凑个数。说实话,关于说她有男朋友,我是从眉毛上看出的。眉毛就像花蕊一样,是人的生理器官,也可以说是性器官。年轻女孩,只要跟人发生过性关系,她的生理就会发生变化,眉毛也跟着必定会发生变化……”(《等等灵魂》)
诚如法国文学批评家纳塔丽·萨罗特所说:“自从 《欧也妮·葛朗台》全盛时期以来,同样的内容像过分咀嚼以后的食物一样,对读者来说,已变得糊烂如糜而且淡而无味了。运用这样的材料所塑造的客体,在今天看来,已显得是像那逼真模拟的画幅一样,看上去是立体的,事实上是平面的。”李佩甫的小说,恰恰正是“看上去是立体的,事实上是平面的”。其小说中的许多人物,都像是被作者任意操纵的提线木偶,缺少血肉和灵魂。只要将这些小说做一比较,我们就会发现,李佩甫就像是开设了一个“小说作坊”,这些小说的主料,一律都是书写欲望的膨胀,其“配方”无非官场文学(脸厚皮黑+勾心斗角)、商场文学(明争暗斗+你死我活)、情场文学(脐下三寸+权钱交易)这类市场上司空见惯的工业组装品,无怪乎《羊的门》和《城的灯》在再版时,分别被改成商业气息非常浓厚的《通天人物》和《上流人物》这样的名字。这两部小说和李佩甫的《生命册》一起,被称作“平原三部曲”。但无论是“平原三部曲”也好,还是《等等灵魂》、《金屋》和《李氏家族》也好,这些长篇小说万变不离其宗,讲述的都是农村人如何摆脱农村和贫瘠的土地、欲望膨胀、寡廉鲜耻、拼命攀爬、损人利己的故事,框架都大体相似,人物更是有着高度的重复性。
李佩甫的小说动辄喜欢拿有生理缺陷的人来说事,残疾人往往多如牛毛。《生命册》中的男主人公骆国栋,因为天生就是一个“罗锅”,所以被人们称为“骆驼”,女主人公虫嫂天生就是一个侏儒;《城的灯》中的主人公冯家昌,十二岁那年,母亲因病不幸去世,其从外乡入赘而来的父亲,因为拉扯着五个幼小的孩子,没过多久就贫病交加,成了一个罗锅;《金屋》中,小时候穷得长年没有裤子穿的杨如意,其继父也是一个罗锅;《羊的门》中,运来的父亲德顺,同样因为积劳成疾,变成了罗锅;《春满荷花》中的老搬运工,居然也是一个罗锅……
除了罗锅扎堆之外,还有一些被描写成歪瓜裂枣的残疾人。《红蚂蚱绿蚂蚱》中的舅舅是一个瞎子;《城的灯》中的女主人公刘汉香的父亲刘国豆满脸都是麻子;《麻雀在开会》中的表姐一岁多丧父母,幼儿时因发高烧成了“聋子”;《黑蜻蜓》中的二姐,照样是一岁没爹,两岁没娘,三岁发烧,烧成了聋子;《寂寞许由》中的“五爷”是麻子,“老三”不仅是个瘸子,而且走路就像划船一般,一悠一飘的;《羊的门》中带领当地人造假贩假的蔡先生,是小时候爬树摔下来成了瘸子的;虫嫂的丈夫老拐,也是一个瘸子,在和虫嫂做爱时很不给力;《生命册》中的老光棍,年轻时就成了独眼龙……
说脏话的人也出奇的多——李佩甫笔下的中原地区,仿佛就是一个脏话的世界。不管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人们一张嘴,出口就是脏话,不仅是村支书,甚至连市长对自己的下属讲话也照样是满嘴污言秽语:“薛市长一拍桌子,黑着脸说:‘我告诉你们,谁影响招商引资,我撤他的职!也别给我这这那那、长毛短,就现在,现场办公!……’”“薛市长脸一沉:‘你慌个,又不是割你肉?你听我说。你听清楚再说。我说的是借!只借一天。’”至于农民说话,简直是须臾都离不开脏话,仿佛不说脏话,他们就不会说话。可以说,“”字已经成了李佩甫小说中人物的口头禅和标志性语言。
在李佩甫笔下,村民们似乎把偷当成了一种职业,张三偷李四,李四偷王五,王五偷赵七,赵七偷黄八。农民为了防止家里的猪被偷,一律都是在猪圈里守着猪睡觉;虫嫂见什么就偷什么,一亩地的西瓜被她几乎偷去了一小半,而且在偷窃被抓时,居然公开拿性来和抓住自己的老光棍做交易。而就是在这偷盗成风的村庄中,却不断上演着一部又一部咸鱼翻身、乌鸦变凤凰的神奇故事。
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几乎套用的都是董永遇到七仙女的故事模式:穷得喝西北风的农村男青年,一律都是学习的天才,个个都会交上桃花运,遇到一个心仪自己的当官的女儿;这些当官的女儿,一股脑都像是脑子进水一样,必定都会莫名其妙、死心塌地地爱上他们,并且毅然地将自己的身体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他们,从而使他们在时代的大潮中,上演出一幕幕惊人的大戏。
然而,这一幕幕的大戏,却让我在观看之时常常忍不住“笑场”。在当代作家的小说中,我很少能接二连三地看到如此之多低估读者智商的故事。在《城的灯》中,罗锅来顺年轻时就失去了妻子,一个人含辛茹苦地拉扯着五个年幼无知的孩子。其中最大的儿子冯家昌,成为了家中唯一识字的人。冯家昌十二岁的时候死了母亲,如此贫困的家庭环境,根本就没有上学的条件,他却在没有上过几天学的情况下,居然成了一个学霸,不仅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镇上的中学,而且还赢得了村支书刘国豆的女儿刘汉香的芳心。不久,冯家昌就将刘汉香生米煮成了熟饭,使本来看不起他的刘国豆颜面尽失,而刘汉香就像是吃错了药一样,爱他爱得死心塌地,十条牯牛也拉不回头。刘国豆只得退而求其次,想办法将冯家昌送进部队,希望他能够在部队立功受奖,将女儿带到部队。到了部队后,冯家昌成为了一名令人羡慕的文职人员,并被首长的侄女李冬冬一见钟情。
我不知道,李佩甫究竟凭了什么魔法,使人相信接下来的情节不是天方夜谭?李冬冬的母亲是一位医生,父亲是一位市长。冯家昌在部队八年没有回家探过一次亲,而李冬冬的父母居然在丝毫都不了解他的家庭状况的情况下,就稀里糊涂地将宝贝女儿嫁给了冯家昌。这种不合常理的事情,在李佩甫的小说中,却成了一再出现的“常态”。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冯家昌的遥控指挥下,冯家的几个兄弟仿佛个个都有一颗“最强大脑”,尽管从来就没有上过几天学,居然都能够无师自通,最终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老三冯家运,通过冯家昌的关系来到部队当兵,在新疆一个荒无人烟的哨所,凭着冯家昌带来的一些书,从ABC开始学起,不久就考上了陆军学院,并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硕士学位。多年以后,冯家昌成了副厅级干部,老二冯家兴成了地级市的公安局长,老三冯家运成了驻外武官,老五冯家福成了一家民营公司的董事长,资产过亿。而刘汉香一直居住在冯家,八年未与冯家昌见过面,冯家昌升为团级干部前也从未给她寄过一分半文——我不知道,刘汉香及其家人的智商是否正常?据我所知,部队一年至少有一次探亲假,冯家昌八年不回家,别说是“守活寡”的刘汉香及其父母,就连部队首长和战友,也必然会怀疑这其中一定有问题,更不要说李冬冬的市长父亲了。
再来看《生命册》中的另一则“天方夜谭”。虫嫂作为一个侏儒,在村里的名声坏到了极点,却为残疾的老拐生下了大国、二国和三花三个孩子。大国不爱读书,十岁多的时候,就爬上火车,一跑就是三天,说是要去乌鲁木齐,结果被警察给扣住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太阳却从西边出来了,大国突然爱上了读书,考上师范,还被一位女同学莫名其妙地爱上了。这位女同学的父亲是县教育局的一名副局长。就像《城的灯》里的冯家昌一样,大国结婚,同样没有告诉家里人。而作为教育局副局长的老岳父,怎么同样是对女婿及其家庭情况不闻不问?之后,二国和三花也都考上了大学,成了村里人无不夸奖和羡慕的一家人。
运用这套写作模式,李佩甫制作出了许多来料加工、如出一辙的面孔。在《羊的门》中,冯家昌因为家里穷,买不起作业本,作业本全是烟盒做的。而《败节草》里的李金魁,同样是因为穷,在六年的时间里,用掉了一万八千多张烟盒纸。和冯家昌和大国一样,有结巴毛病的李金魁,同样是“理所当然”地交上了桃花运,遇到了暗中爱上自己的李红叶。李红叶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还有一个当校长的父亲——在李佩甫的小说中,似乎所有当官的女儿都像三伏天快死的鱼,生怕没人要——为了能够赢得李金魁的“爱情”,李红叶甚至不惜为他脱掉裤子,把整个身子都赶紧交给了他。在彻底征服李红叶之后,李金魁进一步时来运转。李红叶的父亲升迁为市领导,李红叶利用父亲的关系,亲自将一张上大学的推荐表送到了正在废品收购站靠捡垃圾为生的李金魁的手中,而大学毕业后的李金魁,居然从副乡长一路做到市长。《无边无际的早餐》中的治国,平时成绩也不怎么样,但中考时,大李庄小学有六十四个学生参加了考试,却只有治国一个人考上。之后因为读书,治国的人生一路绿灯,从乡里调到县里,并经由县委书记亲自做媒,和一位副市级干部的女儿结了婚,最终攀上了县长的位置。
在当代文坛,自我复制的作家,可说是不少,但像李佩甫这样毫不掩饰地自我复制、不少作品近乎雷同的作家,即便是在古今中外的文坛上,恐怕都不多见。吊诡的是,李佩甫却煞有介事地宣称:“我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写作,至今写了38年,总共写了10部长篇。从80年代以后,我就找到了自己的写作领地,无论是《羊的门》、《城的灯》还是《生命册》,都是一个共同的主题:土地和植物的对话。”在我看来,如果真要说李佩甫找到了什么“自己的写作领地”的话,这个“领地”的名字就叫做:不断重复自己。
在李佩甫的小说中,只要写到农民的野心和炫耀自己,必定是建一座令人人都羡慕不已的大房子。《生命册》里的蔡苇香,在城市里做小姐,后来成为一家板材公司的老总,发达之后回到村里,仅用十几天时间便盖起一座三层小楼,而且里外都贴了瓷片,让全村人羡慕不已。《金屋》里的杨如意,从小失去父亲,之后又失去母亲,靠跟着罗锅继父来顺艰难度日,外出几年后,居然成为了一家涂料厂的老板,回到村里建起了一座二十四间的现代化小洋楼。《等等灵魂》中的暴发户商人任秋风,居然大脑膨胀,发誓要在中原建造世界第一高楼。
《寂寞许由》中的老郭,讨好市长,用新鲜的婴儿胎盘烘干,给市长配了一味药。在《羊的门》中,李佩甫又将这个“桥段”进一步升级和改装,就成了给公社书记当通讯员的王华欣,为了讨好书记,天天晚上主动给书记提夜壶;为了巴结院长,就到刑场上去挖活人脑子,用来治院长孩子的病;为了进一步得到提升,利用老婆在医院产科的工作之便,将烘干的“婴儿胎盘”当作大补品送给领导。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李佩甫采用了一种快餐制作的生产模式,无论是故事的结构,还是人物的设置,以及情节的展开,几乎都如同一个模具里浇注成型的工业产品,没有什么区别。
李佩甫小说中的许多人物,都是苦水里出生,从小就死了父母,靠吃百家奶长大的。这些靠乡村妇女的奶水辛勤养大的人,非但不知道感恩,反而从小就知道怎样调戏和意淫这些辛勤养育自己的乡村妇女。《无边无际的早晨》中的治国,在襁褓中,娘就因病去世,七天之后,他的爹又在挖煤时被砸死在井下,从此成了吃百家奶的孩子。多年以后,他对人吹嘘说,他摸过一百多个女人的奶子,并常常回忆起吃奶时的情景。那些裸露着的乡下女人的奶子,经过他想象的渲染,一个个肥满丰腴地出现在他的眼前。《金屋》里的来来,母亲生他时,在床上折腾了七天,也是由他的父亲抱着,一家一家求奶吃。《生命册》中的吴志鹏,从小就失去了父母,同样也是吃百家奶长大的,他居然还无耻地炫耀说:“在我的记忆里,无梁女人高大无比,屁股肥厚圆润,活色生香。……站在石磙上碾篾子的女人,屁股都是紧绷着的,就像是一匹匹行进中的战马,一张张弹棉花的张弓,捏一下软中带硬、极富弹性,回弹时竟有丝竹之声。那时候,在初升太阳的阳光下,我会沿着村街一路捏下去,捏得女人哇哇乱叫‘吃凉粉儿’。我也承认,我还曾经摸过无梁大多数女人的乳房。在这个世界上,毫不夸张地说,我是见识乳房最多的男人。”接下来,他还逐一点评着国胜家女人、紫成家女人、宝祥家女人、三画家女人、海林家女人、印家女人、水桥家女人、麦勤家女人、大原嫂子、宽家女人的乳房,并称:“女人跟女人是不一样的。”看到这样的描写,我就可以肯定李佩甫是一个缺乏科学常识的人。请问,这个世界上,谁能记起自己小时候吃奶的情景?科学告诉我们,一个人的记忆是从三岁以后才开始形成的。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居然能够分清谁的奶子像歪把茄子,谁的乳头润着一片麻点点……这样缺乏常识的描写,如何能让读者信服。
事实上,在李佩甫不经意的写作中,已经暴露出了其方方面面知识的欠缺。如:“上海人说话侬来侬去,办事小里小气。他们尤其对上海人印象不好。上海人不是斤斤计较,简直是两两计较……”(《等等灵魂》)“你想,做的是小买卖,本太小,利太薄,自然是‘两两计较’了。”(《羊的门》)汉语成语“斤斤计较”里的“斤斤”,出自《诗经·周颂·执竞》:“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它指的是明察、看得清,引申为苛细、琐屑。除此之外,汉语成语还有“斤斤较量”,同样是指在琐细的事情上过于计较。这里的“斤斤”,与表示重量的单位没有丝毫关系。《城的灯》中的老二冯家运,仅仅读了六年军校,拿到一个硕士文凭,一出校门就被破格授予少校军衔,作为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武官,成了住南美国家的一个使节。李佩甫对我国驻外武官的要求,可说是连基本常识都不求甚解。我国的驻外武官,是由中央军委责成总参外事局,从全军优秀现役军官中选拔出来的,一般都是上校甚至少将以上的军衔,哪里会将一个不符合基本条件的冯家运派驻到南美代表国家?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等等灵魂》中,一睡觉就打呼噜的任秋风,入伍后干的是侦察兵,并且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在我看来,部队的首长也是够粗心的,他们怎么会将一个睡觉打呼噜的人安排去搞侦察?《金屋》中的独根四岁,哥哥五岁,姐姐六岁。哥哥在坑塘边洗豆芽,不小心滑进塘里,一群小孩,只有独根的姐姐慌忙去拉,结果被哥哥死死抓住,一起沉到了水中。待小孩们回家告诉大人,来到坑塘时,姐弟俩的尸体已经白胀胀地在水面漂着,姐姐的小手还死死勾住弟弟的手。李佩甫并不知道,人被淹死之后,是不可能立即就浮起来的。人在淹死停止呼吸之后,由于体内的密度大约和水的相等,所以尸体就会沉入水底。随着尸体逐渐产生越来越多的腐败气体,才会浮出水面,这个过程通常要三天以上。
文学批评家们痛感当今某些作家只讲高产,不讲质量。李佩甫也算得上高产,但这样的高产,往往都是一种为了写作而写作的文字堆积。尤其令我感到吃惊的是,他的长篇小说《李氏家族》完全就是由其过去的几个中短篇小说改写、拼凑、混搭而成的一部所谓的“新作”。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在李佩甫的小说中,各种与性有关的段子和噱头就像走马灯一样,不断出现。《李氏家族》中的嬴,阳物大得出奇,他甚至将自己的阳物裸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一甩一甩地在村里走。每当嬴从街上走过,连母羊也开始发情,跟在他的后边。他抛弃了跟他逃过难的女人,强行霸占了漂亮的堂姑。嬴走到哪里,就让堂姑跟到哪里,像公狼和母狼一样随处交欢。于是,村里成了乱伦的世界,哥哥与妹妹,叔子与嫂子,母亲和儿子,人人都像畜生一样。被嬴抛弃的女人却誓死都要复仇,终于有一天,她跟踪到了嬴,怀着满腔的仇恨,比母狼还要凶狠地将嬴拽到了茅屋里,将嬴的阳物血淋淋地割了下来,嬴最终惨死。然而,这个女人却不仅将其阳物珍藏起来,而且每到嬴的祭日,还会将珍藏的阳物请出来,摆在供桌前恭恭敬敬地磕头,似乎是有了这个阳物,她就有了精神支柱。看了这样的描写,我们不得不说,当今的作家在性描写方面,实在是太有才了,即便是兰陵笑笑生再世,也会自叹不如。
李佩甫的《等等灵魂》被出版商飙捧为“传世经典”,并宣称读这样融合了丰富系统人文知识的小说,会让读者充满阅读的乐趣,成为汲取知识的智慧之旅。但我在拜读了这部长篇小说之后,非但没有汲取到知识的智慧,反而看到了一部草率之作是如何的漏洞百出。小说的主人公任秋风,就像《城的灯》里的冯家昌一样,在部队十二年,就从一个士兵干到了副团职。他的妻子在他转业回家的当天,与商场老板邹志刚发生了婚外情——她这样一位头脑聪明、有头有脸的报社首席记者,十二年漫长的日子都等了,却何以非得要在丈夫回家的这一天出轨不可?任秋风在部队这么多年,从来就没有干过任何一件与商业有关的事情,市领导就敢把一个大型商场交给他管理,而他也一夜之间就成了一位商业奇才;更为蹊跷的是,三位商学院毕业的女大学生竟然莫名其妙、心甘情愿地到他那八字都还没有一撇的商场来工作,甚至站柜台。任秋风凭着我们常在报刊杂志上看到的那些并不高明的商战故事,就成为了闻名中原乃至全国的商业巨头——如此小儿科的商战小说,几乎就是弱智的代名词。我们看到,《等等灵魂》中的任秋风,就像《生命册》中的罗锅骆国栋一样,虽然从未经过商,却是经商的天才,手里动辄控制着多少个亿的资金,且生钱的速度简直超过了印钞机,乃至人人都对他们崇拜得五体投地。尤其是那些年轻漂亮的女人们,更是争先恐后,个个都恨不得以身相许。出生在条件优越、很有教养的家庭的上官云霓,在明知道任秋风还没有离婚的情况下,就主动投怀送抱,挑逗勾引。小说中写道:“这一刻,在上官,是没有羞耻感的,她心中升起的是一种圣洁。”我不知道,上官云霓究竟被什么邪教洗了脑,简直不知道世界上有羞耻二字,居然把寡廉鲜耻当成了圣洁。在李佩甫的笔下,那些成功的男人就像种猪配种一样,随时都可以不分时间、地点地发情。难怪李佩甫的小说中听起来最爽,且屡屡出现的一个字,就是男人对女人的一声令下:脱!
更抓人眼球的是,长篇小说《羊的门》中,在呼风唤雨的通天人物呼天成六十大寿时,村子里清纯美丽的小雪儿代表母亲前来祝寿:“我妈说,今天是您的生日,是您的六十大寿,让我给您送礼来了。”这份大礼,就是少女宝贵的贞操。总之,把宝贵的身体送给那些所谓成功的男人,几乎成了李佩甫小说中所有女人的梦想。难怪小说中议论说,什么叫做“献身”?这才是“献身”哪!我想请教李佩甫的是,世界上有什么样的大恩大德,永永远远都报答不完,用尽了母亲的身体,还要让女儿心甘情愿地用贞操来偿还?如果真有这样的母亲,那简直就是禽兽不如。
因为构思粗疏,写作仓促,李佩甫的小说常常丢三忘四,总是犯迷糊,呈现出一种漏洞百出、自相矛盾的叙述。我国法定的征兵年龄,应该是年满18岁的青年。《等等灵魂》中的任秋风,并非有什么特长,却在16岁就入了伍。16岁当兵,在部队十二年,1990年转业,这说明他转业时的实际年龄只能是28岁。任秋风转业后,李佩甫写道:“转眼近二十年过去了,他仍然还记得齐康明的发问……是啊,他已过了而立之年。”28岁怎么就已经过了而立之年?当兵十二年,怎么就成了将近二十年?这中间几年的“亏空”怎么填补?又如,在《学习微笑》中,马科长等人晚上九点钟到卡拉OK厅K歌,一直唱到凌晨两点半,歌已唱到了374首——请李佩甫掰着指头认真算一算,九点到凌晨两点半,一共是多少个小时?以一首歌平均三分钟计算,而且K歌的人一秒钟也不要停顿,五个半小时最多能唱多少首歌?这样简单的加减法,李佩甫在写作时难道只是为了赶速度,就没有一点耐心去仔细算一算吗?由此,我们还能相信,他的创作有什么真正的思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