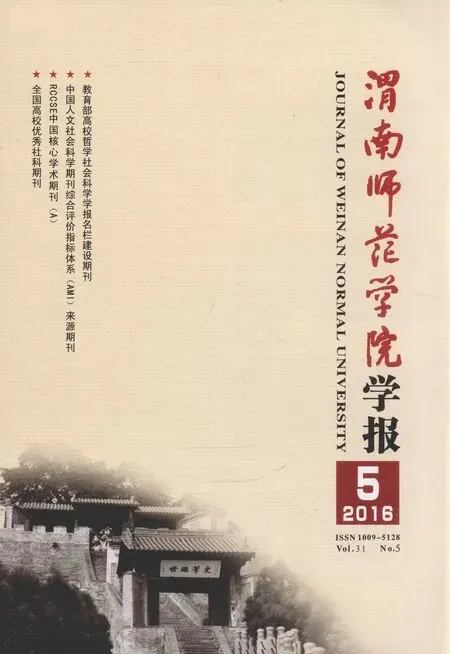论《史记》与《汉书》选录游侠形象的错位——兼谈太史公和班固的史学思想差异
2016-03-16严振南
严 振 南
(广西民族大学 文学院,南宁 530000)
论《史记》与《汉书》选录游侠形象的错位——兼谈太史公和班固的史学思想差异
严 振 南
(广西民族大学 文学院,南宁 530000)
摘要:太史公将道义之游侠视为正义力量的象征,是对国家正义缺位的一种补充。太史公期待一种异质力量的介入,去打破森严的封建统治秩序,来维护社会正义。游侠“以武犯禁”的特征,让其成为主流权力之外最佳的正义执行者。太史公从维护个体生命层面出发,强调游侠敢于犯禁,救人于困厄的侠义精神。班固从国家君主立场出发,有意混淆豪暴之侠与道义之侠,力在突出侠的暴力凶杀的特征,消解侠济危救困的品格,目的在于抑侠。
关键词:游侠;道义;豪暴之侠;抑侠
“侠”产生于春秋战国,兴盛于西汉,伴随着“侠”的大量出现,太史公、班固、荀悦、许慎等人专门对 “侠”的身份进行诠释。西汉时期,太史公始为“侠”正名,其在《史记》一书中首为“游侠”立传,太史公把“道义”作为衡量“侠”的重要标准,对“侠”的身份进行重新界定,并将“游侠”视为侠精神的最佳承担者,“游侠”是“侠”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游侠”的记载,韩非子在《五蠹》中称:
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简其业,而游学者日众,是世之所以乱也。[1]478-479
韩非子将游侠和私剑并举,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游侠和私剑是不同的群体,他们是“侠”的重要组成部分。韩非子在抨击“侠”以武犯禁时,常用的代称是“私剑”“带剑者”,将批评的矛头直接对准的是“私剑”而非“游侠”,“游侠”并非“以武犯禁”“行剑攻杀”的主体,“私剑”才是。《韩非子》一书是从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的立场出发,论述君主该如何治理臣民、管理国家,实现富国强兵,对各种违法犯禁有损国家君主权威的行为进行抨击,韩非子并未将“游侠”直接列为抨击对象。游侠处世方式相对温和,不像“行剑攻杀”的私剑一样暴力。正是因为“游侠”这一群体非暴力性的隐形存在方式,非像私剑行为一样激进,并未过多地引起著述者注意,所以在先秦时期的文献典籍中少有记载,因此太史公在《史记·游侠列传》中称:“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2]3183
只有进一步廓清私剑和游侠二者之间在身份上的差异,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侠”群体,把握“侠”群体的行为特征和精神内涵。陈光宏在《关于中国早期历史上游侠身份的重新检讨》一文中,论述游侠与私剑的关系时称:“一个世纪以来人们所持有的对游侠的一般认识,正是在混淆了游侠与‘私剑’之概念的前提下作出的判定与描述,无论是赋予它游士的特征、门客的特征还是武士的特征,实际上都是将‘私剑’的种种特质加诸游侠之身,或者至少是将游侠与“私剑”的特质杂糅在了一起。”[3]122
一、《史记》道义之侠:个体生命的道义担当
“游”本义是旌旗之上的流苏,在《周礼》中是礼制的象征,诸侯卿大夫身份等级和旌旗之上“游”的数量密切相关,“游”是血缘宗法制度下诸侯卿大夫身份尊卑的重要标志。《说文解字》释:“游,旌旗之流也。旗之游如水之流。故得称流也。大常十有二游,旂九游,旟七游,旗六游,旐四游,周礼。王建大常,十有二游;上公建旂,九游;侯伯七游,子男五游,孤卿建旃,大夫士建物,其游各视其命之数。”“游”是宗族血缘制度下等级关系直接体现。然而,随着王权衰落,井田制瓦解,人们开始脱离血缘和土地的束缚,“游”从象征固定等级变成象征游离状态。
(一)游侠社会状态和心理状态的游离性表现
“游侠”常处于一种游离状态,这种状态表现为:第一,游侠在行为上的“不轨于正义”,是正统君主权威之外的一种异质力量,游走在正义与非正义之间,是被边缘化的群体,不为时人认可,“儒墨皆排摈不载”,故“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2]3183(《史记·游侠列传》);第二,“游侠”在行为准则上的摇摆,李欧在《论原型意象——“侠”的三层面》一文中提到:“‘游’是侠的一种生命构成,这不仅仅是指地理位置的移动,而且也是指行事准则的摇摆,在儒道之间,入世或出世,有所必为与明哲保身,极端利他与极端利己。”[4]44从处境到行为准则,游侠都处于一种游离状态,这种游离性对宗法制度下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形成了一定冲击,正如王学泰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中提到:那种有周天子按照血缘远近从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到庶民安排好的等级制度已经基本上瓦解,宗子与君主合一的宗法国家也不复存在。
(二)朱家、剧孟理想化游侠形象,游侠侠义精神典范代表
最早对“游侠”形象和游侠特征进行记叙和总结的是太史公。太史公在《史记·游侠列传》称:“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2]3181从太史公对游侠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游侠的基本精神品格:一是重诺言,尚践行;二是勇武果敢,具有献身精神和利他精神;三是锄强扶弱,救危救难,具有仁爱之心;四是不自夸,具有谦逊的品格。太史公对“游侠”品格的定性,多建立在汉兴以来,对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等人进行总结的基础上。
关于朱家“游侠”行为,《史记·游侠列传》中记载:“鲁朱家者,与高祖同时。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侠闻”,在儒家思想兴盛的鲁国,朱家却凭借“侠”名著称于世,朱家的这种侠义行为,深受春秋战国以来社会中所形成的尚武任侠风气影响,朱家“所藏活豪士以百数”的行为与《韩非子》中任誉之士的“活贼匿奸”行为相同,然而朱家施恩却不谋求名誉和回报,“不伐其能,歆其德,诸所尝施,唯恐见之”[2]3184。季布在楚汉之争中因助项羽而得罪高祖,“高祖购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2]2729,朱家仍藏匿季布,并借滕公之力向高祖求情,于是“上乃赦季布……上拜为郎中”[2]2730(《史记·季布栾布列传》),然而,朱家却功成不居,不复与季布相见,《史记·游侠列传》载:“既阴脱季布将军之阸,及布尊贵,终身不见也。”[2]3184朱家还乐善好施,面对贫困者常慷慨解囊,朱家“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慷慨施恩于他人,对自己却十分严格“衣不完采,食不重味”。朱家的游侠行为明显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是“侠”与“儒”的结合,儒家思想进入侠的精神层面,规范和指引“侠”的行为。
与朱家相类似的游侠是剧孟,以任侠而显名于诸侯,曾任楚相的袁盎都以宾客之礼接待剧孟,《史记·袁盎晁错列传》载:“洛阳剧孟尝过袁盎,盎善待之。”[2]2744剧孟为时人仰慕,皆源于其侠行,“剧孟母死,自远方送丧盖千乘”[2]3184(《史记·游侠列传》)。剧孟之所以能为诸侯卿相敬重,皆因其“缓人之所急”的任侠品格,袁盎称赞剧孟曰:“且缓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门,不以亲为解,不以存亡为辞,天下所望者,独季心、剧孟耳。”[2]2744世间能急人之难,不把父母在世作为推脱的借口,不把需要救助的危难之人拒之门外,天下人只能指望季心和剧孟。剧孟具有勇于担当的品格,将救助他人视为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因此剧孟具有极高的社会声望,被诸侯认为是争夺天下的关键人物,周亚夫得剧孟喜曰:“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无能为已矣。”[2]3184“剧孟今无动。吾据荥阳,以东无足忧者。”[2]2831得剧孟如同得一个敌国,《史记·游侠列传》称:“天下骚动,宰相得之若得一敌国云。”[2]3184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游侠因其狭义的品格而受到社会推崇,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社会影响力,具有较高的社会威望。
(三)郭解真实性游侠形象,呈现出“侠”复杂的历史化进程
太史公在《游侠列传》提到的游侠之中,郭解的游侠身份最具独特性,他多重的性格和复杂行为,最能反映侠的演变过程,是“侠”复杂历史演进过程的一个缩影,这应该是太史公为什么要着重笔墨来写郭解的直接原因。郭解行为的复杂性表现:一是少年时期的暴力攻杀,《史记·游侠列传》载:“少时阴贼,慨不快意,身所杀甚众。”二是藏匿亡命之徒做不法勾当,抢劫剽窃、铸钱掘冢无所不为,《史记·游侠列传》载:“藏命作奸剽攻,休乃铸钱掘冢,固不可胜数。”三是主事客观公正,不徇私情,秉承公义,郭解侄儿寻衅挑事为他人所杀,郭解了解事情原委后曰:“公杀之固当,吾儿不直。”于是释放凶手,此义举为时人称颂。
郭解性格的多重性表现:一是暴戾恣睢、睚眦必报。《史记·游侠列传》中载:“其阴贼著于心,卒发于睚眦如故云。”二是好德善施,谦卑恭顺,宽以待人。《史记·游侠列传》载:“及解年长,更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因此,当有人对其表现出傲慢无视的态度时,郭解自省,认为是自身道德修养不够,称“居邑屋至不见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不仅没怪罪傲慢无礼者,还免除其杂役,最终傲慢者向郭解谢罪致歉;三是有礼有节,谦让不居功。郭解行事,低调谦和,不矜功傲慢,尊重他人。《史记·游侠列传》载:“解执恭敬,不敢乘车入其县廷。”在调节洛阳结仇者之间矛盾时,郭解谦卑不居功,调节成功后,便悄悄离开,于是“夜去,不使人知”,将功劳转给洛阳当地贤豪,《史记·游侠列传》载:“吾闻洛阳诸公在此间……解奈何乃从他县夺人邑中贤大夫权!”[2]3187
从暴力行杀到尚德行修养,从睚眦必报到宽容待人,郭解呈现出的游侠形象是立体的、真实的,在时间上,它不断加强自身德行修养,完成了从以武力慑人到以德行服人的转变,在空间上,其威望也从一县扩大临县,从一域到多域,最终天下闻名,人争相与之相交,“解入关,关中贤豪知与不和,闻其声,争交欢解”[2]3188,甚至愿替郭解养客,《史记·游侠列传》载:“邑中少年及旁近县贤豪,夜半过门常十余车,请得解客舍养之。”[2]3187人们仰慕郭解侠名,甘愿为之养客。索隐如淳云:“解多藏亡命者,故喜事年少与解同志者,知亡命者多归解,故多将车来,欲为解迎亡者而藏之者也。”[2]3187郭解正如韩非子所说“活贼匿奸”任誉之士,其声誉之高,连卫青都为之求情,汉武帝感慨道:“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郭解声誉之高,私交广,私权盛,对公权威信力形成极大威胁,索引述赞:“游侠豪倨,藉藉有声。权行州里,力折公卿。”[2]3189因此,当宾客中有赞美郭解时,一儒生反驳曰:“郭解专以奸犯公法,何谓贤!”[2]3188宾客怒而杀儒生,郭解因此事而招致杀身之祸,御史大夫公孙弘议曰:“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当大逆无道。”[2]3188于是诛杀郭解及其家。荀悦曰:“世有三游,德之贼也:一曰游侠……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
从太史公对游侠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轻财尚义、任气有勇、彼此信任、舍己为人、崇友乐交,且游离于正统体制之外与主流权威相对立,是游侠的基本特征。而太史公着重赞扬了游侠言信行果、重诺尚行的行为品格,轻生尚义、不畏死生的人生态度,缓人之急、救人困厄的责任与使命,不自矜、重德行的道德修养。太史公在赞美游侠品行时,也指出游侠“不轨于正义”的方面,游侠也有“行剑攻杀”“活贼匿奸”的行为。
太史公笔下的游侠呈现出立体化的人物特征,既有积极亦有消极成分,是辩证统一的存在主体,而决定其游侠身份特征的往往是游侠重修行的品格,因此,太史公称赞朱家、剧孟、郭解等游侠“廉絜退让”的品格,这与豪暴之侠具有明确的界限。《史记·游侠列传》载:“至如朋党宗彊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2]3183这是任侠者与游侠者的本质不同,游侠者不仅有任侠行为,而且更注重内在的品德修养。
《史记》中任侠行为集中呈现在《留侯世家》《酷吏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季布栾布列传》《货殖列传》《淮南衡山列传》等篇目中,且多与“藏匿”“滑贼任威”“置田敛财”等行为相关联,而仅有《汲郑列传》中出现了“游侠”二字,且与内在品行操守修养直接相连,《史记·汲郑列传》称:“然好学,游侠,任气节,内行修絜。”颜天佑曾在《〈史记·游侠列传〉解读》指出,太史公在《史记》中常以“任侠”形容诸人,只有汲黯被赋予了“游侠”二字。而与“任侠”二字同时出现的,似乎多属“暴杰”“奸”“豪杰大猾”等带有贬义色彩的形容词。《史记·货殖列传》载:“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此类人虽高举“任侠”标语,其行为却是劣迹行径,遭时人唾弃,为人不齿,太史公称这一类人为“此盗跖居民间者耳”(《史记·游侠列传》),是对真正任侠者的辱没,“此乃乡者朱家之羞也”(《史记·游侠列传》),这种没有游侠精神作规范的行为,将任侠行为异化为一种私欲行径。他们还以“任侠”的名义行奸邪之事,聚众敛财,“任侠为奸,不事农商”,太史公将其视为“奸富”,《史记·货殖列传》称:“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2]3272
二、《汉书》豪暴之侠:对国家社会秩序的冲击
太史公站在人道主义立场对游侠济危救困的品格进行赞扬,从正面肯定游侠的行为;班固则站在维护封建君主统治的立场,对游侠违法犯禁的一面进行全面披露,从反面批判游侠行为。陈平原在《千古文人侠客梦》一书中提到:“太史公不讳言其‘不轨于正义’,班固则称其‘惜乎不入于道德’,后世反游侠者抓住其‘不法’‘不道德’不放,赞游侠者则力图使其行为合法化、道德化。”[5]22-23
班固认为,游侠滥觞起于春秋战国诸侯卿相贵族。其引证孔子之语:“天下有道,政不在大。”[6]3697然而,周王室衰微后,权力却集中到卿大夫手中,他们背弃君臣礼义,“弃官宠交”。《汉书·游侠传》载:“赵相虞卿弃国捐君,以周穷交魏齐之厄;信陵无忌窃符矫命,戮将专师,以赴平原之急。”[6]3697诸侯卿大夫凭借掌握的国家权力“聚带剑之客,养必死之士”,通过损害国家权威来壮大自身声望,满足一己私欲,藏匿违法犯禁者,却被世人称颂为有“侠”,韩非子在《八说》篇中称:“人臣肆意陈欲曰侠。”人臣卿大夫的行为,最终导致了“官职旷”、国家乱的局面。
(一)游侠对国家君主权力的损害
“周室既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桓、文之后,大夫世权,陪臣执命。”[6]3697战国四公子凭借贵族身份,招纳宾客,成为举世称颂的游侠,他们所专享的来自国家的钱财、名望和权力,是宾客归属的重要条件。他们违背国家和君主而行“义”举,这种本是损害国家和君主权威的行为,却被天下人仰慕钦佩。游侠者形成的威望和名声,是窃取国家和君主权力的结果,这种游侠行为被后人效仿,人们开始背离主流权威,私结党派,不履行臣子本身的义务,而壮大私人声威,“则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矣”[6]3697。因此,汉代陈豨、刘濞、刘安皆效法春秋战国卿相之侠,“从车千乘,宾客上千”[6]3697。所以,班固将四公子视为六国罪人,“夫四豪者,又六国之罪人也”[6]3699。布衣之侠在民间树立威名,众人仰慕而归属,成为一方势力中心,班固认为他们虽是底层平民,却以“游侠”的威望窃取国家生杀权力,是对公权的直接挑战,罪不容诛,班固称郭解这类人“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6]3699。他们虽然有“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的“绝异之姿”,然而,他们以私权害公权的行为,是侠的末流行径,最终杀身灭族是必然,没什么值得惋惜的,即班固所言:“杀身亡宗,非不幸也。”[6]3699
(二)卿相之侠与布衣之侠界限打破
班固在《汉书》中增加的游侠形象,打破了身份等级界限,兼卿相之侠与布衣之侠特征于一身,呈现出“布衣之侠”向“卿相之侠”过渡的特点。万章,长安闾巷豪侠,属于布衣之侠,其擅结交权贵,而跻身人臣之列,“为京兆尹门下督”,他通过攀附朝廷权贵而显明,《汉书·游侠传》载:“与中书令石显相善,亦得显权力,门车常接毂。”[6]3760万章报仇怨、养刺客,名声高过诸侯大臣,最终为京兆尹王尊捕杀;楼护,本是从医之辈,后转而入宦,擅结交权贵且有道义,为权贵赏识,经权贵举荐步入仕途,做过京兆吏、谏大夫、广汉太守等官职;陈遵,性格放纵不拘,擅结交,“门外车骑交错”[6]3709,为权贵人臣赏识,大司徒马宫十分赏识陈遵,举荐他补郁夷令。经过权贵举荐,拜官封侯,“封嘉威侯。居长安中,列侯近臣贵戚皆贵重之”[6]3710。正是凭借结交权贵,陈遵名声大噪,人们皆争相与之结交,并以此为荣,“所到,衣冠怀之,唯恐在后”[6]3711,甚至连王莽都知道他的名声,对他都钦慕有加,“王莽素奇遵材,在位多称誉者,由是起为河南太守”[6]3711,因此,陈遵官职一路高,升做过京兆史、公府掾史、校尉、河南太守、九江及河内都尉、大司马护军等职务。然而陈遵行为不加约束,而被司直陈崇弹劾:“遵兄弟幸得蒙恩超等历位,遵爵列侯,备郡守……始遵初除,乘藩车入闾巷,乱男女之别,轻辱爵位,羞污印韨,恶不可忍闻。”[6]3712陈崇认为陈遵因蒙恩才得以入侯爵,但其不能洁身自好、持身自守,行有伤风化、有辱爵位之事,因此应该被免职。陈遵虽被免职,但其生活一点未受影响,反而“宾客愈盛,饮食自若”[6]3712。陈遵在朝廷与闾巷间变换身份,凭借在闾巷间的声望而闻名于世,为人仰慕,无论是位列高官还是身处闾巷,世人皆愿与之结交。
原涉亦是在朝廷与闾巷间游走之徒,原涉祖父为豪侠,其父曾做过南阳太守,其家世代以侠闻名,“赋敛送葬皆千万以上”[6]3714,及其父丧,原涉退还所有财物,并为父守丧三年,原涉不爱财、重孝道的行为,为世人敬仰,因而显名京师,“郡国诸豪及长安、五陵诸为气节者皆归慕之”[6]3715。原涉居闾巷间多行狭义之事,“专以振施贫穷赴人之急为务”[6]3716,即便自己家贫,也要帮他人厚葬死者。因避灾祸,原涉从闾巷入官场,先后做过卿府掾史、校尉、中郎等官职。原涉以侠义著称于当世,结交者甚多,刺客如云。因怨恨王游公的诋毁,而召集宾客杀之,“杀游公父及子,断两头去”[6]3718,班固认为,原涉豢养刺杀,好凶杀,外表恭敬而内心残暴,“外温仁谦逊,而内隐好杀。睚眦于尘中,触死者甚多”[2]3718。然而,我们可以看出原涉是恩怨分明之人,有仇必报。其杀游公家人,独不杀游公之母亲,原因是原涉与新丰富人祁太伯是好友,而王游公又是祁太伯同母异父的弟弟。因此,原涉派遣刺杀的诸宾客见到祁夫人:“皆拜,传曰‘无惊祁夫人’。”[6]3718其刺杀主簿尹公,原因是尹公在做茂陵县令时曾捣毁原涉坟墓房舍,原涉本不予追究,尹公却故意挡原涉的路,“涉用是怒,使客刺杀主簿”[6]3718。
班固着重突出了游侠暴力凶杀的特点,他们豢养刺客,无视国家法纪,在温良谦让的背后是暴力凶残的内心,荀悦所言:“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亦是从班固所列游侠特征进行的总结。班固记载的游侠打破了“卿相之侠”与“布衣之侠”的界限,“布衣之侠”凭借游侠之名望,而为权贵重用,位列人臣,但因多未能善终,万章为王尊捕杀,陈遵醉酒为贼所杀,原涉被问斩,头悬在长安市上。
(三)班固模糊豪暴之侠与道义之侠的目的:抑侠
班固做《游侠传》亦在给人警示,消解人们对游侠的尊崇和效仿。太史公做《游侠列传》亦在呼吁危难中能伸出援助之手的正义力量,班固所列游侠,在太史公看来皆是属于豪暴之侠,不属于真正的游侠范畴。太史公在《游侠列传》中提到了以四公子为代表的卿相之侠,以朱家为代表的布衣之侠和暴力凶杀的豪暴之侠,而只有布衣之侠才属于游侠范畴。正是对游侠理解的错位,和后人效仿对象的偏差,游侠逐渐被引入误区,将班固所列的“豪暴之侠”等同于太史公所列的“布衣游侠”,这种错误的导向,将游侠形象演化为具有“暴力凶杀,窃生杀大权,威胁国家正常秩序”暴力之徒。因此,从汉武帝时期,核心政权开始对以“游侠”为代表的侠客进行大力打压,汉武帝十分痛恨结客行为,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后,天子切齿,卫、霍改节。卫青、霍去病都十分小心与游侠交往。汉朝帝王采取一系列措施抑制游侠发展,首先是迁徙豪侠,徙豪富茂陵。其次捕杀豪侠,《汉书·游侠传》载:“河平中,王尊为京兆尹,捕击豪侠,杀章及箭张回、酒市赵君都、贾子光,皆长安名豪,报仇怨养刺客者也。”王莽当政之后亦“诛锄豪侠”,严厉禁止权臣与游侠交往,从源头上杜绝游侠借助国家权力而扬一己私名,自西汉以来的任侠风气得到根本遏制。
三、太史公与班固史学思想差异:个体生命层面与国家社会层面碰撞
通过对先秦两汉典籍梳理,我们可以发现,有关游侠的记载主要集中在《韩非子》《史记》《汉书》中,而只有《史记》对游侠是持赞扬态度,《韩非子》和《汉书》都意在批判侠“以武犯禁”的行为,认为侠以私权害公权的行为,是对国家君主权威的践踏。不难发现,三家所论述的对象“侠”是存在明显差别的,《韩非子》批评的是一个笼统的“侠”形象,即所有以“武”为基本行为特征的群体,包括勇士、刺客、游侠、私剑、任侠者等;班固《汉书》中批评的“游侠”是一个以偏概全的“侠”形象,即将豪暴之侠混同为整个“游侠”群体,班固有意模糊“游侠”身份界限,为的是维护国家君主权威和国家“大一统”政权下统治制度的威严,达到抑“游侠”的目的。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太史公已明确区分了卿相之侠、布衣之侠和豪暴之侠的界限。曾国藩在《求阅斋读书录》中载:《游侠列传·序》分三等人:术取卿相,功名俱著,一也;季次,原宪。独行君子,二也;游侠,三也。于游侠中又分三等人:布衣间巷之侠,一也;有土卿相之富,二也;暴豪态欲之徒,三也。
在《史记》中,太史公对“游侠”进行赞美,与其身陷囹圄、惨遭宫刑有直接关系。太史公将“游侠”视为正义力量的象征,是对国家正义缺位的一种补充,太史公期待一种异质力量的介入,去打破森严的封建统治秩序,来维护社会正义。侠“以武犯禁”的特征,让其成为主流权力之外最佳的正义执行者。从生命层面上这是基于人道主义思考,而非从维护国家冰冷的法器层面出发。
太史公开篇引韩非子“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从表面看,似乎是认识到“侠”的消极一面,在表达一种客观批判。其实,太史公引用这句话目的,是为“侠”正名,是对“侠”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进行的控诉,韩非子严厉批判的儒和侠,而汉兴后,儒却被推崇到较高的地位,“侠”却遭受不公正待遇,湮没无闻。于是太史公感叹道: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云。李景星在《史记评议》中也认为,太史公传游侠非奖乱。“游侠一道,可以济王法之穷,可以去人心之憾。天地间既有此一种奇人,而太史公即不能不创此一种奇传。故传游侠者,是史公之特识,非奖乱也。通篇以‘缓急人所时有’句为关键,以‘儒侠’二字为眼目,开首即日‘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以侠之犯禁与儒之乱法者比,便非一味推许。以下随以儒侠对发,见儒固有以文乱法,而季次、原宪等非其伦也;侠固有以武犯禁,而朱家、郭解等非其伦也。后文又以卿相之侠形出布衣之侠而更言游侠之士与豪暴之士不同,以终一篇之旨,意思最为深厚,评量极为公允。”[7]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之所以学界对“侠”身份争论不断,主要在于对“侠”进行记载的典籍出现断层,同时,各典籍中对“侠”的身份未加以明晰,如《韩非子》中笼统的侠形象,其实是将私剑、刺客、游侠、任侠者等混为一起,他们的共同之处,即“武”是其核心标志;太史公则消解了游侠“武”的特征,着重强调了游侠的品格和道义等精神内涵,游侠的基本特征被定义为“缓人之急”;《汉书》为达到抑侠的目的,将游侠引入豪暴之侠的范畴,混淆了太史公所论述的布衣游侠身份。韩云波在《〈史记〉与西汉前期游侠》一文中写道:“由于《史记》在背离《韩非子》基础上对侠的重新认识,这就造成中国历史上《韩非子》之‘私剑’、《史记》之‘道义’、《汉书》之‘豪强’三种不同游侠模式的并行交织发展,而尤以《史记》之‘道义’为游侠定型过程及文化积淀中最基本的模式。”[8]75《史记》之“道义”正是侠人格精神的集中体现。
参考文献:
[1] 梁启雄.韩子浅解[M].北京:中华书局,1932.
[2] [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3.
[3] 陈光宏.关于中国早期历史上游侠身份的重新检讨[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6):119-122.
[4] 李欧.论原型意象——“侠”的三层面[J].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4):42-46.
[5]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6] [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4.
[7] [清]李景星.史记评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8] 韩云波.《史记》与西汉前期游侠[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3):71-75.
【责任编辑朱正平】
The Misplacement of Paladin’s Characters in Historical Records and History of Han Dynasty——Additionally Discussing Differences of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between Sima Qian and Ban Gu
YAN Zhen-nan
(School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Nanning 530000, China)
Abstract:Sima Qian believed that the “paladin” was a symbol of justice and a kind of supplement?to the lack of national justice. Sima Qian looked forward to a special external force burst the hierarchical system maintain social justice.The paladin’s characteristics of force let him become an executor of justice. In order to maintain individual life, Sima Qian stressed?paladin’s force and the spirits of sacrifice themselves to protect others.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national order, Ban Gu intended to confuse the concept?between morality, justice and violence, and highlighted the violence?of paladin, and his aim is to restrain its development.
Key words:paladin; chivalrous; violent; restrain the development of paladin
作者简介:严振南(1988—),男,山东临沂人,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6-01-05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5128(2016)05-0022-06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