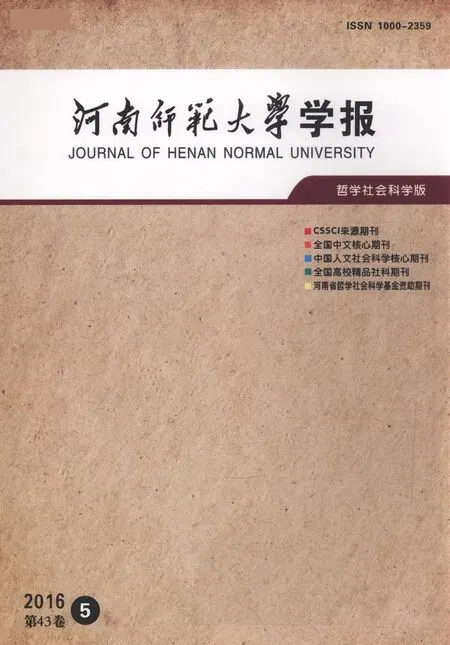东亚简牍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
2016-03-16尹在硕
[韩]尹 在 硕
(庆北大学 史学科,韩国 大邱)
东亚简牍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
[韩]尹 在 硕
(庆北大学 史学科,韩国 大邱)
东亚简牍文化圈是由东亚这一地理空间内共同出现的文化要素组成,是有史以来中国和以中国为中心的周边国家共有的历史发展产物。从地理位置来看,我们所说的东亚地区包括以位于北纬40°、被誉为世界屋脊的帕米尔高原为圆心,呈扇面展开的地区,北面至北纬50°萨哈林岛地区一线(帕米尔高原—新疆—阿尔泰山脉南部—蒙古—黑龙江北部—萨哈林岛),南抵北纬20°越南河内一线(帕米尔高原—喜马拉雅山脉东面—西藏—河内),东面直到包括日本列岛在内的太平洋西岸地区,大致包括今天的中国、韩半岛、日本、越南等地区。
在传统时代,东亚地区周边的自然环境对人类的交流构成了极大障碍。北部一线横贯俄罗斯西伯利亚、蒙古以及中国东北部的寒带森林地区,阻碍了东亚文化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东欧文化的交流;这一地区西、北部逐渐形成的沙漠与高原地带是阻隔西亚文化的主要原因;西部的喜马拉雅山脉阻挡了与印度文化的交流;北纬20°线以南的热带雨林气候影响了与东南亚文化的交流;日本以东的太平洋则封闭了与太平洋以东地区的文化交流。总之,东亚地区周边的自然环境阻碍了其他地区文化的流入以及东亚文化的对外扩张,其结果导致这一地区的文化最终形成一个自成一体的、独立的文化圈。也正因为如此,当时文化最为发达的中国控制了这一区域的文化霸权,并长期保持着霸主地位。正如西嶋定生所指出,自汉代以来,中国以朝贡册封关系为媒介,从政治上控制了韩半岛、日本、越南等王朝国家,并以这种国际关系上的优势为基础,将先进的中国文化传播至其他东亚国家,这一文化的核心内容包括汉字、儒家思想、佛教、律令体制等(西嶋定生《世界史像について》,《岩波講座世界歴史》25(月報3),岩波书店,1997年;《古代東アジアと日本》,岩波书店,2000年)。
对于东亚文化所具有的共同文化要素,以往学界往往只关注和研究其外在表现,对于上述核心内容的深层研究则明显不足。例如,汉字曾是东亚各国共同使用的文字,但是对于东亚地区记载汉字文化形成与发展过程的书写文化的研究却不充分。而且,若强调东亚文化来源的同质性,容易联想到20世纪初日本军国主义者鼓吹的“大东亚共荣圈”,因此,对东亚书写文化的同质性进行探索和研究并非易事。
近年来,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各地的政治、军事、经济区域划分逐渐形成。并且,比起硬实力(hard power),以文化为中心的软实力(soft power)将成为主导21世纪世界体系的主要因素,而反映软实力的文化包括教育、人文、艺术、科学、技术等有关的所有领域。这种软实力的开发与培育一方面体现在新文化的创造上,另一方面则体现在总结历史经验上。我们在对共通的文化要素进行再发现和再解释的过程中,也可以实现软实力的发现与继承。与此同时,最近历史学界超越“一国史”,开始关注“地域史”、“地球史”甚至“宇宙史”,其主要原因即在于21世纪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已步入全球化时代。因此,从事超越“一国史”的软实力研究,不仅符合当前世界历史学界的研究潮流,也符合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共同利益。
因此, 有必要对汉字文化形成与发展进行深入的实证研究(参见李成市《東アジア文化圈の形成》,山川出版社,2007年;李成市《古代東アジアの民族と国家》,岩波书店,1998年)。汉字在文化交流与传承过程中是最为重要的载体,在中国文化向韩半岛、日本、越南等地区传播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迄今为止的研究仍主要集中在语言学领域,有关以汉字作为文化书写手段和工具的研究却十分稀少。当然,这首先是因为可供研究的有关书写文化的资料不足。
近年来,由于东亚各国均加强了考古发掘工作,各国先后出土了相当数量的记载东亚地区文化传播情况的汉字资料,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简牍资料。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是典型的古代中国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时期,该时期的文化资料均是在简牍上书写而成。其影响已波及韩半岛。大约在公元前300年左右,汉字从中国传到韩半岛,这一史实已经得到考古资料的证实。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在韩半岛北部和中国的东北地区设置乐浪郡,近来考古工作者在韩半岛北部出土了相关简牍资料。而且,即使在已经进入普遍用纸书写的时代,韩半岛和日本仍出土了大量包括《论语》在内的木简资料。以汉字为载体的书写文化和以汉字为表达手段的儒家思想,自公元前2世纪以来便成为中、韩、日三国共同的文化要素,也成为东亚简牍文化的象征。其中,中、韩、日三国均发现出土的《论语》简最具典型意义。
中国考古发现的《论语》简均为汉代遗物,主要有八角廊汉简《论语》、罗布淖尔汉简《论语》、悬泉置汉简《论语》和居延新简中发现的《论语》简四种。目前尚未发现汉代以后的简本《论语》,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纸写本《论语》。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纸写本《论语》是出土于楼兰遗址的晋代写本《论语》,其余的均为唐写本《论语》。考古发现的简本和纸本《论语》当时是作为学习文化和儒学的入门读物,与当时的儒学教育特别是蒙学教育关系密切。
韩半岛出土的《论语》简共有三批,即朝鲜平壤乐浪出土的《论语》竹简、韩国仁川桂阳山城出土的《论语》木简(推测年代为4世纪)和金海凤凰洞出土的《论语》木简(推测年代为6—8世纪)。三批《论语》简的年代分别相当于中国的汉至唐代。日本出土的《论语》简大约有30批,它们分别是奈良县飞鸟京遗址、飞鸟池遗址、石神遗址、藤原宫遗址、平城宫遗址、平城京遗址、东大寺遗址等出土的木简《论语》,兵库县袴狭遗址、芝遗址、德岛县观音寺遗址、滋贺县劝学院遗址、静冈县城山遗址、长野县屋大遗址群等出土的《论语》木简。日本出土的《论语》木简的年代为7—9世纪(参见木简学会编《日本古代木簡集成》,东京大学出版会,2003年;《全国木簡出土遺蹟·報告書綜覽》,奈良文化财硏究所,2004年)。
中、韩、日三国出土《论语》简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八角廊《论语》简和乐浪《论语》简。八角廊《论语》简1973年出土于河北定县八角廊西汉中山怀王刘脩墓,共620枚竹简,整理出释文7576字,是刘脩死亡的西汉宣帝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之前流行的《论语》版本之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文物出版社, 1997年)。乐浪《论语》竹简是20世纪90年代初在朝鲜平壤贞柏洞364号木椁墓出土,这里在汉代属乐浪郡,共发现内容为《论语·先进》的33枚竹简589个字,以及内容为《论语·颜渊》的11枚竹简、167个字(参见李成市、尹龙九、金庆浩《关于平壤贞柏洞364号墓出土竹简〈论语〉》,《木简与文字》第4号, 2009年)。从与《论语》简同出一墓的“●乐浪郡初元四年县别户口多少□(集)簿 ”木牍中的“初元四年(公元前45年)”来看,乐浪《论语》简的埋藏时间与八角廊《论语》简仅差10年左右时间, 可知两处出土的《论语》简年代几乎相同,均属于西汉中晚期流行的《论语》版本之一。而且,乐浪《论语》简的形制、规格、字体、符号以及编绳方式、随葬书刀等,也与八角廊《论语》简十分相似。八角廊与乐浪《论语》简均为墓葬出土的典籍类竹简,在韩半岛其他地区和日本均未出现,它表明在公元前1世纪中叶,以《论语》为代表的中国儒家文化及其意识形态已经传播到当时的边郡。由于乐浪郡是朝鲜半岛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基地,因此,应当认为古代韩半岛的书写文化是通过乐浪郡接受中国的影响而发展起来,逐渐被纳入到简牍文化圈的。
中、韩、日出土的《论语》简的用途与当时的儒学教育特别是蒙学教育关系密切。罗布淖尔、悬泉置、居延新简中的《论语》汉简出土于西北边塞的屯戍或邮驿遗址,它们常常和《仓颉篇》《急就篇》等字书和九九口诀表等一起出土,显然是当时的蒙学读物。它表明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随着儒家文化教育的深入,《论语》越来越受人欢迎,渐渐成为汉代士子的启蒙读物。
韩国桂阳山城、凤凰洞以及日本出土的《论语》简,与蒙学教育联系紧密(参见尹在硕《韩国、中国、日本出土〈论语〉木简的比较硏究》,《东洋史学研究》第114辑, 2011年)。桂阳山城出土的《论语》简书写在已残的五面木觚上,五面均有墨书字迹,内容为《论语·公冶长》的一部分,推测这个木觚属于4世纪百济,原长约96厘米。凤凰洞《论语》简为6—8世纪新罗时期的四面木觚,四面均有墨字,已残,内容为《论语·公冶长》的中间部分,据推测原长约100厘米。如果桂阳山城《论语》简确属于4世纪,那么其年代明显晚于中国出土的简本《论语》,而与中国新疆楼兰出土的晋代纸写本《论语》年代接近。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中国虽然是简、纸并用的时代,但纸张的使用远远比简牍普及。因此,韩国发现4世纪的《论语》木简,或者是因为纸张在韩半岛的普及时间略晚于中国,或者是因为这件木牍的用途特殊。
桂阳山城和凤凰洞《论语》简的形制较为特别,均是四面或五面体的觚。觚在古代中国一般用来练习写字或抄写字书类的教材,中国出土简牍中就有《仓颉篇》《急就篇》等字书书写于觚的例子(参见李均明、刘军《简牍文书学》,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9年; 籾山明《削衣、觚、史书》,见汪涛、胡平生、吴芳思主编《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斯坦因所获未刊汉文简牍》,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7年)。而且,根据文献记载,韩、日古代的教育机构也把《论语》作为主要教学科目。因此,这两件《论语》觚的用途可能与中国出土的《论语》简或《论语》纸本一样,主要与习字或蒙学教育有关。如果它的长度确如推测的那样为100厘米左右,体积较大,那么,它很可能是放置在官学场所中让大家都能够看到并利用的《论语》学习工具。而这样的学习工具,在中国的出土简牍中尚未见到。
在日本出土的30余批《论语》简中,除了德岛市观音寺遗址出土的7世纪后期木觚上抄有《论语·学而》部分内容外,大多数木简和木觚上都是反复抄写《论语》的某段内容和句子,表明它们是习字简(参见桥本繁《東アジアにおける文字文化の傳播:朝鮮半島出土論語木簡の檢討を中心に》,福井重雅先生古稀、退职纪念论集《古代東アジアの社会と文化》,汲古书院, 2007年)。因此,日本出土的《论语》简大体上和韩中两国的一样,与启蒙教育或习字密切相关。日本出土的7—9世纪的论语木简,和中韩两国出土的论语简牍在形制和内容上有相似之处,表明汉字、儒学以及记录这些内容的简牍文化是从中国通过韩半岛传播至日本的。
综上所论,由于韩日两国同属于中国主导的东亚文化圈,其历代统治者长期崇尚儒家文化和推行儒学教育,学习《论语》成为儒学教育最重要的科目。因此,《论语》对三个国家的历史进程都产生过深远影响。汉字作为古代东亚书写文化圈的通行文字,简牍作为古代东亚书写文化的共同文字载体,在三个国家的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论语》简作为一个典型标志,具体而微地反映出三国间古代文化的交流状况。
除《论语》简外,中国的简牍文化对韩日两国书写文化的深远影响还表现在其他方面。例如,和乐浪《论语》简一同出土的汉元帝初元四年乐浪郡户口簿木牍,其形制、行文格式和内容等都与中国出土的汉代户口簿木牍相似。韩日两国出土最多的是标签类木简,其形制、用途和中国魏晋时期的木楬相似。可以确定,韩日两国出土的习字简均源于中国的习字木简(觚)。此外,中、韩、日三国出土的书刀、石砚、毛笔等工具也充分表明,与简牍相关的书写文化源于中国的简牍制度。
由此可知,对东亚简牍文化的深入研究是了解东亚地区历史文化核心主干的基础,也是今后在东亚文化圈内开掘和发展软实力的重要契机。为此,我们需要解决的课题有很多,例如隶属于东亚简牍文化圈的各国简牍学界有必要提出共同的研究课题和简帛学理论,采用统一的简牍学用语,三个国家的简牍机构共享从简牍发掘到整理、出版、保护的科学技术,互相交流,共同进行简牍的释文等等。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韩、日三国简牍学会需要联合主办定期的“东亚简牍文化国际研讨会”,通过对东亚简牍文化圈的共同研究,扩大东亚文化圈的视野,进而达到对彼此文化的深入了解,实现三国间和平、发展的共同目标。
10.16366/j.cnki.1000-2359.2016.05.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