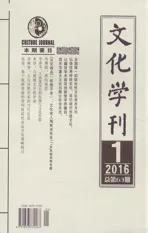白璧德文学批评谈
2016-03-16黄淳
黄 淳
(北京大学英语系,北京 100871)
【文学评论】
白璧德文学批评谈
黄 淳
(北京大学英语系,北京 100871)
欧文·白璧德是美国新人文主义的代表人物,曾对20世纪初中国文化特别是学衡派产生深远影响。关于白璧德文学批评的思想核心与价值,学术界多年来评价各异。然而,对白璧德主要作品中的文学批评思想做一梳理,即可发现其文学批评的重点在于人文主义思想指导下对文学与人生关系的探讨,实质是对文学“伦理性”的解读与批评。把握这一点,不仅对白璧德文学批评的理解至关重要,还能启发我们更深刻地思考文学与人生的关系。
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文学;人生
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这个名字与新人文主义紧密相连。20世纪初,他执教于哈佛大学期间,与挚友莫尔(Paul Elmer More)及诸多学生一起,以人文主义为口号,在美国掀起了一个短暂的批评热潮,其领域涵盖教育、宗教、道德、文学等各方面。为了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有所区别,后人将这批人物的主张总结为一派,冠之以“新”,于是,白璧德也就成为20世纪美国新人文主义的宗师。由于领域繁杂、著作集中,新人文主义为后世提供了很多可供探索的话题,白璧德的文学批评便是其中之一。但白璧德的文学批评究竟是什么?许多国外学者都曾对此发表自己的见解,结论也每每大相径庭。
一、有关白璧德文学批评之争
1931年,当以白璧德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在美国跌入低谷时,Gorham Munson却撰文坚定地支持他的文艺主张。在Munson看来,当时的美国作家Arnold Benett和Willa Cather都颇具人文主义气质,他们的优秀作品也证明,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的价值理应得到重视。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二者关系复杂,完全没有批评固然不可,而过分强调批评则会导致法则至上的“伪古典主义”。在这一点上,Munson认为白璧德的主张堪称典范,因为“没有谁比白璧德教授更严厉地批判伪古典主义了”。[1]
然而,在另一位美国教授Wylie Sypher眼中,白璧德却变成了伪古典主义的代言人。Sypher将白璧德的文学批评和道德批评对比研究,认为前者已完全被后者所取代;道德评判凌驾于审美体验之上,绝对“道德中心”成为品评文学作品的唯一尺度,因此,他得出一个与Munson相悖的结论:白璧德的文学批评说教气浓重,是不折不扣的“伪古典主义”。[2]
Rene Wellek的《现代文学批评史1750-1950》中单辟一章,专讲新人文主义。可尽管有此等关注,白璧德还是未能获得多少好评。Wellek直截了当地将他的观点称为“渴望回到佛陀和菩提树那里”的“白日梦”,并引《卢梭和浪漫主义》及《新拉奥孔》中的文字,宣称白璧德本人实际上也是个浪漫派。此外,Wellek还指出,白璧德对他同时代的主要思想几乎充耳不闻,而且小心谨慎地与文学作品保持距离。[3]如果说前一条指责是Wellek的个人观点,那么后一项则显然是白璧德为众人所诟病的软肋*关于对白璧德这方面的批评,参见J.David Hoeveler Jr.The New Humanism:A Critique of Modern America,1900-1940[M].Charlottesville:UP of Virginia,1977.以及Walter Sutton.Modern American Criticism[M].Connecticut:Greewood Press Publishers,1963.前者认为,白璧德对当时美国文学持"不负责的态度",结果丧失了在文学领域实践新人文主义主张的大好机会(具体可见该书106页)。后者也批评白璧德对当代文学创作"充满敌意"(具体可见32页)。。
当代新人文主义的支持者们却持有不同的看法。James Seaton曾在刊物Humanitas上发表多篇文章,强调白璧德对文学价值的肯定,以及其观点的灵活性和远离各种主义的实证精神。Seaton曾将白璧德与Allan Bloom比较,认为后者呈现出危险的浪漫主义倾向,而前者所坚持的“标准”恰恰提供了应对的良方。[4]而在另一篇文章里,Seaton则采用了类似Munson的方法,通过分析米兰·昆德拉作品中的人文主义倾向,证明白璧德的学说在当代依然有用武之地。[5]
乍一看,白璧德的文学批评确实是一个颇受争议的话题。当然,一个学者的主张在不同读者那里得到不同的甚至看似针锋相对的回应,这原本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但问题在于,这些评价是否确实“针锋相对”?尽管Munson和Sypher在白璧德与“伪古典主义”的关系上判断相反,可他们采用的是完全不同的角度与方法。Sypher细读白璧德的著述,从字里行间搜寻证据;Munson则完全以“实践出真知”为原则,瞄准生活,通过把理论主张应用于实际分析而证明其价值。角度与方法的差别也同样体现在Wellek和Seaton的对比上。前者从学理入手,将白璧德的文学批评看作一个相对封闭的整体,试图发掘它的价值和不足;后者则更看重实践应用,并由此走向对社会、文化和伦理等问题的探讨。侧重点不同,评论的路数自然不一样。虽然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上有分歧,但无论支持者还是批驳者,在论述中都很少有直接针对对方的回应,这也可以证明,他们本来就是一个向东一个往西,并没有针锋相对的意味。
但为什么关于白璧德的文学批评研究会有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角度?角度的选择和白璧德的理论主张是否有关?要想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回归白璧德,研究他的文学批评到底说了些什么。
二、文学与人生:白璧德的永恒话题
初次接触白璧德的文学批评,可能多少会给人一点不得其门而入的感觉。虽然白璧德是位文学教授,他的名字时常出现在有关文学批评理论的著作中,“白璧德的文学批评”是个常常引发讨论的话题,但他本人并没有在哪部著述中系统地阐述过自己的文艺观,更有趣的是,他时常跑题。原本说的是文学问题,结果却总是矛头一转,指向别处。“文学与生活”或“文学与人生”的提法在白璧德的论述中屡见不鲜。如在《新拉奥孔》的前言和结尾,作者反复强调,之所以花力气讨论文学体裁,目的就是要向大家证明,这个讨论“不仅仅关乎文学,而且关乎生活”。[6]又如,批评“伪柏拉图主义”的文学观时,白璧德指出,它的错误不只影响了“现代文学和艺术”,而且影响了“现代生活”。[7]再比如,在《论创造力及其它论文》里,白璧德认为,有标准的批评可以揭示“Spontaneity”在指导创作和指导生活上的双重不足。[8]从文学到生活,这之间的跳跃如此巨大,以至于为了前后连贯、文意通顺,作者常常不得不补上一句“现在让我们回到文学和艺术问题上来”。[9]
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了这个特征。A.Owen Aldridge就曾提出,相比较其他美国批评家,白璧德文学批评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他坚持文学和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而且在空洞理论四处泛滥的今天,这个主张对于文学批评有很大的借鉴意义。[10]说白璧德坚持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这固然不错,但这主张本身是否就是白璧德区别其他美国批评家的特点所在,值得研究。
宽泛点说,完全割裂文学与生活的主张几乎是不可行的。没有了对社会生活最基本的关怀,文学也就失去了它的基础。具体而言,即使在与白璧德同时代的批评家,甚至他的对手中,注意二者密切关系的也大有人在。前面提到的H.L.Mencken便是一例。与白璧德类似,Mencken也是一个20世纪初美国活跃的文学批评家。白璧德曾在《批评家与美国生活》中花费相当的篇幅驳斥Mencken的“自我表达”说(self-expression),认为它忽视了传统标准,缺少细致的分析与甄别,与卢梭的浪漫主义本质相同。假如卢梭和白璧德的观点水火不容,那么Mencken与白璧德也必是一对死敌。但也许是白璧德的说法略微有些夸张了。毕竟,对复杂现象、人物和流派的归纳整合是他论述的一大特色,也是其力量所在*关于此点特征,参见Michael H. Levenson关于现代主义源流的专著The Genealogy of Modernism: A Study of English Literary Doctrine 1908-1922[M].Cambridge:Cambridge UP,1984.,只是这种归纳不应当被我们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
事实上,尽管Mencken深受克罗齐的影响,主张“表达说”,与白璧德的理想相左,但说到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他们的看法并无二致:
“一个批评者如果缺少灵活的头脑和必需的进取心,无法通过艺术作品进入它背后那广阔而神秘的现象世界,那么他至多也不过是个平庸之人……但如果他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必然会跳脱艺术而直抵生活。”[11]
这一点在Mencken对马克·吐温的评价上也表现得格外明显。Mencken热忱地赞美马克·吐温,在他看来,以《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和《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必将流芳百世,因为他们的作者有着“对生活的清晰认识”,也因为这些文字“不仅仅是艺术作品,更是对人生的批评(criticism of life)。”[12]类似关于艺术与生活的观点在同一时期的W.C.Brownell和George Santayana那里也可以找到共鸣。由此可见,20世纪初美国批评家的文学观生活观虽然不尽相同,但积极面对文学与社会生活、坚持它们的密切关系却是彼此共通之处。
三、文学与人生如何关联:白璧德文学批评的核心
真正的区别,或者说白璧德文学批评的真正特色,并不在于是否强调文学与生活之间的关系,而在于他笔下二者关系究竟如何。诚然,与文学相对应的“生活”有着无限广阔的内涵。即使在白璧德那里,这个词的含义也不是短短一篇文字就可以界定的。所以我们不妨用以小见大的方法,选择一些具体的方面,探讨白璧德所讨论的文学到底如何与生活和人生相关联,这种关系又如何体现了他的文学批评的特点。
首先要提到的是教育。白璧德是批评家,但同时也是颇受欢迎的教授。Frederick Manchester和Odell Shepard曾编纂出版过一本纪念他的文集,其中的文章全由他的友人学生写成。文集的标题便是Irving Babbitt:Man and Teacher,很强调白璧德为人师的一面。他的挚友Paul Elmer More也曾说,比起著述来,白璧德的课堂才是展示他学识和风范的最佳舞台。联想到众多弟子,包括T.S.Eliot、Stuart Sherman,还有中国学界非常熟悉的吴宓和梅光迪对这位老师的敬仰与尊重,More的说法当无任何溢美的成分。然而,白璧德所关心的远不止课堂这个小小的天地。他的第一本书《文学与美国大学》开篇即对美国高等教育做了一个整体评价,激烈地抨击教育制度、政策和思想等方面的诸多弊端。类似的见解还出现在其他许多著作中,贯穿白璧德批评事业的始终。及至《论创造力及其他文章》,教育几乎成为批评工作的终极目标。经过一番对文学浪漫派的剖析之后,白璧德总结:“这种周密的考察……不仅超越文学的界限,跨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最终也将与我们对高等教育的考察达成一致。”[13]在与文艺相对的现实生活诸方面里,教育无疑是白璧德最关心的话题。
这其中,文学的价值又如何体现?白璧德认为,教育的任务就是吸收古往今来最好的思想,将学识变成文化,塑造性格与意志,实现个体的提升。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学院和大学必须对科目加以选择,而上上之选莫过于古典文学,因为它行之久远,最具备人文主义价值(humane),最能形成维系全人类的精神纽带。[14]“文化是被思考和被解说的最好的东西。”此处,马修·阿诺德的影响显而易见。不过阿诺德更看重“思考”与“解说”,强调思想相对于功利实践的价值,主张“无偏见的研究”。而在白璧德的语境中,“古往今来”和“吸收”才是关键,发扬文化即保存传统,保存传统则必须潜心研究古典文学。由此可见,推崇古典的白璧德并不是一个埋头故纸堆的学究。文学、教育和文化三位一体说明他正是带着一定的现实目的去理解文学。一方面,文学是实现教育理想乃至文化理想的重要工具;另一方面,教育成为贯穿文学批评的隐含线索,文化理想则是品评文学作品的重要依据。Hoeveler等学者指责白璧德不关心现代文学,批评得虽然很有道理,但多少也有些忽视白璧德说话的语境。崇尚古典,是白璧德思考社会问题后做出的价值选择;把研究文学当作实现文化理想的途径,这恰恰说明他非常看重文学的价值。
除了教育,伦理也是个值得一提的方面。前者关注做事,后者关注为人。虽然伦理依然是个“现实目的”,但在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上,它的重点已经由文学的社会功用转向哲学价值了。白璧德常常仿照亚里士多德发问:“如何才能更好地生活?如何才能获得幸福?”在他看来,这其中便蕴含着文学对人生的意义。他评论华兹华斯的一段话鲜明地表达了这个观点:
“也许有人会问,我们为什么要如此专注地讨论这些问题?比如说吧,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将Tintern Abbey作为一首诗来欣赏,不去关心它的哲学意义?一个人将泛神论与真正的沉思相混淆,到底能有什么后果?这个问题的答案与华兹华斯毕生的探索——幸福的问题——直接相关……是他坚持认为诗人应当是人类中最幸福的群体。”[15]
与其说这是华兹华斯毕生的探索,倒不如说是白璧德毕生的追求更贴切。显然,他也意识到,对伦理的关注会引发其他文学评论者的质疑。所以,在这里,他要借华兹华斯的“幸福观”为自己正名,顺理成章地将诗歌研究变成对生活态度的讨论,将文学问题与伦理问题对接,甚至把伦理作为文学批评的理论支撑。
只是在白璧德那里,这种对接未必完全顺畅。说到生活态度和伦理道德,总脱不开个体的“人”。人及其行为是最重要的研究对象,甚至可以说是唯一重要的对象。白璧德伦理批评的核心也正是基于对人的认识。在他看来,每个人的内心都存在高上自我与低下自我的二元对立。人之所以为人,就必须通过内在制约(inner check),以高上自我控制低下自我;否则,个体只能沦为私欲的奴隶,整个社会也必将礼崩乐坏。白璧德的伦理批评究竟如何,这里暂且不做深入研究。但有一个问题很明白,因为伦理成为评价文学的依据,二元对立和制约也都被白璧德原原本本地移植到了文学批评里:想象力要受到分析理性的制约,同情心要接受判断力控制,对于真正有创造力的诗人来说,想象还必须遵循人性标准(human norm)。[16]这样一来,无论想象力也好,判断力也罢,所有的对立关系都落实在“人”这一点上。文学批评索性变成对文学创作者与批评者的批评。
这也就是为什么白璧德的文学批评很少有具体的文本分析,Douglas Day就曾将白璧德与新批评对比,认为前者对批评理论的兴趣远大于具体的文学对象。[17]甚至有些时候,他连“作者”这个身份都可以忽视:“此外,一个作者的历史地位与他的真正价值并没有直接关系。彼特拉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比但丁高许多,但是作为一个作者或是作为一个人,他都比但丁差得很远。”[18]Sypher也曾抱怨说,白璧德总是兴致勃勃地谈论作家的私事,如卢梭对子女的冷酷、培根的道德污点。这种“重人轻文”的批评方法当然很有问题:即使关系再密切,文学也不可能与生活等同,如何欣赏文字与如何做人归根结底也不是一件事情。
其实,白璧德本人的矛盾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对那些想得到人文主义气质的评论家来说,他曾这样说:“他们必须发挥自己的分析能力……以幸福为指针,甄别实际的经验资料。”究竟如何甄别?白璧德继续道:“就像那些从事科学的人一样,利用同样的分析能力,以功能和用途为目的,甄别经验资料。”[19]可在另一本书里他却批评莱辛,认为他太看重分析,缺少对感觉的把握:“比方说,他没有很充分地关注文字的暗示性,总是把词语当成被动的材料;至于诗人,他总是把他们看作组合字词的熟练工。”[20]至于想象力,白璧德有时会依照Sir Philip Sydney对亚里士多德的解说,把它作为文学作品的根本,“通过制造幻象而达到更高层次的真实”[21];有时候他却格外谨慎,强调“想象力必须服从分析理性这个权威力量”,否则只会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一片混乱[22]。这两处所说的想象力有没有区别,想象力对文学的价值体现在哪里,白璧德都没有完全讲清楚。文学批评到底以什么为依据?是审美还是伦理,是文学感觉还是道德理想,是语言材料还是社会生活?虽然白璧德常说,审美与伦理不可分离,但他本人终究没能找到一个沟通美与善的途径,因此也就无法回到美与善彻底合一的思维方式中。在这一点上,Aldridge的诊断最切中要害:“尽管他试图认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将道德和审美视为一体,但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他又不得不将二者区分开来。”[23]文学具有指导人生的力量,这个命题肯定了文学对教育乃至人生的巨大价值,但白璧德却过分突现道德伦理的一面。这不仅无法帮助他实现平衡乃至统一审美与道德的愿望,而且在面对具体的文学批评时,还将他带入一个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
四、再论有关白璧德文学批评的争议
文章开始所提到的角度选择可以在这里找到些解释。评论角度虽然不同,实质上却都是围绕“文学与生活关系”展开,而且角度上的差异正暗合了白璧德文学批评的矛盾。支持者强调,白璧德的文学批评对当今社会有重大意义,因为他们认识到,文学与生活的紧密结合可以为社会文化带来积极影响;反对者认为他的观点僵化教条,其实就是因为他们看到,文学和生活的关系需要拆解,拆解不够,则文学批评自身的价值将面临挑战。只不过,白璧德为伦理辩护的热情常常压倒一切,以至于大家都过分看重他的伦理关怀,而忽视了这位批评家偶尔流露出的对文学的细腻感觉。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评论角度的选取固然与白璧德文学批评有很大关系,却不完全由它决定。从Munson到Wellek再到Seaton,文学批评已跨越了好几个时期,每个时期的潮流与风尚势必影响角度的选取和对白璧德的回应。不仅Sypher指责他不去“侍弄”正经的文学研究,还有评论家说,白璧德的文学评论只谈些无足重轻的、非艺术的东西,简直就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评论[24]。J.E.Spingarn认为白璧德只关注实际生活而看轻文学[25],Wellek讲解现代文学批评史时,也用“过时”来评价白璧德的观点。联想到这些批评者的时代与身份——前两条评语都来自20世纪40年代,Spingarn是新批评一词的创造者,Wellek则系新批评的坚定盟友,我们便不难体会到“门户之见”也是评判中的重要因素。究竟什么样的研究才算得上“正经的文学研究”?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评论?什么才是不过时的文学批评?其实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针对白璧德的指责与评价,多少都暗含着新批评理念与传统视角的冲突。后起之秀总摆出一副打倒前人的架势,但诚实地说,新批评所鼓吹的文本独立性也只是文学批评的一种方法而已。它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回答了“文学是什么”,但文学的内涵太过宽广,仅仅一种角度还远不能给出完满的答案。白璧德的主张虽然忽视文本,有失偏颇,可强调文学的伦理关怀,这也是自古希腊以来一条重要的文艺批评线索。古老的未必没有价值,后来者也不必以权威自居。到了今天,批评潮流再次转向,伦理批评渐渐兴起。Humanitas的创立与刊载的文字便是明证。1989年文学理论家Wayne Booth也著书The Company We Keep,提出文学批评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便和白璧德遥相呼应:“How to live well”。当然,Booth所关心的当代伦理问题与白璧德的时代并不完全一致,二人的伦理关怀反映在文学批评上,也有许多区别。但无论有多少差异,回溯的痕迹依然很清晰。可见,文学与人生的关系如何,始终是文学批评中绕不过去的话题。
[1]Gorham Munson.Humanism and Modern Writers[J].The English Journal,1931,20(7):531-540.
[2]Wylie Sypher.Irving Babbitt:A Reappraisal[J].The New England Quarterly,1941,14(1):64-76.
[3]Rene Wellek.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1750-1950[M].New Haven:Yale UP,1986.6,9-24.
[4]James Seaton.On the Future of the Humanistic Tradition in Literary Criticism[J].Humanitas,1998,11(1):22.
[5]James Seaton.Irving Babbitt and Cultural Renewal[J].Humanitas,2003,16(1):4-14.
[6]Irving Babbitt.The New Laokoon:An Essay on the Confusion of the Arts(Preface)[M].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10.185.
[7][8][20]Irving Babbitt.The New Laokoon:An Essay on the Confusion of the Arts[M].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10.88.105.51-52.
[9][13][15][16][21]Irving Babbitt.On Being Creative and Other Essays[M].London:Constable,1932.31.233.65-66.22,29-30.83.
[10]A.Owen Aldridge.Irving Babbitt and the Standard of Aesthetics Judgment[J].Neohelicon,1987,14(2):32.
[11]Rene Wellek.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1750-1950[M].New Haven:Yale UP,1988.5-6.
[12]H.L.Mencken. H.L.Mencken's Smart Set Criticism[M].Washington:Regnery Publishing,1987.179.
[14][18]Irving Babbitt.Literature and American College[M].Boston:Houghton Mifflin,1908.96,101.125.
[17]Douglas Day.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Criticism[J].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1966,24(3):431.
[19][22]Irving Babbitt.Rousseau and Romanticism[M]Austin:U of Texas P,1977.282.279.
[23]A. Owen Aldridge.Irving Babbitt and the Standard of Aesthetics Judgment[J].Neohelicon,1987,14(2):30.
[24]Emerson Grant Sutcliffe.Re-Creative Criticism[J].College English,1941,3(7):637.
[25]J.E.Spingarn.The Ancient Spirit and Professor Babbitt[J].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Psychology and Scientific Methods,1914,11(12):328.
【责任编辑:董丽娟】
I561.074
A
1673-7725(2016)01-0064-06
2015-10-25
黄淳(1982-),女,安徽淮北人,讲师,主要从事19世纪英国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