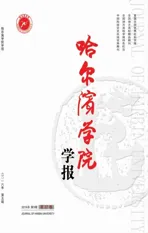再论匈奴“休屠王祭天金人”
2016-03-16吴飞
吴 飞
(河北大学 宋史研究中心,河北 保定 071002)
再论匈奴“休屠王祭天金人”
吴飞
(河北大学 宋史研究中心,河北 保定071002)
[摘要]关于《史记》《汉书》中提到“休屠王祭天金人”,古今学者多认为是外来神像。这种观点受到了今人的质疑,也缺乏有力证据。考察匈奴族及其他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信仰以及铸金人习俗,可以推知“休屠王祭天金人”是匈奴休屠王根据本民族萨满教信仰下令铸造的可通过萨满仪式而引得神明前来依附的小型黄铜质人形祭天神主。
[关键词]祭天金人;匈奴;古代信仰;休屠王
关于匈奴“休屠王祭天金人”的记载,首见于《史记》的《匈奴列传》与《卫将军骠骑列传》,《汉书》亦有相关内容。至于这个“祭天金人”是何形制?作何用途?无论是司马迁,还是班固,都没有作进一步描述。由于其涉及到匈奴人的宗教信仰以及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等问题,引起后世史家的种种猜测。本文拟在对诸家说法略加评述的基础上提出管见。
一、关于“休屠王祭天金人”的研究评述
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春天,骠骑将军霍去病率万骑出击陇西匈奴,发动了著名的河西之战,在极短时间内取得了重大胜利。据《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载:“(霍去病军)过焉支山千余里,击匈奴,得胡首虏万八千余级,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提到在汉军此次缴获的战利品,就有匈奴休屠王的“祭天金人”。另外,《汉书》卷六十八《霍光金日磾传》也提到汉武帝“本以休屠作金人为祭天主,故因赐姓(归降汉庭的匈奴休屠王之子金日磾——引者)金氏云。”结合两书记载,说明匈奴休屠王确曾拥有过一个“祭天金人”。
关于“祭天金人”是何物,现存的汉代文献并没有具体说明。班固在《汉书》的《霍光金日磾传》中只将“祭天金人”称作“祭天主”,照字面意思来看,似乎是祭天用的神主。三国魏晋以来,学者多因袭此说法。裴骃的《史记·集解》说:“如淳曰:‘祭天为主。’”[1](P2930)颜师古的《汉书集解》亦云:“如淳曰:‘祭天以金人为主也’。”[2](P2480)司马贞《史记索引》也载:“韦昭云:‘作金人以为祭天主。’”[1](P2909)
《史记集解》对“祭天金人”做了详细地描述,作者裴骃引述三国时孟康在《汉书音义》中的说法,称“金人祭天处,本在云阳甘泉山下,秦夺其地后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祭天人也”。[1](P2909)《史记索引》也采纳了孟康说法,不过司马贞又补充道:“事恐不然。案:得休屠金人,后置之于甘泉也。”[1](P2909)在他们看来,祭天金人是匈奴各部共用的祭天偶像,只不过在秦军控制匈奴原祭天处云阳甘泉山后,单于将其迁往匈奴右地,由休屠王代为保管。
而北魏崔浩则云“胡祭以金人为主,今浮屠金人是也”,[1](P2909)认为“休屠王祭天金人”是佛像。魏收在《魏书》中更是对崔浩的说法加以发挥:“昆邪王杀休屠王,将其众五万来降。获其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金人率长丈余,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此则佛道流道通之渐也。”[3](P3025)不仅道明了“祭天金人”的由来、性质,对于“金人”个头大小及祭祀方式也言之凿凿,断言“休屠王祭天金人”就是佛像。此说影响甚大。后世如颜师古、张守节均采纳之。直到近现代,还有学者采信此说。[4]
近人吕思勉先生则旁征博引,以《汉书》及如淳注疏“皆曰祭天,不云礼佛”为由,推翻前说,并以《梁书·扶南传》为佐证,指出古人所谓天神金人,并不一定指的就是佛像。[5](P949)陈序经先生也论述:“霍去病获得休屠王祭天金人,是在公元前第2世纪末,印度的佛像雕刻与佛像的采用迟于这个时代,所以这个金人不可能是佛像。假如是佛像的话,那就应该叫祭佛金人或是浮屠金人,我们以为这个祭天金人,只是匈奴休屠王用以为祭天的偶像,与佛教没有什么关系。”[6](P89)当代学者汤用彤先生也力主休屠王祭天金人并非佛像。[7](P10-14)的确,早期佛教是没有佛像的,只以菩提树、佛足迹、伞盖、印度式塔等特定器物来象征佛陀。至于佛教造像艺术产生于何时,前人研究成果颇多。绝大部分学者认为世界上最早的佛像产生于公元1世纪左右,[8]之后逐渐传入中国。因霍去病缴获休屠王祭天金人是在公元前121年,因此,祭天金人绝不可能是外来的佛像。“祭天金人”既然不是外来的佛像,是否有可能是佛教传入我国西北地区后,由匈奴人或是匈奴统治下的其他民族基于对佛陀形象的认识和想象而创制的呢?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这种可能性并不大。迄今为止,尚没有任何考古发现和可靠的文献记载能够证明佛教在公元前2世纪即已传入我国西北地区。主张“祭天金人”是佛像的崔浩、魏收等人是南北朝时期人物,距离汉武帝时代已过去了五六百年,其说未必可信,大抵是以他们那个时代所盛行的信仰去附会“祭天金人”。而公元前2世纪初还居住在河西走廊的月氏人,也是在迁入中亚并建立贵霜帝国以后,于公元1世纪后期,即迦腻色迦王统治期间才开始全面接受佛教信仰。足见在汉武帝时期佛教尚未在中国西北地区大规模传播,也就谈不上在赶走月氏人以后才控制河西走廊的匈奴人在当时会为佛陀塑像。
当代亦有学者认为“祭天金人”虽不是佛像,但有可能是其他外来神像。马明达先生在《七圣刀与祆教》一文中引述《永乐大典》卷2341《梧州府志》中的记载:“祆政庙,在州城东一百步。祆,胡神,按《汉图》,八月以金人祭天,其庙皆胡人居,中国所立,号天神”,认为此则材料“将汉代匈奴休屠王的‘祭天金人’以及匈奴的祭天活动同祆教扯到一起了。”[9](P10)马明达先生的此段论述引起了研究祆教学者的注意。随后“休屠王祭天金人”即祆教神像的说法得到部分学者的支持。此外,亦有说法认为祭天金人乃是当时伊朗人所尊崇之泰西塔尔神或东传的希腊神像等。
笔者认为,“祭天金人”是祆教神像的说法证据并不充分。学界一般认为祆教传入中国在两汉以后,进入休屠王故地所在的河西走廊地区的时间约在魏晋时期。[10](P79)马明达先生在《七圣刀与祆教》一文中所提到的《梧州府志》只是说“按《汉图》,(胡人)八月以金人祭天”。其在文中随后说道:“《汉图》不知是何书,似乎是东汉谶纬一类的书,今已不存,无从考知。”《梧州府志》所提到的“汉图”究竟是否是汉代书籍,描述的是否是汉代事物,都很难说。因此,不能单凭“汉图”二字断定汉武帝时期胡人以“金人”作为祭祀祆教天神的道具。何况梧州府在唐代始有其名,其地远在今华南一带,与匈奴故地相隔甚远。《梧州府志》所说的“胡人”,很有可能指的是隋唐以来从事海上贸易,并在当地定居的波斯人,未必是北方游牧民族。故而“休屠王祭天金人”与“汉图”提到的祆教“金人”不见得是一码事。
不仅如此,在祆教传入中国西北地区后,也缺乏证据证明当地信徒崇拜金人偶像。据唐代段式成《酉阳杂俎》卷四《境异》载:“突厥事祆神,无祠庙,刻毡为形,盛于皮袋”,同书卷十《物异》中亚粟特人的祆祠“内无像,于大屋下置大小炉,舍檐向西,人向东礼”。《沙州图经》卷三描绘敦煌祆祠是“立舍画神主”,《唐光启元年写本沙洲伊州地志残卷》记载伊州祆祠内部则是“中有素书形像无数”,并没有说西北祆教教徒有供奉“金人”的习惯。
至于“祭天金人”是东传的伊朗或希腊神祇塑像的说法,也都没有太多根据。要想真正弄清楚“休屠王祭天金人”的本来面目,还需要从草原民族自身的信仰中寻求答案。
二、“金人”与匈奴信仰之关系
以往学者们无论说“祭天金人”是佛像,还是祆教神像,亦或是其他外国神像,其立论的前提都在于认定匈奴人不会自己设计和铸造神像,所以“金人”及其所表现的神祇当系外来。这一点,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先生说的尤为清楚:“匈奴本为马上横行天下的游牧之民,尽管有建设国家的能力,但文化程度大体任处于未开化之境。因而像金人那样的巨大偶像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本国制造。休屠王金人乃国外制品,……则其所表现的神亦非外国之神不可了。”[11](P23)
但匈奴人果真没有铸造“祭天金人”的能力么?事实上,匈奴人冶炼铸造金属的历史悠久,1979年,在内蒙古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西沟畔匈奴古墓中出土了属于公元前3世纪晚期的铁器,包括铁剑、铁马嚼、铁锥、铁勺、铁辘等。[12](P129)苏联考古学家于1949-1951年期间,在前苏联布里亚特加盟共和国也发现了属于公元前1世纪匈奴人使用的铁器和铸造铁器的模型、冶炼炉等。[12](P129)以上考古发现说明匈奴早在公元前3世纪便开始使用铁器,并至迟在公元前1世纪已掌握冶铁和铸造铁器的技术。就各地已发现的匈奴铁器来看,“形制已很复杂,铸工亦甚精巧”。[12](P132)匈奴铸铜业亦颇具规模,我国内蒙古地区与蒙古国境内的匈奴墓葬中都发现过不少青铜器,不仅数量可观,种类也十分多样,既有兵器,如铜刀、铜剑、铜斧等,也有诸如铜马嚼、铜炉、铜炊具、铜钟、铜铃、铜镜之类的生活用具。除了冶铁冶铜,匈奴人还长于金银器制作。1972年,内蒙古杭锦旗阿鲁柴登的匈奴墓中,曾出土大批制造年代相当于中原战国时期的金银器。其中有鹰形黄金冠、黄金冠带、带有虎牛争斗图案的长方形黄金饰牌、镶有宝石的黄金饰牌,用薄金片压成的虎、鸟、羊、刺谓、兽头、火炬等形状的饰片,及金锁链、金项圈等;银器有虎头饰件,压制成的银饰牌等,都具有很高的技术水平。[13]
在匈奴,从事金属冶炼等手工业劳动的不仅有匈奴本族人,也包括掠夺来的外族奴隶。骁武凭陵的匈奴人有在战争中掠夺人口充作奴隶的习惯。《史记·匈奴列传》中说:“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照这样看,不仅匈奴贵族占有大量奴仆,就是普通战士,只要能抓住俘虏,便有权将其作为自己的奴隶。故匈奴人拥有奴隶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因此,尽管与农耕文明相比,匈奴的文化程度不见得很高,但其金属冶炼铸造技术却未必一定会落后于农耕文明。因为那些被掳掠来的来自农耕文明的工匠在从事冶炼铸造金属劳动的过程中,必然会将自己掌握的冶炼铸造技术传入匈奴。既然匈奴人都能制作出精美的金属武器和生活器皿,那么又何以断言匈奴没有能力铸造“祭天金人”,继而推定“祭天金人”所表现的神非外国之神不可呢!
古代匈奴人迷信鬼神,祭祀祖先,崇拜天地日月,有巫师。这些显然是萨满教信仰的特征。信仰萨满教的民族往往拥有自己的神偶或人形祭祀道具,而铸造拥有特殊用途金属人偶的习惯在中国古代北方大漠草原游牧民族当中也并不罕见。如北魏时代的拓跋鲜卑人有铸造“金人”以占卜立后的习俗。据《魏书》载:“又魏故事,将立皇后必令手铸金人,以成者为吉,不成则不得立也。”[3](P321)契丹人是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之一,据《辽史》载:“及帝崩,所置人户、府库、钱粟,穹庐中置小毡殿,帝及后妃皆铸金像纳焉。节辰、忌日、朔望,皆致祭于穹庐之前。”[14](P838)说明辽朝的契丹人有为皇帝及后妃铸造金像用以祭祀的传统。古代蒙古人所供奉的翁衮像(即萨满教神偶)中,也多有青铜、铸铁制成的人形偶像。[15]同样是北方游牧民族,又同样拥有萨满教信仰的匈奴既然已经具备铸造“祭天金人”的能力,那么他们有铸造“祭天金人”的习惯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休屠王身为匈奴贵族之一,他的“祭天金人”应该属于信奉萨满教的匈奴人在祭天时所使用的偶像。
三、“祭天金人”的用途和形制——从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信仰以及铸金人习俗谈起
关于匈奴人的祭祀习惯,现存的史料记载颇为简略。《史记·匈奴列传》云:“岁正月,(匈奴)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蹛林,课校人畜计。”《汉书·匈奴传》记载与之相同,只不过将“茏城”改为“龙城”。《后汉书·南匈奴传》载:“匈奴俗,岁有三岁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
从这些简单的记载中可知,匈奴在每年正月、春、秋都要祭祀天神。至于祭祀天神时会不会用到“祭天金人”,以及“祭天金人”形制如何,史书并没有提到。
生活在大漠草原上的古代游牧民族,因为自然环境相近,经济基础相同,因此在语言和文化习俗上相通之处不能颇多。如上所述,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多有铸造用于宗教仪式的“金人”的习俗,其中拓跋鲜卑所建立的北魏王朝就以“手铸金人”占卜立后。拓跋鲜卑与匈奴渊源极深。《后汉书》载:“和帝永元中,大将军窦宪遣右校尉耿夔击破匈奴,北单于逃走,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16](P2986)北匈奴西迁后,鲜卑据匈奴故地,留在漠北的匈奴人成为鲜卑重要的组成部分,鲜卑在文化习俗上受匈奴强烈影响。故而我们通过考察拓跋鲜卑的“金人”,也可以对匈奴的“祭天金人”有一个大致的推测和了解。
其实,在拓跋鲜卑人建立的北魏王朝,“金人”并不仅仅被用来占卜立后,凡占卜天命吉凶,皆用此物。《魏书》的《尔朱荣传》载:“(尔朱荣)犹疑所立,乃以铜铸高祖及咸阳王禧等六王子孙像,成者当奉为主,惟庄帝独就”,[3](P1647)“(尔朱)荣既有异图,遂铸金为己像,数四不成。时幽州人刘灵助善卜占,为荣所信,言天时人事必不可尔。荣亦精神恍惚,不能自支,久而方悟,遂便愧悔”。[3](P1648)这些都是将“金人”用以占卜吉凶的事例。能用以占卜吉凶,说明在拓跋鲜卑人眼中,“金人”与平常塑像不同,是用以沟通神明、寄托天意的灵物。但在这些记载中,“金人”并非是神像,而是凡人塑像,如《尔朱荣传》所说的“高祖及咸阳王禧等六王子孙像”及尔朱荣“铸金为己像”,或不知名人形偶像,如《魏书》的《皇后列传》中“手铸金人”者。
不仅北魏有铸造“金人”用以占卜的习惯,早在十六国时期,慕容鲜卑和冉魏也有此俗。《晋书》记载了慕容儁与冉魏使者常炜在谈及冉魏政权合法性问题时,慕容儁曾质问常炜:“又闻闵铸金为己象,坏而不成,奈何言有天命!”[17](P2832)由此看来,慕容鲜卑也相信“金人”可以寄托天命的说法。故铸造“金人”占卜天命当是鲜卑各部共有的传统。至于冉闵,虽是汉人,但曾被后赵皇帝石虎收为养孙,跻身为后赵贵族多年,必定深谙羯人习惯。慕容儁既以冉闵曾铸“金人”而不成之事来向常炜发难,说明当时羯人也有该习俗,与鲜卑人一样,他们眼中的“金人”可以象征天命,因而用铸造金人成功与否来判断天命有无。羯人铸造的“金人”也不是神像,而是可以塑造成占卜者自己的形象,这一点亦与鲜卑人相同。在前燕入主中原之前,羯人还不曾被鲜卑人统治过,因此很难说羯人有此风俗是受鲜卑影响,故而可能是本族固有习惯。
无论是鲜卑,还是羯,都与匈奴存在很深的联系。鲜卑与匈奴之关系,上文已述。而羯人,按《魏书》云:“其先匈奴别部,分散居于上党武乡羯室,因号羯胡。”[3](P2047)其实就是匈奴的一个分支。《晋书》亦载:“(石勒)其先匈奴别部羌渠之胄。”[17](P2707)羯人在血统上虽不见得就是匈奴本族,但长期被匈奴所吸纳和统治,有“匈奴别部”之谓,足见受匈奴影响之深。
两个曾受过匈奴巨大影响的民族均有铸“金人”以占卜天命的习惯,恐怕并非出于偶然。二者对金属偶像的这种特殊信仰,应该有着共同的文化渊源。如果再与“休屠王祭天金人”联系起来,那么鲜卑人与羯人对金属偶像的特殊信仰当来自于匈奴。
不过,“休屠王祭天金人”既言“祭天”,那么便不大可能单纯被用于占卜,而应被作为一种祭祀天神的道具被使用。在鲜卑人与羯人的信仰中,“金人”有某种预示神意的特殊功能。考虑到他们的“金人”可能与“休屠王祭天金人”有一定的渊源,可以推知和鲜卑人、羯人一样,匈奴人也相信“金人”这一用某种金属制成人形偶像具备通灵的特质,可以用于沟通神明。休屠王拿“金人”祭天,也应缘于此种认识。这种“祭天金人”很可能是在祭祀节日当中能通过特殊萨满仪式而引得神明前来依附的祭天神主。既然史书中提到的鲜卑人与羯人所铸“金人”都不是神像,那么“休屠王祭天金人”有可能也只是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抽象的人形偶像,而并非对某位神明形象进行具体描摹的神像。汉魏学者称其为“祭天主”或“象祭天人”而非神像,大概基于此缘由。
关于“祭天金人”的大小。纵观历史,无论是北魏的“金人”,还是契丹皇帝及后妃的金像,以及蒙古的青铜翁衮像,体型都不大。北魏占卜立后所用“金人”乃系嫔妃“手铸”,说明体型不可能很大,否则以女子的体力根本办不到这一点。契丹皇帝及后妃死后的金像,既然都能放在穹庐中的“小毡殿”里,而这类毡帐又是装载车上的“太庙”,[18](P122-168)也表明体型不会大。蒙古族的青铜翁兖像,一般供奉于香案之上,有的翁兖像干脆就是用毡子做成的小布偶,挂在毡帐内供奉,[15]形体很小。盖因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需要经常迁徙,“金人”、金属神像之类的物品如果体型庞大,势必难以搬运,给牧民们的祭祀活动带来麻烦。由此可见,“休屠王祭天金人”也不大可能是庞然大物。若然如此,白鸟氏所谓“那样的巨大偶像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匈奴)本国制造”的论断便是无的放矢了。
关于“休屠王祭天金人”的制作材料,古代文献记载中称其为“金人”。在古代汉语中,“金”既指金子,也泛指金属,因此不能单凭“金人”二字就断定这个“祭天金人”的材质。在上文已列史料中,冉闵、尔朱荣为自己铸造“金人”均没有成功,可见在当时铸造“金人”失败的概率很高,这与其制作材料有关。按《魏书》载,北魏尔朱荣“以铜铸高祖及咸阳王禧等六王子孙像”,用以占卜北魏孝庄帝元子攸是否有皇帝命,看来北魏人是用铜来铸造“金人”的。在中国古代常见的铜料中,铜锌合金的黄铜很早被用于制作铜器,但其冶炼难度很高,炼成以后熔铸所需温度也高于金银,然而用黄铜所铸器皿颜色明亮,美观程度接近金器,因此从铸造难度和金属美观程度两方面来考察,黄铜都极有可能是铸造“金人”的材料。既然北魏所铸“金人”的原材料可能是黄铜,那么休屠王的“祭天金人”也可能用相同材料制成。天然黄铜极难获得,而人工冶炼黄铜技术在明代以前还未臻于成熟,故而在明代以前,黄铜制品的出现具有极大的偶然性。[19]因此,匈奴的“祭天金人”弥足珍贵,以至于被汉朝人当作重要战利品记入史书。而这个用黄铜铸成的“祭天金人”所焕发出的类似黄金的明亮色彩大概给汉武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才会赐休屠王之子金日磾以“金”姓。
还需要指出的是,“休屠王祭天金人”并非像孟康等古代学者所认为的是匈奴各部共尊的祭天偶像。按《史记》《汉书》记载,匈奴要在五月“大会茏城(龙城)”祭天。这个“茏城”(龙城),作为“匈奴单于祭天,大会诸国”处,[2](P165)虽然还无法确指其地,但应该是在单于直辖的匈奴中部地区,绝不会在偏居匈奴右臂一隅的休屠王领地。单于祭天处既不在休屠王领地,又怎么会将匈奴各部共尊的祭天偶像放置在距离单于庭遥远的休屠王处呢?况且,倘若“休屠王祭天金人”就是单于祭天时所用之物,那么在元狩二年(前121)春天的河西之战中,休屠王丢失“金人”,正常情况下必定会被单于问罪。但实际情况却是,“其秋(元狩二年秋),单于怒浑邪王、休屠王居西方为汉所杀虏数万人,欲召诛之”。[1]单于要杀休屠王的原因,是他与浑邪王在和汉军的战争中连吃败仗,折损了匈奴数万人马,与丢失“祭天金人”并没有关系。故可以推知“休屠王祭天金人”只是休屠部自己用于祭天之物。
综上所述,西汉时期匈奴“休屠王祭天金人”既不是佛像,也不是祆教的神像,更不是东传的伊朗或希腊神像,应当是匈奴征服河西走廊之后,驻牧于当地的休屠王根据本民族萨满教信仰下令铸造的小型黄铜质人形祭天偶像,是在祭祀时能通过特殊萨满仪式而引得神明前来依附的祭天神主。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丁万录.匈奴休屠王“祭天金人”研究管窥[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5,(4).
[5]吕思勉.读史札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6]陈序经.匈奴史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7]汤用彤.魏晋南北朝佛教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
[8]宫治昭.近年来关于佛像起源问题的研究状况[J].敦煌研究,2000,(2).
[9]马明达.说剑丛稿[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
[10]张露.魏晋时期少数民族的迁入及影响[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5,(4).
[11]刘文俊.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93.
[12]林幹.匈奴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3]田广金,郭素新.内蒙古阿鲁柴金发现的匈奴遗物[J].考古,1980,(4).
[14]脱脱.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5]卢玉华.蒙古萨满神像[J].北方文物,2007,(2).
[16]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7]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8]沈括.熙宁使虏图抄[A].贾敬颜.五代宋金元边疆行纪十三种疏证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4.
[19]马越.中国古代黄铜制品与冶炼技术的研究状况分析[J].中国科技史杂志,2010,(2).
责任编辑:魏乐娇
“King Xiutu’s Mental Statue of Worship”
WU Fei
(Hebei University,Baoding 071002,China)
Abstract:Many scholars,in history and contemporary,believe that “King Xiutu’s mental statue of worship” recorded in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History of the Han Dynasty” is a foreign idol. This theory is lack of adequate evidence and challenged by modern researchers. The research on the northern nomadic people shows that their national belief and convention of making statues support the assumption that “King Xiutu’s mental statue of worship” was made according to their Shamanism belief. The Shaman rituals call for the god to come into the statue to carry out the practice of worshipping.
Key words:the mental statue of worship;Xiongnu;ancient belief;King Xiutu
[收稿日期]2015-06-16
[作者简介]吴飞(1989-),男,山西长治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
[文章编号]1004—5856(2016)05—0085—05
[中图分类号]K28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5856.2016.05.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