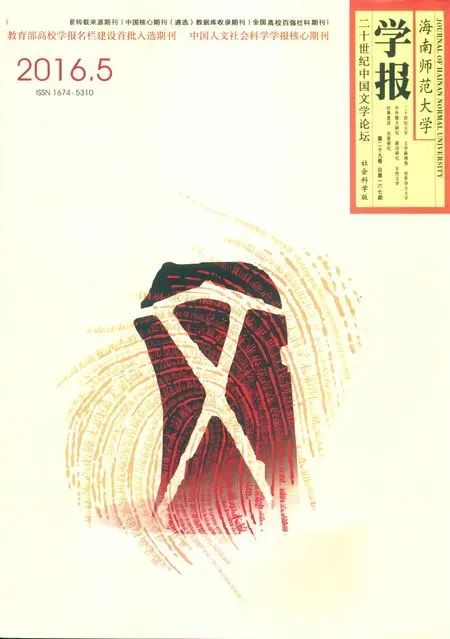《文心雕龙》的雅俗观及文学雅俗之辨
2016-03-16黄维樑
黄维樑
(俄亥俄州立大学 文学院,美国俄亥俄州 哥伦布市)
《文心雕龙》的雅俗观及文学雅俗之辨
黄维樑
(俄亥俄州立大学 文学院,美国俄亥俄州 哥伦布市)
摘要:《文心雕龙》谓文学风格有八种,第一种是典雅,而“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文心》一书,“雅”字常出现。《文心》论“谐”,则说它“辞浅会俗,皆悦笑也”,又说“俗皆爱奇”。《文心》并没有“雅文学”和“俗文学”的名目,也没有把“雅”和“俗”放在一起加以比较讨论;但上引的观点,对我们今天的文学雅俗之辨,颇有参考价值。一般来说,通俗文学“辞浅”、“奇”情、富娱乐性(刺激、“悦笑”),其读者为普通大众;高雅文学则辞较深、情较不奇、缺乏通俗的娱乐性,其读者为文化修养较高的人,尤其是文学学者。《诗经·国风》的情诗、很多唐诗宋词、荷马的史诗、莎士比亚的戏剧,在发表、流行的当时是通俗文学。屈原的《离骚》、杜甫的《秋兴》、艾略特的《荒原》、乔艾斯的《尤利西斯》,在发表时一直到现在,都是高雅文学。通俗文学如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且成为学者注释、赏析、研究的对象,则转化成为高雅文学。文章引述现代学者对雅俗文学的见解,列举古今中外的作品,包括上述提到的,以及狄更斯、余光中、九把刀等,作纵横析论,以畅题旨,并指出《文心》雅俗观历久弥新的理论价值。
关键词:《文心雕龙》;高雅文学;通俗文学
一、引言
文艺自古就有雅俗之分。《论语》中的《卫灵公》及《阳货》说孔子认为“郑声淫”,“恶郑声之乱雅乐”;换言之,“郑声”是俗乐。《论语·述而》且有“雅言”之说,雅言即雅正之言,是雅士、大夫的言辞。《孟子·梁惠王》把“乐”分为“世俗之乐”与“先王之乐”,“先王之乐”即雅乐。道家虽有逍遥、齐物之论,但对雅俗仍分别看待。《庄子·天地》:“大声不入于里耳,《折杨》、《皇荂》,则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于众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胜也。”意思是:大度的音乐入不了市井里巷之人的耳朵,而《折杨》、《皇荂》一类的曲调,听着就嗑然笑起来;所以,高雅之言不能在大众心中留下印象,至理名言也不能传播出去,俚俗的话却赢得听众。句中“高言”、“至言”即高雅之言。战国楚宋玉《对楚王问》:“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这是雅俗之异的经典故事。
时光流转二千多年,雅文艺和俗文艺,仍然是谈艺者的话题,是学术研究的对象。郑振铎1938年出版的《中国俗文学史》是一块里程碑。1980年代中期大陆的“中国俗文学学会”成立,其成员集体努力的一个成果,是吴同瑞等编的《中国俗文学概论》;此书于1997年在北京出版,是另一个标志。《概论》之后,2000年由范伯群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面世,又是个标志。台湾则有曾永义2003年出版的《俗文学概论》,与大陆的同类论著映照。*郑著1938年出版后多次重印;吴编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范编书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曾著由台北三民书局出版。有俗就有不俗,即有雅。在世纪之交,台湾的中兴大学举办学术会议,研讨雅文学与俗文学,《通俗文学与雅正文学:第一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于2001年出版;到了2012年,已办了九届。大陆则有朱栋霖、范伯群主编的《中国雅俗文学研究》第一辑于2007年出版,其后还有多辑。*此外有门岿、张燕瑾《中国俗文学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范伯群《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亦可参见谭帆《中国雅俗文学思想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此书首篇《“俗文学”辨》中对俗、世俗、风俗、通俗、雅俗等义解说甚详。这里提及的雅俗研究论著,只是笔者向来注意所及的,这绝不是一份有关论著的完整书目。本文所论为文学,为行文需要,有时不用文学而用文艺或艺术一词;所用的高雅文学一词则与雅正文学、雅文学相当。本文介绍《文心雕龙》对雅与俗的看法,征引古今学者对雅文学和俗文学的析论,对种种相关论点和文学现象加以综合研议,提出笔者对文学雅俗之辨的见解。
二、《文心雕龙》论“雅”和“俗”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研讨文学的论著,以体大虑周著称。这本文学理论的经典,有《定势》篇“雅俗异势”和《通变》篇“隐括乎雅俗之际”等说法,但没有“雅文学”和“俗文学”的名目,也没有直接把“雅”和“俗”放在一起加以比较论述。但它对“雅”和“俗”有多处论及,其观点对我们今天的文学雅俗之辨,甚有参考价值。
先说“雅”。首篇《原道》有“雅颂所被,英华日新”之语,第三篇《宗经》有“酌雅以富言”之说;“雅”固然指的是《诗经》篇章,却也与本文所论的雅文学相关。次篇《征圣》称“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其中“雅丽”与《体性》篇的“典雅”,可说是《文心雕龙》的关键词。“雅丽”、“典雅”是刘勰珍重的文学风格,甚至是最理想的风格。一直到最后的第50篇《序志》,他仍强调写作人要“按辔文雅之场”。《体性》篇论文有八体,一是“典雅”,而“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文心雕龙》以儒家学说为主导思想,刘勰认为征圣宗经,这样写出来的文章才典雅。次说“俗”。八体之七为“新奇”:“摈古竞今,危侧趣诡者也”,这里用了“奇”、“趣诡”等字。八体之八即序列最后的是“轻靡”:“浮文弱植,缥缈附俗者也”,这里用了“俗”字。刘勰论“俗”,下面将较详细地介绍其说,这里先行指出,他对“雅”和“俗”的看法,和近世和现代很多学者对雅正文学和通俗文学的解释,并无二致。
清代李渔《闲情偶寄·词曲部》认为戏曲的观众有读书人与不读书人,能让“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的才算成功。这里包含的意思是:读书人欣赏的是高雅文学,不读书人欣赏的是通俗文学。读书人即是学士大夫,不读书人即是一般平民大众。文学的雅与俗,是风格的体现,而题材影响风格。唐代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有“典雅”之品:
玉壶买春,赏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
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阴,上有飞瀑。
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其曰可读。
雅士大夫的生活及其品味,这是一写照。*题材影响风格。可参见林淑贞《题材风格论》,《诗话风格论》,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首章释“俗文学”,就这样指出:“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换一句话,所谓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曾永义在比较过多种“俗文学”的解释后,认为郑振铎的说法“最为平正通达”*曾永义:《俗文学概论》,台北:三民书局,2003年,第23页。。
金荣华论雅正文学,说“雅”指措辞,“正”指内容;《论语》说“子不语怪力乱神”,从传统的雅正文学看,“怪力乱神”就是“不正”;所以雅正文学就是措辞典雅而内容不涉“怪力乱神”的作品。金氏论通俗文学,则说:“通俗文学是写给大众看的文学。”*金荣华:《通俗文学与雅正文学的本质和趋势》,《通俗文学与雅正文学:第二届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中:中兴大学中国文学系,2001年,第8页等。
吴同瑞认为俗文学之美,包括“传奇美”,即“无奇不传,无传不奇”之美。这和清代金圣叹对《水浒传》宋江浔阳江遇险一节的批语可互相印证:“此篇节节生奇,层层遇险。”*吴同瑞等编:《中国俗文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4页。吴氏称俗文学还有“谐趣美”,即诙谐灵动的趣味,供“大众消遣娱乐”。*吴同瑞等编:《中国俗文学概论》,第25页。当代有论者指出,“台港通俗文学是台湾和香港发达商业社会的产物,它有着强烈的商品化特征”,有大众认同的“喜闻乐见”的承载形式。“台港畅销小说的特点是故事性、传奇性强,善于运用悬念来吸引读者”。“跌宕起伏、曲折动人的情节,从语言方面来看,通俗文学的语言都通俗易懂”。*朱寿桐主编:《汉语新文学通史》下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63页。
回到《文心雕龙》。《体性》篇的新奇和轻靡二体与“俗”有关,已如上述。此外,《知音》篇说:“俗监之迷者,深废浅售;此庄周所以笑《折杨》,宋玉所以伤《白雪》也。”在这些地方刘勰对俗有贬意。《谐讔》篇也论及“俗”,说“谐”这种文体“辞浅会俗,皆悦笑也”。换言之,“谐”的作品,或者说吴同瑞所称有“谐趣美”的作品,可供“大众消遣娱乐”,“会俗”正是适合大众阅读或观赏之意。“辞浅会俗,皆悦笑也”之外,刘勰在《史传》篇中提出了另一个重要观点:“俗皆爱奇”。刘勰论史时指出,史家“贵信史”,然而“俗皆爱奇,莫顾实理”,总爱夸张,“传闻而欲伟其事”。“俗皆爱奇”,读史如此,观文亦如此。刘勰“辞浅会俗,皆悦笑也”、“俗皆爱奇”等语道出了俗文学的特色,兼及其功能,与上面引述的近世和现代的相关见解正可互相发明。
《谐讔》篇在解释“谐”的意义之后,举了好几个谐趣的故事:“昔齐威酣乐,而淳于说甘酒;楚襄宴集,而宋玉赋好色。意在微讽,有足观者。及优旃之讽漆城,优孟之谏葬马,并谲辞饰说,抑止昏暴。”其中“优旃之讽漆城”的故事,据《史记·滑稽列传》所说,是这样的:优旃“善为笑言,然合于大道”;话说秦二世打算把一座城髹漆,优旃说:这好啊,虽然百姓将为费用发愁,但很好看呢;只是有个困难,哪里可找到一个大的房子罩住城,以便把它阴干。秦二世听后取消了漆城的计划。“优孟之谏葬马”同样出于《史记·滑稽列传》:春秋时楚庄王所爱的马死了,打算采用为大夫举殡的仪式来葬它。群臣劝谏,阻止不了。优孟故意说,用大夫礼太薄待了,应该用国君的礼仪来葬它才对。先秦时期如果已有手机短信、微博、短信,那么漆城、葬马一类的时事,一定是通俗文学大好的题材,写成的谐趣短文,为千万网友所爱读和转发。
依照“辞浅会俗,皆悦笑也”、“俗皆爱奇”的理论,这里再举一例。《孟子·离娄下》有齐人与妻妾的故事:
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瞷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遍国中无与立谈者。卒之东郭墦间,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餍足之道也。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与其妾讪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
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
齐人言行怪异,整个故事有传奇色彩,属上述所说“怪力乱神”中的“怪”。故事讲完了,孟子还作了主题阐释,或者说教训总结。《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有小说家之目,认为: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我们不妨把这类“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视为通俗的故事和议论。*《孟子·齐人》有一妻一妾的故事,不但是个有趣的寓言,且是个技巧卓绝、题材独特的短篇小说。《齐人》具备人物、事件、情节结构等小说要素,统一而完整,字字珠玑,最能符合现代“有机体”的理论要求。它的反讽(irony)技巧,如“良人”一词的正言若反、悲喜场面的巧妙经营等,尤其令人拍案叫绝。可参见黄维樑:《中国最早的短篇小说》,《中国文学纵横论》,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8年。六朝的志怪、唐的传奇、宋的《京本通俗小说》、明的《三言》《两拍》、20世纪的言情(包括“鸳鸯蝴蝶”)、武侠、侦探、推理、奇幻小说,即以“奇”、以种种“怪力乱神”吸引读者。现代的张恨水、金庸、琼瑶、亦舒一直到当今九把刀、郭敬明的热卖作品,就是这类传奇、通俗小说。
在西方,先有荷马史诗在诵读时吸引了大量听众,以至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戏剧的大受欢迎,以至印刷发达通俗读物大增,20世纪广播、电视出现后大众传播日盛,包括通俗文学在内的大众文化流行,通俗剧(melodrama)、连载小说(serial fiction)、好莱坞电影、电视肥皂剧(soap opera)等等是其主要类型,而这些都不脱“辞浅”、“传奇”的特色。因为地球缩小成为村庄,而“东海西海,心理攸同”(钱锺书语),东方的受众(或者说“听阅人”,audience)自然悦读、悦听乐观之,受之者极众。
《哈利·波特》一类小说的奇幻不必说,这里只说目前两岸三地都有众多读者的九把刀。原名柯景腾、笔名奇特的九把刀,作品以奇标榜。其小说《卧底》以这样的内容开始:
外表平凡的少年圣耀,有着极不平凡的手掌掌纹,掌纹的轮廓脉络是一张摄取人魂的恶魔之脸。所有进入他生活圈子的人,都会驾鹤西归。面对自己像得了瘟疫一样的凄惨人生,圣耀到了近乎崩溃的边缘。于是,他四处求仙拜佛,极力去挽救最后的亲人——妈妈。但是,手掌仍然没有回答,恶魔的脸仍在继续狞笑……*参见九把刀:《卧底》,南宁:接力出版社,2006年,封底折页《关于本书》。
他另一部小说《杀手》所述的四个故事中,首个题为《杀手鹰:阳台上灿烂的花》,题材离不开通俗小说的情爱与暴力。酷酷的杀手与美术系大二女生有一段爱情;他行凶杀人,使用暴力而若无其事。*根据《杀手》,台北:春天出版国际文化有限公司,2005年7月初版7刷。九把刀的文字浅白,青年读者易读且爱读;爱读的一个原因是流行语多,令人觉得亲切。如当前畅销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其常用的“靠”(与粗口“操”的音近)一词,就是“会”合当下青年流行“俗”语的“浅”白之“辞”。
《文心雕龙》“辞浅会俗”、“俗皆爱奇”的说法正道出了今天我们所说通俗文学的特色。《体性》篇的八体中,“典雅”排头,“奇”、“趣诡”、“俗”等在末;首尾之异,应有刘勰抑扬轻重之意。从其它篇章的论述看来,扬雅抑俗之意,甚为明显:如《辨骚》称《楚辞》为“雅颂之博徒”;《乐府》称“自雅声浸微,溺音腾沸”,“溺音”即郑声,就是轻靡附俗之声。《体性》再扬雅声,称“习有雅郑”,“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所以“童子雕琢,必先雅制”。
三、通俗作品后世需要注释
刘勰在《知音》篇中称知音甚难,知音难的原因之一为作品优劣难分。他这样说:
夫麟凤与麏雉悬绝,珠玉与砾石超殊,白日垂其照,青眸写其形。然鲁臣以麟为麏,楚人以雉为凤,魏民以夜光为怪石,宋客以燕砾为宝珠。形器易征,谬乃若是;文情难鉴,谁曰易分?
文之“雅郑”(“雅俗”)也难分吗?还是二者截然可辨?
刘勰亟称《诗经》之为儒门经典,是《宗经》篇所示写作人宗奉的五经之一:“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辨骚》篇开宗明义即以“《风》《雅》寝声”为憾;由此看来,《诗经》为雅正文学的代表,殆无疑义。然而,《诗经》的篇章在当时写作、传播时全都是雅正文学吗?《诗经》里的《雅》和《颂》固然多是大夫之作、庙堂之篇,是雅正文学;但《诗经》里《国风》的很多作品,如《关睢》、《桃夭》、《摽有梅》、《将仲子》、《女曰鸡鸣》、《有女同车》、《狡童》、《静女》等,辞意浅易,讲的是恋爱婚姻,是一般老百姓能懂能唱的,是当时大众化的流行歌曲,其性质与功能与今天的流行歌曲无异。朱熹《诗集传·序》:“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正是此意。至于社会抗议诗如《魏风》的《硕鼠》,语言同样浅易,反战诗如《豳风》的《东山》,篇幅虽较长,内容也并不深奥。《小雅》的《蓼莪》涉及孝道,内容也不“古雅”,语言亦甚浅白。这里随意举出的《诗经》篇章,都有《文心雕龙·谐讔》所说“辞浅会俗”的特色,是当时的通俗文学。这些,刘勰却在亟称《诗经》之为儒门经典、为雅正文学的代表时,没有加以辩说。
周朝已有采集歌谣的官员,后来鲁国也有乐师编定诗歌。孔子以《诗经》教学生:“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三百五篇有兴观群怨的功用,一旦入了教室(classroom),“升堂入室”,渐渐演变成为经典(classic),地位大为提高了。孔子之后传授《诗经》的,有鲁国申培公、齐国辕固生、燕国韩太傅三家,又有鲁国的毛亨、赵国的毛苌。《诗经》成为教材,专家加以研究,以至后世论者和文学史家大力推崇,乃成为雅正文学,取得经典地位。这样的过程是通俗文学“雅正文学化”的一个典范。换言之,刘勰所称述的雅品,其中相当一大部分的出身并不“高贵”。
里巷歌谣的用词,是当时流行的民间语言,通俗易懂。但语言因时代而变化,一代有一代的语言。《诗经》第一首《关雎》的“左右流之”、“左右芼之”,流、芼二字应是当时的口语,是捋取、采摘之意。不知道孔子教学时,师生对流、芼二字的理解有没有问题,有没有“词语解释”这一项。今天教师向中学生以至大学生解说《关雎》时,则必要有这一项,否则学生就不明白。此诗“寤寐思服”中的思、服二字的情形大概相同。作品成为研读对象,很多语词要注释才能让读者明白。这不止是雅正化,更是典雅化了;典在这里有古典、典奥、古奥的寓意。语词要注释,作品涉及的人事物要注释,这是雅正文学和“雅正化”文学常有以至必有之事;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又是常常流转变化的。且略举当前一些语词为例。
现在一般大众读来觉得语言浅易的作品,如果继续流传,一二十年后可能变得不全然浅易,不要说一二百年后以至一二千年后了。例如,当代通俗的词语中,“晒”指将自己珍惜的事物或引以为傲的才能在人前展示(用时每含贬义,有炫耀之意),此词大概源自香港式粤语;埋单、爆料等词亦然。这些词语现在大陆和台湾也流行。它们的寿命如不长,在后世成为“古”且“稀”之言,就非注释不可。超哈、好康、冻蒜、奥步、酷、轰趴这些闽南话或音译的外来语,台湾当代的读者读来不成问题,年代久远则难说。公车在台湾指巴士之类的公共交通车辆,在大陆则指政府机构(公家)的车辆。台湾的公车等于大陆的公交车。此公不同彼公,后世非注释不为功。“酷酷嫂”周美青,几个世代后的人读来会否误会周美青是个冷酷、残酷的妇人,大概也得靠注释。大陆的政府官员向民众拜年,说要“和大家一起置顶幸福,hold住美好未来”,这真是潮语。*南京《扬子晚报》2012年1月19日,第A5版。潮流是夹杂中文英文,是网罗网络语言。中英夹杂的“hold住”且不说。“置顶”为网络语,是“把XX置于最高地位”之意。若干年或若干世代之后,“置顶”如果不再“置顶”或“置中”(且容笔者杜撰此词,它是“把XX置于其中”之意)潮语,甚至不再是潮语,幸福的读者就不幸地不懂了,至少“无感”(no feel)了。“无感”是另一个潮语。在英语里这类的例子也绝不缺乏。如当代英语的conscience意为良知,sadness意为忧伤;在莎士比亚的剧本中,conscience解作思想,sadness解作严肃。不靠注释,我们就不能了解其意。莎剧《汉穆莱特》中丹麦王子疯了,2012年2月一位篮球王子也“疯”了:Jeremy Lin(林书豪)成为Linsanity(“林来疯”)。从Lin和insanity到Linsanity,如果林书豪不能“永续地”(sustainably)风靡若干年,一两个世代之后的读者在作品中遇到Linsanity或“林来疯”就要靠注释才能明白了(幸好Linsanity已火速般被纳入全球语言观察〔GLM〕字库,以后的英文字典可将这个字列入)。
注释包括解释词语的意义,还有解释非潮流的较远年代的事物。如果今天某些微博短文流传后世,后世的读者如非渊博之士,就要靠注释才能读懂下面这则微博:
鲁迅回乡发现:闰土房子被强拆,大儿子上课时死于地震,老二喝三鹿结石了,老三打疫苗残了。阿Q因土地征用,多次上访被毙了。孔乙己研究生毕业即失业,去KTV买醉被打废了。祥林嫂丈夫去山西挖煤丧命,儿子在幼儿园校车车祸中死去。鲁迅怒发微博,被删帖封号,后以短信发《新狂人》,当即送安定医院。
在这篇戏剧性十足的批判现实主义微型小说中,三鹿、上访、KTV等都要注释,为什么说是安定医院而非别的医院,为什么说在山西而非别的地方挖煤,亦然。说不定闰土、祥林嫂、狂人以至鲁迅,也成为注释的对象。
四、通俗作品的高雅化、正典化
原来通俗的作品,流传广远,其内容思想和写作手法受到多方面肯定,且成为谈论、学习、研究的对象;各种注释(包括上面所说语词的注释)、分析、评论随着产生,作品乃高雅化、正典化(canonized)。这里说的高雅化,与读者和研究者的身份属高人雅士不无关系。《诗经》中《风》诗的高雅化,情形如此。很多唐诗、宋词(自然包括有井水处即有人歌唱的柳永词)、元曲、明清民国小说的高雅化,也如此。这里再举些例子以为说明,如充满“怪力乱神”的《西游记》。百年来肯定这部古典小说的言说极多,这里引述一条最近的评论。最新的电视连续剧《西游记》的制作人张纪中认为:
《西游记》的主题其实并非曲折、离奇和惊险,而是贯穿其中的文化表达,是对世界和内心的价值指证。每个人的从生到死都是一部《西游记》,都是取经的过程,遇到的都是妖魔鬼怪,无非《西游记》以更高明的方式把我们的心魔,如贪欲、色欲、嫉妒外化了,同时它还讲了怎样去对待这些心魔。
张纪中说:“我重拍《西游记》最大的动力,就是希望让今天的人们能够更清晰地知道我们的人生,去除我们心中的欲念,变得更加善良。”*转引自《观众尖锐评说新〈西游记〉》,《深圳特区报》2012年2月15日,第C08版。张氏是电视连续剧《西游记》制作人。其说法正好用来说明“通俗文学”不普通、脱凡俗的文学品位。
又如张恨水的小说。1920、1930年代张恨水写了《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作品,极受读者欢迎。然而,当年的文学界一般都视他为通俗小说家,说他的作品为“鸳鸯蝴蝶”小说,不能登大雅之堂。近二、三十年来,张恨水等一些鸳鸯蝴蝶派作家,有人作深入研究了,“平反”了。1988年和1994年,中国大陆先后举行了张恨水学术研讨会,各地学者云集,对张氏小说所写的人情世相,对其反映的社会现实性,特别重视。首届会议的论文集,于1990年出版。在此之前,美国的学者如夏志清、林培瑞(Perry Link),早已著文探讨张氏等鸳鸯蝴蝶派作品的文学价值。张恨水这位雅俗共赏的小说家,渐渐正典化了。*可参见《译丛》(Renditions)1982年春秋两期合刊通俗小说专号中,张恨水等通俗小说家作品的英译及评论;赵孝萱《张恨水小说新论》,台北:学生书局,2002年;另请参见黄维樑:《香港文学初探》,香港华汉文化事业公司,1985年;《香港文学再探》,香港:香江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两书中多篇论高雅与通俗的文章;以及黄维樑:《文学的雅与俗》,《期待文学强人》,香港:当代文艺出版社,2004年。
在西方,荷马的史诗《伊利亚德》和《奥德赛》由诗人吟诵时,虽然内容丰富、情节动人,语言仍是浅易的;普罗大众容易听得懂,更爱听其“怪力乱神”的惊险奇诡故事,它们乃能流传广远,历久不衰。罗马继承希腊文化,荷马的史诗进入教室,成为经典,乃既正且雅了。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汉穆莱特》等剧,生动语言进入时人之耳,常涉及性爱暴力的故事刺激时人之心。美国继承英国文化。一直到19世纪,美国从大城到小镇,莎剧处处上演,处处朗诵。达官贵人与普通百姓,常常在同一剧院里观赏莎剧,而剧院的喧哗吵闹,也许不下于中国数十年前的京剧、粤剧剧场。在17至19世纪,莎士比亚当然有其知音。不过,到了19世纪末,莎剧的语言“变得”难懂起来,连大学生阅读也感到吃力,非靠注释与导读不可,莎氏作品的学术研究于是日益蓬勃,学者认为莎氏文才卓越,其人物性格、时代风尚、哲理宗教等议题饶具探讨价值。经过文人雅士的品题、品评,莎剧这些俗物才“提升”为雅品。*参见Lawrence Levine:William Shakespeare in America,Highbrow/Lowbrow: the Emergence of Cultural Hierarchy in America,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Lawrence Levine在书中第225页引述Hiram Stanley的话,这样形容“俗人”即普罗大众:他们只喜欢“饮食烟酒男女,喜欢吵闹活跃的音乐和舞蹈,喜欢华丽的表演……”他们喜欢的,用今天的话来说,是通俗流行普及商业消费的大众文化,诉诸感官为主的。反过来说,较为文静的、诉诸理性的文化,就是高雅、精雅的文化。我们尚可补充的是:欣赏高雅文化需要修养、训练,而通俗文化较不需要。
再以狄更斯为例。他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大概仅次于国宝莎士比亚。他一生写了十多部小说,受大众欢迎的程度,与后来东方的张恨水、高阳和金庸相比,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美国同样被“追捧”。1842年和1868年,狄更斯先后两度在费城,受到今天摇滚乐巨星一样的欢迎;光是与“粉丝”握手,就用了几个小时。第二次在费城时,狄更斯自诵作品,狄迷露营等待购票,“黄牛”则炒卖,其盛况只能用狂热来形容。1930年代朱自清参观伦敦的名人故居,引述文学史家之言,称狄更斯是“本世纪最通俗的小说家”*佩弦:《文人宅》,《中学生》1935年第55期,第53页。。时光使狄更斯高雅化、正典化,他成为学者研究的重要作家(major writer)、英国文学史上雅俗共赏的大文豪。他实至名归,其小说人物形象鲜明、典型多类、刻画入微,情节动人而笔调细致锋利,庄谐兼之,对人生社会有刘勰所说的“顺美匡恶”之效。而且,其内容有普遍性。加州大学的狄更斯专家约翰·乔丹(John Jordon)最近指出:“狄更斯笔下的种种社会问题,今天仍然如影随形跟着我们:如贫穷、财富不均、虐待儿童、社会阶级、生于低层人望高处引生的各种情事。”狄更斯已成为英国文化遗产的一大笔财富。2012年2月7日是他二百周年诞辰,英国的王储、伦敦的市长、全国文化学术各界的精英,为此举行连串庆祝活动;英国文化协会主办的“狄更斯2012”更是全球性的,参与的国家有50个之多。我们只能用普天同庆、盛况空前来形容。现代的狄学与莎学一样,都是严肃的雅士的学术。*参见黄维樑:《全球朗诵狄更斯》,《深圳特区报·人文天地》2012年2月9日。
通俗作品流传久远,为不同时代读者、批评家、文学史家所肯定,成为研究注释的对象,高雅化了。也有一些通俗文学当代就迈向高雅化的。20世纪产量与读者都极多的武侠小说,文学地位低,甚至有人认为不入文学之流。然而,从1980年代起,情形有了很大的改变。以《书剑恩仇录》、《射雕英雄传》等名闻遐迩的金庸(查良镛),在1980年代中期获香港大学颁授荣誉博士学位,1994年获北京大学颁授荣誉教授职衔;他的武侠小说得到多方面的肯定,且有了外文译本。一些较不保守的文学批评家,更把金庸雅俗共赏的小说与鲁迅、巴金、沈从文的作品并列,予以极高的评价。1980年代以来,研究金庸小说的学者,愈来愈多,有关论著和学术研讨会不断出现,“金学”建立起来。他的小说,不管是《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鹿鼎记》或是其它,就都登龙门、得高位,“问鼎”高雅文学了。
上面提到的九把刀,自言爱情、奇幻、武侠、科幻、惊悚、爆笑文学等都是他的“拿手好戏”,其作品离不开“俗皆爱奇”的“奇”。他的书先在台湾出版,后来也在香港、大陆发行。大陆有这样的书评:“九把刀以现实社会为蓝本,构建了一个虚拟世界,并通过对非现实世界的描述呈现了现实世界中的种种矛盾,弘扬了真善美。”*参见九把刀:《卧底》,南宁:接力出版社,2006年,封底折页《关于本书》。“阅读九把刀的作品会产生奇妙的快感和美感,是因为其作品融合了各种复杂审美心理,让人进入了一种高级享受的精神层面。”*《中华读书报》书评,转引自九把刀:《卧底》,南宁:接力出版社,2006年,封底。2011年11月大陆某机构且颁给九把刀一个“中华文化人物”奖,11月5日,他又在北京大学演讲。如果这些好评和荣誉增多,作品又成为学者专家研究的对象,则九把刀的高雅化是为期不远的。他的《杀手》首章题为《任性的杀手》,作用有类于序言,用了四个比喻形容杀手,又用了弗罗伊德、人类学等词,有文化点缀之效。*根据《杀手》,台北:春天出版国际文化有限公司,2005年7月初版7刷。如果他的作品终于高雅化,那么这些文化点缀正是“伏笔”。九把刀由于《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小说和电影的流行,“那些年”三字已成为潮语,被袭用套用之多,不下于二、三十年前起流行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一语。*畅销卖座的通俗文艺影响不可小觑。香港一位专栏作家古德明在2011年12月21日刋出的文章《那些年的最好之一》中说:台湾作家九把刀小说《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最近拍成电影,“那些年”马上成为流行词语。上海作家毛尖发表《约夏贝尔》一文说:“那些年,我们只读外国诗。”香港教育学院副教授沈旭晖发表公开信,题目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黄毓民》。“‘那些年’应是英文in those years的化身。”古氏所举之外,其它例子甚多。另一位香港专栏作家陶杰2011年11月25日在其专栏文章《最难忘的对白》中指出:“最近外国流行票选‘我最难忘的电影对白’,西方电影经典像《北非谍影》男主角堪富利保加‘我们将永拥有巴黎’(We'll always have Paris),还有《乱世佳人》女主角慧云李的‘毕竟,明天又是新的一天’(After all, tomorrow is another day),通常是大热双冠军。”他语带夸张地说:“美国荷里活,对于人类,是伟大的文化贡献,凭这一对感人千古的对白就够了。”长时期为歌星周杰伦撰写流行歌词的方文山,其作品得到不少人的喜爱。台湾清华大学前任校长刘炯朗在一篇关于方文山的长文中说:“方文山的《青花瓷》也让我们想起十九世纪英国名诗人济慈(John Keats)写的一首诗《希腊古瓮之歌》(Ode on a Grecian Urn)。”*刘炯朗:《国文课没教的事》,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第139页。如果有更多这样的相提并论,方文山一定文重如山,向高雅之门迈进了。通俗作品为高人雅士所接受、所喜爱,乃成为雅俗共赏的文学。这一节所论的种种,正附带出这个观点。
五、“雅”“俗”难划分与“雅”“俗”可共赏
通俗作品可能转化为高雅作品,正因为如此,用以分辨雅俗的一些标准,有时会变得模糊起来。上面征引《文心雕龙》“辞浅会俗”、“俗皆爱奇”的说法,以指出通俗文学的特色。现代西方学者也认为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的特色,是以诉诸受众的感官为主的,常有煽情滥情之处。反过来说,较为文静的、诉诸理性的文化则属高雅文化。目前很多正典、高雅作品是由通俗作品转化成的,因此以诉诸感官与否、以奇情煽情滥情与否,作为雅俗之辨的标准,似乎也有点含糊不清了。
正典性的作品如《麦克佩斯》、《牡丹亭》、《西游记》、《尤利西斯》、《百年孤寂》等的“诡异”、“谲怪”成份,是每个文学学者都知道的。连高古的《楚辞》也如此。刘勰盛称《楚辞》,誉它“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难”;同时指出《离骚》、《天问》、《招魂》等篇的“士女杂坐,乱而不分;娱酒不废,沉湎日夜”的“荒淫之意”,以至“木夫九首,土伯三目”等的“诡异”、“谲怪”内容。
至于滥情煽情,到底情是何物?滥情煽情与多情深情的界线怎样划清?《红楼梦》中黛玉葬花、黛玉焚稿表现的是多情深情,还是滥情煽情?香港的“通俗”“流行”“言情”小说家亦舒的《香雪海》这样写情:
上天啊,我一生活了近三十岁,最痛苦是现在。我心受煎熬,喉头如火烧。我辗转反侧,不能成眠。与香雪海在一起,我看到的是叮当;与叮当在一起,我闭上双目,看到的又是香雪海。整个人有被撕裂的痛苦,但表面上还不敢露出来。我一不敢狂歌当哭,二不敢酩酊大醉,一切郁在体内,形成内伤。*亦舒:《香雪海》,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83年,第37页。
这写的究竟是什么情:通俗的?高雅的?无疑,这是爱情的苦杯,与《圣经》中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那一个,同样使人肝肠寸断。如果应该分辨亦舒小说中这段情的雅俗,我们似乎也应该分辨耶稣客西马尼园那份情的雅俗。然而,有这样的需要和可能吗?
电影《泰坦尼克号》(Titanic)、小说及电影《麦迪逊之桥》(TheBridgesofMadisonCounty)、小说及电影《霸王别姬》的爱情,是雅的还是俗的?以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而著名的白桦,1990年代他是一位“后中年”作家,那时电影《麦迪逊之桥》放映,他看了很喜欢。一次,他有爱奥华城(Iowa City)之旅,特别要求当地的文友,带他到附近参观电影中的麦迪逊之桥。一位当年二十余岁的英文系女生,看过《麦迪逊之桥》之后说,她不欣赏这本小说及电影,嫌它不深刻。她看了电影《泰坦尼克号》,却大为感动,影片中的露丝,遇到像杰克那样的深情男子,实在刻骨铭心。1998年,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Madeleine Albright)在北京观看一部中国电影,她和该电影的导演都表示不喜欢《泰坦尼克号》,嫌它肤浅。当普天下很多年轻人用眼泪浮起《泰坦尼克号》之时,它被评为肤浅,与奥氏心气相通的是导演《霸王别姬》的陈凯歌。
李渔在《闲情偶寄·词曲部》里表示:戏曲的文词“做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又与不读书之妇人、小儿童看,故贵浅不贵深”,因此要像元曲那样“意深词浅,全无一毫书本气”,方为佳构。*吴同瑞等编:《中国俗文学概论》,第381页。“意深词浅”难能可贵,但是感情思想的深刻、深切与否,感受往往因人而异,并无明确更无绝对的标准来加以衡量。“雅”“俗”确难划分,“雅”“俗”确可共赏。*可参见朱自清:《论雅俗共赏》,《观察》第3卷第11期,第17-18页。金庸通俗的武侠小说至今得到高级知识分子,包括文学教授的嗜读(否则自然谈不上上述的“问鼎”高雅文学);还有写《杀夫》的李昂爱读琼瑶,写《游园惊梦》的白先勇爱读还珠楼主,都是高雅作家对通俗作品的“垂青”。英国1960年代流行乐队披头士(The Beatles)的歌曲为当时不少高雅的现代文学家(包括台湾的余光中、香港的黄国彬)喜爱;21世纪韩国电视通俗剧《大长今》迷倒的观众包括人文学科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金耀基等等。凡此种种,既印证了《孟子》的话:“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另一方面,也说明雅俗难辨,正像《文心雕龙·知音》说的“文情难鉴,谁曰易分”。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界流行“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理论,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成为研究对象。纽甘穆(Horace Newcomb)等人指出,通俗文化,尤其是电视这媒体,所呈现的内容,远远比表面我们看到的要复杂得多。*参见Stanley J. Baran & Dennis K.Davis,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Foundations,Ferment,and Future, Belmont,CA:Wadsworth/Thomson Learning,2003,pp. 247-249.这再次说明深浅雅俗之难以鉴别、划分。当然,文学作品之传后,要情思深刻且具相当的普遍性,题材和技巧有相当的创新,即《文心雕龙·辨骚》说的“自铸伟辞”。有时还要加上运气。雅文学和俗文学基本上都如此,不同的是俗文学流传后世,而成为注释、研究的对象,就雅化了,不再是俗文学了。我们只能说,某些被众多评论家认定是粗俗、恶俗的低劣文字,是无论如何高雅化、正典化不来的。
六、一诞生就“高雅”的作品
文学有其雅俗难分之处,却也有作品一诞生就是高雅文学的。《诗经》中的《雅》(尤其是《大雅》)、《颂》、屈原的《离骚》、“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的汉赋、李白的《蜀道难》、杜甫的《秋兴》八首,以至今人余光中的诗如《唐马》、《慰一位落选人》,散文如《鬼雨》、《逍遥游》,以及现代作家钱锺书、梁锡华、董桥、黄国彬的“学者散文”,一出生就有高雅的身份。一百年前陈独秀倡言文学革命,要打倒贵族文学、建立平民文学。我们确有“贵族”文学。
余光中的《乡愁》、《民歌》等“辞浅”,所以通俗,但是另一些诗如《唐马》、《慰一位落选人》则不然。这里仅以此二首诗为例略加阐述。《唐马》一诗,从秦时明月汉时关,到唐三彩,到20世纪香港的赛马博彩,到中国、苏联的边境冲突,读者都必须有认识;香港那些中学毕业后就忘了《诗经》的普罗大众,怎会去读它、读懂它、欣赏它、喜欢它呢?《唐马》一出马,就跑进高雅文学的殿堂。*以下为余光中的诗《唐马》:“全文骁腾腾兀自屹立那神驹/刷动双耳,惊诧似远闻一千多年前/ 居庸关外的风沙,每到春天/ 青青犹念边草,月明秦时/关峙汉代,而风声无穷是大唐的雄风/ 自古驿道尽头吹来,长鬃在风里飘动/旌旗在风里招,多少英雄/ 泼剌剌四蹄过处泼剌剌/ 千蹄踏万蹄蹴扰扰中原的尘土/叩,寂寞古神州,成一面巨鼓/ 青史野史鞍上镫上的故事/无非你引颈仰天一悲嘶/寥落江湖的蹄印。 皆逝矣/ 未随豪杰俱逝的你是/ 失群一孤骏,失落在玻璃柜里/ 软绵绵那绿绸垫子垫在你蹄下/ 一方小草原驰不起战尘/看修鬣短尾,怒齿复瞋目/暖黄冷绿的三彩釉身/ 纵边警再起,壮士一声忽哨/ 你岂能踢破这透明的梦境/ 玻璃碎纷纷,突围而去?/仍穹庐苍苍,四野茫茫/ 觱篥无声,五单于都已沈睡/沈睡了,眈眈的弓弩手射雕手/穷边上熊觊狼觎早换了新敌/毡冒压眉,碧眼在暗中窥/ 黑龙江对岸一排排重机枪手/ 筋骨不朽雄赳赳千里的骅骝/ 是谁的魔指冥冥一施蛊/缩你成如此精巧的宠物/公开的幽禁里,任人亲狎又玩赏/ 浑不闻隔音的博物馆门外/芳草衬踏,循环的跑道上/ 你轩昂的龙裔一圈圈在追逐/ 胡骑与羌兵? 不,银杯与银盾/ 只为看台上,你昔日骑士的子子孙孙/ 患得患失,壁上观一排排坐定/ 不谙骑术,只诵马经。”余氏的《慰一位落选人》,内容涉及尼克松、福特、卡特几位美国总统的经历,又有水门案,又有华府地理,更有英国诗人约翰·邓恩(John Donne)的语句,在中国方面,则毛泽东、刘少奇、牛鬼蛇神等或隐或现。读者若非对美国当时的政治、中国文革的本末,有基本的认识,就难以理解这首诗。换言之,只有“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士人、雅人能理解此诗。此诗一出生就成了“贵族”,过了五十年、一百年后,连雅人也难解索,要读懂此诗,就更非靠注释不可了。
在西方,17世纪米尔顿(John Milton)的史诗《失乐园》(Paradise Lost),也是一诞生就是“贵族”,只有博学的读者才能理解诗中各种神话、宗教的典故。约翰逊(Samuel Johnson)有“容易的诗”(easy poetry)之说,《失乐园》显然应属于对比性的“艰难的诗”(difficult poetry)。此诗开首的逶迤绵长句子,构成其高昂气度(lofty style)的,就够使读者“英雄气短”了。艾略特(T.S.Eliot)1922年发表的长诗《荒原》(The Waste Land),意象并置、情景割裂、时空交错,已够晦涩了;诗中英文之外还有德文、法文、意大利文、拉丁文、希腊文的典故,还有似乎更烦人的梵文。这样语言多元化,只有钱锺书一类的学者才能消化。艾略特为美国人,他认为英国文化较诸美国深厚,而入了英籍。《荒原》一发表就入了诗中精英之籍。同年乔艾斯(James Joyce)出版了《尤利西斯》(Ulysses),煌煌然的意识流长篇小说,写的虽然只是几个平民百姓的凡俗生活,但里面希腊罗马阿拉伯的神话传说、荷马史诗、《圣经》故事,与当时爱尔兰的社会事物或平行或对比地交织绾结,文学系的教授忙于解读、注释,可说一出版就超俗入雅,稳登高雅文学的高位。
大体而言,自20世纪初以来,作品一诞生就属于高雅文学的,一般都比较讲究技巧,如比喻、象征、典故、音乐性;如属叙事文学(narrative literature),则不重视故事的奇情曲折,而讲究叙述手法,包括意识流等等。在内容方面,则高雅文学可能刻意表现存在主义、心理分析学、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思想。因此,高雅文学在理解上对读者有较高的要求,阅读时需要具备一些专业知识。有论者指出:“教育越普遍,文学专业的知识分子在整体知识分子中所占的比例就愈少,非文学专业的知识分子不一定对‘雅正文学’有兴趣,在阅读倾向上,他们大概是偏向‘通俗文学’的。”*金荣华:《通俗文学与雅正文学的本质和趋势》,《通俗文学与雅正文学:第二届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9页。正因为要理解、欣赏雅正文学应具备相当的专业知识。能够理解、欣赏雅正文学的读者,在今天来说,至少要具备优质大学文学系优秀毕业生的专业水平。具备这样专业水平的读者,大概可“换算”为前文李渔说的“读书人”。
文学批评是一门力求科学化的艺术。在不少批评家眼中,文学的雅与俗可分也不可分。作品有一诞生就属于雅正的,也有由通俗转化成雅正的。*有颇多学者曾指出有通俗变成雅正的现象,如周庆华即谓:“在中国,雅俗文学观念的对比,历来并不是绝对分明,而是时有变动。”参见《通俗文学与雅正文学:第二届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401页。又吴同瑞也说:“时代推移,‘今’逐渐成为‘古’,语言文字有了发展变化,历史积淀越来越多,于是‘俗’的才逐渐变成‘雅’的,其间的畛域原是很难划分的”;“雅与俗既是相互区别的,又是相互联系的,两者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参见吴同瑞等编《中国俗文学概论》,第2、4页。文学雅俗之辨涉及复杂的问题,连雅俗这等名目也很难说没有争论。事实上除了“高雅、通俗”、“雅正、通俗”之外,我们还有不少相近的用语,如“严肃、流行”、“精致、通俗”、“精英、普及”、“高级、通俗”(high culture,popular culture)以至“小众、大众”等等。“高雅、通俗”或“雅正、通俗”之称在学术上并没有绝对“雅正”的地位;“高雅、通俗”或“雅正、通俗”之称,其实是学术界某种约定俗成的方便而己。不过“通俗文学与雅正文学全国学术研讨会”在中兴大学己办到了第九届,我们应该乐于让“雅正、通俗”之名长长久久地沿用下去吧。
七、结语
《文心雕龙·论说》指出“论”这种文体在“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一理”就是一个道理、一个论点。本文到了这里,也应是概括前文作个结论的时候。
杜甫《秋兴》八首、余光中《唐马》、米尔顿《失乐园》、艾略特《荒原》一类作品,文化内涵丰富,艺术技巧高超,有刘勰说的“熔式经诰”的“典雅”色彩,有相当的深奥性,无疑是天生的、本色的高雅文学,愈流传愈高雅,若成为经典则更是典雅。《奥德赛》、《西游记》一类作品,面世时因为“辞浅会俗”、令“爱奇”的受众“悦笑”,而可称为通俗文学。这类作品流传久远,雅士学者肯定其价值,并解说、注释、导读之,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其文学地位日益提高,以至成为文学经典,这类通俗文学于是转化成高雅文学。《文心雕龙》对“雅”和“俗”的解释,对今天我们辨析雅文学和俗文学颇有参考价值;虽然,刘勰对雅和俗的分辨,尚欠精细;对“俗”向“雅”的转化,也缺乏论述。不过,《文心雕龙》的“辞浅会俗”、“俗皆爱奇”之说,简直是形容通俗文学的八字真言;一千五百年前之论,历久弥新。
(责任编辑:王学振)
The Concept of Refinement and Popularity inIntentandOrnamentinLiteratureand a Distinction between Refined and Popular Literature
HUANG Wei-lia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hio State University, Columbus City, USA)
Abstract:As stated in Intent and Ornament in Literature, there are eight literary styles, the first of them being known as elegance which often occurs. Although there are neither items like “refined literature” and “popular literature” nor any contrastive analysis of “elegance” and “popularity” in Intent and Ornament in Literature, some relevant ideas quoted from the book are of much reference value for a distinction between refined literature and popular literature. Generally speaking, popular literature is characterized by simple language, “unusual” passions and entertainment, and its readers are the general public; while refined literature is marked by abstruse language and less entertainment, and its readers often embrace fine cultural attainment, esp. on the part of literary scholars. Love songs from “Airs from the States” of The Book of Odes, numerous poems and Ci poems of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epics by Homer, and dramas by Shakespeare are referred to as popular literature at the time of their publication and popularity; whereas Qu Yuan’s Li Sao, Du Fu’s Eight Poems of Qiuxing, T.S. Eliot’s The Waste Land, and Joyce’s Ulysses have been known as refined literature since their publication. Popular literature can turn into refined literature once it can be time-honored and be subject to annotation, appreciation and study by scholars. This paper aims to expound on the distinction of refined and popular literature and highlight the enduring theoretical value of the concept of elegance and popularity in Intent and Ornament in Literature by quoting modern scholars’ views on refined and popular literature and by referring to numerous literary works at home and abroad.
Key words:Intent and Ornament in Literature; refined literature; popular literature
收稿日期:2016-02-28
作者简介:黄维樑(1947-),男,香港人,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原)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文学及比较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6)-05-007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