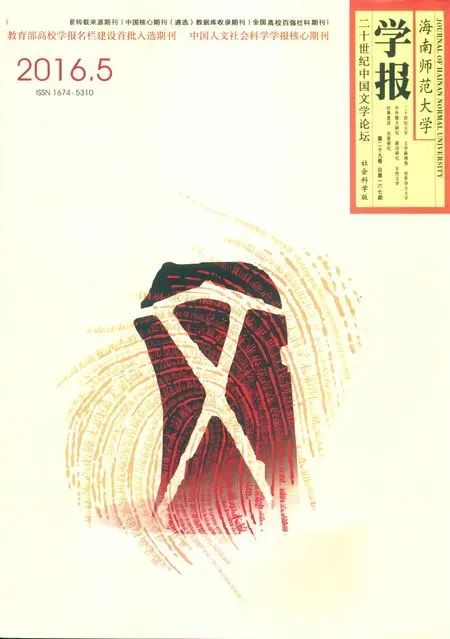时代刻痕与人生履迹的别样叙事
——评《陈骏涛口述历史》
2016-03-16宋依洋
宋依洋,王 科
(1.辽宁师范大学 海华学院, 辽宁 沈阳 110167;2.渤海大学 文学院, 辽宁 锦州 121013)
时代刻痕与人生履迹的别样叙事
——评《陈骏涛口述历史》
宋依洋1,王科2
(1.辽宁师范大学 海华学院, 辽宁 沈阳 110167;2.渤海大学 文学院, 辽宁 锦州 121013)
摘要:由陈骏涛口述、陈墨采编的《陈骏涛口述历史》是陈骏涛先生人生历程的纪实,生命体验的回望。在娓娓叙谈中,口述史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剧烈变革和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特别是勾画了新时期文学的风云变幻,不啻是一部别样的新时期文学概观叙事和知识分子的心灵秘史。
关键词:陈骏涛;陈墨;口述历史;时代刻痕;人生履迹;别样叙事
当下,口述历史已经不再是大名人的“专利”,它似乎已经开始走下“神坛”,步入了寻常百姓家,各色各样人物的口述史,将集纳成宝贵的口述史料库,成为社会历史不可或缺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日前,口述史专家陈墨先生采写的著名文学评论家陈骏涛的《陈骏涛口述历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应该说就是其中一部。这是陈骏涛先生人生历程的纪实,也是他生命体验的回望。它可能没有政界名人述说的事件让你身心震撼,也没有文坛巨擘揭秘的史实使你心灵彻悟,然而,它所进行的人生回顾和精神追寻同样让你怦然心动,它所进行的历史反思和人生自审同样使你深受启迪。更何况,在如述家常的叙述中,它所关涉的中国社会剧烈变革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它所呈现的中国社会的历史影像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嬗变图景,彰显着家国情怀,充盈着人性温馨,在一定程度上贴近、弥补了历史的真实。从这个角度观照和解读,你不能不认为,这是一部别样的新时期文学概观叙事,或是一部能够激引我们共鸣的知识分子心灵秘史。
这部口述史是新时期文学参与者的朴素叙事,反映了中国当代文学行进的艰辛历程。这位当代文学在场的著名评论家、活跃在当代文坛上的“新时期文学吹鼓手”,在漫谈式、絮语式的忆旧中,讲述了新时期文学波峰浪谷的发展历程,披露了一些翔实的、丰富的幕后细节,为文坛提供了一些颇为具象的、值得珍惜的史料,从而皴染出新时期文学某一时段、某一节点的历史风云,为那个文学时代留下了值得忆念的刻痕。弹指一挥间,几十年的光阴过去了,波涛澎湃的文学运动瞬时间成为凝固在古潜山中的历史。最宝贵的青春远去了,英气勃发的青年学者眨眼间变成了华发苍颜的八秩老人。面对白云苍狗、春风秋月的沧桑变幻,解析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人生悖论,人们应该怎样检视自己的一生,如何盘点过往的岁月?作为本书的主人公,陈骏涛先生检视、盘点的,主要是聚焦在他为之献身的当代文学活动上,凝定在他所参与的当代文学流变中——这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使然。那些年间,他和同道者一起,为新时期文学正名,为青年作家和青年评论家呐喊,他寻觅新的研究路径,探索新的研究方法,他参与文学社团活动,助力女性文学发展,“始终不曾懈怠过”*陈骏涛、陈墨:《陈骏涛口述历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3页。。奋斗的成果,曾经使他欣喜、欢乐,拼搏的挫折,曾经让他沉思、苦闷。他对文学事业的坚贞,使他“从一而终”,无愧无悔,他对缪斯女神的钟爱,使他不离不弃、日夜辛劳。对往事的追忆和思索,复原着当年的潮涨潮落;引用的日记和笔记,再现了昔日的云起云飞。这些看似片片断断的口述,实则折射了新时期文坛的风雨历程;这些朴素无华的叙事,不啻是这位新时期文学点赞者的可贵证言。
这部口述史介绍了某些现象生成的始末,为重构当代文学历史积累了史料。马克思曾经说过,对历史而言,某些事件离开我们越远,它的意义就越能看得清楚。也就是说,历史往往是在经过岁月的积储和漫长的沉淀之后,才逐渐被人们所认知、厘清乃至定格的。伴随中国社会大变迁诞生的新时期文学,从酝酿、萌生到崛起、繁荣,有着怎样深刻的内在动因和自身规律?作为文学的主体、那些在浪头搏击的弄潮儿,曾经有过怎样的运筹和“壮举”?对于这些渐行渐远的人物和史实,尽管每部当代文学史都力图秉笔直书,但由于史料不足,角度殊异,难免众说纷纭,更不要说是有意无意的拉黑和屏蔽了。大概正因为如此,重写当代文学史的呼声一直不绝于耳。也正是由于同样的原因,有关当代文学的口述历史也就不容我们忽视了——这些口述历史虽然只是参与者个人文学生涯中不能遗忘、未曾失忆的些许小事,但说不定若干年后,它可能就会成为重构文学史的珍贵资料。身处于当代文学研究的高端,游走在当代文学活动的纵深,陈先生参与了许多文学活动,亲历了许多文学论争。因之,一种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促使他穿越悠远的时空隧道,在新世纪的节点上,以历史文化的视角,在总结自己人生经历时,叙述和反思了这段难忘的文学征程。
陈先生的口述不是宏观的综述,而是围绕自己工作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讲述一些少为人知或不为人知的事实,从而为新时期文学的历史拾遗补缺。在全书52节的口述中,有关新时期文学的叙事占了将近一半。这其中,对《文学评论》复刊、批判“四人帮”文艺黑线、召开各类专题讨论会等的叙事,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考察当代文学的新场域、新视角、新资料。比如,《文学评论》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艰难复刊的,它在复刊之初,为什么会降下身段,发表了很多拨乱反正的文艺时评?陈先生揭示了其中的一些深层因缘。他告诉我们,《文学评论》酝酿复刊,有两个深远的背景。一是邓小平复出后整顿意识形态领域所做出的战略决策,二是文艺战线、知识分子思想觉醒的巨大促动。1975年7月,邓小平委派胡耀邦到中国科学院主持工作,胡耀邦经过调研很快向中央呈递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得到邓小平和国务院的支持、认可。这样,《文学评论》也才等到了复刊的契机。这之中,作为复刊筹备组成员的陈骏涛先生,曾受命赴南方四省八市进行调研。基层群众对“四人帮”文艺帮规的愤恨和憎恶,对改变文艺现状的渴望和呼声,使他感受到了文艺战线拨乱反正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然而,由于“四人帮”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干扰破坏,《文学评论》的复刊计划不但胎死腹中,还被当作右倾翻案的典型事例遭至批判。陈老师介绍的这些史实,真令今天的读者感慨万千: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新时期文学的起步何其艰难!1977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文学的春天降临人间,《文学评论》才得以“凤凰涅槃”。复刊之后,刊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以拨乱反正为主,推出了大量的政治性文艺评论,对“四人帮”之流的种种谬论进行犀利的批驳,为“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批判的作家作品“落实政策”。虽然当时和现在都有人认为,这有悖于这个权威文学理论刊物的宗旨和定位,但陈先生认为:历史证明,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文学评论》在批判“四人帮”的斗争中冲锋在前,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既是当时扫清障碍、开辟道路所必须,也是建立新时期文学秩序之必需。*陈骏涛、陈墨:《陈骏涛口述历史》,第199页。陈先生指出,这一切,都是来自当时负责社科院工作的胡乔木的亲自部署。胡乔木的讲话,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了当时《文学评论》办刊的方针,甚至是约稿组稿的指南。期间,陈先生或亲自执笔或与同事合作,写了多篇拨乱反正、重评现代文学经典作品和推介当下优秀作品的文章,有的还被新华社发了通稿,在学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不过,这些文章当时多是用颇具战斗性、团队性的化名发表的。此外,陈老先生还介绍了《人民文学》座谈会、第四次文代会暨第三次作代会的一些情况,让读者了解了一些文学史上看不到的历史细节,好些幕后的动人场面和深刻话语发人深思,至今还让我们对那个思潮澎湃的年代感念不已。
陈先生的口述史还评析了某些历史节点事件,为考察当代文学转型提供了某种参照。在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中,哪些事件可以称为转型拐点,应该为历史永远铭记?对此,学界大多已形成共识,并对其历史意义有了公允的评价。然而,对这些事件的精准诠释和深度阐发,还有不少工作要做。何况,还有一些事件的原始风貌和发展过程已被历史湮没,有待我们进一步开掘和解读。应该说,陈骏涛先生的口述就做了这样的工作。他在许多专家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某些历史事件的肇始、流程做了总结梳理,对某些历史嬗变的价值、意义做了分析论断,从而为我们深入考察当代文学的时代转型树立了一种参照系。
当年,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成为新时期文学主潮之后,如何看待这些文学思潮和现象,如何评价这些令人眼前一亮的文学作品,曾成为文学理论家们必须迎接的挑战。那时,陈先生和许多学者一样,投入到对“方法论”变革的潮流之中,但他又认为,方法的变革必须以观念的变革为先导。于是,他与一些敏锐的理论家一起,以新的观念统领新的思维,热情地投入到“方法论”的探索和研究之中。厦门会议、海口会议,以及与之有关联的扬州会议、广州会议、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讨论会、中国当代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一场场会议相继召开,一个个口号接连提出,令人茅塞顿开、耳目一新。其中,有的会议是陈先生积极参与、组织的,并在会议上作了发言。在陈先生看来,这些会议“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上,应该是可以留下一笔的”*陈骏涛、陈墨:《陈骏涛口述历史》,第250页。。对一些会议中的重要观点和发言,时隔多年,陈先生还能如数家珍。无疑,这些口述史实,已经并将继续成为人们深入思索新时期文学变革的参考资料。
在对新时期文学林林总总的叙述中,陈先生还评述了当年的一些作家作品,如徐怀中的《西线轶事》和《阮氏丁香》,王蒙的中短篇小说和理论批评,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张承志的《黑骏马》,路遥的《人生》,以及陆文夫、陈建功等人的作品。这位当年活跃于文坛的“闽派评论家”,以他着力倡导的新的美学—历史批评观,曾对这些作品进行过深入的诠释和评析,并产生一定影响。用陈先生的总结来说,其批评之所以有些影响,是因为源于以下两点:一是更新了文学观念——即破除了文学只能为政治服务的狭隘观念和人物塑造的二元对立模式,二是皈依了文学本体——即践行了创作方法的多样化特别是多维度的艺术创新。陈先生的批评观念,当时和现在,都探索了一种全息解读作家作品的可行路向。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为了提升新时期文学的认知度,“为历史留下当代人创造的文学财富”,在纯文学处于低谷时期,陈先生还完成了两个可以称之为浩大的文学工程:主编了“跨世纪文丛”和“红辣椒女性文丛”。虽然如今陈先生在谈起这件事情时,是那样的云淡风轻,未曾详叙个中的甘苦,但是,我们从中能够想见,倘若没有一种坚定的文学精神和执着的艺术理念,没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实干加苦干,就不会有这些文学选集的出现。这是值得当代文学史、出版史和文学研究史记上一笔的。
陈先生的口述史在精神追寻中也进行了灵魂自审,他对自己人生历程的反思甚至忏悔,在某种程度上,也能拨动人们的心弦。这位承传了中华民族优秀道德情操的当代知识分子,在总结、梳理自己的人生历程中,不仅表现出那种忧患意识和爱国情结,那种对理想人生和美好社会的向往,以及对同志、对亲人的真诚和挚爱,同时也对自己的人生过程进行了严肃的自审和反思,对人宽厚,对己严酷,显示出一代知识分子丰盈的精神世界。
对于即将进入“耄耋”之龄的陈骏涛先生来说,要和自己的灵魂博弈,甚至审判,显然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但他就像一位严正的法官,不,就像一位童真的少年,向众人敞开了五脏六腑,对自己进行了严苛的灵魂审判。它不同于时下某些回忆录或者口述史,专讲当年过五关斩六将,不说曾经失荆州走麦城,贪功诿过,往自家脸上贴金,从而遮蔽了历史的真容,而是遵循自己人生的一贯原则,严格严肃地抖落自己灵魂中的“小”字,真诚真切地表述自己的检讨,宽和宽容地对待历史的误会,洋洋数十万字的口述,没有一点强调客观和责难他人的语言。对“文革”的反思和回忆,就是陈先生最勇敢的忏悔。那场全民癫狂的历史动乱,留给了我们太多的教训,人性的迷失、兽性的发酵、正义的沦亡、伦理的错位,真是不堪回首。但时至今日,能够深刻反省,与历史错误划清界线者,却鲜有其人!而陈先生深知,一个不知道忏悔的民族,不能涅槃,一个不懂得忏悔的人,难以前行。在口述中,他袒露胸怀,大胆解剖自己,将自己那时年轻懵懂、天真烂漫的日记公之于众,晒在太阳之下:出于对出身不好的忧惧,他思想斗争分外激烈,在站队上颇费思索;他先是随大流当“保皇派”,后来跟着造反风潮变为造反派,在文学研究所第一个贴出了造反大字报,并成为造反组织的一个骨干成员;不仅如此,他还参与了许多对“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曾两次到唐弢先生家中,主持了对病中的唐弢的批判会……知耻近勇,这是光明磊落的人格彰显,是中国知识分子可贵的道德救赎。看到陈先生的这些叙述,我们不但没有对他当年的某些行为表示不解,相反倒是生发出一种敬意。假如我们全民族都能够这样坦诚地对那场人类浩劫进行真正的反省,永远以那场荒谬的“文革”作为镜鉴,那么,它必将加速我们民族精神的升华和中国梦的实现。
此外,作为著名文学评论家,不管学界同人如何称许,陈先生却一直对自己的学术水平定位很低。应该说,这绝不是矫情,而是真正的谦虚。他反复说自己“学养不足,知识功底不深”,“我的评论文章,除了少数以外,多数都是一般化的,或者说浅层次的。满足于追踪式的评论,缺少挖一口深井的功夫,这是我的最大弱点”。*陈骏涛、陈墨:《陈骏涛口述历史》,第477页。相反,对他的前辈、导师、同人,却总是师恩难忘,钦敬一生,热情赞扬,从无半句龃龉之语。读到这些情真意切的叙述,着实令人感动。
在家庭生活方面,陈先生对于自己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作为,也进行了严苛的自审。他对父母的养育之恩刻骨铭心,但由于各种原因,父母离世,他却没有能够归乡奔丧,对此,他痛悔莫及,责备自己是“不孝之子”。对为家庭贡献了一生的妻子,他也十分钦敬,为自己不会关心人的性格和执着于事业的“自私”,深感愧疚。对自己的两个爱女,他虽然疼爱有加,但却关心辅导甚少,直到现在,他还痛责自己:“我对孩子确实没有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肺腑之言,倾吐了无尽的感伤和悲凉!
读这部口述史,我们还不能不说到陈先生的大弟子陈墨先生,他秉承“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古训,不仅力主为恩师做口述历史,并以他多年的采编经历和积累的经验,在“采编人杂记”中,对口述者唠家常似的直白絮语点铁成金,把看似漫不经心的零碎叙事整合升华,在梳理概括中作出诠释评判。这不仅使平实、坦诚的心灵独白锦上添花,更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这部看似唠家常的人生口述史的史学分量和文学价值。
(责任编辑:毕光明)
Comments onChenJuntao’sOralHistory
SONG Yi-yang1, WANG Ke2
(1. Haihua College,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67, China;2. College of Literature, Bohai University, Jinzhou 121013, China)
Abstract:Chen Juntao’s Oral History dictated by Chen Juntao and edited by Chen Mo is a documentary of Chen Juntao’s life course and a recollection of his life experience. Through its tireless narration, the oral history has mirrored the dramatic change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spiritual journey of intellectuals, and has particularly outlined the vicissitude in the literature of the new era. The oral history is not less than a unique overview narrative of literature of the new era and a secret history of the soul of intellectuals.
Key words:Chen Juntao; Chen Mo; oral history; the trace of the era; the mark of life; unique narrative
收稿日期:2015-11-17
作者简介:宋依洋(1986- ),女,辽宁沈阳人,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院教师,主要从事中外文学研究。王科(1945-),男,辽宁北镇人,渤海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6)-05-006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