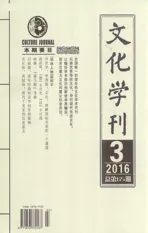“德”不可失“法”不可违
——关于当前“失德”与违法社会现象的文化探析
2016-03-16曲彦斌
曲彦斌
(辽宁社会科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1)
【观察与评论】
“德”不可失“法”不可违
——关于当前“失德”与违法社会现象的文化探析
曲彦斌
(辽宁社会科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1)
基于民俗文化因素:要“辨风正俗”;基于法律文化因素:应强化“法治”;总和民俗文化与法制文化:“德”不可失,“法”不可违。
失德与违法;德治与法治
汉语的“失德”之说,始见于《诗·小雅·伐木》,大意是指失误、过错或者罪过。时下所谓“失德”,则是指有悖社会的道德规范,亦即道德失范;有悖道德规范的言行发展到违反法律规范之度,也就触犯了法律——违法了。毋庸讳言,道德失范业已成为时下备受公众关注的一大社会公害。早在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就已指出:“在社会精神生活方面存在不少问题,有的还相当严重。一些领域道德失范,成为社会公害;文化事业受到消极因素的严重冲击,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东西屡禁不止”。甚至,近年来更逐渐发展为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这一点,也正应了古代先哲《管子》说的,“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法者,民之父母也”。也就是说,“德”不可失,“法”不可违。对民俗文化缺乏有效的辨风正俗、移风易俗,现实法制文化建设的薄弱,是产生社会道德风尚严重失范的两个至为关键的文化因素。
一、关于民俗文化因素:要“辨风正俗”
就民俗学视点而言,社会风尚缺乏必要的辨风正俗和移风易俗规范,不能不说是当前社会道德失范与违法现象趋于泛滥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因素。健康向上的社会道德风尚,是预防社会违法犯罪的最基本的重要防线。社会道德风尚,则往往主要体现为出自一时一地社会风尚的积淀和传承扩布的社会风俗,亦即民俗。
从一定意义而言,文化就是传统。民俗是一种重要的传统,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属于社会文化范畴,因而又谓民俗文化。由于作为文化的民俗体现着一时一地的社会道德风尚和文化价值取向,所以它还具有规范社会生活秩序的民间习惯法性质和功能。作为文化的民俗,是制衡、调控社会生活秩序的一种不成文法的非主流制度规范,而且具有较强的守成性(稳定性)和传承性。宋代的王安石曾经上书宋神宗,提出要“变风俗,立法度”的政见,显然注意到了民俗的习惯法功能,民俗与法的密切关联。因而,在《风俗》这篇专论中他又强调,要使人民生活安定、富裕的关键是端正风俗,“风俗之变,迁染民志,关之盛衰,不可不慎”。
正如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所说,在性质上,民俗“更近于一种道德规范,但它对人们生活和心理的普及及深入比起一般道德更进一步。”(《民俗文化的凝聚力》)在辨风正俗过程中激活、弘扬民俗文化中的某些优秀传统,会有助于有效地淡化时俗中的不良因子,有助于扬弃陋俗、恶俗,维护法律制度的尊严和实施,是健康向上的社会道德风尚成为预防社会违法犯罪的最基本的重要防线。削弱或突破了社会道德风尚规范的这道防线,陋俗、恶俗以及与之相伴的犯罪现象就将泛滥成患,就将进而突破法制的防线。
社会的发展进步必然要冲破包括民俗文化在内的旧制度、旧思想的束缚,通过有选择的继承、吸收、改造和创新、整合,构建具有现代文明特质的、适合调控现代社会新秩序的新制度。个中,当然包括了经过移风易俗之后的新风俗、新道德风尚。然而,移风易俗的前提,首要在于辨风正俗。
辨风正俗是同社会文明进程相伴随的一种社会变革过程,是保持社会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社会在积极变革中发展进步,辨风正俗是与之相伴的变革运动。这也是鲁迅早在1930年在《习惯与改革》中分析过的,“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形容,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击碎,或者只有表面上浮游一些时”,到头来则会有如“沙上建塔,顷刻倒坏”。鲁迅这一见解,对于时下讨论“辨风正俗”问题,可谓一箭中的、切中紧要,道出了它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的关键所在。社会秩序的稳定,是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的必要条件;只有在国家法律制度的保障下辨风正俗分清良莠是非,才能保持全社会有一个稳定、良好的秩序。否则,听凭失德、违法犯罪现象泛滥,只能造成社会生活的无序化。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巨大变革,对于以旧经济制度为基础生长起来的其他相关制度和精神文化,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以期通过一系列改革、调控和整合,建立与现代文明相适应的物质生活、文化生活乃至政治生活秩序。其中,这些变革和碰撞给社会风俗习惯、社会风尚带来的冲击尤其激烈、显著,甚至改革的阵痛也难免为之带来暂时的混乱或动荡,直接关系着社会生活秩序的调整、调控和稳定。中外社会发展史和改革史均一再证明,社会风尚、风俗习惯是社会改革阵痛最主要也是最直接的晴雨表、显示器。东汉《风俗通义》中提出的“为政之要,辨风正俗最其上也”,意思是说,治理国政的首要关键,在于辨察风尚、匡正民俗。《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了“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二十字基本规范。事实上,实施这一规范本身,正是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公民道德建设的辨风正俗的“为政之要”。
换言之,切实有效地“辨风正俗”是实施“德治”与“法治”方略的必然环节。否则,就难以依法而治和以德而治。因而,无论“法治”还是“德治”,都务必进行“辨风正俗”。所以,通过透析社会风尚、风俗习惯及其发展趋向,并通过辨风正俗、移风易俗把握导向,及时加以调控,是确保必要的社会稳定从而使改革健康有序进行到底并获取成功的重要保证。社会风俗、道德风尚的规范,是精神文明建的核心,适时地在全社会开展以广大城乡居民为对象的,以“辨风正俗”为主题的全民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教育活动,将其作为进入新世纪前的进一步深化精神文明建设的专题教育活动,势将对于弘扬民族正气、净化社会风尚、振奋精神、凝聚民心、预防社会犯罪和稳定社会,发挥积极有效的推动作用。
二、关于法律文化因素:应强化“法治”
中国法学界对于“法律文化”的关注和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这种关注,主要在于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改革、文化变革的不断深入,法律文化的冲突也愈加激烈和凸现出来。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本土内部和与外部的法律文化冲突,亦将更加突出。社会物质生产与消费方式的变革,是产生法律文化冲突的最根本原因。法律文化的核心,是“法治”问题。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法家也曾主张“法治”。不过,他们讲的是相对儒家的“礼治”而言的“礼法”,认为合乎仁德的法治则为“礼法”,也就是《管子》所说的“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法者,民之父母也”。《韩非子·心度》说的“治民无常,唯以法治”,强调的也是这种“礼法”。不过,秦汉以来开始实行过的这种“法治”的主体是帝王,亦即《韩非子·定法》说的“皆为帝王之具也”;其客体,则是臣民。显然,这与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全社会任何人都必须依法办事的现代法治文明截然不同。而且,中国古代法律多是以刑法罚则规定为主的强行法,往往压抑人性、背离人性甚至是践踏人性。因而,很难形成使人们自觉依法办事的守法传统,在那样的法律文化氛围中,人们处于无奈的被动守法状态。现代法律是个人合法权益与社会生活秩序的基本制度保障。现代法律文化关注、保护个人的合法利益与权利,强调无论任何人,时时事事都必须依照法律规则行事。
社会变革与转型进程中古今中外法治理念、法律文化传统的冲突,势必形成一种暂时的、过渡性的,或是某一局部的无序过程。这个过程之中,各种社会犯罪既是难以避免的,也是法律制度必须加以规范的内容。当然,这也是个健全、完善现代法律制度,建立现代法律文化的发展进步过程。
现代法律文化要求全社会的成员认同法律,自觉地把自己视为法律的主体,不仅需要依法行事,还要依法监督包括政府和其他执法者的执法、守法行为;既要适应法律规范,还应身体力行地积极推进法律法规的完善与进步。
时下在民间,尤其是一些偏远乡村,依法进行了结婚登记的婚姻,在许多人的的思想意识中还不是“生效”的婚姻,只有履行过民间风俗习惯约定俗成的那些程序的婚姻才会获得认可。在此非正常法律文化情形之下,那里的早婚、包办婚姻、买卖婚姻、近亲结婚、订婚以及收受彩礼,甚至是童养媳、换亲、重婚、转亲等旧式婚嫁习俗的流行仍然很普遍。其中,订婚以及收受彩礼等,对于当事者双方以及双方家庭,都具有为大家所共同认可的约束力。这些违法行为大面积流行的事实本身,则是对现行有关法律的不认同。相反,在涉及村民的一些直接的、切身的利益问题,诸如承包责任制、减轻农民负担等农村经济改革政策的操作规则和稳定性方面,却渴盼法律法规的保障和切实公正执行。至于一些地方出现的执法腐败,甚至向村民封锁有关法规、政策信息的做法,更加激发了人们对学习法律知识和利用法律进行自我保护的渴求。这种为满足自身现实利益需求而“无奈违法”同时又渴望法律保护的状况,几乎是各种弱势群体所共同的社会心理,也是面对现代法律文化的共同尴尬处境。毋庸讳言,由此引发的各种社会犯罪屡见不鲜。
要求社会成员遵法守法,首先要大家知法;要大家知法,不能只是颁布法律了事,还要通过各种必要的方式和渠道进行广泛宣传,尽最大限度地使之家喻户晓。同时也应注意到的是,法律文化传播的准确与否,直接关系着全社会大多数成员法律意识和具体法律观念的建立、积累,关系到对相关法律的认同与判断。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法律宣传和法律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偏颇和谬误,同样不可避免地会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例如有的影视作品名曰宣传法制,却在内容或细节上出现许多法律谬误或曲解,势必对法律文化带来消极误导甚至破坏等负作用。再如,不加批判地报道、揭露以权弄法的社会新闻案例,就会无形中宣传了“权大于法”;过分地渲染所谓“现代包青天”事例,仍然是在宣传“权大于法”和“人治”的法律理念。
法律是规范社会成员行为和社会生活秩序的制度,其规范——依法行事和执法,需要靠具体的人来实行。社会法律文化的质量和普及的程度,直接关系着遵纪守法的水平和执行法律的程度。因此要最大限度地帮助全社会成员了解自己在法律保护下的权利和义务,尤其是全面了解同自己生活与工作相关的法律知识,提高人们依法行事和监督执法的的自觉性,依法维护自己和社会的正当权益,坚定地维护法律的尊严,勇于同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斗争。这一点,是现代法律文化的核心,是减少社会犯罪的基本要素,也是现代社会文明的最重要标志之一。
三、民俗文化与法制文化:“德”不可失,“法”不可违
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法律还得靠权力来支持,还得靠人来执行,法治其实是‘人依法而治’,并非没有人的因素”。文化可谓传统,法治既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社会文化。任何国家的法律,几乎都是建立在民间习惯法的基础之上的,是民俗、道德规范的制度性升华。近代中国从清末新政开始的多次民事习惯调查运动的意义,就在于注意到了风俗习惯这种文化对社会生活秩序的规范和调控功能,试图通过对社会风俗习惯的关注和了解,制定更能切合社会实际的法律制度。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过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主要还是强调民俗作为习惯法和道德制度对社会生活秩序的规范作用。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还谈到,“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的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
习惯法又称民俗法,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固有的民俗文化和法律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是现代法律文化的渊源。按照这种固有的传统民事习惯,诸如“私了”“民不举官不究”“法不责众”之类的行为和现象,尽管在某种范畴里有其合理性,则难免有纵容乃至助长违法犯罪活动而又直接违反法律的负面作用,干扰着法治社会的正常生活秩序。在中国这样具有悠久“礼治”传统的国度,“礼俗”是我国古往今来最主要的习惯法。即如《礼记·曲礼上》所言,“礼从宜,使从俗”,“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也……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习俗,非礼不备;纷争辩讼,非礼不决”云云。因而,它特别强调“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意在强调“礼义”在不同地方的规范功能。汉代的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谈到他对“礼”与“法”的辩证性见解,代表了一种传统的主流性认识。他认为,“夫礼,禁于未然之前;法,施于已然之后。法治所为用者易见,而礼所为禁者难知”。相对旧有的习惯法传统而言,现代法律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建立健全切合国情的现代法律制度并加以强化,是治理社会“失德”(道德失范)现象的更高层面的制度保证。
民俗有优良劣陋种种区别,需要通过辨风正俗、择优汰劣和移风易俗来加以规范。民俗文化处于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中。社会的进步并非要要求一概消灭传统民俗。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包括继承文明健康于社会有益的优良民俗的同时扬弃劣俗陋俗,铲除危害社会的恶俗。娼、赌、毒等丑恶现象和迷信活动,均为由来已久屡除未尽的劣俗陋俗,一当其行为与后果同法律制度相抵触,便突破了道德规范的界限而需要运用法律手段予以禁止、取缔和惩处。对于那些扰乱社会道德观念和社会生活秩序,危害了社会和人民利益,触犯了法律的不法分子,理当依法惩处。至于一般的从众者,也应在辨风正俗中认清其本质并接受教训。不过,无论是否需要对其进行法律干预,都需要通过辨风正俗、进行移风易俗和社会道德风尚的规范,而且是个绝非一朝一夕立马可决、一劳永逸的艰苦过程。
过度关切物质生活而忽略了社会道德风尚要素的重要性,那么,社会发展的天平就会失衡,如此其畸轻畸重的结果,便难免产生颓废与秩序的混滥乃至犯罪。例如时下人们所关注的“诚信”,既是社会道德风尚规范问题,同时也是个法律制度的规范问题。一当突破了“诚信”的社会道德风尚规范的维度,便往往导致犯罪的边缘。因为,“诚信”不单单是民俗所制约的道德规范,更重要的是建立在法制规范的平等与公正基础之上的行为与秩序规范。
不过,法律面前的平等也不是绝对化的。例如,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法律实践不仅要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还要注意“民族政策”照顾“民族特点”。所谓“民族政策”,是在宪法规定允许的限度内的法律实践原则。所谓“民族特点”或说是“民族特殊性”,则主要是基于该民族特定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民族风俗习惯,包括宗教信仰和某些习惯法。法律文化对民俗文化的这种具体的兼容,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具体需要,符合国家的法律精神和法律原则。
无论属于政治文明的法律文化还是属于精神文明的民俗文化,各有其独特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功能。法治以法律的权威性和强制性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法律文化要求社会成员自觉地接受法律的规范、维护法律的权威,是积极健康的社会道德风尚的法律保障。民俗文化以社会风尚约定俗成的道德习惯力量制约、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但是,要“辨风正俗”。积极健康的民俗文化受到法律的支持和保护,超出法律原则的陋俗、恶俗则属无视法律、违反法律甚至是犯罪的行为,理应受到法律的规范和制裁。法律文化不能兼容那些违反法律原则的陋俗、恶俗。
总之,对于全体社会成员来说,“德”不可失,“法”不可违;对于执法和执政者而言,依法治国的“德政”是“法治”与“德治”的和谐统一,是政治文明的集中体现,社会进步需要“德政”,人民需要“德政”,现代文明也需要“德政”,“德政”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责任编辑:董丽娟】
C91
A
1673-7725(2016)03-0026-05
2015-11-25
曲彦斌(1950-),男,山东蓬莱人,研究员,主要从事社会生活史和民俗语言学研究。